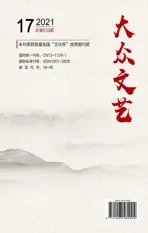离婚的权利:从《诉讼》到《摇摇晃晃的人间》
2017-07-13兰州大学730000
阎 瑾 (兰州大学 730000)
离婚的权利:从《诉讼》到《摇摇晃晃的人间》
阎 瑾 (兰州大学 730000)
《诉讼》与《摇摇晃晃的人间》都表现了选择离婚的女性,本文以这两部影片为例来讨论女性所要面对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压力,并结合了劳拉•穆尔维和波伏娃的论点,由此来看身处于现代社会中的女性在自我意识与自我审视上的觉醒。
《诉讼》;《摇摇晃晃的人间》;女性主义
2014年上映的以色列电影《诉讼》及2016年上映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都将目光放在了两位选择离婚的女性身上,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性格都迥然不同,但她们所追求的权利以及所面对的挑战是有其共性的。本文将通过外界因素对女性的影响以及女性对于自身权利的思考这两方面来进行讨论现代女性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的心理状态。
一、女性离婚的外界阻力
《诉讼》与《摇摇晃晃的人间》中的两位女主人公:薇薇安与余秀华都要求离婚,影片表现了她们所面临的一系列阻力,这两桩离婚案所历经的时间都十分漫长,而女性在选择离婚之前也同样经历了长时间的煎熬,制作者考虑到电影时长的限制,因此仅仅表现了她们生活的部分。她们代表的是整个女性群体,通过她们的斗争我们得以一窥女性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及她们的权利诉求。
首先来看《诉讼》中的薇薇安,她所处的社会环境要比余秀华更复杂,这是因为宗教在这桩离婚案中的存在,以及法律对于男方明显的偏袒,薇薇安从一开始就处于一个乞求者的位置,她若想要获得自由,就不得不通过宗教法庭来得到离婚权利。然而她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公正的法律平台:在经书之中明确提到了倘若男方提出离婚,不需要提出相关证据法院即可允许离婚,而如果是女方想要离婚则需要提出相关证据。由于双方都无法提出符合标准的证据,每次的争辩总是不了了之,最终形成了拉锯战的情形。片中的法庭从一开始就竭力劝阻薇薇安,这里的法庭是作为一个社会维稳的形象存在的,而非是个体利益的维护者,因此薇薇安的合法要求被法庭多次忽视。整部电影以115分钟来讲述这个离婚案,但在现实时间中,这场荒唐的官司却经历了数年。
除去不合理的法律条例,薇薇安还需要面对丈夫的拒绝离婚,这也是这场离婚案迟迟无法结案的重要原因。薇薇安的丈夫是一位十分虔诚的信教者,受到众人的尊重,可是薇薇安所渴求的并不是一位标榜道德高尚的丈夫,因为这种高尚背后所隐藏的是一种冷暴力:从表面上看,他是一名称职的丈夫,并没有不良嗜好,也不曾有过家暴行为,但实际上他有意的忽视薇薇安的心理诉求,并以道德和法律来控制妻子,这对薇薇安造成的心理创伤并不亚于身体创伤。片中的女邻居指出了这个社会中男女权利的不对等关系:你需要尊重你的丈夫,然后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这就使得处于这一关系中的女性失去自我意识,只能被动接受男性所赋予的。在影片的结尾,薇薇安的丈夫同意了离婚,但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要求:薇薇安在离婚后不能再嫁。这一要求依旧是对薇薇安的一种另类束缚,她以爱情换来了自由,但从本质上来讲,她依旧未曾彻底脱离这个社会强加于她的婚姻。
在《摇摇晃晃的人间》中,制作者并没有拍摄余秀华与丈夫尹世平在法庭的离婚过程,但通过之前的拍摄来看,余秀华所面对的离婚阻力并非是法律,而是传统。片中余秀华因为身体残疾而不得不接受家庭所安排的婚姻,这个入赘招来的丈夫并不像薇薇安的丈夫那般担任强势的角色,可以说在这场婚姻中,他反而是处于劣势的,这种情形在余秀华成为名人后更加明显。他拒绝离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更有为自己发声的因素在其中。片中他重复提到自己这些年在外打工的辛苦就是一种呐喊,余秀华可以通过诗歌来舒缓不平,而尹世平缺乏发声平台和自我意识。
与丈夫尹世平相比,余秀华的母亲才是这桩婚姻的重要阻力之一,这位强势的母亲所代表的是中国传统,在她的传统信仰体系中,女性需要一位丈夫来组建家庭,由此才能获得生命意义。母亲在一个女儿的生命中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一方面她对女儿发出负性信息,另一方面又传递着喜爱之情,在两者的反复作用下,女儿在成长的过程只能担任一个接受者的角色。童年的女儿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并不了解,只能通过母亲来看世界,但随着她对世界的认知进一步深入,她会开始想要脱离母亲的控制,这个过程中的女儿往往是叛逆甚至是过激的。而对余秀华的母亲而言,余秀华的成功是另一层意义上的失败,因为它使得余秀华对自己的价值有了重新的定义,进而颠覆了母亲的传统理念,且使余秀华她自己可能会面临无依无靠的未来。余秀华执着于离婚,这一行为本身也带有对母亲的一种反叛,因为这桩婚姻是母亲在她尚处于心智不成熟时所安排的。在反叛之外,余秀华对于母亲还抱有深深的固恋,这位一直陪伴她的女性才是余秀华真正的保护者,丈夫反而是一种阻挡自己与母亲相守的存在。在选择离婚后,余秀华向母亲发火,因为她感到母亲舍不得这个女婿,这种想法使她感到被母亲排斥的痛苦。
此外,母亲考虑到另一重阻力,那便是社会舆论,尤其考虑到舆论对于女性的严苛,余秀华的选择或许会引起极大的舆论反应,而她们所生存的环境又是较为封闭的,在这种情形下,舆论对人可以产生巨大的伤害。年轻的余秀华不惮于他人的语言暴力,但是对于母亲而言,处于社会环境中的人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考虑他人的看法,这是生存的一部分,也是人无法避免的一部分。而观看电影的观众也在无意识的扮演着判断者这一角色,这其中不乏恶意的和猎奇的目光,余秀华同意拍摄的同时就需要考虑到观众的存在,在之前的一些新闻片中,观众可以感受到余秀华的敌意,这是由于观众的目光有时是一种无声的压迫,和舆论一样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着人物的行动。
在这两部影片中孩子的形象是缺席的,相应的在婚姻中,孩子是一个被动的失语者,但同时也是想要摆脱婚姻的一方无形之中所要承受的道德重担。而对于女性而言,她们所要承受的这种道德重担普遍来讲要超过男性,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对女性的定位,另一方面也是女性自身的心理机制所致。片中的两位女性也在无形之中承担这一压力,不过因为孩子们的独立,作为母亲的她们也可以相对自由的去言说自己的权利。
二、女性自己对权利的认知
两部影片除了表现外界因素对女性离婚的干扰,同时也表现了女性在这一过程中的自我觉醒和自我言说。片中的两位女性并不相同,但她们对于个人权利的认知是一致的,也是坚定不移的。
《摇摇晃晃的人间》中的余秀华已是名人,经济赋予她以自由,《诉讼》是一部情节电影,其中制作者为主人公设置了一个较为自由的经济背景,因此这两桩离婚案所聚焦的并非是经济利益上的纠纷。且这两部影片中的女性都尽到了婚姻的责任,对于女性而言,波伏娃认为“婚姻被以双重名义强加给她:她应该为共同体生孩子……她也有满足一个男人的性需要和料理家庭的职能”1,《诉讼》中的丈夫、邻居以及好友都认为薇薇安尽到了她作为妻子的职责,《摇摇晃晃的人间》中的余秀华也为丈夫育有一子,尽管身有残疾,但依旧能够尽到料理家庭的责任。因此两部影片关于婚姻的探讨就不再围绕谁对谁错,而是讨论个体对于婚姻的满足程度,这就使得女性对自我的表达更加纯粹。
片中的两位女性选择离婚,一方面是对丈夫不满,另一方面是对自己诉求的一种言说。两位女性都一致认为她们的丈夫都不懂浪漫,这在世俗观念上似乎是一个难以立论的缺点,因此社会舆论容易倾向于丈夫一边,却忽视了在婚姻之中女性对于情感的需求。余秀华生活在对爱情、自由的向往之中,而这种向往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之中显得格格不入。她自身也存在矛盾性,一方面追求纯洁的超越性,这是因为丈夫的缺席和母亲的庇佑使得她的“青春期”被延长;另一方面她又有被爱的需要,而她的丈夫不能很好的担任这一角色。这种心理的落差刺激着这个女性进行写作,以求一个发泄的出口。余秀华和《诉讼》中的薇薇安在心理年龄上存在差异,薇薇安是作为一个成熟女性在为自己争取权益,而余秀华时而会表现出和年龄不符的孩童气:她笨拙的打理自己的头发,向母亲发脾气、撒娇,面对喜欢的男性时会表现出少女般的欢喜,这也使得她的抗争格外困难,因为她所面对的是一个非诗意的成人世界。不可忽略的是作为成人的薇薇安也有对于追求爱情的渴望,片中的她在几场法庭戏中穿着时尚,这是因为离婚有望,她重新燃起被爱的希望,但当她为了自由放弃了爱情时,她再次打扮成普通的装束,服装的变化是一个成年女性绝望的控诉。
在劳拉•穆尔维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她分析了引发视觉快感的观影心理机制,而在这两部影片中,男人不再是唯一的看的承担者,女性观众也在现代观众中占据一定数量。因此在形象上不刻意凸显可促成欲望的美感。薇薇安和余秀华的人物形象都不属于劳拉•穆尔维所指出的可满足观众窥淫癖的角色。她们是作为主体的人出现在银幕之上,而非被看的“物”。余秀华在诗中多次谈及到“性”,在影片中,女性对于性的主动姿态拉进了与观众的距离,同时消解了观看的快感,这也是对世俗观念的一次“敲打”:女性有追求性快乐的权利。从生理构造来讲,男性在完成生殖职能的同时就可以获得快感,而女性的“生殖职能与情欲往往会分离”2,这就使得婚姻的保障有时反而是对女性的束缚和压制。在忽略女性生理需求的社会体系中,离婚是女性自身的一种反抗,也是对自我权利的一种争取。
女性为自己发声的方式在两部影片中也是不同的。《诉讼》的导演就是女演员自己,她通过这部电影来为自己发声,同时也在影响着以色列乃至世界的观众。而《摇摇晃晃的人间》的导演是一个男性,这就使得电影是以男性视角来讲述人物遭遇的,这其中因为制作者的解读而产生了一些理解与表达上的偏差。当余秀华离婚之后,制作者竭力表现她内在的脆弱与无助,并通过一场海边的玩耍戏来体现余秀华小心翼翼的胆怯,但是他忽视了一点,倘若余秀华真如影片中所表现的那般脆弱,她是不可能完成从一个农村妇女到独立女性的转变的。为了生存,余秀华曾学过乞讨,为了学习,她阅读了大量书籍,其数之多已足以使她完成对自我的思考。能够打破自己生存束缚的人是强大的,而这种强大才是余秀华生命中最值得表现的特质。这种女性自身的力量已被她的诗歌忠实传递出来:“有时我是生活的一条狗/有时生活是我的一条狗”。她不是被同情的对象,而是值得尊重的强者。因此余秀华虽不是导演,但她依旧可以通过电影中所展现的诗歌来为自己言说。
女性争取自我权利是建立在对外在世界具备一定认知的基础上,对她们而言,在广阔的世界面前,束缚自己的条例和标准是难以忍受的,在这种反抗的过程中,女性也是在抒发表达的欲望以及对自身权益的重新审视。因此女权主义并非是女性对权力的争夺,而是女性在追求自由选择的权利,而这也是所有人应当拥有的权利,这一词曾引起许多非议,因此更多人习惯以“女性主义”来代替。人同时具备超越性与内在性两个特性,前者需要在融合过去的前提下延展到未来,由此完成自我超越,在这个过程中人可以获得自我;后者则是在一个较为稳定的环境中维持生命的延续,保证家庭的安稳。过去的传统女性往往被强制固定在内在性之中,只有通过丈夫来与世界接触。而这两部电影中的女性则是通过她们自己的渠道认识到这个世界:薇薇安有着一份工作,这使得她可以接触到外在世界,而余秀华则是通过网络平台展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由此获得了掌握超越性的可能。她们无法再被禁锢于她们的夫妇共同体之中,因为更大的世界摆在他们面前,她们拥有自由选择的可能性。传统的女性由于无法直接接触世界,因而只有通过爱情或宗教来获得自我,但“作为生产者和主动的人,她便重新获得超越性”3,因而薇薇安和余秀华能够站出来为自己言说,并能够通过影像或诗歌来向更多的女性传达自我意识。
弗洛伊德曾就女性研究上做过这样的评价:“纵观整个历史,人们总是在女性特质之谜上碰得头破血流”4,而这里的“人们”中的绝大多数应当是男性,因此女性需要自己为自己的特质和权利来言说。著名脱口秀《阴道独白》就表现了女性对自我的认识,并通过讲述她们的经历来引导观众理解女性特质和女性需求。《诉讼》的薇薇安宁愿放弃爱的权利也要获得自由,《摇摇晃晃的人间》中的余秀华即便是一个残疾人,也不惮于孤独终老而选择离婚。她们所追求的也不需要观众“头破血流”的去理解:仅仅是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
注释:
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547.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559.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883
4.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下册)[M].北京:三联书店,2006:655
[1]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下册)[M].北京:三联书店,2006:635-680.
[2]安东尼奥•梅内盖蒂.电影本体心理学[M].艾敏、刘儒庭.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100-162.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547-949.
阎瑾(1994.1- ),女,籍贯:甘肃,工作单位:兰州大学,学位: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