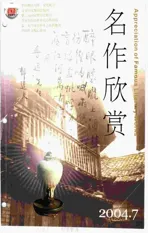拒绝合唱:散文的同质化与异质化(下)
2017-07-13广东耿立
广东 耿立
拒绝合唱:散文的同质化与异质化(下)
广东 耿立
当下的散文创作一直是在繁华与贫乏中行进的,创作数量的巨大无法掩盖同质化的病灶。互相模拟,互相山寨,其实这源自创作者精神的匮乏、创新意识的欠缺,更是精神谱系的断裂和内在文章图式的贫乏。如何突破散文创作的困境?其实就是要求一个散文家精神的自治、人格的自治、生命文体的自治,就是靠近散文精神自由的本质,提倡散文创作的异质化,拒绝合唱。
散文 同质化 精神自治 异质化
散文的出路:异质化
所谓散文创作的异质化,主要是指散文精神的异质或者异端,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同质化的藩篱。说到底,散文的精神,就是人的精神质地,取决于人的内在纹理和品格,尤其在当下,这和一个人的知识储备、学历才华、力气,都无关,这才是散文的根本,按王开岭的话说就是:一个写作信仰问题,是对作家生命关怀力的考验,对其精神诉求和承担能力的考验!
所以我觉得,冲破同质化不是简单地写什么和如何写的问题,而是在散文写作的原点重估:你为何写?非得写吗?这才是散文写作的根本:不散文,毋宁死;不倾吐,毋宁死。这就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是立场的问题,是姿态的问题,散文是一种对自我的雕刻和塑造。我以为这才是散文的底座,无此底座,散文必然会地动山摇。由于多年文学不能自由独立,吃下的是狼奶,很少能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观念、平等的意识,普世观念竟在这片土地成了荒寒和攒击的对象。
散文写作最关键的是异质化,而不是同质化。如果现在仍按审美抒情的路走,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互联网时代,乃至微信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交流的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自然也改变了思想和书写方式。事实上它使人的精神更自由,心灵更开放。自由的精神和开放的心灵使人从集体的规约中解放出来,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规制中解放出来,它影响人的生活,影响到社会、自然,也影响到文学。作家要关注世界,关注存在,关注万物,关注人本身,并且艺术地呈现。这些原则也应是散文的原则,这些维度也应是散文的维度。散文之所以进入同质化的狭小道场,我认为是散文观念的问题:基于内心的懦弱,或者内心的素养不够,一些有毒的东西堵塞,使你不敢、不能面对内心的真实。
鲁迅说中国少有单身鏖战的英雄,少有抚哭叛徒的吊客,所谓的抱团取暖,这对散文是十分有害的。塞壬说:“我只是一个在黑夜沉迷于内心的写字的人。这样的字写出来之后,被归类成了散文。从2004年到现在,我庆幸,我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完全不理会外面的那些热闹,我自始至终还只是那个写字的人。”“一个人专于写字,固执地选择用文字表达,一定是出于某种无法逃避的理由,但凡可以不写,那定然不会写这种劳神子的东西,去酒吧喝酒,去赌博,去纵欲都是可以用来选择的。所以谈到写字的人的真诚,我就说是个伪问题,没有人会对自己的日记撒谎。如果有一天我不再写字,很有可能是我找到了其他的表达方式,但也许是,我不再那么渴望表达,我对这个世界,对自己已无话可说。”
塞壬的观点就是:散文是非表达不可的倾诉,否则不要写。散文的异质化,我觉得还是先要解决如何体验生活书写生活的问题,我们应该回到生活,回到肉身。克里玛曾说:“当作家认为历史比人更伟大,革命理想比人类更重要的时候,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这样的评价对散文的启示最大,那些凌空蹈虚、假大空玄、精雕细刻、没有人性气息而又天马行空的所谓想象,把散文推向了绝境。拿什么来拯救散文的同质化?只有一个法子:回到自身,回到个人体验。比如周晓枫的散文,在当下整个散文文坛的异质性是那么明显,她的散文文体的先锋,语言的云谲波诡,新鲜的人生体验,是别人没有的,她说:“最鲜活、最丰富、最不可替代的直接经验和素材,无不来自身体的亲历。”
但现代社会正在使我们的散文变得麻木。索尔仁尼琴有一句名言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对散文来说,来自最鲜活、最丰富、最不可替代的直接经验和素材比虚幻的美文分量更重。
散文是讲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的,也许网络的浮躁使很多的写作者过于匆忙,底蕴不厚、根基不牢,审美的眼界狭窄,导致很多的文字只是生活表面的滑行,历史记忆浮表的捕捉,无法获得散文文本的力度。
散文应该是精神的裸奔,是最少伪饰与依傍的,散文没有小说的利器(故事、结构、技法),也没有诗歌的节奏与意象,散文是最直接的表达,话语多是直达人心。我想散文目前需要的是一种精神的先锋,是一种俯视苍茫的精神高度,是与众不同的独特的感受与洞见。颠覆过去的陈旧的文本规范,寻找新的话语方式。目前散文缺少卡夫卡那样的精神变形记。我们设想如果卡夫卡没有对异化的锥心刺骨的痛感,没有那种无依无靠的飘零感与孤独感,没有洞察人性的畸变与霉变,没有那种利益下的亲情的不可靠,他不会愤激地写出人的甲虫躯体,来表现那种饥饿艺术家的绝望与愤懑。
人们看到更多的是散文的物理空间之大,却少有人去关注其精神空间。实际文本所呈现的精神含量和丰富性是不够的,尤其在描述深刻的心灵事件,挖掘人性的深度,关注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态,揭示普遍信仰危机,承担良知和批判功能方面,散文往往是缺席的。这并非艺术本身的天然属性,而是一种人为的弃权和出让,一种无能造成的无为。散文自身蕴藏的深阔与幽邃被我们浪费了,我们没有很好地去填充它,就像分到了一所大房子,却没能力去设计、装修和买家具一样。
散文很多时候不是表达的问题,而是勇气的问题,是精神和灵魂不撒谎的问题。
散文是自由的文体
散文的自由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自由,它有着最自由的文体,散文的特质是非虚构,但它的文体又具有虚构一样的创造性。散文是一种“反限定”和“反规范”的文体,夏榆说,散文其实是不可限制的。它有着最自由的文体,也有着最自由的精神。它的面貌取决于书写者的个人气质和精神风貌,取决于书写者的自由精神和独立品质。回望21世纪以来发生的散文事件,繁多复杂。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散文事件,就是散文这种文体在有抱负也有才华和能量的作家那里变得气象恢宏,思想磅礴,文体绚烂,散文不再是文人雅士赏玩的小品,它成为一切优秀的书写者进行强劲表达的载体,它直接诉诸世间生活和人的存在,对此做出思辨及艺术表达。我觉得这个时期的散文是从某种被规制的状态中获得解放,从而获得丰沛强劲的生命力。
散文的灵魂,无论对传统纸媒还是现代新媒体,应该都是一致的,这灵魂即是散文的命,是自由,又往往不在限制与藩篱中徘徊。
网络对散文创作是一次革命。正如竹简挣脱了甲骨,又如纸质替代了竹帛,网络自由无疑是对散文创造力的一种天然唤醒。周作人说:“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所谓王纲解纽,即是束缚尽脱。它是思想的解放,个性的张扬,表达的自由。凡散文辉煌的时段,都是思想自由的时期,历史上诸子时代、魏晋及明末,都是散文的最好时期,这恰恰是统治者权力最弱化的时期。
我们现在常说民国范儿,我们怀念的是民国的那种出版、结社的自由,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现代散文发展的高峰,朱自清先生在为其散文集《背影》写的序言中说:“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绚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这样的判断就是民国散文范儿的最好的例证,是自由之花的累累果实。
网络是一种自由的状态,少了牵制,多了放旷。探索即是自由,思想的自由、文字的自由。网络文学的复杂,多元共存的审美格局,是和自由分不开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无数网上网下作家在不断反叛传统的过程中进行艰辛探索的结果,也正是他们经历了无数次的怀疑、忽略甚至被否定的结果。他们顽强地坚守着散文之所以是散文的表达的需要,冲破“短小精悍”“形散神不散”“欲扬先抑”“卒章显志”“意境”等被视为艺术铁律的传统规范,在探求种种新的审美价值与形式表达的过程中,成功地将艺术引向更为自由、更为深邃的审美到审智的空间。戏剧家尤奈斯库说:“所谓先锋派,就是自由。”
我想反过来,自由就是先锋。自由就是我行我素,然而回到散文的烂漫,我认为,这种自由不是无边的,是一种主体性的思想的自由,思维的快乐,是无限贴近真相与真理,贴近自己和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反抗。这种自由,是一种形式上的突破,是一种怀疑后的表达。
米兰·昆德拉曾说,小说的天质是反专制主义的,“小说作为建立在人类事物的相对和模糊性之上的世界的样板,与专制的天地是不相容的。这一不相容性比一个不同政见者与一个官僚、一个人权斗士与一个行刑者之间的区别还要深,因为它不仅是政治或道德的,而且也是本体论的。这就是说,建立在唯一真理之上的世界,与小说的模糊,与相对的世界,两者由完全不同的说话方式构成。专制的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疑问,因而它永远不能与我所称为小说的精神相苟同”。
这其实也可代替为散文,散文的自由,是向一切的专制开火,向不合理的所谓的范式挑战。其实所谓的范式就是专制,散文文体是最模糊的,因为模糊,才有广阔与博大,这里虽然泥沙俱下,但孩子与血水,蚌病成珠,还是值得的。散文最反对的是规范,是范文笔调,无论桐城派还是杨朔,乃至余秋雨,学他们者生,似他们者死。当然,专制主义多多,不管来自何方的妖孽,要扫除一切,天上地下,唯我(自由之谓)独尊。
拒绝合唱
叔本华说,要么是孤独,要么就是庸俗。这话说出来虽然让人不舒服,但对散文来说,要么是同质化的庸俗,要么是异质化的孤独。孤独注定是精神卓越之士的命运。
孤独是一种精神的掘进,不是抱团取暖。我强调散文应该具有强大的精神体积和美学重量,拒绝合唱!
叔本华说:“人们欠缺忍受孤独的能力:他们内心的厌烦和空虚驱使他们热衷于与人交往和到外地旅行、观光。他们的精神思想欠缺一种弹力,无法自己活动起来;因此,他们就试图通过喝酒提升精神,不少人就是由此途径变成了酒鬼。”
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人需要得到来自外在的、持续不断的刺激——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与其同一类的人的接触,他们才能获取最强烈的刺激。一旦缺少了这种刺激,他们的精神思想就会在重负之下沉沦,最终陷进一种悲惨的浑噩之中。
叔本华有一个比喻,把平庸之辈比之于那些俄罗斯兽角乐器。每只兽角只能发出一个单音,把所需的兽角恰当地凑在一起才能吹奏音乐。大众的精神和气质单调、乏味,恰似那些只能发出单音的兽角乐器。
在这个时代,散文的拒绝合唱,我以为是一个需要淬炼的过程,这不仅需要散文家持续的忍耐力和对生活的心灵发现力,而且需要有鲜活的感受能力,更需要人格的力量。对于当下的散文家而言,写出一篇漂亮和优秀的散文已经不是难题了,难度在于一篇散文放在数以万计的散文中的时候就往往被取消了。回顾当代中国散文的进程,留下来的散文家也没有几个了。所以当散文与历史和文学谱系放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为自己文本的“生命力”敲响警钟。
要忍得住孤独,就要写得慢一点,在一个快速拆迁和不断加速度前进的动车时代,作家是踩下刹车的那个人。但是我看到的则是作家过于快速、急躁和随意的写作方式。显然在一个看似自由的年代,诗意却被强大的日常生活消弭了,安静的空间和舒适的行走已经被现代工具强大的势能所取代。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散文家成了旅游见闻者、红包写作者、流行吹鼓手、新闻报道者、娱乐花边偷窥者、“痛苦”表演者、国际化的“土鳖”分子、翻译体的贩卖者、自我抚慰者和犬儒主义者。话说回来,我们的散文学会了抱怨,也学会了撒娇,学会了演戏,学会了波普,但是就是没有学会“散文家”的“良知”。我向那些仍然彷徨、仍然分裂、仍然理想的有工匠精神的散文家致敬!在一个不断加速“前进”的时代,心存真诚和敬畏地做一个不断“后退”的先锋主义者显得更加艰难。我们不能回到过去,也不能超越当下,由此只能面对生活和现实,老老实实地写作。
塞壬说:“单一的字,它有方向感,它有准确的指向,甚至是内指和外指,用好字,着迷于汉字的细微指向,是一个写散文的人最沉醉的事情吧,它需要这个人慢,熨帖,它需要他安静,还有什么比用准确的字实现了表达更让人快乐的?对汉字的感受力,和对生活的感受力应该不是一回事,我还想说,对汉字的感受力跟语言和修辞也不太像是一回事,前者要的是心灵,后者是技术。我今天想说,强调语言,更细分些,我更苛求单个的汉字。”
散文像单个的字,有时需要苛求慎重,需要打磨,因为不同的汉字软硬长短明暗是不一样的,世间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雷同的汉字。
一个散文家的孤独是面对时间的写作,时光无涯人生短促,散文家是面对存在表达,面对的是岛屿的一隅、山峰的一巅,散文写作者的胸襟和眼光需要阔大,需要人类的悲悯;但作为个体来说,没有必要向群体看齐,没有必要关心写作的潮流和风向,甚至不必关心现实的政治导向。写作者尤其不能充当某些利益集团的工具和应声虫,不能下作成权力的奴仆。审美需要距离,散文也是,是跟制约限制你自由、妨碍你独立的东西保持距离,这是一个文体的尊严,因风骨而对抗各种利诱和内心的卑弱,即所谓的不看脸色和眼色,不揣度,不靠近,在世俗中来,但不到世俗中去。
写作是个体的事业,从来就不是同声合唱。写得慢一点,拒绝合唱,这才是散文的正道。
作 者:
耿立,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出版有《遮蔽与记忆》《新艺术散文概论》《会飞的春天》等。编 辑:
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