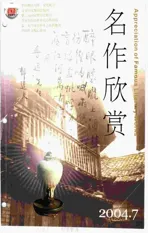穿越时空的“京味”文学
2017-07-13北京李春雨
北京 李春雨
本期头条
穿越时空的“京味”文学
北京 李春雨
“京味”文学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历史特质,而且具有超时空的发展潜质。在多重维度的比较视野下来审视“京味”文学,或许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它的某些本质问题以及它与相关问题的本质联系。
“京味” “京派” “海派” “中国味” “世界味”
何谓京味文学?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又很难回答。这是因为京味文学更多的时候呈现出一种含糊不清的状态:“京味”文学与其他文学的界线怎么划分?范围如何划定?哪些人的创作属于“京味”文学?它和“京派”文学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类似的问题可以提出很多来。更何况,京味文学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文学和文化,北京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依傍着北京而生的“京味”也常常被视为一种“中国味”。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京味”和“世界味”之间又呈现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足够说明京味文学从诞生到今天,是极其丰富又错综复杂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研究京味文学时,必须有一种开阔的视野和比较的眼光,才能在纵横交错的文学谱系中追寻到它的真实面貌。
“京味”与“京派”
“京味文学”和“京派文学”这两个概念似乎从出现开始就相互纠缠在一起,它们虽然都是依托北京这座城市形成、发展的,且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在创作风格上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甚至即使描写了北京的人和事,也不一定就是“京味”或“京派”作家,就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张恨水的不少作品尽管京味儿十足,天桥、大栅栏、小胡同如此等,留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再给他乔装打扮,但谁都会认出他不是京派。”其实,又有谁认为张恨水是个“京味”作家呢?这两个流派既然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异性,那么将它们捆绑在一起的这同一个“京”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1.本地人与外乡人
首先从人员构成上,京味和京派就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京味文学的代表作家基本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道地北京本地人,而被纳入京派的作家如废名、沈从文、朱光潜、凌叔华、李健吾、萧乾、汪曾祺,他们几乎都是“外乡人”。这就直接决定了京味和京派的文学视角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本地视角,一个是外乡视角。
京味作家对待北京的感情是热烈的、直接的。在现代作家当中几乎没有人像老舍一样对北京文化有着如此熟悉、地道的描写。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老舍的一生都倾注在表现北平的市民世界,他的代表作《茶馆》《骆驼祥子》无不以北平为创作背景。据舒乙统计,老舍作品中提及的二百四十多个北京的山名、水名、胡同名、店铺名,有95%以上都是真实的。事实上这种真实和熟悉根本上来源于老舍对这座城市最深沉的爱。老舍曾在《想北平》一文中说道:“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是完整的,像一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若不是有这份炽热又毫无保留的爱,又怎么会“一闭眼我的北平就是完整的”?
京派文人虽然大多寓居北京,也深受北京文化的吸引和惠泽,但是相比于京味作家炽热而又直接的爱,京派文人对于北京的描写和感受始终站在一个外乡人的角度。虽然师陀也曾深情地写道“北京是个例外,凡在那里住过的人,不管他怎样厌倦了北京人同他们灰土很深的街道,不管他日后离开它多远,他总觉得他们中间有根细线维系着,隔的时间愈久,它愈明显”,但是这种与北京像一根“细线”维持着的关系和老舍那种对北京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情,显然是不同的。一个显在的事实就是,即便对北京再怎么亲切熟悉,寓居在此的京派文人,始终忍不住回望的是自己的故乡。沈从文的翠翠生活在湘西沅水边,师陀取材立足的是中原的乡野大地,废名“竹林的故事”也没有发生在北京的竹林。北京对于京派文人来说更像是良师益友,在沟通中互相了解,有所收获。老舍曾说过:“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像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而京派文人则有着天然的优势。一方面,北京文化具有一种强大的亲和力和同化力,能够唤起他乡游子对于故乡、对于乡土的眷恋之情;另一方面外乡人的视角又让京派文人对北京文化有着更为自主和更为深刻的理解和阐释。
2.生活化与散文化
从语言来看,京味文学堪称最具代表性的北京文学。老舍作品的语言充满了浓浓的北京味,这种风味并非仅指北京常见的俗句俚语或者习惯句式等方言上的特征,它更包含着北京人的生活和个性,是一种北京独有的文化氛围,它有着独特的文化历史的韵味:机智幽默,醇厚谦和,干脆利落。特别是老舍的话剧,让人感受到浓郁的北京风味。比如《茶馆》中王利发(茶馆掌柜)的出场:
王利发:唐先生,你外边蹓蹓吧!
唐铁嘴(惨笑):王掌柜,捧捧唐铁嘴吧!送给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相面吧!手相奉送,不取分文!(不容分说,拉过王利发的手来)今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您贵庚是……
王利发 (夺回手去):算了吧,我送给你一碗茶喝,你就甭卖那套生意口啦!用不着相面,咱们既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由柜台内走出,让唐铁嘴坐下)坐下!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戒了大烟,就永远交不了好运!这是我的相法,比你的更灵验!
这个出场就彰显了王利发为人做事的原则和分寸,面对就爱耍嘴皮子、抽大烟而又身无分文的唐铁嘴,王利发很客气,不仅不会强制把他赶走,反而设身处地地怜惜他,即便是教训也表达得委婉得体,不失分寸。再看他一张口就是“哥儿们,都是街面上的朋友,有话好说。德爷,您后边坐”。见到实业家秦二爷更是加倍热情:“哎呦! 秦二爷, 您怎么这样闲在,会想起下茶馆来了?”一次次开口,使一个老北京茶馆掌柜的形象跃然纸上。而老舍笔下的其他人物形象同样鲜活生动,如清朝遗民常四爷一开口就是“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干吗?”充满着刚正耿直、好管闲事的正气。松二爷则以提笼架鸟为乐,对自己的鸟非常上心,总喜欢说:“我饿着,也不能叫鸟儿饿着!”这里面不仅有旗人的生活情趣,更有他们爽烈的个性特征。茶馆里其他进进出出的各色人等,老舍都用独特的京味语言真实地展现了他们的生活和个性。虽然是话剧,但语言却十分自然随意,没有半点“生硬”和“舞台腔”。所谓“开口就响”“话到人到”,老舍剧作特有的浓郁的京味特征,首先是通过纯口语的人物对话显现出来的。他们纯粹的京腔京韵与京白能够让我们一下子进入京味文学的世界,这是老舍给他的人物亮出的一张特有的身份证。
再来看京派,不像京味小说中明显的京片儿和白话,京派小说普遍存在一种散文化的倾向,不以情节为重,更加注重用诗化的语言营造独特的意境。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废名。废名的小说善于用古典诗般的语言刻画人物的动作和心理,比如小说《桃园》中“王老大一门闩把月光都闩出去了”,“闩”字的运用别有一番韵味,值得人反复回味。废名在小说中不会大量运用叙述性的长句子,他用数量更多的断句来表达,而这种语言上的切割就使得小说别具一种诗意。同时在这种俭省的单句中,余留了许多空白,更加含蓄、耐人寻味。不仅废名如此,沈从文的《边城》同样是一首诗,如其中对白河的描绘:“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可清澈见底。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凌叔华的小说有着明显的中国古典诗词意境的痕迹,师陀的一系列以河南村镇生活为背景的小说都体现了他“用旧说部的笔法写一本散文体的小说”的努力。京派小说家在文体方面的创新更像是回归传统的试验,带来的是语言的古典和雅致。
3.市井化与学院派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都,北京拥有三十多年的建城史和将近九百多年的建都史,可以说从古到今全国最优秀和最精英的学堂和文化机构都集中在这里,形成了一种精英色彩浓厚的“学院文化”。但同时北京也是一座大都市,生活着大量形形色色的底层平民,自然也沉淀着浓郁的“市井文化”。这两种文化兼容于这座城市之中,一俗一雅,深刻地影响了京味和京派这两种文学形态的形成和发展。
京派文人大多在高等学府中担任教职,拥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属于不折不扣的学院派。他们虽然不像其他流派团体一样,拥有严密的组织,但是常常会举办一些文化沙龙,比如说林徽因每逢周六就会在自家的四合院里举办茶会,邀约各类学术精英、社会名流前来品茶聚会、谈古论今。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后来回忆道:“每到周末,许多伯伯和阿姨们来我家聚会,这些伯伯们大都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曾留学欧美……在他们的朋友中也有文艺界人士,如作家沈从文伯伯等……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文化领域,涉及的面和层次比较广、深,思想的融会交流有利于共同的视野开阔,真诚的友谊更带来了精神的力量。”这种类型的茶会也因为它的精英化取向被冰心讽称为“太太客厅”。在创作上也是如此,周作人、俞平伯、废名等人的作品不仅吸取了西方文学的资源,又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常常在流露浓郁个人情怀的同时,穿插大量的民俗掌故。即使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也是字斟句酌,特别讲究文辞的漂亮和严谨。
北京也是全国最为繁华、休闲娱乐方式最多的城市。老北京茶馆、百年老字号、老北京杂耍、皮影、兔儿爷、糖人等,这里的“市井文化”充满了勃勃生机,在京味文学中也有诸多表现:养鸟、遛弯、下棋、泡茶馆、耍贫逗乐,北京人的生活姿态在诸多作品中可见一斑。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满怀深情地追忆了北京的节令习俗:北京人过端午节,“家家必须用粽子、黑白桑葚、大樱桃供佛”,“妈妈不能对孩子发气,孩子是过年过节的中心人物”。到了初五那一天,男孩子要用雄黄抹“王”字,女孩子则要带“葫芦”,“葫芦是用各色的绒线缠成的樱桃,小老虎,桑葚,小葫芦……联系成一串儿,供女孩子们佩带的”。在老舍笔下的祥子、虎妞、张大哥、老马和小马,都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人物,描写的也是胡同里发生的家长里短,这里面既饱含了浓浓的生活气息,又体现出老舍对旧文化、旧市民批判中带有的不忍和深切的同情。
内涵如此丰富的北京文化,它的基调是宽广、深厚的,无论朝代更替,时代变迁,它都透露出从容、安稳的气质,因此,它既能直接孕育出像老舍这样土生土长、专门写北京城与人的京味文学作家,又能潜移默化地培养出如周作人、沈从文、废名等不是北京人,也不写北京事的京派文学作家。
“京派”与“海派”
作为全国的两大文化中心,北京和上海无论在文化氛围上还是精神气质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依傍着这两座城市而生的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自然也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
1.都市里的乡土追求
京派的作品里始终呈现着这样两种鲜明对立的世界:一是乡村世界,一是都市文明。京派作家对自然村野的审美表现体现了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情怀。他们对于都市文明的表现则明显带有一种批判的眼光。沈从文就一直自称为“乡下人”,他在《篱下集题记》中说:“在都市住了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
海派文学在阅读观感上常常给予我们一种感觉,就是它主要以描写商业化、世俗化的都市生活为主,比如穆时英在《上海的狐步舞》中描写“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一只Saxophone正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呜呜地冲着他们嚷。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些热衷于描写都市的海派作家其实大部分都不是上海人,张资平就是广东梅县人,穆时英是浙江慈溪人,施蛰存出生于浙江杭州,刘呐鸥原籍是台南。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这种身份上的特殊性让海派作家在描写都市的同时,也总会不经意地流露出一种归家的情怀和乡土的意识。例如施蛰存的小说《渔人何长庆》中的菊贞,虽然向往着上海的新奇与繁华,在嫁给长庆之后与人私奔到上海。但她跑到上海做了什么呢?“四马路,在那儿做野鸡了。”施蛰存的这种安排意在说明都市文化往往使人道德沦丧、人性扭曲;而长庆把她接回小镇后,她照样从事祖遗的生活,恢复了先前的朴素正直,跟长庆过上了稳定和谐的生活。在这里,乡村似乎具有了修复人性的功效,我们甚至能够感受到这篇小说在语言风格、情节安排以及它所反映的人性特点上,与京派小说有着一种相似性。小说讲到菊贞跟人私奔之后,长庆“当然是不欢喜,但也并无什么悲戚”,这样的句子读起来,简直让人疑心是出自废名之笔。而长庆和小镇对于一个做过妓女的女人的包容,也很容易让人想起沈从文笔下的萧萧。所以也有人称施蛰存为“海派中最近京派的人”。事实上不仅是施蛰存,对乡村的回归也是很多其他海派作家描写的隐含主题,穆时英的《黑牡丹》、刘呐鸥的《热情之骨》等作品都有关于都市人逃离都市,渴望回到故乡的书写。
2.乡土描写的不同底色
当然,京派和海派笔下的乡村是不尽相同的。京派作家普遍有乡土生活的经验,他们把自己的创作情感全部都投入到想象中的遥远而宁静的故乡,所以才有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湖北风情,师陀的黄河原野,汪曾祺的江南水乡,故乡在他们笔下成了一个纯朴自然的“乌托邦”。正因为有了这种切实的生活体验,京派作家更注重人和土地、和大自然的整体关系:“从审美情趣上看,‘京派’小说家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心仪陶渊明,这种选择使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表现出对田园牧歌情调的倾心向往……但他们的田园牧歌式的小说比西方的自然派作品更讲求自我的逃遁,更讲求情感的客观投影,因而有某种类似非个人的性质,‘万物与我为一’的理想正是它的注脚。”“京派批评家的文学视野所关注的,主要的不是社会或历史的进程与规律,而是个体的人、是主体对生活的体验与领悟……在京派作家的文学功用观中,人的因素也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文学对社会施加影响同样是通过人,通过对国民的每一个个体的人格塑造来达成的。”“‘人’——个体的‘人’,就成为流派批评的文学本质论与文学功用论的交汇点,成为他们将自己的社会关怀与文学理想联系起来的重要枢纽(或者中介环节)。”
对于海派作家来说,他们也写乡村,有的是对童年生活的追忆,比如施蛰存早期的小说《上元灯》,就是通过对充满诗情画意的童年生活的描绘展示出初恋般美丽的乡村记忆。但大部分海派作家都缺乏长期的乡土生活经验,应该说现实意义的乡土对于海派作家来说是相当隔阂的,他们写乡村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感于机械化和商业文明给现代都市带来的畸变,敏锐地捕捉到都市人严重的精神危机,而将乡土作为一种情感和精神寄托,或者作为一种对都市的批判。《黑牡丹》中的“我”实在无法抗拒都市生活,不得不“又往生活里走去,把那白石的小屋子,花圃,露台前的珠串似的紫罗兰,葡萄架那儿的果园香……扔在后边儿”。在这些小说中,都市和乡村之间拉着一根若隐若现的绳子,现代都市人被割断了与自然的联系,成为都市的游子,而对乡村生活产生一种远远的呼唤,这种呼唤使得海派都市小说的乡土虚构和想象更加虚化,建构在作家个人情感和想象的基础上,常常透着一种单薄和虚弱——它缺乏那种真切可感的人性关怀,那种深层的文化意蕴,那种犀利的社会批判。
3.“都市—乡村”的二元对照
无论是京派作家更善于写乡村,还是海派作家更擅长写都市洋场,我们都应该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两个派别的书写背后都蕴含着“都市—乡村”的二元评判标准。也就是说,京派作家虽然写的是乡村,但背后隐藏的是对都市的批判;而海派作家虽然写的是十里洋场的光怪陆离,但他们对都市中人性扭曲的描写,是在与乡村的对照下得以映射出来的。
沈从文到了北京才开始回望湘西,身在北京来写湘西,湘西的“美好”是在沈从文看见了都市文明的“丑陋”之后才被唤起的。对沈从文来说,的确是没有“京城”就没有“边城”,可是他一旦建构起了自己的湘西世界,你所看到的就绝不只是对理想人性的诗意描写,而且还有对包括“京城”在内的那些所谓文明大都市的理性反思和批判。我们看到沈从文笔下乡村生活的真善美大多出自虚构和想象,在世外桃源般的湘西世界里,人性善良淳朴,人物各安天命,每个人都敢爱敢恨、纯真自然。而在都市小说的描写中,主人公往往患有肺病、失眠症甚至疯瘫,除了生理上的疾病,更显而易见的是精神上的缺陷,这些形象普遍面色憔悴,道貌岸然。例如《八骏图》中那位自诩为心灵医生却抵挡不住诱惑的教授,《绅士的太太》中被称作“废物”、患有疯瘫病和性无能的绅士。沈从文乡土小说中的人物或精力充沛,或内心沉静,《边城》中天保和傩送“结实如小公牛”,龙朱“美丽强壮像狮子”,而《渔》中吴家兄弟弃仇不报,内心安宁,将“如昔年战士”般的勇敢都用在挥刀斫取鱼类上。但现实中的湘西世界并不像沈从文笔下的那么美好,都市也不见得就有那么黑暗不堪。沈从文自己也曾说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他供奉希腊人性的小庙,那是在残酷现实中一种忧伤而美好的向往。同样,在北京时描写湘西,离开才越来越感受到北京的吸引力和魅力。这种心态和情形在京派作家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同样,对于海派作家来说,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成为冒险者的天堂,以20世纪30年代来看,那时候的上海与中国其他城市有着巨大的反差,舞厅、码头、摩天大楼,种种都市化、现代化的意象成为了上海的新标志,提供了北京所不能提供的对文学想象的刺激。海派文学热衷于时尚、摩登的尝试,无论是在对作品题材的选择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与京派作家古典、大气、宁静的牧歌情调很不一样。但是海派作家的作品里,也同样存在着对都市文明的矛盾态度,他们表面看来醉心于对都市文明那繁华、喧闹生活之渲染,实际上却是在揭示畸形的城市文明下的人性扭曲。
“北京味”与“世界味”
京味文学不仅具有地域性,也是一种很强的民族性文学形态。它源于北京、属于北京,但又超越了北京,很多时候被看作是“中国味”的代表,当我们纵观20世纪的京味文学,它从20世纪初诞生开始,一直到现在的“新京味”文学,都与“世界味”有着深刻的联系。
1.北京“新文学”的现代性
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是在与整个中国文学传统的交相冲突中产生的、带有重大转折性质的文学,但是对于北京来讲,这个“新”有着独特的含义。“五四”新文学的发端之地就在北京,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中心也在北京,现代文学中很多重要品格的坚守还是在北京,包括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文学社团流派,同样是以北京作为依托根据地。所以北京的“新文学”从形成之初,就既蕴含着传统北京的地域文化色彩,又明显地带有西方现代化色彩。
拿老舍来说,老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作为京味作家的扛鼎人物,老舍使用的语言大多是地地道道的京片子,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在老舍的创作中,还始终贯穿着一种欧化的句式。比如在《二马》中,老舍使用了大量的倒装句,“他没有地方去,虽然伦敦有四百个电影院”,“他听什么都可哭;因为他失去了人类最宝贵的—件东西:爱”,等等,北京话讲究干净利落,而老舍作品中的语言时常出现重复的语句:“中国人!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开眼的时候了!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二马》)
虽然老舍的作品内容大多都是北京的人和事,但在描写方式上借鉴了很多外国文学的手法。比如他的剧作《茶馆》,各幕之间的连接运用了西洋戏剧报幕的方式,老舍为此特别设置了一个角色——大傻杨,他在幕间唱一段数来宝,既简要回顾上一幕的情节内容,同时开启下一幕的演出。中外戏剧艺术在老舍的话剧中浑然一体,相互辉映。还有很多研究者认为老舍受到了狄更斯很大的影响,甚至他的《老张的哲学》与狄更斯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在情节上就存在着“横向移植”的情况。老舍写了大量的城市贫民形象,有在寒冬中缩着脖子战栗的巡警,有拼命生存却不断受到打压的车夫,也有被生活所迫沦落风尘的少女等。虽然在内容取材上老舍立足的是自身的贫民生活经历,但在描写的手法上,他更多借鉴的是狄更斯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
2.“新北京”文学的世界味
京味文学当中的“京”不仅包括老北京,也包括新北京。在全球化语境的冲击下,作为首都的北京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近些年来,北京也在向建设世界城市而积极迈进。反映在文学上表现为涌现了一批以汪曾祺、刘心武、陈建功、邓友梅、刘绍棠、韩少华、王朔等为代表的京味作家,他们的作品中一方面最深沉地流连感怀着老北京,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从而呈现出一个多元的话语世界。
刘心武的《风过耳》描写了一群聚集在高档歌舞厅等场所的北京新一代青年,他们“玩深沉、玩忧郁”,陈建功的《髪毛》《飘逝的花头巾》等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大多有着优越的生活,在精神上极度自负和自我,嘲笑现实,但现实生活中又常常处于迷茫的状态,到了王朔这里,这类人物形象就更加突出,王朔特别善于在嬉笑怒骂的调侃中塑造出一个个鲜明的“顽主”形象。王朔笔下的“顽主”习惯于把精力和聪明全部浪费在空虚无聊的贫嘴与游戏上,他们大多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和远大理想,整日无所事事、混吃混喝。表面上逍遥快活、吊儿郎当,内心却充满了焦灼和苦闷。这一类人物虽然都是北京的小青年,但是他们身上这种以自我调侃、自我迷失、自我放逐的姿态来进行反叛的精神,实际上与进入现代化以来人类面临的精神危机有着相当程度上的贯通性。比如《第二十二条军规》《万有引力之虹》这些作品,都是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嘲讽态度表达了社会环境与个人发展之间的不协调,借主人公的荒诞言行影射现实,看似幽默可笑,实则反叛社会现实。王朔自己曾说过:“我在约瑟夫·海勒的作品中找到的共鸣也超过在昆德拉作品中找到的……我喜欢纳夫科夫的《罗丽塔》,那里面没有社会的震动,全是个人的东西,写的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我喜欢这种。”他所提到的约瑟夫·海勒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最擅长的就是用精神反叛和消解一切传统价值和意义,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嘲笑和自嘲成为他们寻求解脱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可以说新京味文学在面对现代化、都市化、国际化的冲击时,一方面感怀着旧北京的消逝,另一方面又在“旧北京”崇高意义的阴影下,努力地寻找自己诉说“新北京”的方式。
3.地域性与超地域性
实际上,不管是京味、京派、海派,还是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东北作家群、巴蜀作家群等,他们之所以能够以区别于其他流派的姿态进入文学史,就是因为他们各自在文学描写上带有强烈的地域性色彩(这一点我们从命名上就可以看出来),地域性是形成作家文学风格的重要资源,也是我们区别不同作家作品的重要标志。在长期的、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地域文学形成了自己稳定的特点,构成了自己相对稳固的发展模式,像京派和海派文学及文化,不管它们各自形成历史的长短如何,也不管它们所在地域的形态和内容有多大差距,作为一方文学和文化的特点来讲,京派和海派是相对稳定的,这也正是我们对地域文学和文化包括一些文学流派关注和研究的立足点。不同地区、不同味道的文学都处于一个变动发展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京派与海派得以不断生存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的创新与流变,但有一种味道是永久不变的,那便是这座城市的精魂。城市文学是城市精魂的表达,它以文学空间容纳了城市的文化空间。巴黎的时尚,东京的古典,莫斯科的广博,它们的城市风格与本土的文学创作在相互影响下形成了某种固定而独特的风貌。
但是如果我们过于看重地域文学和文化的稳定性的特点,就不仅会妨碍我们更深入地探讨地域文学和文化的本质内涵,甚至会走向一种偏差和局限,这是因为地域文学与文化在形成自己稳定特色的过程中也是在不断流动和变化的,不断地会注入新的内涵甚至其他地域的文化。拿京派作家来说,他们在表现北京文化所体现的某些共同性时,常常超越北京,构成了属于整个中国新文学的一些特殊的东西,比如人们看到了京派文学里面也有“新感觉”,也有心理分析,不光是海派作家有《上海的狐步舞》和《梅雨之夕》,京派也有这种超越传统、超越古典、超越北京地方的东西,如废名的《桃园》与《桥》、萧乾的《梦之谷》、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等。
其实不管是京味文学反映了当地的地域性,还是也融合了外地的地域性,当我们直面文学本身价值的时候,不禁想问,文学最大的魅力到底是什么?是因为它展示了各个地域的不同色彩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人学,是在探讨人类历史上面临的共同话题,反映的是超越时空的人类某些共通的人性。
本成果受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为:16ZDJ04,并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号为NCET-12-0802)支持
①许道明:《京派文学的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②老舍:《想北平》,《老舍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5—56页。
③老舍:《三年写作自述》,《老舍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3—274页。
④师陀:《〈马兰〉小引》,《师陀散文选集》,范培松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
⑤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页。
⑥老舍:《茶馆》,《老舍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5—266页。
⑦废名:《桃园》,《废名作品新编》,吴晓东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页。
⑧沈从文:《边城》,《沈从文精选集》,燕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
⑨师陀:《〈江湖集〉编后记》,《师陀研究资料》,刘增杰编,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60页。
⑩梁再冰:《回忆我的父亲》,《窗子内外忆徽因》,刘小沁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⑪沈从文:《篱下集题记》,《沈从文文集》(第1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页。
⑫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穆时英全集》(第1卷),严家炎、李今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35页。
⑬鲁迅:《“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编年版)》(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⑭许遭明:《京派文学的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页。
⑮黄健:《京派文学批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8页。
⑯穆时英:《黑牡丹》,《新感觉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⑰李然、谭谈:《源与流——王朔创作问答》,《喧嚣的经典——审读王朔:口诛的浪漫》,辽宁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05页。
作 者:
李春雨,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汉语国际教育文化传播。编 辑:
斛建军 mzxshjj@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