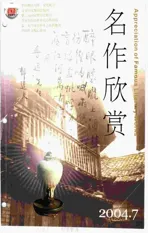“五经”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之十二《春秋》:正名分而明责任(上)
2017-07-13山西刘毓庆
山西 刘毓庆
经典重读
“五经”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之十二《春秋》:正名分而明责任(上)
山西 刘毓庆
《春秋》是“经”又是“史”,它开创了以坚持道德原则与价值判断为核心的中国史学传统,使史学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个监督系统;它也开创了以文化而不以血统为原则的多民族国家传统。所谓“春秋大义”,其实就是九个字:定是非,正名分,明责任。《春秋》所倡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
《春秋》 经学 史学 春秋大义 价值观
如果说《尚书》是“述三代以彰王道”,注重政治管理体系的建构;《易经》是“推天道以明人事”,注重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礼》是“制礼义以倡人道”,注重人的行为实践体系的建构;《诗经》是“顺人情而循礼义”,注重人的道德伦理体系的建构;那么,《春秋》则是“正名分而明责任”,注重人的名分意识和责任意识的体系建构。这五种“经”各有范畴,但在“觉世牖民”方面也有所交叉。比如《礼》讲的是“礼”,《诗》的核心是“止乎礼义”,但“礼”在《春秋》中同样是重要的内容,甚至司马迁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再比如《尚书》是“史”,《春秋》同样是“史”。正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易类”总叙所说:“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也就是说,《尚书》《春秋》的内容几乎全部可以作为真实史料进入史学范畴。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五帝本纪》及《殷本纪》《周本纪》,就大量参考了《尚书》,《世家》部分则大量参考了《春秋》,《列传》部分则大量参考了《战国策》。
作为“五经”之一,《春秋》也是最有故事、可读性最强的一部。同样是“史”,它比《尚书》语言浅显,且人物事件众多,虽记事简赅却深寓褒贬,因而读者更容易接受。又因其是编年体史书,所以史家在研究史料时也多能循其脉络,理顺中国春秋时代的政治文化纹路,自古以来就备受史家重视。从“觉世牖民”的角度看,它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孟子·滕文公下》有言:“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正因为《春秋》的叙事行文中暗寓褒贬,那些乱国奸臣、祸民贼子就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而心怀畏惧。
那么,《春秋》是一部怎样的书?关于《春秋》的“三传”是怎么回事?所谓“春秋大义”又是指什么?《春秋》有着怎样的文化意义?它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与当今流行的西方价值观有着怎样的不同?下面我们就从这五个方面来分析。
《春秋》的性质及意义
《春秋》是一部怎样的书?它是什么性质?为什么叫“春秋”呢?杜预在《春秋左氏传序》中这样回答: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这是说《春秋》是鲁国的史记,它记事之法是按时间顺序。至于为什么叫“春秋”,是因为它是按年编写的,而一年中有春夏秋冬四时,故交错抽举“春秋”以代表四季。杜预的这个解释可能有师说来源,但并不能令人满意。另外还有两种异说,一种是说孔子作《春秋》,始作于春,书成于秋,故取了这个名字。还有一种说法是,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取“春秋”以为名,想让为人君者不失“中”道。这些看来都是臆说,是离开古人的生活背景而所做的逻辑推测。我认为这和古代的农业社会生活有关。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春天是播种的季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这两个季节对人们来说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周族,这是一个以农业起家的民族,故周朝社会特别重视农业。每年开春,周天子要亲自开耕,并祭祀社稷;秋天则要答谢社稷神。像《周颂》中的《载芟》和《良耜》两篇,就是有关周天子春祭、秋报社稷的歌子。同时祭祀、朝聘等重大活动,一般也在春天或秋天。如《周礼·州长》说:“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周礼·小行人》说:“令诸侯春入贡,秋献功,王亲受之。”《鲁颂·閟宫》说:“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墨子·尚同中》说:“古者国君诸侯之以春秋来朝聘天子之廷。”渐渐地,人们就以“春秋”来代表一年了。中国古代问人年龄,常问“春秋几何”,如今人们歌中也唱“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以“春秋”指代一年的说法都来自于这种古代农业社会的习俗。但在中国早期非农业社会时期,也有用“冬夏”来代表一年的,我们从《山海经》里就频繁地看到“冬夏”的概念,如言“冬夏有雷”“冬夏有雪”“冬夏播琴”“冬夏不死”等,但没有“春秋”。这反映了没有进入农业时古人的一种观念。进入农业社会后,“春秋”的意义就大过了“冬夏”,人们更习惯用“春秋”来代表一年了。
也正因为如此,把史书称作“春秋”,就很自然了。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有本国的编年史书,大多都叫作“春秋”,如《墨子·明鬼下》中提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也有些其他的名称,如《孟子》中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但各国的“春秋”都失传了,现在存留下来的就只有鲁之“春秋”了,这就是列入“五经”的经孔子修订过的《春秋》。
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可以说是我国春秋时期二百四十年历史的大纲,相当于孔子在当时修订的一部“近代史教材”。可贵的是,《春秋》虽然是“鲁史记”,但它在记述鲁国历史的同时,还记载了同时代其他诸侯国的历史,其中既有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会盟、朝聘等政治事件,也有日食月蚀、地震山崩、水灾虫灾等自然现象,还有祭祀、婚丧、宫室、搜狩等经济事件,因而在后世学者研究春秋时期的历史时,能够得以看到那一时代各个国家的情况,也就是说,《春秋》所展示的是一种“天下”视野,而非单纯的鲁国视野。这就是孔子的伟大之处。
关于孔子为什么要编《春秋》,它的意义何在?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详引董仲舒的一段话做了说明:
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眀也。
这是说,孔子看到了周的衰微和诸侯之间的相互侵害的现实,同时他自己用于当世的出仕愿望也受到了重重阻力,他感到自己所奉行和倡导的“道”难以推行,所以决定对二百多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进行评断,为天下设立一个是非标准,对天子、诸侯、大夫的非礼之行,一律给予贬抑。他认为空谈道理,不如用具体事情来说明更容易被人接受,所以著《春秋》“以达王事”。又说: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从经的角度看,《春秋》具有“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的素质,能把古今不易之理,存于文字语脉之中,使人们可以之为价值尺度,以衡量事物。就其功能而言,《春秋》能“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能把一些混乱得让人感到迷惑的问题弄清楚,把是非混淆的问题弄明白,把人存犹疑无法判定的事情判定清楚。就其目的而言,则是“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在明确的是非态度与行为选择之中,以实现王道,拨乱反正。又说:
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这则是就《春秋》的政治意义而言的。无论是君还是臣,不知道《春秋》,就不明善恶,不知守常应变之道;不懂得“《春秋》之义”,就会君行无道,臣行篡弑,国家自然会处于混乱状态。为什么?就是因为不知礼义。“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它可以礼义禁祸乱于未然之前,笔伐乱臣于已然之后。让后世知君当如何为君,臣当如何为臣。
简言之,在古人心目中,《春秋》的意义,在于其能维护伦理道德秩序,保证社会的永恒稳定。
《春秋》及“三传”
由于《春秋》记事的文字过于简洁,甚至有的只记结果没有原委,于是孔门弟子及其后学传经时,便对《春秋》作了“传”。什么叫“传”?许慎《说文解字》说:“遽也。”清代段玉裁注:“遽,传也……按,传者如今之驿马。驿必有舍,故曰传舍。又,文书亦谓之传,司关注云:‘传如今移过所文书是也。’引伸传遽之义。则凡展转引申之偁皆曰传。而传注、流传皆是也。”东汉刘熙《释名》:“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所以,传,就是要通过解释的方式,把重要的文书流传下去,让后人看到并看懂。为《春秋》这部经书解释的书,就叫“《春秋》传”。先秦时传授《春秋》的有三家,分别有《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合称“《春秋》三传”。
《公羊传》因传自公羊氏而得名。《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公羊传》十一卷,班固自注说:“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注说名高。唐朝徐彦《春秋公羊疏》引戴宏序,记述了《公羊传》的传授历史:
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
这个传授谱系告诉人们,《公羊传》始由子夏的学生公羊高传授,开始是口授,到汉景帝时,才由公羊高的后裔公羊寿与他的弟子胡毋子都,共同合作用文字记述下来。这就是今天见到的《公羊传》的传本。当然这个谱系并不十分可靠,中间一定有遗漏,因为从子夏到汉景帝约三百余年,而《公羊传》的传授仅有六代,每一代都需要延续六七十年以上才能衔接,这显然不可能。《公羊传》引及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等,这应当都是公羊高之前传授《公羊传》的经师。研究《公羊传》解释《春秋》的学问,被后人称作 “公羊学”。
“公羊学”因兴于齐地,因此把齐之阴阳学说带入了解经之中,从而带有神秘色彩。而其价值取向是强调“大一统”,主张变易,倡“三世”之说,即所谓“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公羊传》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所传闻世”是“据乱世”,“内其国外其夏”;“所闻世”是“升平世”,“内诸夏外夷狄”;“所见世”是“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这里体现的是观念形态的演进。有人把这种观念说成是历史进化论,其实这讲的只是观念的变化。“所见世”所谓“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反映的是文化上的认同。并不因为其“夷狄”血统而排挤之,只要他们接受了华夏礼义,便不必分彼此。
《公羊传》作为文献,在传播过程中有两位功臣,一位是汉代的何休,他是董仲舒的四传弟子,著有《春秋公羊解诂》;另一位是唐代的徐彦,他在何休《解诂》的基础上,撰写了《春秋公羊传注疏》,即今《十三经注疏》中收录的本子。“公羊学”作为一种学说,在发展中也有两位影响甚大的学者,一位是汉代的董仲舒,他发挥公羊派的学说,并把它直接运用于政治,为维护天下一统做出了理论上的说明。如说:“《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汉书·董仲舒传》)另一位是近代的康有为,他发挥公羊学的理论,主张“改制”,倡导“大同”,产生了很大影响。
《谷梁传》因谷梁俶而得名。谷梁相传也是子夏的弟子,“俶”或作“赤”,或作“寘”“喜”,其实都是一音之讹变,这与《谷梁传》最早的传授形式有关。《谷梁传》与《公羊传》一样,最早也是靠口耳相传的。口传因发音各异,便会出现变异。它的写定时间很晚,当在《公羊传》之后,内容上也有些是从《公羊传》来的,当然也可能与它们同出一源有关。在西汉时,《谷梁传》与《公羊传》同立于学官,属《春秋》今文派的两家。《谷梁传》的特点是主张“尊王”,强调君臣职分,如清代钟文说:“《谷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夫贵礼贱兵,内夏外夷之旨。”其解经“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甚是严谨。晋朝时,范宁为作《集解》,唐朝杨士勋在范宁《集解》的基础上撰写了《春秋谷梁传注疏》,即今《十三经注疏》中所收录者。
《左传》,又名《春秋左氏传》,因出自左丘明而得名。相传左丘明为孔子同时人。《汉书·艺文志》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襃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这段话把左丘明著《左传》的原因以及《左传》隐而晚出的原因,都说得很清楚。关于《左传》在先秦的传授情况,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据刘向别录说:“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此经既遭焚书而亦废灭。”现在见到的《左传》,是汉时从孔家老宅的墙壁发现的。武帝时虽已献于朝廷,但没有立于学官。属古文经学的一种。今见到的最早的注本是杜预的《春秋左氏集解》和孔颖达因杜而作的《春秋左传注疏》,《十三经注疏》中所收即此。
《左传》记事始于鲁公元年,终于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多十三年。《春秋》经终于哀公十年,而《左传》续经至十六年孔子卒。《左传》解经有很大的自由性,不是像《公羊传》《谷梁传》那样据经文字句说解,而是“论本事而作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因而有些地方与经相矛盾,有些地方经无而传有,即所谓“无经之传”“异经之传”。这说明左丘明撰《左传》,把握的是《春秋》是以礼为核心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判断,而不是《春秋》叙事的表层,也没有把《春秋》当作绝对真理。在这一点上,与公、谷两家就不同了。
同样是解释《春秋》,但“三传”并不相同。前人关于“三传”的比较评论甚多,如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就汇各家之说云:
“三传”皆有得于经,而有失焉。《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郑康成之言也。《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义有三长,“二传”之义有五短,刘知几之言也。左氏拘于赴告,《公羊》牵于谶纬,《谷梁》窘于日月,刘原父之言也。《左氏》失之浅,《公羊》失之险,《谷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专而纵,《公羊》之失杂而拘,《谷梁》不纵不拘而失之随,晁以道之言也。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谷梁》,或失之诬,或失之乱,或失之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谷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叶少藴之言也。《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谷》经学,理精而事误,朱文公之言也。学者取其长,舍其短,庶乎得圣人之心矣。
这些都是学者们从研究中所得的体会。就其要者言之,《左传》主于“历史”,即把原来《春秋》中记述不详的历史事件以文学性的语言记述下来。《公羊传》主于“大义”,即阐发君臣等名分大义,《谷梁传》主于“微言”,即着意探究每个字中深藏的意义。比如庄公二十三年,《春秋》经文的记述是:“夏,公如齐观社。”这年的夏天,鲁庄公要到齐国观看祭社活动。这件事,《左传》是把事件的过程记录下来,并且详细记录了曹刿劝谏鲁庄公的言论:
夏,公如齐观社,非礼也。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
曹刿认为鲁庄公去齐国观礼不合礼制。国君无大事不得轻易越境出国,出国观社这件事不合于礼制,如果你一定要去,史书会把这件事记下来,因为“君举必书”。但记下这样一件不合于礼法的事,让后来人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不能立法于后世,这是一个很严重又很严肃的问题。同样对于这件事,《谷梁传》的解释则是:
常事曰视,非常曰观。观,无事之辞也,以是为尸女也。
它只是对原来的“经”文做了解释,经常做的事叫“视”,非正常的临时去看叫“观”,“观”是无事之辞,鲁庄公没有什么工作任务,为什么要去齐国?自然是为了去看美女。这自然是非礼的。这就是《春秋》“公如齐观社”一事的“微言”深义。而《公羊传》的解释则是:
何以书?讥。何讥尔?诸侯越竟观社,非礼也。
它探究的是《春秋》为什么要记录这件事,原因就是“诸侯越竟(境)观社,非礼也”,它对鲁庄公的否定,表达的是一种贬抑的态度,这就是“春秋大义”。从这里便可以看出三家传经的区别来。至于何善何否,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认识。今天大多人抬高《左传》而看不出《公羊传》和《谷梁传》的价值,这显然是欠周全的。
作 者:
刘毓庆,山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著有《古朴的文学》《朦胧的文学》《雅颂新考》《诗经图注》《从经学到文学》等专著二十余部。编 辑:
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