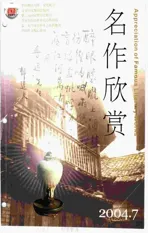我写作,因为我对世界有话要说(下)
2017-07-13北京徐小斌
北京 徐小斌
我写作,因为我对世界有话要说(下)
北京 徐小斌
《羽蛇》成为20世纪90年代末我的最后一部长篇。
写《羽蛇》这样一部小说的想法,从很早就开始了。也许,是从生命的源起就开始了。达利写过关于子宫的记忆,他说子宫的颜色如同地狱一样,它像火一样红,闪闪发光,喷着蓝焰,流动、温暖、黏稠,像两只煎好的金黄色的蛋。多么奇怪啊,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如果闭上眼睛,也常常能看到两个连在一起的金黄色的蛋,慢慢地向下飘去,渐渐从中间黑起来,变得如同日冕一样美丽,最后消失在黑暗中。
精神分析学认为子宫生活与乐园生活有关,而出生自然就是失乐园,因此出生注定是个悲剧。
我们是不幸的,生长在一个修剪得同样高矮的苗圃里,无法成为独异的亭亭玉立的花朵。为了保证整齐划一,那些生得独异的花朵,都注定要被连根拔去,尽管那根茎上沾满了鲜血,令人心痛。有幸保留下来的,也早已被改良成了别样的品种,那高贵的色彩在被污染了的空气侵蚀下,注定变得平庸。
我们又是幸运的,在当今的世界上,还有哪一国的同龄人可以有我们这样丰富的经历?童年时我们没有快乐,少年时我们没有启蒙,青年时我们没有爱情,中年时我们没有精神,老年时我们没有归宿──另一个世界的宠儿们闻所未闻的都曾经走马灯似的从我们年轻的眼前飞驰而过,那真是神话般的叙事,那一切都是发生了的,但是那一切却深深地镌刻在那个女孩以及许多同代人的记忆之中。
于是,在世纪末的黄昏,我们可以找出一张仿旧纸,在上面记下听到、看到和经历过的一切,立此存照。
死去了的,永不会复活。我们也不希望他复活,还魂之鬼永远是丑恶的。
但我们还是忘了,从所罗门的胆瓶里飞出来的魔鬼再也飞不回去了。我们把它禁锢了许多年,每禁锢一分钟,它的邪恶就会十倍百倍地增长。它的邪恶浸润在这片土地上。它毒化了这片土地。它充分展示了另一种血缘中的杀伤力与亲和力,那是土地与人的血缘关系。于是,在我们这个有了高速路、网络对话与电子游戏的时代,形而上的、精神的、灵魂的土壤却越来越贫瘠了。
而羽蛇象征着一种精神。一种支撑着人类从远古走向今天,却渐渐被遗忘了的精神。太阳神鸟与太阳神树构成远古羽蛇的意象。在古太平洋的文化传说中,羽蛇为人类取火,投身火中,粉身碎骨,化为星辰。羽蛇与太阳神鸟金乌、太阳神树若木,以及火神烛龙的关系,构成了她的一生。一生都在渴望母爱的羽丧失了其他两种可能性。那是融在一起的真爱与真恨,自我相关自我复制的母与女,在末日审判中,是美丽而有毒的祭品。
还有另一位母亲。那是烛龙的母亲。无论烛龙如何爱他的母亲,最终却也逃不过被彻底遗弃的命运。烛龙是因为爱他的母亲,才在暗夜中举起火把的,但是他的母亲却在恶魔的诱惑下,把他出卖了,贬黜了,把一棵生气勃勃的年轻的树,连根拔去,让他死在了异国他乡。在土地与人的血缘关系中,我们很想猜测烛龙在死前对他的母亲怀有的真实情感,但终于遗憾地发现,我们并不具备那么高超的想象力。
我们只记得烛龙最后说的话。他对羽说:“你看过《人与森林之神》吗?森林之神说,我们的智慧发轫之处,正是你的智慧终结之处。人回答,神话的时代已经过去,尽管没有神话的时代毫无魅力。”也许正因为这个,烛龙想改变,但是还没来得及,他就死去了。不想改变的羽也同神话时代一起死去了。而源远流长的若木,生生不息的、永远属于现在的金乌却结结实实地活了下去。与她们一起活着的,还有我们。
神话的时代结束了,但是母亲却是存在的,是母亲决定一代又一代的诞生。那象征着子宫的金黄色,出现在一代又一代孩子的童年记忆里,无论他们将来长成什么样的巨人或伟人或小人,他们都逃不脱血缘的维系,变了质的血使他们达到最远端的根蒂。在引渡的过程中,他们走向注定要遇难的航程,摆脱掉那些精神的、道德的、历史的、沉重的包袱,人的生命,变得如此之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要在有限的生命中获得快乐,必须忘掉灵魂的拷问。
──脱离了翅膀的羽毛不是飞翔,而是飘零,因为它的命运,掌握在风的手中。
所以我在题记中写道:世界失去了它的灵魂,我失去了我的性。
我写《羽蛇》,是在极端崩溃的状态下进行的,我不是不会哭的孩子,只是我的哭声无人听见。
据说,《羽蛇》在评“茅奖”时,第一轮就被刷了下来,原因是:没看明白。但我想,或者是看得太明白。
尽管如此《羽蛇》还是飞了出去,她被位于纽约的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签了,预付八万美金,我的代理人说:“你高兴一下吧,你的预付比张爱玲还高两万美金呢。”
《羽蛇》和五卷本文集出版后,我一直想写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后在一个类似“清宫秘闻”之类的小册子上,发现了德龄姐妹的一段轶事,上面写了她们曾经是现代舞蹈之母伊莎贝拉·邓肯甘愿不收学费的入室弟子。顿时兴趣大增。
读了整整一年史料,一百多本,资料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北图;二是故宫的朋友帮助搜集;三是各个书店,特别是故宫、颐和园等地的书店。在读史料的过程中我发现,有很多对历史人物历史场景的描写在历史书中是有问题的。譬如对光绪、隆裕、李莲英,对庚子年,对八国联军入侵始末,对慈禧太后当时的孤注一掷,对光绪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勇敢表现和之后的奋发图强,对隆裕和李莲英的定位等,都有很大出入。
历史背景是大清帝国如残阳夕照般无可挽回地没落,本身就是一个大悲剧,而在前台表演的历史人物包括慈禧、光绪、隆裕等都无一不是悲剧人物。在大悲剧的背景下的一种轻松有趣愉悦甚至带有某种喜剧色彩的故事,与背景之间的反差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张力。
君主制、君主立宪制与共和制的争论贯穿始终。甲午战争战败,大大刺激了年轻的光绪皇帝,他开始想变法维新,就在此时,康有为应运而生。戊戌变法是整个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运动,这一点历史越久远,就越明了。可惜只有一百零三天。假如变法成功,那么中国很有可能如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那样,突飞猛进。在变法过程中,光绪曾经当面顶撞慈禧太后,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胆量的!后来,根据容龄的回忆录,光绪的确在慈禧的千手千眼之下大胆问“康”,这都是史实,无数史实证明了光绪绝非懦夫,而是一个有血性有思想、勤政爱国的君主。变法失败后两年,便发生了庚子国变。在庚子年中,充分暴露了慈禧的无知、狭隘、专横、误国,她由于相信了荣禄提供的假照会,其中勒令皇太后归政一条,极大地刺激了她,她竟不顾清朝当时的国力,以卵击石,一方面怂恿义和团扶清灭洋,造成杀害德国公使克林德的惨案,另一方面竟敢同时向十一国宣战!并连杀了两名主和大臣,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入侵,此举无疑是把国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庚子年西狩,慈禧的确吃了不少苦,也有所反省,但她推行的所谓五年新政完全是掩人耳目,“国体不变,新政何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打败了君主制的俄国,完全说明了问题;而庚子年后,慈禧被洋人打怕了,由排外转为媚外,所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便是当时她臭名昭著的口号。就是这样,也没能抵挡住随后而来的侮辱:日俄大战的战场竟然在中国东北境内,这自然是堂堂中华的奇耻大辱!而这正是德龄姐妹进宫前后的历史背景。
无数志士仁人在寻找救国之路。主要是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主张共和制)和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主张君主立宪制),也就是被慈禧诬为“乱党”“逆党”的两派。尽管对他们的历史评价至今仍在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热爱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而表层的故事多以后宫为主,后宫以宫眷为主,女性占绝大多数,这样,表层就会好看。当然,后宫也很险恶,譬如慈禧与皇后联手杀掉四格格的侍女茧儿,对四格格敲山震虎,对德龄的多次试探,对容龄暗恋光绪的怀疑及对卡尔、怀特等的监视……都令人感到清宫中充满了陷阱。当然,在史实中,容龄爱的是一个太监,而德龄则暗恋光绪,德龄是在出宫后才认识怀特的,怀特并非牙医,而是当时美国驻沪副领事。
当然也写了慈禧人性的一面,这段时期是她真正的晚年,她害怕孤独,渴望亲情,即使这样,她也无法克制自己的多疑与乖戾。她其实至死没有真正的反省。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潮流谁也无法阻挡。她死后三年,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写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初衷,就是开创历史小说的一个新样式。让“历史”更加“小说”,让历史真正小说化,而不是那种板着面孔的历史小说。
这部小说一不留神就很畅销,很多人说:“这部小说有阅读快感。”
更多人对我失望,他们原本是希望我写羽蛇那种风格的小说。
但我写什么,不是任何人可以左右的。人的成长过程便是一个祛魅的过程。我对世事看得越来越开,我写了《炼狱之花》,笑着讥讽了黑恶势力,还笑着拿了一个加拿大的奖。
是的,我不再痛苦不再流泪不再自我折磨了。我真的长大了。
2016年4月我参加伦敦书展,获得了2016年度英国笔会翻译文学奖。
获奖小说叫《水晶婚》(中文版曾经刊于《天南》),写一个平凡女子从结婚到离婚的十五年,折射出中国这十五年天翻地覆的变化。后记叫《水晶婚:我的无泪之痛》。
按照西方批评家的分类,这部小说是绝对的女性主义写作。我写了我们所经历的两个时代:铁姑娘时代和小女人时代。
我曾经去过的北大荒,麦收季节,无论男女,都要扛着一百公斤重的麦包上跳板——试想一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扛着一百公斤的重物,还要走独木桥式的三米长四十五度的跳板,然后把麦包卸进粮囤里,今天想起来是不是很可怕?有很多女孩因此得了终生的疾病,也有很多女孩尽全力也无法完成,譬如我,被安排去背五十公斤的“尿素”,这是很受照顾了,但即使这样,我也几乎被压得吐血;夏锄季节更为荒唐,领导在动员大会上说,每人每天包一根垅,干不完,哭也得给我哭出来!要知道,黑龙江土地的“一根垅”,是整整七公里啊!那时我还只有十六岁,且患着严重的痢疾,中午老牛车送饭只能往人最集中的地方送,这就意味着我这个落后者永远吃不上中午饭,在那样可怕的劳动强度下生着病并且一口饭都吃不上,喝水都要把前面的水缸放倒,像小狗一样地钻进去,才能喝上一口已经见了底的满嘴泥沙的水。岂止如此,我们在特大涝灾中从齐膝深的水里捞麦子,在十一月的寒冬从冰河里捞麻,即使来月经也绝不能请假,三十八个女孩睡在两张大通铺上,在零下五十二度的寒冬没有煤烧,为了活下去,我们去雪地里扒豆秸烧,喝尿盆里的剩水——我至今吃惊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唯一的解释就是青春的力量吧,除此之外真的无法解释。
“铁姑娘”的时代终于过去了,但事情并没有因此变好,在今天,是一个地道的“小女人”时代,智商高不高无所谓,最重要的是要“情商”高,而中国式的情商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女人要懂得如何取悦男人,取悦上司。绝不能动真情,谁动真情谁就是输家。譬如我认识“70后”的一个女生,容貌中等偏下,身体还有缺陷,但她可以把几个男人同时玩弄于股掌之中,完全靠手段,什么时候需要谁,算得很精确,就像学过运筹学似的。她觉得自己就是胜利者,很以此为自豪。这类人不少,甚至有一批所谓精英女性都是如此。觉得自己很有生活智慧,譬如她们认为在情感中运用手段获取男性青睐,然后让自己在与男人的关系上掌握主控地位并从而获得更多的金钱财富是一件特牛的事。这种人被万千女生羡慕,被认为是高情商。
然而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严重的女性自我贬低和丧失尊严,甚至比“铁姑娘”时代更糟。
我笔下的女主人公杨天衣,无疑是个“低情商”的姑娘,她在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依然保留了自己完整的天性。这个在少年时代就深受中外爱情作品影响的女子,不幸嫁给了一个与她的价值观截然相悖的人,但她并没有服从命运的安排,她的内心一直顽强地爱着她所爱的,她无法改变她的爱情观。她也曾经遭遇“性的困扰”,但她终于懂得,她是一个无法把爱与性分开的女子,没有爱,她宁可守身如玉,也无法支配自己的身体去接受无爱的性。她与丈夫数度龃龉,矛盾日深,最后终于爆发,他们的婚姻维持了十五年,十五年的婚姻叫作“水晶婚”。
21世纪中期之后,在政治需要与纯文学越来越壁垒分明的时候,人的壁垒也越来越分明了。有些事想来真是非常好笑:有些人在多年前写过的北大荒,完全脱离现实,后来才知道他从一开始就当干部,根本没有下地劳动,但是在多年以后,他照样受宠爱:他嘴上说些貌似尖刻的话以博得众人喝彩,但是在利益面前他一样也没有落空——无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他都是精英;确切地说,他是披着精英外衣的变色龙,这种变色龙还不少:他们会在众人面前装清高,暗地里却为着争夺权力而到处送礼写信,他们会在微博微信中把自己装成一个忧国忧民的正派知识分子,然而摇身一变,早已暗中改变了身份。他们是绝顶聪明的人,同时也是制度造成的怪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是北岛的金句,这句话在中国可以一直沿用。
在《羽蛇》中,曾经借男主人公之口说:“……过去的十年把所罗门的瓶子打开了,魔鬼钻出来,就再也回不去了。经济的、物质的,都会有的,会腾飞,会赶上甚至超过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可是形而上的、精神的、人的一切……会一塌糊涂,这是最可怕的,这比贫困还要可怕。”不幸的是,在十八年之后的今天, 《羽蛇》中几乎所有的预言都应验了!
但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历史就是一个怪圈,一切都可以触底反弹。何况,在量子缠绕的今天,就更不必惧怕那些长袖善舞的衰人以及他们背后日益猖獗的黑恶势力,要知道,他们以出卖灵魂换取的利益,在八面玲珑中编造的春风化雨不过是一堆废物,他们貌似成为赢家的人生,不过是个零,甚至负数。
我写作,因为我对世界有话要说。
作 者:
徐小斌,当代知名女作家,一级编剧。主要作品有《羽蛇》《敦煌遗梦》《双鱼星座》《迷幻花园》《德龄公主》等。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在海外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