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燕郊致施蛰存书信九封(1981-1982)
2017-07-08易彬
易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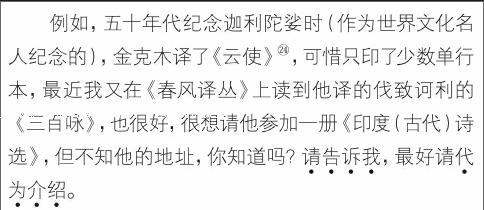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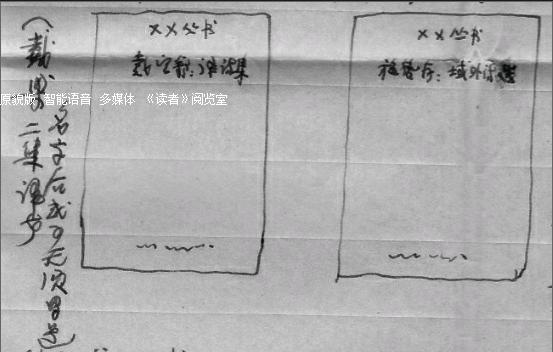
(一) 一九八一年九月四日
蛰存同志:
得到你的信,真高兴!
暑假我到长沙去了(离此一百二十华里),今夏大热,简直受不了。我估计你可能出去避暑去了,可我自己前天才回来,距你给我的信寄到之日已将近一个月了。
四次文代会a,日程太紧,我住北京市四所,和你们的住处相近,但也没法多去,只去一次,匆匆间见到王西彦、许杰、马宁、郭风几位,很多想见到的都没能见到,真太遗憾了。
但我在报上读到你的新作,引起很多感触。(不止对你一个人的)我之称你为前辈,自己认为是恰当的。我认为一个人的劳绩是不能(当然更不应)无视的,你为新文学运动作的贡献,应当得到应有的评价。而我呢,毕竟是得到你的教b的后辈中的一个。
出版译诗丛书,是我开的头,给他们提的建议,开始似乎还不那么热心(这些年人们提到诗就摇头,假、大、空泛滥之后果有如此者!),现在期待颇切,我也乐于帮他们“跑跑腿”,现在,得到你的援助,可庆幸处,岂仅得一忘年之知己而已。
译诗集计划以人名集,就带有“全”集之意了。我们的设想,某个人的译作,不管过去是否出过单行本,都要把它包括进来。望舒译洛尔迦,译恶之华,都是一绝,不可不收,这似乎也不涉及版权问题。最近看“人文”书目,洛集他们亦未列入重印计划。此外散见各处的译诗,我所保存的仅叶赛宁、《西莱纳集》c两组。今秋我拟去桂林查阅该地图书馆所藏报刊,我记得那里是有《星岛日报》(当年望舒在编“星座”时的)的,当可查到一些。资料搜集到后,当即寄到你处,请你编定。“人文”处,所拟出的全集,我估计不会包括译作,因译作成书者多达三十种上下,有些(如《弟子》、《紫恋》d)恐亦在一般人的视野之外。不过这只是我的揣测罢了。总之,如这里先出,也就没问题了。
你的译诗,我记忆最深的是《现代美国诗抄》e,我认为也是译诗中之一绝(你当可相信我辈中人皆不善于说不由衷之言的),其中不少诗(如《咏树》)后来有好几个译本(杨周翰等),平心而论,确都译得差些。我建议你把原计划的四册合成一集,使之全,读者必定会感激你的。过几天我到长沙,和他们具体商量好,再写信给你。至于篇幅多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另外,还有这些事要麻烦你告诉我:
1.《现代》上的陈御月,是否望舒的笔名?安簃是否你的笔名?f
2.我想建议把朱湘译的《番石榴集》列入译诗丛书g,需要找朱的家属,不知你知道不?有什么线索?
3.抗战前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于熙俭译的《邓肯女士自传》h,此书大可重印,但找不到于熙俭其人,你知道吗?
4.我很喜欢艾林·沛林,拟写一小文谈他的作品在中国的流传。抗战胜利后你在上海出的那套“域外文学珠丛”i(我没记错吧),我一直保存其中两种(《战胜者巴尔伐克》(?)《称心如意》)。文革乱后,已失去了,我明显记得其中是有艾林作品的,而且记得东欧小国短篇集,在你那套丛书中有三种或更多些。不知你手中还保存这些书不?能不能把尊译艾林作品篇目见示,(从周作人起到胡愈之、鲁彦直至解放后所译的,我大体有个眉目了)。介紹东欧短篇,我认为也是你的一大劳绩。
5.记得你在“珠丛”序言中曾提到你想过用“北山译乘”名这套丛书j,此名甚好。译诗丛书,你能代拟个名称吗?简截地叫“译诗丛书”,似乎不够味,我又想不出,只好向你再啰嗦一阵了。
开学了,想必甚忙。本期我没课,因而可以较自由些。你年事已高,千万多珍摄,不能不以此类琐事相扰,乞谅!乞谅!
盼赐复 即颂
健好!
彭燕郊
81.9.4
(二)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七日
蛰存同志:
得九月七日来信,大喜。十日回长沙(我家属还住长沙,距湘大一百二十华里),一是过节,二是找出版社的同志商量译丛的事,他们听到我所说的你的意见,同样大为高兴。现在他们正在定明年的计划,译丛事实上已列入计划了的,接下去的就是具体安排了。
你提出几点,都很中肯。望舒译诗集,就是个“洛尔迦诗钞”要不要收进来的问题了。我已去信绿原同志(他在人文外国文学部),请他代征求一下人文的意见。如他们不同意,也就算了。
集名依你所说,不用译者名集,我想了一下,确乎好些。如“洛”集不收入戴集,诗集用的不是他的名字,即不带有“译诗全集”的含意,也就较有回旋的余地了。但如朱湘的《番石榴集》能收进来,用原书名怕商务会有意见,去年这里出了李健吾的《福楼拜评传》,其实商务是不会再印此书的了,据说也仍然提出异议,理由是他们书店现在还存在。
丛书名确乎不宜太雅。“外国诗歌丛刊”(“丛书”似较能与目前的大型文学丛刊——实即变相杂志)有个分别,确较通俗,但目前此类名字的刊物(如外国文学丛刊、美国文学丛刊等)不少,用一个既通俗、又大方、又好记的名字,当更理想些,你看怎样?要我想,一时却想不出。
开本,如你所说的,甚好。但“百花”那套小丛书我未见到。我也喜欢诗集印雅致些,不要搞来堂而皇之的一大本。直行排,大约不可能,可以试着跟他们提一提。
绿原答允译一册“欧美现代诗选”,沈宝基在长沙铁道学院,他在写一篇论阿波里奈尔的论文,已译了十来首阿波里奈尔的诗给我了。他有个学生也在译。梁宗岱、卞之琳不知已回信给我了没有(我到长沙来了,信是寄到学校里的),其余的尚在联系。十二册当可无问题。
现在,可以确定的首先是你和望舒的、绿原的。请把书名拟定(你和望舒的)、篇幅大体上多少行。你看是不是一般在二百页上下为好,一百五十页似乎薄了些,厚一些倒没有什么关系。一般每页(横排)二十二行上下,用五号仿宋体。
望舒译的那几首叶赛宁诗,过几天我回学校,当即抄奉。
我想要知道你译了那[哪]几篇艾林·沛林?收在那[哪]本书里?我拟写一文,亟须你告知。艾林的其余译本,我大体上掌握了。至盼!至盼!
匆匆 祝秋好
彭燕郊
81.9.17
(三)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二日
蛰存同志:
你九月廿四日写给我的信我是三十日接到的,那天我就回长沙去了。一来是回家过国庆节,再则是译诗丛书的事,还有,此间办一民间文学刊物(名《楚风》,每期约十四万字,季刊)暂无人负责,我只好顶着k。在长沙共住十二天,译诗丛书的事已全谈妥了,明年一月开始出书,现在就得赶快些交稿。你的和望舒的,盼能即寄给我,如此,则出书可更早些。湖南人民出版社算是较有魄力的了,最近出版的鲁诞百年纪念集l,想亦已寄给你了。这样的出版物,国内是不多的。我们这套丛书,从内容到形式,我都想搞得尽可能好些。出版社也寄予较大期望。你的那本,能否也在200页上下?梁宗岱的,差不多也是那个样子(如收入莎氏十四行,当更多些)。
谢谢你把《艾林·沛林还历纪念》m寄给我。现奉上,请查收。《文心》想是孤岛时期出的刊物,不知后来还出不?这回回长沙家里,清理一个书柜时,竟又找到了《称心如意》,也够我称心如意了。这样,我写《艾林·沛林在中国》,资料就丰富了n。
梁宗岱同志有部《蒙田散文选》o,嘱我找地方出版,我是个好事之徒,又勾起了我多年就有的一个想法:能不能出一套“世界散文译丛”?郭风对散文很有劲头,他曾设想过编一套散文丛书,约我把过去的习作也整理整理p,但有几个月没接到他的信了,不知他近来怎样,大约工作够忙的。他那“榕树”,似乎也好久没出了。
如能出散文丛书,你和望舒的这方面译作,是都可以成集的。记忆中望舒在星岛日报(还有《华侨日报》,黄茅编付[副]刊)发表过不少巴罗哈的散文,用的是“江兼葭”这个笔名q。也译过阿左林。还有卞之琳和徐霞村也译过。现在的中、青年,是连这些作家的名字都没听说过的,水平怎能不日见低落?!
你寄给我的那本书,开本似嫌小了。现在流行印大三十二开(是否即过去的二十四开?),堂而皇之,实在也不好,但他们似乎认为要够“气派”才好。你的意见呢?丛书的名字,想来以“外国诗丛”为好,还未最后和他们商定。
《流冰》r我也藏有一本,但那译法,似乎太旧了,重印恐不会受读者欢迎。朱湘遗族尚未找到。绿原同志要我找徐霞村,我这两天就写信去。散文诗,我想还是不收入为好,如能出散文译丛,编进那里头似乎好些。巴金不知在上海不?久不见他露面了。邢译波氏散文诗s,确差些(石民也译过t),沈宝基同志最近在我的劝驾下,也译了一批,我给郭风寄去了。郭译《鲁拜集》u后来收进他的译诗集里去了。他的译诗,以此为最好。能找到好插图,单独印也是件大好事。可惜叶灵凤死了,找谁问这些事?
我所最怀念的一本译诗集是韦素园译的《黄花集》(开明版)v,如能找到就好了,你能帮忙找一找吗?我的一本,抗战时早已丢失了。
又:我藏有你的《追》w,不知你自己有没有?这次回长沙没找到。如你要,下次回去找出寄你。
盼早寄稿来。匆匆 颂
教安
彭燕郊
81.10.12
急于付邮,请恕潦草,此间每日只一班邮。
(四) 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
蛰存同志:
你好!
这些时我一直在等你的信和稿件。
《梁宗岱译诗集》已编好,卞之琳和孙用的译诗集正在联系中,他们对译诗丛书都很支持,很热情地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也提供了一些线索。
朱湘的家属正在找,北大中文系有个孙玉石同志是研究他的,可能知道情况。我已写信去了,还写了信让我在厦大的妹妹去找徐霞村,听说徐在那里工作。
你和望舒的译诗集什么时候能寄出?我希望最近就能得到。
“人文”将出一不定期的译诗丛刊名《外国诗》,这样,译诗或能兴旺发达一些了吧。他们可以为译诗丛书吹一吹风,这对我们也是个鼓励。
我想,丛书除了总结“五四”以来译诗成果外,也得努力组织力量译那些必要译而至今未译的重要作品,出版那些应出版而未出、或未认真地出版过的名作佳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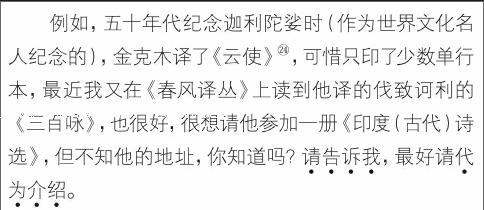
上海有沒有搞法国诗翻译的同志?龙沙,还有维尼,缪塞,拉马尔丁,我想都得好好译过来。又如塔索和彼得拉克,至今没译,真太遗憾了。你看能找到合适的译者作?
上次寄信时,忘记把你的埃林还历纪念一文寄上。这两天清积存资料,找出了抗战时你发表于桂林创作月刊上的一篇译文,一并寄上,请查收。
希望这几天就能接到你的信和书稿。
匆匆不尽 即颂
秋安!
弟 彭燕郊 上
1980.10.30y
(五)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蛰存同志:
有好多天我一直在等你的信,直到收到收到z你2日的来信@7收才安下心。接到你的信后我就决定上长沙来,那几天连接着又接到孙用、卞之琳、林林的信,更感到非快些来和出版社的同志商量不可了。你说周煦良同志译的霍思曼能加入我们这个译丛,这真是太好了,同时你又告诉我金克木同志的地址,这都得感谢你!这样,目前可以确定的就有这样几种了:一、戴望舒译诗集,二、你的域外诗选,三、卞之琳译诗集(题未定),四、梁宗岱译诗集,五、周煦良译霍思曼《西泼洛州的少年》,六、孙用译世界诗选(题未定),七、林林译《日本古典俳句选》,八、如金克木同志稿未被别处约去,则还可以有一本《印度古代诗选》了。这个阵容列出去,我相信是很可以的了@8。
因学校里有些事拖住了,我直到前天才回长沙。昨天到出版社,和两位负责同志就丛书事进行了较详尽的讨论,确定了:一、这套丛书可以先出第一集,十二种,以后陆续出。二、丛书要起一个好名字,我介绍了你想的几个名字,一时不能确定下来,请再想想。三、书名准备这样安排,让每本书有个同一的“规格”,初步设想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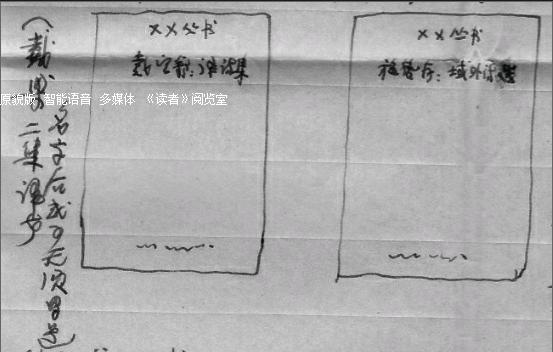
这样,对象[像]戴、梁(将来或有朱湘)的集子,保留了“译诗集”的书名,对别的译者,也可以用先列出译者名字的办法使之与他书一致。不知你以为如何?四、要有一篇总序。五、每集都要写一篇后记,后记中要写入作者介绍。六、封面、装帧要搞得好些,尽可能地好,要印一部份[分]精装本,如林林译的“俳句选”,他是对外友协的负责人之一,与日本俳人协会联系较密切,势必要拿一部分到日本去的。同时,也要考虑向国外发行。
给周煦良同志的信,请代转去,我热烈盼望他最近即把稿寄来。望舒那一部,一定要请你写篇详细些的后记。“洛尔迦诗钞”你原来写的,我想要保留下来。那篇译文是否保留,请你决定(我记得你译了一篇介绍洛尔迦的文章),十二月份务请把稿寄来。你的那一部,我希望至迟在明年一月份给我。金克木同志处我已去信联系了。
出版社有位同志问了罗念生同志,看罗的回信,似乎他可以代表朱湘家属。罗在信中说,朱湘的女儿,本来要由他抚养的,后来闻一多要去了。卞之琳已答允编一集。
房子事想已搞好了,这么大年纪了,还要为这些事折腾!近来想较舒适,亦一大好事。暇盼来信。即颂
文祺
彭燕郊
1981.11.14
又:《番石榴集》我藏有一册,但其中有缺页,将来必要时再向周煦良同志借抄。
(六)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七日
蛰存同志:
你好!
先得请你原谅,我上月十四日离校,在长沙停了几天,十九日到桂林。在广西第一图书馆查阅资料,昨(6)天才回到长沙。校里的同志把你上月十九日的信带来了。今天才能给你写信,已拖延十几天了。
译诗丛书你一定得来一本,一百二○页是薄了些,能加上一些新译是太好了。目前情况大体是:第一本先出望舒譯诗集,第二本出梁宗岱的。三本以下,视卞之琳、孙用、周煦良、朱湘、金克木、林林诸人稿到先后再定。这次在桂林,读到孙毓棠抗战时发表的《鲁拜集》@9,觉得不少比郭译好多了,很想写信征求他的意见,看能不能编入丛书。比亚兹莱的插图,浙江出的一文学插图集里有二十五幅,惜印得不算好。如找不到更好的,虽不太理想,也可以用的。朱湘遗族情况,据徐霞村说,可问罗念生。徐还说朱的儿子最近才落实政策回来,我拟写信去问罗,估计没什么问题了。林林译俳句,是用的你说的那种译法。曾见过两三种《万叶集》译文,用的都是中国的五言诗,确甚觉乏味。彭君所译,则未见到。
封面依你的意见,确较好。情况大约是这样两种:一种是“(戴)望舒译诗集”等,下面似无须再印译者名字,因如果朱湘的叫《朱湘译诗集》下面再印,似乎重复。一种是书名下再排译者姓名,如《霍思曼:西泼洛州少年》下面署:周煦良译。封面图案、色彩均统一,或图案统一而色彩略有不同,或图案风格统一而各有不同,均可。希望能找得一位好设计者。
我还想搞一本徐志摩译诗集#0。中山大学有位研究生,收集了五十余首,已可成集。如能编成,或请卞之琳写一序、跋。
你给望舒译诗集写的序跋不要太短了。“洛尔迦诗钞”我已问过绿原同志,他说他们不拟印,收进来没问题。还得打听一下有无“手续”问题。金克木有复信来,伐致诃利的《三百咏》人文已要去了#1。《云使》可以交给我们,但也得先问过人文。
“文苑”事,我一回来就拿着你写的计划和一位同#2谈了。他的看法和我一样,估计出版社没敢出它。杂志内容固应“杂”,但目前已有类似《名作欣赏》、《艺丛》之类的刊物了,且都无甚“苗头”。出版界是一股风的。此间有一大型文学丛刊,学上海的《收获》的,也是尽量登小说,迄无何起色,然他们乐此不疲,对于办“文苑”这样的刊物,却无兴趣。据说,目前读者倒是趋向于要求高级读物,且不怕“专”,有个趋势,译作的销量上升。最近出的《拜伦抒情诗七十首》初版八千册,很快就卖光了,就得重版。与上半年有所不同,广州一地,即有外国文学刊物四种。我看到的两种,内容很差,亦“一股风”也,但此风颇能说明问题。
明春我可能去北京,拟就便再到上海,希望能有机会去拜访你,到时当可海阔天空地长谈了。我也有些想法,恐亦不切实际,不过极想征求你的意见。
信寄挂号,是因为我们这里有时有些乱,多因孩子们集邮,有时连信也“集”去了,而邮票则以花花绿绿的为多。你那里该不是“大杂院”吧。此举亦颇是说明一个人年纪大了就有些过分小心。
在桂林借阅抗战时报纸,见四三年《新文学》杂志有你译的约翰·根室的《大使夫人》#3,借阅该刊,恰缺这一期。另有两篇,则是已收入《称心如意》的了。
不多写了,下次再谈。 匆此 即颂
文祺
彭燕郊
81.12.7
(七)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蛰存同志:
春节好!
十五日来信收到好几天了。我寒假前仍忙着一些琐事,到二十二日才离校回到长沙家里过春节。今天除夕,在家给你写的这信。
《望舒译诗集》我们当然希望能作为第一种出版。目前,梁宗岱译诗集稿已在我这里,正在写作者简介。每个作者都要写一短短的——二、三百字上下简介。同时得写一短跋,对译者也略作介绍——略侧重于译诗方面。梁老本人卧病已久,一时也找不到别人写,只好以“编者”名义写一写。另外想写一总序,也是以编者名义,不署个人名字,这样较好些。
拙诗有承奖誉处,内心甚为感奋,特别是你指出我的一个老毛病,往往恣肆为文,不善于控制自己(控制真是一个不容易的艺术)。另外,我从开始写诗就爱(语言方面的)散文美,欲从这条路上找出语言美的新路子,结果也带来了个毛病:不够精炼。友人灰马(三十年代在《新诗》上发表过诗作)说我“太不注意形式”,我认为他说得对,时刻记着他这句话。你说我那首《钢琴演奏》可删者至少在三分之一,可谓痛下针砭矣!我感谢你,我会永远记着的。愿以后能写好些。
我近来没时间写了,写了,也没时间去完成它,我写诗很少肆口而成的。总是觉得不满意,写诗很少给我快乐,只给我苦恼,并使自己对自己不满,或年纪大了,有以致之。
我们这些人都是饱经风霜的了,死了好几个,如今,既然还活着,当然想多作些于“四化”有益的事,其奈心有余力不足何!绿原序,有欲言又止之慨,其心情也不难想见。
此集#4在京发售,情况较热烈。王府井大街书店三天就卖光了,此间未到书,爱诗的朋友们时来打听,大约过些时才能到。如何发行工作环节也太多了。
望舒集,仍盼赶一赶。尊集,也盼接下去就赶出来。
劳荣集望寄来,可寄学校,因我过了年就想回去,下学期我有课,还带两个研究生,不能在家多停留的。匆匆不尽,盼复。即颂
文祺
弟 彭燕郊
82.1.24
(八)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蛰存同志:
我月初回校后,又到岳阳去开了十来天会,前天才回来。读到你的信,很高兴。在北京时,确曾打算过取道上海返湘,后来因种种原因改变了计划。不过,今年内我总要到上海一次的。张式铭同志告诉我你精神十分健朗,在京时,刘北氾同志给我看了你的近影,确实很健朗,依稀仿佛,尚存当年风采(那是在战时的永安,我还是个小青年,在路上见到过你,你当然不认得我)。我到上海,目的之一是约稿。“诗苑译林”第一批四种,出版社说就要付排了,或已付排。望舒集,当照你的意见,将道生的那两首仍编进去。这次寄来的《瓦上长天》#5是原来就有的。另外那几首,我想到图书馆去找找看,象[像]《文学周报》这样的杂志,应该是好找的。现在是大热天,你当然要多休息。秋凉后,望能把《域外诗抄》编起来。“外国散文译丛”仍望你给予支持,我想,以《域外文人日记抄》#6为基础,再加上历年所译,也甚有可观了。如编辑事务,特别象[像]抄稿,找资料等,只需你开个目录,可以要人去作的,请先考虑考虑吧。罗念生同志已允编一《希腊罗马散文选》,另介绍了一本培根的,一本琉善的#7。我看是可以搞得起来的。这件事希望你多支持,除了你自己的之外,给我们出主意,介绍稿件或提供线索,至盼!至盼!
湖南是大陆性气候,到现在这时候,稻谷成熟,乡里人所谓“发南风”天气,大刮热风,非常难受。上海是沿海,入夜就凉快了,而这里最难过的是从黄昏到午夜,真不得了。暑假,你得多多珍摄,能搁下来的就搁一阵再说吧。余容再叙。即颂
夏安!
彭燕郊
80.7.22#8
(九)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蛰存同志:
十五日的信收到好几天了,恕迟复。你要我把望舒译诗集抄个副本给你,我们研究了一下,一时怕抄不出来,因为有五百多张稿纸,抄很费事。且书已发排,尽管印刷厂生产能力差,我们去催一下,我们可以请他们多打一份样子给我们,再寄给你,这样比抄一道要便捷得多。
现在,我把你寄来的望舒译诗底稿先寄给你,我认为这都是十分珍贵的资料,放在我这里,我生怕搞坏了。请你收到后再清点一道,看有缺的没有,很可能忙乱中搞错了放到另外个地方(因同时处理几部稿子),还可以找的。
你的《域外诗抄》务必在明年一月一定交稿,千万!千万!你所听说的译诗销售情况不确。目前文艺刊物确在大跌,有的省级刊物已跌至几千份。不过他们反正有公家的钱可贴,无所谓的。目前读者兴趣转入“高档”读物,译诗已是属于“一上架就喊再版”一类。(“上架”指在门市部开始出售)所以出版社乐于印较高级的读物,虽然初版往往因书店不肯多进货而印数偏低,但很快就再版,可以不断地印,反而不怕蚀本的。
望舒译的散文,“人文”集中未列入译作一项(译诗除外),你如没有时间,可否给提供线索,让我要我的助手到北京图书馆或上海图书馆去查阅旧报刊,抄下来再编成集,你的,也同样由他去找去抄,再编起来。“外国散文丛书”一定要搞,出版社劲头不小,我以为不妨促一促。资料找齐了,你再动手编定一下,也不费你太多时间。这事,希你能俯允。我们将非常之感谢!
嘱转信,我未转去。此等事,以不了了之为最好。此间似又进入一热潮,我们系里要提为付[副]教授的有十一人,占比例很重,其办法是由两个“专家”对科研成果写出鉴定(有印好的表格一类的东西)。事关重大,我是愧乏菲才,谢绝了。当然,这是个很有意义的工作,去年我参加省里的评审工作的一大部分,结果发现此等事不是象[像]我这种条件的人所能胜任的,颇后悔不该去参加,当然是个工作,不参加也不好,为此陷入矛盾、苦恼之中。……凡此琐琐,实不足为长者道,闲谈而已,当不见怪。
一写,又写了这么多。盼来信,祝
教安!
弟 燕郊
82.9.27 晚
整理说明:(1)格式。对书信格式做了大致统一的处理。(2)标点。原信没有书名号,涉及书名、丛书名处均作双引号。整理时,凡书名处,用书名号;丛书名处,如译诗丛书,用双引号。也极少数标点(逗号、句号、括弧)明显用错的情况,径直改正。(3)书写。有一些书写习惯(如“哪”作“那”)或书写错误,一般即在正文中用[]标示出来(如“那[哪]”),情况更复杂的则用注释说明。
【注释】
a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于1979年10月30日到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按:施蛰存先生也参加了会议,但目前并没有彭燕郊当时与其会面和交往情况的记载。
b此处“教”后疑有脱字。
c[法] 特·果尔蒙著、戴望舒译:《西莱纳集》,《现代》第1卷第5期,1932年9月。
d[法]蒲尔惹:《弟子》,戴望舒译,中华书局1936年版;[法]高莱特:《紫恋》,戴望舒译,光明书店1935年版。
e1934年10月,《現代》第5卷第6期出版“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其中有施蛰存译《现代美国诗抄》30首。《咏树》为乔也斯·凯尔默(Joyce Kilmer)的作品。
f陈御月为戴望舒笔名,安簃为施蛰存笔名。
g朱湘选译的《番石榴集》 (商务印书馆,1936年) 收入古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希腊、罗马以及意、法、西、德、俄、英等国诗作数十首。“诗苑译林”丛书后来出版洪振国整理加注、罗念生作序的《朱湘译诗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hIsadora Duncan:《邓肯女士自传》,熙俭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i1948年9月,施蛰存的三种译作《丈夫与情人》 (匈牙利莫尔纳著)、《称心如意:欧洲诸小国短篇小说集》 (原名《老古董俱乐部》)、《胜利者巴尔代克》(波兰显克微支著),列入上海正言出版社“域外文学珠丛”。该丛书原计划出版10种,但实际上仅出三种。参见沈建中编撰:《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70页。
j1945年10月,施蛰存译作东欧诸国短篇小说集《老古董俱乐部》,列入福建永安十日谈社的“北山译乘第一辑”,书末刊有广告“北山译乘第一辑——施蛰存先生选译”,参见沈建中编撰:《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第522页。
k彭燕郊当时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湖南分会副主席,前信提到参加全国四次文代会,彭燕郊的身份为民间文艺工作者。
l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m施蛰存:《艾林·沛林还历纪念》,《文心》第2卷第4期,1940年2月。
n此文后来未见写成。
o梁宗岱译法国作家蒙田的 《蒙田散文选》曾连载于郑振铎编辑的 《世界文库》 (生活书店发行)第7-12册,1935年11月至1936年4月。
p彭燕郊的散文诗集 《高原行脚》,后收入郭风主编“曙前散文诗丛书”,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q经多方询问,“江兼葭”很可能是“江兼霞”的误记或误写。“江兼霞”这一笔名比较复杂,可能是戴望舒、施蛰存等人合署(另一个笔名“江思”,情况类似,也是戴、施等人合署)。
r[苏]查洛夫等:《流冰 新俄诗选》,画室(冯雪峰)译,水沫书店1929年版。按:1983年2月,施蛰存作回忆文《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 (《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其中谈到了《流冰》。
s[法]波多莱尔:《波多莱尔散文诗》,邢鹏举译,中华书局1930年版。
t[法]波德莱尔:《巴黎之烦恼》,生活书店1935年版。
u应是指郭沫若所翻译的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郭译本的版本较多,最早应是1924年的泰东书局版。
v韦素园译:《黄花集》,北新书局1929年版。按:此书所录为俄罗斯的散文和诗歌作品,作者有契里诃夫、勃洛克、都介涅夫、科罗连珂、戈理奇、蒲宁等等。
w可能是指施蛰存小说集《追》,初版为水沫书店1929年版。
x[印度] 迦梨陀娑:《云使》,金克木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按:该书印五千册。
y“1980.10.30”属误署,邮戳显示,寄到上海的时间是1981年11月2日;同时,信中有“埃林还历纪念”以及戴望舒、施蛰存译著方面的信息,故时间当为1981年。
z此处两个“收到”,当是误写。
@7此处宜有一个逗号。
@8这里所提到的翻译人物,“诗苑译林”丛书后来出版了戴望舒译《望舒译诗集》 (1983)、施蛰存译《域外诗抄》 (1987)、卞之琳译《英国诗选》 (1983)、梁宗岱译《梁宗岱译诗集》 (1983)、周煦良译《西罗普郡少年》 (1983)、孙用译《译诗百篇》 (1988)、林林译《日本古典俳句选》 (1983)、金克木译《印度古诗选》 (1984)。
@9孙毓棠译:《鲁拜集》,《新文学》1卷2期,1944年。
#0“詩苑译林”丛书后来出版徐志摩译、晨光辑注:《徐志摩译诗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1金克木译:《伐致诃利三百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同”后应是有脱字,看起来,应是“同志”或“同事”。
#3约翰·根室:《大使夫人》,施蛰存译,《新文学》第1卷第1期,1943年7月。#4当是指绿原、牛汉编:《白色花:二十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5指戴译法国诗人魏尔伦的诗歌《瓦上长天》。
#6施蛰存编译:《域外文人日记抄》,天马书店1934年版。按:该书收入曼殊斐儿、托尔斯泰、乔治·桑等七人日记。
#7彭燕郊筹划、组稿的“散文译丛”后来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代中段出版了数种,其中有罗念生编译的《希腊罗马散文选》,1985年。
#8“80.7.22”属误署,信封上的邮戳显示,寄到上海的时间是1982年7月25日;同时,结合信中“诗苑译林”付排的细节,可确定为198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