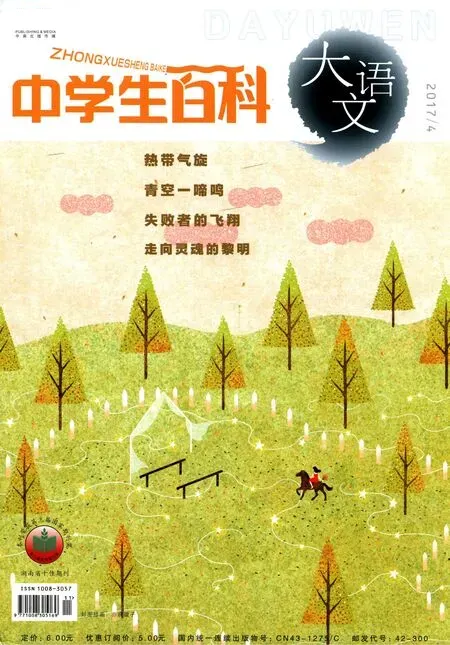觉醒
2017-06-28文丨王瑞琪
文丨王瑞琪
觉醒
文丨王瑞琪
东半球睡去,西半球醒来。
——题记
词典上的觉醒被给定了一个过于简洁的释义:多指自错误中醒悟。但事实上,觉醒远不止这么简单。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懂得一个小道理,掌握一种知识,却很难真正地发现自己。泰戈尔说过:怀中的水是清澈的,海中的水却是黑色的。小道理可以用文字来讲清楚,大道理却只有沉默。觉醒亦难被吝啬的三言两语解释清楚。
我们一生中破晓的日子那么多,可这么多次自混沌中醒来,却没有几次可称为觉醒。
物以稀为贵,觉醒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经历。
但若有了那么一次,我们将迎来新生。
诗人在写下自己的第一行诗句之前,不会为其间的平仄韵律、隐晦比喻苦苦纠缠。他须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其中蓄满了饱和的情感,再有某件触目的事物做引子,诗酒才能愈酿愈香。诱引他写下处女作,觉醒的使命才完成。
这不同于醍醐灌顶的迅疾,而是一段缓缓蓄势的过程。卡尔维诺曾说:“我对一切即兴、迅速、含混、出自本能、唾手可得的事物没有信心,我相信缓慢、平和、细水长流的力量。”觉醒便有这样的力量。
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同的人接受着同样的教育和思想,追求着“钱、名、权”这几个关键词,努力做了别人眼中的完人,却永远地错过了自己的人生。他们混沌的一生模糊到没有自己的身影与念头,困乏到从来没有力气找寻自己的天赋。
英国也曾有过这样一个完人—— 一个伦敦证券经纪人,拥有他人眼中优裕美满的生活:婚姻幸福,收入可观,孩子健康。这是多少人穷尽一生奋力追逐的生活。但我们的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并不在乎如何将生活的面包做得更大更香,而是毅然地选择了自己应过的艺术人生。他说:“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他的觉醒未必风平浪静,但我想塔希提岛的月亮一定比满地的六便士清澈。
那些看不见色彩的人认为这个痴狂的画家疯了,正如尼采所言:“那些听不见音乐的人认为那些跳舞的人疯了。”觉醒的人不能叫醒装睡的人,清明地昏晕是遁世的逃避,而觉醒是一种直面自我的勇气。
我曾不止一次被一位老师问了如此几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儿去?
简单的问题却没有简单的答案,或许在重重逼问之下我会找到觉醒的那条路。错过了自己的天才,生命将是一场浪费,台湾作家刘凯如是忠告青年。赢得面包的路有很多,但适合自己的未必是最平坦的那条,不要因贪恋安逸而荒废了脚力,能攀上高峰就不要和大多数人一起在平原沉沦。我们的眼中固然有树木,心中也要能装下森林。
登顶珠峰的人不止于第一个,觉醒的人也定能将混沌一点点染净。东西半球昼夜交替,我们不能永远醒着,但也不会一直在黑夜中昏睡。醍醐灌顶带来的是一次性的冲撞,缓慢平和的觉醒才更富有感染力。每一个美好的早晨,都是从第一个苏醒的人那儿开始;整个社会的觉醒,要从第一个觉醒者开始。
去听自己的声音,用丰富的内心摆脱这些生活表面的相似。觉醒不是脱离现实,而是不去一味地服从现实。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更有诗和远方。
觉醒的人在通往远方的路上。

点评
日日破晓睁开眼睛,算是一次次醒,但在作者眼中,这不能称之为觉醒。那么,如何才是觉醒呢?觉醒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经历,它的出现让人有新生之感;觉醒是一段缓缓蓄势的过程,具有缓慢、平和、细水长流的力量;觉醒是一种直面自我的勇气。作者层层推进,以一种从容的行文姿态,一步一步地丰富着觉醒的内涵,所以读者阅读的过程,也就变成了一点点被唤醒的过程。而作者也似乎意识到读者的存在,于是自事理的剖析中走出,开始关注“我们”自身,强调个人的觉醒对于社会的意义,即“整个社会的觉醒,要从第一个觉醒者开始”,也在觉醒上对“我们”做了精要的指导,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更有诗和远方。”
这样,作者从觉醒的相关内涵和相关内容开始,明确概念,又不拘泥于其中,从而给予我们一场思想上的洗礼,以及对生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