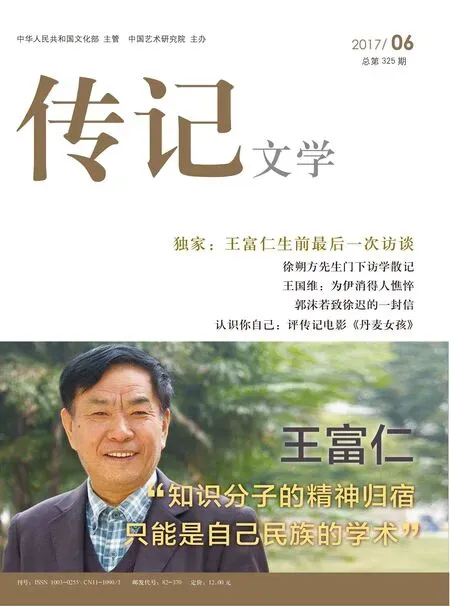忆恩师徐朔方先生
2017-06-21张梦新
文|张梦新
忆恩师徐朔方先生
文|张梦新

自2007年2月17日(农历丙戌年除夕)徐朔方先生离世至今,已经10个年头,但先生的身影却时在脑海。特别是随着自己也从中年步入老年并退休离开讲台,暇时回想以往与先生相处并受教的情景,他的音容笑貌更是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位教学认真、直言不讳的严师
我是杭州大学附中1966年高中毕业的“老三届”,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支边黑龙江,在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经过参加共和国历史上唯一在冬天进行的高考,通过初试与复试两次考试,与来自全省各地的140名学子进入了杭州大学中文系。
我对自己能在而立之年迈入大学校门深感庆幸,更对母校杭州大学和中文系充满了感激之情。杭大中文系,这个拥有姜亮夫、夏承焘、王驾吾、胡士莹、任铭善等著名教授的百年老系,人文荟萃,名师辈出,在“求是育英”的这方圣土上培育了一届又一届的优秀学子。在我们77级求学的四年中,除了王毅、陆坚、姜新茂这些系领导,姜亮夫、王驾吾、吕漠野、蒋礼鸿、沈文倬、刘操南、徐朔方、吴熊和、蔡义江、郭在贻、王元骧、王维贤、倪宝元、陈坚、郑择魁、朱宏达等老师,都为我们上过课。
77级汇聚了从1966届到1977届共12年的优秀毕业生,当时全国570万考生仅录取了27.3万人,而浙江由于当时高校较少,30余名考生中只能录取1人,我们杭大中文系77级的学生更是百里挑一。因此,杭州大学和中文系的领导对于77级的教学和培养分外重视,当时担任77级教学任务的老师,都是富有教学经验的老师,而且系里采取的是拼盘式教学。
以古代文学课为例,上《诗经》《楚辞》等先秦文学的是刘操南、平慧善先生,上两汉文学的是孔镜清先生,上隋唐五代文学的是吴熊和先生, 上中晚唐和北宋文学的是邵海清先生,上南宋文学的是陆坚先生,上元明清文学的是洪克夷和平慧善先生。
徐朔方先生给我们上的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初见先生,只见他身材中等,面色红润,神色严峻,双眼炯炯有神。当时虽已50多岁,但上课时嗓门洪亮,中气十足。先生上课从不照本宣科,每次上课,总是只带几支粉笔,作家、作品都烂熟于胸,娓娓道来。其讲课内容丰富,见解精到,颇能发人深省。记得上完陶渊明的诗文课后,先生布置了一次书面作业,让我们对陶渊明的诗文写一篇评论或赏析。下一次上课伊始,徐先生一连报了10个人的名字,我也在其中。先生让我们报到名字的同学都站起来,众人不知就里,都忐忑不安,整个大教室鸦雀无声,但结果是虚惊一场,先生说这些同学的作业是做得比较好的,表扬了我们。而正当大家的心情放松下来时,只听得先生话锋一转,又点名批评了某位同学作业不认真,还特别指出这位同学竟然把陶渊明的“陶”写成了桃子的“桃”。这次作业讲评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但对同学们的触动很深,大家都领教了先生的“厉害”,从而更自觉认真地完成他布置的作业,经常到图书馆翻阅相关资料,到资料室查看文献和论文,尽可能把作业做得内容丰富、材料充实,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包含自己的见解。
此后,我们又从与任课老师们的接触闲谈以及从图书馆、阅览室的文献、论文中,逐步加深了对先生的了解。先生生于1923年,本名徐步奎,浙江东阳人,毕业于浙江大学。1956年4月8日,先生的文章《〈琵琶记〉是怎样的一个戏曲》在《光明日报》副刊发表。同年夏天,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京、沪、穗、渝、杭等全国文艺界和高校专家学者在北京举行《琵琶记》大型研讨会,当时还只是一名青年讲师的徐朔方大胆鲜明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舌战群雄,被封为否定派的主将。研讨会的第三场讨论会记录说:“徐朔方同志的发言引起大家很大注意。他对《琵琶记》的看法和前两次会上发言的同志的意见不同。他认为在《琵琶记》这部作品中有很多封建说教的部分。”在第六场讨论会的会议记录中说:“负责这个小组讨论的是黄芝冈、王季思、徐朔方三名同志。会上,徐朔方同志和他的老师王季思教授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三位同志——侯岱麟、顾学颉、陈北鸥先后发表了他们对戏剧中典型意义的看法,并对徐朔方同志的意见提出了反对意见。”
从这两段60年前关于《琵琶记》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记录文献中,我们见到了时年33岁的徐朔方不惧权威、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胆识和独立不倚的个性。而这种唯实求真、坚持学人本色,不随波逐流、保持士子风骨的学术胆识,是先生获得丰硕学术成果的重要原因,也是他留给莘莘学子与世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先生曾称赞77级是他教过的最好的一届学生。这一评价,成为了我们杭大中文系77级学生的骄傲。
一位循循善诱、严格而慈爱的导师
1982年1月,我从杭大毕业后,幸运地与费君清、颜洽茂等多位学友留在中文系任教,并有幸在1984年4月被任命为中文系的党总支副书记,先后在郑择魁先生和吴熊和先生两任系主任的带领下,为中文系的发展尽己绵力。而到1988年,因杭大恢复了新闻系建制,我被调去与张大芝、邬武耀先生等创建新闻系。1995年春,受到当时校长沈善洪先生“博士工程”的鼓励和鞭策,我继张涌泉、颜洽茂、费君清三位学友之后报考了古代文学博士生。因为此前我曾费时数年整理出版了一百多万字的明代文学家茅坤的诗文作品《茅坤集》,于是想把茅坤研究作为今后的博士论文题目。另一方面,因为本科阶段听过徐朔方先生的课,又于留校后与先生同在中文系6年半,耳濡目染,深为先生的学问和人品所折服,于是鼓足勇气,报考了先生的博士生。
先生的试卷很难,知识覆盖面很广,因为四卷本的《中国文学史》和六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的内容基本没有出重过一道题,因为自己毕业后一直担任古代文学和大学语文的教学,业余时间阅读了较多的古代文学作品与文献,又对先生的专著和论文有一定的研读,所以还是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幸运地成为先生的入门弟子。当时我已47周岁,继30周岁时“抱着儿子上大学”(这是《钱江晚报》2007年5月17日在恢复高考30年之际对我采访后刊登的一篇专题报道的题目)后,又创造了杭州大学的一项纪录:最大龄博士生。
当时我忝任杭大新闻系的党总支书记,还要担任新闻系本科生的古代文学课与研究生的古代文学和新闻写作等课程,日常工作较为繁忙,博士生又有外语学习与测试等要求,加之当年我母亲去世,所以感到精神压力很大。先生为此多次找我谈话,他喜欢散步,有时我们沿着徐先生居住的杭大新村宿舍的小路,有时在西溪校区的林荫道上,有时则沿着宝石山的登山石阶边走边聊。先生和我谈课程、谈学术,谈我的学位论文的框架结构和内容章节,也与我交换了如何处理好学校工作与个人读博关系的一些看法。在先生的循循善诱和与先生的亲切交谈中,我焦虑的心情得到了舒缓,对攻读博士学位也增添了信心。
先生194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外语系,1981年评为杭州大学教授,是“活跃于中国文史学科教学与研究第一线的屈指可数的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之一”(著名学者、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语),他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因此,他要求我们也特别严格,每周都要指定阅读书目。
我虽然读的是元明清文学,但先生决不让我们只读元明清的典籍和文献,《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史记》《汉书》、唐宋八大家的原著等都要求我们精读。读后不但要做汇报,还要完成先生布置的作业。当时我住在西溪路杭大新建的教师宿舍,与先生的宿舍相距只有四五百米,先生就每月数次叫我,有时还有另一名博士生吴敢到他家中学习。有时是听先生讲,有时是让我们读一段他指定的原著,然后先说译文再谈体会;有时则是让我们阐述某一问题或作业,然后他与我们一起交流讨论。这样的座谈式、互动式和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循循善诱,很能提高我们的学习主动性和独立思考能力,让我们受益匪浅。
在我的博士论文撰写过程中,先生也耗费了大量心血。记得是1998年的春节,大年初二清晨6点多钟,我还躺在被窝中,我家的房门突然被人咚咚咚地敲响。我吃了一惊,赶紧披上棉衣就起了床。打开房门,我惊讶地发现竟然是先生站在门口。他手拿一卷线装书,兴奋地对我说:“我发现了茅坤的几首轶诗,你快查对一下,是否可以写入论文。”面对满头白发、手拄拐杖的导师,我的心灵被深深感动了。就在举国欢度春节的日子里,年过七旬的先生竟还在手不释卷地学习。茅坤的《初过湖上逢雨》《由湖上归抵家再赋》等15首诗,是先生在查阅归安陆心源所编穰梨馆《过眼录》卷二十二《茅鹿门诗翰册》时发现的,为《茅坤集》所未收。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先生提供了新发现的15首轶诗,更是因为从他大年初二清晨冒着严寒大驾枉顾我家所体现出的对学生的深切关爱,以及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
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与督促下,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茅坤研究》得以完成,并于1999年6月顺利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专程来杭,担任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2001年9月《茅坤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又于2011年获得浙江省高校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和浙江省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其中饱含了徐朔方先生和章培恒先生的心血。

徐朔方著《晚明曲家年谱》书影
一位鞠躬尽瘁、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
先生一生勤奋治学,十分严谨,是一位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他早在1954年就在《文学遗产》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了《论〈西厢记〉》等论文,1956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论著《戏曲杂记》。60岁以后,先生又先后出版了《论汤显祖及其他》《史汉论稿》《元曲选家臧懋循》《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沈璟集辑校》《晚明曲家年谱》《汤显祖评传》《小说考信编》《元明清戏曲经典》(《汤显祖全集笺校》《徐朔方说戏曲》《南戏与传奇研究》《古本小说集成》《明代文学史》等。而且更令人惊叹的是,先生几乎每年还有数篇高质量的论文问世,而这一切,还都是在承担着繁忙的教学任务和指导多名研究生的工作之外完成的。
在这里,囿于篇幅,我只简单介绍一下先生《晚明曲家年谱》和《明代文学史》的情况。
《晚明曲家年谱》共录明代戏曲家年谱39种,收入1993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徐朔方集》之中,分为年谱、行事系年和事实录存三类,又因为曲家籍贯之异而分为苏州、浙江、皖赣三卷。中国古代戏曲作家的地位大多低微,相关资料十分缺少。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写《汤显祖年谱》起,就一直大海捞针般地努力搜寻有关曲家的资料。经过30多年的艰辛,爬罗剔抉,披沙拣金,终于完成了《晚明曲家年谱》这部巨著,勾勒了39位晚明曲家的生平及创作系年,为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研究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材料,也为研究者树立了熔史料考证、理论思考和艺术分析于一炉的年谱范本。
而《明代文学史》的前期准备加后期写作更是历时40余年。1962年,身为讲师的先生接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来信,约他编写《明代文学史》。虽然以后因种种原因,此事搁浅了,但是撰写《明代文学史》的念头一直萦绕在先生心中。先生“大胆地认为所有名家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或断代文学史有一个通病:编写者在执笔之前并没有通读他所论述的全部作家作品”,因而坚持“编写文学史应该将所编时期所有的作家作品巨细无遗地全部加以阅读研究”。为此他千方百计地阅读了大量的明代典籍及作品,写卡片、做索引,做了极为充分的准备。
终于,在距1962年几近40载之时,《明代文学史》被立为了国家“九五”社会科学重要项目。此时先生已近80高龄,健康水平已大不如前。要阅读卷帙浩繁的明代典籍,写成一部文学史,任务的艰难可想而知。特别是2000年先生的夫人宋珊苞老师身患重病,并不幸于是年12月17日去世。暮年痛失老伴,这对先生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先生的一位公子徐礼杨在美国,另一位徐礼松在北京,无法照顾他的生活。但先生不坠青云之志,一心为完成《明代文学史》而勤奋工作。
2001年6月,承蒙省民政厅余刚学友的帮助,我和先生的首位博士弟子廖可斌把先生送进了古运河边的杭州福利院,以便解除他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但先生却把他的房间变成了撰写《明代文学史》的工作室。不足20平米的房间内有两张床,一张床上堆满了书,一张床上铺满了书稿与卡片等资料;桌子上则放着几只饭碗、茶杯和许许多多的药盒与药瓶。由于患有高血压、高血脂、胰腺炎等疾病,加上写作的劳累,当时年近八旬的先生健康状况已经很差,每天都要吃药、打针和治疗;老年性白内障,又使先生的视力非常差,但他硬是用颤抖的手,坚持每天从早到晚、字斟句酌地修改着一页页书稿、一句句文字、一个个细节。值得庆幸的是,此时访问学者孙秋克副教授来到先生门下访学,在先生的主持与指导下,孙秋克积极协助徐先生努力工作。终于,历尽艰辛,80高龄的先生在2003年春天写成了《明代文学史》的初稿,完成了他多年的夙愿。这部煌煌42万余字的巨著,于2006年6月在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基金和浙江省社科学术著作出版资金的资助下,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封底印着四行字:“著名学者徐朔方教授在明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结晶;全国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优秀成果;一代国学名师与后辈学人共同打造的力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倾力推出的学术精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鉴定专家认为该成果是“迄今所见明代文学史著作中学术性最强、特色最明显的一部”,“将明代文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2003年7月26日,先生因跌伤住院治疗,虽经多方救治,但一直昏迷不醒。2007年 2月17日,丙戌年除夕下午4时45分,徐朔方先生鹤驾西逝,享年84岁。《明代文学史》,这部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就成了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巨著;而先生这种对学术至死不渝的执着追求,更为我们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徐朔方与家人在一起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