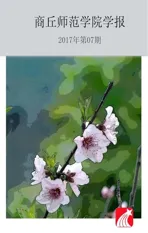论道家的语言传播
2017-06-19詹石窗谢清果
詹石窗 谢清果
(1.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610065;2.厦门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福建 厦门361005)
论道家的语言传播
詹石窗1谢清果2
(1.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610065;2.厦门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福建 厦门361005)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术流派,道家学派向来重视语言传播。老子率先提出“正言若反”的命题。从最终效果看,“正言”是能给人带来益处的,是有价值的。因此,说话要讲究效用性,不说空话、假话、大话。为了保证正言能够成为信言,道家提出了“希言守中、言必有宗、善言无迹、名止于实、得言必察”的传播原则。道家除了注重语言传播的真实性之外,还关注传者与受者间的顺利沟通的方式方法,坚持“通畅性”原则,即“善”的原则,因此采用了一套道家独有的话语系统,这就是庄子学派所概括的“寓言”“重言”“卮言”。道家运用寓言、重言、卮言等语言传播方式,以期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而更为重要的是,道家特别注重语言传播的价值理性和审美意境,那就是沉浸于“道”的体悟之中,忘我、忘言,这实际上生成了悟性之境,也就是语言传播的大善效果。
道家;语言传播;求真
任何一个学派都有自己的思想。要使思想发生影响,必须通过传播来实现。传播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语言传播是最为关键的。道家通过“言”与“实”“意”关系的阐释,表达了语言在传播中应当秉持真、善、美价值取向的立场。道家以“道”为自己论说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且认为“道”集真善美于一体,非真不足以言道,非善不足以证道,非美不足以体道。就传播角度而言,真是传播的出发点,无论是传播内容,还是传播主体心态,都应当有精诚之真。善是传播过程顺利进行的法宝,因为在传播中会发生诸多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自我身心的关系等,所以传播当以“德交归”(《老子》第60章)为善;换句话说,传播活动当“道法自然”,即顺应自然、社会、人生之本性,而无所忤逆。美是传播效果的评判原则,美是一种超功利的感受。鱼儿与其有“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之悲壮,不如彼此体验“想忘于江湖”之乐。道家认为真正的传播当如没有传播一样,正所谓“至言去言,至为去为”(《庄子·知北游》)。
一、正言、贵言、信言:语言传播主体的求真意向
语言包括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亦即交谈中的言语和静态的文字。语言和文字的使用表明人是一种符号动物,也标志着人的社会存在。正如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Edward)所说的:“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做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正常的言语之外,其他一切自主的传达观念的方式,总是从口到耳的典型语言符号的直接或间接的转移,或至少也要用真正的语言符号做媒介。”[1]19也就是说,语言是人类传播中最完善的符号系统。人作为社会关系的存在,语言传播则是维护其关系的基本纽带;同时,语言也总是与人的思想活动相关联,因此历史上的思想家们往往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语言”上高谈阔论,道家学者也不例外。
道家对语言传播的见解可谓别出心裁。老子率先提出“正言若反”(《老子》第78章)的命题。这一句的字面意义是说,正面的话好像反话,有类于“忠言逆耳”之意,这是人际传播中时常碰到的现象。河上公注曰:“此乃正真之言,世人不知,以为反言。”[2]298老子深知自己提出的“柔弱胜刚强”思想会遭到世人的讥笑,因为在世人的话语系统中历来是刚强胜柔弱,所以以一个“反”字暗示了“真”的意涵。智者老子不仅看到人生可“强”的方面,如“自胜者强”(《老子》第33章),而且指出应注意柔弱的一方面,即“守柔曰强”(《老子》第52章),如果一味地强下去,则会“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42章)。因此,老子告诫世人,真理有时是反常规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于是老子进一步指出:“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老子》第49章)作为一个“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圣人,一个传道者,在老子看来,相信自己话的人,应当跟他诚心地说;不相信自己话的人也应当要跟他耐心地说。久而久之,大家都能相信这样的话。当然,老子也明白“正言”的传播并不可能一帆风顺,正如新生事物总是倍受世人的误解与打击,此之谓:“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第41章)真理常常是朴素的,甚至赤裸裸的。为名缰利锁困扰着的世人对于合道的“正言”往往是嗤之以鼻的。因此,“正言”的传播必然是困难重重。“正言”从本质上讲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正言”必定是合道的、正确的,即“言有宗,事有君”(《老子》第70章)。说话是有根据的,事情是有主宰的,不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之类的瞎扯。换一句话来讲,说话要讲究真实性,不可“虚言”(《老子》第22章)。所以,“正言”亦是“真言”。传者唯有内心保持“真”质,语言精诚真实,才能打动人。《庄子·渔父》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不过,道家认为这个“真”是人的天赋本性,是不可改变的,但是却可能被遮蔽。遮蔽语言之传者与受者双方的东西往往是机智和知识。老子曰:“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老子》第81章)辩论必伴有机心,智者多诈,此二者威胁着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因此老子提出了“四绝”思想,即“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第19章);“绝学无忧”(《老子》第20章)。这些便带有语言传播学的意义:其一,传者当圣且智但不以圣智为怀,亦即不利用信息不对称来愚弄他人,从而使人们在信息充分沟通中广泛受益。其二,传者的语言应当顺应人们的自然本性,不用仁义之念干扰人们本来至孝至慈的纯真心境。传者要考虑自身语言可能引起的后果,要尽可能维护他者平静的心灵。其三,传者的言语也不要激发人们的功利心,以避免人们在功利的诱惑下作奸犯科,沦为盗贼。其四,传者要尽可能避免在追求知识过程中给人们带来忧愁。《庄子·人间世》曰:“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也就是说,语言文字可能会成为人们钩心斗角的工具。因此,语言传播的知识和智能等内容应当考虑能给他人带来快乐,而不是愁苦。
“正言”必当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最终效果看,“正言”是能给人带来益处的,是有价值的。因此,说话要讲究效用性,不说空话、假话、大话。否则,就会出现“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老子》第17章)的被动局面。道家要求语言要完全地信实;如果说话者的言语中带有浮夸、隐瞒等不够信实的成分,终究会导致信任危机。于是,老子再次告诫世人“悠兮其贵言”。也就是说,说话要谨慎,不然就会陷于“轻诺必寡信”(《老子》63章)的境地。从这种意义来说,“正言”亦是“信言”。
为了保证语言传播主体语言的正确、正当、正直,道家要求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希言守中。道家崇尚自然,在语言传播方面说话遵循语言经济原则,话要少而精,因为从传播效果而言,喋喋不休的说教,往往适得其反,正所谓“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第5章)。话说过多,反而会使自己加速陷于困窘之地,不如管好自己,坚守中道,抑即“希言自然”(《老子》第23章)。话少说,让彼此之间自自然然地沟通交往,渐渐地在点点滴滴的生活言语交流中,将自己所要表达的意义传达给对方,起到润物无声的效果。这就叫作“少则得,多则惑”(《老子》第22章)。老子所以一再指出“多言”的害处以及希言的益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对话双方在知识储备、理解能力、实践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有时甚至是差异悬殊的情况下,虽然你说的都是事实,都有根有据,但是对方无知,他就是不理解、不相信。老子就曾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老子》第70章)可谓是曲高和寡,知音难觅。老子也不得不慨叹:“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同上)其含义用现代话来说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间的对话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不说为妙,必须等待时机,努力创造对话条件。
此外,对话的双方应当具备相当的悟性,能领会到一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意义,这样才能顺畅沟通。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1章)这里我们姑且把“道”理解为语言包涵的意义,名就是语言符号。“从语言传播看,它揭示了有限的‘言’与无限的‘意’的关系,提出了怎样用有限的‘言’表达无限的‘意’的问题。”[3]语言符号具有外延意义(基本义、逻辑意义)和内涵意义(引申义、审美意义)的双层意义,且内涵意义的获得往往与人的文化背景、亲身经历、感情色彩等有着密切联系。也就是说,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具有很大的伸缩性、灵活性、主观性和文化性[4]25-26。人们力图言“道”,但说出来的东西往往不完全是传者所想表达的或所能表达的。语言作为符号是可以用于指称事物,但是能指与所指的未对称性(随意性)决定了符号自身的局限性,无论如何准确地运用符号,符号总归是符号,并不是事物本身。因为符号是相对稳定、有限和抽象的,而事物是动态、无限和具体的[5]110-112。但这不等于说语言符号无用,关键是在用与不用之间保持一种灵动的张力,即“希言”。维特根斯坦把哲学分为“可说的”和“不可说的”。他认为对“可说的”要说清楚,对“不可说的”要保持沉默。沉默不是不言,“它将用明显的可以讲述的东西来意味着不可讲述的东西”[6]51。就语言传播而言,传者说能说、可说的东西,至于不能说、不可说的方面留待受者去感悟。
(二)言必有宗。道家认为要说,就要说得有根据。“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第14章)“道纪”大体上指纵观历史,把握事情来龙去脉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思考和处理各种事情的经验方法,用现代话来讲,可以统称为“传统”。这种智能运用在语言传播上,是“言有宗,事有君”(《老子》第70章)。老子为了让受者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他常常引用圣人的话,比如,“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57章)。“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老子》第78章)。他还特别注重引用当时流行的各领域中的名言警句,比如“用兵有言”(《老子》第69章),“故建言有之”(《老子》第41章)等。
(三)善言无迹。老子要求传者要做到“善言无瑕谪”(《老子》第27章)。就是说,说话要做到恰到好处,滴水不漏,没有让人有可指责的地方。老子以“人之迷,其日固久”为例,探讨当如何善言开导。基本思路是:“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老子》第58章)具体说来,“方而不割”就是方正但不割人,老子要求传者言语要犀利,但不要伤害人。“廉而不刿”就是锋利但不伤人,传者观点要旗帜鲜明,但不能得罪人。“直而不肆”就是直率但不放肆,传者不应当隐瞒自己的观点,应该秉笔直言,坦白相告,但不能无所顾忌,使人难堪。“光而不耀”就是光亮但不耀眼,传者风光无限,春风得意,但在与他人言时,不能得意扬扬,不要去刺激他人。人际中言语若能做到这四点,可算是“美言”。老子说:“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老子》第62章)美好的言论可能获得他人景仰,自重的行为可以赢得他人尊重。如果是上下级之间,上级对下级尤其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语。老子明确指出:“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老子》第66章)。只有说话谦逊、礼贤下士的领导,才能得到属下的拥护,达到“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的理想效果,即天下人都乐意推举他为领导[7]67。同时,必须注意的是,要办成一件事,应该特别讲究信用,即“言善信”(《老子》第8章)。不过,判断其言是否信实,往往不能根据语言华美与否,老子告诫世人,华丽的语言往往是不能信赖的。是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第81章)。信实的语言必当是朴素,不需要过多的修饰。《庄子·齐物论》也指出,“言隐于荣华”。华丽的语言可能消解了内涵的意义。
(四)名止于实。《庄子·至乐》还提出“名止于实,义设于适”的主张,语言文字当以事实为根据,并且运用适当的语言文字表达恰当的意义,这里蕴含着语言符号运用的能动性问题。道家讲究凡言必言之有物,反对空言。《庄子·则阳》曰:“有名有实是物之居。”物作为语言文字的所指,蕴含于符号之中,这是强调了名或言必有实的原则。作者还说:“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语言所承载的知识,恰当的传播当使符号所指之“物”在受者身上实现准确解码。
(五)得言必察。道家意识到,“言”可能并不传播事实。因此,对于听到的话要进行审察,以确定其真假。《吕氏春秋·慎行论·察传》提出“夫得言不可以不察”的观点。这是因为“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对于听闻的话不加审察就接受,不如没有听到。作者举例说:舜曾说“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意思是说有夔一个人就足够了。但这句话经过传播就变成了“夔一足”,即夔只有一只脚。两者意思相去甚远。还有宋国丁氏常一人在外,家里要挖井,于是他说:“吾穿井得一人。”这句话传开后,变成“丁氏穿井得一人。”由挖井需要一个人变成挖井挖到一个人,令人啼笑皆非。作者还说到一个形近字也可能在传播中发生误会,引起理解上的偏差。总之,“凡闻言必熟论,其于人必验之以理。”听到的话要反复验证才行。
二、寓言、重言、卮言:语言传播方法的求善准则
道家除了注重语言传播的真实性以外,还关注传者与受者间的顺利沟通的方式方法,坚持“通畅性”原则,即“善”的原则,因此采用了一套道家独有的话语系统,这就是庄子学派所概括的“寓言”“重言”“卮言”。
(一)寓言:对语言传播模糊性的理解与运用

在道家看来,“道”是玄妙难知的,语言只能描述现实世界的事物,而道是超然物外,是派生万物的存在,所以语言在描述道的时候常常是“强为之名”(《老子》第25章)。为改变这种勉强的状况,庄子学派广泛运用了“寓言”这种表述方式,借助寓言模糊而广阔的诠释空间,使“无名”(《老子》第32章)“不可名”(《老子》第14章)且以恍惚窈冥状态存在的“道”得以敞开一个无限意义的空间成为可能。
庄子学派对寓言有着深刻认知。《庄子·寓言》曰:“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通常生活中自己父亲说儿子好,不如别人的父亲说好有说服力。同样,我们借助他者来表达自己想说的话,传播效果自然更好。《庄子·天下》曰:“以寓言为广。”郭象注之曰:“言出于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9]539成玄英亦疏之曰:“寓,寄也。世人愚迷,妄为猜忌,闻道己说,则起嫌疑。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信九矣。”[9]538相对于己言来说,寓言的影响更广。不过,寓言还有一个类似于隐喻的功能,借助某物某事来说明另一物另一事。两者间有一定的相似性。老子就以水喻道,他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第8章)当然,还有以婴儿、山谷等来喻道的。不过,庄子学派的隐喻不以两者的相似性为基础,而是以“意义的盈余”即超出“能指”(或语言文字)的意义的方式来实现隐喻的。陆西星《读南华经杂说》就深明《庄子》寓言是要义,他指出寓言乃是“意在于此,寄言于彼也。”寓言重在形象,通过语言描述的形象去把握寄寓的道理。庄子就借助“鱼之乐”“庄周梦蝶”阐明了“天地与我并生”的“物化”思想。庄子寓言传播思想大体有三大特点:其一,只喻不议,喻中寓理;其二先喻后议,喻议结合;其三,先议后寓,议寓相连[7]150-152。
(二)重言:对语言传播稳定性的理解与运用
虽然从发生学角度而言,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但是一旦约定俗成之后,特定的语言符号就表达特定的意义,从这一点来说语言符号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有了这种稳定性,就使跨越时空的意义传播成为可能。《庄子·逍遥游》曰:“名者,实之宾也。”语言文字是第二位的,只是客观事实的表现形式。“重言”乃是厚重之言,并不是指语言文字本身,而是语言文字承载的意义。虽然后人理解古人的意义有难度,但是通过理解历史进程,把握当时的语境与情境,可能会明白语言文字当时的意义,这个意义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就像我们现在去阅读古文,还是可以读懂一样。运用传播符号学理论来说,语言符号具有“可传承性”[10]42。
“重言”字面含义是重要之言,即有分量的语言。不过,在《庄子》一书中,当有明道之言和重道之言两层含义。《庄子·寓言》曰:“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重言是指年长者(延伸为古代圣人)的话,并不只是年龄的年长,而是学识才德过人的年长者的话。在语言传播中运用这样的话有助于增强语言的可信度。《庄子·天下》也说,“以重言为真”,世人常常相信“重言”是可信的,也可以理解为“重言”的意义具有真实性。老子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老子》第21章)在老子看来,“道”作为士人追求的终极意义,是永恒存在的。从古至今“道”之名就一直在传承着,而“吾”对道的把握,便是通过这个“名”(语言文字)来实现的。可见,言以载道,换句话说,“道”的意涵可以在“言”中得到相对稳定的保存。“重言”其实就是“道言”,亦即得道的圣人之言。成玄英称:“重言,长老乡闾尊重者,老人之言,犹十信其七也。”[9]538林希逸亦解释曰:“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黄帝、神农、孔子是也。”[11]403《老子》书中常常引用圣人之言,如“古之所谓‘曲则全’者”(《老子》第22章)。还有“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第79章)就是引用《金人铭》中的句子。其实,与老庄同时代的人们早就有了崇古情怀。孔子明确表态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亚圣孟子亦曰:“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先秦儒家集大成者荀子亦言:“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荀子·非十二子》)墨子提倡“言有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便是其中语言传播的第一表(根据)。儒墨两家所推崇的圣人大体只是三皇五帝。而道家则自创圣人谱系,将之推至更为久远的上古年代。仅以《庄子·胠箧》为例,该篇中就载有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等十二代圣人的传承谱系,试图强化自身语言的神圣性。不过,有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庄子》书中尧、舜、禹、孔子等圣人往往成为庄子学说的代言人,他们在《庄子》书中俨然就是履践道家无为之道的圣人。此外,庄子学派自觉大量引述圣人著作和当时流传的名言警句。著作有《法言》(《庄子·人间世》引)、《记》(《庄子·天地》引)、《书》(《庄子·盗跖》引)等,名言有“野语有之曰”(《庄子·秋水》引)等,还有大量直接间接引用《老子》或先老学之言。总而言之,道家坚信“道”(意义)是可以通过语言来传播的。正因如此,道家特别重视“重言”,因为它承载着圣人历史实践的信息,这些都是后人的精神财富。
(三)卮言:对语言传播创造性的理解与运用
根据传播符号学理论,语言符号还具有“强生成性”(即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的生命力)“二元组合性”(总是跟自己最毗邻的另一符号进行组合)“非对称性”(同一符号可指称多个内容,反之多个符号可以指称一个内容)“超时空性”(符号可以指称不在眼前的事象、没有发生过的事象、非物质形态的事象)等特征。这些特征归结为一句话,语言符号具有变动性的特点[10]38-45。道家显然深明这个道理。《庄子·寓言》曰:“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卮是一种器皿,它空的时候是仰躺着的,装水到一半时是中立的,而装满时便倾。所谓“卮言”,第一种理解是日出日新之言。王先谦曾说:“夫卮器满则倾,空即仰,随物而变,非执一守故者也,日新则尽其自然之分,己无常主也。”[12]948同样一个器皿,在不同情况下会有不同的情态;同一个“言”(语言文字)在不同情境下会表示不同的意义,也可以说不同的意义可以用同一“言”来表示。可见,“言”具有多义性。因此,人们运用“言”就有了广阔的意义创造空间。还一种理解,卮言意为中正之言。陈景元解曰:“日出未中则斜,过中则昃,及中则明,故卮言日出者,取其中正而明也。” 而这两种意涵是相通的,因为变化不离其正,正是“卮言”的创造性所在。卮言在道家看来是道言,言道之言,此言乃无心之言,自然流淌之言,中正之言,日新之言,无可无不可的圆言,曼衍无终始、支离无首尾之言,耐人体味之言[13]231。对于语言的运用如此能达到信手拈来,随心所欲,那可以说是运用语言的大师了,庄子便是这样的人。
成玄英疏云:“卮言,即无心之言。”“卮言,不定也。”“卮言”思想要求传者主体能够在言语时不抱成见。因为“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语言所指称的对象有其自在性、自为性,人的主观不能取代它,而只能“因其固然”。于是,庄子学派提出“言无言”的语言传播原则,即说出没有主观成见的语言。这样,终身说话,却好像不曾说;终身不说话,却好像都在说。
语言的创造性源于世界运动变化的丰富性。郭象注曰:“夫自然有分而是非无主,无主则曼衍矣,谁能定之哉!故旷然无怀,因而任之,所以各终其天年。”成玄英疏曰:“曼衍,无心也。随日新之变转,合天然之倪分,故能因循万有,接物无心;所以造化之天年,极度生涯之遐寿也。”[9]539-540语言符号描述千变万化的世界,力求客观地反映事实,即“接物无心”,那么以这种语言传达的信息来处事,事与物都能各安其序,所以能“尽其天年”。《庄子·人间世》曰:“为人使易以伪,为天使难以伪。”就是认为有心(为人)必有伪,无心(为天)则难以起伪了。
语言符号除了如上所言的表述和理解功能、传达功能以外,还有思考功能,亦即语言激发人的创造功能。语言符号承载的意义使受者在接受后在自身的情境中往往会生成崭新的意义。这是因为“思考本身也就是一个操作符号在各种符号之间建立联系的过程”[14]46。正因为思考才有创造性。不过,同时也可能带来破坏性。思考的同时往往被自己的主观偏见、成见、妄见所宥,不知不觉中干扰了信息的准确传播。故而应注意如下。
“卮言”要求公正以言。辩论往往是各执一词,为了战胜对手,常常运用诡辩等手法。庄子学派指出“人固受其黮暗”,“辩也者,有不见也”(《庄子·齐物论》),论辩使人受偏执的迷惑。“彼至则不论,论则不至;明见无值,辩不若默”(《庄子·知北游》)。明道的人不去论辩,论辩者不明道,故而辩论不如沉思。辩论对道而言,并不能越辩越明,但对于客观世界的诸事诸物诸象而言,则是智力所及。《庄子·徐无鬼》:“知之所不能知者,辩不能举也。”知性无法认知的对象,必须依靠悟性之知了。道家反对辩论这种特殊的语言传播方式,是因为辩论可能破坏人纯真的天性。《庄子·盗跖》曰:“辩足以饰非。”辩论者往往会竭力粉饰自己的不足或过错。
“卮言”要求力戒“溢言”。《庄子·人间世》引《法言》之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希望实事求是地传达“常情”,不去传播“溢言”。“溢言”是过头话,不合实际情况的。所以“卮言”要求不要去增加原来没有的方面,也不要遗漏本来有的方面,做到全面,客观、准确地表达实际情况。《庄子·人间世》强调指出:“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溢言的事情必然是不真实的,而不真实就没人信,没人信则传言者会遭殃。因此,语言传播敢不慎乎?作者进而指出语言传播如果不符实,可能还会带来很大的危害。“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夫风波易以动,实丧易以危。故忿设无由,巧言偏辞。”花言巧语和偏执之言都是“丧实”之言,都可能影响人们的喜怒哀乐,带来无穷后患。
三、不言、无言、忘言:语言传播效果的求美境界
道家运用寓言、重言、卮言等语言传播方式,运用了大量的比喻和其他方法,彰显了传播技巧,以期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不过,这些语言传播方式还只是重在语言传播的工具理性;其实,道家更注重语言传播的价值理性和审美意境,那就是沉浸于“道”的体悟之中,忘我、忘言,准确地说,是生成了悟性之境。这种情况,道家称为“得意忘言”。“忘”既是悟道的途径,也是对语言广泛意义的完全统摄,而语言符号此时好像被抽干了意义似的,被弃之不顾。如果执着于语言名相,那就会阻碍对“道”之意的领悟。因此,“忘言”是道家语言传播的最佳效果的表征,同时也是一种“美”的享受。
(一)不言:融入非语言符号,增强传播效果的方式
日本的林进指出:“各种非语言的象征符号体系如仪式和习惯、徽章和旗帜、服装和饮食、音乐和舞蹈、美术和建筑、手节和技能、住宅和庭园、城市和消费方式等等,都包括其中。这些象征符号体系在人类生活中各个领域都可以找到。”[15]18这些象征性非语言符号也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们主要以形象的方式传达了许多语言符号不能或不完全能传播的信息。生活中其实处处是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相结合才能保证传播活动的顺利进行。老子率先提出“不言”的语言传播理念。在他看来,就无限的道意而言,语言是苍白的。“不言”或少言比多言更能达到传播效果。老子是基于“多言数穷”的认识基础上,提出“不言”的。老子的“不言”思想历来引起不少争议。聪明的白居易对此也颇感困惑,他在《读老子》诗中说:“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他自鸣得意以为抓住了老子的致命弱点;其实,自己不过是老学的门外汉而已。老子所说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第56章)的名言,首先是他一贯讲究慎言慎行的必然结果。他认为无论是说话做事,都应当奉行“唯施是畏”(《老子》第53章),言多必失,谨防祸从口出。不过,“老子没有否定语言传播的价值,而是从批判的角度,说明了语言传播的局限性,揭示了现实社会中语言传播的异化现象,提出了语言传播的最佳境界是‘不言’,‘不言’才是最好的‘言’。”“从语言传播看,只要一切符合‘言’的自然性(即‘言’的规律),不在‘言’的自然性之外去刻意追求,就能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这便是老子所谓‘不言’的真正内涵。”[3]其实,最好的语言是没让人感觉语言的存在,正如天地的美不需要言说而自美一样,庄子就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物以其内在规定(理)呈现为现象界的形象,这是自然而然的。语言传播的最好感觉那就是让受者好像成为对象本身,对象的一切了然于心,而没觉得语言符号在告诉他什么。“老子用否定的方法建立的对语言传播的认识,使我们对语言媒介可以有更清楚的了解,它促使人们对语言传播中言与意的关系、语言的美与真及美与善、语言传播的最佳效果等等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3]
其实,老子提倡“不言”,还有一个意图,那就是实现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相互配合以实现最佳的传播效果。老子曰:“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2章)。称“不言”的传播效果是“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老子》第43章)。“不言之教”的重要内容包括形象传播、体态符号传播等。老子形象地刻画了得道圣人的日常行为表现,而圣人的以身作则,便是对百姓的不言之教:
古之善为道①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焉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老子》第15章)
这种不言之言的效果是“不言而善应”(《老子》第73章),意思是说百姓争先效仿。《管子·心术上》:“不言之言,应也。”《管子·心术下》“不言之言,闻于雷鼓。”可以说,不用言语的语言,有着潜移默化的效应。在道家看来仁义礼智信的教化效果是有限的,很容易适得其反。老子就说:“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老子》第38章)相反,圣人“为而不争”(《老子》第81章)的行为形象,反而深深地感动百姓,进而自觉地配合圣人施政。正如施拉姆(Wilbur Schramm)所言:“尽管非语言的符号不容易系统地编成准确的语言,但是大量不同的信息正是通过它们传给我们的。”[5]126也就是说,信息的传播并不完全依靠语言符号,只有充分地运用非语言符号的传播艺术,语言传播才能得以更顺畅地进行。
此外,不言也指面对不可言、不能言的东西,当保持沉默。在道家看来,道正是这样的存在。《庄子·知北游》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是无限的,语言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语言来表现无穷的大道,必然会显得窘迫。《吕氏春秋·审应览·精谕》曰:“目击而道存矣,不可以容声矣。”意思是说,两个见面即相知,无须语言。眼睛所见的形象也是一种承载意义的符号,是谓“目视于无形”(同上)。见到形象,则对方的心志自明。这正是不言的原因之一。
(二)无言:无不言的语言传播效果
道家崇尚“无为”,无为不是不为,其实是为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无言其实就是言无言,无言方可无所不言。道家追求“无言”之境,试图以“无言”的方式去体悟道意。这其实是“道”的存在方式决定的。道虽然不是具体事物,但也是物的存在,是无物之物,这就决定语言在表达道的时候当是“无言之言”。《庄子·则阳》曰:“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自然是无言了。无名为众名之源,无言为众言之主,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在语言传播过程中,常常也有“此时无言胜有言”的情景。无言并不是不说,只是此时此地此人不该说则不说。无言又何尝不在“言”。“无言”可以通俗理解为“无不当之言”。言必及道,言必合道。庄子学派说:“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庄子·则阳》)他们认为口之所言,乃应事而言,事过则舍,其内心未尝动,没有情感渗入,故“无言”。《庄子·寓言》所说的“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也是这个意义。此外,《列子·仲尼》曰:“得意者无言,进知者亦无言。用无言为言亦言,无知为知亦知。无言与不言,无知与不知,亦言亦知。亦无所不言,亦无所不知;亦无所言,亦无所知。”得意者沉醉于意境中,故无言。进知者在品味智能的佳酿时,亦无言。然而,他们此时此刻又何尝无言,何尝无知,又何尝言,何尝知?知与无知,言与无言没有绝对的界限,如果有界限了,那就是小言,小知了。道家倡导“去小知而大知明”(《庄子·外物》),认为“小知不及大知”(《庄子·逍遥游》)。大知是没有局限的,而小知则囿于己见。道家倡导“大言”,摒弃“小言”,这是因为“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庄子·齐物论》)。闲闲乃宽裕之意,炎炎乃燎原烈火;间间者,分别之意,詹詹者费词之意,含竞辩之意。道家提倡“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庄子·齐物论》)。大言乃是言满天下,无所不言,却又无所言,因为其言无瑕谪。小言则私心自用,费神焦心。
道家注重无言,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无言,无言是得“意”的结果。黄老道家作品《吕氏春秋·审应览·精谕》曰:“知谓则不以言矣。言者谓之属也。”谓是所指,即意义。语言是从属于意义的,意义既然获得了,就无须“言”。
(三)忘言:语言传播效果的极致
忘言是对语言工具的升华,其实质便是意义的获得。“语有所贵者,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庄子·天道》)在道家看来,单纯的贵言是舍本逐末。“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可传于人者,皆其粗也。”(《文子·精诚》)“粗”意谓“末”。因为本在“意”,末为“书”(含语言文字符号)。语言有形式上笔划的形象存在,还有发音上的声音存在,然而离开了意义,语言本身的形式存在便没有任何价值。其实正如解释学所说的,语言一旦以文本的形式呈现,其意义便非立言者所能限定,文本所载这“言”总是包含着不断延伸的意义空间。庄子学派将圣人之言视为“糟粕”,其旨在告诉世人不要死于文字之上,而应于圣人的心地上驰骋。《庄子·秋水》曰:“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物之外在形象和内在功用常常是可以言论的,也可以用思维来把握。在道家看来,终极的意义是言语道断,即语言成为进道的障碍,必须“忘言”。只有忘言了,才能实现对意义的完全占有。而此时,意会内涵之意义是不能言传的。轮扁说:他“斫轮……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此种斫轮之技乃基于悟性,非语言的理性所能表达。《庄子·外物》曰:“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言好比捕鱼之荃,逮兔之蹄,行动的目的在于鱼兔,而非荃与蹄。语言运用的最终目的在于传意,得到意,就不需要去在乎“言”。究其实质,作者是想表达一种思想即语言不能代替生活本身。一切包括语言在内的活动都应以维护人的存在为前提。“得意”的含义在于对语言的超越,是人对自己存在价值的获得。此种佳境是“无言而心说(悦)”(《庄子·天运》)。可见,道家除了关注言与意的关系问题,还以“心”的方式体现人的主体性,并关注着自由与幸福。此所谓“言不尽意”。其意义在于“尽心”、“洗心”,即心的冰释。《易传·系辞上》也肯定指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但这不等于说不要言,言表达不了意。而是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里的“尽神”便是“尽心”之意。卦象、卦爻辞都是在尽言、尽意、尽利,最终还在于悦心,是谓“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忘言的精髓在于忘心。《庄子·大宗师》曰:“悗乎忘其言也。” 悗,无心也。言必有心,无心则无言。语言常带有个人的目的性,而这在道家看来是人生之累的根源,应当舍弃。无言,无心,逍遥自在。
在语言表述世界的问题上,道家意识到有感性之知、知性之性、悟性之知三个层面,尤其欣赏悟性之知。所谓悟性之知其实是“意义的盈余”,它并没有脱离符号承载的感性对象与知性之知,但它无疑是一种超越。道家认为人们陷于前两者太久了,或者说太在乎符号本身了,阻碍了自身精神的超脱,于是提出“忘言”的思想,忘记语言洞察事物的本质。其实,道家把进入“忘言”当成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进道的过程。《庄子·知北游》记述了一位名叫“知”的求道历程。他请教“无为谓”三个问题:“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无为谓不回答。“非不答,不知答也”。“知”再问狂屈,狂屈说他知道将要告诉“知”,可是“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后来只好去问黄帝。黄帝说:“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知”听了,还以为他与黄帝知道,无为谓与狂屈不知道。不过,黄帝却说:“彼无为谓真是也,狂屈似之,我与汝终不近也。”作者所要表达的是语言传播的困境。“知”为了求道,得先“知道”,黄帝所言,其实是对“知道”的语言表达。知道只是得道的第一阶梯。《庄子·则阳》曰:“可言可意,言而愈疏。”第二阶梯是安道,而“安道”是“道”化在生活中,自己是有体验的,但是想用语言表达的时候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庄子·列御寇》曰:“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因为道自道中悟,道外勿谈道。所以狂屈,一个率真而为的人,他想说却说不出来。也就是说,狂屈体会到道不能言的困境,是个近道者。而第三个阶梯就是得道,一个人一旦得道,道就是我,我就是道,没有任何的主观愿望,连想说的冲动都没有了,所以“无为谓”不知道回答。这第三个境界其实就是“忘言”的境界。忘言的境界就是道的境界。
在语言阐述意义的过程方面,道家还一套臻至“忘言”境界的方法,那就是《易传》所诠释的言、象、意三者的关系。这里的象主要指卦象,言是卦爻辞,意是圣人演卦之意。王弼是诠释三者关系的代表。他将易理与老庄之道熔于一炉,其思想集中在《周易略例·明象》。首先他认为言、象、意三者关系是:“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着。”“言”可表达“象”,“象”可表达“意”。不过,我们认为“象”可以涵盖具象、抽象、意象三个层面。这样,就可以构成一个诠释世界的符号系统。其次,对“象”来说,“言”是表达“象”的工具,而“象”是表达“意”的工具。得“象”当忘言,而得“意”当忘“象”。明确说明得“意”须经历“忘言”与“忘象”两个阶段。“象”是此过程的中介物。“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再次,王弼强调“言”与“象”的工具性和过程性,不可停滞于言与象本身。明了“象”,“言”的使命就结束了;停滞于“言”,也就是不明“言”,就生成不了“象”。广泛地说,“言”可指人们一切活动动机的语言表述;“象”指为此动机而构建蓝图。“意”便是保证完成这个蓝图的指导思想。同样,“象”的作用在于导向“意”的生成,如果停滞于“象”,也就是不明“象”,就生成不了“意”。“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最后,“意”是对“象”了然于心,即忘象的结果。而“象”也是“言”了然于心,即忘言的结果。总之,言与象是通向意的桥梁,只有忘言、忘象,圣人的思想才能明白。“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语言使用好比巧匠手中的锤子,锤子用得越顺手,其实主体越是忘记锤子的存在。“锤击不仅有着对锤子的用具特性的知,而且它还以最恰当不过的方式占有这一工具。”“对锤子这物越少瞠目凝视,用它用得越起劲,对它的关系也就变得越原始,它也就越昭然若揭地作为它所是的东西来照面……用着操作着打交道不是盲的,它有自己的视之方式,这种视之方式引导着操作,并使操作具有自己特殊的状物性。”[16]85-86语言也一样,语言用得越熟练就越是忘记语言。语言并不是不要,而只是“每寄言以出意”[9]399,得意自可忘言。
综上所述,道家的语言传播思想洋溢着真善美向度。在道家看来,语言是悟道的工具,但语言与道(意义)是履与迹的关系。《庄子·天运》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脚印能够说明鞋子的存在,但不能穷尽鞋子的本质与内涵,更不是鞋子本身。同样,先贤之意也不是他们的话语所可以穷尽的。不过,道家并没有因此舍弃语言,而是把语言当成明道的必要阶梯,诚如《庄子·大宗师》所言:
闻诸副墨(文字)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诵读)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见解洞彻),瞻明闻之聂许(耳闻),聂许闻之需役(实践),需役闻之于讴(咏欢歌吟),于讴闻之玄冥(深远幽寂),玄冥闻之参寥(空廓),参寥闻之疑始(迷茫之始)。
这是女偊入道历程的自白。这段话的意思可以意译为:开始我向书本文字学习;后来又抛开文字靠口头咏诵;接着我就不听不看,靠主观见识的通彻;再接着我想也不想,在模糊不清的声音中获得悟觉;再接着我的身体也不动了,处于无为之中;再接着我混混沌沌,无见无知无感;再接着我在寥廓幽深的宇宙空间徜徉;最后我贴近宇宙精华凝结的本源[17]179。对宇宙本体的领悟,或者说对终极意义的把握,是离不开文字(副墨)与语言(洛诵)的。道始终是向语言敞开的,没有真切的现实感受,即没有立足于所见(瞻明)、所闻(聂许)、所为(需役)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真”信息。当然要获得终极意义,还需要善于消融感性之知、理性之知,进入悟性之知,即歌咏(于讴),力求超越有限通达无限,这便是“善”的修为。这样自我在超越中忘却,进入无言之境,体验着渺茫(玄冥)、空寂(参寥)和万物本原(疑始)的创生力,这便是“美”的境界。
注 释:
①“道”,王弼注本、河上公本均作“士”。帛书乙本以及傅奕本则作“道”。
[1][美]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2]河上公.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王卡,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
[3]张卫中.老子对语言传播的批判[J].社会科学战线2002(3).
[4]齐沪扬.传播语言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5]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6][奥地利]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逻辑哲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 郭志坤.先秦诸子宣传思想论稿[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8] 伍铁平.再论语言的模糊性[J].语文建设,1989(6).
[9](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0]余志鸿.传播符号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11]郭庆藩.庄子集解: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2](宋)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M].陈红映,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13]朱哲.先秦道家哲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5][日]林进.传播论[M].东京:有斐阁,1994.
[16][德]海德格尔(M.Heiderger).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17]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责任编辑:高建立】
B223
A
1672-3600(2017)07-0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