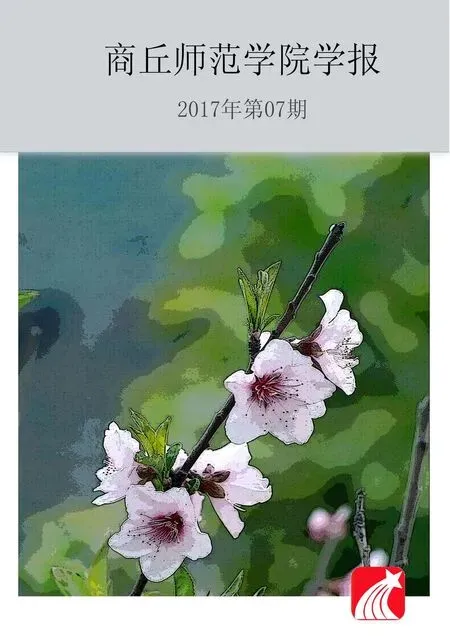以《诗》入诗:王闿运诗歌的经学实践
2017-06-19潘链钰
潘 链 钰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以《诗》入诗:王闿运诗歌的经学实践
潘 链 钰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王闿运论学主张通经致用。在王闿运的诗歌创作中也明显存在一种致用意识。王氏为数较多的引《诗》入诗之作正是这种意识的实践。王闿运引《诗》入诗之作移花接木,别具匠心,成为他主张的因道通诗、以诗达道的典范之作,对后世有重要意义。
王闿运;以《诗》入诗;经学实践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为学主治《春秋公羊传》,宗今文经学。对于“经”,王闿运力主致用。通经致用是王闿运经学思想的主要原则。“经世”理念贯穿于王闿运一生,是儒者修齐治平理想的精神回归。王闿运“经世”思想的产生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是时代环境的造就。王闿运生于内忧外患之世,乱世则《春秋》兴是历史之趋。更何况早在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大儒早就敏锐感受到当时儒学的空谈之害。因此他们都主张致用之学与经世之能,而绝非停留于辞章义理。其次,是王闿运自身的求学经历。9岁即诵四书五经的王闿运,幼时却非专意于科举,而是更青睐于经史辞章。第三,经典本身便蕴含着经世之力。在晚清这个特殊的时期,经世致用只是文人处世的诸多选择之一。多事之秋,有人明哲保身,选择隐退;有人左右奔走,谋取私利。但王闿运选择发扬经学的致用之道,实际是发扬经学本身具有的经世之力。如果说前面两点原因是王闿运从时事和自身出发试图发挥经学以求治世的话,那么第三点实际上是王闿运力图从经典本身寻求致用之道。
“经典”本是经籍和典籍的合称。“五经”在先秦被尊奉为“经典”乃是毋庸置疑的事情。那么,“五经”当中的《诗经》自然也是经典。然而,作为经典的《诗经》却又是文学作品,这一点也毋庸置疑。《诗经》既是经学作品,又是文学作品,身兼二义,品性独特。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曾从“文体范式”的角度论述“五经”:“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1]22刘勰认为,“五经”之体乃是后世文体发展的范式。当然,刘勰的文体观若追究其目的,依旧是“圣因文而明道”的功用之论。《诗经》的“文体”之功也是经学之力的外在表现。这是从文体“形式”角度出发谈论《诗经》的致用之力的。那么,如果从《诗经》的内容的角度谈论其致用之力,又该如何?恰好,王闿运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以《诗》入诗,实践其致用之力的。这正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诗者之情,感而微妙
王闿运是晚清著名诗人,湖湘诗派的魁首。在王闿运看来,诗歌之法,首端在情。“古之诗以正得失,今之诗以养性情。虽仍诗名其用异矣。故余尝以汉后至今诗即乐也,亦足感人动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谏为本,专为人作;今以托兴为本,乃为己作。史迁论诗以为贤人君子不得志之所为,即汉后诗矣。主性情必有格律,不容驰骋放肆,雕饰更无论矣。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无所感则无诗,有所感而不能微妙,则不成诗。”[2]51
“有所感而不能微妙,则不成诗。”在王闿运看来,诗歌不仅要有所感,且须以一定的微妙之音体现出来。这似乎跟王闿运认为的诗歌载道讽谏的致用之论并非完全吻合。那么,王闿运的诗歌主张又是如何呢?王闿运论诗主张“载道”。但在湖湘诗派诗论中,王闿运的“载道”已经不是韩愈所谓的“文以载道”。湖湘诗派的诗学具有强烈的革新意识。以王闿运为首的湖湘诗派认为,诗歌革新乃在八字:“诗不论理,亦非载道。”诗之言理,始自宋诗。宋诗以议论入诗,诗之言理且求平淡之美已然成为共识。而此处王氏之诗论,第一要义便是要反驳宋诗之言理。可见王氏对宋诗、宋学分道扬镳的明显诗学倾向。
王闿运论诗并非止于“不言理”,而是进一步地扩大为“不载道”。“载道”之说,源自唐之韩愈。韩愈因见中唐之诗文空疏绮靡,特以载道之说,逆转“八代之衰”。继而柳宗元以“明道”呼应,仍不离载道之宗旨。二者之实质都在复古而革新。尔后宋之江西,明之七子诸流,皆借此而扬革新大旗,此不赘言。王闿运之“不载道”乃因见汉学之凋敝,宋学之空疏,都无能重扫近代诗文之颓气。而欲将诗返璞归真,必须一则避宋诗论理之旁拓,二则须避唐后载道之诗的疏蓬,最重要的一点则是超越此二者之上的、既非论理亦无载道的“缘情”。
然而,若认为王闿运的诗歌主张乃是摒弃论道而专主缘情,则谬矣。王闿运所缘之情,内涵有三:第一,“情”者不避食色。第二,民间之“情”与下层劳作者之“情”尤难可贵。第三,诗情须“绮丽”之情,“典雅”之情[3]。很明显,王闿运所缘之情,依旧是劳苦大众之情,庄正典雅之情,而非滥情、俗情、诡情。这样的“情”广泛存在于人世之间,需要诗人虚心体察,洞观世事。王闿运这样论述诗情的由来:
生今之世,习今之俗,自非学道有得,超然尘埃,焉能发而中感而神哉?就其近求之,观古人所以入微,吾心之所契合,优游涵咏,积久有会,则诗乃可言也。其功似苦,其效至乐。究而论之,如屠龙刻棘,无所用之。人生百年幸有可乐,殊不必劳心于至苦,运神于无用。故余之论未尝劝人学诗,诚见其难也。[2]51
这样的诗情并非简单得来,因为其功似苦。但这样的诗情倘若真的得到,那么其效却是至乐。
二、因道通诗,诗自工矣
如果理解王闿运的诗歌观,仅停留于诗之情,那么便不能全览其思想之精义。王氏一生,孜孜不倦言诗言情者,非谓诗乃世间宗主,亦非谓情为人世至高。于诗而言,王氏认为诗歌乃是打通人心向道的一个法门。若须向道,则必当由情。所以,王闿运的诗歌,始终跟经学的致用之思保持一致。既然诗歌跟经学致用保持一致,那么学者该当如何打通经学与诗歌呢?要而言之,若要理解诗歌的真义,需要因道通诗。若要追求诗歌工整,也需要以道悟入。
王闿运一生恃才傲物,认为当其之世,诗歌无人能出其右者。“今人诗莫工于余。”在他看来,诗歌本身乃是一种领悟道理的法门。尤其是当一个诗人有了足够的阅历和体验之后,更加觉得诗歌乃是通向一定的道的。王氏这样自述生平学问所得:“然余生平志趣、学问皆由诗入,则天性所近,工夫自然。初亦不料其通于大道,有如是效验也。”可见,回首自己多年的诗歌创作经验,再结合自身的人生阅历,王闿运发现,诗歌正是通向大道的法门。
为了进一步论述诗歌可以通达大道,王闿运还举出孔子论述夔习礼而神乐的事情。《山海经·大荒经》记载:“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4]322黄帝得夔皮制鼓而神威大振,关键在于夔曾习于礼。
王闿运所谓:“孔子称夔不习于礼,则神之于乐者尚有不达。斯古人之异与?”正值此意。当然,王氏神化夔与黄帝,衍用故事,其意旨在说明夔乃是先通于礼而后才有黄帝运用鼓乐之神力。也就是说,只有先掌握经典,才能怡悦性情。王闿运自述自己的求学经历,也是这样谈及经典与诗歌的关系。他认为,如果没有积累三四十年的治经学道的功夫,是很难真正理解经典和诗的大义的。反之,如果“以三四十年之工力治经学道必有成,因道通诗,诗自工矣”[1]51。这里,王闿运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他认为若要诗歌工整,必先深入学习经典。经典之道成了通达诗歌的最重要的环节。
三、以《诗》入诗,自铸瑰词
王闿运关于诗和经之关系的看法有这样两条脉络:于诗而言,诗缘情,通于道,达于用。于经而言,经在用,用在诗,诗在情。可见,王氏并不偏废其一,而是两者兼重。这种看法与那种认为王闿运轻视诗歌而只重致用的观点并不一样。之所以我们重视并论述王闿运的诗学观,考察他的经学观,又注意到二者之关系,是因为在王闿运的诸多诗作中,有这样一些诗歌:第一,诗歌的内容多来源于《诗》这个经学作品。第二,诗歌的形式典雅庄重,化用《诗》中之词。第三,这些诗作虽引《诗》之词入诗,却不失六朝神韵。这样的作品,既是王闿运经学思想的孕育,又是其伟岸才思之喷涌。立处于王氏诸多诗集中,显得极为显眼。这就是本文所要重点谈及的引《诗》入诗。
王代功曾这样评价王闿运以经义入诗之法:“盖自汉魏以来,以经入诗者唯谢康乐,用经典字面耳,府君之诗不用经典字而能以经义入诗,实古人未辟之境也。”[5]249其实,“经典字面”也常为湘绮所用,大致就是本文所谓以《诗》入诗。关于这一点,根据《湘绮楼诗文集》第5卷至第11卷诗来分析,大致其诗直接引用《诗》中字词者,多达44处,其中37处乃是直接用《诗》中字词,另有7处化用。值得一提的是,王闿运之诗,也从《书》中摄取词语6处,《礼》中5处,《易》中4处,《春秋》中5处。但王氏还是最热衷于从《诗》中提取词语入诗。为观方便,现将《湘绮楼诗文集》第5卷到第11卷诗中直接引《诗》的37句做成如下表格(见表1):

表1 《湘绮楼诗文集》第5-11卷直接引《诗》情况

序号王闿运诗句诗题字词出处原句29儒臣新节使,雅咏古车攻仲秋府学释奠观礼二首《诗·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30适野叹何加,行国念我卿除夕行成都市,遂至洗马池《诗·郑风·叔于田》叔适野,巷无服马,岂无服马,不如叔也。31适野叹何加,行国念我卿除夕行成都市,遂至洗马池《诗·魏风·园有桃》园有棘,其实之食。心之忧矣,聊以行国。32老臣忧国意,非是慕彤弨丁尚书总督四川《诗·小雅·彤弓》彤弓弨兮,受言藏之。33未闻青骊驾,已动鹊防吟成都送别黎侍郎培敬《诗·陈风·防有雀巢》防有鹊巢,邛有旨苕。34之子怀瑾瑜,幽独久离家感哀陈鄞县诗一首《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35良友犹一身,斯言异埙篪同上《诗·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埙,仲氏吹篪。36书来告鞅掌,遗篇绝唱酬同上《诗·小雅·北山》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37原隰高下间,皇华映光容答赠袁校经一首《诗·小雅·皇皇者华》皇皇者华,于彼原隰。
纵观这些引《诗》入诗之作,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鲜明的致用实践性。王氏选《诗》中之词语,非显示其学问之深远,而是只借《诗》写诗,有一种明显的致用意识。其次,王氏选用的词语,往往拈出平淡而出于本真。王闿运没有将所选的词语故意转化变型,而是直接借其本义而用,没有典奥之感。第三,王闿运将这些词语运用到诗作中,往往先是“缘情”而用,而不是有意安插。因此,在读这些诗作的时候,先是感觉到《诗》中之情景仿佛在王氏诗歌中再现,具有感同身受的艺术效果。最后,从所用之词语看,王闿运更偏向于借鉴《诗》中的正面力量,积极歌颂者多而借来贬低者少。可见,他是有意识地作一种引导。但总归一点,还需要强调的是,王闿运以《诗》入诗,最终目的是实践性的弘道,也就是以《诗》为例,发挥经典的致用之道。
之所以王代功会评价王闿运以经入诗为辟古人未有之境,是因为自唐宋以来之诗均偏于神韵,即使宋代诗歌(如江西诗派)被人诟病为重议论,但是,前人少有以打通经史子集之胸怀囊括四者入诗。在王闿运看来,他的理想乃是三代以上的儒者气象。三代以上儒者有一种贯通经史的气魄,但此种气魄自三代后趋于衰颓:
王充曰:有文儒,有世儒。此又三代下之儒也。项籍所谓记姓名者矣。章句传经,谓之书匠;词赋供御,等于俳优。比之孟、荀,更非其拟,亦何怪赵宋诸子哀而陋之。然彼识二陋,而更无一得。空谈性道,自命圣人。无以位之,强名道学。此流既辟,儒裂为三。言实行者无门可附,贵者特达,贱称独行。然后知四教分途,尽时变矣。六经具在,三儒罔识。趋之愈下,政教分崩。否必有通,昏将复旦,不极其敝,焉能知圣乎?此又三儒之功也。而若豪杰之士,暗合圣行。则天地有穷,人心不息。但不能治世,殊于行义达道者矣。[5]249
可见,王闿运十分痛心四教分途,尽时而变。因此,他着力于在诗学上熔铸一种“合经史文词为一”的观念。他曾道:“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此等诗皆以存一朝典礼,非文人之作,所谓经术可入词章。一贯之学,为文家上乘。”[2]2370王氏认为,如果诗歌仅仅为了记存某某,那不过是典籍。诗歌中之上乘者,应该贯通经史。“诗有经史学,自汉以来无此家。自顾眇薄,不意能开此派。”[2]2230
王闿运的“通经”观,手段在“通”,目的在“用”。用,即是致用。所以,全面地说,王闿运的“通经”观应该叫“通经致用”观。通何种经?致何种用?这是了解王闿运“通经致用”观的关键。在王闿运自身的诗歌创作中,他积极地实践自己的“通经致用”观,将《诗》真正的引入诗,用《诗》写诗,成为真正的经学实践者,这一点对后世有着重要的意义。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2]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6.
[3]潘链钰.湖湘诗派诗学革新论[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4(2).
[4]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郭德民】
2017-03-18
湖南省教育厅社科项目“王闿运经学思想研究”(编号:16C0983)。
潘链钰(1988—),男,湖北鄂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I206.5
A
1672-3600(2017)07-005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