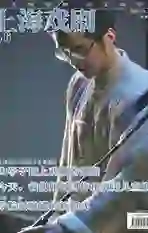怀念恩师徐玉兰
2017-06-15唐月瑛汪秀月钱惠丽杨婷娜
唐月瑛+汪秀月+钱惠丽+杨婷娜
编者按:4月19日,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因病于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6岁。“人如白玉戏如兰,功绩载史册;情似高山爱似海,桃李播天下”是徐玉兰先生德艺双馨的人生写照。回顾徐玉兰先生的艺术人生,她那富有激情的表演、高亢激昂的唱腔、神采夺目的艺术魅力,以及她塑造的性格迥异的经典人物形象,都令观众念念不忘。辉煌的演艺生涯之外,她还培养了唐月瑛、徐小兰、金美芳、刘觉、刘丽华、翁荔英、徐持萍、汪秀月、汤丽芳、钱惠丽、钱丽亚、张小君、刘志霞、郑国凤、杨婷娜、李璐彦等徐派弟子。
本期,唐月瑛、汪秀月、钱惠丽、杨婷娜四位徐派弟子深情回忆她们与恩师徐玉兰的往事,缅怀纪念这位越剧宗师。徐玉兰所留下的宝贵艺术财富,将始终为后辈与观众所铭记。
唐月瑛:我们的徐老师是个很有大将风度的人
我是徐老师早期的学生,1948年我15岁的时候进入玉兰剧团,拜了徐老师为师,拜师后我就一直没和老师分开过,我们是师徒但更像亲人,68年来我跟着她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南征北战”直到现在。老师去世了,83岁的我哭得像个小毛头,老师,我多想再看看您,再跟您聊聊从前的事情。
那时候因为仰慕您喜欢您的戏,我报考了玉兰剧团。刚刚进团时我是一心想要学小生的,但您考虑到团里小生多花旦少,我各方面又更适合唱旦角,您就拍板叫我去改花旦,开始我心里有些不情愿,但听您说“作囡囡(花旦)好,可以和小生搭戏,我来决定你就去唱旦角”,我立马遵从了您的建议改了行当。可是老师您是唱小生的,为了让我在业务上得到更好更专业的学习,您特地自掏腰包帮我和团里其他的小姐妹请了昆曲传字辈的朱传茗、方传芸、汪传钤等老师来教学。那时候,我们玉兰剧团推出了《国破山河在》(后改名《北地王》)、《风萧萧》、《信陵公子》等一系列新编历史戏,这些剧目基本都属于反强暴、除邪恶和分清敌我、颂扬正气的一类,人们都说徐玉兰有胆量,敢作敢为。
那是当然,我们的徐老师是个很有大将风度的人,她的魄力和气场让大家都信服,遇到事情她也从不慌乱,而是经过一番认真思考下定了决心后再着手去做,只要是她决定的事情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做。1952年,玉兰剧团正在如火如荼演出着《西厢记》《玉面狼》等剧目,但是军委总政一号召,老师便毫不犹豫放弃在上海安逸的生活,耐心做好家人的工作,毅然带领全团北上参加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到了部队后我们很快就开始了下部队慰问演出,1953年春节前夕,我们到达舟山群岛慰问驻岛部队,本打算结束任务回上海过春节,但忽然接到电报要我们速回北京。到了北京才知道,是要到旅顺、大连慰问部队演出,于是我们在周恩来总理的带领下一路北上,直到安东。安东紧靠朝鲜,过一条鸭绿江对岸就是朝鲜的新义州,在这里,演出时常常可以听到对岸频频传来的激烈炮声、枪声、飞机声,想到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士们,徐老师和剧团的姐妹们商量之后主动向胡野擒队长请缨,要到朝鲜去慰问志愿军战士。胡队长试探地问道:“那儿可是战场,炸弹不长眼,要死人的!”老师斩钉截铁:“志愿军不怕死,我们也不怕!”在老师的坚持下,上级领导经过慎重考虑,1953年4月24日,老师和我们剧团的全体人员正式入朝了!
从此,老师和我们辗转抗美援朝战场慰问演出,前后持续八个月之久,其中除慰问演出外,我们還至板门店参加交换俘虏的工作,后来停战协定正式生效,老师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全团编入朝鲜和平谈判代表团-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文工团,慰问朝鲜人民军。在泥土堆垒的露天舞台和矿洞里,我们的演出条件着实艰苦,但老师却常常教导我们,志愿军战士为保卫人民更辛苦更危险,他们都没叫苦,我们更应该怀着深深敬意为战士们演出,枪林弹雨不算什么,把戏演好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这样一个徐老师,在生活中又是细心温柔的。平时工作中她十分关心团里的同事们,尤其奔波在一线的舞美队同志们。那时候演出密集,条件也艰苦,舞美队常常要通宵装卸台,出了一夜的力抽根香烟成为他们最期待的放松方式,但是因为经济拮据,很多同志连盒香烟都不舍得买,这些徐老师统统都看在眼里。她常悄悄把我叫过去,偷偷塞给我钱,叫我去买香烟给舞美队的同志,要知道这些钱,不是团里的经费可是她个人的工资。
老师,我有那么多话想跟您说,今天只一句话吧,我会一直一直的想念您的。
汪秀月:今晚一定要卯足劲儿演好《红楼梦》
我是1959年进入上海越剧院的,从那时算起,我跟随徐玉兰老师已有58年之久。58年里从跟在老师身后懵懂学习,到和老师一起登上舞台演出,再到“领师命”去戏校带学生, 徐派艺术早已深入我的骨髓,徐派弟子也成了我最重要的身份标志。
《红楼梦》是老师的代表作品,也是每个徐派传人必学必演的剧目。我常说我是幸运的,1982年为赴日本演出,老师一招一式地辅导我《红楼梦》,后来红楼团筹备期间我们到江浙巡演,除《红楼梦》外,老师又提携我一起登台演出了《西园记》《皇帝与村姑》等剧目,经常是我演上半场,老师压台演下半场。我又说我的学生们是幸运的,因为即便是在病床上,老师也时时牵念着她们,只要我到医院去看望她老人家,她总归会问到我,“小家伙们最近学了什么戏?”“《红楼梦》什么时候演?”等等。我是2007年到戏校去带这班学生的,今年本科毕业前夕,越剧院和学校安排他们去江浙巡演,其中演出剧目就有《红楼梦》。巡演出发前我其实是犹豫的,这边,老师身体状况很不好我实在舍不得走开,那边,作为主教老师我又放心不下这几个学生,最后我同阿唐师姐、惠丽阿妹商量决定,她们在上海好好守着老师,而我还是去给学生把场。记得走之前去医院和老师告别,我拉着她的手说:“老师,这次巡演小家伙们会把《红楼梦》演好的,您放心!我不敢辜负您的嘱托,我尽力教了她们,这也算是我对您的交代。”老师听罢欣慰地笑笑,还竖起大拇指对我讲:“小汪,你可以交代了,你交代得很好了。”那天,她还在华山医院的20楼病房,我走后几天她就陷入了昏迷状态,这句“你交代得很好了”也成了她对我最后的留言。
4月19日,老师去世的这天,我和学生们正在温州大剧院准备晚上将要演出的《红楼梦》。下午5点左右,我收到短信说老师快不行了,当时心里一下子特别难受,但我谁也没说,只是默默走到后台去看学生,看到他们都在认真化妆,我心里稍稍安慰了一些,说好了这次巡演结束我还要带他们去跟老师汇报演出情况呢,老师一定会等我们的。过了一会儿,又一条短信过来,简简单单几个字:老师走了。一瞬间我的泪涌了出来,学生们察觉异样围了过来,当我哽咽着说出老师过世的消息时,他们也都哭了,但是看到他们的泪珠滚下来,我却忽然一个激灵,连忙叫他们不能再哭了,当时距离晚上开演还有不到两小时,妆哭花了可以再补,但是嗓子哭多了要毛掉的,这样演出会受到影响的。好在学生们都很懂事听话,他们擦擦眼泪,我继续嘱咐:“今晚你们一定要卯足劲儿演好《红楼梦》,只有把徐派艺术传承好,才是对徐老师最好的怀念,最好的报答。”听完,他们点点头,忍着泪继续化妆。当大幕拉开,舞台上学生唱起老师那段熟悉的“如今是千呼万唤唤不归,上天入地难寻见”时,我的泪水和悲情交织在一起,那一刻台上是“哭灵”的贾宝玉,还是对老师最真诚的留恋、哀痛和不舍。直到当晚演出结束,全体观众自发起立为老师默哀,我难掩伤心,终于痛哭起来……
现在,老师走了,唯有传承好徐派艺术,带好这批学生我才能告慰恩师,报答师恩。老师,您放心,小家伙们都很争气,您在天有知也会护佑他们的,是吗?
钱惠丽:对待艺术,她一贯比生活付出得多
“惠丽,快来医院!”手机听筒里阿唐师姐的声音有些急促,我呆愣了一下又瞬间意识到了什么,立马回过神来拿起包离开了会场。4月19日这天,我本来是打算下午开完会就去看望老师的,但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让我提前赶了过去,17点18分,我敬爱的恩师,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含着泪,轻轻为老师画完人生最后一个妆。她一生追求完美,我知道她肯定想漂亮亮亮地和我们说再见。
老师,您忘了吗?上次您生日,我带着特地定做的健康无糖蛋糕来看您,您边吃边说“格个好吃”。于是我们拉钩约定,下次您生日我们还吃这个蛋糕。但是您,那个一辈子从不说狠话,但句句有分量、说到就一定会做到的您,怎么就食言了呢……
我来自浙江诸暨,高中毕业,我去考诸暨越剧团时,唱的就是一段自学的《红楼梦·哭灵》。那时,我便有了一个信念,那就是我要以饰演贾宝玉的老师为榜样,我要学她的艺术!
幸运的是,当时周宝奎老师退休后被诸暨越剧团聘去做指导老师,她看过我的戏后蛮喜欢我的,觉得我是块学徐派的料。于是她就找机会跟徐玉兰老师推荐,说:“诸暨有个唱徐派的小姑娘,嗓子条件很好,跟你年轻时声音很像的,不如你就收她当学生吧!”徐老师是个很严谨认真的人,即便老姐妹极力推荐,她还是撂下了一句“那也要听一听看一看才知道行不行”。
之后,诸暨越剧团想要带《红楼梦》来上海演出,但当时承演方对演出质量有所怀疑,为打消他们的顾虑,团里用录音机录了盘磁带,里面是几段《红楼梦》的经典唱腔。机缘巧合,这盘磁带辗转到了上海越剧院著名琴师李子川老师的手上,李老师是个风趣幽默的人,他揣着磁带去拜访徐老师,并佯装不知内情地问道:“老徐,你听听这个录音是你什么时候唱的?”听完磁带,徐老师有些疑惑,问:“这个我怎么也记不清楚了,是什么时候啊?”那时在唱腔上我是极力模仿老师的,没想到真的把她给糊弄过去了!听了这句话李老师大笑起来:“老徐啊,这哪里是你!这就是跟你说的那个诸暨小姑娘啊!”徐老師吃了一惊,立刻安排我来上海见她。来的时候我剪着个清清爽爽的短发,清瘦的脸庞还带着些害羞,站在老师面前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七上八下的,为了缓解我的无措,老师叫我即兴唱几句给她听,唱罢只见她点点头,我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了下来,看来,老师对我还是蛮有好感的。
后来,到上海来演出《红楼梦》的事情定了下来,剧团的领导想请徐老师演出前来指导一下。但是繁忙的徐老师实在抽不出时间去诸暨,于是我们剧组便提前一周来到上海,请她帮忙看一看。看完排练徐老师觉得搬到舞台上问题还是有不少的。于是她征求意见:“要我指导没问题,只是整个戏要全部推翻重新来过,不知你们愿意吗?”团领导满口答应。我听到消息开心不已,从小的榜样“贾宝玉”能指导我,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再困难我也会克服的。于是徐老师就从出场开始,一招一式地对整个戏和舞台调度进行了修改。其实,对于我来说,已经习惯了的表演要改过来是不容易的,但短短两三天下来我已经全部改过来了,徐老师非常高兴,夸赞我悟性很高。
那轮演出中,还有一段令我终身难忘的故事。那时因连续演出疲累,营养跟不上,某天演出我竟昏倒在台上,徐老师听到后心疼不已,为了能更好地照顾我,马上在自己家里的卧室中为我加了一张小床,要我吃住都与她在一起。为此,小勇哥哥和小敏哥哥还都吃过醋:“惠丽,你真是福气好!我们从来都没被妈妈这样照顾过。”老师听罢也只有笑笑。
那次《红楼梦》演出结束后,我的贾宝玉得到了很多的肯定,但徐老师却没有对我放松要求。她一方面告诫我不要听到掌声就头脑发晕,一方面又在为我规划未来的道路。作为红学会的成员,她想着我的贾宝玉观众认可了,新闻界肯定了,但还不知红学专家们欣赏不欣赏,她认为我的《红楼梦》要想在舞台上站得住脚,那些专家们的“鉴定”必不可少。不久之后,中国红学会在南京召开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学术讨论会,徐老师应邀出席,一到南京,她便积极奔走,盛情邀请了参加会议的两百多名专家观看特地安排的《红楼梦》专场演出。首演那天,徐老师还亲自上台,向南京观众隆重介绍了我,要知道那时我还只是诸暨越剧团的一名青年演员,老师不遗余力地为我奔波,这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
1986年,我足岁24岁时来到了上海,进入了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刚到上海,除了老师和观众,我可以说是举目无亲,而老师就像母亲一样给予了我很多很多的关怀。记得我生日那天,又是徐老师为我忙前忙后,张罗着在她家过了生日。老师专程去订了一个生日蛋糕,奶油足味道好,吃的时候她还狠狠地切了一大块递给我,叮嘱我:“你要补充营养,多吃点儿!”那时红楼团刚刚成立不久,我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她总是担心我营养跟不上,还买了牛奶冰在自家的冰箱里,要我每天去喝。除此之外,她更是时常自掏腰包买补品给我。我和徐老师之间的感情,是深沉醇厚、含蓄隽永的。对老师,我永远心怀尊敬与仰望。
艺术上,徐老师是很开通的。对于流派,她认为“流派流派,就是要流”,即在传承中要不断发展、创新。她自己就以身作则为我们树立榜样。《红楼梦·哭灵》和《北地王·哭祖庙》同样是“哭”,同样是“弦下腔”,却各有特色。即便晚年她还是一直不断吸收新的东西。如《皇帝与村姑》中,皇帝乔装改扮成算命先生时的唱段,徐老师还吸收了当时热播的电视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曲中的京韵大鼓元素,化用在自己的唱腔之中,无怪观众会赞赏这段唱新颖、别致又好听。
作为徐派传承人,在艺术上我自然也努力向老师靠拢,学习这样的创新。在我主演的《舞台姐妹》“饮恨”一场中,我借鉴了歌曲《说聊斋》中的音乐元素,用偏向民族歌曲的演唱方法处理唱腔。
对于自己的成功经验,老师曾总结说:“一是学,二是悟,三是化。学,就是广采博取,不断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悟,就是要迅速提高艺术感应力,努力培养自己准确把握剧种规律、敏锐领悟艺术美感、入微体察观众心理的悟性;化,就是把所学习所感受到的新东西,加以咀嚼、消化、改造、复合,再融汇糅合进自己新的藝术创造中。”
因此,在创排新戏的过程中,我始终牢记老师的“学、悟、化”三字经,并将它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如《玉簪记》《双飞翼》《甄嬛》等剧目,我都认真思考和尝试,化用川剧、昆曲、话剧等其他艺术门类的特长,用于自己的人物塑造,获得了一致好评。
此外,她还经常教导我要多看戏多学习。记得有段时间我因为工作繁忙,又要去观摩其他院团的剧目,累的时候我无意跟她嘟囔了一句“今天不想去看戏了”,老师听到了立即教育我说:“你要去看,如果感觉戏好,你要记下来,哪里好以后自己可以用;如果这个戏不好,你更要认真去分析,到底是哪里不好。只有这样才能在自己的戏里避免犯错误。”
除了艺术造诣,我还特别钦佩老师的艺德,并努力向她学习。记得有一次演出《红楼梦》,唱到哭灵“伤心不敢立花前”时,因连续演出的疲劳加上营养跟不上,彼时又完全沉浸在角色之中,难抑悲痛欲绝的情绪,我突然倒在灵桌上,休克了。经抢救醒来后,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把戏演下去,要知道徐老师过去抱病坚持演出可从没犹豫过!于是我不顾众人的劝告,撂下了句:“我不能让全场观众失望,我能挺得住,徐老师知道也会支持我的!”就又打起精神重新返回台上,坚持完成了演出。我患糖尿病十几年,但一直坚持创作演出。我坚定认为: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戏曲演员,必须具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忍常人不能忍的痛苦与煎熬,方能在舞台上熠熠生辉。
我走上领导岗位后,她常常告诫我“你做事情要为大家做”,“你要说话一定要站在大家的角度说”。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她也总是宽慰我“宰相肚里好撑船”,“成大事要有大的气量”。
她爱学生,总是掏心掏肺地教授我们;她爱美,总是穿着高跟鞋示人;她爱生活,做得一手好醉蟹令人念念不忘,但是对待艺术,她一贯比生活付出得多。
老师一生中最后一次走进剧场看的戏,是2014年6月24日在上戏剧院,那天是我的新戏《双飞翼》修改后第一次公演。那年老师已经93岁高龄,我也已经50岁了,但老师却还像老早一样嘱咐我“不要紧张,好好演就行”。老师,我还记得演出后,您一如既往地点评“还不错,打磨一下可以更好”。您总是这样,严厉又宽容地待我。
老师,您就这么走了,带着那么多人的不舍和眼泪。但是您放心,虽然您“违约”不能再赴今年生日蛋糕之约,但我绝不会忘记对您的承诺,我会更加努力发扬徐派艺术,将徐派传承下去。
老师,您一路走好,我会永远怀念您!
杨婷娜:对艺术“苛刻”,对后辈呵护
我和徐老师的真正缘分要从1995年说起,那时我进入上海戏校,专业系统的学习只有一年,头一年主要以基本功训练为主,第二年开始陆陆续续排演折子戏了。二年级的某天,教研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有些神秘地跟我说:“婷娜,明天有位老师要来学校帮你讲《哭灵》,你猜是谁?”我有些摸不到头脑猜了半天也没猜出,主任看着我一脸迷茫的样子哈哈大笑,并告诉我那个人就是徐派宗师徐玉兰老师,听到“徐玉兰”三个字我的脑袋“嗡”的一下,整个人兴奋地已经不能用喜出望外来形容了!能够见到徐老师,那电影里的贾宝玉,我心心念念的艺术家,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呀,并且这次不仅能够在现实中见到,而且她还会手把手教我,想到这里我真的是特别特别地激动。
到了第二天徐老师来到教室,看着她超级严肃的表情,我的心又开始噗通噗通紧张起来,她会不会觉得我唱得不好?会不会不喜欢我?这些问题飞速地在我脑海飘过,但还没等我继续想下去,老师已经开口叫我唱一遍给她听了。于是我赶紧调整状态唱起了《哭灵》,一段唱完她点点头,鼓励我说:“小家伙嗓子不错嘛!”听了这句话我心里美滋滋的,可她又说:“但是气息不够,唱法有些不对。你要学会用丹田气。”接下来她就开始教我呼气,练横膈膜,她拿着我的手放在丹田的位置,让我感受自己呼吸的力量,练了一段时间她又叫我躺下来唱,并且跟我解释:“躺下来对气息要求更高,要是你躺着也能唱好,那么以后唱就不成问题了。”在她的认真指导下,不仅我的《哭灵》有了进步,唱腔也有所提高。
毕业前夕学校老师为我选定《北地王·哭祖庙》一折作为公演剧目,这个戏在校期间是京剧老师帮我打的底,京剧要求规整的程式化动作,注重的是外部呈现和基本功是否扎实,在表演的情绪和人物的塑造上要求相对不高。临近对外公演了,教研组长又把徐老师请过来给我把关,尽管之前我唱过这段唱腔给老师听,但当我加上身段动作排出来给她看时,没想到她却毫不留情地宣判了我的“死刑”:“全部推翻,重新来过!”听到这里我慌了,考虑到演出在即的实际情况,我怯生生询问她:“老师,我们能不能这次先按照目前的套路演,等演出结束再重新抠?”听我说完这句话,老师皱了皱眉头用毋庸置疑的语气告诉我:“你这么想行不通,这个戏必须重排!我不要你加那么多炫技的动作,一点人物感都没有,那是个空壳子。这怎么演?怎么对得起观众?”听了她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不知道该怎么办,本来毕业公演我的底气就不是很足,短时间内重新推翻完全从头来,对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没有信心了,沉默了一会儿,细心的老师看出了我的顾虑,她拍拍我的肩膀说:“婷娜,这样,我们努力去试试,你能做到多少是多少,老师相信你。”于是我就在她的指导下,从出场开始全部重新来过,难忘古稀之年的她手把手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给我示范,既讲唱腔又讲人物还要重新抠站位。一天下来,别说是她,连我都累得够呛,但是在吃饭的时候,老师却默默地把自己面前的红烧肉、叉烧都夹到我的碗里,并嘱咐我说:“唱徐派对体力可是要求很高的,没有强壮的身体和持久的耐力是唱不动的,晓得吧?”然后慈爱地笑笑,再指一指碗里的红烧肉和叉烧,说:“你快多吃点儿肉,身体壮壮地唱好徐派。”
那次的《哭祖庙》让我得到了很多的肯定,我也收获了舞台上第一束鲜花。还记得那束花,虽然小小的但却令我非常开心,演出一结束我赶紧卸了妆,立马捧着花跑到复兴西路老师的家里,一脸自豪地把花献给她,老师笑盈盈地接过花对我说:“你可千万不要骄傲哟,这是对你的鼓励,希望你以后继续努力。”那幅温馨的画面我至今记忆犹新。
后来我毕业进入上海越剧院,老师因年事已高每个戏都亲自辅导已经不太现实,于是她便将我托付给了惠丽老师。惠丽老师对我尽心尽责,但即便如此,我在院里排的每台戏,只要她身体状况允许,还是会到现场为我把场,甚至那时排《皇帝与村姑》,有天排练结束她打电话给我叫我到她家里去,到了之后我才发现她已经提前让阿姨烧了满满的一桌菜,说是给我补补身体。于是我就边吃边听她给我讲戏,从唱腔到人物情绪再到整个戏的调度,她边讲边示范其中的唱段,一顿饭下来我开玩笑地说:“老师您饭基本没吃,但戏却唱了有半场了。”她爽朗地大笑说:“这还远远不够呢,走,我们到楼上去,我借了邻居家的大客厅,你去走走戏!”就这样,又是一招一式地细抠和讲解,她全程站着为我示范,直到夜里十点。
对艺术,老师不仅是严谨的,同时也是开明的。她一直鼓励我们打破界限,勇于创新。记得后来要参加“小蝶杯”青年演员大赛,我想移植一出京劇叶派的《小宴》参赛,于是跑去征求她的意见,没想到她听了之后十分高兴,肯定了我,说越剧女小生武功功底相对薄弱,对于刚刚戏校出来的我来说身上功夫还在,《小宴》是出很考验人的戏,试试看也算是一种历练了。得到了她的支持,我有些“得寸进尺”向她说明,有意想请京剧院的杨渊老师来传授我这出戏,她立刻表示赞同。很快,我就在杨渊老师的帮助下学习了整出京剧《小宴》,后来又在几位老师的帮助下,把它移植成了越剧。在这出戏排练的过程中,徐老师时刻关注着我,待整个戏基本拉出框架来之后,她又特地为我请来了化妆师,在她家里为我造型、试妆。试妆时,老师不断根据吕布这个人物的特定性格对我们提意见,比如眉毛应该怎么画更有少年得志的张扬,眼梢稍微往上拉一些更显得英气,化妆师就在她的建议下一次次修改,直到她满意。演出时,她又早早来到后台为我把关,看到我的面红不够,她直接拿起笔刷亲自为我改妆,服装穿好,她又围着我看了半天,帮我整整衣领折好水袖,直到确认所有环节无误,才拍拍我肩膀说,上台去吧。
如今老师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难忘老师一点一滴的教诲,今后,我会尽自己的全力把徐派传承好,您放心吧。
(整理/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