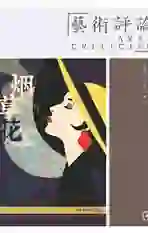拷问城与人
2017-06-14刘妍
刘妍
冯大庆编剧、王晓鹰导演的话剧《失明的城市》取材于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的长篇小说《失明症漫记》。小说和话剧都有一个关键词:“失明”,其实,这里失明的并不是人赖以生存的城市,而是活在城市中的人。编剧和导演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原作的改编与重构。其重构是建立在尊重并彻悟原著基础上的再创造,既没有偏离原作,更没有歪曲或颠覆其思想,而是以适宜的手段,经由本土化、现代化的审美,构筑了一个——既不失原著精髓又符合我国国情的艺术殿堂。带着观赏时的震惊与震惊之余的沉静,潜心比较和研究,一边是小说原作,一边是剧本在几个细雨的夏日,我对话剧及小说原作进行着“反刍”。雨时急时缓、时大时小,伴着清凉的雨滴,这部奇异的戏剧,在我的内心膨胀着。和在剧场一样,剧中一个个纤细的触角不断撩拨着我的内心小说原作者萨拉马戈说的不错,看这部小说需要有坚强的神经;他的话同样适用于观赏取材于这部小说的剧本和话剧演出。
戏剧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实验室,这是许多戏剧家的共识。就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关注而言,没有哪种艺术样式能够如此直接、逼真而生气盎然。小说的力量是透过文字浸润在行文的字里行间,而戏剧是通过表演挥发在舞台的角角落落。“戏剧由于其有形性——而且由于它要求唯一真实的表达,即空间的表达——能够使艺术和话语的神奇手段有机地并且全部地施展开。 ”[1]这部戏成功的关键也正在于舞台艺术和话语手段的有机且有效的施展,即创作过程中“空间的表达”,具体体现在剧作改编中的城市意象的有意凸显。
城市意象在剧中的凸显不仅为演出提供了视觉奇观,更重要的是,城市已然成为人文背景,这无疑为这部剧增添了思想分量和现代意味。城市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标志,它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方便、快捷和享乐;同时,城市也是人类罪恶的渊薮,它不断滋生着淫乱、野蛮和霸权。在对现代性的追问中,人们未曾间断过对城市异化现象的反省。城市吞没着人,使人性扭曲变形,在城市的挤压下人几乎被压扁成为了可怜的碎片。但另一方面,城市对人的消解程度却因人而异。有良知的知识人从来就是城市腹中最难以消化的、最坚硬的部分,比如這部剧的编剧、导演和原小说作者,他们就是城市中具有硬度的最难以消化的分子;他们以文化情怀和艺术志趣宣告了自己对于城市的反叛倾向:
黄昏。繁华、喧闹的城市,高楼林立,人群熙攘,霓虹闪烁。
汽车的刹车声、警笛声、风格各异的乐声、男男女女的交流声在城市上空形成怪诞的交响。
剧本的开篇就奠定了剧的基调,剧作家以对城市的离心姿态显示了自己对于城市的叛逆:在市声繁华的反衬下,城市人渺小而可怜,成为被压榨被掌控而麻木不知的——失明的人。
在审视并表现其叛逆姿态时,剧作承继了原作的精神气韵——对人性的深度拷问。小说和剧作里城市中的人处于一个极端残酷的情境中——失明。而患失明症的人们并非真的失去了视力,更确切的说,他们失去的是理智。正如作家本人所指出的:“归根结底,这部小说所要讲的恰恰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理智上成了盲人 ”[2],“我们大家都是瞎子。说是瞎子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够创造一个值得我们生活于此的世界,而现在这个世界不值得” [3]。理智上的 “失明”,看不见自身的弱点,看不到自己兽性的一面,自高自大,失去自我审视的结果就是人类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尊严与体面遭到严重践踏,世界走向残酷与邪恶,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从这个角度说,小说《失明症漫记》和剧作《失明的城市》不过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和现代人生存现状的一个缩影。小说和剧中一个个惨烈的镜头预示着现代人已经病入膏肓,要将现代人从人性沉沦的深渊打捞上岸是何其艰巨而漫长的人类的要务。尽管如此,小说作者和剧作家都固守着一个理想:人的尊严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剧作借黑眼罩老人之口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我们已经一无所有,只剩下这最后一点儿当之有愧的尊严了,至少我们要为属于我们的权力而斗争。 ”小说和剧作再三强化了一个共同的意念:“活着的人们需要再生”。
萨拉马戈在原作扉页用“箴言书”形式写了这么一句话:“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看见,就要仔细观察。 ”经由作家和剧作家的苦心经营,依托着失明这个虚拟的假定性,现代人实现了一次难得的内心的审视与精神生命的净化、再生。
为了深切而艺术地表达剧中现代性意蕴,在戏的细微处,话剧《失明的城市》在原作的基础上充分张显了具有剧场效应的戏剧元素,在戏剧情境、人物及人物关系的设置等方面,对原作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人物谱系更加明晰,情节更加简约蕴藉而富于动感。具体体现在情境设计、人物设计与塑造等方面。
戏剧艺术的直观性有别于观赏小说,较比原小说话剧《失明的城市》在整体架构上,凸显了舞台空间意象。生硬高耸的阶梯建筑营造了冷漠、疏离的现代生存空间,这个象征性舞美语汇将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盘托出。
在具体情境中,话剧与原作差别最大的有两处。一是导致偷车人死亡的原因;一是第一个失明者对待妻子“服淫役”的态度。关于前者,小说中偷车人腿伤是因戴黑墨镜的女子愤怒于他的调戏用鞋跟踢伤了他的腿。而剧作中,是由于患了失明症,偷车人被警察强制抓进警车,推搡中他的腿被车中坏掉的椅子露出的铁棍戳伤。尽管是一个小小的细节的差异,却显示了不同的创作指向。小说重在强调偷车人的人性的弱点;而剧作则意味深长。警车是权力的化身,警察是城市的霸权者,伤由他们造成自然强化了城市霸权者对失明症患者的强权与冷漠;也正因此,他的死更加令人思索和怜悯。至于后者,对待妻子的态度正是衡量男人的人性底线。剧作与小说相反,第一个失明的男人主动劝妻子去服淫役,这与他自私狭隘的小市民气一脉相承顺理成章;而小说中他阻止妻子同样是出于自私,让别人的老婆去服淫役,自己坐享其成。相比而言,剧作中更显其卑微与无耻,连同他老婆来到疯人院时他惊喜的喊叫“你也瞎了,太好了”等细节,对这个男人劣根性的暴露入木三分。
话剧《失明的城市》的人物谱系,除了个别因舞台演出效果做出调适外,与原作基本一致。对小说原作调整幅度较大的是戴黑眼罩老人形象的挪移和提升。小说中老人的许多细节在剧作中得到了保留:比如他带来了录音机,启发大家讲失明前的最后瞬间等,而最大的不同是,在剧作中,剧作家赋予了老人一个智者的形象:大彻大悟,敢做敢当。老人很清楚自己患失明症的原因:“在失明的那个时刻我们已经是盲人了——害怕让我们失明,害怕让我们仍然失明。 ”“人有两个自我,一个在黑暗中醒着,另一个在光明中睡觉。 ”他认为:“一切都是境遇造成的我们是能看但看不见的盲人。 ”当医生的妻子达琳杀死了盲匪,其他人为了保全自己希望她自首,达琳怕连累了同伴们也想自首时,老人坚定地说:“要是谁敢去自首,我就用这双手掐死她! ”他说:“在我们被迫生活的这个地狱里,在我们自己把这个地狱变成地狱的,我们应当感谢那个有胆量进入虎穴杀死饿狼的人! ”在许多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都是他力挽狂澜——“我们用自己的手去拿食物。 ”在盲人反抗中,他无疑是一个暴动的领袖,当大火燃起,又是他毅然决然地带领大家冲出火海获得自由。剧作赋予了老人智者的情怀,于是在剧中智者与圣母般贤达的琳达相映成趣。不能忽视的是,正是他的自在与超脱,游魂般的跳入跳出,无形中为戏增添了神秘色彩和宗教意味,也使这部戏的悲悯情怀更加强悍炽热,较比原作老人形象在剧中更具符号性,更有象征意味。也因此,他为剧作增添了另类的神秘和灵动。
在人物关系设置上,剧作与小说有比较明显的不同。除了简化群体突显主要人物外,最大不同在于戴黑墨镜姑娘的人物关系设置上。
剧作中,将她的“爱情”对象由小说中的老人位移到医生。应该说,两种笔墨处理各有千秋。小说中,处于失明状态又被关在精神病院的姑娘爱上了老人(小说中,老人并非具有人格魅力的智者),而当她复明时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他——谢了顶的老人。两相对照,在特殊情境中人性的孱弱或者严重些说人的动物本能自然托出。而剧中,黑墨镜姑娘爱上了眼科医生博尔,这不能不说是剧作家的高明之举。她爱上了医生,因为“疯人院里我太孤单了,心里总感到恐惧”。内心的孤单和恐惧使她爱上了医生;而医生与她的恋情是缘于“内心的脆弱”。与医生内心的脆弱与爱的自私相对,他的爱人琳达的爱显得博大笃定:因为爱情誓言中的“我愿意”,她毅然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与煎熬,坚韧地陪伴在丈夫身边,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爱护着身边的人,为他们解除各种艰难困苦。令人悲愤的是,当一切尘埃落定,她舍弃性命固守的爱人却背叛了她,她的爱情随风而逝,她不得不悲哀地承认:“也许我是所有这些人当中最瞎的”这位在丈夫眼中“最后的理想主义者”在惨淡的生活中不能不感慨:“我想我们没有失明;我想我们本来就是盲人。 ”在爱情上的失明与残酷的现实让她闭眼沉默,“真希望一切都不曾发生”。当大家因复明激动地笑时,只有琳达——“喜极而泣”。琳达的悲剧远非她个人的悲剧,而是都市生活中爱与美的共同际遇:在欲望與诱惑面前,在人性的沉寂处,爱与美只能被肢解而溃败。与原作相比,这种人物关系的设计使琳达的悲剧命运更加撼动人心,从而强化了戏剧的悲剧效果。
比较小说原作与剧作更容易体会阿契尔之谓: “小说家的语汇中的‘适宜的(advisable)一词,用戏剧家的语汇来翻译就应该是 ‘必须的(imperative)。小说家好像是在玩一个时间拖得很长的牌局,而戏剧家则必须尽其所有在一次里孤注一掷。 ”[4]“孤注一掷”是冒险,更是义无反顾的挺进——向着剧场这个神圣的殿堂。在这个近乎极致的戏剧挺进中,剧作者冯大庆完成了她“所希望的表达”:“它很极致,不受种族、政见、派别、意识形态的局限,抒发的是人类共同的心声,面对的是所有人都可能面对的问题、困境,甚至灾难;它还应该好看,艺术而自然地传达人们对幸福的渴望、慰藉、温暖” [5]在把握原著的基本主题、价值取向、人物命运和现实境遇的基础上,剧作更重视挖掘原作中所蕴涵的穿越时空的精神气质和艺术能量,使原作的思想蕴涵找到了恰当的途径、得到了有效的释放。从这个角度而言,改编的成功决定了剧作思想和内容的成功,因为“戏剧的最异乎寻常的、能够激动和深深震撼观众心灵的强大的力量,是思想,是内容”。同时,就戏剧而言,其内容又不止于剧本,还包括“演出、演员表演的内容,导演的演出设计内容,美术家的布景的内容,配乐的内容,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并与戏剧的 ‘一切艺术结成联盟的内容。内容,只有内容,才是戏剧的主要力量” [6]。所有这一切的联盟,特别是戏剧情势、人物对话的生机盎然连同戏剧空间的生气勃勃使《失明的城市》保有了字词以外的扩散力和戏剧空间的发展力,更使它有效地作用于人最敏感内心,从而具有了一种弥足珍贵的内视力。
在实现文学文本向舞台演出文本的转化中,该剧不乏可圈可点之处,特别是,导演王晓鹰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的导演艺术始终着意于:“导演语言能否使人思想,而不是使思想明确化。 ”[7]把书面的文字“死”的语言向舞台上“活”的表演的转换中,编导者们似乎更着力于让经典原作真正地“活”在观众心中。和原作的“极致”描写相辅相成,舞台呈现比原作更具有强烈的视听冲击力,身体、声音和情绪表达通过音乐语汇、肢体语汇等营造直抵人心。如此舞台呈现源于改编者和导演及演员足够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功力,源于他们抓住了经典文本中人物的“魂”,并通过自己的感悟和理解准确地传达出来。《失明的城市》及王晓鹰之前执导的《萨勒姆的女巫》《哥本哈根》及之后的《深度灼伤》等剧目,对人的深度思考、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使他这些作品胸襟博大、悠远深邃、卓尔不群。
《失明的城市》卓尔不群,它入筋入骨、入情入理,炽热又荒凉。饱满而充盈的舞台展示逼视并拷问了城与人的魂灵,对情绪鼓荡着的都市与人《失明的城市》不无镇静的作用。凝视剧作和演出,我们不能不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盲人,我们的城市是不是已经失明不管是否喜欢这类题材,观者都无法否认这部话剧改编的严谨、科学和成功。编剧冯大庆的文本改编和王晓鹰的舞台呈现比较完好地守护和弘扬了这部西方经典文本的文学高度、人文价值和艺术趣味。特别是,这部戏的改编在创新与超越的同时,更有效地维护了文学经典的价值与权威。当下,伴随“娱乐至死”越演越烈,经典文本改编的话剧乃至影视剧无厘头的戏仿、肆意颠覆甚至无聊的穿越大行其道,经典改编的底线一次次被冲破。面对经典遭此被蹂躏与践踏的厄运,我们四顾茫然的时候,更需要经典改编的经典案例,更期待藉此探索经典改编成为新经典的艺术创作经验。只有经典改编也成为新的经典,经典的再生能力才能显示其威力,才能更有效地传播经典文本的思想、文化与艺术价值;惟其如此,经典才能更充分地彰显其自身的生命力和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