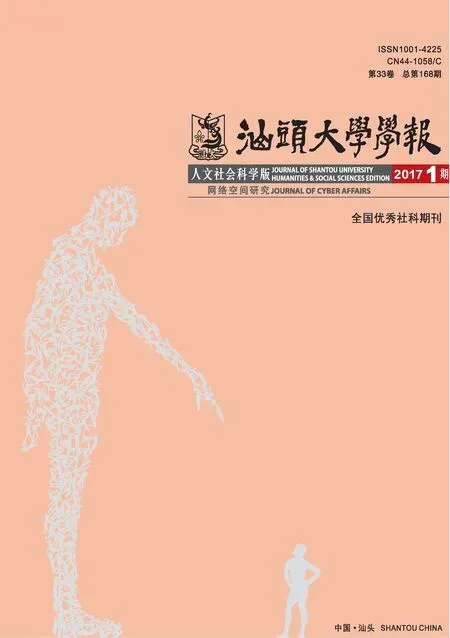新媒体与公共领域的重构
2017-06-12段永朝
段永朝
新媒体与公共领域的重构
段永朝
公共领域的兴盛和衰落,伴随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全过程。在互联网背景下,随着信息经济崛起,公共空间的重构有哪些新的可能,以及新媒体在公共领域重构中将扮演何种角色,是思考信息社会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欲理解信息社会公共领域如何重构,要充分理解公共平台的丰富性和公共意见表达的多样性,聚焦公共领域权力、意义与秩序的建构方式,在新的互动、传播机制下探索公共领域的构建路径。
公共领域;新媒体;信息社会;认知科学

段永朝财讯传媒集团(SEEC)首席战略官,网络智酷总顾问。高级工程师。中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员,数字论坛创始成员,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企业导师,北京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特聘教授,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特聘教授。
说到公共领域,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哈贝马斯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①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这本书原名为《Strukturwandel der Oeffentlichkeit》。对于“Oeffentlichkeit”一词,在汉语学界有“公共领域”、“公共论域”、“公共空间”等不同译法。根据国内哈贝马斯研究的权威学者曹卫东博士的解读,这个词涉及两个不同的层面,即社会层面和思想层面。从思想层面看,“Oeffentlichkeit”指的是个体和共同体(包括社会和国家)的一种特殊观念,是一种韦伯式的理想范型,兼有批判的功能和操纵的功能;就社会层面而言,“Oeffentlichkeit”指的是一个话语空间,它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充当二者的调节器和修正仪。思想层面上的“Oeffentlichkeit”可以翻译成“公共性”,而社会层面上的“Oeffentlichkeit”则应当翻译为“公共领域”。②曹卫东,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其他,中华读书报,1998年11月4日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总体上说了两件事:一个是十八、十九世纪公共领域是怎么兴盛的,另一个就是怎么衰落的。迄今为止,我们今天所存在、感受到的,依然是那个“衰落了的”公共领域。所谓“衰落”,就是指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公共领域,蜕化为商业机构和政党利益集团的附庸,公共知识分子丧失了批判精神。但是,互联网是否是公共领域重建的契机?这是我们将公共领域视为互联网思想基石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怎么理解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公共领域?互联网到底提供了公共领域重构的哪些可能?这个公共领域还是哈贝马斯思考的那个公共领域吗?显然不是的。哈贝马斯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他思考的是现代性背景下的公共领域。互联网背景下的公共领域,一定是交织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那个公共领域。
三个事例
先讲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2013年美国波士顿爆炸案。2013年4月15日当地时间下午2点49分,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现场发生爆炸惨案,造成3人死亡,264人受伤。警方对此案的侦破过程中,非常迅速地启动了网友参与提供线索的机制,为迅速侦破案件提供了有力的帮助。①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ston_Marathon_bombing这是一个借助众包力量抓罪犯的典型事例。
第二件事情,与“高频交易”有关。所谓高频交易(HFT),就是全程由计算机自动下单完成的证券交易。②蓝海平,高频交易的技术特征、发展趋势及挑战,证券市场导报,2014年第4期,p59-64高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每秒钟下单的次数会达到成千上万笔。每一单的速度是以毫秒计算的。10年前,从华尔街涌向硅谷的高智商人群中,有一个群体叫做“宽客”(Quant),③Emanuel Derman,《宽客人生》,中信出版社,2007年7月这群受过数学、物理学、金融学专业训练的高智商人士,致力于用数理模型、大数据开发各类复杂多样的金融衍生品,并使用各种专门的交易算法、风险模型进行统计套利。
第三个例子,发生在新闻传播业。2014年3月18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发出了第一条当地4.4级地震的消息,这条报道,是由一个叫做Quakebot的机器人做到的。这个机器人,已经在《洛杉矶时报》运转了十多年。④腾讯科技,别惊讶,机器人才是洛杉矶地震首篇新闻报道作者,http://tech.qq.com/a/20140319/010344.htm过去一年里,机器人在新闻媒体的应用事例层出不穷。比如新华社就在财经、体育新闻报道中部署了一款叫做“快笔小新”的新闻机器人,每3秒钟就可以制作一条新闻。腾讯则在2015年底,发布了自己的新闻写作机器人Dreamwriter。
通过这三个事例,可以看出互联网、大数据、算法、模型,已经深深嵌入到这个世界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中。但是,今天很多做新媒体或者是拿新媒体说事的,说的无非是两件事:第一是把它当投资的商机,第二是把它当作营销、套利和舆情操纵的工具。如果讨论新媒体只是从这两个角度去谈,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从这些事例的背后,看到新媒体对新的公共领域构建的可能性,以及新媒体在公共领域构建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一定跟我们当下的想象不同。不同在哪里?就在于机器已经卷入到公共空间的日常生活中来了,它通过高频交易、机器人新闻报道、众包的方式抓罪犯等等方式,参与到公共空间构建中来了。这首先有别于哈贝马斯的那个公共空间。所以我们需要在新的公共领域建构的前提下,重新理解媒介的功能和公共领域的建构。
公共领域:新媒体的变革核心
新媒体变革的核心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仅仅把它当做新的媒体传播手段、新的事件营销方式,以及新的舆情分析工具的话,恐怕会遮蔽新媒体的重要变革价值。新媒体也不仅仅是社会互动、媒介赋权、舆论建构的新场域、新模式。新媒体到底对社会带来哪些重构的机会,对公共领域带来哪些重构的机会,需要在赛博格、人机共同体、平行世界、多重主体等这些全新的语境下思考,需要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机器人、区块链、物联网、分享经济等蓬勃发展的语境下思考。
今天的信息科技、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已经在认知科学的大背景下交织、融合在一起。⑤Cognitive Science,1978:Report of The State of the Art Committee to The Advisors of The Alfred P.Sloan Foundation;October 1,1978;参见:http://csjarchive.cogsci.rpi.edu/misc/CognitiveScience1978_OCR.pdf2002年,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和商务部,共同组织了56位不同学科的学者,起草了一份482页的研究报告,名字叫做“改变人类的聚合科技: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Converging Technologies for Improving Human Performance:Nanotechnology,Biotechnology,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这份报告中有一句掷地有声的预言:四大科技的聚合,将会改变未来人类这个物种。①Converging Technologies for Improving Human Performance:NANOTECHNOLOGY,BIOTECHNOLOGY,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NSF/DOC-sponsored report,Edited by Mihail C. Roco and William Sims Bainbridge,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June 2002
在前沿科技与社会创新、经济发展密切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五年后、十年后,这个世界会变得“面目全非”。我们思考新媒体和公共空间的语境一定会发生重大的迁移,不能仅仅认为新媒体是帮助媒介机构渡过一个什么样的关口,也不要指望新媒体是为了帮助某一派去战胜另一派。
互联网对今天大学里教授的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政治学,以及这些学科的立足之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互联网最先挑战的是经济学。从电子商务开始,互联网就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提出挑战,比如物质的稀缺、人是自私的、分工创造财富等等。今天曙光初现的分享经济,让人们看到了合作也是人的天性,看到了这个信息富足的社会,以及多种可能性的社会。从规模经济到范围经济,将信息视为新的生产要素,跨越企业边界的融合创新,自由职业者的自由联合,这些都会深刻地改写传统经济学的教科书。
社会学的学理基础也面临巨大的挑战。过去传统社会学从法国思想家孔德开始,到今天仍然没有脱离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用结构动力学观点看待社会的组成要素、组成原则和运行规律。这完全是牛顿力学的观点。在今天互联网网民已经超过自然人口一半的情况下,在智能终端业已极大地塑造了人们的日常行为的情况下,人与人的连接成为常态,连接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纽带,基于这种连接的信息流动、情感流动、思想流动,成为塑造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的重要力量。
还有一个就是政治学和传播学。与罗斯福被称作广播总统、肯尼迪被称作电视总统相仿,奥巴马被称作互联网总统,而新当选的特朗普,则被称作社交网络总统。当社会运动、社会民意随时在虚拟空间传播、散布、流动的时候,虚拟空间里凝聚的政治表达、政治意志、政治团体,就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并与现实世界形成强烈的互动。西方学者已经在非常宽泛的领域,研究“实时全民公决”随时可以发起、可以进行对当下政治意味着什么,研究性别政治、身份政治在互联网赋权机制下的新内涵和新表征。今天的政治学,一方面进入了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炫酷科技下的计量政治学,另一方面又在强大的、汹涌而来的草根民意下,瞬间瓦解。特朗普胜选,或可作为反思传统政治学准则的一个参照。
传播学也是如此。传统的传播学是奠基在旧的信息理论的基础上的。消息、信息,被视为可以“搬运”的箱子。媒介的物理功能,就是扮演搬运信息的角色,致力于消除信息不对称,并将此上升为“看门狗”、“把门人”的道义高度。然而,工业资本主义200年的兴盛历程,已经充分说明这样的事实:媒介机构已经沦落为权力意志的附属品,沦落为权势集团、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和帮凶。这是媒介的真实生态。这也是哈贝马斯分析资本主义公共空间从兴盛到衰落的重要结论。
新媒体变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面对公共领域的重构的挑战。公共领域的重构,并不是“恢复”到过去那种公正、中立、圣洁的状态。今天的公共空间中充斥着多样化的意见表达、情绪表达,充斥着后现代元素,比如恶搞、拼贴、反讽、人肉、卖萌,这些新媒体事件以后现代方式展现自身的存在,参与、互动、自我表达并非可以用过去的分析框架、分析工具予以收编和综合。公共空间并非静止不动的同质空间,而是高度变异的异质空间。这首先提出一些问题:公共领域的“重构”意味着什么?公共领域的“重构”,是传统的建筑师、工程师的风格吗?这种重构如何冲破工业主义的逻辑,如何体现互联网的风格,体现自组织的涌现呢?这是理解公共领域重构的思想基础。
新媒体与公共领域重构的关系
借助互联网和智能科技,新媒体让我们进入了触觉时代。触觉感知和以往通过视觉、听觉感知很大的不同就是:触觉是非线性的。这对于媒介而言是一件大事。传统媒介之所以受到互联网、新媒体的巨大冲击,就是因为过去的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它是线性叙事。线性叙事的法则,就是传播过程是顺次展开、先后相继的。但是触觉叙事是可以边“摸”边看的,它可以同时进行。这种媒介内容生产与消费的“并置性”、“同时性”,是新媒体非常重要的特点。超链接、超文本和交互叙事,完全解构了传统的线性叙事,展现出一个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的“互文空间”。互文,就是不同文本之间的对话。
在这种境况下,媒介机构已经不可能通过控制节目单、栏目设置、选题,来控制议程,掌握话语权。隶属于传播者的话语权已经被传播者和受众共享。工业时代的大众媒介把公众变成了大众(Mass),变成了大批量生产。信息时代的新媒介让大众重回公众,这是公共空间、公民社会得以成立的基础。
此外,媒体的把门人规则可能被颠覆。传统社会里,记者被称作“无冕之王”,媒体被视为天道良心的载体。目击者、见证人、把门人的身份,在新媒体里需要重新思考。对媒体这个“中介”来说,互联网“去中介化”即意味着媒介扮演的传统的信息中介,特别是信息的“物理中介”的角色将被颠覆。在印刷机时代、纸媒时代,媒体的一个使命就是把信息从这边搬到那边去。好比一个送信人、一个信使。互联网在去中心化的同时,也在去中介化。很多传统媒体的焦虑正在这里。中介性是媒介的立足之本,这一点似乎无可争辩。媒介作为一个行当,特别是作为靠发牌照才能获得合法性的特殊行当,中介的合理性,就被误以为也是靠发牌照来保证的——这一点恰恰害了媒体。发牌照,只是说你的运营合法性,但不是你的“中介合法性”。很多传统媒体没有看清楚这一点,于是就希望官方总是用牌照来设置门槛。互联网对这种做法是嘲笑的。
这种嘲笑不能说毫无道理。有牌照会有秩序,在工业版图下有其合理性。去中介化之后,把门人规则失效了,门槛变成零了。传播学或者新闻理论,对媒介身份的认定,恐怕就不能将“中介”看作一个本质特征了。当然,媒介依然担负着传递信息的责任,但在“去中介化”趋势下,媒介不能将“中介”视为自己独特的权力。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目击者、报道者,真相有赖于社会网络的长期质疑,而不是哪一个媒介观察者的断语。可以说,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传播是零门槛。
第三,媒介与商业机构联盟,这在现代媒介诞生之后就存在了。媒介的“二次营销”理论,就是基于与商业环境的共生关系。一次营销把内容卖给受众;二次营销把有购买力和消费欲望的受众,卖给广告主。新媒体环境下,仍然有人希望这个二次营销继续奏效,并且是以“武装到牙齿”的方式,即媒体人操弄着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式的媒介武器,一边更快地售卖内容,另一边更精准地售卖广告。这是媒介的未来吗?或者说,这是我们期待的,肩负公共空间构筑使命的那个媒介吗?这是很深层次的核心问题。媒介的立足之本受到挑战。我们需要问:未来媒介跟商业是何种关系?
欲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重新审视什么是未来的商业。今天我们熟悉的商业环境,是与工业化进程相伴随的商业化。在这个大的框架下,你可以看到GDP主义、增长导向、创富故事、金融大亨,你也可以继续看到对确定性的迷恋,对预测、控制的无可扼制的偏好。今天的商业化已经变成了癌症。这不单是人和环境、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问题,还有国家和国家、群体和群体、人和人自身的历史的关系问题。全球都是如此。很多拯救地球、绿色能源、救助欠发达地区的儿童的事情,最后都不得不变成一个又一个的项目,纳入到工业化的滚滚巨轮中,苟且存在。在工业化的话语依然强大的时候,探讨未来新的商业生态、商业文明,注定是贫乏的。“GDP导向”批判,不是喊两句口号,也不是把GDP刷成“绿色”就能够实现的。这需要根本上的转变,当然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够发生的。
公共领域重构的反思
公共领域重构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有密切的关系。在经济领域,会发生哪些深刻变革呢?分享经济的兴起已经初现端倪。除此之外,对GDP的追求,或许会逐渐转到“快乐经济”,转向“全民总酷值”,从有限经济转向普遍经济①乔治•巴塔耶,《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乔治•巴塔耶文选》,吉林人民出版社,汪民安译,2003。(巴塔耶的观点,值得系统研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再狭义地追求GDP,扬弃“生产和消费两分法”的思想,认识到互联网时代最本质的经济特征,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一(Prosumer);②托夫勒,《财富的革命》,吴文忠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6月生产与消费不再是相互剥离的过程,而是“同时”、“并发”的历史进程。必须看到,生产中凝结着消费,生产本身就是消费;消费中孕育着、滋生着生产,消费本身就是生产。在“产消合一”的总框架下,什么最重要呢?Happy(快乐、幸福)最重要,玩儿high(玩儿得尽兴)最重要。其实真正的happy,并不需要消耗很多东西。95%的东西是被浪费掉的,而不是被消费掉的。正如白炽灯泡一样,白炽灯95%的电能是被消耗掉的,而不是被用来点亮的。白炽灯是工业时代的象征。对真正的快乐和幸福来讲,95%都与它无关,都被浪费掉了。不是消耗在这个领域(比如经济领域),就是消耗在那个领域(比如社会领域),或者消耗在某些“伪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构建,就是公共领域要与快乐经济结缘。公共领域的职能,已经超越了批判阶段,它并非要杀富济贫,也不要自恃正义。公共领域并不是要介入到传统工业经济的某种游戏中,扮演某个仲裁者、制衡者的角色。它需要新的游戏。这种游戏事关人的连接行为、认知。关于人的游戏,要重新改写、重新改版,这才是互联网对公共空间真正的颠覆。
按照桑内特的观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衰落,与传统媒体的侵蚀不无关系。③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7月今天的媒体新生代已经感受到了自己所肩负的双重使命,就好比一个身患绝症的人依然要拉家带口,要支撑家业一样。传统媒体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它自己已经身患重病,但依然不得不受到商业变革的胁迫、政治对垒的绑架——更重要的是,它迫切需要自己的新生。
从这个极度痛苦的煎熬中,我们看到,公民记者、自媒体、公民新闻这些东西已经在顽强地生长,在风起云涌地展开,好比春风化雨一样,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尝试着为我们找到一条此前并不存在的道路。展开的过程中我们会遭遇到很多现实的焦虑。你会遭遇到很多揪心的问题,比如你依然会问:是否存在新闻真实?新闻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但无论如何,一定要常怀“超越”之心。“超越”和“求解”是两种不同的心态。“求解”就是典型的工业思维,认为这道题总是可以解出来的,解不出来要不是你笨,要不就是这道题出错了。但超越思维不是这样,它是承认这道难题之所以“难”的合理性。“超越”就是先把它放下,搁置起来。超越,就是承认某些问题一时间难以获得最终的解答,甚至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答案,在这个前提下,如何看待公共空间的秩序?这是互联网环境下提出的一个新问题。
在这种处处两难、时时纠结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更大的画面,是远景的画面。这就是互联网对人的重塑。从根本来讲,信息的自由流动其实是很朴素的、其貌不扬的一句话。就像微博上说的一句话:转发就是力量。比如“公共领域”这个词的确不错,但是它忽略了很多难题。其中一个难题,就是无论哈贝马斯还是阿伦特,他们都没有见识过“草根的世界”。草根的世界,今天看貌不惊人,其实里面蕴含着大量前所未有的新意。
其实,不管这是否荒诞,我们需要承认,未来虚拟空间这个领域不能忽视。我们现在还是在用传统的视角在看待和使用互联网,但是将来它要变成你真正的生活场所的时候,会怎样?那时候康德和黑格尔,就只是一种思想的道具,人们还会有其他的思想的道具,那时候新的哲学思想会是什么?我觉得,公共领域的构建,真的忽略了机器进步的步伐,忽略了互联网带来的变化,也忽略了脑神经网络对社会记忆的颠覆。托夫勒曾经说,互联网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记忆体。三十年前他就预言,我们有很多记忆会交给网络,人脑的记忆体将来的分工会发生变化,人脑中80%的东西将来要清空,要让互联网承担记忆的功能。如果集体记忆发生转向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惊人的画面啊!
所以,当我们真正站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角度下看待公共空间构建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把互联网当作工具、当作物理性的。当然现在互联网的成熟度还很低。现在的互联网还是幼年期,甚至胚胎期。今天的互联网不要看它很牛,很让我们张皇失措,但其实它还很小很小。这其实还只是互联网的史前史。它需要经历艰难的“解毒”过程。解什么“毒”,就是解工业化之毒。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以为互联网与工业化是势不两立的。不是这么简单。互联网脱胎于工业文明,一定继承了工业时代的特质,比如对速度的热衷。但互联网一定有它独特的、反叛工业文明的思想基础,比如拒绝确定性、拥抱复杂性,因为复杂性才是孕育生命的土壤。
哈贝马斯与阿伦特的差异
依据哈贝马斯的论述,他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是18世纪自由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在那个时候,资产阶级中有教养和卓见的阶层,自发地聚集在被称为公共领域的公共空间如咖啡店、沙龙等场所,自由论政、高谈阔论、臧否时代,充分发挥公民社会制衡政府的作用。但是,这种理想的公共领域却在伴随资本主义日益发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空洞、虚饰,甚至反动。哈贝马斯说,“尽管它依据一种理想来表达自己,比如所有公民都可以参与讨论,但在实践上这种理想远未达到。劳动阶级被排除在外,这就意味着一些根本的问题被排除在讨论之外。在权力和经济利益方面,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是同质的。资产阶级任何成员之间的个体差异主要是经济利益,并在市场中表现出来。存在于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巨大经济利益冲突并不在讨论之中。实际上,这种利益冲突甚至在政治上不被承认。”①[英]埃德加(AndIe Edgar)著,《哈贝马斯:关键概念》,杨礼银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5-126、126、127、38页。
十八世纪建立起来的公共空间,之所以注定会走向衰落,根由就是哈贝马斯总结的“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日益臃肿、官僚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上层建筑建立起来之后,商业机构和媒介机构,政党门派和权势集团各自找到了自己在庞大社会阶层中发声的位置。社会公众被编排进工作计划、生产计划的同时,也成为选举计划、罢工计划、斗争计划中的“棋子”。公民丧失了独立批评的可能,并非因为他无法发声,而是因为他的发声无法与体制化的声音相抗衡。
虽然哈贝马斯的公共思想源于阿伦特,但哈贝马斯的“男性哲学”、“沉思哲学”的痕迹非常重。相比之下,阿伦特独特的女性视角,使得她更是很纯正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继承者。亚里士多德讲,人是政治性的动物,阿伦特在努力地还原到亚里士多德那个层面的政治观。这个政治观,与马基雅维利②马基亚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在中世纪后期政治思想家中,他第一个明显地摆脱了神学和伦理学的束缚,为政治学和法学开辟了走向独立学科的道路。他主张国家至上,将国家权力作为法的基础。他是名符其实的现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马基雅维利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主张结束意大利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他在其代表作《君主论》(1513)中认为共和政体是最好的国家形式,但又认为共和制度无力消除意大利四分五裂的局面,只有建立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政体才能使臣民服从,抵御强敌入侵。他强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权术政治、残暴、狡诈、伪善、谎言和背信弃义等,只要有助于君主统治就都是正当的。这一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政治观是背道而驰的。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是世俗的政治,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保有一定的崇高的味道。
此外,阿伦特跟哈贝马斯很大的区别在于对待理性的态度。阿伦特是个行动主义者,她看重行动,当然她也看重言谈。但言谈的含义,更像奥斯汀所说的“以言行事”。哈贝马斯看重的是什么?表面上看,哈贝马斯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入手,通过商谈互动、回归生活世界,建立普遍价值和共通的存在感。他同样看到了言谈和行为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放弃理性的终极作用。阿伦特跟他很大的不同在于,阿伦特基本上没有用理性这个词思考过公共领域,这一点上,她是尼采式的。尼采就非常痛恨“沉思”这个词。
阿伦特的公共思想里有几个重要概念。一个是“人是复数”。在阿伦特所谓私人领域和社会领域中,人都可以是单数的存在,甚至可以说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他的劳动和生产,都围绕自己的需要而展开。这当然是合理的,但仅仅这样,就是有问题的。所以阿伦特在公共领域中提出了人是复数的存在,即人存在的价值必须以他人为前提。人必须以他人为前提,这也是存在主义的一种思想,但她比存在主义更加阳光、更加积极。存在主义者萨特有一句名言:他人即地狱。但是在阿伦特这里,不是这样。她认为只有他人的存在,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第二个关键概念是“行动”。这里是体现她作为女性思想家的最为重要的思想,和哈贝马斯非常不同。哈贝马斯的讲法是“沉思”。就是罗丹著名的《思想者》雕塑的那个样子。沉思就等于理性。沉思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将这个世界的终极真理一眼洞穿。沉思就是试图得到超越个体、超越群体,甚至超越时间的见解,希望一劳永逸、永恒地解决内心的疑惑。康德、黑格尔都是这个样子的。这就是男性哲学的突出特征。在阿伦特看来,柏拉图以来的“政治哲学不再是建立在行动者的真实政治经验上,而是建立在哲学家的经验之上。哲学家孤独地思考,然后再从思考中回到现实来处理他们并不理解的世界。即自柏拉图以来,政治哲学是从哲学家的观点,而不是从政治行动者的角度发展而来的”。①陈高华,“哲学与政治: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之思”,《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在公共领域里,阿伦特的观点是行动。这个行动并非单一的指称某种具体的行为,而是与言说共同交织在一起的意义的存在。这种意义并不是像油漆一样,随便在那个对象上一刷就有了意义。意义不是刷上去的。意义并不先于人而存在,意义也并不先于行动而存在。意义不可能预先灌制在某个地方,只等你去打开它、看到它、消费它。并不存在你在行动前就能知晓、洞察,并且在下一步即将迈向那里的什么伟大的意义。这是有问题的。这是历史决定论。某些社会历史学家们,按照历史决定论的思维模式,假设了人类历史的伟大进程,又告诉我们这一进程被切分成几段,我们下一阶段一定比上一阶段好,告诉我们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逆的——这种东西在阿伦特这里是毫无价值的。
更进一步,把复数的人和阿伦特的行动的含义放在一起,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阿伦特的公共空间。她说,“行动,是唯一无需借助任何中介所进行的人的活动,它对应于人的复数性条件,即对应于这样一个事实,是人们,而不是单个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并居于世界之中。尽管人的境况的一切方面都以某种方式与政治相关,但这一复数性尤其是所有政治生活的条件——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是充分条件。”②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1页。
她认为所有与意义有关的东西,都蕴含在真正的行动中。并且你不是一个人在单独行动,因为你是复数。你只有在行动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意义。这种行动的思想,既不是第一个私人领域里的艰辛的劳作,也不是第二个社会领域里的思虑盘算、勾心斗角。第三个领域,即公共领域里的行动就更加映衬了一种共属于个体与他者的“间性”的存在。它是一个过程,是一种状态,一种真正的精神解放的状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空间的复兴,并非简单是哈贝马斯或者阿伦特公共思想的复兴。我们的下半身其实还浸泡在传统文化的“溶液”里边。传统的理性思维、科学精神、历史的进步论,这些术语都需要打上引号。但是,“批判”一语的含义需要更新。批判并非驱逐,更不是替代。利奥塔反对“宏大叙事”,德里达消解“意义”,福柯颠覆“权力”,他们都对建构一语保持缄默。他们担心一旦建构,便成为新的宏大叙事,新的僵化的意义和权力。这说明后现代者对现代性的批判固然深刻,但对现代之后可能是什么一无所知。现代之后,我们迎来的互联网,也许会给宏大叙事留下地盘——给宏大叙事留下地盘,本身并不错——关键要看留下什么样的地盘。如果对这个问题没有很好的反思,或者反思没有变成集体记忆的话,宏大叙事早晚会卷土重来。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警惕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并不是把它扔到历史的垃圾堆。互联网本质是一个快乐的世界,快乐的特点是一个字:“玩”。“玩”不是玩世不恭的“玩”,“玩”就是当下的快乐,但又不是“及时行乐”。比如拿“老大哥”来说,可概括为“跟老大哥一起玩”。因为“老大哥”总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出来,这里不能用“纯净水”思维。所谓“宏大叙事”的要害在“宏大”而不是“叙事”。不要试图从外到内地感动自己,以为自己可以手拿把攥地掌握终极的真理,成为正义的化身,也不要试图用一种暴力去取代另一种暴力,两种暴力在实质上是一样的。所以需要跟“老大哥”一起玩,陪“老大哥”一起玩。这才是互联网的公共精神。它不是把某些东西藏在自己背后,然后去攫取资源、攫取权力,为自己背后的那点东西忙活。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依然生活在工业时代的延长线上。
公共空间本质上是一种“间性”空间。通俗地说,就是公共空间本质上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必须承认这一点,而且要心甘情愿地承认这一点。其实过去一百年来的思想已经触摸到它了,比方说荣格的心理学,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的原型,本来就是雌雄同体的。这种间性思维非常重要。公共领域是一种饱满的空,而不是一种充盈的实。我非常欣赏阿伦特把它叫作一种行动的领域。行动,通过对话、通过言行来完成完全脱离物质利益狭隘视角的空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隐喻。
公共领域的新土壤
如果我们要谈公共空间的重构,我认为有三个前提和一个土壤。这三个前提分别是:公共平台必须足够丰富,意见表达必须足够多样性,权力的赋予与消解在同步发生。
公共领域的意见表达,在社会学、政治学和传播学上有一件事情必须是得到突破的,就是“意义的生产”。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意义生产方式是可以事先生产出来,传达给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群人,在碰撞下能否达成共识。这是已经注定要过时的意义的生产方式。这种意义的生产方式有一个致命的假定,就是假定意义可以事先生产出来。这是错的。意义不可能事先生产出来,意义只能是边生产边消费,不可能先生产再消费。这种情况下,意义的生产方式注定发生重大变化。
其次,公共领域事关权力的重构,事关权力的赋予和消解。福柯不但是对权力、对赋权、对话语和知识怎样结成权力有重要的剖析,更重要的是指出一种可能,赋权和权力的消解必须同时存在。赋权不再是某种授予,中国人也在讲君权神授,西方人也在讨论权力到底从何而来。我认为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虽然没有解决,但已经变得不是一个问题。权力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权力如何运作。权力的授予和消解一定同时存在。
公共空间的土壤是什么?就是大数据,无处不在的大数据,甚至是大数据哲学,它会带来古希腊时期非常喜欢的流动性哲学(即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而不是柏拉图的哲学)。我们今天看到物质的流动、信息的流动、资本的流动,未来可以看到更多的思想的流动。这些流动性的市场一定会仰仗大数据,但这个大数据不是采样,它是实时的,它是一种“呼吸”,它是“活”的大数据。
这样就带来了新媒体的三个值得关心的问题。
第一,我们需要重新看待人。我们需要重新回到人的本源来思考人。这个人已经被机器包裹,这个人和机器的边界无法区别,界面已经消失。这个时候再看人的欲望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满足的。
第二,我们需要看到社群的本质,重新理解关系,重新理解跨主权的主权消解。
第三,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公共秩序以及重新定义秩序。秩序是“长”出来的,而不是授予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新媒体到底新在哪里?需要考虑到三种情况,新媒体是结构性的嵌入、它是一种新物种的诞生、它是全新的体验。
传播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传播再也不是搬运工的角色,传播不是为了消弥信息的不对称。麦克卢汉讲“媒介即信息”,这句话已经被解读了半个世纪,但我个人认为这句话的解读依然不深刻。“媒介即信息”是彻底告诉我们,不要试图把媒介分成媒介所承载的内容本身和作为载体的媒介,这样的两分法已经完全失效了。
在我们思考新媒体、新媒体的未来以及新媒体带来的变化的时候,要时刻警惕今天思想的底座、知识的底盘、思维的框架,在百分之八九十的可能性下都被绑架在传统的底座下。由于过去学科的专业化,使得文科背景的人不善于搞算法,忽略了高频交易、高频的意见表达、高频投票的可能,甚至是平行空间,我们认为它只是存在于科幻世界里。公共领域的确是非常棒的词,可能我们会忽略掉这些。
第二个就是我们下半身可能泡在工业社会。我们仍然相信理性,仍然相信至善,仍然相信可能达成共识,我们对知识和确定性依然非常迷恋。
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可能更加需要担心的是,当我们努力建构一个新的世界、新的话语场的时候,会不会为宏大叙事或者新版本的宏大叙事留下地盘,或者说我们为老大哥赋予什么样新的可能?未来我们将怎么样跟这些老大哥一起来玩耍、戏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图象?
在这种情况下,借用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两种公共空间理论,我们需要看到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男性哲学统治了思想界2000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今天的互联网看成有生命的、有灵性的、有活性的,不得不让它注入更多的女性的色彩。公共空间一定需要一种柔性的、间性的,或者说跨界的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新媒体和公共空间如何重构才会获得最佳的思想基础。
本文研究结论是:第一,我们已经不得不进入到一个平行世界,一定需要深刻地理解平行世界各种可能性都同时在场。不要试图于用一种可能性去摒弃或者打击另外一种可能性。我们不如用戏弄、戏谑,甚至嘲弄、自嘲这样的方式。所有的物种都有理由存在。今天只是所有物种滋长的时刻,不要有太多的功利心。
第二,媒介受到的挑战依然加剧,而不是减轻。这是因为对媒介的挑战已经从去中心化进入到再中介化的时代。媒介的未来到底是什么?
第三,在新的媒介生态中,如果媒介有存在的理由或者新生的理由,媒介一定要学会看待未来的世界。用你饱含柔情的、充满温度的眼睛看这个世界,你必须学会看到不确定性的、多样性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同时,又相信秩序会从这里诞生。
(责任编辑:钟宇欢)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Media and Public Sphere
DUAN Yong-chao
The flourishing and declining of public sphere was along with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capital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et, along with the rise of information economy, what is the new possible public sphere reconstruction? What is the new role of new media playing in the public sphere refactoring? These are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public sphere refactoring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the richness of public platform and diversity of public opinion expression,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meaning and order of public sphere, and explore paths of construction under a new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public sphere; new media;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cognitive science
G20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