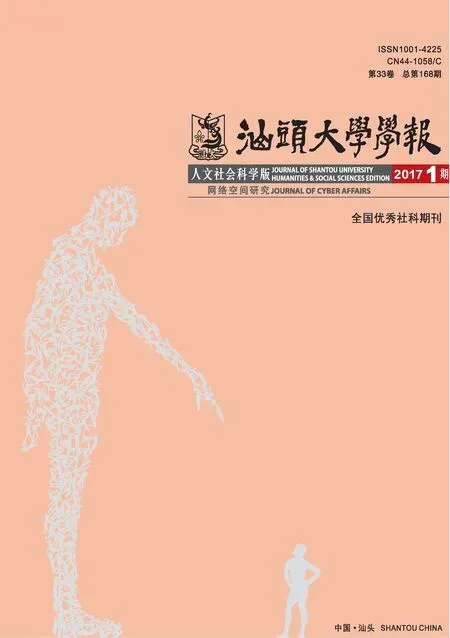国际传播中的十大关系分析
2017-06-12吴飞
吴飞
国际传播中的十大关系分析
吴飞
今天的传播环境给国际传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面临更大的挑战。观念之冲突、文化之差异,较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彰显而激烈,共识与冲突并存,理解、误解与曲解同在。国际传播活动已经超出传统地缘政治边界,超越了传统的时间与空间格局。要想建构一个美美与共的世界和平格局,需要进行更全面的国家传播战略设计。国际传播场需要众声喧哗,允许不同的观念、价值和生活方式共存,无论是个体、媒体还是社会组织都能生活在弥漫着宁静、平和的信息之网中,让和平传播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旋律。
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全球化;文明冲突

吴飞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国家互联网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新闻传播理论,传播社会学。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
观念之纷争、文化之差异、利益之冲突,当今之世各种事件较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彰显,共识与冲突并存,理解、误解与曲解同在。国际传播活动已经超出传统地缘政治边界,超越了传统的时间与空间格局。如何在这个全球化和新传媒技术推进的全球互动世界,进一步增加全球意识,增进各国相互理解?中国如何才能建构更有效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策略?面对“信息爆炸”、形形色色“异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究竟该怎么办?又如何面对跨语境间、国家和民族间以及宗教与意识形态间的差异?我们将从十大关系入手来探索这一问题的答案。
一、官与民——传播主体的多元化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认为,我们正处于全球化“3.0”时代,这一时代的全球化推动力则来自个人和小的集团。人的力量大增,不但能直接进行全球合作,也能参与全球竞逐,利器即是软件,是各式各样的电脑程序,加上全球光纤网络的问世,使天涯若比邻。①[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肖莹莹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5页。在全球化“3.0”时代,传播的时间与空间结构改变了,国际舆论场的格局亦被重塑了,传统的以国家为主的区域性单元舆论场逐渐成为全球传播舆论场的分场。在这种复杂的舆论环境中,民间舆论场越来越呈现出巨大的影响力。
国际传播和软实力建设是一个相当复杂与漫长的系统工程,是一项自觉的公民工程。每一个中国公民,包括官员、学者、艺术家、科学家、企业家、中国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人员、留学生、甚至在中国城市马路上的行人、旅游景点的小摊小贩们,都是中国形象的建构者,《外交评论》执行主编陈志瑞认为:“这些年,在海外建了很多孔子学院,把奥运会、世博会也办得漂漂亮亮、风风光光,还不断的向各国伸出援助之手,可是这些并没有化解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敌视,‘中国威胁论’等负面的东西还是层出不穷。”在分析其中的原因时,陈志瑞认为有两方面的主要原因:其一是政府在文化外交的作用过于突出,他认为在实施主体、议程设置、传播渠道等方面,文化外交过于依赖政府,有违文化外交的特性;其二是中国文化外交缺乏明晰的外交伦理支持,他说:“我们有丰富的外交理念,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韬光养晦、和谐世界等,但是缺乏整合,很难有具体政策,把理念展示出来。”①雷东瑞:中国软实力与文化外交论坛在京举行,http://news.sohu.com/20120511/n342994774.shtml,本文作者于2012年11月10日下载。
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早在1996年就认为,现在人民在改造他们的政府和影响政府行为方面的能力超过了人类历史的以往任何时候,即使在一党制国家,统治者们也不能完全不顾公众舆论而独行其事。②United State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A New Diplomacy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November,1996.1964年,美国第28届外交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有些外交政策的目标是能够直接针对外国人民而不是它们的政府。通过应用现代新闻媒介,今天有可能联系外国中的大部份人或其有影响的一部份人,影响他们的态度,有时甚至诱导他们向我们设想的行动方面发展。这部分人反过来就能够对他们的政府施加明显的,甚至是断然的压力。③[美]赫伯特•席勒:《新闻工具与美国帝国》,《国际新闻界》,1979年第1期。转引自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398页。
二、新与旧——传播渠道的多形态化
离美国大选结果揭晓日只有11天之际,FBI宣布重启对希拉里“邮件门”调查,希拉里支持率应声大跌。几乎在同时,韩国总统朴槿惠“闺蜜干政”事件持续发酵,导致首尔万人举行烛光抗议,要求弹劾朴槿惠。发生在美国和韩国的事件,正通过社交媒体在全球扩散。
新媒体外交成为美国外交的新战略,被《纽约时报》誉为“E外交”。④季萌:《新媒体外交初探》,李希光主编,《软实力与中国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2008年5月,白宫在Fac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上开设主页,此后美国30个政府部门也加入,20多家美国官方机构在Youtube上发布视频,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注册了Facebook和Twitter与网民互动。中国也在新媒体外交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2009年2月,《中国日报》发行美国版时,就在Twitter上购买了推广套餐;新华社不断扩充自己的英文网站;2009年9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网站语种数量达到59种。
美国前公共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哈罗德•帕切亚斯(Harold C. Pachios)认为,在其他的诸多事例中,因特网的普遍运用给予了非政府组织支配国际关系以巨大的权力。关于环境、人权、经济以及地雷方面的国际条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非政府组织的倡议和行动下签署的。⑤Harold C. Pachios,“The New Diplomacy”. December 4. 2002.转引自廖宏斌:《文化、利益与美国公共外交》,外交学院2002级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32页。伊万•波特(Evan H. Potter)在《网络外交:掌握21世纪的外交政策》一书中指出,新传播科技为外交家提供了到达国内外目标受众的新机遇,外交政策针对的公众范围越广,就越有可能通过新媒体避开传统媒体的过滤,但这并不是说传媒媒体就不再作为工具,外交部门仍然主要依靠主流媒体来了解公众舆论,并传递关键消息。⑥Potter, E. H.,Cyber-diplomacy: Managing foreign policy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2.加里布(Edmund Ghareeb)探讨了互联网对阿拉伯世界政治话语的影响,并指出互联网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Edmund Ghareeb,2000)。国内学者也指出,中国的新媒体外交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诸多问题,中国亟需加强网络技术研究和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发布工作,并通过加强与国外网络媒体的对话、改变国内网络管理思路与体制等方式来推动网络外交的发展。①唐小松、黄忠:中国网络外交的现状与对策研究,《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4期。
周笑博士分析了互联网技术的演进路径,他认为,“就在1990年前后,新兴传播媒体从‘点对点’的个人主义信息网络逐步发展出‘面对面’的社群主义信息网络,这一方面,大幅度降低了信息跨境传播的成本,带来无域化网民全球性的大规模增长,另一方面,则实现着日益精确化的分众化传播,持续提升了信息公民个人的文化动能和经济动能,也就是以个人努力影响和作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能力”。②周笑:国家、个人、社会与一个悖论,载李希光主编:《软实力与中国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97-305页。
三、内与外——传播空间的去地域化
在全球化时代,舆论焦点的中国大地上再也没有一个事件是国内的事件了。2016年4月21日,杭州文二路学院路口因废弃雨水管泄漏而发生路面塌陷,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协警礼为奇是最先发现塌陷险情的人。当美国媒体CNN将这个抓拍的视频放到全球最大的社交平台上后,短短不到一天的时间,点击量达到约300万次,转发15000次。网络上纷纷管这位不知名的杭州协警叫做“中国英雄交警”。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传播的眼光,不能只盯着国际事务。国内事务处理的好与坏,同样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国家形象、国民形象与政府形象既体现在国际交往之中,也体现在国内事务之中。如果中国国内国泰民安,国民真是生活得很幸福,那么国际舆论就算再有妖魔倾向,也不可能坏到哪里去。
中国长期以来坚持面向国民进行正面的舆论宣传,旨在提升国民的对政府的良好形象。但事实上,正是部分媒体报喜不报忧的宣传策略,损害了国内媒体的信誉,更伤害了政府的信誉。要想改变这种格局,就需要坦诚面对所有的问题和困难,国家的繁荣与发展让国民可以真正得到分享,同样国家的困难也可以让民分忧。
2009年7月16日,哈佛大学的盖茨从海外旅行归来,因家中前门损坏而试图撬门进入,白人警官克劳利等接到他人报警,赶到盖茨住处后与其发生争执,警察一度将盖茨拘捕。一时间,种族问题成为整个美国关注的焦点。7月22日,在记者会上,奥巴马被问及白人警官与黑人教授之事,他表示:“公平地说,首先,我们都感到很气愤;其次,坎布里奇市的警官行动愚蠢地逮捕了在自己家中的人;再次,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国家很长历史中,非洲裔和拉美裔常常受到执法者不合情理的干扰。”此言一出,立即引来批评。7月30日晚,奥巴马特别邀请黑人教授盖茨和白人警官克劳利到白宫玫瑰园“一起喝啤酒”。美国媒体称为“啤酒峰会”。“啤酒峰会”结束后,奥巴马发表了一份声明称“我始终相信,团结的力量远胜于分歧的力量。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够从今晚所发生的事情中得到积极的教益。”“啤酒峰会”取得了积极效应,美国国内媒体给予了较好评价,而包括中国媒体在内的国际舆论界同样给予了肯定。一件美国国内棘手之事,反而变成了奥巴马提升其国际形象的机会。白宫显然也很满意这一事件的处理方案,在2012年秋季举行公众开放日活动中,白宫玫瑰园旁的草地上插着一幅彩色照片,显示奥巴马曾在玫瑰园中与白人警官、黑人教授一起举行过“啤酒峰会”。③参见温宪、燕晓哲:奥巴马“取胜之道”,《环球人物》,2012年第30期。
四、张与驰——国际传播的节奏感
《礼记•杂记下》有言:“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事实上,任何有生命力的形式,都得有张驰有道的节奏感,而这种节奏感,既是生命象征,也是生命的魄力所在。
国际舆论场的建构,同样需要这样的快慢张驰的节奏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事件中,都需要发出声音,就算要出声,也并非一定都要高调。如2008年12月16日,法国总统萨科奇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期间,不顾各方阻力,会见了西藏分裂势力。中国政府对萨科奇此举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和警告,有些中国的爱国网民甚至在网络聊天室里抗议,抵制法国货。萨科奇此举直接导致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在出访欧洲五国时绕道法国,与环法五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和爱尔兰签订了许多条件丰厚的合同。如此的对抗效果,在国际上的反映是多元的,很难说是完全成功的。
中国对一些“敏感”事件、人物的紧张反应,很容易成为对手制掣中国的工具。因为对手太容易发现中国的弱点和敏感区域了。比如说,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就发现当时中国对台湾问题相当敏感,因此他在回忆录中就不无得意地说,对中国的国际事务,可以有效地利用台湾这张牌敲打中国,而事实也证明,美国人掌握的这张牌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取得了效果。中国政府在台湾或者西藏独立之类事务的高度紧张,甚至非洲一些小国的政客都已经明显感觉到了,他们频繁在中国和中国台湾之间游走,企图利用不当外交手段获利。
五、显与隐——传播方法的柔性化
宣传这一词成为政治学甚至是日常用语,是一战时期,当时参战各国在宣传方面做足了功课。因在实践中,宣传带有明显的政治与宗教意念的推销、灌输、煽动、鼓动、洗脑、偏执等特征,宣传者常指把“不正确、不可靠的消息灌输给大众”,因此,西方社会的民众很快对“宣传”产生了一种戒备和厌弃心理。有鉴于此,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提出要将中国的对外宣传的“宣传”定位在“说明”(publicity explain)上,不用或慎用“宣传”(propaganda)一词。①赵启正:《积极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见刘洪潮主编《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许多国家都有国家形象与国家文化的宣传事务,不过一般不直接用“宣传”一词来表达,当时更流行的词语是“公共外交”。如2003年1月,美国成立了“全球传播办公室”(the Offic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OGC),其主要目的是“协调海外传播策略”,传达“清晰而有力的信息”、“整合美国总统的理念以及美国的政策和价值观”,从而“防止误解与冲突”,更好地保证“国际受众的知情权”,为美国赢得支持。2009年1月韩国成立国家品牌委员会,由这个直属于总统的咨询机构来负责国家形象的整体建设和提升。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德国都有类似的国家品牌传播机构,做得比较灵活。英国还设立由驻外使馆、英国文化协会、工商会议所、非政府组织等组成的英国海外特别小组以调整对外宣传策略。
传播学的研究表示,要想达到较好的宣传效果,则其宣传性的内容当被隐藏在有意味的故事文本之中,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获得相关的信息的观念。如美国有一个卡通片,名叫The Simpsons(辛普森一家),经常以讽刺喜剧的方式,来表现地道的美国思维和行为方式,大人小孩都喜欢看,长盛不衰。2005年曾播出过一集,描写辛普森一家的中国旅行经历。整个故事是通过一个七八岁小孩的观察来表现的。小孩初到北京,看到从北京飞往美国的飞机上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货物,而从美国流入中国的是源源不断的美钞,简直就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和英国的贸易逆差情况的重现。普通的两个对比镜头强化了美国人对中美贸易逆差的担忧。辛普森一家到中国来是为了领养一个被拋弃的女婴,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中国公安机关的监视,连旅店的房间里也都装了录像监视装置等。公安人员获悉辛普森一家的内部谈话,得知他们是不够领养资格的人,于是取消了他们的领养安排。整个情节传达的侮辱信息就是:中国虽然经济很发达了,但本质上仍然是一个警察国家。这是走进千家万户的节目,影响很大,尤其是对儿童。这应该算是美国在国内运用“软实力”的表现。影片制作者将自己对国际政治的诠释,通过卡通,带入美国观众的思想习惯之中。
国际传播当然也不是说就不可以有钢硬的、显性的宣传手段,只是更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双向的沟通与互动的方式来引导、说服来实现的。这种强调交互式的参与沟通,以对话取代独语,以沟通取代命令的交互式的沟通对话,会更有效而更完整地了解他国公众心中的想法,也可能使信息的传递更为完整、更正确。
1998年中宣部将英文名称更改为“Publicity Department”、1991年设立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成立国家汉办、CCTV9英语国际频道寻求海外落地。中国吸收了大量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公共外交战略手段,如重视文化软交流活动,拍摄国家形象宣传片,大力发展中国文化的外译工作,建立孔子学院等等。这些文化交流活动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过,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宣传的手段太明显,传播策略比较单一,缺少国际上认可的媒体渠道,不会讲述中国的故事,就连张艺谋之类的艺术家讲述的故事,也只能是一些迎合西方人口味的另类或者过去的中国故事。更严重的是,长期来中国要求讲述正面的故事,不得报道负面内容,连“小骂大帮忙”的空间都不大,使得不少外国人认为中国故事不真实或空洞说教,没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也缺少可信度。
六、硬与软——传播战略的双重布局
韦伯认为,权力是控制他人、事件或资源的能力,使得某人想要发生的事发生,尽管会有阻碍、抗拒或对立。①周宪编著:《文化研究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无论是硬权力还是软权力,控制和影响他人,都是权力的基本欲望。正如约瑟夫•奈所言:“权力就是有所作为与控制别人的能力。简单地说,就是能随心所欲的能力,能够影响别人行为而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②Nye, Joseph S.,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Basic books, New York, 1990,p.33.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将软权力定义为“当一个国家使得其他国家以其预期目标为目标时的同化权力。”③[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111页。可见,“软权力”是一种更高远的控制与影响力,它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在国际政治中,“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样重要。亨廷顿就认为,物质上的成功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而经济和军事上的失败则导致自我怀疑和认同危机。④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S . Nye .Jr., Power and l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October 1998.在冷战期间,西方曾使用硬实力遏制了苏联的扩张,但是它同样使用软实力来侵蚀铁幕之后的共产主义信心。
西方国家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国家制度和公民构建的经验丰富,发展出一套比较成熟的政治理论,以自由、法治、民主和平等理念为核心内容,利用西方拥有的政治、市场和文化优势,在全世界传播。可以说,西方利用自己已经完成的历史进程来制定一种“标准路径”加以推广。用王绍光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占据了道德制高点。⑤王绍光发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召开的软实力研讨会,2007年7月20日:载载门洪华主编:《中国:软实力方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0页。对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或美国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观的问题?王希教授认为:“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勇气打破西方的思维定式,以历史的眼光来观察西方和美国的发展,认识它们在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处理。简言之,不应该迷信西方或者美国制度和核心价值观的完美和神话。”⑥王希:软实力的硬内容:国家制度和核心价值观,载李希光主编:《软实力与中国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3-51页。王希教授还指出,我们要有勇气来正视和承认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价值观的存在。这些价值观本身就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民族发明出来的,而是人类共有的经验和追求,并且以不同的形式得以表现,以不同的方式得以运作。“普世”包含了一种内在的本质。不需要赐予,也不需要强加于人,更用不着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就“自由”和“民主”而言,它们本身在美国历史上就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其内涵融入了不同类型的美国“自由观”和“民主观”的冲突的结果。⑦王希:软实力的硬内容:国家制度和核心价值观,载李希光主编:《软实力与中国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3-51页。
英国波特兰公关公司(Portland)2016年6月14日发布一项研究报告称,按软实力排名(文化和公民价值观影响力,而非金钱和武器),美国名列第一,英国第二,德国第三,中国名列第28名。波特兰公司指出,尽管经济增长出现放缓,中国依然在国际舞台上显示出自己的经济实力,并对国际体系进行改造,致使国家的“软实力”水平得到提高。如正在推动中的亚投行是亚洲开发银行的竞争对手,也是中国全球活动的新的里程碑,展现出了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态度。
中国对软实力构成的三要素——文化、价值观和政策——的建设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在文化上,中国尚未梳理出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未来发展最具有正能量、而又可能有广泛吸引力的元素。中华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天人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上”、“克己奉公”等政治与社会文化智慧,乃至“天下体系”的治理模式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都没有得到系统的梳理,更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在价值上,我们因为纠缠于可能因为接受普世价值而处于被动地位,反而未能利用这些全球广泛接收的理念来传播和建构中国的影响力;而在政策安排上,中国一直没有建立强大的智库群,使得我们在国际交往中仍然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自发试验状态,构成软实力的各部门间经常独立作业,缺乏协调,有时不但未能成为合力,反而会相互抵消。有学者指出,中国还没有形成一套综合与连贯的国家软实力战略,其软实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临时举措和应急性反应。①William S. Cohen, Maurice R. Greenberg, "Smart Power in U.S.-China Relations",a Report of the CSIS Commission on China, 4 March 2009, http://csis.org/ files/media/csis/pubs ... uschinasmartpower_web.pdf
七、行与言——做得要好,说得更要好
丁刚曾发表文章称,在非洲听不到“中国声音”。他发现“在开罗的酒店里,打开电视,当地电视台的国际新闻几乎全部是转播。当然,你可以非常容易地收到CNN、BBC的电视,那里面播出的不仅有国际新闻,还有非洲和当地的新闻。让人可以感觉出,这两家西方主要电视媒体的记者,在非洲是十分活跃的。当地人获取当地的新闻,甚至也是以这些西方媒体为主要渠道的。中国媒体虽然在非洲各地都设有记者站,但它们报道的当地新闻,大多还是为中国受众服务的。而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则主要是中国国内的新闻以及中国的观点。②丁刚:在非洲听不到“中国声音”,《东方早报》2010年6月2日。当然,话语权的缺失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其一,全球传播渠道更多元化,但西方社会仍然掌握主动权。尽管西方已不能完全主宰信息传播渠道,但不可否认的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在技术和高等教育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英语仍然是国际传播领域的通用语言,在新媒体领域方面,西方同样拥有核心技术和竞争力。约瑟夫•奈就认为,在软实力方面,美国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与它相比。因为“所有的电影制片厂联合起来也无法打破好莱坞的垄断,因为如果规模重要的话,作为世界上影片产量最多的国家,印度就可以称雄世界。而且,它们所有的大学联合起来也无法动摇哈佛和斯坦福的地位。因为完全靠数字并不能从国外吸引最好、最聪明的人,而正是这些人不断加强了美国重点大学的竞争优势。”③Josef Joffe , Defying History and Theory :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Last Remaining Superpowe”, America Univalled :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71.
其二,在国际信息新闻传播市场,缺少中国的故事。赵启正认为,我国国际报道的许多文章理论性太强,而且有的报道总是想在一篇文章里把所有的道理都讲完,导致效果太差。此外,人才队伍知识结构、职业化等也成问题。那么如何才能向外国受众讲好中国故事呢?首先应明白其思维方式和接受习惯与中国人的区别。马胜荣教授则认为表示,中国人的接受习惯,是希望媒体能给一个有一定结论性的报道,讲清楚一件事情的原因、过程、结果,并给予评论。外国受众则希望只要把事情告诉他就行了,至于结论怎么下,由自己决定。赵启正说,我们的价值观、理论、观点一定不能生硬地传播,要通过外国人喜欢的人性化故事方式来传递。刘长乐亦表示,我们不能每天喋喋不休、反复地讲道理,可以通过文化、艺术传播等方式来扩大讲故事的空间。马胜荣教授强调说,向外国人讲中国故事,不纯粹是方式方法问题,首先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传播能力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必须尊重事实。要传播实际情况。就中国新闻的对外报道而言,就是既要讲发展成就,也要正视存在的问题,讲两面才符合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点。①以上观点均转引自梁益畅:国际传播的三个维度,《中国记者》, 2010年第4期,第40-42页。
其三,国际传播人才也严重不足。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兴起在中国还只有几年光景,虽然今天看起来颇为热闹,但大体是外表光鲜,而楼阁空空。中国真正懂国际政治经济的人才不多,了解国外国人文历史的也不多,除了英语、法国、德国这些大国的语言还有一些人才储备外,一些小民族语种在高校求学者已经越来越少了。不像西方社会,几个世纪以来,便有大量的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和各类志愿队深入全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掌握了西方以外世界的大量的地方性知识,因此,他们的政策和行动往往会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效。
八、我与他——“他者”的客观化
近几年中国在向全球发出自己的声音上面,是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中国在国际传播场,仍然缺少真正了解中国、愿意为中国鼓与呼的第三方力量。相反,中国政府在国际事件的表态上,多由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统一代言。但对中国官方的传媒,西方受众持有一种“坏孩子印象”。“‘坏孩子印象’造成一种逆反心理,即使我们的报道是实事求是的,但传播效果却打了折扣,正面报道无形中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甚至变成了负面报道。”②李珮、刘海燕:传媒全球化下的有效对外传播策略,载李希光主编:《软实力与中国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57-263页。
所以,想要更好地达到国际传播的正面效应,在国际信息市场上更多流通关于中国的好声音,中国就需要发现甚至是培养更多的“中国的老朋友”,接受更多的外媒到中国内地来,让他们看到中国的发展变化,让他们可以客观地观察中国社会的进步,进而有机会发出客观的报道,撰写出更准确的研究报告。事实上,在中国呆得时间越久、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有更透彻的了解之后,外国人对中国的书写与传播就会变得更真实,也要正面得多。试回想一下早期在中国长期居住的西方传教士们,他们多数人撰写的著作比那些匆匆的过客撰写的文章要客观得多、深刻得多。方汉奇先生指出,“20世纪40年代前后来中国采访的一些美国记者……他们有过较长时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其中一些人还曾经以同盟国记者的身份,在中国战区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的报道,和中国人民同过呼吸,共过患难,有一定的感情。这些美国记者由于了解情况,加之采访深入,往往能够比较公正、比较客观地看待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当政者的不少举措,有所批评,对中国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则寄以希望,对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乐观其成。”③方汉奇:美国记者的爱恨中国情结——对100 年来美国记者有关中国报道的回顾与反思,《国际新闻国界》2002年第2期,第78-80页。
早期的中共领导人十分注意利用国外媒体来传播影响力。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1936)、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等可被视作是中国共产党运用软实力的早期典范。1949年后,面临外部封锁和孤立,中国利用十分有限的资源,扩大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1950年创办的China Reconstructs、Peking Review、《中国画报》等外文刊物和Radio Peking等在传播中国国内的制度变迁和人民生活改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在美苏争霸的情形下,中国注重在亚非拉国家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配合经济援助,扩大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在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也注意发展与外国友好人士的关系往来,通过他们来传播中国的影响。譬如,1959年,中国国际和平促进委员会就出面邀请美国著名的黑人学者杜波伊斯来中国访问,杜波伊斯及其夫人后来在各自的自传中都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热情讴歌了中国的成就,这在冷战时期的美国是十分罕见的。①Wang Xi, Black America and Red China: The Extended Problem of Color Line across the Paci fic,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2009.
再如美国作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现任花旗集团全球投资银行的高级顾问),在出版《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之后,又撰写了一本新的著作《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他在这本书序言中写道:“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在各个地区是如何迥异,这种复杂性通常说来并没有引起外国媒体的真正重视,但正是这些差异,让世人看到了中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质疑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所持的那种普遍简单化的观点。经过这些深入的国情调研,鉴于我个人的科学视角,我越来越赞同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我亲眼见到,中国要多方应对各种严峻的系统性问题,比如收入不均、失业、农民工问题、腐败、犯罪、金融系统脆弱、能源限制、可持续发展问题、环境污染、道德观与家庭观念变革等等,而且这些问题在中国的不同区域表现各异。有的问题是由于经济急剧发展导致的;有的源于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转型;还有的是为了适应不断深化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改革的需要。”②[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序言。
九、一与多——在多元价值中寻找共识
美国公民保持着拥有枪支的文化传统,这在欧洲人看来很难理解;捷克人每年喝掉的啤酒比沙特阿拉伯人和爱尔兰人多;巴基斯坦人在谷歌上搜索“性”略高于越南却远超爱尔兰人和捷克人;厄立特里亚人在谷歌上搜索“上帝”一词的频率全世界最高,同时也是搜索“性”最频繁的五个国家之一;印度和中国是邻国,并且还有领土争端存在,但是他们都拥有独特的饮食文化,在这种饮食文化中,哪些动物的哪些部分能吃或不能吃都是学问;阿根廷人看心理医生的频率是所有国家中最最高的,而巴西人购物的花费占自己收入的比重是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世界价值调查小组的一项范围覆盖65个国家和世界上75%的人口的调查数据表明,虽然全球化改变了很多文化的形态,但是各个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却从未改变。“东正教、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使得他们各自影响的文化区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它们不仅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还影响经济发展。”③[美]盖马沃特:《下一波世界趋势》,王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218页。
各种不同的文明之间,肯定是存在差异的,诚如亨廷顿所发现的那样:“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亚洲文明和美国文明之间根本的文化差异显现出来。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顾及他人的面子’,以及一般而言国家重要性要高于社会,而社会又高于个人。此外,亚洲人倾向于以世纪和千年为单位来等待社会的演变,并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态度与美国所主张的信念相反,即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以及只专注于眼前利益的最大化。冲突的根源其实在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④Huntington, S.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p.225.中文译文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译文有改动。不过,发现文化与文明间的差异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对待这种差异。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早就提出:“我所设想的人类团结不是全球均一,而是多样性的联合。我们必须学会欣赏和容忍多样性、复和性和文化差异……多样性的联合,而不是均一,是欧洲的遗产。这种多样性的联合必须扩展到整个世界——包括日本、中国、印度和穆斯林文化。每种文化,每个人都对人类的团结与幸福有其自己的独特贡献。”①Dallymayr. F , Beyond Orientalism, Essays on Cross-Cultural Encounter,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
自20世纪末以来,“文化多样性”的口号已经成为各种势力想在联合国中争得一席之地的有力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归进其组织原则中,并作为维持“文化地缘体系”平衡的主要理论支持。2001年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第31次代表大会上,世界各国代表一致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其第一条就规定“文化多样性”为“人类共同遗产”,同时,认为它和人类的生存秩序中的“生态多样性”一样对人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赛亚•伯林在其著作《扭曲的人性之材》中介绍了文学史家和随笔作家赫尔德的观点。赫尔德认为价值并非普通的,他指出,每一个民族都有他自己的传统、自己的个性、自己的面貌。每一个民族都有他自己的道德引力(moral gravity)的中心,而且彼此各不相同:在自己的民族需求的发展过程中,其幸福取决于而且只能取决于它自身独特的个性。②[英]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伯林强调,不同的文化价值是平等的:同等真实,同等终极,同等客观,不存在价值的等级秩序。但对于人性来说,不管多么复杂善变,只要还可以称之为人,其中必然含有“类”的特征。不同文化之间也同样具有可通约的共同价值。虽然民族文化的差异很大,但核心部分是相互重叠的,这些核心价值和终极目标都是敞开的,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我们有必要也有能力超越自身的文化、国家和阶级的特殊价值观,突破文化相对主义者企图限制我们的封闭盒子,进入“他者”的文化。只要我们充分发挥想象力,总是可以理解“他者”的心灵,理解他们的生活目标,从而实现人类文化的共同性与多样性。③[英]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78-89页。
在文化间的协商、沟通、理解的基础上,寻找跨文化的公共空间,一是跨文化的“共义域”,即跨文化交流双方共同的经验范围所构成的交流语境和背景。“共义域”越是广泛、完全,双方之间的了解和认识越是深刻、明晰、准确;而当“共义域”缺失或者不完全时,就会造成传播的不顺畅,误解和曲解也就由此产生。在跨文化传播中,由于传播者与所反映对象之间,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经验范围严重缺失,使得两者之间的“共义域”超乎寻常的褊狭和缺失,因此难免出现曲解,造成误读。④Sim, Soek-Fang. Demystifying Asian values in journalis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March, 2006-VoI. 56 Issue l, pp. 429-432.二是少数和的共同空间,即吸引少数族群同时又让主流受众感兴趣的表达空间,并且让新闻报道接受不同文化群体受众的检验和评价。它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因公共兴趣而聚集,同时又展现同—议题的多样观点,消解群体间语言偏见(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避免使用抽象的语言描述与刻板印象一致的行为,特别是当行为者是一个外部群体的成员的时候。⑤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页。
有学者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认知混合”( cognitive contamination) ,这建立在对一个基本的人类特性的认识基础之上:如果互相交谈,时间长了,就会开始影响彼此的思考。当这类“混合”出现时,人们发现,将其他人的信仰和价值归结为堕落、疯狂或邪恶会越来越难。勒温创造了“群体规范”( group norm )这一术语——任何“群体动力学”过程所趋向的那种意见统一;而集体间的认知污染过程被认作是“融合”(syncretism )。一个经典事例乃是希腊的众神被罗马获取——宙斯变身朱庇特,阿佛洛狄忒变身维纳斯,等等。宗教思想(以及其他认知和规范的范畴)会从一种世界观被“转译”到另一种世界观。很明显,在这—转译过程中,它们并非总是保持不变。
西方长期误解中国的部分原因,在于支撑中国和西方社会的伦理基础,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罗布•吉福德(Rob Gifford)在《中国之路》中指出,在欧洲,“基督教的存在……往往独立于君主权力,这一点在制衡皇权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基督教还造就了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他们不会向君主宣布效忠。”相比之下,在古代中华帝国,通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都会到政府部门担任公职,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佛教的影响力。此外,儒家社会道德的基础不是君权神授。在这一体系中,忠孝原则从家庭延伸到政府,形成“家国”的概念,皇帝扮演着“君父”的角色。中国人对家庭极度看重,向裙带关系敞开了大门。正如官员应该服务于政府一样,①[美]伯格、[荷]泽德瓦尔德:《疑之颂:如何信而不狂》,曹义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0-11页。他还得帮助亲属发家致富。至于法律体系,肯尼斯•斯科特•拉图雷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在《中国人及其历史与文化》(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中写道,中国社会“缺乏律师这种博学的专业人士,而律师在西方却举足轻重……裁决通常会偏袒向身家最丰厚的人。”②[美]哈伊里•图尔克:中国领导人选拔机制的根源,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7539
社群主义者沃尔策为了缓和道德领域中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这种张力,提出了“道德最少主义”(moral minimalism)的观念。他认为,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道德。这些不同的道德之间有某些共同的部分,共享某些普遍的道德原则,如禁止杀人、虐待、压迫、说谎、欺骗等等。就这些共享的原则而言,“道德最少主义”是普遍主义的。但是,这些共享的原则在道德中只占很“薄”的部分,而更“厚”的部分是特殊的,它们存在于特殊的文化背景中,体现了不同道德体系的差别。在沃尔策看来,因为任何一种道德都是有骨有肉的,我们不能把“骨头”从“肉体”中剥离出去,所以我们应该做的不是说服“他们”接受“我们”的道德,而是“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道德。这种主张通常被称为“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我们”尊重“他们”的文化,“他们”也尊重“我们”的文化。在某些(“薄的”)东西上,“我们”与“他们”拥有共识,而在其余(“厚的”)部分,则应该相互承认和尊重对方的差别。因此,沃尔策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是一种最多主义的观念。”③姚大志:沃尔策: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之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47-52页。
十、争与和——引领世界舆论方向
美国在全球一直是魔鬼与天使的双重角色,一方面美国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大力实施国际救援,并广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这些和平行动和经济政治上的强势地位,使得美国成为全球追求“美国梦”的人们的理想家园;但另一方面,美国单边行动,以武力干预他国主权,直接诉诸武力或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在全球强行推进民主体制,而美国式的消费理念和大众文化更因其强大的国际传播力量成为全球各国文化保护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者的恶梦。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论”所担心的不外乎他所说的“如果确实如此并且美国人不再坚持植根于欧洲的自由民主政治意识形态,那么我们所知的美国就会跟随另一个自由意识形态规定的超级大国而步入历史的灰烬而不再存在。”④[美]亨廷顿:《如果不是文明,那是什么?》,美国《外交事务》,1993年11-12月号,第191页,第190页。
伯林曾指出:“完美的世界,最后的解决,一切美好事物和谐共存,这样一些概念,对我来说,并不仅仅是无法实现的——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而且它在概念上也不够圆融;我不能够理解,这种和谐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些至善(Great Goods)是不能够一起共存的。”⑤[英]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伯林虽然有些悲观,但却道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人与人、国与国、不同的民族和宗教之间,因为经济利益、价值观念之间存在难以化解的矛盾,因此冲突在所在难免。问题是,到底是否存在解决问题的方案。从柏拉图到现在西方传统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即他们认为,1)人类价值的追求也如同数学、物理这类科学问题的解答相似,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2)而且所有重大问题的答案都有方法找到;3)所有重大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互相融合,和谐统一的——因为真理不可能互相矛盾。美国的单边主义政治哲学与欧洲的文化传播论者,多半是这种理论的持有者和实践者。但是他们显然忽视了,就算是科学问题的求真也存在多种不同的路径,人类生活方式与价值更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因此,化解人类冲突的求解之道并非只有一条线索,一个答案,前文所述的多元主义的承认政治,显然是一条更宽容、更现实,也更容易达成的理想目标。
佛教经典里有一个阿育王皈依佛教故事,据史实记载,阿育王皈依佛教是因为他对于加林加国的征服战争。据推定,阿育王是公元前268年即位后10年,也就是公元前259年左右,他向印度东南岸的加林加国发起了入侵战争。战争以阿育王压倒性的胜利而告终。阿育王在加林加国的征服战争后,反省了战争的悲惨,发誓不再发起战争。他不相信战争作为政治手段的有效性,也认为战争不一定是最好的手段。之后,阿育王根据佛教的“真理”来施行政治,在其领土各地砌建了刻有敕令和佛教教谕的巨大石柱。另外,他还在处于国境之地的摩崖石刻上也刻写了敕令和教谕,以宣喻佛教治国之理念。因此,阿育王笃信了佛法,大施仁政,以佛法治国,以慈悲、仁道教化民众,促使人民安居乐业。当阿育王再次巡视全国的时候,夹道欢迎的百姓,已经是心悦诚服的高呼万岁,欢欣鼓舞。见此情状,阿育王深深感叹:“法,可以战胜一切;惟有法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①参见李向平:《和合为尚——佛教和平观》,北京:宗教文化出版杜2003年版,第26页。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最理想之境,当然不是在全球推行战争与冲突,而旨在化解各冲突方之戾气,建构和平之舆论环境。霍布斯在《论公民》中列出了自然法的各种基本的原则,而概括起来无非是说和平和合作比暴力和普遍的竞争对自我保存更为有利。国家的产生必须寻求一种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强权力量,来克制个人的天赋权利,使之转换为社会状态中的人的自由,实现秩序和安全。这样就必然要求是从自然的状态过渡到人为的社会。②李伟:洛克和霍布斯自由主义思想比较,《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12 月,第57-60页。
和平传播也正是在这一理念之下被少数学者所关注。汤姆•布鲁诺认为,和平传播不仅是关于国家、文化或群体之间的传播研究,而且还包括了群体之间或群体内部的个人间的传播研究,它还涉及移情作为互动的本质的研究。和平传播本身包括发生在大脑中的和谐——紧张的个人内部交流模式,还指个人对内的“平静心态”。③汤姆•布鲁诺:和平传播:跨文化关怀的道德规范,载[美]拉里•萨默瓦、理查德•波特主编:《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麻争旗等译,北京广社2003年版,第508-517页。凯尔特纳则指出,和平传播“包括对人、过程、系统和条件的研究,研究用和平的手段而不是暴力和战争来解决任何社会层次的斗争”,④Keltner, J. (1987, November). Peace Communication: Scope and dimens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Boston.他指出,“维持和平……是干涉敌对双方不断扩大的斗争,并在斗争变成武力和毁坏之前,解决差异”,可见,凯尔特纳所关心的不是关于和平的谈话,或者把它作为—个抽象的概念,他相信通过交流行动把持有不同分歧的人带到更和平的环境中。⑤转引自[美]拉里•萨默瓦、理查德•波特主编:《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麻争旗等译,北京广社2003年版,第511页。
《庄子》有一名篇“混沌”,陈述的是他反对一味求同的思想。美国哲学家安乐哲在其著作中分析说:“强加一种既定模式简直就是为秩序从无数个可选择性中选择唯一,并且赋予其凌驾于他者之上的特权。‘倏’和‘忽’试图将一个不可括而为一、且有理由不一致的‘道’转换成一个单一秩序的世界。事实上,它们不仅杀了混沌,而且也杀了它们自己。”⑥[美]安乐哲:《和而小同:中西哲学的的会通》,温海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和平传播的基础是“推己及人”。中国人讲交往过程中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也有类似的观念,那就是“移情”。有学者指出:“移情可作为所有交流过程的基础,因为它关系到我—你、自我—他人超越类别差异的努力。移情的作用和解决冲突的过程是同构的,并朝着主我或客我的共性运动,以防止冲突扩展。这是移情的一般情况,不管是互动的一方还是双方有移情行为,当然哪怕有一方发生移情行为,这总比没有发生好。”①汤姆•布鲁诺:和平传播:跨文化关怀的道德规范,载[美]拉里•萨默瓦、理查德•波特主编:《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麻争旗等译,北京广社2003年版,第511页。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孔子之孙子思又推进了一层,他说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②《礼记•中庸》。
“单边主义”、“种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乃至“大汉族主义”都会造成文明冲突,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也许就在冲突之中永远的消失。费孝通先生将文化自觉归结为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自然是一种理想之境。对此乐黛云教授指出,只有具备这样的文化自觉,才有可能建设多元共处共生的全球社会。但是,我国长久以来“唯我独尊”的心态是一大障碍。当国家贫弱时,它会演变成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当国家逐渐强盛时,它就滋生为企图覆盖他族文化的东方中心主义。历史已经证明西方中心主义是行不通的,东方中心主义重蹈西方中心主义的老路,也不会有好的结果。③乐黛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8月14日。国际传播场,需要有众声喧哗,允许不同的观念、价值和生活方式共存。如果真要有一种旋律的话,那就是“和平”的天籁之音,无论是个体、媒体还是社会组织都能生活在弥漫着宁静、平和的信息之网中,让和平传播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旋律。
(责任编辑:钟宇欢)
Ten Relationship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WU Fei
More and more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rised with challenges in the overall context nowadays. Cultural discrepancies and ideological conflicts are performing themselves intensely in the current times while agreements and clashes coexist with comprehension, misunderstanding and distor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have exceeded the traditional geopolitical boundaries and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s well. The actua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with mutual respect and appreciation requires a much mor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design in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ield should present itself as an open stage inclusive of various ideologies, values and lifestyles, which may sound like pieces of harmonious music on this concert. Peaceful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the main theme in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with all the individuals, media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being involved in a placid communication atmospher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Globalization; Cultural Con flicts.
G20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