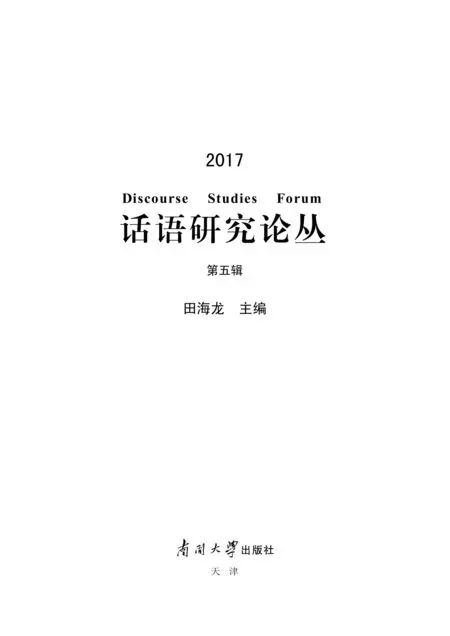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人际意义的多模态话语研究*
2017-06-11刘嘉辉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刘立华北京交通大学话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
◎刘嘉辉 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 ◎刘立华 北京交通大学话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人际意义的多模态话语研究*
◎刘嘉辉 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 ◎刘立华 北京交通大学话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国内学者对其相关问题做了不同的研究。本文在讨论“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以社会符号学派Kress和van Leeuwen的视觉语法为基础,建构新的人际意义多模态分析框架,在跨文化传播视域下对“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的人际意义传播进行探讨,研究侧重宣传片的结构、内容和互动模式,其中也包括该宣传片如何实现其跨文化传播的效果。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作为一种特定的话语及多模态话语形式,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展示中国特色元素,凸显了该宣传片的人际意义,同时也照顾了宣传片的国际化受众。“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是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的典范,该宣传片也因此构成了“一带一路”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人际意义;多模态话语
1. 引言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简称“一带一路”。2015年3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颁布。《愿景》提出了“一带一路”国家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在内的“五通”。“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一项充满中国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的方案。据南方网2017年4月14日的报道,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大。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在与世界互动过程中依然面临很多的问题和挑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带一路”倡议在提供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很多的挑战和困难。2016年8月17日,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要求积极宣传“一带一路”建设的实实在在成果,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对外传播“一带一路”以及如何讲述“一带一路”的故事,成了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推广的重要内容。
本文在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以Kress和van Leeuwen的视觉语法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1作为研究案例,对“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建构多模态情境下人际意义的社会符号学体系进行研究,着重考察宣传片的人际意义的表达模式,同时考察宣传片这一特定话语形式在跨文化传播视域下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此外,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多模态话语分析相结合,为“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研究视角。
2. “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研究现状与多模态话语发展
2.1 “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研究现状
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促进国际合作,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国际演讲中深入阐释该战略的深刻内涵和积极意义。这些讲话作为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展示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国家理念和国家政策(刘立华、徐硕,2016)。从全球化视角来看,中国正在发展中的“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与世界各国进行经济与文化上的互动与沟通,通过多种手段与途径增强“一带一路”建设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传播力(周凯,2015)。但是,由于存在“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加上我国并不注重、不善于对外传播,“一带一路”一些沿线国家对我国依然存在歪曲、片面的认识。因此,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我们应当借助此契机,积极对外塑造和输出我国国家形象(徐旭伟,2016),对外传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发挥好先行保障、如何发挥全阶段全系统支撑的作用,已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寇立研,周冠宇,2015)。
针对“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策略,计宏亮(2015)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带来中国总体外交策略的转向,同时也将推动国际秩序发生深刻调整,形成新的国际运行规则,因此倡导多元包容的文化精神,构建符合“丝绸精神”的话语体系变得十分必要。黄俊、董小玉(2015)则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遭到了话语强势的西方媒体的污名化传播;要突破传播困境,需要明晰战略的传播路径,转换传播模式;发挥逆向传播的强大舆论功能,注重国际国内传播互动;建构主动型传播模式以及提高传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梁海明(2015)指出,在“一带一路”海外传播中,要达到让各国增加了解、消融误解的目的,应从他人角度考虑,避免自说自话,片面展示中国意图,更要重视综合利用金融、文化等传播手段,才能更好地实现传播效果。袁赛男(2015)则认为,要想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传播中消除国际误解,寻求国际共识,应根据变化的世界格局及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对已有的传播理念、方式、策略进行适时转向。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储殷、黄日涵(2016)认为,在新的全球政治经济语境下,当代国家应整合“软实力”与“硬实力”,把“巧实力”打造成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路径。周兆呈(2015)则提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应注重叙事框架的完善,善用民间力量,强化换位思考,进一步营造平等互信的机制和环境。巴殿君、朱振恺(2015)认为,从地缘政治上看,中国“一带一路”的目标是“稳疆兴疆”、建立“命运共同体”、推动“南南合作”、构筑“新型国际关系”。
以上有关“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研究文献,内容都较为宏观,大多强调一种传播模式的转变或是对西方受众的照顾,但是鲜有对宣传文本或是话语的详尽分析。其次,以上研究大多都采用新闻传播、国际关系、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范式或是理论,从话语视角来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传播的话语研究还很少。最后,话语分析本身也构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同时,鉴于话语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和重构作用,对“一带一路”倡议实践中的话语实践的考察,能帮助揭示我国与世界在互动过程中的身份建构与磋商过程。
2.2 话语与多模态话语研究
2.2.1话语与话语分析
话语这一概念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学研究。话语往往关注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Fairclough(2003)对话语的界定坚持了一种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的观点,认为社会生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各种运行机制以复杂的方式制约着这一系统的运作。法国思想家福柯则认为,话语是特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陈述,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Foucault,1980)。以上论述阐明了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之间的辩证实现关系,话语一方面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留下的痕迹,是社会变化的“凝固体”,是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变化的“晴雨表”,同时也是观测社会互动和变迁以及身份磋商的重要标示之一(Martin,1995;Wodak,1999)。另一方面,话语不仅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或是观点的表达和信息的传递,话语的功能还在于能影响受众、建构社会现实(Berger & Luckmann,1966;Burr,2003)。在学术层面,话语也构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观察社会、研究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施旭,2008)。因此,话语实践的重要性在于其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呈现、信息的传递,或是观点的表达,更为重要的是,现实生活中话语实践传递了一种价值和立场,这些价值和立场一方面是话语主体的利益表达,同时也是形塑话语双方主体身份的重要手段,也正是在这种以话语为主要形式的互动过程中,话语双方主体的身份被逐渐建构起来,这种被不断建构或是重构的身份进而影响着社会活动的进行。以上也构成了我们研究“一带一路”话语实践的重要意义。
话语分析则是一种以语言和意义为核心成分进行研究的宽泛的方法派别(Fairclough,1989,2001;Blommaert,2005;Chouliaraki & Fairclough,1999;Wodak,1999,2001;苗兴伟,2004;van Dijk,2008a,2008b,2009,2014;田海龙,2015)。话语分析通过对谈话细致的分析,来观察语言条目的分布和语言结构。话语分析致力于对理所当然的知识使用批评性方法,强调知识和社会过程之间以及知识和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Philips & Jorgensen,2002)。在话语分析看来,现实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被认识,世界的表现形式则是话语的产物。话语通常是一种权力或是政治的表达手段(Laclau & Mouffe,2001),其目的不是为了被理解,而是要相信和顺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互动程度的加深,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也越来越频繁。在这一发展趋势下,以话语为主要载体的互动导致了国与国之间话语权的争夺问题。国际政治权力斗争不仅是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传统硬实力之间的竞争,更是价值观、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竞争。而每一种竞争的背后,则是某种观念或观点的争夺,抑或对某种观点或观念的解释权、话语权的争夺。尽管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影响已经开始超越经济而深入到了政治、文化和全球性问题等诸多领域,但是当我们面对西方守成国家,特别是美国提出的人权标准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抑或西方媒体的指责或片面报道时,我们有时只能被动地“解释”或“说明”。其次,从全球的视角来看,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在全球事务中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在与守成大国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共建一种新的话语秩序,参与、共享进而主导话语权,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作为特定的多模态话语形式,是“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重要话语模式,这一宣传片话语模式的成功与否,事关中国国家形象建设、国家话语权提升以及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构。
2.2.2多模态话语研究发展
多模态话语研究最早于20世纪90年初代由西方学者提出,研究涉及图像、颜色和声音等非文本模态,且研究多以Halliday所提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Kress和Hodge(1988)的社会符号学研究为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提供了基础。随后,Kress和van Leeuwen两人(1996)所做的研究被认为是该领域的里程碑。Kress和van Leeuwen(1996)所创立的视觉语法理论,认为视觉设计像语言一样,是一种社会符号。后人将他们的理论运用到教科书、书画和广告图像等研究领域,旨在寻找语言语法和视觉语法的异同点。此外,O’Toole(1994)将元语言功能运用到艺术,特别是对图像的研究。van Leeuwen(1999)则对声音和音乐模态进行研究,试图证明两者对多模态话语研究的必要性。
Machin(2007)认为Kress和van Leeuwen的视觉语法是研究多模态的理论基础。很多学者将Kress和van Leeuwen的理论运用到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如Thibault(2000)的电视广告研究,Stenglin和Idema(2001)将视觉语法与二语习得相结合的研究,Lemke(2002)的超模态(hypermodality)研究,Unsworth(2001)和Kress(2003)对新媒体时代下的读写研究,以及Scollon和Philip(2004)两人的多模态话语研究与学习形式的相关性研究等。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推动了多模态话语研究这一领域。
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也呈现出多发之势。李战子(2003)在《多模态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中首先介绍了多模态话语研究的相关理论,提出了图像分析的框架并强调了多模态话语研究在教学中的重要性。自此,国内学者纷纷对该领域进行研究,如胡壮麟(2007)对多媒体与多模态进行的区分研究。张德禄(2009)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提出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该框架主要由五个层面的系统及其次级范畴组成,分别为文化层面、语境层面、意义层面、形式层面和媒体层面等;张敬源、贾培培(2011)的研究也是以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视觉语法的关系为切入点,对Kress和van Leeuwen构建的视觉语法进行探讨,提出视觉语法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对其分别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此外,我国许多学者将多模态话语研究运用于其他领域当中。曾庆敏(2011)对多模态教学模式在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罗小春(2012)将多模态话语理论运用到对电影海报的研究当中;耿敬北等(2016)以多模态话语分析为框架,对QQ群话语进行了研究。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也将多模态话语研究运用于如电视广告和电影等动态话语中。
截至目前(2017年4月7日,下同),在CNKI数据库上输入关键字“一带一路”,检索出的文献数量多达31398篇,时间跨度为2014年至2017年。输入关键字“一带一路”和“传播”,检索出文献数量为728篇;输入关键字“一带一路”和“宣传片”,检索出文献数量为7篇,但真正有关“一带一路”宣传片的研究文献仅为1篇。从其他数据库,如百度学术等搜索出有关“一带一路”宣传片的研究也是寥寥无几,有的文章研究的是《一带一路》纪录片的宣传片而并非“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从以上数据可得,虽然如今国内学者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十分深入,并且对“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进行定量定性研究,但从“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角度来看,相关研究还是较少,对”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的话语模式研究更是屈指可数。此外,相关研究均侧重视觉语法理论介绍,应用研究还比较少。
3. 理论框架建构
“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是典型的动态多模态话语形式。在这一话语形式中,图像、音乐、文字等符号在持续性联动过程中进行整合,进而构建出话语的整体意义。Halliday指出,情态和语气两个系统是语言模态中人际意义的主要体现,情态反映语言行为的参与者对于人和事物的判断,语气则反映交流的语义角色和交换物的属性(Halliday,1994:68-69)。视觉语法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图像模态中的应用,并且认为视觉语法的再现、互动和构图三大功能分别对应系统功能语法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互动意义可以看作是关于图像的制作者、图像所呈现的对象和图像的观看者之间的关系,同时提示图像观看者对呈现对象应持有的态度。因此,互动意义可被看作是传递语篇交际功能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需要通过与外界的互动来得到更多的认知,认知投入越多,互动意义越丰富,对多模态话语的理解就越深刻。这种人们通过感官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方式构成了模态(顾曰国,2007:3)。该研究把图像模态、音乐模态和文字模态中涉及的任务关系统一称为人际意义。
视觉语法的互动功能主要包括接触、社会距离、态度和情态、视觉语法这四个维度(Kress & van Leeuwen,1996)。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人际意义理论和图像语法的互动理论,本文构建多模态人际意义的分析框架(如表1所示)。

表1 “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人际意义多模态分析框架
以上多模态分析框架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包括对宣传片的结构分析以及互动分析。结构分析包括对宣传片的情节分析和内容分析,情节分析部分主要交代该宣传片按主题和时间节点分割为若干部分,并逐一对每个部分进行总结与说明。内容分析主要包括对宣传片图像、文本和声音的分析,其中着重对突显人际意义的图像、文本和声音模态进行举例说明分析。互动分析是本文重点分析的对象,主要包括接触互动、社会距离互动、态度互动和情态互动。
4. 宣传片人际意义的多模态分析
胡壮麟等(2012:115)认为,人际功能除了具有表达讲话者的亲身经历和内心活动的功能外,还具有表达讲话者的身份、地位、态度和动机的功能,人际功能同时能完成对事务进行推断、参加社会活动、建立社会关系的任务。通过以上功能,讲话者使自己进入到某一个情景中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推断,并试图影响别人的态度和行为。Thompson(2000)认为人际意义是人们使用语言与他人互动,建立和保持关系,并表达自己对事物的观点,从而影响、引出或改变他人的想法。Thompson进一步指出,语气、情态和态度对实现人际功能至关重要(Thompson,2000)。此外,此功能还表示与情景有关的角色关系,包括交际角色关系,即讲话者或听话者在交际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之间的关系。根据Halliday的观点,人际意义需要通过语气(mood)和情态(modality)两个系统来实现(Halliday,2000)。
4.1 “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的结构分析
“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中文名为《一带一路,连接你我》,配以中英文字幕,旁白为英语,时长1分30秒。该宣传片于2015年9月17日登陆美国CNBC电视台的美国频道和世界频道,并滚动播出2。该宣传片集合多种社会符号资源模态,气势磅礴,让观众对中国“一带一路”这一宏伟倡议有了一定的了解。根据宣传片内容,可把该宣传片总结为以下六个部分,如表2所示。

表2 “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主要内容
宣传片以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George Yeo)的寄语为开端,接着介绍“一带一路”的起源含义以及该项目所覆盖的地区和大洲,然后举例展示该项目的发展以及将要进行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紧接着介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然后总结“一带一路”项目并在最后部分展示该项目的主旨。“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综合运用文字、图像、色彩、声音(旁白)、音乐等多种符号模态,展示了“一带一路”项目的精神理念。以上述情节分析时间分配为基准,各个部分具体的文字、图像、色彩、声音(旁白)、音乐等模态的使用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宣传片模态使用一览表

上述五种模态整合成为图像(Image)、声音(Sound)和言语(Verbal)三种模态。具体来说,宣传片开头4秒以恢弘的音乐、黑色为背景,用动画的形式展示新加坡前外交部长的寄语,“THE ONE BELT, ONE ROAD POLICY WILL BRING ABOUT A COMPLETE RE-OPENING OF EURASIA – GEORGE YEO, FORMER FOREIGN MINISTER, SINGAPORE”。寄语体现出杨荣文对该项目开拓亚欧新篇章寄予了厚望;此外,该寄语以大写英文字母的形式呈现,一方面对其寄语给予重视,另一方面,大写字母不宜一目了然,从而会让观众付出更多的注意力。
随后,一条红色的道路随着平缓的背景音乐,以动画的形式从红墙出发,寓意为“一带一路”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女声英语旁白随即出现,向观众介绍“一带一路”的起源和含义。同时,红色道路穿过中国广州和上海这两个重要城市。此外,红色道路展示出如“A MUTUALLY BENEFICIAL”和“ROAD OF INTERCONNECTION”等能体现出中心思想的重要词汇。宣传片播放到0’15’’的时候,“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白色道路的形式出现,画面呈现出“一带一路”亚欧大陆和非洲沿途重要城市的英语名称。代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红色道路以西安为起点,代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白色道路则以泉州为起点,然后各自迈向其他城市。
第三部分多以远景构图,画面多以物为主要内容,首先展示的是阿拉伯装饰的人和骆驼在沙漠上行走以及古帆船在海上行驶的画面,让观众联想到古代丝绸之路的辉煌,同时红色道路显示出“TRADE”和“MULTILATERAL”的主题词。紧接着音乐转为急促,画面使用快镜和常速相结合的手段呈现现代化建设进程,其中包括沿线道路、铁路、港口、能源设施、健康医疗和教育等,随后音乐再次趋于平缓。
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多以近景和特写构图,画面多以人为主要内容。
最后一部分在红色道路上展示“THE ROAD LINKS US ALL”,以及引出该宣传片的主题“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4.2 宣传片人际意义的互动分析
Kress和vanLeeuwen的视觉语法理论阐述了图像互动意义,包括接触(Contact)、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态度(Attitude)以及情态(Modality)四个方面(Kress & van Leeuwen,2006)。本节将从这四个方面,在跨文化传播视角下探讨该宣传片是如何通过多模态符号资源的互动来共同构建人际意义的。
4.2.1接触互动
吴安萍、钟守满在《视觉语法与隐喻机制的多模态话语研究》中提到,接触是再现参与者通过目光指向与图像观看者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想象性的接触关系。此外,接触可分为两种:一为“索取”,即宣传片的参与者的目光指向观众,有眼神交流;二为“提供”,即宣传片的参与者没有指向观众,无眼神交流(吴安萍、钟守满,2014)。宣传片正是运用图像画等因素使得观众与参与者产生特定的关系,进而构成他们之间的互动。
如上所述,“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一带一路,连接你我》综合运用文字、图像、色彩、声音(旁白)、音乐等多种符号模态,展示“一带一路”战略的精神理念。纵观整个“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所出现参与者的目光没有指向观众,整个“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没有出现“索取”类图像。“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的参与者集中出现在0’45’’后,均表现为“提供”类图像。
同时,宣传片的信息传递也构成了宣传片与潜在受众的基础。“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中多处出现有关中国的城市,如广州、上海、西安,或中国元素的画面,如红墙等,以及不同肤色的人种、个别沿线国家的风貌。以上画面在以舒适的背景音乐、中英字幕、特定的流水声、不同的色彩等多模态符号的衬托下,向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观众提供信息。观众通过视觉、听觉等多种渠道与宣传片中所出现元素进行互动。
4.2.2社会距离互动
Kress & van Leeuwen(2006)提到,社会距离与镜头取景框架大小选择有关,进而决定图像中再现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的亲疏关系。在宣传片这一话语模式中,社会距离指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的距离。在视觉图像交流中,由于社会距离的不同,图像参与者与图像观看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存在着不同。社会距离指表征参与者与互动参与者间的距离,主要尺度有亲近距离、个人近距离(远距离)、社会近距离(远距离)和公共距离等。
“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的前两个部分以及第三部分的前半段,多以“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城市的繁华、基础设施的建设图景与动画相结合,并且多用远景拍摄制作,让观众更直观了解中国愈加繁华的同时,也拉近了画面中出现的人、景、物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宣传片的后半段多以近景和特写镜头为主,例如,在宣传片0’47’’- 0’49’’谈到健康医疗以及教育等问题时,使用了特写镜头。第一个画面清晰显示一位华人女医生拿着先进的设备为一位外国人答疑,第二个画面虽然没有面部特写,但从手臂的肤色可判断是两位非洲小孩穿着干净的校服在认真地学习。此外,宣传片在0’54’’时还使用了非洲妇女用上干净水资源微笑时的特写镜头,在1’04’’时使用了白人妇女灿烂笑容的特写镜头。这些特写镜头,极大地拉近了宣传片和潜在观众之间的社会距离。同时,字幕“为急需帮助的国家提供资源,实现共同发展,并将促进国家间投资、贸易和文化交流”,又凸显了一种自我的积极评价(Martin & White,2005)。“实现共同发展”的表述又充分考虑了受众的利益诉求,让观众感受到“一带一路”不仅造福中国,还能为沿线欠发达国家提供帮助,从而拉近了“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接下来谈到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协同发展提供融资支持时,宣传片中出现了4处不同肤色的人相互讨论、群策群力的画面,接下来又出现了两个不同肤色的人为合作成功而握手、白人妇女拥抱黑人小孩、不同肤色的人坐在餐桌前举杯同庆的画面,这些画面同样也让不同国家、种族的观众感受到当今社会不同人种之间交流的频繁,这在无形中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此外,“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的中英字幕、温柔的女声英文旁白,同样也拉近了中国观众和外国观众的距离。
4.2.3态度互动
态度是由多模态语篇中画面的拍摄视角来表现的,是对再现参与者持有主观态度还是客观态度的一种表达方式,主要分为水平视角和垂直视角。水平视角又可以分成正面角度和倾斜角度(Kress & van Leeuwen,2006)。从水平视角分析,该宣传片总体以正面角度叙事,这说明观众与宣传片中呈现的参与者之间是一种平等的社会关系,且说明观看者对片中所描绘的事实、事件、人物感同身受,与该宣传片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契合,即“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和平协同发展。吴安萍、钟守满(2014)认为,垂直角度由俯视角度、平视角度和仰视角度构成。俯视角度表示图像观看者处于强势地位,平视角度表示图像观看者与再现参与者之间平等的人际关系,仰视角度表示再现参与者处于强势地位。宣传片交替使用平视和俯视的角度,如以俯视的角度向观众呈现上海的繁华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给观众一种自然、全景的感觉,一种深刻的印象;在展示“一带一路”的发展以及不同国家的人的合作时,均采用平视的角度,给观众一种亲切、真实和可信之感。宣传片唯一一处仰视镜头在0’36’’时,画面显示的是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背对镜头,面向高楼和蓝天艳阳,旁边是葱郁的大树,这个画面并没有让观众感到压迫,反而让观众感受到成功男士的自信。
4.2.4情态互动
情态是互动意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Kress & van Leeuwen(2006),情态可分为三种程度:高情态、中情态和低情态。情态指对关注世界所做的陈述的真实度或可信度,且图像中越是运用更加饱和的颜色或不同的颜色越是具有更高的真实价值。该宣传片开头和结尾选取颜色一致,均采用白字黑底的形式呈现,给观众一种清晰、明了和简约的感觉。城市的繁华以及夜幕下的灯光璀璨、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种种成就、不同肤色人种之间的相互交流,这些画面在色调的选取上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外,贯穿整个宣传片的高情态色彩为红色,寓意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红色道路以及红墙和绿树的搭配,更是给观众特别是崇尚红色的中国观众在视觉上一种强有力的冲击感,进而达到该宣传片与观众之间互动的目的。
5. 反思与结语
本文以“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为语料,尝试在跨文化传播视域下对“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进行多模态话语研究。该研究在视觉语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在避免完全运用视觉语法作为分析理论的同时,同样适用于对多模态文本的分析。该研究结合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和理论,对宣传片中选取的部分镜头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宣传片并非只是照顾了中国观众的感受,而是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民都有了归属感,中国在宣传片中呈现为一个日趋国际化、现代化而且照顾受众感情和利益诉求的国度。同时,就选择的传播渠道来看,宣传片在美国CNBC电视台的美国频道和世界频道滚动播放,增强了宣传片的国际传播效果,也从侧面表现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正逐步提升。其次,“一带一路”宣传片是中国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经典案例。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西文化的互动和碰撞将变得更加密切和频繁。“一带一路”的话语实践无疑是观测中国与世界互动的重要标尺。这种互动不仅仅是一种言语的呈现、信息的传递或观点的表达,更为重要的是,话语实践传递了一种价值和立场。这些价值和立场一方面是话语主体的利益表达,同时也是形塑话语主体身份的重要手段,也正是在这过程中,话语主体的身份被逐步建构起来,这种被不断建构或重构的身份影响着整个社会活动的进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之相适应的话语体系的研究和建设。
注释:
本文为北京交通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专项基金资助项目“‘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及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构与重构研究”(编号:2016JBWZ006)的阶段性成果。
①“一带一路”官方宣传片获取网址:http://v.huanqiu.com/observation/2015-09/7552247.html。
②中美联合制作的宣传片登陆美国主要电视台,2015年9月27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27/c_128271421.htm。
Berger, P & T. Luckmann. 1996.. New York: Doubleday.
Blommaert, J. 200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rr, V. 2003.. London: Routledge.
Chouliaraki, L. & N. Fairclough. 1999..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Fairclough, N. 1989.. London: Longman.
Fairclough, N. 2001.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s method in soci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Fairclough, N. 2003.. London: Routledge.
Foucault, M. 1980.. Brighton: Harvester.
Halliday, M. A. K. 1978.. London: Arnold.
Halliday, M. A. K. 1994.. London: Arnold.
Halliday, M. A. K. 2000..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Jorgensen, M. & L. Philips. 2002..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Kress, G. & R. Hodge. 1988.. New York: Cornell UP.
Kress, G. & T. van Leeuwen. 1996.. London: Routledge.
Kress, G. & T. van Leeuwen. 2006.(2nd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Kress, G. 2003.. London: Routledge.
Laclau, E. & C. Mouffe. 2001.. London: Verso.
Leeuwen, V. T. 1999.. London: Macmillian.
Lemke, J. L. 2002. Travel in hypermodality., 1 (3): 299-325.
Machin, D. 2007.. London: Hodder.
Martin, D. 1995. The choices of identity., (1): 5-20.
Martin, J. R. & P. R. R White. 2005.. London: Palgrave Marcmillan.
Toole, M. T. 1994.. London: Leicester.
Scollon, R. & L. Philip. 2004..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Stenglin, M. & R. Idema. 2001.. London: Rouledge.
Thompson, G. 2000. I.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imited.
Thibault, P. J. 2000.. Campobasso: Pallad into Editore.
Unsworth, L. 2001..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van Dijk. T. A. 2008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van Dijk. T. A. 2008b.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Dijk. T. A. 200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Dijk. T. A. 20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dak, R. et al. 1999..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Wodak, R. 2001. What CDA is about—A Summary of its history, important concepts and its development. In R. Wodak & M. Meyer (eds.),Oaks: Sage Publications.
巴殿君、朱振恺,2015,论“一带一路”战略内涵、风险及前景——以国际关系为视角,《湖北社会科学》,第10期,38-42页。
储殷、黄日涵,2016,“一带一路”视阈下国家形象构建的巧实力探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78-84页。
耿敬北、陈娟子,2016,网络社区多模态话语分析——以QQ群话语为例,《外语教学》,第3期,35-39页。
顾曰国,2007,多媒体、多模态学习剖析,《外语电化教学》,第2期,3-12页。
黄俊、董小玉,2015,“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传播困境及突围策略,《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2期,121-127页。
胡壮麟,2007,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1-10页。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2012,《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寇立研、周冠宇,2015,“一带一路”对外传播需要把握的十对关系,《对外传播》,第3期,21-23页。
计宏亮,2015,“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权的建构刍论,《理论导刊》,第7期,101-103页。
梁海明,2015,“一带一路”海外传播应避免的几大误区,《中国记者》,第10期,32-34页。
刘立华、徐硕,2016,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话语创新实践案例研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第3期,19-30,135页。
罗小春,2012,多模态语篇分析研究——以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海报为例,《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第5期,46-48页。
李战子,2003,多模态话语的社会符号学研究,《外语研究》,第5期,1-8,80页。
苗兴伟,2004,“话语转向”时代的语篇分析,《中国海洋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第4期,64-71页。
施旭,2008,话语分析的文化转向:试论建立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范式的动因、目标和策略,《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131-140页。
田海龙,2015,新修辞学的落地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兴起,《当代修辞学》,第4期,32-40页。
吴安萍、钟守满,2014,视觉语法与隐喻机制的多模态话语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第3期,23-28页。
徐旭伟,2016,“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家形象塑造问题研究,《声屏世界》,第3期,16-19页。
袁赛男,2015,构建“一带一路”战略视域下的新对外话语体系,《对外传播》,第6期,13-15页。
张德禄,2009,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探索,《中国外语》,第1期,24-30页。
周凯,2015,全球化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的对外传播,《对外传播》,第3期,18-20页。
张敬源、贾培培,2012,关于视觉语法的几点思考,《当代外语研究》,第3期,38-40,160页。
曾庆敏,2011,多模态视听说教学模式对听说能力发展的有效性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6期,72-76页。
周兆呈,2015,国际舆论视野中的“一带一路”战略,《南京社会科学》,第7期,1-5,23页。
Multimodal Discourse Study of Interpersonal Meaning of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Promotional Vide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Liu Jiahui,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Liu Lihua,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has been a heat topic among scholars in China since it was put forward in 2013.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search situation of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first, then presents an analytical model with the basic of Visual Grammar put forward by Kress & van Leeuwen, and finally gives a multimodal discourse study of the interpersonal meaning of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promotional vide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study concentrates on the structure, content and interactive mode of the video. It is found in this research that, being a multimodal discours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promotional video fully shows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elements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audienc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promotional video is a model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and this video is also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ocial practice of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promotional video, interpersonal meaning, multimodal discourse
刘嘉辉,男,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硕士生。研究方向:话语研究。
刘立华,男,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话语研究、跨文化传播。
刘立华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100044)上园村3号,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
电子邮件:lhliu@bjt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