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新诗回眸”四人谈
2017-05-24王珂陈仲义霍俊明道辉
王珂+陈仲义+霍俊明+道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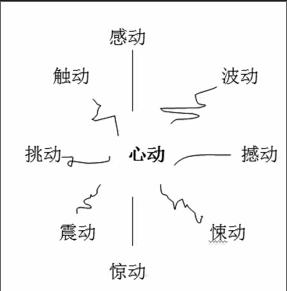
百年新诗:过去可回首将来有知音
王 珂(学者,东南大学教授)
作为一个有30多年专业新诗研究经历的学者,一个时时宣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诗消得人憔悴的”人,我常喜欢用莱蒙托夫的两句诗来描述我“反思百年新诗”的结果:“反顾过去,往事不堪回首/遥望将来,竟无一个知音。”“正像一座冷落的殿堂总归是庙,/一尊推倒了的圣像依然是神!”2002年6月的某一天,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参加我的博士论文《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的答辩会,当专家们都说自己根本不读新诗时,我差点说出你们可以否定我研究新诗的博士论文,但是你们不能否认新诗的客观存在。行文至此,我猛然发现这两句诗才是当时我的亲切感受,前一句说明新诗“曲高和寡”,后一句说明新诗“客观存在”。
新诗的数量可以统计,如2006年出版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刘福春著)收入1920年1月至2006年1月在海内外出版的汉语新诗集、评论集17800余种,涉及7000多位诗人。新诗的源头却难确定。新诗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是从“诗界革命”算起,新诗大致诞生于1897年,到1997年就有百年历史。二是从“白话诗运动”算起,新詩大致问世于1917年,到2017年才百年。正因为两种观点都存在,以“百年新诗”为题的各种纪念活动竟然也持续了20年,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纪念”到今天,这在人类的纪念活动史上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奇观。它正说明了新诗这种文体的复杂性,连自己的生辰都不清楚,前后居然相差20岁,更不要奢谈什么“新诗是否形成了传统”“新诗是否建立了自己的诗体”“新诗是否有文体合法性”“新诗是否应该建立自己的艺术标准”“新诗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是否存在”“新诗诗人是否有‘字思维”“如何新诗,如何现代”“浪漫主义如何影响新诗”等学术性问题。
正是长达20年的以“百年新诗回顾与反思”为题的各种研讨会、各种诗会和各种专栏文章等“纪念活动”,反而让理论家们越来越深入地考察新诗的历史,思考新诗的未来。如以上所列举的20年来新诗理论界的几种主要“论争”的结果令人欣慰,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新诗学术研究,也影响了新诗创作界,很多诗人也被卷入“百年新诗的回顾与反思”的“热潮”中。甚至一些古代汉诗研究者,尽管不读新诗,也公开宣称不喜欢新诗,却知道新诗坛发生的一些“事件”,如近期研究唐宋诗词的大家莫砺峰教授,在东南大学的一次学术活动中说他知道新诗坛的“梨花体”,让专门从事新诗研究的我十分惊讶。我三年前还参加过以“百年新诗”为题,针对普通民众的新诗朗诵会,目睹了生活在福建的诗人舒婷的“宝刀不老”与“盛名不衰”。这是2013年6月18日搜狐网的报道:《舒婷做客紫气云谷 领衔百年经典诗歌朗诵会》。这场朗诵会是2013年6-10月南京举办的“中国新诗100年·翠屏两岸诗会”中的一场。数百名舒婷30年前的“粉丝”涌入会场,让一同到场的中国台湾诗人鸿鸿感受到了中国大陆新诗爱好者的“狂热”,他对我说这种新诗民间热在台北市是不可能发生的。
正是因为纪念“百年新诗”的活动跨度长达20年,给了诗人和诗论家畅所欲言的机会,主要出现了悲观派和乐观派。悲观派认为新诗是失败的,一些新诗诗人也反戈一击。如生于福建的老诗人郑敏在2002年说:“中国新诗很像一条断流的大河,汹涌澎湃的昨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悲的是这是人工的断流。将近一个世纪以前,我们在创造新诗的同时,切断了古典诗歌的血脉,使得新诗与古典诗歌成了势不两立的仇人,同时口语与古典文字也失去了共融的可能,也可以说语言的断流是今天中国汉诗断流的必然原因。”正是因为新诗与古诗成了“势不两立的仇人”,新诗诗人,甚至一些新诗领袖,如胡适、沈尹默、郭沫若等像杜甫诗所言“晚节渐于诗律细”,失去了新诗领袖应有的“晚节”,被旧诗“招安”。这种“复辟”行为实际上自我否定了他们年轻时的革命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宣布了新诗的失败。1999年现代文学史家钱理群把这一现象归结为新诗文体的不成熟,他说:“和充分成熟与定形的传统(旧)诗词不同,新诗至今仍然是一个‘尚未成型、尚在实验中的文体。因此,坚持新诗的创作,必须不断地注入新的创造活力与想象力;创造力稍有不足,就很有可能回到有着成熟的创作模式、对本有旧学基础的早期新诗诗人更是驾轻就熟了的旧诗词的创作那里去。”钱理群的这种观点在新诗研究界以外的文学学者中相当流行。
在20年来对新诗得失的持续争论中,早期和晚期的两次争议影响最大。周涛的文章《新诗十三问》原文刊于《绿风》1995年第4期,《星星》1997年第2期再次刊发引发大讨论,《诗刊》1997年第5期还发表了署名“莫”的综述文章《周涛文章<新诗十三问>引起讨论》。周涛在20世纪80年代曾被誉为“新边塞诗的三剑客”,是“西部诗的领军人物”,但是在90年代中期他就认为诗一文不值,原因是他发现新诗从诞生之日就是错误的,还认为百年新诗走过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尽管他发出这个有些“哗众取宠”声音的时间是1995年,他还是用了“百年新诗”这个特定词语。他的“讨伐之声”在两年后才得到了真正的响应,1997年成了名副其实的“新诗合法性反思元年”。从此以后,三教九流都可以对新诗说三道四,甚至横加指责,如韩寒2006年在自己博客上针对现代诗坛发布了6篇短文,其中一篇《现代诗和诗人怎么还存在》宣布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理由是写诗如同开赛车一定要开在指定路线的赛道里才会有观众看。这个观点与新诗理论界的“诗体重建”观点有“英雄所见略同”之处。韩寒的写诗如赛车需要“赛道”的观点几年后被著名老诗人流沙河“支持”。2015年8月14日《晶报》发表了《流沙河:新诗不耐读是因为没秩序》,流沙河说:“现在好多新诗不耐读,因为没有秩序。”“我不相信,中国的诗歌能把传统抛开,另外形成一种诗。最大的可能是把传统的东西继承过来,然后把现代的一些观念、一些文学、各种认识结合起来才有前途。”这些悲观论者的观点一出现就受到了乐观论者的反驳,乐观论者也主要来自诗人,如伊沙、沈浩波等诗人直接反击韩寒,甚至认为韩寒这样的“司机和俗手”不配谈诗歌。
身为新诗学者,我自然不能置身事外。20多年来也写了数十篇文章讨论“新诗的合法性”问题,还出版了《新时期三十年新诗得失论》和《新诗现代性建设研究》等专著。代表性论文有《并非萧条的九十年代诗歌——为个人化写作一辩》《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20世纪,青年诗人“横行”诗坛》《网络诗将导致现代汉诗的全方位改变——内地网络诗的散点透视》……特别是如同这次应《福建文学》的约稿写“百年新诗”文,我还多次写过这样的“命题作文”。如2005年应《文艺争鸣》之约,我写了《理性地对待“新诗”这种特殊文体 》(《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但是我的呼吁不但没有人响应,一年后的2006年竟然成了新诗的“灾年”,韩寒“发难”新诗正是在这一年。新诗受到了以网民为代表的民众的激烈攻击,一些官方媒体也“公然”否定新诗。2016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记者李舫发表文章《恶搞中沦为大众娱乐的噱头 谁在折断诗歌的翅膀》,全盘否定了当代诗歌,引发轩然大波。诗人李少君发表“檄文”《强烈要求〈人民日报〉记者道歉》。钱理群在2006年5月30日到6月2日写的《诗学背后的人学——读<中国低诗歌>》也说:“我对当代中国诗歌几乎是一无所知,坦白地说,我已经20年不读、不谈当代诗歌了,原因很简单,我读不懂了。”这一年“中国新诗向何处去”成为公众话题。这年9月,我针对当时网友恶搞诗人赵丽华的“梨花体”事件,写了《著名女诗人为何被恶搞》,这篇文章立刻被新浪网、人民网等多家门户网站转载,引起巨大反响。我到北京开会,《今日中国论坛》编辑专门找到我,请我写《中国新诗向何处去》,后来刊发于《今日中国论坛》2006年第11期。
20年来,在新诗理论界,我始终是乐观派的代表,从20世纪90年代为个人化写作辩护,到后来为整个新诗辩护,我始终用那句名言来描述新诗:“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当然我也承认新诗,尤其是当代新诗存在很多问题,毫不留情地指出诗坛弊端,甚至被诗人嘲笑为“新诗城管”,被诗评家视为“学术警察”。去年冬天在甘肃岷县参加一次诗歌活动,《星星》副主编李志国还说我的那篇《诗人坏,诗评家更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新诗持乐观态度并不是因为我研究新诗就有“敝帚自珍”的心理,而是源于30多年的研究,我已经研究出新诗的成绩与问题。2009年我的论文《新诗30年的五大成就与五大问题》的摘要是:新诗的起源与命名决定了新诗是一种偏激的文体,它的先锋性、动态性文体特征导致得失共存。30年来的新诗主要有五大成就和五大问题:促进了思想解放,发展了汉语诗歌,优美了现代汉语,丰富了国人情感,记录了国人生活;职能单一,文体极端,诗人严重缺乏学养,做人浮躁偏激,诗坛拉帮结派炒作风太盛。目前应该加强三方面的建设:以艺术方式加强标准建设,以改良方式加强诗体建设,以多元方式加强社会化写作。30年来的先锋诗颇能呈现新诗为中国思想解放所做的贡献,很多诗人争做诗意的先锋而非诗艺的先锋。诗人的“纯文学”写作同样具有政治革命的潜能。应该客观公正地评价新诗。
2010年我的论文《新诗百年的十大成就和十大问题》的摘要是:新诗百年,一直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和“公信度危机”,“新诗革命是否成功”“新诗是否形成传统”是近年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新诗主要取得十大成就: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完美了现代汉语,丰富了国人的感情生活,发展和丰富了汉语诗歌,展示出国人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丰富了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支持了中国现代音乐,促进了中国妇女文学的发展、民族诗歌的繁荣和中国现代学术的进程。新诗还存在十大问题:生不逢时,长于乱世,缺乏必要的文体标准,过分重视自由诗,职能单一,普及教育工作落后,新诗人严重缺乏诗家语意识、诗体意识和经典意识,年轻诗人浮躁偏激,受到外国诗歌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的负面影响,新诗评论界正气不够。目前新诗最需要重视“和谐诗歌”和 “经典诗歌”的建设。
如上所言,无论是在新时期30年还是在100年,我都把新诗的第一成就总结为:参与了中国的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加快了民主进程。因为我推崇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曾以守常之名在1916年8月15日的《晨钟》创刊号中的主张:“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1917年出现的“白话诗”正是新文艺的“先声”,没有新诗革命,就没有文学革命,没有文学革命,就没有文化革命及政治革命。我赞同海外学者李欧梵的观点:“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和作家个性的共同特点在于,他们都具有一种强烈的性格力量,这种力量赋予五四文人一种格外积极的心态……正如夏志清所说的,‘中国青年在五四运动时期所表现的那种乐观和热情,与受法国大革命激励而出现的那一代浪漫派诗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百年后的今天,作为新诗革命的受益者,我们不难发现胡适在1933年7月在芝加哥大学的讲演中的预言已经实现了。他说:“其时由一群北大教授领导的新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其领袖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也知道为获得所需,他们必须破坏什么。他们需要新语言、新文学、新的生活观和社会观以及新的学术。”
今天的中国,确实出现了胡适所言的“新语言、新文学、新的生活观和社会观以及新的学术”。尽管一路坎坷,几起几落,百年磨难,风雨兼程,这种抒情文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白话诗”阶段,重在“白话”不在诗;“新诗”阶段,重在“新”不在诗;“现代诗”阶段,重在“现代”不在诗;如今已经进入了“现代汉诗”阶段,既重视“现代”又重视“汉诗”。在前三个阶段文体都不太成熟,在最后一个阶段文体已经成熟了。应该给“现代汉诗”下这样的定义:用现代汉语和现代诗体,抒写现代生活和现代情感,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的语言艺术。它主要有启蒙功能、治疗功能和审美功能,尤其是新诗的启蒙功能(传统的“诗教”)和治疗功能(现代的“诗疗”),让新诗大可以“爱国”,小可以“治病”,两者相得益彰。因此要重视诗歌精神重建的启蒙现代性建设和重视诗体重建的审美现代性建设,分别由五部分組成。启蒙现代性建设要重视一大问题、两大需要、三大功能、四大任务和五大建设;审美现代性建设要重视六大特质、七大类型、八大诗体、九大题材和十大关系。一大问题指生存问题。两大需要指人的生理需要与审美需要。三大功能指诗的启蒙、治疗和审美功能。四大任务指要促进改革开放,记录现代生活,优美现代汉语和完美汉语诗歌。五大建设指要建设现代情感、现代意识、现代思维、现代文化和现代政治。六大特质指要重视新诗在新世纪的六大文体特质:在写什么上多变的情绪多于稳定的情感,在写作手法上叙述受到重视,在写作语言上平民化口语多于贵族性书面语,在诗的音乐性上内在节奏大于外在节奏,在诗的结构形式上视觉结构大于听觉结构,在写诗的思维方式上图像思维越来越重要。七大类型指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和媚俗艺术。八大诗体指自由诗、格律诗、小诗、长诗、散文诗、图像诗、网络诗、跨界诗。九大题材指校园诗、城市诗、乡土诗、生态诗、旅游诗、爱情诗、打油诗、哲理诗、政治诗。十大关系指要处理好新诗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宗教、性别、年龄、地域、民族的复杂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