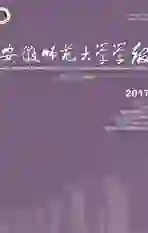理念、话语与制度变迁
2017-05-20沈燕培
沈燕培
关键词: 理念;话语;话语性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
摘要: 话语性制度主义以理念和话语作为解释制度变迁的核心概念,通过阐释理念的实质内容和话语的互动性过程,呈现制度变迁的动态性与非均衡性,弥补了新制度主义在解释制度变迁时局限于均衡和静态性的不足。话语性制度主义不是替代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而是对它们的补充,其理论和方法在各个领域的运用中正逐步完善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 D23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3032307
Key words: ideas; discourse;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new institutionalism
Abstract: Ideas and discourse are the core concepts of discrusive institutionalism. The substantive content of ideas and the interactive processes of discourse not only present the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but also overcome obstacles that the three more equilibriumfocused and static older institutionalisms posit as insurmountable.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is not a replacement for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and 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but rather a complement to them.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have been gradually applied and developed in many fields.
在当代比较政治学中,新制度主义作为一个理论流派日趋成熟,研究成果丰硕。但有些学者认为,新制度主义在解释政治现象时存在一定的局限,忽视了理念和话语对制度变迁的功能与影响。基于此认识,他们提出话语性制度主义,并将其称为继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之后的第四个新制度主义流派。
一、话语性制度主义的理论背景
政治学源于对制度的研究,美国学者盖伊·彼得斯说,“回溯到第一次系统地思考政治生活,研究者首先关注的问题是能够构建个体行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朝向良善结果的统治制度的本质。个人行为善变与无常的本质,以及引导个人行为朝向集体目标的需要,要求形成政治制度。”[1]3政治思想家通过系统分析制度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开创了政治学。19世纪下半叶,政治学作为学科具有了独立性,其研究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制度和规范。但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政治學发生了一次行为主义革命,倡导政治科学的研究应以政治行为为中心,注重对个体心理、动机研究,注重对政治现象的定量化研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自身缺陷,政治学研究者开始反思制度的功能和重要性,促进了政治科学中制度的回归;与此同时,高度重视制度研究的社会学为政治科学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框架,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作为解释性因素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都对政治科学中制度的回归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84年,《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发表了詹姆斯·G.马奇和约翰·P.奥尔森撰写的《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2],拉开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序幕,其研究领域和分析途径不断拓展。但是,制度的回归与发展并没有带来理论、方法和观点的内在统一,一些学者面对新制度主义的内在混乱,对其进行了流派的划分。包括盖伊·彼得斯(B.Guy Peters)的七分法、西蒙·雷奇(Simon Reich)的四分法、克拉克(William Roberts Clark)的二分法、豪尔(Peter A. Hall)与泰勒(Rosemary C. R. Taylor)的三分法。
其中,大多数人认同的是豪尔和泰勒的三分法。1996年,彼得·豪尔和罗斯玛丽·泰勒在英国《政治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把新制度主义划分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3]46三个流派都以制度作为探究对象和分析工具,通过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理论解释丰富了政治学中的制度研究。但是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思考“什么是制度变迁中的实质力量”,认为新制度主义的现有框架过于突出“粘性”,过于强调偏好和规范对行为的约束,本质上是静态的,“无法很好地处理文化、信念、理念等‘非物质成分对行动者感知、行为和制度选择的影响”[4],无法很好地解释和处理现实中制度变化的动态性,即制度的变迁。为了弥补新制度主义的不足,“话语性制度主义”开始登上研究舞台,美国波士顿大学薇安·A.施密特(Vivien A. Schmidt)第一个将“话语性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的三个流派相连接,称为“新制度主义”的第四个流派。[5]
“话语”分析产生于语言学研究,在近代语言哲学和欧洲政治发展的推动下,话语研究已经从单纯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主题或方法转向为研究的范式。一些新制度主义学者将话语涉及到的理念、知识或价值的生产、传播等过程作为解释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强调话语对政策的作用方式在于对行动者偏好的影响、行动者认知的改变、行动者政治变革能力的增强。话语性制度主义对于宽广的政治学研究范围而言是一个伞状概念,关注的是理念的实质内容以及通过理念转变和对话交流而产生的交互性过程。[6]尽管“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一词在坎贝尔(Campbell)[7]的著作中早已出现,科林·海(Hay)也提出了与“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类似的概念,即建构制度主义(constructivist institutionalism)[8],但是在施密特看来,他们关注更多的是理念的实质内容,而不是蕴含着对话的交互性过程;仅仅把理念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引入制度研究中并不能称其为“话语性制度主义”,关键还需要一个行动性和交互性非常强的概念——话语。话语不仅仅是理念或其内容(说什么),更是一个语境(在哪里说、什么时候说、怎么说、为什么说),这一术语涉及的不仅仅是结构问题,也是行动问题。当前,话语性制度主义者已经有了共同的分析框架,形成了四个方面的共识:一是都非常认真地对待理念和话语,即使理念的定义和话语的使用非常广泛;二是都以一种或两种原有的三个新制度主义的流派为背景,将理念和话语放在一定的制度语境中;三是当他们把话语作为一种遵循“沟通逻辑”的活动时,都会把理念放在一定的“意义框架”中,即使他们之间在“交流什么、怎样交流、在哪交流”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四是他们都能以更加动态化的视野去研究制度变迁,以克服新制度主义原有三个流派存在的“均衡”“静态”的障碍。[9]
二、话语性制度主义的“理念”与制度
新制度主义的一些学者早就关注到理念与制度的关系问题。1998年,坎贝尔通过对历史制度主义和组织制度主义的比较,认为理念能够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通过认知理念和规范理念可以迫使政策制定者尽可能的考虑并构建行动者所需要的符号和概念,使行动者的政策目标合法化。[7]2002年,利伯曼(Lieberman)在解释政治现象的过程中,认为制度分析方法面临三个困境,即简化论、外衍性、过于强调秩序和结构;而理念在制度解释中,对变化和行动很敏感,能够有效地解释政治制度的动态变迁。[10]由此可见,理念在制度解释中有其特定的地位,相对于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话语性制度主义与它们的区别不在于把理念作为新的变量嵌入到制度分析中,而在于各个流派对理念解释逻辑的不同。
历史制度主义强调理念作为制度变迁的动力作用,把理念作为一个既定的价值观念。在解释制度变迁时,历史制度主义坚持路径依赖、回报递增路径,把历史上形成的对物质利益追求的惯性作为行动者偏好形成的基础因素,利益仍是行动者偏好的独立源头,理念作为其中的一个因变量,不直接影响制度结果,必须被某一制度结构下的成员接受才能成为原因,理念的发挥必须依靠既有的要素和渠道,历史制度主义代表人物彼得·豪尔就强调“任何理念的社会力量都必须在这些理念被有力的政治组织采用,并且与其他意识形态方式整合在一起,被更广泛地扩散到社会机体时才能得到产生和增强。”[11]170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套用制度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假定一套政治人的固定偏好和计算理性,认为个体是政治过程的核心行动者,个体展开理性行为的目标是效用最大化,但个体效用最大化将导致一些失常的功能,如搭便车等现象。为避免个人理性和集体行动的困境,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制度界定为规则和动机的集合,是个体理性行为在不同的动机与环境识别中形成的选择,理性使行动者为追求效用最大化,降低交易成本,会存在利他主义的行为,并接受制度调适,保持制度均衡。这就是诺斯所指出的:“人们是通过某些先存的心智构念来处理信息、辨识环境的。先存的心智建构帮助人们解读环境并解决所面临的问题。”[12]2324因此,理念或动机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偏好形成中还是发挥了先导性和能动性的作用,只是在解释逻辑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更关注个体行动者,认为在对普遍性的效用最大化追求中,主体偏好是行动者通过算计而产生的高度策略性。遵守制度不是道德义务使然,而是追求利益进行制度设计的逻辑结果。社会学制度主义把人看作不同背景下的社会人,把制度作为独立变量对其进行认知和文化的解释,排斥文化的情感色彩;在制度的生成和维系上,以“适当性”逻辑和文化途径解释制度化与同构性。社会学制度主义关注到理念问题,但把理念视作当然的认知图示,主张心理学的认知模型,忽视了行动者的能动性。
话语性制度主义直接以“理念”和“话语”作为解释对象,对理念的理解既涉及理念感知行动者策略利益的实证主义,也包括理念建构利益的建构主义。理念是行动者偏好的独立源头,利益与理性选择都是行动者观念的反映,利益不能同利益理念相分离,不同的利益理念会赋予行动者不同的理性选择,理念是行动者偏好和行为的根本因素。话语性制度主义将理念分为三个层次,即政策、程序与哲学。政策理念变化最快,当旧政策失灵或不符合政策设计者的要求时,政策理念就会发生改变,但是对制度变迁能否发挥作用,还取决于政策自身、行动者偏好、话语能力和政治变革能力等。程序是认知性的概念和理论,通过规定和说明决策者如何解决具体的问题,而对决策、制度变迁产生影响。有学者认为程序的改变会出现在“危机驱动”或者“大转折”时期,也有学者认为程序理念随着时间推移会出现阶梯式的渐进改变和调整以适应现实的变化。话语性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转换只是政策谈判、选举协商和政治妥协等行为的结果。无论社会是在稳定时期还是危机时期,理念的作用始终存在;无论是渐进积累还是剧变转折,理念的变化始终发生,其结果取决于行动者的思想,大多数情况下会直接决定制度的实际变迁。哲学,也有学者称其为“公共意识”、“核心理念”或“世界观”,是“一种规范性的背景假定,这种假定会通过限定决策精英可能想到的、对于其支持者和自己来说都可接受的和合法的程序范围,进而制约决策和制度变迁。”[13]94理念的三个层次实际上呈现了理念在不同的制度需求上的功能以及对制度变迁程度的影响力,凸显了理念的独立性与行动者的能动性。
以上不同流派对理念的解释存在一定的差异,话语性制度主义认为理念的多样性源于对其不同方面的关注,即理念的认知性和规范性。认知性理念说明的是“是什么、做什么”的问题,给行动者提供指导方针和行动规定,旨在通过基于利益的逻辑和必要性来评价政策和程序;规范性理念阐释的是“好或坏、应该或不应该”的问题,注重政策、程序与哲学的一致性,将价值观嵌入到政治行为中并影响政策的合法化。[9]理念的二重性使得不同流派對理念解释的侧重点不同,有些流派只关注理念的一个方面,如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其关注的是理念的认知性,在利益偏好的认知基础上构建制度约束,使其利益偏好合法化。话语性制度主义主张认知性理念和规范性理念都是必要的,都会对制度的维持或变迁产生影响。与先前的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相比,一方面,话语性制度主义在认知理念上遵循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的传统,关注新理念如何获得认可、如何确立制度转变的秩序等问题;另一方面,在规范理念上又与社会学制度主义有类似之处,能够始终以一个“适当性”的逻辑关注着对话的规范性内容,并进一步研究理念如何构建规范、话语、行动者的偏好结构等以改变原有制度内的行动,分析行动者如何和为何能够在民族价值上形成共鸣等问题。[14]
制度和理念的内在逻辑要求必须有行动者这一中介与桥梁,没有行动者,理念不会自动发挥影响。话语性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既是行动者的理念与行动,又对行动者的理念与行动形成制约,制度在行动者的交互行动中构建起来。在这一交互行动中,认知性理念和规范性理念发挥作用的机制就是通过具有建构作用的话语。
三、话语性制度主义的“话语”交互性与制度变迁
原有的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都强调保持制度的稳定与平衡,历史制度主义通过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实现制度的延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通过假设理性人的固定偏好保持制度的稳定性,社会学制度主义以政治制度的适当性逻辑要求行动者遵循文化预先设定的规范。他们认为制度是既定的、静态的,是外生冲击下的产物,而话语性制度主义关注的是对制度化完成后制度变革的解释,要剖析的是非均衡、动态性、内生性的制度变迁过程。理念作为话语性制度主义的重要内容,只能说明制度变迁的原因,使行动者能够在理念的变化轨迹下预见到制度的转变,但并不能解释制度变迁如何发生、理念如何推动制度变迁等问题。行动者通过“话语”的交互性使理念对行动者发生影响,这是话语性制度主义以“沟通”为逻辑解释制度变迁的关键。
话语的交互性是行动者表达和传递理念并使其合法化的互动过程。在政策制定和政治交流的公共空间中,话語包含着行动者“说什么、对谁说、怎样说、为什么说、在哪里说”等问题。话语性制度主义把话语分为协作性对话和沟通性对话,二者发挥作用的场域不同,交流互动的主体也不同。协作性对话主要在政策场域内,交流主体是政策行动者,以政策构建的个人和团体为中心,主要包括政府官员、政策顾问、专家和利益集团等,他们按照自身的政策和程序理念制定和解释政策,这些共同的理念构成了这一群体共同行为和身份的基础。沟通性对话主要在政治场域内,范围广泛,其交流主体被称为政治行动者,一方面包括政治领袖、政府发言人、政党活动家、游说者等,他们提出自己的政策、程序、哲学,吸引公众讨论,希望形成公众舆论以寻求其政治理念的合法化;另一方面包括媒体、社区领袖、社会活动家、公共知识分子、利益集团等在内的全部公众,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对话交流,对政府制定的政策进行回应、辩论、审议,直至修订。[15]话语性制度主义借助了社会学的场域理论,对场域进行了区分,并寻求在不同场域中的话语方式。布迪厄“场域自主性”理论认为,“一个场域越是自主的,这个场域的生产者只为本场域其它生产者生产而不为社会场域的消费者生产的程度越大。”[16]按照这一理论,话语性制度主义中的政策场域较之于政治场域自主性更强,基于集体身份和共同利益,其话语的交互方式主要为协作性话语,通过协作保障场域内成员的利益与权力。政治场域自主性较弱,场域内成员处于布迪厄所说的“敌我”逻辑,他们希望在沟通性话语中,改变政策场域的既定结构,寻求政策场域外利益和理念的合法化。实际上,政治场域与权力场域紧密联系,权力、位置与制度间的相互制约也不能忽视。话语性制度主义认为行动者的利益策略源自其权力和位置,而权力不仅源自位置,即行动者有条件行使权力,还源于目的(如行动者的利益策略是从自身出发还是从公众出发),行动者行使权力的理念和话语是强化了还是削弱了他们的权力,取决于公众对其陈述目的的回应。[6]而在话语的交互性过程中,原有的制度安排会对规范框架和认知范式产生影响,因此无论是上层精英间的协作性对话,还是从政治精英到普通民众的自上而下沟通性对话,话语性制度主义始终强调理念和话语不能是随意的,必须具有相关性、充分性、适当性、适用性、可信性等特征,以保证话语对制度变迁功能的实现。话语性制度主义的场域划分和话语要求,增强了话语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为分析话语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提供了前提。在各个场域的对话中,话语性制度主义并不否认原有流派的物质利益、文化规范等基本要素,而是强调理念和话语既可以构建利益,也可以改变利益,不仅能够反映文化规范,也能够重构它们。这表明话语性制度主义要通过理念和话语的交互性,实现结构性的制度制约与行动者主体能动性的统一。
话语性制度主义认为有感知的行动者是连接理念形成、话语互动和制度变迁的主体。有感知的行动者不仅拥有思想,而且能够将其思想通过话语与其他行动者分享并引起集体行动;行动者的思想、语言、行动对于解释制度变迁的驱动力是话语互动性的关键因素。原有的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都将制度看作是既定的,在行动者之外的,是行动者思想、语言、行为的框架和约束,话语性制度主义不仅把制度看作是既定的,而且看作是偶然的;制度不是强加于行动者的外在框架,而是内生于行动者的,是有感知的行动者能够改变和创造的,是其思想、语言、行动的结果;在制度中的行动不仅是理性计算、路径依赖、规范遵循的结果,更是有感知的行动者创造和维持制度的过程。[9]话语性制度主义对有感知的行动者的解释,实际上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结构化理论认为行动者具有能动性,其能动作用“不仅仅指人们在做事情时所具有的意图,而是首先指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能力”,[17]69“个体有能力‘改变既定事态或事件进程,这种能力正是行动的基础。如果一个人丧失了这种‘改变能力,即实施某种权力的能力,那么他就不再成其为一个行动者。”[17]76话语性制度主义正是从有感知的行动者出发,将行动者的理念与话语置于社会结构中;结构兼具使动性和制约性[17]263,既是行动者行动的“意义框架”,又是行动的结果,个体行动者在实践的过程中既受到社会结构(在某些方向上)的制约,又(在另一些方向上)得到社会结构的使能与赋权。基于结构的二重性,话语性制度主义提出有感知的行动者必须具备背景观念能力和前景话语能力。背景观念能力解释的是路径依赖下制度变迁中的继承性和持续性,行动者需要根据理念规则和既定话语环境的理性,把握最初制度的“意义框架”,要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法”向“对的听众”表达他们的观点,获得“对的回应”。[18]前景话语能力解释的是行动者对路径依赖的超越和对原有制度框架的创新,行动者能够在行动于其中的制度之外进行思考和对话,说服他人改变制度或维持制度,在互动性的对话中将个人理念转换为公众认同后的集体行动,使其合法化。在话语的交互性过程中,行动者发挥背景观念能力和前置话语能力妥善处理结构与行动的关系,实现动态化的制度变迁。可以说,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话语性制度主义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论基础。
四、話语性制度主义的发展趋势
理念对行为的影响一直是政治学者思考的问题,但是“制度主义者始终没有提出一个很好的理论来解释思想理念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13]91话语性制度主义把“理念和话语”置于政治行为和制度分析的核心地位,提出了解释制度变迁的新思路。
第一,话语制度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各个领域。近几年一些学者开始运用话语性制度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分析各国政治制度的变迁和政策问题,既有对全球范围内公共政策与国际关系的分析,也有对一个国家具体制度与政策的阐释,并在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发展了话语性制度主义。例如,女权主义学者支持话语性制度主义,将其作为女权主义政治分析的方法,但他们认为当前话语性制度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前提还是混乱的,存在一些有争议的核心概念,如Agent、Power、Position、Ideas、Discourse。[19]他们提出要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话语性制度主义作为女权主义政治分析的框架,重新构建因果关系,区分话语的基本要素,尽可能鉴别“什么情况下是行动者使用话语,什么情况下是话语被使用”。[20]话语性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在欧盟问题研究上也使用得较为广泛。关于欧盟主权国的债务危机问题,施密特认为在解决危机问题的谈判上,沟通不能仅限于欧盟领导者之间,还要面对市场和公众,这些要素在沟通中互相影响[21];在欧盟再生性电力能源保护问题上,劳伯(Lauber)用话语性制度主义解释了欧洲再生性能源自由化相关法律的出台与欧洲议会和部长理事会的反对之间的悖论现象出现的原因。[22]此外,话语性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还被运用到了电子信息行业的行为讨论中,利亚姆(Liam)和詹姆斯(James)认为在标准化的过程中,电子文档格式的争论一直是一个有关制度竞争和战略利益的研究专案。他用话语性制度主义的独特视角,分析了在争论中行动者扮演多样化角色的方式。[23]可以说,从人权、民主、环境问题到一个国家的具体制度[24],话语性制度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野,在不同的学科中逐步发挥作用。
第二,话语性制度主义需要注意到制度的静态性研究。话语性制度主义主要是针对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有关制度变迁解释中存在的静态性、均衡性的不足提出的,要从话语的动力性中解释制度变迁。但一些学者发现,话语性制度主义同样也具有静态功能,话语的交互性也会阻碍制度变迁。英国布里斯托大学马特·霍普(Mat Hope)和爱沙尼亚塔林大学的林加·若德拉(Ringa Raudla)通过爱沙尼亚的财政政策和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案例,分析了话语性制度主义以及政策在简单政治体系和混合政治体系中的静态性。他们校正话语性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认为话语性制度主义有强大的潜力去解释制度的静态。话语性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的模式应该是:行动者没有眼前利益,行动被文化规范警示、被历史路径规定了,但制度变迁了,此时话语是解释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相反,利益集团被侵蚀了,制度约束放松了,文化规范被质疑了,但政策却保持稳定,此时话语就成为解释制度静态的重要因素。[25]女权主义者在研究话语性制度主义时,也发现了话语因素对政策变迁的阻碍现象。他们以捷克共和国的堕胎法为例,认为它是对女性生育权的否定,违背了人权,呼吁修订。但是从身体健康和人口的质量、数量角度出发,医学话语坚决反对修订堕胎法,赢得了政治支持,成为强势话语。从话语性制度主义的分析来看,政治和话语是交织的,强势话语的持续性保持了制度的静态,反映和强化了制度的路径依赖。[26]
第三,新制度主义的不同流派需要加强学习交流,建立共同的分析基础。豪尔和泰勒在对新制度主义流派分析时指出,“每个流派都从其他流派中获得知识的话,将有助于它们建立一套更为精深的理论来更好地解决在它们自己的范式下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3]462006年,施密特在美国政治科学学会年会上所作的报告《给和平一个机会:调和四个(不是三个)“新制度主义”》中指出,话语制度主义是对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补充,而不是代替它们或形成竞争关系。[14]话语性制度主义认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物质利益,承认历史制度主义的关键节点和回报递增机制,也使用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文化、理念等概念。话语性制度主义解释了制度变迁中动态变化的复杂性时,其理念和话语都还需要在最初的制度场景内;话语的交互性过程是否始终都能够发挥作用实现制度变迁,还需要将话语作更为细致的划分,不同权势下话语的有效性也是存在明显的区别。也有学者将四个新制度主义流派放在一起分析其共同的缺陷,认为在比较公共政策分析中,他们都存在“制度决定论”“第二好的解释方法”等方面的不足,建议新制度主义要修订有关制度影响公共政策的核心命题。[27]新制度主义的每一个流派都对既定制度下的作用力提供了部分解释,抓住了人类行为及其相应制度影响的不同维度,它们之间应该保持一种更为开放和广泛地学习与交流,推动新制度主义的发展。
总之,话语性制度主义把理念和话语作为一个宏观变量引入制度分析,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有新制度主义流派的不足。尽管有学者争论话语性制度主义作为第四个制度主义流派的必要性,如贝尔(Bell)认为历史制度主义可以从理念的视角容纳话语性制度主义[28],但话语性制度主义者并不认可这一观点,认为理念必须与话语、行动、结构等因素结合起来才具有解释力。当然,话语性制度主义本身还存在不足,其基本概念、理论体系都有待于完善与发展。总体上,话语性制度主义还处于萌芽和起步的阶段,国内关于话语性制度主义的研究才初见端倪,话语性制度主义的解释动力、路径选择、话语的互动性、行动者能力等理论,对于探讨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方式、中国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制定都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与解读。
参考文献:
[1]B.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M].王向明,段红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James G.March & Johan P.Olsen.The New Institutionalism:Organizational Factor in Political Life [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4,78(3):34749.
[3]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4]肖晞.政治学中新制度主义的新流派:话语性制度主义[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2328.
[5]Mat Hope & Ringa Raudla.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and policy stasis in simple and compound polities: the cases of Estonian fiscal policy and United States climate change policy[J].Policy Studies,2012,33(5):399418.
[6]Vivien A.Schmidt.Taking ideas and discourse seriously:explaining change through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as the fourth “new institutionalism” [J].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0,2(1):125.
[7]John L.Campbell.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the role of ideas in political economy [J].Theory and Society,1998,27(3):377409.
[8]Colin Hay.Interpreting Interpretivism Interpreting Interpretations:The New Hermeneut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Public Administration,2011,89(1):167182.
[9]Vivien A.Schmidt.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Ideas and Discourse [J].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08,11(1):303326.
[10]Robert C.Lieberman.Ideas,Institutions,and Political Order:Explaining Political Change [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2,96(4):697712.
[11]劉圣中.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的比较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2]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3]约翰·L.坎贝尔.制度变迁与全球化[M].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4]Vivien A.Schmidt.GivePeaceA Chance:ReconcilingFour(not Three)“New Institutionalisms”[EB/OL].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7280511_Give_Peace_a_Chance_Reconciling_Four_not_Three_New_Institutionalisms1,2006.
[15]Vivien A.Schmidt.Putting the Political Back into Political Economy by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Yet Again [J].World Politics,2009,61( 3):516546.
[16]李全生.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146150.
[17]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18]Vivien A.Schmidt.Speaking of change: why discourse is key to the dynamics of policy transformation [J].Critical Policy Studies,2011,5(2):106126.
[19] Carol Bacchi & Malin R?nnblom.Feminist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A Poststructural Alternative [J]. Nordic Journal of Feminist and Gender Research,2014,22(3):170186.
[20]Teresa Kulawik.Staking the Frame of a Feminist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J].Politics & Gender,2009,5(2):262271.
[21]Vivien A.Schmidt.Speaking to the Markets or to the People? A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t Analysis of the EUs Sovereign Debt Crisis [J].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14,16(1):188209.
[22]Volkmar Lauber & Elisa Schenner.The struggle over support schemes for renewable electric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a discursiveinstitutionalist analysis [J].Environmental Politics,2011,20(4):508527.
[23] Magee Liam & A.Thom James.What's in a WordTM? When one electronic document format standard is not enough [J].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eople,2014,27(4):511482.
[24]HO,Ching Wai.Teacher Education as an Institution in China:A Discursive Study,“1949- Present”[D].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Published by ProQuest LLC,2015.
[25]Mat Hope & Ringa Raudla.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and policy stasis in simple and compound polities:the cases of Estonian fiscal policy and United States climate change policy [J].Policy Studies,2012,33(5):399418.
[26]Radka Dudova.The Framing of Abortion in the Czech Republic: How the Continuity of Discourse Prevents Institutional Change [J].Sociologicky asopis/Czech Sociological Review,2010,46(6):945975.
[27]Claudio M.Radaelli,Bruno Dente & Samuele Dossi.Recasting Institutionalism:in 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Public Policy [J].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2012,11(4):537550.
[28]Stephen Bell.Do We Really Need a New “Constructivist Institutionalism” to Explain Institutional Change [J].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11,41(4):883906.
責任编辑:陆广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