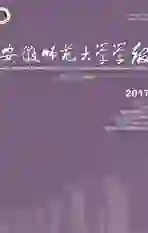徽商研究再出发
2017-05-20梁仁志李琳琦
梁仁志+李琳琦
关键词: 徽商研究;会馆公所;征信录
摘要: 徽商会馆公所类征信录是有关徽商会馆公所、义园善堂兴建过程、经费收支、运行机制、管理体制及相关徽商活动的原始档案材料汇编。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从整体上系统了解徽商商业慈善组织或机构的具体建立、运营过程,徽商的商业经营状况、商业网络,徽州绅商在建设、经营这些会馆公所过程中与官府和当地民众的互动关系,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具体、生动、富有生活气息的徽商。因此,这批文献对商业史、社会史、慈善史、政治史、教育史等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甚至为重写徽商史乃至商帮史提供了可能。
中图分类号: K09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3027110
Key words: Huizhou merchants research; halls and offices; letter of credit
Abstract: The Huizhou merchants guilds and office collection is a compilation of the original archives of Huizhou merchant Guildhall, potter's field town hall, its source of funds, operation mechanism, management system and related activities. It can not only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Huizhou commercial charity organization or organization's specific establishment, operation process, Huizhou commercial business condition, commercial network, Huizhou gentry and businessmen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se halls, and the official and l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ople, but also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specific, vivid, full of life Huizhou merchant image. Therefore, these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business, social history, history of charity, political history, history of education and other research has important value, and make it possible to rewrite Huizhou merchants history and even the history of business.
一
王国维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1]33。徽商研究的兴起就是以大量新资料的发现为直接导因的。傅衣凌1947年发表的《明代徽商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一》①一文,即是以方志、文集、笔记中大量徽商资料的发现为基础。日本学者藤井宏的《新安商人の研究》②,是国外最为系统研究徽商的著作,藤氏在中译本序言中写道:
1940年,我曾在东京尊经阁文库读书,因另有目的,浏览万历《歙志》,对其中构成新安
商人核心的歙商活动状况记载之详明,史料之多,大为惊讶,自是,我遂开始对有关新安商人的研究。不久,就将其成果吸收到《明代盐商之一考察》一文中……战后不久,我在静嘉堂文库翻阅明代各种文集时,发现汪道昆的《太函集》乃是有关徽州商人史料之宝藏,为之狂喜。拙著《新安商人的研究》就是根据《太函集》所提供的大量珍贵史料作为本书的骨架,也只有根据《太函集》各种史料始有可能为立体的、结构最密的掌握新安商人营业状况开辟道路,谅非过言。[2]51
上引文字,凸显了新资料对徽商研究兴起的重要意义,也反映出资料对研究本身的重要作用,即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骨架”。
20世纪80年代,安徽师范大学张海鹏教授以敏锐的学术眼光,组建团队,当时为明清史研究室,后一度改称徽商研究中心、徽学研究所,现为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师范大学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作出了開展徽商研究的重要决策。他率领安徽师范大学徽商研究团队“从积累资料做起”[3],“利用两次的寒暑假,北上合肥、北京,南下徽州各县,遍访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科研单位,访求珍藏,广搜博采,埋首于史籍、方志、谱牒、笔记、小说、文集、契约、文书、碑刻、档案之中,爬梳剔抉,索隐钩沉,抄录了百余万字的资料,涉猎各类书籍共230余种,其中徽州各姓的宗谱、家规近百种”[4],并在此基础上于1985年出版了“迄今为止徽商研究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原始资料汇编”[5]426——《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张海鹏在该书前言中写道:
大家在实际工作中都深感研究徽商所遇到的一个困难问题,就是材料比较分散。有的学者为了研究一个问题,只得穷年累月,东搜西索,披览摘抄;一些外国学者则是要远涉重洋,其劳神费力更可想见。值此“徽州学热”在国内外刚刚兴起之际,我们想,如能把分散的有关徽商资料进行摘录,汇集成编,这对大家的研究工作多少可以提供一点方便。为此,我们集研究室全体同人之力,并借“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在最近几年中,利用教学之余,冒寒暑,舍昼夜,到有关图书馆、博物馆、科研单位以及徽州各地,访求珍藏,广搜博采,从史籍、方志、谱牒、笔记、小说、文集、契约、文书、碑刻、档案中,进行爬梳剔取,初步摘录近四十万言,编辑成册,定名为《明清徽商资料选编》。[6]23
这段话既表明了该书的“资料”来源,也表达了作者编纂该书的目的。事实证明,这本书极大地方便了徽学乃至经济史、商业史的研究者。以此为基础,徽商研究迅速升温,国内外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成果不断涌现。故而,叶显恩称赞该书“极大地推进了国内外的徽学研究”[7]29。
以张海鹏为首的安徽师范大學徽商研究团队正是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出了《徽商研究》[8]。“这部近55万言的徽商研究专著……对驰骋明清商业舞台数百年的徽州商帮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研究,是徽商研究中的一部创新性著作”[5]432。《徽商研究》的成功可以说正是奠基于《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叶显恩就说这两部著作“是徽商研究的里程碑。前者是一项重大的徽商研究的基础工程,后者则是一部有丰富创获的研究成果。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29这两部书的巨大学术影响进一步凸显了新资料对徽商研究的重要意义,也反映出安徽师范大学徽学研究团队重视新资料搜集整理的优良传统。
当前,徽商研究主要依据正史、文集、笔记、小说中的相关资料,同时重视利用徽州“数以万计的文书、数以千计的家谱和数以百计的方志”,并已取得丰硕成果。然而正史、文集、笔记、小说皆成于封建文人之手,有时与事实“失之毫厘”甚至“谬以千里”;方志、家谱往往扬善隐恶,需要研究者“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去处理这些材料,必须于字里行间发现史料的真正意义,还给他们真正的面目”[9],常常费力费时;文书则往往较为分散,归户性强的文书并不多见,整理起来也颇为不易。此外,无论是正史、文集、笔记、小说,还是方志、家谱、文书中的记载,所反映的大都是徽商个体的活动情况,对徽商群体缺乏整体性观照。由此,目前的徽商研究大多是在对大量个体徽商资料进行归纳的基础上,再得出关于徽商这一商帮群体的整体影像。这种研究固然有其必要性和可取之处,但必然会影响到我们对徽商群体及商帮组织活动的整体而细致地把握。
此外,正如一位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商人的研究,大体上属于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但是,经济史的研究较多关注商人的资本来源、经营品种、经营方式、经营地域,往往使用统计学的方法,得出符合历史面貌的认识和结论。对于商人的文化性格,一般停留在他们是否“诚信”的道德层面,面对商人的心灵却很少关注。因此,在历史学者的笔下,商人只是商人,是抽象的商人,而不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普通人。[10]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非是历史学者不愿意关注有血有肉的商人,传统史料对商人记载过于抽象当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传统时代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商人描写,这就为古代文学研究者对商人丰满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这些素材对历史学者而言却只能作为旁证,而难以作为真正史料对待或全部的史实来源。这种“苦恼”却是古代文学研究者所难以理解的。因此,要想让历史学者笔下的徽商有血有肉,对富有生活气息的徽商资料的发掘整理就显得尤为必要。
2005年始,安徽师范大学徽学研究团队再次奔赴上海、北京、南京、江西婺源及安徽合肥、黄山、宣城等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复印和手抄了大量未曾面世的由徽商创建或参与建设的会馆、公所的征信录文献,经过整理、标点,最终汇集资料达到180余万字。这类会馆公所类征信录资料不同于正史、文集、笔记、小说和方志、家谱、文书,它更多地反映了徽商群体及商帮组织的活动情况,以及在建设、经营这些会馆、公所等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具体、生动、富有生活气息的徽商形象。通过对这些资料进行解读,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徽商这一群体的整体性活动场景,而不再是一个个个体徽商影子的叠加;还可以更加直观地观察到有血有肉的徽商,而不只是抽象的徽商。从这个意义上说,徽商会馆公所类征信录文献的大量发掘、整理和利用,必将推动徽商研究再出发。
二
会馆、公所是旅外同乡所建立的方便客籍人士“行旅栖止”的公共建筑,更是联乡谊、谋事务、办慈善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从现有资料来看,会馆、公所的共同点多于不同点。其共同点表现在,它们在名称上往往是相通的,都是地域性的社会组织,功能性质也几乎相同;如果非要说不同点的话,公所“同业”的色彩相对来说要浓一些,其近代性也更强。
明清时期,徽商足迹几遍天下,重视乡谊和族谊的徽商,在其侨寓集中之地多建有会馆或公所。特别是南北两京、苏浙、湖广、江右,既是徽商辐辏之地,也是徽商会馆公所集中之区。诚如清人所言:“凡商务繁盛之区,商旅辐辏之地,会馆、公所莫不林立。”《旅常洪都木商创建公所碑记》,常州市木材公司编:《常州市木材志1800-1985》,1986年,第35页。也如徽人所说:“矧吾徽六邑,士农工贾,虽曰咸备,而作客为商者为更盛,是非大丈夫,志在于四方者也。溯思前人敦仁慕义,古朴纯真,凡诸城镇无不有会馆设焉,实乃恭桑与梓之义。”光绪《新安怀仁堂征信录·同治六年分募簿启》。据陈联统计,清代的徽商会馆在百所以上。[11]
会馆、公所和义庄、义园、义阡、殡所等善堂、善会组织是“孪生兄妹”。明隆庆三年(1569)江西抚州推官黄愿素曾说:“今天下一统,歙人辐辏都下,以千万计。嘉靖辛酉年,既捐赀创会馆,以联属之矣。又念邑人贫而病卒,而莫能归榇也,相与为义阡之举,以为瘞旅之所。”道光《重续歙县会馆录·节录义庄原编记序》。前者主要是客籍同乡生者的“联属”之地,后者主要是客籍同乡死者的“瘞旅之所”,践行的是“敦睦之谊,冥明一体,生有所养,死有所葬”光绪《京都绩溪馆录》卷四《会馆建修缘起·绩溪义园记》。的理念。所以,或先有会馆、公所,再建义庄、义园、义阡、殡所等善堂、善会,如上述京都歙县会馆;或先有义庄、义园、义阡、殡所等善堂、善会,再建会馆、公所,如京都绩溪会馆,就是“由于先有义地,故同乡得以岁时会集谋复建馆耳”。据《绩溪义冢碑记》载:“乾隆丁巳,同乡诸耆长构地,立绩溪义冢于三义庵,岁时会集省奠。事各就绪,乃谋复建会馆,众议咸协,于壬戌春展墓之次再申前议,遂捐输得数百金,立今会馆。”光绪《京都绩溪馆录》卷四《会馆建修缘起·绩溪义冢碑记》。正因如此,徽商在客籍地所建的善堂、善会亦称会馆,如浙江杭州塘栖镇的新安怀仁堂义所也称“新安会馆”,据史料载:“兹据新安会馆司董蔡子香、洪浩然等禀称:窃生等籍隶安徽,向在塘栖生理者,或有病故之后,其棺木一时未能回里,不免风霜雨雪,殊属堪怜,是以择在塘栖水北德邑该管地方,设立新安会馆,停泊棺木,又在南山设立义冢,掩埋寄存未能归里棺木。”光绪《新安怀仁堂征信录·钦加六品衔、署杭州府仁和县塘栖临平分司陈为晓谕事》。徽商在客籍地所建的这类与会馆功能相辅相成的善堂、善会很多。正是基于这种联系,我们把徽商善堂、善会征信录纳入到了本汇编中。
此外,“清末民初在同乡组织的发展史上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便是同乡会的兴起”[12]。而许多同乡会就是在会馆公所基础上改组而成,如汉口徽商所建新安六邑同乡会即是在徽州会馆基础上改建;民国十二年(1923)由歙县商人建立的歙县旅沪同乡会也是在歙县会馆基础上改建。考虑到徽商所创建的同乡会与会馆之间的延续性,本汇编也收录了两种徽商同乡会资料。
关于徽商会馆公所征信录类文献留存情况的专题性研究或统计尚未及见。但从徽商会馆公所及善堂善会的数量或可推知,这类文献的实际数量当非常可观,留存下来的也应该为数不少。只不过因分藏在各地公、私之手,我们暂时无法准确统计。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徽商会馆公所类征信录有50余种,能够看到的约30种;收入本汇编22种,再加2种同乡会资料,共24种。现将收入本汇编的22种征信录类文献按编排顺序简略介绍如下:
《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又名《紫阳书院志略》,清董桂敷编,嘉庆十一年(1806)刻本。除卷首外,凡图说、道统、建置、祟祀、学规、禋产、艺文、杂志八卷。汉口紫阳书院是书院和会馆的联合体。嘉庆时的翰林院庶吉士、婺源人董桂敷在《汉口重修新安书院碑记》中说:“余维书院之建,一举而三善备焉:尊先贤以明道,立讲舍以劝学,会桑梓以联情。”嘉庆《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卷七《艺文·汉口重新新安书院碑记》。“会桑梓以联情”,就是指汉口紫阳书院所具有的商人会馆的功能,说明它也是徽商在汉口“敦睦桑梓,声应气求”的联络、计议之所。嘉庆时,时任湖北汉阳知府的徽州人赵玉在《紫阳书院志略序》中说:“盖尝论之,名省之会馆遍天下,此之书院即会馆也,而有异焉。崇祀者道学之宗主,而不惑于释道之无稽;参赞之源流,而不堕于利名之术数。入学有师、育婴有堂、宴射有圃、御藻有楼、藏书有阁,祭仪本家礼、御灾有水龙、通津有义渡,宾至如归、教其不如、恤其不足,皆他处会馆之所无,即有亦不全者。而后知创始诸君之功不朽也。”嘉庆《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卷七《艺文·紫阳书院志略序》。
《重续歙县会馆录》。明徐世宁、杨熷续录,清徐光文、徐上镛重录,道光十四年(1834)刊本。是录分会馆录与义庄录两部,每部又分为前集、后集、新集三种,记述了自明嘉靖至清道光间会馆、义庄之缘起、兴革、规章、碑记及历年乡会试邑人中式题名,捐输商号名称等。潘世恩在《重续歙县会馆录序》中说:“吾歙会馆原录作于前明徐月洲先生,名曰《歙县会馆录》,而义庄统焉。自乾隆乙未,其裔孙杏池先生续之,乃析会馆、义庄为二编,而分载原录于其前,曰《续修录》。迄今六十年,锓板久失,而事之当增载者又日益多,编校之任,诚后贤之责矣。蓉舫驾部,月洲先生之八世孙也,慨然思所以继其先志者,爰仍旧录之例,录自乾隆四十一年以后者为新集。于是此数十年中,凡馆舍之圮而再新,经费之绌而渐裕,地亩之侵而复归,规条之议而加密者,咸有稽考。既成,将合旧录梓之,名曰《重续歙县会馆录》。”
《(黟县)登善集》。清道光(1821-1850)刻本,不分卷。“登善集”是徽商在徽州本土设立的由“杭郡惟善堂载回旅榇暂停之所”,是杭州新安惟善堂的中转机构,“各邑并于邑界水口登岸处设登山集,集有司事如堂”。胡敬:《新安惟善堂前刊征信录序》,光绪七年《新安惟善堂征信全录》。“登善集”之名,典出《国语·周语》“从善如登”四字。是集记载有记、募启、公呈、告示、章程、买契、输契、税票、捐输等内容。
《陕省安徽会馆录》。清胡肇智辑录,方延禧校雠,同治六年(1867)刻本。除前序、会馆全图、后跋外,正文凡五卷。歙县人方鼎录在《陕西安徽会馆录序》中说:“馆建于嘉庆庚辰,迄于今四十有八年矣。昨岁丙寅,乡人复加修葺,焕然一新。适胡季舲先生秉臬关中,更与乡人谋著为录,以志既往而昭将来。首列图,其规模可见也;次列公启、碑记,其缘可知也;次列条规,敬将事也;次列醵资姓氏,旌众力也;次列兴作所用房劵、地契,備考核也;次列义地、条约,所以妥旅魂而期遵守。秩然有叙,灿然不紊。”馆录的辑录者胡肇智、校雠者方鼎录和方延禧均为徽州人,故将此馆录收入本汇编中。
《新安怀仁堂征信录》。清光绪(1875-1908)刊本,不分卷。新安怀仁堂是徽商在浙江杭州塘栖镇设立的会馆善堂,停放一时未能回里的徽人棺木,或掩埋、寄存无法归里的棺木。该征信录记载了新安怀仁堂义所的缘起、地方政府的批文、堂规,以及募捐经费和收支账目等。
《闽省安徽会馆全录》。清光绪四年(1878)刊本,不分卷。闽省安徽会馆创建于清同治元年(1862),倡始者为桂丹盟廉访潘茂如观察等皖籍官员。《闽省安徽会馆全录序》云:“安徽会馆之在福州者,桂丹盟廉访潘茂如观察曩营于九彩园,余赀则于北郭马鞍山置义地,十四年于兹矣。岁丙子,观察以馆舍尚狭,议移爽垲□城南梅枝里旧筑而扩之,既亲董其役,唐俊侯军门复任巨赀为负畚先,越明年落成。……溯江淮三千里间固有息息相通者,宜足抒桑梓之恭且志萍蓬之聚也。于是考祀义庐馆约及义地之应补葺者,都为一录。”
《京都绩溪馆录》。清道光十一年(1831)由经理、协理诸人公同订定、校录、付梓,清光绪间(1875-1908)附刻。前有会馆、义园图各一,正文共分六卷,前四卷为道光十一年刻印,后二卷是光绪间增刻的。馆录记载有规条、捐输名氏、契据、会馆建修缘起、筹添来京试费缘起、辛卯后历年添造房屋各账等内容。
《新安惟善堂征信全录》三种。一为清光绪七年(1881)刊,一为十七年刊,一为二十九年刊,皆不分卷。三种征信录详细记载了位于杭州城外海月桥桃花山麓的新安惟善堂创建、扩建、重建的过程,以及从嘉庆年间到光绪二十七年的置产、募捐和收支等情况。
《(武汉)新安笃谊堂》。清光绪十三年(1887)续刊,不分卷。是录记载了笃谊堂的缘起、条规及同治、光绪年间的捐输和收支账目。笃谊堂位于汉阳,是汉口新安书院附设之善堂。
《嘉庆朝我徽郡在六安创建会馆兴讼底稿》。清光绪十七年(1891)汪家麒手录本,不分卷。嘉庆十四年(1809)、十五年间,在六安经营的徽商拟在州治东北儒林岗下创建会馆,“为驻足之地”,而六安地方士绅以“擅自创建,妄行掘挖,伤害来龙……添盖楼台,欺压形势,致害合学风水”为由进行阻挠,以致兴讼。底稿详细记录了双方历时两年的兴讼过程。阅此,可知徽商在侨寓地兴建会馆以及商业经营之不易。
《新安会馆收捐清册》。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刻本,不分卷。新安会馆创建于光绪二十年,是由寓居南京的“茶商及杂货商号、漆铺各业解囊佽助”修建而成。清册除前面插刊光绪二十一年《新安会馆公启》外,主要记载了光绪十九年十月至二十年新安会馆经收的茶商、漆商和药材商的捐款情况。
《新安屯溪公济局征信录》。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本,不分卷。是录记载了屯溪公济局的创办缘起、条规章程、置产助地,以及光绪二十八年的收支账目。屯溪公济局创议于光绪十五年,是一个“仿各善堂成规”,为前来屯溪镇觅衣食的“四方穷民”送诊送药、送棺送葬的慈善机构,经费主要由“茶业各商慨然乐助”。光绪十八年又附设保婴所和养疴所,慈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后因“茶商续捐已成弩末”,又通过官府征收木捐“赖以济用”。
《歙县馆录》。即歙县试馆录。清歙县汪廷栋编,光绪三十年(1904)木活字本,不分卷。汪廷栋在《歙县馆录弁言》中说:“馆录者,吾邑汪聘卿学正创试馆时所手订也……光绪癸卯春,予重到金陵……次年二月,同人有厘订之议,佥以责属予,予不敢违,爰理其旧绪,订以新章,分为五录,曰契据录、公牍录,循其旧也,曰碑记录、馆规录、收支录,补其阙也。”试馆坐落于南京江宁县治石坝街,“为吾邑乡试士子而设”。
《九江新安笃谊堂征信录》。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刊本,不分卷。是录记载了九江新安笃谊堂的缘起、条规及捐输和收支账目。该堂创建于光绪二十九年,“仿汉阳新安笃谊堂停柩送榇章程,就地建造殡所义园,为徽属逝者寄厝之地。”《九江新安笃谊堂征信录·笃谊堂落成,首士绘图粘契请县盖印词》,光绪三十二年刊本。
《重建新安会馆征信录》。清汪廷栋等编辑,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本,不分卷。该征信录之内容、结构与《歙县馆录》几同,除前叙、后跋外,正文分公牍录、图说录、碑记录、馆规录、器具录和收支录。汪廷栋在《碑记录》中说:“金陵马府街旧有新安会馆,毁于兵,四十年未能兴复。光绪甲辰夏,予因公过其地,惜之,爰集同乡公议重建。本处人少力薄,又借助于他山,幸赖各埠同乡咸念桑梓,解囊相助。经始于甲辰十月,初竣工于乙巳腊月。”
《徽商公所征信录》。清宣统元年(1909)刊本,不分卷。这里的“徽商公所”又称“徽国文公祠”,是由旅居杭州的徽州木商于清乾隆年间创建。咸同兵燹“公所被焚”,宣统时得以重建。之所以要编征信录,是因“公所向无征信录,人多疑之。今将紧要底据及每年收支逐笔刊明,条分缕晰,俾后继者率由旧章,永维公益,是则木商之大幸也已。”
《思义堂征信录》。清金文藻辑撰,宣统三年(1911)石印本,不分卷。思义堂是徽商于嘉庆十八年(1813)在南汇县新场镇东南三十六都建立的善堂,“凡徽籍之物故于此,无力扶榇者代为埋葬,有力之棺寄停堂中以待回籍搬迁。”光绪十一年六月《安徽思义堂公牍》,清金文藻:《思义堂征信录》,宣統三年石印本。咸丰十一年(1861)堂在战乱中“遭毁圮”,“同治纪元,诸同仁又踊跃输将,集捐万缗,重建堂宇。”宣统三年六月《思义堂刊征信录启》,清金文藻:《思义堂征信录》,宣统三年石印本。因“斯堂重建已后,费用浩繁,皆出同乡善姓捐助,尚未刊行征信”,所以经理者“将光绪十三年至宣统二年逐年收支账籍汇列成册,镌印征信录,禀呈钧座,分送同乡,以示大信而昭慎重”。宣统三年六月《思义堂刊征信录启》,清金文藻:《思义堂征信录》,宣统三年石印本。
《徽宁医治寄宿所征信录》。民国五年(1916)第五刻,不分卷。是录记载了徽宁医治寄宿所开办缘起、经过、简章规则、总理协理、乐输芳名、收支帐目,以及医治寄宿名额。该医治寄宿所是徽州、宁国两府绅商在上海设立的专为两府贫苦病人医治寄宿的慈善机构,宣统元年(1909)动议,二年始建,三年落成。
《徽宁思恭堂征信录》。民国九年(1920)第四拾刻,不分卷。徽宁思恭堂又称徽宁会馆,是徽州、宁国两府绅商于乾隆十九年(1754)在上海城南设立的善堂机构。此征信录即是“徽宁两郡人作客是邑,置办义冢、公所册籍也”。
《新安思安堂征信录》。黟县旅休同乡会编,民国九年(1920)第一刻,不分卷。该录记载了思安堂的建立经过、董事姓名、捐输芳名及收支账目。思安堂是旅居上海、休宁的黟县籍绅商于民国六年在休宁县十六都珠塘铺建设的善堂,额曰“思安”,“有丙舍以起停由沪运屯旅榇及为在屯同乡殡所,附设同乡会以为私团研究、进行慈善之会议场,至于殡厝满期,照章掩埋,则于堂之左近山麓置有义冢。”《新安思安堂征信录·休宁县公署布告》,民国九年第四十刻。
三
“馆之有录,所以纪事实、备考证也”《重续歙县会馆录·重续歙县会馆录序·徐宝善序》,道光十四年刊本。。徽商会馆公所类征信录是有关徽商会馆公所、义园善堂兴建过程、经费收支、运行机制、管理体制及相关徽商活动的原始档案材料汇编,内容可靠,史料价值高。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从整体上系统了解徽商慈善组织或机构的具体建立、运营过程,徽商的商业经营状况、商业网络,徽州绅商在建设、经营这些会馆、公所过程中与官府和当地民众的互动关系,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具体、生动、富有生活气息的徽商。因此,这批文献对商业史、慈善史、教育史、政治史、社会史等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甚至为重写徽商史乃至商帮史提供了可能。
(一)商业史价值
徽商会馆公所类征信录类文献的商业史价值,学界已有专论。具体讨论可参见王振忠:《试论清、民国时期徽州会馆征信录的史料价值》,黄浙苏主编:《会馆与地域社会:2013中国会馆保护与发展(宁波)论坛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若从整体的视角来利用这批文献,则其史料价值当更为凸显。如一些学者认为,近代以后徽商就彻底衰落了,甚至“几乎完全退出商业舞台”。但透过这批征信录我们却发现,进入近代,徽商竟掀起了大规模重建或重修会馆公所、善堂善会等商业或慈善机构的高潮。如黟县的登善集倡建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杭州塘栖镇的新安怀仁堂之重建始于同治四年(1865),西安的安徽会馆于同治五年由“乡人复加修葺,焕然一新”方鼎录:《陕西安徽会馆录序》,《陕西安徽会馆录》,同治六年刻本。,福州的安徽会馆改建于光绪三年(1876)潘骏章:《新建闽省花巷安徽会馆记》,《闽省安徽会馆全录》,光绪四年刻本。,新安屯溪公济局在光绪十五年(1889)也得到重建。其他如九江的新安笃谊堂、杭州的徽商公所、南汇的思义堂,上海的徽宁医治寄宿所、徽宁思恭堂,休宁的新安思安堂等的重建或创建,也都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在这些机构的创建过程中,徽商不只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更是最主要的经费提供者。如新安怀仁堂,“创自前人,历有年所。自咸丰庚申遭乱,其屋尽毁于兵燹,斯时露棺暴骨,行者伤之。直至同治乙丑,同人渐集,始得共助堆金,迁葬于南山之麓。爰后于会馆旧址筑垣墙、治屋宇,共造厝所十七间,外起门房七间。是时规模虽云粗具,然较之旧日,尚未得其半,而经费已有所不支矣。不意于庚午春,有同乡江君明德者运茶申江,道出栖镇,见此会馆,慨然动容,旦望此工程浩大,倘非多为捐助,何日得以告竣?于是查访同事,慷慨许助,曰:‘君等欲成此事,吾当为将伯。遂于茶捐内抽捐以成斯善举。”《新安怀仁堂征信录·新安怀仁堂征信录缘起》,光绪刊本。新安屯溪公济局之重建,“所需经费非宽为筹置恐不济事,现经茶业各商慨然乐助,每箱捐钱六文,禀由茶厘总局汇收,永为定例。每年计有六百千文,即以此项为正款经费,其余酌量劝捐,随缘乐助,共襄善举。屯镇以茶业为大宗,此后遇有应办善事,即于此局公议,以归划一。”《新安屯溪公济局征信录·禀呈》,光绪二十八年刊本。可以说,近代以后,靠“茶捐内抽捐”或“茶业各商慨然乐助”,几乎成了徽商慈善机构重建或重修所需经费的最重要保障。上述事实清晰表明:一是近代以后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日趋稳定,徽商出现了一个中兴的局面,其社会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仍不容小觑,故认为近代以后徽商就彻底衰落甚至退出历史舞台的观点,并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二是中兴以后的徽商已从“首重盐业”[8]22转向“以茶为大宗”[14]475,传统的徽州盐商没落了,茶商则成为近代徽商新的中坚。
以往的徽商研究往往局限于某一特定區域,这就常常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在一地经商之徽商群体除了跟家乡保持密切联系外,跟在其他地方经商之徽商群体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通过这批征信录的记载我们却发现,不同地区经商的徽商群体之间的互动频繁。如北京徽州绅商与扬州徽商关系颇为密切,北京歙县会馆之重建更有赖扬州徽商之资助《重续歙县会馆录·续录后集·附记》,道光十四年刊本。,正如日本学者寺田隆信研究后所说:“歙县会馆从扬州盐商那里得到巨大的经济援助。”[15]再如杭州的新安惟善堂之经费来源,除收取杭州徽商的“盐业堆金”“箱茶堆金”“木业堆金”“典业堆金”“面业堆金”等各业堆金外,常州、江都、海盐、泰州、南通州、海门、枫桥、南翔、德清等各地徽商或徽州商号也都积极捐输。光绪七年《新安惟善堂征信全录·前刊·捐输名目》。金陵新安会馆在光绪三十年(1904)重建过程中,也是“幸赖各埠同乡咸念桑梓,解囊相助”,除金陵省城外,上海、南通州、扬州、东台、芜湖、汉口、九江、安庆省城的徽商或徽州商号也都积极捐助。汪廷栋等:《重建新安会馆征信录·碑记录》,光绪三十二年刻本。据此可以推论,我们对徽商商业网络、关系网络之构建乃至明清商帮之“帮”的意涵等问题仍有进一步认识或讨论之空间和必要。
(二)慈善史价值
在以往的慈善史书写中,慈善活动和机构的组织者或经营者主要是士绅,商人几乎都是以捐助者的身份出现。但这批徽商会馆公所类征信录文献打破了我们对明清慈善事业的旧有认知,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徽商不只是捐助者,也是组织者、经营者,他们所构建起的慈善事业不仅体系庞大、网络完备,而且组织严密、经营有道,可以说丝毫不逊色于士绅主导的慈善事业的发展。且相较于士绅主要是在拥有地利、人和之便的当地进行慈善活动,徽商慈善网络的建构则主要是在外地,所面对的困难和承受的风险要大得多,由此,其经验和教训也更值得借鉴。
与此同时,传统的慈善史研究或注重宏观制度层面的考察,或注重对慈善机构的个案研究,但对由不同的慈善机构所构建起来的慈善网络之关注则受制于史料,往往甚少关注或语焉不详。这批文献确为我们揭示了徽商慈善机构之网络化、系统化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并非每一个善堂善会都是独立运行的,而是与其他善堂善会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慈善链条或网络。如黟县登善集之设就是为了完成杭州新安惟善堂之后续工作,“缘徽郡之在浙省贸易间有贫苦病故而柩难归者,即寄停于徽郡之惟善堂义园中,即在堂中给以川资送柩回徽。以各邑之柩到埠时皆有义所可寄,惟黟邑柩到渔亭向无义所,必先起放于沙滩,方能告知死者之亲属来领,风雨已甚伤心,暴水尤虞漂泊。兹职等在渔亭买受汪姓渔山公共山业一片,公建义园,便于柩到即起停其中。”《(黟县)登善集·建登善集请示公呈》,道光刊本。杭州新安惟善堂的规条中也明确规定:“登善集每于船户载到之时,照依惟善堂知照册分别核收,即于通衢四镇填写各柩姓名、住址,以待亲属领回。或虽有亲属,赤贫者,准其到集报明,司事查其的实与路之远近,助给抬费;或自有山地祖坟可以附葬者,又给助葬钱二千文。此为极贫而论,不得视为常规。倘自能扛抬营葬,有意迟延、托词窘乏者,六个月尚不领回,即代葬集中公地。……嘉禾苏松等郡邑各善集将来载到旅榇,堂中专人代为照料一切,俱照杭郡之式以归一致。”光绪七年《新安惟善堂征信全录·前刊·禀呈》。二是不同地域的徽商善堂善会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如江西九江的新安笃谊堂,即“仿汉阳新安笃谊堂停柩送榇章程,就地建造殡所义园,为徽属逝者寄厝之地。”《九江新安笃谊堂征信录·笃谊堂落成首士绘图粘契请县盖印词》,光绪三十二年刊本。杭州新安惟善堂除与登善集为合作关系外,与徽商在常州所设公堂也有密切关系,其在道光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禀杭嘉湖道宪宋》所附的条例中就说:“常州公堂亦系新安众商创,捐钱五百千文,仍存公堂营运,周年一分生息,收来专为津贴旅榇载送之费,议定不准提本,以杜挪移,堂中宜勒石垂久。”光绪七年《新安惟善堂征信全录·前刊·禀呈》。综上,徽商会馆公所类征信录为我们了解明清商人与慈善事业之关系提供了丰富史料,也为我们重新认识明清慈善事业的运作实态提供了宝贵资料。
(三)教育史价值
明清商人在经商地侨寓的现象十分普遍,关于清代商人侨寓化的状况,可参见龙登高:《从客贩到侨居:传统商人经营方式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王日根:《论清代商人经营方式转换的若干趋向》,《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梁仁志等:《明清侨寓徽商子弟的教育科举问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1期。但侨寓商人子弟的教育问题却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究其原因,史料缺乏当是主要障碍。为解决侨寓徽商子弟的教育问题,徽商会馆常常附设书院、义学等。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紫阳书院。它既是崇祀朱熹之祭祀机构,也具有一般书院的教育功能。如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两浙都转运盐使高熊征为方便侨寓杭州的徽商子弟读书科举,遂应徽商之请建立紫阳书院。该书院在建设和维护过程中,徽商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建设及日常所需巨额费用均由侨寓杭州的徽州盐商汪鸣瑞独立承担,徽商吴琦等也每年捐银四百两以补膏火。关于徽商捐建杭州紫阳书院的动机,孙延钊认为:“大抵鹾商多来自徽郡,为朱子故乡,子弟别编商籍,得一体就近考试,即以斯书院为会文及祀朱子处。故其父兄对于院款,皆自愿输将。”[16]可谓实情。无锡也有紫阳书院,“系祖籍新安的盐商创办,从购房至经营、开课经费均由这些盐商独立完成”[17]793。本汇编所收录的《汉口紫阳书院志略》为我们了解汉口紫阳书院的建设、经营、教学以及汉口徽商子弟的教育等情况提供了丰富详实的第一手材料。具体情况可参见李琳琦:《徽商与清代汉口紫阳书院——清代商人书院的个案研究》,《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
齐如山曾说,书院“未立之初,当然或者也有官员的提倡,但大都是多数绅士的努力,所以书院的资金,都是由地方筹募,多数是由富家捐出,或把原属教官之学田,拨出若干,间乎也有官员捐的廉,总之这笔款,不归官员管理,都由绅士经手”[18]207。这就传统书院的一般情况而言大体是准确的,但徽商在侨寓地所设的商人书院却让我们看到了“不一般”的情况。如杭州紫阳书院、无锡紫阳书院之建徽商均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再如汉口紫阳书院,不仅资金主要由徽商筹募,其兴建款项乃至日常经费、教学活动的管理工作等也主要由徽商负责。可以说,在杭州、无锡、汉口等紫阳书院的创建和经营过程中,徽商已取代士绅而成为了真正的主导者。由此可见,《汉口紫阳书院志略》等也为我们认识传统书院以及教育的“另类”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本汇编收录的《旅溧新安同乡会简章》中有这样一条规定:“会员权利……本会将来设立旅溧公学,会员子弟或本身有享受免费之权利。”徽商同乡会组织公学之设当是徽商会馆设立书院、义学等传统的延续。这条材料为我们思考后会馆时代侨寓徽商子弟的教育问题和同乡组织与教育之关系问题提供了启示。
(四)政治史价值
商人与政治的关系,是传统商帮史或政治史研究中均无可回避的重要论题。徽商会馆公所类征信录类文献则为我们讨论这些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通过检阅这些文献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一是无论会馆公所还是善堂善会等机构的设立,都必须得到地方官府的认可和支持。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在创建伊始都必须向各级政府逐级呈送禀文进行备案,有的还同时请求政府给予示禁保护。通过呈请地方政府“发给执照,以凭管业”和对一些可能会出现的不法行为提前“出示晓谕,严行禁止”,就为这些机构的建设、后续管理和正常运作取得了合法性,并扫清了各种障碍或隐患。
二是当这些机构的利益遭受侵害时,通常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予以解决。如位于南汇县的新安思义堂“寄棺被刨”,堂内执事就连续向南汇县令祁呈文请求严缉究办。在光绪十一年六月初四日的呈文中提出:“现由职等报知各家属查明殓物,另外开呈外,事关公所寄停棺柩刨窃多具,为开棺柩细号清单赴案呈报。伏乞公祖大人电鉴,俯赐勘缉,获犯严究。”随后又在七月二十三日呈文中继续给官府施加压力:“现在各家属以报案多时,日久更难破获,屡来堂中问信,不得不再备情投叩。伏乞公祖大人恩赐,再刻严比勒限,缉获赃贼,按律究办,以肃法纪而靖地方。”金文藻:《思义堂征信录·安徽思义堂公牍》,宣统三年石印本。
三是徽商常常依靠徽州籍官员的力量来维护徽商群体的利益。如旅汉徽商在与汉口土著就汉口紫阳书院建设发生的争讼中,第一次能够取胜,乃因徽州仕宦在朝者势力强大,“共为排解”董桂敷:《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卷八《杂志·书牍·上姚太史书》,嘉庆十一年刻本。之缘故;发生在雍正初年的第二次大规模诉讼能够反败为胜,则因“雍正甲寅(1734),以文公之灵,天假湖南观察许公登瀛,考绩鄂城,爰斋沐、过汉江,瞻谒书院,毅然以成就钜举为己任。”登瀛乃徽商子弟,在他的周旋下,湖北巡抚杨馝“饬观察邗江朱公氵雷,廉得其实,追浮冒,归还祠屋,事始明而祀费有助”。董桂敷:《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卷三《建置·纪书院本末》。而事实上,徽商无论是建设会馆公所,还是善堂善会,从一开始都会主动与当地的徽州籍官员合作谋划,以寻求他们的支持,这些徽州籍官员通常也会积极配合和支持徽商的行动。可以说,徽州籍官员的支持对徽商在外地的开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徽商对教育的重视和对徽州籍官员的资助也为徽州籍官员的成长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上述三点只是从宏观层面的观察,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文献还为我们从微观层面观察提供了线索。如《新安惟善堂征信全录》就记载了杭州新安惟善堂给当地官吏送礼的情况,如给地保送年规,《光绪五年支用各款总录》中载:“支钱七千文,阿宝定例年规六千文、地保定例年规一千文”;《同治四年至光绪四年支用总录》中载:“付逐年地保年规送历费,钱六千八百四十文”;同治十年后,每年都是“付地保年规送历费,钱一千一百四十文”,从未间断。其它徽商会馆公所征信录类文献中也有类似记载。
综上,徽商会馆公所类征信录为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考察传统社会徽商乃至商人群体与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非常丰富、细腻、生动的资料,具有重要的政治史价值。
(五)社会史价值
与传统史学偏好走“上层路线”不同,社会史更喜欢走“群众路线”,关注对底层民众日常的研究。徽商会馆公所类征信录文献正是社会史研究的资料宝库,因为不同于正史、方志、家谱、文集等的记载,它所记录的正是大量普通徽商具体入微的经营史、生活史、奋斗史、交往史,它所揭示的也多半是普通商人群体对社会、生活、生命等问题的基本认知。如在《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嘉庆朝我徽郡在六安创建会馆兴讼底稿》等文献中,就保存了大量反映徽商与经商地土著士民之间矛盾纠葛和诉讼的内容,为我们具体生动地了解明清时代的土客矛盾,以及徽商在外地生活、经营的艰辛提供了丰富史料。这在其他类型的文献中是很难见到的。
徽商在侨寓地建有大量的义园、殡所、善堂,并制定有详细的管理制度,“凡旅榇之至,则先告于司事,司事即遣信告于其家,予以迎柩限期。其家人有力者,任其自备资用迎归故里;力不足者,酌助之;极无力者,尽给之。期已过而其家人莫有至焉者,司事将堂中所置公地代为埋葬,仍立石识姓名,俾异时来迁移者毋贻误。”光绪七年《新安惟善堂征信全录·前刊·新安惟善堂前刊征信录序》。践行的是“奠安旅榇,矜慰游魂”“生有所养,死有所葬”以及“魂归故土”的理念,表现出徽商对死者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思考。但其背后反映的则是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正如绩溪人胡元洁在《新安惟善堂续刊征信录序》中所说:“权厝所之有举莫废而死者安,死者安而其一家之人安,家积成邑,邑积成郡,而一邑一郡之人胥安。茔之事一人任之,或数人任之,前之人任之,后之人复任之,纲举目张,无侵无旷,亦各安其所安,则心安而事无不安。”光緒二十九年《新安惟善堂征信全录·续刊序》。这就为我们从社会史的角度重新理解徽商、认识徽商提供了史料。
总之,我们希望这批资料的面世,能够嘉惠学林,切实推动徽商研究进一步发展。我们也期待着能以这批徽商会馆公所类征信录的出版为契机,实现徽商乃至中国商帮史研究视角和路径的重要革新,促进徽商研究再出发。
参考文献:
[1]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M]∥王国维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2]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中译本序言[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3):5155 .
[3]瞿林东.二十年的功力——评一个徽商研究的学术群体[N].中华读书报,20060106.
[4]王世华.张海鹏与徽学研究[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2025.
[5]卞利.20世纪徽学研究的回顾[J].徽学:第2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411446.
[6]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G].合肥:黄山书社,1985.
[7]叶显恩.张海鹏与徽学研究[C]∥王世华,李琳琦,周晓光.纪念张海鹏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暨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8]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9]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J].读书,2006(9):2130.
[10]朱万曙.商人与经济史、文化史及文学史[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103110.
[11]陈联.徽州商业文献分类及价值[J].徽学:第2 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384391.
[12]高洪兴.近代上海的同乡组织[M]∥洪泽.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上海: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
[13]李则纲.徽商述略[J].江淮论坛,1982(1):1418.
[14]刘汝骥.陶甓公牍:卷三[G]∥官箴书集成:第10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
[15]寺田隆信.关于北京歙县会馆[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1):2856.
[16]孙延钊.浙江紫阳书院掌故征存录(一)[J].浙江省通志馆馆刊,1945,(1)2:3844.
[17]李国钧,等.中国书院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18]齐如山.中国的科名[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
*本文系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徽商会馆公所征信录汇编》一书的序,发表时略有删改。
责任编辑:汪效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