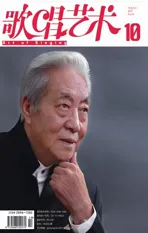融合东西,交汇南北(上)
——论施光南的艺术歌曲
2017-05-18梁茂春

2017年4月16日梁茂春在“施光南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感谢金华方面的盛情邀请,此行我和蔡良玉与大家一起参加了在金华市金东区东叶村举办的“施光南纪念馆”开馆仪式,又参观了修葺一新的“施复亮施光南故居”。今天(2017年4月16日)又参加了在新命名的浙江师范大学“施光南音乐学院”举办的“施光南学术研讨会”,这都引发了我们对当年与施光南一起学习、生活的回忆。
施光南是1957年秋(17岁)插班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理论学科的,从此我们成了同班同学。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那时,施光南、蔡良玉和我三个人的钢琴教师都是青年教师蒲以穆。蒲老师曾安排我和蔡良玉弹四手联弹,后来我们成了夫妻。蒲老师又安排我和施光南弹四手联弹,后来我们成为终生的好友,直到光南49岁时突然离世,亲密的友谊保持了30多年。这次来金华的学者、朋友中,施光南最早的同学可能就是我和蔡良玉了,我们心有荣焉。

1958年夏,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四年制”全班同学合影,后排右一为梁茂春、右三施光南,前排右三为蔡良玉
感谢上苍,让我在此生有这样一份值得珍惜的友谊;也感恩光南,他对我的帮助和影响太大太大了,不仅使我对民间音乐的兴趣有了极大的提高,甚至使我在性格、精神面貌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很得意、很自豪地写道:“我对施光南的作品非常熟悉,常常是他的作品‘首唱’的听者,首唱者就是施光南本人,而听者往往只有我一个人。他在钢琴上自弹自唱,他能够模仿男中音、男高音,还能够模仿女高音,甚至还能够唱花腔女高音,演唱轻灵流丽的花腔,是他的绝活,甚至是他的本色。”①照片4就记录了这种情况。照片拍摄于施光南的家中,他的钢琴就在旁边,他先弹唱完新歌之后,再向我介绍他的艺术构思。
我原本准备的是一篇论述施光南艺术歌曲的论文—《融合东西,交汇南北—论施光南的艺术歌曲》。现在改为边论述边回忆,以便大家可以更加具体地了解施光南艺术歌曲创作的真实情况。

1983年施光南在梁茂春家中合影
施光南一生的音乐创作涉及群众歌曲、表演唱、歌剧、舞剧、舞蹈音乐、器乐独奏、合奏等众多音乐体裁,我今天只谈其中的一种体裁—艺术歌曲。我认为艺术歌曲是施光南音乐创作的主要成就,甚至可以说是他音乐创作的核心和基础—连他的器乐作品,都有艺术歌曲的旋律内涵;他的歌剧咏叹调,都可以看作是他的艺术歌曲的精华。
他创作的艺术歌曲深刻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如《祝酒歌》《周总理,你在哪里》《在希望的田野上》等。他通过艺术歌曲来思考人生,歌唱生活,歌颂爱情。他的艺术歌曲,是我国当代音乐的一座丰碑,是中国艺术歌曲史上的一个高峰。
施光南的名字家喻户晓,是与他的艺术歌曲普遍流传有关系的。施光南是真正意义上的旋律大师,而他的旋律才能,最充分地展现在了艺术歌曲的创作上。
一、施光南艺术歌曲创作的三个阶段
先说明一下我对“艺术歌曲”的概念和限定。本文中的“艺术歌曲”,专指带有钢琴伴奏的独唱歌曲;从美学上讲,其艺术品位必须是高雅的,是歌曲艺术中的精品。施光南的艺术歌曲创作,大体上从1959年到1990年,前后三十余年,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后”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是施光南艺术歌曲创作的“初绽期”,代表作品是《革命烈士诗抄》。这是一部由六首歌曲组成的声乐套曲;是中国第一部声乐套曲,谱写于1959年至1960年,首演于1961年,乐谱于1963年由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
声乐套曲《革命烈士诗抄》写于施光南19至20岁的时候,这时他刚刚进入天津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②1959年秋,我在天津十一经路新华书店买到一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新出版,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当我在琴房里捧读这本新书的时候,施光南进来了,看到我手上的新书他非常感兴趣,拿过去就急切地翻了起来。很快,他就看到了邓中夏的《过洞庭》这首诗,当即就朗读了起来,并且对我说:“你知道吗?这首诗是邓中夏同志写给我妈妈的,妈妈在我小时候就背给我听过,因为妈妈有邓中夏同志亲笔给她写的这首诗。这本书太好了!” 他还给我解释起《过洞庭》的诗句,也使我对《过洞庭》这首诗有了较深刻和具体的理解。
真没有想到,当时我只是随意买了这一本诗集,却引起了施光南这么强烈的兴趣和共鸣。我马上把书借给他,不久后,他自己也买了一本,并开始构思这部声乐套曲。他从《革命烈士诗抄》中选出了六位烈士写的六首诗,分别是:邓中夏的《过洞庭》,彭湃的《田仔骂田公》,叶挺的《囚歌》,杨超的《就义诗》,刘绍南的《壮烈歌》,瞿秋白的《赤潮曲》。施光南精心地为这些烈士的诗词谱写了旋律和钢琴伴奏,组成了一部结构严谨的声乐套曲,这成了施光南的成名作之一。整部作品内容上非常革命化,符合当时重视革命传统的时代潮流。

《革命烈士诗抄》乐谱封面
这部作品于1961年夏在北京文联礼堂,由全国音协举办的“新人新作演唱会”上首演,首唱者是天津音乐学院声乐系学生石惟正(男中音)。当时我正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学习,施光南约我一起欣赏了这部作品的首演。之后,他又请我到他位于北京后圆恩寺的家中,在钢琴上从头至尾给我弹唱了全部六首作品,并讲解了他的艺术构思。他说:“这六首歌曲,概括了革命烈士一生的经历—从宣传革命、参加实际斗争到狱中抗争,直到英勇就义,最后是歌颂光辉的革命理想。”
《革命烈士诗抄》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当时我曾写了一首诗《一腔热血化宫商—听声乐套曲〈革命烈士诗抄〉》来表达我对这部声乐套曲的听后感。③
第二阶段是“文革”十年,这是施光南艺术歌曲创作的“压抑期”,代表作品是《打起手鼓唱起歌》《马铃声声响》和《马蹄敲鼓我唱歌》等。这些歌曲,采用欢快活泼的旋律和清新跳动的节奏,暗中“对抗”“文革”时期极其枯燥的斗争音乐,表现出一位正直的音乐家的艺术良心。
说这是艺术歌曲的“压抑期”,第一,是由于“文革”时期只提倡战斗风格的音乐,排斥一切抒发个人情感的歌声,在宣扬“打”和“杀”的“斗争哲学”和“暴力美学”的驱动下,音乐只留下了“高快硬响”一种风格,艺术歌曲体裁受到了全面的压抑。第二,由于施光南在这一时期谱写了《打起手鼓唱起歌》等不同于“高快硬响”风格的歌曲,被当时音乐界的领导人批判为“资产阶级创作倾向”“形式主义创作方法”“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④音乐界的掌权者下令封杀施光南的所有作品:不准出版,不能广播,不让传播(即“三不政策”),甚至将施光南本人下放到农村、油田进行劳动改造,剥夺了他的创作权利多年。
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施光南的歌曲,包括他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和不久后谱写的《马铃声声响》等,在“三不政策”的严厉压制和监控下,竟仍能“不胫而走”,传唱全国。
施光南的《打起手鼓唱起歌》等艺术歌曲,在“文革”的乱世乐坛中独树一帜。这使我想起鲁迅在评论晚唐时期陆龟蒙、皮日休等人的小品文时所说,“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⑤。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这是施光南艺术歌曲的“喷发期”。从1976年开始直到他去世,前后有十多年。“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施光南被压抑多年的创作激情一下子奔腾起来,如《祝酒歌》《周总理,你在哪里》《在希望的田野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多情的土地》等艺术歌曲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地涌现出来,将他的艺术歌曲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

之后,他谱写了大量歌剧中的咏叹调,如《伤逝》中的《不幸的人生》《风萧瑟》《冬天来了》等,《屈原》中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山鬼之歌》《离别之歌》等。
这一时期的作品,是施光南艺术歌曲创作中的最高成就,是他艺术歌曲中最具生命光彩的一部分。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中国艺术歌曲的施光南时代”。
二、指向人心的神奇旋律
一条优美的旋律,并不是想写就能够写出来的。许多时候,努力、苦干、搜索枯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后,或许都无济于事。旋律的成功率太奇妙了,与刻苦和努力无法成正比。这里有太多的偶然和玄秘的因素,有许多不可人为控制的缘分。
当然,谱写好的旋律需要刻苦和努力,但更需要的是天才和缘分。施光南就是这样一位谱写旋律的高人,他的旋律才能是天生的。对于他来说,谱写旋律不是一件需要煞费苦心的事,随便哼哼一下,一条精妙的旋律就出来了,似乎旋律女神会经常眷顾施光南。
施光南始终坚信一条音乐创作的铁律:旋律是音乐的灵魂。他认为,“特别对于普及性最强的歌曲形式来说,更是如此。一般人接受一支歌曲的第一印象,首先就是:旋律好听不好听!”⑥他说过:“我的美学观点,就是强调音乐作品的旋律。”他毕生的奋斗目的就是创作出美的旋律。
施光南的艺术歌曲以直指人心的神奇旋律最为动人,最为“勾心”。就艺术歌曲旋律创作方面的成就而言,毫无疑义,他可以被称为“当代旋律大师”。我没有能力从“旋律学”的理论上论述施光南的旋律创作的高度成就,我只能从传播的角度,通过一些例证,来谈谈什么样的旋律才是出类拔萃的旋律。
例证之一。施光南在学生时代谱写的声乐套曲《革命烈士诗抄》中的第二首《田仔骂田公》,是为彭湃烈士的诗谱曲的。20世纪20年代彭湃在故乡广东海丰领导农民运动的时候,曾经根据当地的“敲板歌”形式填词创作了一首《田仔骂田公》(当地方言中,“田仔”即贫农,“田公”即地主),通过教农民大众歌唱方式,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经过了数十年的历史风雨,当年《田仔骂田公》的曲谱已经荡然无存。施光南在创作时,根据广东民歌的风格特点重新为《田仔骂田公》谱上了旋律。歌声中的“冬冬冬”是模仿鼓声,接以羽调式的民歌化旋律,模写了“大革命”时代贫农骂地主的吼声。钢琴部分双手都是“空八度”的伴奏织体,偶尔采用四度叠置的不协和音响,也是对“鼓声”的模仿。伴奏和歌声形成复调对置的关系,有分有合,非常灵活,手法简单而效果生动。
这部套曲在首演之后,遂传唱各地。不久后,“文革”爆发了,彭湃等革命烈士都受到了无端的怀疑和冲击,声乐套曲《革命烈士诗抄》也因受到牵连而销声匿迹了。
我要说的事情是,“文革”结束后不久的1978年12月初,我和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史教研室的徐士家老师一起到广东海丰地区收集革命音乐史料。当时,曾碰到当地不少群众用海丰方言唱施光南写的《田仔骂田公》给我们听,原来施光南的作品已像民歌一样在群众中流传了,甚至被误当成“革命历史民歌”。这说明施光南在对民族民间音乐的学习、掌握上确实下了很深的功夫,这使他创作的旋律能够像民歌一样众口传唱。
例证之二。“文革”中期,1972年7月,施光南在北京完成了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并送到中央乐团的女中音歌唱家罗天婵那里,罗天婵亦非常喜欢。当年国庆节期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首播了罗天婵首唱的《打起手鼓唱起歌》,此后立即红遍全国,受到众多歌唱家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时我在天津的一场音乐会上,就听到三位不同的歌唱家先后演唱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可见,这首歌曲确实是受到许多歌唱家和听众的真心喜爱,其欢乐、轻快的旋律,太触动人心了!《打起手鼓唱起歌》的曲式是二段体结构,它的整个副歌部分的唱词全部是衬词“”,旋律充分突出了维吾尔族手鼓的节奏型,抒发了欢快、热烈的情绪。钢琴伴奏部分,则是各种手鼓节奏的综合、串联。这与当时单调、枯燥的“文革”歌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感觉耳目一新。
然而好景不长《,打起手鼓唱起歌》风风火火地在全国传唱了几个月之后,从1973年3月开始,这首歌就受到了当时国务院文化组领导人的批判,给此歌定的罪名有:“此歌模仿德国歌剧《自由射手》”“‘’是形式主义”“一些人成群结队在大街上唱,怪腔怪调的”。
“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打起手鼓唱起歌》才重又广泛传唱,一直到现在,仍是受到广大听众喜爱的歌曲。这说明能够扎根在歌唱家和民众心里的旋律,一定是好的旋律。
例证之三。正在《打起手鼓唱起歌》受到批判和禁唱的时候,倔强的施光南一方面采用给组织写信申诉的办法进行对抗,同时也用新的音乐创作来与之坚决斗争。1973年他又谱写了一首名为《马铃声声响》的艺术歌曲(韩伟词),一开始就用“叮叮当,叮叮当”的衬词,来模仿山间马铃的清脆音响。因为《打起手鼓唱起歌》中的衬词“”被批判为“形式主义”,而且批判还正在火头上,现在施光南又用“叮叮当”的衬词来写歌,这不是明白无误地表达对抗情绪吗?朋友们为光南担心,都劝他不要“针尖对麦芒”地硬顶。施光南却坚决地说:“‘’这样的民歌衬词怎么会是‘形式主义’?我就不信这个邪!我写‘叮叮当’,就是要出这口气儿!”
《马铃声声响》是一首反映我国西南山区赶马姑娘劳动场景的歌曲,年轻姑娘赶着马儿把物品或书信送到各个山乡,马铃声和姑娘的歌声一起传遍了村村寨寨。这是施光南在“文革”中谱写的又一首广受大众喜爱的艺术歌曲。但是当这首歌曲“出世”时,施光南的全部歌曲已经被禁止广播和出版,因此他的作品只能依靠口传和以手抄谱的形式传播。
1975年夏秋之交,我作为天津音乐学院的青年教师到内蒙古地区的“知青兵团”招生,正值边境地区的草原上在举办“那达慕”盛会,于是我去乌拉特中后旗观摩。附近的“乌兰牧骑”演出队和歌舞团都集中到草原上进行演出,甚至把钢琴也拉到了草原上。我就在那里听到了一位蒙古族女高音在钢琴伴奏下演唱《马铃声声响》。这令我感到好生奇怪,于是就去问这位演唱者:“你是从哪里得到《马铃声声响》乐谱的?”她告诉我:“是手抄来的。”她还给我展示了手抄的乐谱,还是带钢琴伴奏的谱子。
大家或许知道“文革”期间有所谓“传抄本”小说,如《第二次握手》等,现在我看到了传抄的歌曲。这使我坚信,能够靠手抄而流传的旋律,肯定是特殊的、能够活在人们心里的旋律。
例证之四。这件事就发生在昨天(2017年4月15日),在“施光南纪念馆”前的广场上,当时坐满了从北京、浙江省、金华市请来的嘉宾,周围则站满了光南的故乡东叶村的村民们,以及从附近十里八乡自发前来“迎接施光南返故乡”的乡亲们。最让我感动的时刻是在“施光南纪念馆”开馆仪式的最后,当地村民男女老少都激动地齐声高唱施光南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那歌声在广场四周此起彼伏、直冲云霄,充分表达了当代农民盼望农村兴旺发达的心情,也表达了他们对施光南深厚感情。
我深信,能够反映普通百姓内心情感的旋律,就是最美的旋律。
以上是我亲身经历的四个例子。通过这些事例,说明施光南创作歌曲的旋律大致有以下特点:1.可以像民歌一样在民间流传;2.能够深深扎根于广大歌唱家的心灵深处;3.能够不靠广播、不靠乐谱出版,真正做到“不胫而走”;4.能够深刻反映普通百姓的内心向往。
我们这一代(指“四零后”)的作曲家中,能够达到像施光南这样对民间音乐熟悉和了解,已经不多见了。关于他潜心学习、研究民间音乐的事例太多了,这里我只说一件事。有一次,光南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相信吗?我的旋律老师应该说是程砚秋。是程砚秋和其他戏曲演员高超的创腔经验启发了我,是他们的‘依字行腔’的原则指引了我,开了我的旋律创作之窍。”

2017年4月15日,在施光南纪念馆前的广场上,东叶村村民与来宾们共同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正是由于光南在民间歌曲、戏曲、说唱等方面都下过艰苦卓绝的功夫,才使他在旋律创作方面这样的得心应手,使他的旋律充满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风格特点,这样地契合中国人民的审美习惯。施光南的艺术歌曲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其丰富多彩的民族旋律显得美不胜收。中国旋律之美,语言和曲调结合之美,在施光南的艺术歌曲中被发挥到了极致。
施光南不仅喜爱和熟悉民间音乐,他更重视学习并深刻懂得中国文化的内涵。他是一位有文化涵养的作曲家,他把握住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他的艺术歌曲的生命力,就在浓郁的民族意韵之中。而施光南艺术歌曲的民族意韵,植根于他丰富多彩的民族旋律之中。施光南的艺术歌曲对于世界艺术歌曲的贡献,主要就在他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国音乐风格。
施光南对于声乐作品的“腔从词出”和“腔随字转”等中国传统理论深有体悟,他的歌曲在词曲结合方面大多是天衣无缝的。他一方面从前辈作曲家(如赵元任、黄自、聂耳、李劫夫、刘炽、唐诃、生茂等)的作品中接受了成功的经验,更多的是他从戏曲、说唱、民歌中深入学到了词与曲互为依存的道理,既不“以词害曲”,也不“以曲害词”,词与曲的相辅相成和相得益彰在他的艺术歌曲中有很多精彩的典范。(待续)选·自序》,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②中央音乐学院1958年夏搬到北京时,将部分师生留在天津并新成立了天津音乐学院。当时我们班已是附中理论学科的高三年级,也被留下,成为1959年天津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一年级的学生。
③梁茂春《一腔热血化宫商—听声乐
套曲〈革命烈士诗抄〉》,载《梁茂春音乐评论选》,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
④参看何民胜《施光南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页。
⑤详见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⑥施光南《我怎样写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