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青年的梦
2017-05-17作者雅克朗西埃编摘丁茜茜图片网络
作者_雅克•朗西埃 编摘_丁茜茜 图片_网络
底层青年的梦
作者_雅克•朗西埃 编摘_丁茜茜 图片_网络
【编者按】
无数的文学作品都描写过底层青年,一般来说这个群体的梦是从鄙视自己的过往开始的,在游刃于新世界的法则加速的,从成功者冷眼旁观他的失败时醒来的。但在雅克·朗西埃看来,底层青年的幸福并不在于实现飘渺的梦,也不在于征服社会,它在于无所作为,就在此时和此地,无视社会层级的屏障,放下就在面前的苦恼,用纯粹的感受拥抱平等,不加算计地共享这可感的一刻。

朗西埃认为,感觉的分配是那种“界定知觉模式”的东西,而这些模式则是最先使那种次序可见且可说的东西。
那天富凯和马蒂尔德来,想把外面的消息带给他,她们觉得,讲些好听的,会给他点希望,但刚说了一句,就被于连打断。
——不用烦我了,我的生活已经很理想了。你们给我讲那些麻烦事,那些现实生活的琐事,对我多少是种扰乱,让我都不能做我的梦了。人如果真的要死,他只能尽量往好处想,如果是我,我也只能用我的想法去面对。别人讲的,对我又有什么要紧?我跟别人之间,马上就再没关系了。拜托你们,别再提那些人了,有法官和律师要见,已经够我受的了。
其实,于连自己想,我的命运,好像就该是不明不白的死去。我这样的无名之辈,肯定半个月就被人们忘光了,我要是再演场好戏,也只是给人们看我犯傻……
不过奇怪的是,到了临死的时候,我竟然学会了怎么享受生活。
最后几天里,于连走上塔楼,去小平台散步,他抽的上等雪茄,还是马蒂尔德托人从荷兰寄来的,他并不知道,他每天上来的时候,其实城里都有好多人举着望远镜等着看他。他的心思落在维吉镇。他没跟富凯打听过雷纳尔夫人在那的情况,不过富凯跟他提到几次,说她康复得很快,这句话真是让他心神荡漾。

司汤达的童年经历了法国大革命
1830年,《红与黑》刚一出版,就遭到很多批评,它的人物和情节被人指责不合实际。主人公于连本是个未经世事的农家子弟,他怎么就这么快精通了世间的钻营?他本来如此年幼,怎么又显得如此老成?他如此精于计算以至于不近人情,怎么又表现出如此狂热的爱情?而以上这段转折最大的剧情,更是被人评为前后脱节。于连为了出人头地苦心经营,终于在社会上获得成功,现在却又前功尽弃。他把揭穿他的雷纳尔夫人开枪打伤,因此被逮捕候审并面临死刑指控。然而,死到临头的时候,被关到了监狱里面,他却学会了享受生活。他以前惯于想方设法摆平事端,现在却连外边人们怎么说的都懒得去管。甚至后来,他被定罪之后,他还对雷纳尔夫人说过这样一句:在监狱里有她陪伴的几天,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间。
所以说,底层青年于连被关进监狱却懂得了享受,这破坏了司汤达这部小说的整体结构和氛围。司汤达写这本书,本来是要在他冷眼旁观的叙述中,写出那些人物追求感情、热衷梦想的故事。司汤达的这种写作风格,有这样两个源头,一是他喜欢钻研的古意大利编年史纪事,一是他盛赞的英国小说《汤姆•琼斯》(Tom Jones)里行侠仗义的故事,在《红与黑》里他还借用了其中一些场面和人物:爬梯进窗的冒险见面,藏身衣柜的惊险时刻,事发突然的分手告别,结识女仆又再度相遇,优柔寡断的贵族青年,老谋深算的阴险人物,天性浪漫、唯独钟情于有教养男青年的少女。这样看来,它其实属于以前的一种浪漫作品,这种故事,讲的是一个人物怎么经历与他本来身份无关的意外事件,怎么接触不同的社会环境,比如他可以讲这个人物从出入王侯的宫殿,到流落在一处小屋避难,也可以讲这个人物从在家务农、在乡下做神父、直到混进权贵和资产阶级的沙龙。比如,在以前的小说里,汤姆•琼斯这个弃儿的经历,还有法国作家马里沃所写的《农民暴发户》(Marivaux,Le Paysan parvenu),都反映出这种社会阶层的变动,但法国大革命之后,这种情况又有了一层新的含义。现在底层人能闯到社会的上层,他靠的是这个社会还没有找到新的基础,这个社会里既有贵族阶层的恋旧、教会内部的倾轧,也有了资产阶级的利欲。
司汤达的童年正赶上大革命的热潮,年轻时经历了拿破仑发动的战争,后来又见识到复辟时的权力斗争。他的这些经历,正好可以写进这个底层青年闯荡社会的故事。所以司汤达在这部小说里,为了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为了刻画出革命时期和帝国时期之后的这个尽是权争的社会,他就给主人公于连安排了一群精于此道的人物:其中有俄国的贵族,精通外交手腕,教他求爱之道;有詹森派的神父,教他防备教会内的阴谋;有意大利的谋士,掌握着国家的机密;也有巴黎的院士,通晓贵族家的秘闻。不过司汤达写这些细节,并不是教人怎样去谋取神职或者权位,他写极右派的密谋,并不是想恢复以前的秩序,他写于连按人授意寄出53封情书,也不是让人这样去博取忠贞不渝的爱情。
那么要理解这部小说的意义,我们可以参考文论家奥尔巴赫的一句评论,他把这部小说看成浪漫现实主义创作史上的关键之作:“现代以来,在真实可信的现实主义作品中,人物所处的环境是一个持续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司汤达是最早创作这类作品的人。”奥尔巴赫的这句评论,正好也能形容《红与黑》 出版前后环境的剧变。在它出版的1830年,巴黎人民只用了三天时间就赶跑了波旁王朝的新国王。又两年后,巴尔扎克在他初获名声的作品《驴皮记》里,写到老泰伊番举办大型宴会招待新闻记者,这个资产阶级控制舆论制造权威的场面,正像是《红与黑》中权贵间和教会内的谋权斗争。所以说,司汤达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不断变动的环境中,写出这个底层青年想要征服整个社会的故事,他的这部作品位于小说体裁之始,有着重要的意义。

《红与黑》写到社会各个群体典型人物的种种算计,文盲木匠盼望多挣点钱,代理教主想要升为正职,贵族少女向往浪漫的奇遇。
此外,当时很多评论说书面临终结,因为作家接触和认识到的世界已经被整个逆转。七月革命的爆发,确实让社会不同于以前那个小说刚获新生的社会,底层青年闯荡社会的故事也显得现实社会有些脱节,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历史在此真正的变化,是它不再要求作品的结构、人物的思想必须应对各种社会力量的发展变化。
《红与黑》一直在描写主人公做事、发言、表态时所作的算计,也写到社会各个群体典型人物的种种算计,文盲木匠盼望多挣点钱,代理教主想要升为正职,外省的资产阶级觊觎地位和荣誉,贵族少女向往浪漫的奇遇,这些人让主人公更是陷入他们各自目的和手段上的算计。作者按照他的设想写出这些人物在小说世界里如何去追求各自的成功。但到于连犯下枪杀案的时候,所有那些算计和设想却全都不见了。小说接下来只有一系列行动,既没有铺垫也没有动机,这里的叙述只用了很少的笔墨,甚至只字不提于连和玛蒂尔德这对恋人长时间以来培养出的感情。于连告别玛蒂尔德,来到韦里耶尔,买了一对手枪,击伤雷纳尔夫人,然后站立不动,没做任何反抗,被抓到监狱,在狱中受到雷纳尔夫人的探望,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然而他的这些行动,小说里没有一句解释。于连开枪的原因,小说里交待他已经认出那封揭发信是雷纳尔夫人所写,但小说并没有让这个原因联系起他的思考和意识。
因此,于连这些单纯的行动,结束了他对周围人物做出的层层算计,也终结了那些人物在目的和手段上的种种谋划,打断了小说在各种因果间安插的逻辑。做出这些行动之前,于连还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底层青年,懂得理智的考虑前因后果,而做出这些行动之后的他,只是活在眼下的时间里,回顾着他以前得到的东西。在司汤达看来,于连之前的行动,和他所说“现实生活的琐事”,都是由“贵族意识”决定的事情,它们应该属于过去的世界。在这时的社会里,像于连这样的无名之辈,即使犯下如此轰动的命案,也会半个月就被人忘光,现在只有他所说的理想生活,才能给他带来前所未有的一些幸福。
这位劳动家庭出身的稚嫩青年,外表像姑娘般文弱,他有神父教他拉丁语,还有拿破仑的事迹给他雄心,但他天真的表演却不再为这个新社会所容许。在这个社会里,他的那些远大抱负能换到的东西,不过是报纸上的一条花边新闻。事实上,司汤达写《红与黑》这个题材,正是因为看到两条类似的新闻,在《法庭公报》上记载了两件类似的罪案,这些罪案源于被这个社会视为危害的底层青年的才智和能力。所以,对于充满野心的底层青年来说,这个社会能给他的唯一回报就是超不过半个月的舆论轰动,相较于半个月的舆论轰动,于连选择了独自面对这段时间,在梦中享受纯粹的乐趣。
然而,于连最后的这个收获,又让我们想起小说的开头。他一出场时,内心就有过同样的感受。小说写到,他读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这让他心中生出远大的志向;他在市长雷纳尔先生家经历了一些细微小事,这让他的生活有了很多展开。不过这些“细微小事”,还分不同的两种:一种是按小因积成大果的旧式逻辑展开,比如雷纳尔夫人在仆人装填床垫时,帮于连把他藏在床里的拿破仑像遮掩起来,后来又在于连踩她的脚当众挑逗她时,故意掉下剪刀掩饰过去,这些小事让雷纳尔夫人无意中站到了于连一边;而另一种小事,它们既没有这样的因果联系在里面,也不会联系到人的目的和手段。它们发过来取消了这些联系,突出了只凭感觉而有的幸福,仅由生存而生的感受:比如,于连和雷纳尔夫人去乡下游玩,经常陪孩子们玩捉蝴蝶,还有于连在示爱的那个怡人夏夜,听到了风吹树叶的轻声作响。
于连交替经历的这两种细微小事,让他远大的志向在两种想法间分裂起来,一种是他一定要做的事情,而另一种是与人共享时带给他的单纯幸福。所以,于连既有他要做的事,又有他纯粹的享受,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他和雷纳尔夫人之间所有的故事。但小说写到的这种张力,不只是关于他个人的感受,从这里,其实可以分出底层人摆脱自身束缚的两种方式:一是把人们的定位全都逆转,一是在游戏中把这些定位悬置。而对于连来说,他完全征服的时候,实际上没有了任何的奋斗,这时他跟雷纳尔夫人共有了完全对等的感情,他就只是趴在雷纳尔夫人膝头哭了起来。那一刻的幸福,让他在感情上再没有做作的姿态,让他对社会的限定不管不顾,让他放下了所有目的和手段上的考虑。最后在监狱里,面对死亡再无期盼的时候,于连再一次感到了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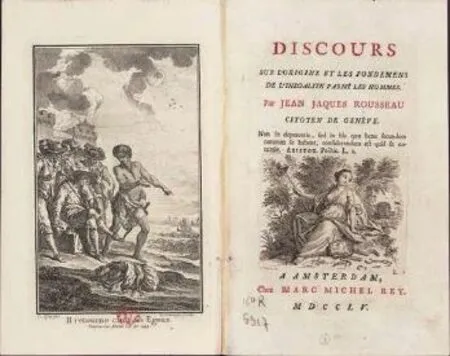
《论科学和艺术》中,卢梭写道:艺术和科学不但没有促进人的幸福,提高人的道德品质,反而败坏腐蚀人的天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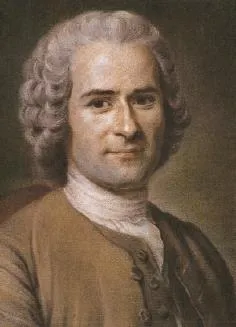
卢梭认为孤独沉思的时刻是完全自我自在之时,只有在此时自己才是大自然所希望的造物
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底层青年的原型。70年前,同是工匠家庭出身的卢梭,在于连家乡汝拉山区旁的比尔湖上,躺在船里度过了整个下午,他也做了一个这样的梦。底层出身的卢梭,过去总觉得社会辜负了他,现在流落到整个禁闭之地,却觉得自己受到了包容:“在我心头,有些感觉萦绕不去,好像我自己想被永远关在这个监狱般的避难所,好像我心甘情愿在禁锢中度过一生,好像我不需要任何反抗能力、任何出去的希望,好像我本来就该关在这个封闭的地方不与外界沟通,好像这个地方抹煞了世上发生的一切,让我忘记了世界的存在,也让世界忘记了我的存在。”卢梭把自己的处境看成监狱,就像小说里,于连因谋杀被抓紧“真正”的监狱,卢梭在他身处的监狱里,也甘于接受了他与同代人相互诋毁度过的一生。
关于这种快乐的本义,卢梭给出了答案:“它的关键和本质,就是难得拥有的闲情(farniente),我在这暂居中所有的作为,其实就像一个安于闲适的人,有滋有味而且郑重其事地将时间度过。”这种闲情,不代表懒散,它的力量来自古希腊所说“余暇(otium)”。正是有了余暇,人才能放空心思,底层青年于连才能静下心来,停下一直在做的投机和算计,不再想超脱他本来的处境。不过这种余暇的享受,不只是超脱了本来的位置,而是消除了那些位置的层级。人们经常批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思想,指责它导致了恶性的革命。但人们过于忽视的,是另一种平等的革命:它提倡本质的感觉,给人以无为的享受,这种能力所有人都能平等拥有,不管他是在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享乐之人和劳作之人,还是新说法里仍有分别的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把人身份悬置起来的这个状态,让人的利欲和层级在感觉中消解,让人的知识和享受不再有特别的限定。
说来司汤达更多是受到卢梭的影响,他对《社会契约论》的反对,其实是为了强调另一种更完善的平等,也就是人所共有的单纯享受,它只来自自身的存在和现有的一刻,在这种平等的面前,那些阶级高下之分,那些上流阶层的权争,都成了不值一文的闹剧。
于连的这一番经历,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发现:底层青年的幸福,并不在于征服社会,它在于无所作为,就在此时和此地,无视社会层级的屏障,放下就在面前的苦恼,用纯粹的感受拥抱平等,不加算计地共享这可感的一刻。而在大革命以前,在巴士底狱被攻陷的十二年之前,卢梭在《独步漫想》里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