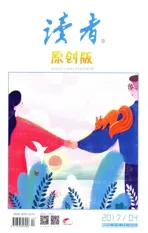“骨头级”的航海家
2017-05-04格桑亚西
文|格桑亚西
“骨头级”的航海家
文|格桑亚西

一
这是怎样神奇的旅行啊,诡异玄妙,没完没了。
人早已死去好几百年,几个国家还不停地争抢干骨头,让他下葬多年后还任人摆布,不得安宁。
一次次被挖掘、摊开,在太阳底下晾晒,用细亚麻布重新包裹,装箱,登船。从欧洲到美洲,再从美洲到欧洲,反复跨洋越海,在深邃的大西洋上来回折腾,海风吹,海浪涌,海鸥唱,湿湿的,腥腥的,咸咸的,也不知道那具高大枯瘦的骸骨,能否经受得住。
但若他真的在天有灵,想必,是喜欢的。
现在,算是尘埃落定了。他终于在一座大教堂里安顿下来,塞维利亚,这里是他最后的归宿。
疲惫的归帆靠岸,溯瓜达尔基维尔河而上,摇摇晃晃驶向宁静的港口。这里不是他的祖国,却是他功成名就的起点,也是其落帆的终端。
500多年前,他的首航是何等风光,君王祝福,祭师祷告,男女老幼倾城而出,万人空巷。最后的回归,却只有孑然的枯骨。
没有封土墓丘,没有几人合抱的苍松柏树,只是在塞维利亚大教堂宏伟的穹顶下专门辟出一个区域,放上厚重的长方形台基,台基上四位头戴王冠、衣饰华美的执杖者抬着一具棺木。
他们是来自西班牙大航海时期的四位最重要的国王,每人手里握一柄旌旗的杆,分别代表着斯蒂利亚、莱昂、阿拉贡和那瓦拉斯达地区。
国王们的头颅由雪花石膏雕刻而成,身体用青铜铸就。石质的脸上涂有浓重的宫廷妆,看不出悲喜,凝重的神情类似中国帝王陵寝前守墓的翁仲,又像扑克牌中的老K。
天光透过彩绘玻璃高窗照进来,不是很亮也绝不暗淡,是一种偏淡的酒红色。在宏大教堂的映衬下,悬空的棺木显得有些小,和想象中豪华、硕大的形象不同。棺木的色泽沉郁低调,其材质似乎取自陈旧船板,又像埋藏很久的阴沉木。
石脸铜身的国王们抬着棺木是固定不动的,但在视觉上总有些摇晃之感,仿佛还在海上,从未靠岸。海天茫茫,风吹浪涌,船颠簸着,水手们窃窃私语,军官们局促不安。唯有他,目光始终坚定地望向落日深处,望向朝思暮想的新航路,心无旁骛,一路向西,只为发现彼岸的中国和印度。
这是匠心独具的设计,依据他的生平事迹演绎,既传神又写意,对航海家而言,大概没有比这更称心如意的葬式了。
这也是骸骨的摇篮,在模拟的大海母亲的怀抱中,伟大的航海家不再是帆船上目光深远、意志坚定的领袖,不再是追金逐银的贪婪赌徒、势利商贾,他变小了,变回透明纯净的赤子,有如他的初生,也有如与他初见时天真喜悦的印第安人。
一切,若只如初见时该有多好。
二
1492年,在支离破碎的欧洲大陆上招摇撞骗十几年、四处碰壁的意大利热那亚毛纺织工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已经42岁了,依照孔子的说法,不惑已过,天命不远,该当是梦幻褪色,夕阳残照,归隐守成的薄暮之年。
偏偏,就在这一年,他时来运转。
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被他的勇气和魅力打动。她说服丈夫,下发批文,拨出专款,在公帑不足的窘迫境况下,不惜动用自己的私房钱,全力支持他漂洋过海,探索发现。
这时,距离初次提出申请已经过去整整六年,搁到一般人头上,怕是早就放弃了。
招兵买马,紧张筹备,1492年 8月3日,三条百吨小船搭载区区87个亡命水手,破浪乘风,向着未知的大海进发。
风凭西风带,水击大西洋。人少得可怜,船寒碜狭小,航海图不合格,没有GPS导航,指南针还是中国的舶来品。遇上星月暗淡、大海怒发冲冠,六分仪完全派不上用场,罗盘也只能指引大概的方向。马可·波罗的游记里记述的究竟是真实还是幻想,没有人知道。给养更是糟糕,无非是大桶劣质朗姆酒、大块发霉硬面包、冷硬的咸干肉、鼠咬虫蛀的臭奶酪。时间长了,不要说葬身鱼腹,就是因缺乏新鲜果蔬引发的坏血病,也足够让漫长的航行夭折。船上水手的素质更是良莠不齐,许多人根本就是人渣和恶棍。眼睛是黑的,银子是白的,胀满人内心的,不是海风,是占有财富和女人的赤裸欲望。
和大一统的东方中国比,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须知早在87年前的大明王朝,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朱棣特命正使郑和、副使王景弘出使西洋时的船队,单是147米长、60米宽的艨艟巨舰就有62艘,更不用说兵士编制近3万人。旌旗蔽日,猛士如云,真正的耀武扬威。
幸而隔有大半个世纪的时空,两个西洋也不是一回事,否则在海上迎头相撞,铺天盖地,号令统一的中国联合舰队,恐怕当场就把他们吓得半死,继而归降、收编,发他一先锋、偏将。
果真如此,印第安人将免除一场浩劫,玛雅文明也不至于消失,我们也不会因为对他们的天文历法一知半解,以为世界末日要来。
果真如此,烟草不会风靡世界,玉米和马铃薯不会传遍欧亚大陆,地球人口不会呈几何级数增长,历史可能会走入另外的岔路,抵达无法预知的角落,我们也许还在穿长袍马褂,作揖磕头。
上帝默认了哥伦布的幸运。
三
1492年10月12日,出海已逾70天,就在船员们濒临绝望,打算叛乱的紧要关口,海鸟出现,带绿叶的新鲜树枝出现,芦苇出现,继而大块陆地出现。
人们欢呼起来,以为到了中国、印度,至少是日本,而事实上,他们到达的不过是巴哈马群岛的圣萨尔瓦多。
哥伦布年轻时不好好读书,数学和地理尤其没有学通,到死他都在纳闷,为什么总也见不到高高在上的中国皇帝和酷爱舞蹈的印度湿婆。
他完全搞错了。
就这,也已经是石破天惊之举。
原来在欧罗巴和亚细亚之间,还横亘着广袤的未知大陆。无意间的地理大发现,把人类的认知边界推到了全新的广度。
毋庸置疑,有着天壤之别的文明的碰撞,在最初短促且懵懂的惊喜之后,带给了原住民无穷无尽的灾祸。
诚如马克思所述,大航海的动因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冲动,是注定要以血与火书写的狂草。
那是种通行全球的世界语言,不辨肤色,不需翻译,所有的种族都懂。不管辞藻如何华丽,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弱肉强食;无论举止怎样彬彬有礼,行为方式永远简单粗暴—发现、征服、奴役、榨取。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荒芜印第安原住民的玉米田,膏腴西班牙自个儿的橄榄地。顺便,他们给新大陆带去了老鼠,这的确不是有意为之,然而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带有令欧洲人闻之色变的黑死病毒。
病毒在玛雅、印加、阿兹特克蔓延,原住民没有抗体,肆虐的天花病杀死了超过一半的印第安人,幸存者放弃城市,逃入深山,留下叹为观止的巨大废墟。
这是兵不血刃的胜利,欧洲人带走黄金白银,留下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对当时已经人满为患的旧大陆来说,他是新天地的开拓者;对新大陆的土著民族来说,他是火星四溅的大灾星。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千秋功过,不好评判,看你的立场、观点、方法,考验你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总之事实就在那里,颠扑不破。
数百年后,他的后辈们终于不远万里,组团来到中国,而我们英明了几千年的君主,也因为闭目塞听、智识老旧,终于应对失措。
四
从42岁启航到55岁去世,他的人生经历了13年的辉煌,这期间总计四次到达被他视作亚洲的美洲。
1504年11月,他完成最后一次远航,但因为没能取得预期效益,船只也损毁严重,他被锁上镣铐,以戴罪之身黯然回到西班牙,接受审讯。旋即又被释放,过上了富有的生活,同时忍受着长年漂泊海上患上的风湿和关节炎的折磨。
1506年5月20日,他在西班牙瓦拉多里德市逝世,遗言是:“承万能主宰的佑助,我在1492年发现印度大陆以及大批岛屿。”
到死,他的地理课依然不及格。
然而,这并不是他旅行的结束。
他先是被葬在瓦拉多里德市的一个修道院里。3年后,遗体被转移到拉·卡图加岛的一个修道院。1537年,他的儿媳玛利亚将其亡夫迪亚哥和他的遗骨送往了现今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美洲大教堂安放。1795年,西班牙人将其遗骨从大教堂的祭坛中挖出来,运往古巴的首都哈瓦那,一直到1898年西班牙和美国开战,他的遗体才被运回西班牙,并最终葬于塞维利亚大教堂。
直到现在,时不时就有媒体报道发现了新的证据;国与国也还在争吵,辩解着他的墓葬的真伪;而专家学者也时时推波助澜,有说是真身的,有说是他子侄的,总之是反复纠结于塞维利亚大教堂棺木中骨殖的真假。
哥伦布的发现深刻影响了世界格局,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他的一生都充满着争议。
哥伦布并未被火化,没有骨灰,他只能是“骨头级”的航海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