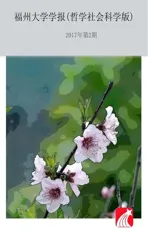再论闽南文化形成于初唐
2017-04-27张嘉星
张嘉星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 福建漳州 363000)
再论闽南文化形成于初唐
张嘉星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 福建漳州 363000)
关于闽南文化形成于何时,学术界存在着“魏晋说”和“初唐说”两种主张。笔者支持初唐说观点,理由有三:第一,任何事物的形成,都是一个经由滥觞、孕育渐成、发展壮大的长期过程,因而不得以起源期、酝酿期来混淆并代替形成期;第二,这些发展阶段可以根据闽南地区人口之族源变化所推动的地方行政建制及其增减等标志性事物的出现,来确定其各个分期的时间节点;第三,唐代中原南迁新居民“陈家军”的定居点在当时的“泉潮间”,即现在的福州与潮州之间。开漳立州的历史大事件,促进并稳固了新泉州行政机构的建立;“陈家军”在福州所属的福清县、长乐县,两者都旁证了闽南语言文化的初步形成时间是初唐。
汉民入闽; 闽越化; 闽南文化形成期; 地方行政建制; 陈元光; 漳港显应宫
一
关于闽南文化形成于何时,史料缺乏具体的记载,学术界则存在着两大主张:
第一种观点认为闽南文化形成于魏晋。然而正如张籍《永嘉行》所言:“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能晋语”的“北人”来到吴越故地,促使该地区在“西汉中期便基本实现了民族‘大换班’,主要居民与主导民族已由汉族取代了越族,汉文化取代了越文化”。[1]闽地则不然,从《三国志·蜀书·许靖传》所载许氏在公元195年前后自会稽出发,“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三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看,当时的汉文化在东瓯(浙南)和福建、两广民众中几乎没影响。更何况,福建的汉化晚于东瓯,不多的入闽汉民主要居住在闽北,人口的民族比例是汉人极少而闽越人极多,两民族间少有深层次的文化交往。因此说,这一时期的闽南不可能全盘汉化,闽南民系形成于魏晋之说不攻自破。至若现代闽南语言文化何以会浸染“魏晋因素”,这完全可以从历代南下汉族移民携带的文化基因中有着一定的“魏晋风貌”,以及“吴越同音共律”([汉]赵晔《吴越春秋·夫差内传》)的文化相似性得到合理的解释。
第二种观点是闽南文化形成于初唐。比如厦门大学黄典诚教授,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说过“闽南话属于‘唐音’”,并且生动地比拟说,假如李、杜在世,完全可以和闽南人通话;又说“李白、杜甫在世的话,未必会同厦门人交谈,倒可以同龙岩人通话”。[2]由于方言是区域文化的核心成分和文化的最重要载体,方言的形成期也就代表了民系与民系文化的形成期,因而黄典诚教授的这一重要观点一直被福建省内文史学界的教授们沿用着,甚至被民间推衍出闽南话就是唐代共同语“普通话”的说法来。可见此说之深入人心。
如果说,上引黄典诚教授回答了闽南区域语言“是什么”的问题的话,那么,李如龙教授则是通过汉人移民史及移民方式来推断闽南方言闽文化的形成过程的。
李如龙先生首先引朱维幹教授、谭其骧教授的研究成果,指出影响深巨的“西晋永嘉入闽”之说乃无根之萍,因为它是采自乾隆版《福州府志·外纪》卷七五引《九州志》,而《九州志》并无此文。[3]并且晋代南迁的汉人大多止于苏南,并无入闽的记载,可见即使汉人有在西晋南迁入闽者,怕也是先到苏南再辗转入闽的。其次,李如龙先生又通过地方行政建制及人口数量等,来探索闽文化的形成期:
当时(指晋代,笔者注)门阀制度盛行,名门贵族南迁之后携着家奴乡民聚集在一起,往往要建立侨置州郡,而闽中并无侨置州郡之设。当时的福建还是一片荒凉。据《晋书·地理志》所载,自建安郡分立晋安郡时建安郡统县七,晋安郡统县八,才各有4300户,全闽8600户,人口数当仅有数万。(第25、26页)
北人入闽于正史资料最早记载为《陈书·世祖纪》所云:“天嘉六年(565)三月乙未诏: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可见侯景之乱(548-552)后,过江北人有继续南下入闽的。关于永嘉乱后的这次移民,罗香林研究的结论也与此相近,他说:“仕宦的人家,多避难大江南北,当时号曰渡江,又曰衣冠避难,而一般平民则多成群奔窜……多集于今日江苏南部,旋复沿太湖流域徙于今日浙江及福建的北部。”(第26页)
这次迁徙是长时间、小批量的,主要定居地应是闽北,也有辗转到了闽江下游、木兰溪和晋江流域。……当时的闽北占有全闽一半的县份和一半的人口。(第26页)
值得注意的是,晋代汉人入闽的“迁徙是长时间、小批量”的,虽然也有“辗转”来到闽南者,但为数甚少。根据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在开元年间(713-741)陈家军“平乱”建漳后约30年,闽南地区拥有了漳、泉二州七个县,人口已达5万多户,户数占到全闽五州24县总数的一半以上,是晋代全闽人口户数的11倍多。由于以陈政、陈元光为主体的初唐南下汉民是福建地区首次成批迁入的,由此可见,彻底改变福建的人口结构的原因乃“陈家军”的到来,对汉文化的在闽传播和闽南文化的形成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在闽东地区,其汉民陆续南下的时间比闽南早,陆续迁来的汉人也比闽南多,李如龙教授反而认为其方言的形成应在唐末五代“三王”入闽之后,比闽南话的形成要晚二百年。这也间接反衬了闽南文化不可能形成于魏晋。
台湾老一辈语言学家吴守礼教授对闽南文化形成期的看法则是:永嘉兵乱、东晋渡江、增置晋安郡等,都证明了汉民在闽南的一系列活动,然而此后300年仍有“蛮獠”在顽抗,说明晋代汉族入闽只是闽南方言的“滥觞”,而非形成期。“最显著而且和闽南方言的形成有关联关系的历史事实是在唐高宗二年(669)河南光州固始人陈政父子受了朝廷之命,率领了由五十八姓人民组成的军民——可能大多是河南中州人——到福建去平定蛮獠啸乱。”[4]他还发现一个重要现象:“曾是‘漳州府治’的‘龙溪’虽然早在六朝时期的梁代已建置在先,但漳州人却奉祀陈元光,尊为‘开漳圣王’。”可见闽南语言文化的形成与陈氏开漳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此外,吴守礼同样以地方建制的增废来旁证闽南文化的形成期,指出与漳州齐名的另一闽南方言中心地之“泉州”,在晋代属晋安郡,其“泉州”之名是在唐开元十三年(725)把“闽东的泉州”改称为“福州”以后才有的,言外之意是:初唐以前的今泉州—闽南与今福州在语言文化上仍是难分彼此的一个整体,闽南文化区尚未从闽东南的大格局中独立出来。
如此看来,闽南文化形成期之“魏晋”说至少存在三个“致命伤”:一是片面地扩大了汉民长时间、小批量、零星进入闽省各地在汉文化置换闽越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且似乎故意遗忘了零星入闽的汉民主要定居在闽北,同时又一厢情愿地把当时的“泉(今福州)潮间”理解为现代的泉州与潮汕之间;二是未采用历史的眼光看待陈元光的尊称“开漳圣王”,其管理和影响的范围要比漳州大得多;三是没有将文化的形成视为一个渐进式动态进程,而是把这一历程简约化。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观点无疑是违反科学研究最起码的常识的,不可不细辨。
二
毫无疑问,闽南民系及其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同一切事物和有生命体的形成一样,经由滥觞、起源、渐进发展且演变、质的突变而形成。
所谓滥觞、起源,指的是事物从无到有、刚刚开始发生;酝、酿、酝酿,《辞源》释“积渐而成”,《现代汉语词典》则为“比喻做准备工作”;发展,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量到质的递进式变化,形成则指事物质的突变而基本定型。可见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行进式”,其中滥觞、起源、渐进发展、质变而定型等词语代表了事物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滥觞、起源、渐进发展而演变等,都不能等同于经过质变之形成。以此常识来观照闽南文化“积渐而成”的阶段性发展状况,我们大致可以根据人口族源属性的变化所推动的地方行政建制的增加、完善等区域文化发展的分期性、标志性事物的出现,来确定该进程各个重要历史阶段的时间节点。
(一)闽南文化起源期
闽南地区的汉文化接触,始于闽越族同华夏族有较大交往的先秦。从文献记载看,《周礼》之《夏官·职方氏》曾留下“七闽”的记载,《秋官·司寇》则称每年有“闽隶百二十人”前往周朝服役。闽南文化酝酿期则在东汉建安十二年(207)创立建安郡(在今建瓯市),辖建安(同在建瓯)、南平、将乐、建平(在今建阳)、东平(在今松溪)、邵武六县和闽东地区设吴兴(在今浦城)、侯官(今福州地区)两县,因闽南地区只有一个东安县(在今南安),不久即撤,可见汉魏时期迁入福建的汉民主要留居在闽北山区,鲜少到达闽东南沿海者,应视为闽南文化起源期的标志性事件较为合理。
(二)闽南文化酝酿期
从东汉建安十二年设立东安县(治在今泉州南安,辖今莆、泉、漳、厦、岩)到西晋太康三年(207-282)分建安郡东南地置晋安郡时,晋安郡领闽东6县和闽西1县、闽南2县。闽南地区的晋安县辖今泉州和莆仙,同安县则辖今厦门地区和漳州大部分地区。
晋安、同安两县的设置,是闽南地区汉人渐增的历史见证,意味着闽南正式进入了区域汉文化的酝酿期。同时也应看到,尽管在建安郡增置闽东南的晋安郡的七八十年里,入闽汉民由闽东北渐进闽南,可是来到闽南的汉民多有回迁者,人口增长迟缓,郡县建制并不稳定,时有置、废、撤、并、改,且屡设屡废。例如南朝宋泰始四年(468)改晋安郡为晋平郡,梁天监年间(502-519)又析晋平郡地置南安郡而领晋安、龙溪、兰水(辖今莆田、泉州、漳州、龙岩地区),勉强达到3个县的建制。由于此期闽南的汉族移民来源于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原籍地,其语言和文化应是比较多元而无序的。因此笔者认为,将西晋太康三年(207-282)至6世纪初的300年间看成闽南文化酝酿期,奠定了汉语言文化的基础,应是比较客观公允的。至于地名晋安、晋江等历史文化地名“活化石”遗存,既是汉晋文化渐染闽东南的重要标志,显示了闽南与闽东文化的亲密关系,同时也充分表明此时的闽南尚未从闽东南的区域大格局中剥离出来,尚不是一个语言文化独立体,是本时期尚处于闽南文化酝酿期的又一个重要依据。
(三)闽南文化发展期
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一说天监六年),闽东南析晋安郡(在今福州)地置南安郡,下领晋安(今泉州、莆仙)、兰水(今南靖县大部与平和县东部)、龙溪(今漳州东北部;梁山西南部属潮州除外)三县,隋开皇九年(589)改晋安县为南安县,闽地汉民人口呈持衡性缓步增长。由于来闽移民多有返回北方者,因而南朝《陈书·世祖纪》说,世祖天嘉六年(565)三月乙未下诏许诺“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郡者(今潮汕地区,笔者注),并许还本土”。比如在陈光大二年至唐武德初年(568-618)的50年间,莆田人口便屡增屡减,县级机构也屡建屡撤,至武德五年(622)撤南安县而升为丰州、析置莆田县[5],5年后的贞观元年(627)又废丰州,径以南安、莆田、龙溪三县返属泉州(今福州)。由于这一时期的汉民仍旧来源于不同的原籍地,语言和文化仍是多元不一的,闽南地区照旧未从闽东南的整体中“裂变”出来。因此我们说,从六世纪初年到唐高宗时期“蛮獠啸乱”爆发前的668年,应为闽南汉语言文化渐变性的发展积累时期。
(四)闽南文化形成期
唐总章二年(669),陈政奉诏入闽平定“蛮獠之乱”,率将校士卒3600多名及家属无算;不久唐廷又派兵增援,陈母、陈政两兄及子侄等举家再领固始89姓7000余军士及家属入闽,“蛮乱”遂平。陈元光于是奏请设立一个州级行政机构来管理这片新土地,于垂拱二年(686)获准建漳州。这近20年的时间段(669-686)便是闽南语言文化由量变的发展期转向质变裂化的骤变期。
1. 闽南地区出现人口“种族大换班”
同一地区同一时间迁入而聚居的人群,是移民语言文化的坚固载体。中原“陈家军”一整批军事移民的到来,打破了秦汉以来北下汉民原籍地不同、入闽时间不同、迁入人口时有北还、批量不大的零散式移民的局面。这种同一时间入闽的同籍移民,集“军事—政治—经济”之文化优势而“空降”闽南,从而实现了本地区人口结构及其文化属性的“大置换”,一如董楚平描述的吴越地区之“种族大换班”,闽南地区的主导民族也“由汉族取代越族,该地区的文化面貌也就为之大变,即汉文化取代了越文化”(见前引)。尽管人事有自然代谢,然而以“陈家军”为“文化载体”的中原语言文化却通过“代际传承”而保留了下来,成为现在的闽南语言文化的主体。
2. 漳、泉同为“陈家军”移民定居点
值得特别提醒的是,“陈家军”定居的落脚点并不限于漳州地区,而是在当时漳州以东、以西、以北的“泉潮间”,即今天的福州与广东潮汕地区之间。对此吴幼雄教授有着清醒的认识:
唐朝前期,今福建省有两个泉州。唐武德六年(623)改建安郡为泉州(州治今福州),久视元年(700-701)析南安县东北置武荣州(今泉州)。景云二年(711)改泉州(今福州)为闽州,改武荣州为泉州(今泉州)。开元十三年(725),又改闽州为福州(《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年·江南道五)。则知唐初泉州(治在今福州)的地域几乎包括今福州、莆田、泉州和漳州等福建的沿海地区。陈元光戍守的“泉潮”间,是今福建南部与广东潮州交界的漳州地区,非今之泉州。唐初陈元光入闽戍守的安仁(即绥安,今漳浦、云霄一带),系泉州(今福州)之南,绥安地属唐初泉州南部(即今福州之南),故亦称泉南。唐初沿用习惯叫法,把泉州(今福州)南部地区称泉南,所以丁儒《归闲二十韵》亦作“泉南”。景云二年,闽南的泉州设置,……泉南遂移名为闽南泉州的别称。由此则知陈元光《喜雨次曹泉州二首》时,闽南泉州的地名尚未出现。[6]
实际上,陈元光戍守的“泉潮间”几乎包括了福建沿海的福州、莆田、泉州和漳州等地区,显示了“陈家军”所率汉民入闽的强大影响力。因而在漳州地区以外的闽东南地方志,多有关于其后裔定居某地及其军事活动的记载,例如南宋《仙溪志》(仙游县)卷三《祠庙》称:
陈政仕唐副诸卫上将,武后朝戍闽,遂家于温陵之北……今枫亭二庙,旧传乃其故居。[7]
此陈氏“故居”在今泉州以北五十多公里开外的莆田-仙游-惠安三地交界处的仙游县枫亭驿,乃福州通往闽南的交通要道。在唐五代,泉州(今福州)驻军武官往往“家枫亭”,连五代时期的留从愿亦安家枫亭赤湖留宅村,陈家军也不例外,其部伍“平乱”的流动作战前线在漳州,而“后方根据地”却在泉、莆[8],因而陈氏“唐军”子裔不乏留居南安、惠安、晋江、仙游者:
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兵入闽征剿泉、漳之间的“蛮獠”,军事行动结束后,一部分唐军在仙游入籍。[9]
何氏,祖何嗣韩,河南光州固始人,唐初随陈政、陈元光入闽,分镇泉州,食采螺阳,家于惠安。[10]
陈政、陈元光……部将许天正领兵驻守泉州,南下士兵与本地共同开发,相当一部分将士留居晋江。[11]
陈政、陈元光父子……其部将许天正、潘节驻守南安一带,后来居留南安。[12]
唐初,陈政部将潘节领兵驻守泉州,将士们与当地百姓共同开发,后来相当一部分将士散居驻地。[13]
南安、惠安、晋江、仙游一带的“唐军”属于漳州“陈家军”同一时间、同一批次的中州军事移民,其语言文化以全面覆盖的态势出现在闽越故地,这在福建地区是第一次,与自秦汉以来入闽北方移民之长时间、多原籍地的间断性、零杂性非军事移民方式的渐进式入闽决然不同,判然有别。因而史学界多有将福建地区汉族政权的确立期定为“陈家军”入闽者,就是这个道理。从此,以“陈家军”为汉文化“载体”的这一同源性、同质性的先进的中原文化取代了福建沿海“泉南”地区(今福州之南)的刀耕火播土著文化。这一闽南文化区域形成期的显形表征就出现在垂拱二年至开元二十九年(686-741)的55年间。再加上约二百年后,唐五代王审知三兄弟之“三王”所率光州军民入闽,有更多的与“陈家军”同籍的光州军民落籍闽南。闽南地区经历过第二次大规模同一朝代同一原籍的军事移民文化的洗礼,闽南地区的移民-中原汉文化得到了强有力的巩固。
3. 闽南文化区域两个中心城市格局的形成
在闽南文化区域的形成期,即垂拱二年至开元二十九年(686-741)的55年间,出现了三个最重要的显性标志,一是增置了漳州,二是今泉州设而不废且定名,三是漳、泉两个中心城市之文化区域基本格局的形成。这三个显性标志的核心标志是增置漳州,它触发了闽东南地区政治文化的一系列质的裂变,朝廷开始重视合理分割闽东南之行政区块,以形成行政管理的合理布局。
首先在建漳(686)前后(嗣圣初年至圣历二年,即684-699年)的16年间,唐廷先后三次分泉州(今福州)地置武荣州(泉州曾用名,治在今南安丰州),都未久即废、废而又置,一直到久视元年(700)才确立了武荣州,景云二年(711)将其定名为泉州,而沿用至今;原泉州即今福州则改名闽州,从而将闽南地区彻底从闽东南的整体中独立出来。泉州的确立使泉、漳互为犄角,大大增强了本地区的行政管理效力,为汉民和原住民正常的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其次,增置的漳州促进了闽南地区两个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基本格局的形成,一是泉州州治原本无县,而于开元六年(718)析南安县东南地置晋江县;二是新泉州的老属县龙溪距离州署遥远,而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划隶漳州。至此,漳州领有州治属县漳浦和龙溪县,又在大历十二年(777)析汀州龙岩县来属;新泉州则于久视元年(700)增设清源县(今仙游县),两州共有了漳属漳浦、龙溪、龙岩和泉属南安、晋江、莆田、清源共7个县级建制,县份是南朝——闽南文化酝酿发展期的2倍多,从而彻底改变了原有的语言文化面貌。
再次,陈氏家族连续数代任职漳州——闽南的最高行政长官,时间长达150年之久;其部下也多兼任“泉潮团练使”而执掌泉、漳、潮三地军政。到了唐末五代,泉、漳两地先后由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和陈洪进节制,后者又于北宋初建隆年间(960-963)先后知泉、南(漳)军府事、清源军节度使等职,更加强了闽南政治、军事、经济、语言、文化的一致性,从而将当时的“泉南”即现在的福州以南的闽南及粤东文化区打造成了一个文化整体。虽然闽南历经宋、元、明、清朝代更迭,北方移民、难民南下,然而与后来的北方文化对闽南文化影响只是更加多样化罢了,再也没有改变闽南语言文化以中古—唐语言文化面貌的基本格局。
4. 闽南文化对闽东地区的渗透
闽南文化也渗透到与泉、莆山海相连的闽东地区福清县。如前引宋代《枫亭志》卷一《地理》称:“福清灵著王庙,旧名威惠,在福清县治西隅后王山,祀唐陈元光。”明万历《福州府志》同载:“灵著王庙,旧名威惠,在福清县治西隅后王山,神姓陈名元光。”
“陈家军”的“势力范围”甚至达到比邻闽东福清的长乐县。据《海峡都市报》2015年7月4日报道,福州市长乐县漳港镇在一处沙堆中挖出了一座“显应宫”,当地人错以为其地宫后殿供奉的是“大王神”,也有说是“开漳圣王庙”,从而引起文化界关注。宫庙所在地遂于2015年6月27日召开有关显应宫“神主”为何人的学术研讨会,原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省文史馆馆员欧潭生、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汤漳平院长等专家学者应邀参加。地方文史家汤漳平教授指出,显应宫地宫后殿正中供奉的正是陈元光,该神像和另外四尊彩色泥塑(见图1)与漳州“开漳圣王庙”如出一辙。地宫后殿左侧供奉的雕像群则是奉旨增援陈政的陈母魏妈等(见图2;妈,闽南话指奶奶),援军原由陈政的两位兄长陈敏、陈敷带领,后敏、敷及其两子殁于来闽途中,由魏妈代子为帅。塑像中,魏妈两侧是戎装的儿媳、孙媳,两旁的侍女怀抱着婴儿,表现了魏妈一行携家带口征闽于行军途中。

图1 正中的神主为陈元光

图2 右四骑神兽的老妇人为陈元光的祖母魏妈
显应宫的出土及“陈家军”雕像群的存在,表明初唐汉文化所及区域不止于漳州—闽南,而是如口碑记载的“泉潮间”。欧潭生甚至认为,显应宫的出土及“陈家军”雕像群的再现,表明陈政、陈元光父子“开漳”的范围包括了部分福州地区,长乐漳港镇也是陈氏部将移民到此而命名的。也就是说,早在初唐,同漳州间隔着泉州和莆仙的闽东地区,也侵染了“陈家军”带来的汉文化。
换句话说,长乐县漳港镇显应宫的出土和重见天日,以“实物”的“身份”证明了闽南文化的形成在初唐。
注释:
[1] 董楚平:《汉代的吴越文化》,《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2] 参见丁仕达为郭启熹《龙岩方言研究》一书所作的序,香港:纵横出版社,1996年;厦门日报记者宋智明采访李如龙教授的报道:《方言专家细说闽南话的“前世今生”》,《厦门日报》2006年2月24日,第10版。
[3] 李如龙:《福建方言·第一章第二节:中原汉人入闽和闽方言的形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笔者按:下引李著,咸注页码;书中所引罗香林语,见《客家研究导论》,台北:古亭书屋,1975年,第41页。
[4] 吴守礼:《闽南方言过台湾》,《综合闽南方言基本字典·代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
[5] 笔者把莆田县纳为闽南语区,是因为莆田原属泉州,宋代以前莆田方言与闽南话并无二致。莆仙方言是否可以作为闽语的5个分支之一,目前学界仍有争议,其语音、词汇很接近闽南话,只是语法带有闽东方言的某些特点罢了。
[6] 吴幼雄:《泉南民俗文化一隅——泉州的陈元光崇拜》,《泉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泉州人祀奉陈元光考》,《陈元光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
[7] [南宋]黄岩孙:《仙溪志》卷三《祠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
[8] 何清平:《陈政陈元光父子寓枫亭》,《福建陈氏网》,网址:http://www.fjchens.cn/lcms_content.asp?cid=42;又《仙游新闻网》,2014年1月13日,http://www.xyxww.com/wtpd/wh/20140113/428400007.aspx,2014年12月15日。
[9] 《仙游县志》第三篇第二章《人口变动》,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年。
[10] 《惠安县志》第三篇第一章《人口演变》第一节,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
[11] 《晋江市志》卷三第一章《人口演变》第二节,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年。
[12] 《南安县志》卷三第一章《人口演变与分布》第二节,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13] 《泉州市志》卷三《人口》第一章第一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责任编辑:余 言]
2016-12-17
张嘉星, 女, 福建漳州人,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教授。
K207
A
1002-3321(2017)02-002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