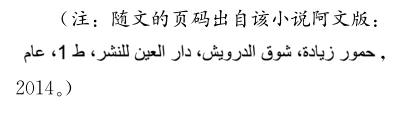一段沉寂的历史 一群苦行僧的救赎
2017-04-24邹兰芳
邹兰芳
自20世纪60年代苏丹著名现实主义作家塔伊卜·萨利赫以小说《北迁的季节》(又译《迁往北方的季节》《风流赛义德》)蜚声世界文坛、被BBC评为20世纪最著名的阿拉伯小说家后,苏丹似乎没有出现过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家及作品。直到2014年年底一位皮肤黝黑、身材瘦高的70后作家以史诗般的小说《苦行僧的渴望》摘取阿拉伯世界年度最佳小说奖———纳吉布·马哈福兹奖桂冠时,这块炽热、陌生、神奇的土地再度让世人眼前一亮。这位作家叫哈穆尔·奇亚戴。作为萨利赫的学生,奇亚戴在授奖词里说自己的文学情怀和创作意图与老师惺惺相惜,旨在“打破非洲这块土地的孤寂和被人遗忘,将这块土地上独有的说书遗产传承下去,将苏丹人富有的传说故事融入人类共同的情感世界中,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遭遇、焦虑、梦想、雄心、成功和失败……”。
一
这部长达460页的长篇小说以苏丹历史上著名的反英埃反专制的民族主义宗教革命“马赫迪运动”失败后喀土穆沦陷、生灵涂炭、民生凋敝为背景,以男主人公黑奴巴赫特从复仇到自杀的情节推进为主线,展开众多人物的命运和错综复杂的关系。
1898年12月英埃军队入侵苏丹,“马赫迪运动”宣告失败。狼烟四起、一片混乱中,深陷囹圄七载的巴赫特得以释放,他非但没有感到自由,相反,出狱后的第一件事也是人生中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为其挚爱、希腊裔埃及人女传教士秀杜拉(后来改名夏娃)复仇。孤儿出身的巴赫特相貌丑陋,秉性勇敢、忠诚、善良,年轻时在奴隶市场上被一欧洲人买去做性奴,受尽欧洲人、土耳其人的精神凌辱和肉体折磨。后被征兵加入马赫迪的“苦行僧队伍”与埃及政府军会战恩图曼。大败后,被苏丹贵族舒瓦克招为掘墓人,为死去的夫人下葬,由此邂逅了在舒瓦克府上为奴的美丽的秀杜拉,顿生情愫,直至日思夜想,最终为秀杜拉复仇殉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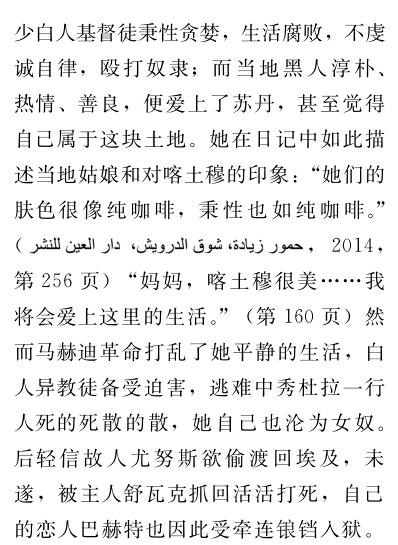
显然这是一部关于血与火、生与死、信仰与背叛、自由与专制、爱情与战争、宗教与伪宗教的悲剧性史诗小说。当一切都化为烟尘,历史无情地碾压过众多小人物时,留在大地上的只有永生不息的渴望———渴望爱、渴望正义、渴望救赎。作者不羁的灵魂深处感到:“在这充满怀疑的灰暗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人们能做的和不得不做的就是创造自我的意志并寻求这一意志实现的满足感。”正如小说扉页中作者援引中世纪苏非大师伊本·阿拉比的名言:“每一种因遇到了自己所渴望的而平息的渴望终究是不可靠的”,真正的渴望就是渴望本身,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是一场永不相遇的爱情,是苦行僧式的苏非圣徒毕生寻找的真主之爱,或曰真理之光。这束光若隐若现,其终点被永远地设置在前方,遥不可及,类似幻觉;圣徒意识到那是个幻觉,可同时他又必须相信其真实地存在,因为只有借助这种信仰的真实性,他才能想象得更深更远,才能不被残酷的现实羁绊,才能突破那个幻觉而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不断地踽踽独行。这也正是作者文学创造思想的真实写照,他将这一苏非理念作为整部小说的基调,也作为整个人类悲剧命运的注脚,展开了对爱情、对革命、对宗教的反思。
二
首先,贯穿整个小说的就是一场凄美的爱情———巴赫特和秀杜拉的跨肤色、跨地域、跨宗教、跨阶层之恋。这场恋爱注定始乱终弃。当巴赫特看到秀杜拉的日记后终于明白了他俩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日记中这样写道:“巴赫特和这座城市不一样,在把这些回忆录集结成册出版时,书里一定会提到巴赫特。他那么与众不同,堪称楷模,定会吸引西方读者。他的爱情之旅值得西方文学大书特书,他简直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情人,却明珠暗投,掉落在这片野蛮的土地上。他若不是黑人……他若不是苦行僧黑奴……”(第429页)不言而喻,已沦为女奴的秀杜拉也爱上了同为奴隶的巴赫特,但多少带着西方人对黑人猎奇的心理,巴赫特对秀杜拉的热恋让人想起莎士比亚笔下的北非黑奴奥赛罗,是西方文学喜爱的人物。然而肤色和宗教像不可逾越的鸿沟让秀杜拉望而却步,她终于不敢接受巴赫特的爱情,转而相信故人骗子尤努斯,结果死于非命。因爱人之死而酗酒流浪街头的巴赫特也被军警抓进大狱,一蹲就是七年,罪名是“情痴”。
巴赫特对秀杜拉的渴望如此了斷,小说中其他次要人物的渴望亦概莫能外。他们每个人都被上帝或真主放逐,像苦行僧般行走在一条渴望的精神之途上,希望找到一剂治愈自己心灵创伤的良方以获得救赎:巴赫特思念秀杜拉;秀杜拉迷恋自己的基督使命———拯救喀土穆这只“上帝的黑羊”;玛丽茜莱暗恋着巴赫特;哈桑一心追随“救世主”马赫迪的召唤,为铲除社会的不公发动圣战。然而最终都化为泡影:巴赫特出狱复仇,最后选择自杀;秀杜拉偷渡未遂被主人残酷杀害;玛丽茜莱为巴赫特不惜牺牲一切却得不到爱情;哈桑终于怀疑自己一心追随马赫迪的行为是否代表正义:我们是否配得起真主赐予我们的胜利?(第447页)以暴制暴能否换来人类真正的公正?历经战争洗礼的他尝遍了战争失败的痛苦,战争夺去了他的导师,妻子也不知下落。哈桑在无限思念妻子法蒂玛时深感人类的脆弱和罪恶,内心独白道:“我没有一天忘记你,法蒂玛!……亚当的子民是多么脆弱啊!每当真主给予他隐秘的恩惠引他走向崇高时,他的内心却总是让自己堕落于尘世的浮华。”(第318页)
在小说的末尾,已经用5个仇人的生命血祭恋人的巴赫特准备自杀,他对恋人秀杜拉(夏娃)说:“我来了,夏娃,终于来了。……也许我给自己找个休息的理由,对终极的渴望已让我身心俱疲,我累了,已经顾不上了。过一会儿,他们就要把我送上绞刑架,你我之间只有一条绞索之隔。别伤心,此次相会再不分离,此次相会后,思念将永远平息。”(第459页)当上帝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时,他们注定宿命般地在尘世中寻找丢失的那一半,只有重返伊甸园,才能了却那无尽的思念和苦苦的寻找。可是还能回得去吗?
三
其次,小说用小人物巴赫特这样的黑奴苦行僧的命运来折射苏丹、埃塞俄比亚地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史上“缺失的一环”———平民史诗。苏丹在这段历史进程中充满了奇伟诡谲的事件,一波未平又起一波,统治者们竭力淹没前朝之事。作者奇亚戴旨在通过文学文本为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边缘人物书写一部自我救赎的心灵自传,作者的历史观是:人类历史不是精英的历史,它更应该是被压迫者的历史,他要展开“历史的皱褶”,让世人关注像巴赫特、秀杜拉这样虔诚守信的边缘人物的悲剧命运,为后殖民叙事发出非洲的声音。
历史上努比亚地区早期的基督教徒和当地土著与埃及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一直时好时坏,而现代西方对苏丹这个地区的了解肇始于18世纪的法国旅行家蓬塞和法国外交使节杜·鲁勒,彼时,一套西方的哈哈镜吓坏了当地人。直到奥斯曼土耳其在埃及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从地缘经济、政治、军事的角度出发,出兵苏丹,把苏丹纳入埃及的版图(1820年),苏丹被迫拖入现代化的轨道。强壮的苏丹黑奴因其“勇敢、耐劳、忠于主子”而被配置为现代化军队最合适的材料。此时,已完成殖民地扩张的欧洲列强正丧心病狂地对东方殖民地国家敲骨吸髓。殖民地之殖民地的苏丹奴隶制盛行,奴隶被随意抓去做性奴,做牲口,做炮灰;而苏丹社会内部则深陷沉疴痼疾,战争频仍,饿殍遍地,瘟疫四起,政府腐败无能,人们在两条歧路上往返:一边成为蛮风俚俗的牺牲品,另一边则陷于精神萎靡、宗教不举、政治废弛的迷茫生活中,人性的尊严和光辉黯然无存。无疑,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激进的革命风暴是在所难免的。
小说中,作者着重探讨了信仰问题和暴力问题。苏丹人民终于忍受不了殖民者的流血、沉重的赋税和残酷的统治,在苦行僧穆罕默德·艾哈迈德(1840—1885)的带领下以“马赫迪”(“救世主”)之名发动了反抗英埃统治的民族主义革命(1881年),这也是一场穆斯林世界期待已久的宗教复兴运动。而当时的埃及业已在英法欧洲大国的控制之下,中下层士兵们被命令跟一个以穆斯林世界所期望的使命为己任的人作战,后来,他们自己的国家却被一个镇压了人民运动的外国基督教强国所占领。历史便是弱肉强食。
“马赫迪”出现时穆斯林世界已丧失了一切健康和活力,中世纪的思想、学术火炬已完全熄灭。以“降临世界推行正义和公平”为己任的“马赫迪”一呼百应,深得民心,率领“苦行僧之旅”很快占领了恩图曼、喀土穆,建立了马赫迪王国。然而这场革命最终被英国殖民者镇压(1898年)。由此作者在小说中展开了对信仰和暴力的反思。以匡扶正义、倡导社会平等的“马赫迪”在占领了喀土穆、摧毁了旧秩序时,接踵而来的却是暴力、恐怖和屠杀。“苦行僧军旅”屠杀了开门欢迎他们的传教士和苏丹女佣,杀进教堂俘虏了大批修女们,或把她们分配给达官贵族,或压到女奴市场进行买卖(第250—251页),秀杜拉就是在马赫迪军队屠城时被沦为支持马赫迪运动的机会主义者舒瓦克家的女奴的,后又被他残忍杀害。还有,1882年当英国占领亚历山大时,埃及穆斯林在群情激奋中屠杀了无辜的外国侨民以讨还殖民者的血债(第162页)。作者对这种暴行提出质疑:革命是否就是暴政的别名?作者没有否定这场宗教民族革命的积极意义,也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只是质疑带领被压迫者进行正义事业的“正义性”应该如何得以实现。答案恐怕不是简单地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给出,它必然涉及人之本性的哲学性思考,在文本中,作者将苏非主义大师的至理名言作为问题的引导。
再就是信仰问题。小说中,作者塑造了哈桑这个人物,他从小受到正统伊斯兰的教育,与导师的女儿法蒂玛成婚,不久抛下妻子投身到马赫迪革命运动中。在经历了战争大肆杀戮后,他感到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导师死去,妻子离散,他内心十分痛苦,开始怀疑自己狂热的信仰,发出了喟叹:“狂热的信仰几乎使我成为异教徒。”(第454页)小说中另一位人物善良的优素福问巴赫特:“我对你这么好,你们为什么要侵犯我们?”巴赫特只说为了马赫迪,为了信仰,而信仰究竟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楚。戴法阿拉长老警示迷茫中的年轻一代:“孩子,当心,盲目的信仰也会被当作异教招来杀身之祸的。”(第117页)
人类历史总是处于不断循环中。奇亚戴用历史小说影射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反思2011年发生的“阿拉伯剧变”和接踵而来的阿拉伯世界局势,2014年该小说的出版是对“阿拉伯剧变”的最好祭奠。当人民怀着对民主的渴望,对腐败、专制的愤怒走上街头、广场后,时至今日目睹的是政权频频更迭,经济停滞,物价飞涨,极端主义分子狂热无度,暴力愈演愈烈。作者通过小说提出了关于人性、革命、暴力、信仰等哲学性命题,希望為现代阿拉伯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四
该小说在叙事艺术手法上也堪称翘楚。埃及著名小说家、文学批评家萨勒娃·伯克尔认为:“该小说是一部鸿篇巨著,是苏丹文学史上的丰碑。”在这部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中(埃及著名小说家、评论家易卜拉欣·阿卜杜·马吉德语),作者采用了形式多变、富有特色的叙事技巧,实现了多种文体的交融,将苏非赞美诗、《古兰经》《圣经》经文、诗歌、传说、民歌、历史文献、小说中人物的书信、日记、独白、对话等文体巧妙地织入小说叙述中,引领读者站在不同立场、不同时空看待这一生活世界,加上倒叙、闪回、意识流、反讽等现代主义小说技巧,使作品呈现出多元化、立体感的架构,创造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意象世界,不仅加强了小说的真实性,同时也表现出后现代主义强调的相对性。
出生于麦罗埃的哈穆尔·奇亚戴从小就聆听着关于这个地区神奇的传说,“这里的良驹是一匹尼罗河马和一位纯洁美丽的姑娘杂交的产物”,“居住在山区裸体而独眼的人们有着惊人的习俗”,这里“盛产黄金和棉花”,“一半是森林,一半是沙漠”,“它位于山脚下,沐浴着尼罗河的潮润。一切都不曾改变,却面对了世事的种种变迁而保持着原有的形态”。正是这些流传久远、不曾改变的故事和神话赋予作者小说世界的奇伟和魔幻。奇亚戴曾做过记者,现在是公民社会运动的积极推进者。2009年移居开罗,迄今已发表了两部短篇小说集:《恩图曼记》和《山脚下的睡眠》;两部长篇小说:《苦行僧的渴望》和《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