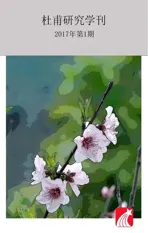天宝六载:杜甫诗歌嬗变的关节点(下)
2017-04-22谷曙光
谷曙光 俞 凡
天宝六载:杜甫诗歌嬗变的关节点(下)
谷曙光 俞 凡
历来谈论杜甫诗风诗旨,最多的便是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然而考察其早年诗作,并非向来如此。在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中,诗风是不断嬗变的,变是常态。杜诗之所以形成沉郁顿挫的主导风格,具有深刻复杂的多重原因,诗人的遭际、境遇和所处的时代等,都起到了重要而微妙的作用。譬如杜甫在长安的十年,特别是天宝六载(747)参加李林甫主导的制举的经历,既是他人生的一大转关,在诗人的创作历程中也显得十分紧要。以天宝六载为分界点,考察杜甫十年间的作品,可知其诗歌在情事、诗艺、风格等方面都呈现出不易察觉的微妙变化,而诸多变化对于诗人锻炼、塑造深沉婉折的诗风,干系重大。天宝六载,既是杜甫的人生转折,杜诗亦从这里转折。论文还对李林甫与杜甫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观点。
杜诗 嬗变 天宝六载 关节点
五、人生转关与诗风嬗变
陈贻焮说:“以应诏退下一事为分界,此前此后杜甫简直判若两人。”㉙天宝六载应制举的失败,确实使杜甫的境遇、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杜甫《秋述》一文是体味诗人制举落第后几年间心态心境的重要文章,其文开头说:“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更沉痛的叹息是:“我,弃物也,四十无位。”读之令人鼻酸。杜甫感觉被国家、被君主抛弃了,这种强烈的被遗弃感会改变一个人的心态情志,生出诸如忧伤、消沉、沮丧等负面情绪。诗人悲愤交加,在痛苦的体验和领悟中,重新思考人生,这也为他的诗歌创作打开了另一扇门。以天宝六载为中心,在前后十年左右的时间中,杜甫诗歌抒写的情事、艺术和风格亦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和面貌。
(一)从浪漫的裘马轻狂到深沉的内心独白
从诗歌题材内容看,天宝初至六载,杜甫留存的诗作主要是围绕登览、宴饮、赠友之作。天宝六载之后,虽然仍有登览、宴饮之作,但是内容和情感与之前已有所不同。旅食长安期间,诗人还创作了相当多的投赠诗和忧国虑民之作,这更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1.登览宴饮之作

天宝六载之后,杜甫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长安附近,其诗开始频繁流露出有志难酬的抑郁和苦闷,同时增加了对于国家、时局的关切。《行次昭陵》《重经昭陵》两首,系诗人行经昭陵所作。《行次昭陵》前半说太宗功业,赞颂得体,后半感慨时事,又沉郁悲凉。回望太宗“指麾安率土,荡涤抚洪炉”的文治武功,多么显赫!而今却危机四伏、难以为继。其诗以“寂寥开国日,流恨满山隅”结笔,笔力高古,感慨深沉。
作于天宝十载的《乐游园歌》亦值得重视。杜甫参加了一次春日游筵,按说美景、美食、美酒,换了旁人,当乐不可支,而此诗前半部分写游宴也确是繁侈富华的,然而诗的重心却在后半部分,“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圣朝亦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自叙年华虚度、功业不就的彷徨,抚今追昔,一唱三叹。何以游宴难以消愁解闷?先看清人叶燮之评:
即如杜甫集中《乐游园》七古一篇:时甫年才三十余,当开宝盛时;使今人为此,必铺陈扬颂,藻丽雕缋,无所不极;身在少年场中,功名事业,来日未苦短也,何有乎身世之感?乃甫此诗,前半即景事无多排场,忽转“年年人醉”一段,悲白发,荷皇天,而终之以“独立苍茫”,此其胸襟
之所寄托何如也!㉛
此评乍看有理,实则仍是隔靴搔痒。其实,关键在“圣朝”二句。杜甫天宝六载遭一重创,之后困守长安,苦心钻营,凭借献“三大礼赋”,得以待制集贤院,似有转机,但实际仅得“参列选序”资格,并未实授官职。前途、理想、抱负,仍在虚无缥缈之中,因之忧郁深广,产生一种类似“我爱国,国却不爱我”“我忠君,君却不要我”的被遗弃感。故“圣朝”二句,实激愤语。倒是卢元昌之解说鞭辟入里:“当此春和,一草一木,皆荷皇天之慈,忻忻然有以自乐,独我贱士,见丑圣朝,今幸三赋,得叨宸赏,乃待命集贤,又复逾年,夫岂皇天悯覆、终遗贱士乎?”㉜可谓探骊得珠之论。作于同一年的《杜位宅守岁》后半云:“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年届不惑,而功业无成,将不再以功名拘束,惟纵饮以寻乐。这其实仍是反话,“若自放而实自悲也”㉝。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天宝十一载),乃纪游之作,同行之人高适、岑参、储光羲皆有诗,三人诗只是单纯地写景游览,杜诗则忧愁万端,政治预见性极强,“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表现出对于帝国的忧虑、时局的焦灼、前途的迷惘,目光敏锐,极具政治器识。
2.投赠干谒之作
天宝六载之前,杜甫的投赠诗主要是写给友人,多表现为一种平等的、情感上的交往。天宝三载至五载,杜甫写了大量的诗赠予李白:三载《赠李白》,四载《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赠李白》《冬日有怀李白》,五载《春日忆李白》《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等。这些作品,感情真挚,吐属珠玉,如“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诉说了与李白的友情以及对李白的思念。
天宝六载之后,杜甫的这类诗主要用于投赠干谒,“实用性”增强,对象多为居高位者,表达自己仕进无门的苦闷和抑郁,更重要的是希望对方能够提携自己。如《赠比部萧郎中十兄》、《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赠翰林张四学士》(九载)、《赠韦左丞丈济》、《病后过王倚饮赠歌》(十载)、《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十载)、《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等。其中诗句如“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此生任春草,垂老独飘萍”,凄惨如哀鸿泣血,无助如飘泊秋蓬,刻画出诗人因怀才不遇、坎坷备尝,在生活和心灵上遭受的双重苦闷和悲愁。杜甫在诗中屡屡表示,希望能够得到高位者的眷顾,他甚至一度请托鲜于京兆向杨国忠求助(《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当时杜甫在长安已经七八年,杨国忠其人,他不可能不了解,但仍如此作为,可见其时已窘迫到了极点,他的忍耐也差不多到了极限。怀着困兽犹斗之志,诗人无所顾忌,费尽心机。换言之,他在求官这条路上,已经黔驴技穷了。我们对杜甫此时的作为亦不能过于苛责,如仇兆鳌所说:“少陵之投诗京兆,邻于饿死,昌黎之上书宰相,迫于饥寒,当时不得已而姑为权宜之计,后世宜谅其苦心,不可以宋儒出处深责唐人也。”㉞是为平情之论。
3.忧国虑民之作
天宝初,唐朝延续着开元时期的繁荣,杜甫尚且年轻,少经世事,又不曾受饥寒之苦,因而其诗几乎没有忧虑民生之作。为数不多的困惑,也是诸如“往还时屡改,川陆日悠哉。相阅征途上,生涯尽几回”(《龙门》)之类,顾宸评释:“相阅征途,谓阅视征行之人,往来无尽,而吾之生也有涯,不知尽吾之生,得几回相阅始尽也,此种有劳生之感。”㉟不过是淡淡的哀愁罢了。或是《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四载)中隐隐流露的由于隐居而产生的,对生命何归的怅惘之感,“向来吟橘颂,谁欲讨莼羹?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诸句,精微冲淡,潇洒出尘。
然而天宝六载之后,杜诗开始大量出现忧虑国计民生的作品。他将自己的遭遇与百姓、士兵的疾苦融合在一起,推己及人,其作品既表达了对于国家未来的担忧,对百姓、士兵悲苦生活的深切同情,又反映了自身生活的艰辛不易。《兵车行》(天宝十载)、《前出塞九首》(天宝十载)、《白丝行》(天宝十一二载间)等作品都是如此。《兵车行》前段描写送别的场景,后段通过征夫之口展现兵役之苦,揭示了穷兵黩武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和灾难。《前出塞九首》记叙一个普通士兵出征的各个阶段,借征夫之行,写征人之怨,对统治者“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的穷兵黩武进行批判。《白丝行》则是“为伤才士汲引之难,弃捐之易而作”㊱,核心在“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杜甫沉重深广的忧患意识,正是从这一时期萌发的,并随着时间和阅历的增长,一步步聚拢、凝结、深化,在创作中逐渐凸显出来。这显然与长安困守时期的荆棘与苦难,特别是天宝六载的挫折,密不可分。
(二)从凌云健笔到惨淡经营
杜甫诗歌的艺术手法和风格,天宝六载后,也发生了缓缓的变化。今人每言老杜是现实主义诗人,实则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趋向现实,趋向社会的。在天宝六载前的创作中,杜甫很多时候与其他盛唐诗人一样,诗歌的浪漫气息,随处可见,昂扬、积极、欢快的调子亦不难找寻。但在天宝六载之后,杜甫的作品变得忧伤、忧郁,诗风渐渐转向现实、深沉、婉折,沉郁顿挫的风格初现端倪。
首先,在写法上,天宝六载之前的诗歌受题材的影响,以传统的描写、抒情为主。如《夜宴左氏庄》描写宴会之景,《陪李北海宴历下亭》描绘历下风光,《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描摹新亭景致。然而天宝六载之后,其诗中记叙和议论的运用逐渐增多。一是杜甫经常采用叙事的方式,通过个别人物的命运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现实。刘熙载曾称赞:“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㊲二是在杜甫创作的诸多反映自己心态境遇的投赠干谒诗中,诗人注重自我情感的宣泄。旅食长安期间的作品,杜甫动辄牢骚满腹,他要倾吐块垒,大发议论,直截了当地抒发自己在应制之后的困窘和苦闷,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从头到尾都是不合时宜,与其说是投赠,不如说是内心独白,心灵变奏曲。
其次,在语言上,天宝六载之前多优美精炼之作,“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之五)者颇不乏例。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游龙门奉先寺》),“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语言绮丽精美者亦有,孤立地看“春酒杯浓琥珀薄,冰浆椀碧马脑寒”(《郑驸马宅宴洞中》),或许误以为乃宫体诗。但天宝六载之后,诗人更多的是自铸伟辞,语必惊人。杜甫甚至开始用一些狠重、激烈的语词,令作品展现出瘦硬奇峭的面貌。狠重或有助于宣泄愤恨,而激烈则能增强诗之张力。这不能不说是激切悲愤心态、情感在诗歌语言方面的投射。如“酷见冻馁不足耻,多病沉年苦无健”(《病后过王倚饮赠歌》),“饥卧动即向一旬,弊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特别是《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的“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几句,激切狠重,诗的刺激性增强,张力扩充,是为语言上的奇效。众所周知,杜诗的遣词造句,极得后人赞许。天宝六载后,诗人确实更讲求炼字炼句,而诗句的精微烹炼,会令诗意更精警显豁。可以说,困守长安时期的杜诗语言进入了一个更为用意经营的境地。
再次,在风格上,天宝六载之前的诗歌与诗人的精神风貌一样,总体显得昂扬、奋进。如《今夕行》中高唱的一样,“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无论是宴饮诗,还是思念友人的诗作,基调大多是明朗轻快的,少见后期的“沉郁顿挫”之感。在描写宴会之景时,杜甫说“蕴真惬所欲”(《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这样直接而不受拘束的欢快在天宝六载之后已渐少见。应制举之后,诗歌风格从雄阔、昂扬慢慢地转为深沉、平实,并向着沉郁顿挫的风貌渐次发展。且不论如《兵车行》等直接叙述民生疾苦的诗歌,即使是写游筵的《乐游园歌》,也在前半段铺陈颂扬之后,忽转而悲白发,“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无限低回,郁勃深沉。杜诗中的感慨愈来愈多,自叹今非昔比、讽刺权贵、慨叹人情淡薄,种种感慨,一一形诸笔墨。如《贫交行》(十一载)“见交道之薄,而伤今思古”㊳,以管鲍之交讽刺其时人情冷暖。凡诗鲜不抒情,而杜诗之抒情,厚重有力,力透纸背。这种艺术效果,实非一蹴而就,乃是情志不舒,长期郁结之生活、心理状况渐次造就。
六、诗风变化的关键契机
由上可见,天宝六载前后,杜甫的诗歌在抒写情事、艺术呈现、艺术风格上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把这些变化汇聚起来看,如此集中并且朝着类似的方向发展,一定有着内在的变化契机。究其原因,天宝六载的挫折应是关键因素,它带来的影响不可小觑,实为杜甫诗风变化的嚆矢。下面再以之为关节点,申论这一问题。
制举失败是杜甫一生的转关。这一场“野无留才”的制举在杜诗风格变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一个关键的契机。在唐代,科举对于绝大多数读书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而非正常原因的科举失败带来的打击显然更令人难以接受。正是这次经历,使得杜甫第一次比较清晰地认清了号称盛世的唐帝国的政治腐败,权臣欺君罔上,士林噤若寒蝉。折翅饮恨的杜甫不得不谋划今后的出路。虽然家道败落,生活陷于困顿,杜甫仍不忍放弃家族世代为官的传统、济世佐君的理想,他始终对做官怀有一种异乎常人的强烈渴望。他虽厌恶权贵,却又不得不谋求权贵的汲引提携。痛苦激发了诗人的创造力,情绪的起伏波动令诗中的叙事、议论明显增多,他喋喋不休地叙说自己的境况,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平之鸣,诗风遂转向深沉、郁勃。
制举带来诗人生活境况的变化:从放荡齐赵到旅食京华。天宝六载之前的杜甫,在吴越和齐赵漫游,留存下来的诗作主要是游历名山大川、结交名士、宴会赋诗。杜甫凭借卓颖的才华,足以应付这种生活并轻松取得旁人的称赞,获得自身的满足感。这一阶段的杜甫是相对惬意的,反映在作品中,诗歌风格就显得明快。而长安是当时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权贵云集,等级分化也十分显著,杜甫作为一个家道中落的小官之子,也许应制举前别人会因他的才华而赞叹,但是在制举失败后,无身份、无赀财,在长安举步维艰,生活的失意、窘迫直接反映在诗人的作品中,造成诗歌情事、风格的急遽变化。
制举失败加深了诗人对社会的深刻洞察:体味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漫游期间,诗人由于涉世未深,对整个社会的认知还不十分深刻。长安时期,诗人既能近距离观察权贵、官场的真实情况,参透华筵背后的丑恶,又能直接接触到下层的普通民众,体会他们的苦难。通过对上与下、贵与贱、富与贫的透彻洞察,使得诗人对社会有了去皮见骨般的立体、深邃的认知。唐帝国的繁荣表象之下,隐藏的是各种危机,皇帝日益昏聩、耽于享乐,各级官僚阴狠狡诈、上下交征利,而普通百姓却承受着最深切的苦难。由于地位较低,在与上层交游时,杜甫难免遭受白眼、奚落,这也让他更加看清官场的势力和人情的浇薄。亲历阶级差异、贫富贵贱,两相对比,出于对国家的深切关心、君主的无限忠悃,诗人创作了诸多“长太息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艰”的作品,杜诗的批判色彩和讽刺意味也日渐增强。
研究杜诗的嬗变,应基于其生活、境遇、心态的变化。陈贻焮云:“应诏一事,实是转关;此前此后,他判若两人。”㊴诗人不幸诗家幸。苦难是一种馈赠,反过来说,杜诗亦是苦难的结晶。成就杜甫一代诗圣的因素多元,这其中,诗人先天的禀赋、后天的努力必不可少,而苦难的经历,更是重要契机。傅璇琮认为:“杜甫旅食京华十年,正是从这些现实矛盾的日益深化、社会危机的愈加严重中逐渐提高认识,并锤炼其诗笔的。从这个意义说,李林甫导演的这一次天宝六载制举试的阴谋,对诗人杜甫来说倒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㊵此论很艺术,亦甚辩证。无论是天宝六载前或后,杜甫都是想要仕进济世的,但是当他亲身经历不平、陷于困厄后,更能推己及人、感同身受,他尝试着去贴近社会最底层民众的生活。他甚至对所谓的盛世也产生了怀疑,敏锐地嗅到了隐藏在盛世华筵外表下的危机。
苦难令诗人深沉,崎岖助成诗人的慷慨悲歌。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在天宝六载前后,杜甫诗歌确实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无论是情事、艺术还是风格,都前后有别。这些转变基于生活境遇的改变、阅历的增加,也源于诗人心态的变化。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综合发酵,产生合力,推动杜诗朝着沉郁顿挫的风格基调缓缓发展。诗歌亦是一剂“疗伤贴”,杜甫践行的是“痛苦诗学”“苦难诗学”,日久天长,日渐凝聚,杜诗逐渐形成“沉郁顿挫”的主导风格。而天宝六载的制举,当是杜诗嬗变中的一个关节点,须格外引起重视。
笔者此文,无意于过度强调天宝六载之于杜甫的重要性,导致杜甫诗风转变的因素复杂多元,更与社会大变迁密不可分。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歌者。杜甫所处的开元天宝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大起大落的时代,也是历史的风陵渡口。杜甫身处其间,经历欢乐、兴奋、骄傲,亦有迷茫、孤独、悲怆……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守夜人,亦有它的敲钟者,杜甫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守夜人、敲钟者,他的作品或可喻为那个时代的暗夜的明灯、清晨的钟声。从他天宝六载前后的吟唱,我们分明感受到了些许不同,这些许的变异却有着见微知著的重要意义。天宝六载——杜甫的人生转折,杜诗亦从这里转折。
注释:
①此处借用股市术语,以启发思路,未必允当,读者鉴之。
②⑫⑬⑭㊵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第140页、第144-145页、第152页、第154页。
③莫砺锋等:《杜甫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④⑯㉔㉙㊴陈贻焮:《杜甫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第91页、第95页、第97页、第112页。
⑤洪业著、曾祥波译:《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2-54页。
⑥本文的杜诗系年,一般依据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征引杜诗,亦据此书,下文不再说明。
⑦㉑㉕㉗㉞㊳(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1页、第58页、第64页、第124页、第125页、第116页。
⑧关于杜甫第一次应举,有开元二十三年和二十四年两说,姑且采用赞同者较多的开元二十三年。
⑨⑩(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346页、第1159页。
⑩从开元二十三年到天宝六载之间,杜甫有无参加科举,尚难判断。
⑮天宝初年,皇权、相权(尚有不同派别)、太子等几股势力,斗争险恶。丁俊《李林甫研究》分析:“太子经二狱而不倒,这让李林甫陷入了深深的恐惧当中,于是,朝不保夕的心理使得他自固愈切,开始与安禄山交通,也开始封锁进贤之路。”(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429页)
⑰洪业认为孔巢父也是这次特科的失败者,参看《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第三章。
⑱(唐)元结:《元次山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2-53页。
⑲(唐)杜甫著,(宋)赵次公注,林继中辑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⑳(清)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88页。
㉒参看(清)卢元昌《杜诗阐》卷一。
㉓(明)王嗣奭:《杜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㉖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㉘参看汪篯《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载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㉚(清)张谦宜:《絸斋诗谈》,载《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32页。
㉛(清)叶燮:《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㉜(清)卢元昌:《杜诗阐》,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30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343页。
㉝㉟㊱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第269页、第75页、第319页。
㊲(清)刘熙载:《诗概》,载《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6页。
责任编辑 陈宁
作者:谷曙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100872;俞 凡,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2013级本科生,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