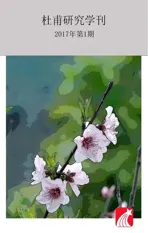杜甫《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创作时地考辨
2017-04-22孙微
孙 微
杜甫《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创作时地考辨
孙 微
关于杜甫《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的创作时地,宋以来的旧注多有失误,如赵次公将此诗编于潭州诗内,黄鹤以为是杜甫由秦州至同谷途中道经两当所作,黄生又主张将此诗编于成都诗内等等。当代学者李济阻等又提出此诗为杜甫赴蜀途中访两当所作,其说亦有失误。此诗应为杜甫寓居同谷期间游历栗亭时顺路前往两当所作,杜甫于艰苦困顿之中仍不避路远,坚持前往两当县吴郁故宅表达自己极端愧悔自责之情,体现了他笃于情义的敦厚性格及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尚情操。
杜甫 《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 同谷 栗亭
杜甫《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诗云:
寒城朝烟澹,山谷落叶赤。阴风千里来,吹汝江上宅。鹍鸡号枉渚,日色傍阡陌。借问持斧翁,几年长沙客?哀哀失木狖,矫矫避弓翮。亦知故乡乐,未敢思宿昔。昔在凤翔都,共通金闺籍。天子犹蒙尘,东郊暗长戟。兵家忌间谍,此辈常接迹。台中领举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杀无辜,所以分白黑。上官权许与,失意见迁斥。仲尼甘旅人,向子识损益。朝廷非不知,闭口休叹息。余时忝诤臣,丹陛实咫尺。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行迈心多违,出门无与
适。于公负明义,惆怅头更白。
吴侍御,即吴郁,排行十,凤州两当县(今属甘肃)人。天宝中,为雍县尉。至德二载,在侍御史任,因为民辩诬,取忤朝贵被谪。上元二年放还,居成都,杜甫往访之,有《范二员外邈吴十侍御郁特枉驾阙展待聊寄此作》诗。据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永泰二年十月,吴郁为青苗使在蜀。大历中,迁金部员外郎。杜甫任左拾遗时,吴郁任侍御史,同在凤翔行在供职。当时为肃清叛军间谍,抓捕了一些人,吴郁为其中的良民理冤,得罪上司被贬谪。杜甫时因疏救房琯忤旨,正遭困境,对于吴郁的遭贬,未能仗义执言,深感愧疚,自觉有负于明义。乾元二年,诗人经过吴郁故宅时,想起几年前的这件事,遂作此诗。
杜甫由秦州至同谷纪行诗的时地班班可考,只有这首《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的创作时地歧见纷纭,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梳理,以厘清杜甫作此诗的真正时间和地点。
一、旧注对《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创作时地的歧见
宋本《杜工部集》将此诗编于《发秦州》之前,《万丈潭》之后。然而赵次公却不同意这种编次,其曰:
此篇旧在秦州诗下,合迁入于此。题盖言两当县人吴侍御宅在江上,而身谪长沙,不得去也。诗云:“借问持斧翁,几年长沙客?”正言其客于潭州矣。……首四句以秦地之时候景物,言其宅在两当之江上,用引下段“亦知故乡乐”之句。自“鹍鸡号枉渚,落日傍阡陌”,又以楚地之时候景物如此,而乃在长沙也。
又曰:
旧本见题是‘两当县吴侍御江上宅’,故置之发秦州往同谷间,然亦自非所由之路矣。
今按:赵次公将此诗编入大历四年潭州诗内,实是出于对“几年长沙客”的误解所致,此句杜诗明显是用贾谊贬谪长沙之典,不一定是确指吴郁之贬所;赵次公又将此诗下文所云“枉渚”坐实为长沙地名,遂将此诗移编于潭州诗内,更是错上加错。不过他指出由秦州至同谷并不经过两当倒是没错。王嗣奭《杜臆》曰:“时侍御尚在长沙,公过其空宅,思及往事而赋此。”所论良是,此后王嗣奭此说成为理解此诗的通行之论,然他将“长沙”坐实为吴郁贬所,亦有疑问。此后的杜诗学界几乎没有赞同赵次公之说者,不过赵次公将此诗编次随意移置的做法对明清的杜诗学者仍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清初的黄生即又主张将此诗编于成都诗内,其曰:
编诗者因题中“两当县”字,遂次于秦州诗后,此可笑也。吴是此县人,故书其籍,而“江上宅”自在成都,时亦携家寓蜀者,故云:“借问持斧翁,几年长沙客?”“亦知故乡乐,未敢思宿昔。”此其以两当为故乡,而身在谪籍亦明矣。然则编诗者止看题而不看诗耶?此诗宜与《范员外藐吴侍御郁特枉驾》诗相次。
可见黄生是因为注意到杜甫成都诗中有《范二员外邈吴十侍御郁特枉驾阙展待聊寄此作》一诗,遂又以为《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应作于成都,然而此说于诗意难以契合,既然吴郁“身在谪籍”,远贬长沙,为何又忽然跑到成都来了呢?这些问题黄生都不能圆满地解释,故其说实属误解,不能采信。
黄鹤曰:“两当县,在凤州城西。凤州亦西至成州二百七十里,殆是公自秦西至同谷时,道经两当,故作此诗,乾元(二年)十月也。”应该指出的是,黄鹤终于改正了赵次公的错误,将此诗大致归入由秦州至同谷之间。然而黄鹤并未详考秦州、同谷、两当的相对位置,其“道经两当”之说亦不准确。朱注:“《旧唐书》:凤州两当县,汉故道县地,晋改两当,取水名。《水经注》:两当水,出陈仓县之大散岭西南,流入故道川,谓之故道水。”今人李济阻等《杜甫陇右诗注析》指出,同谷在秦州西南,两当在秦州东南,三地相距甚远,杜甫自秦州赴同谷,是经西和县折向西南,根本不经过两当,所论良是。若无李济阻等地方学者通过实地考察予以纠正,旧注中的此类明显失误很难被人察觉。然而黄鹤此说仍然被许多明清杜诗注家所沿袭,如仇兆鳌《杜诗详注》曰:“殆是公自秦西至同谷时,道经两当,故作此诗。盖乾元二年十月也。”但是仇兆鳌、浦起龙等人虽然接受了黄鹤的“道经两当”之说,却又矛盾地均将此诗编于秦州诗之最末、《发秦州》之前。浦起龙对此解释曰:“此系发秦州后所经,但不得混入纪行诗内,故先编此。”也就是说,虽然《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肯定作于《发秦州》之后,但是为了保持秦州至同谷十二首纪行诗的完整独立性,注家只能把这首诗的编次提前,这实际上等于搁置了此诗的创作时地问题。这样一来,《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便成为秦州至同谷诗编年中的一颗久未排除的地雷,以至后人议论纷纭,迄无定论。
二、今人对《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创作时地的推测
李济阻等人纠正了黄鹤、仇兆鳌关于此诗作地的失误之后,进而提出此诗是从同谷赴蜀途中专门去两当县看望吴郁故居所作,其云:
杜甫离开同谷以后,是从现在的徽县、两当交界处(嘉陵江与永宁河、田家河会合地——合河口)沿嘉陵江而下入蜀的。这儿离吴郁江上宅(现在甘肃两当县西坡公社境内)较近,诗人很可能是从这里专门看望吴郁去的。(从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考虑,诗人在秦州居住期间专门去两当的可能性极小)。
因此,李济阻等认为,这首诗似应定为“赴蜀途中访吴郁两当故居”的作品。另外,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又提出:
两当在今两当县东三十五里,西北至秦州数百里,自不当列入秦州诗无疑;然杜翁自秦州至同谷,取上禄道,已见前考,绝非经两当,故鹤注亦非。盖公至河池,未即时南行入蜀,而曾因事枉道先东至两当耳。河池、两当皆在散关入蜀驿道上,详《通典所记汉中通秦州驿道》篇,故此诗当编《木皮岭》之后。
此说与李济阻等人的说法较为相似,似是受到了李济阻的影响。吴郁嘉陵江边的“江上宅”遗址在今两当县西坡乡琵琶洲附近。因此从距离来看,无论是从徽县、两当的合河口还是河池的入蜀驿道,去两当县西坡乡都很近,所以杜甫由同谷入蜀途中前往两当县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然而李济阻等人将距离远近作为考量《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创作时地的唯一标准,未能综合考虑杜甫在同谷生活及创作的实际情况,似仍有不妥,故有继续探讨之必要。
另外,仍有学者坚持黄鹤、仇兆鳌的由秦州去两当之说,只是对旧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订,如徽县学者孙士信认为,杜甫去两当寻访吴郁故宅是在寓居秦州期间,此行在发秦州之前。此说的主要理由是,各种版本的杜集中此诗都次于《秦州杂诗》之后。高天佑亦同意孙士信此说,并提杜甫出此行的具体路线应是:秦州—皂郊堡—娘娘坝—李子原—徽县高桥乡—太白乡—两当(今杨店乡)。然而据《九域志》,秦州至同谷265里,秦州至两当约500里,杜甫光是由秦州至同谷这段路程就艰苦卓绝地走了月余,则由秦州往返更为偏远的两当应不会短于这个时间,而杜甫从乾元二年七月末至十月初,前后在秦州也就住了三个月左右,若在此期间还要花一两个月往返两当,实在不太可能。

三、《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创作时地平议
综上可见,除了赵次公、黄生因对诗意的理解有误故而得出错误结论之外,由宋迄清的杜诗注家均将此诗编于秦州至同谷纪行诗中,殊不知杜甫至同谷的路线并不行经两当县。然而悬揣古人如此编次的主要理由,恐怕还是诗中表现的时令。《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开头曰:“寒城朝烟澹,山谷落叶赤。阴风千里来,吹汝江上宅。鹍鸡号枉渚,日色傍阡陌。”从诗中描写的景物来看,无疑是深秋初冬之景。而杜甫在秦州至同谷纪行诗《寒硖》《石龛》诗中已经有“况当仲冬交”、“仲冬见虹霓”之句。因此,对杜诗中时间季节信息颇为敏感的注家感到此诗中“山谷落叶赤”之景似乎比《寒硖》《石龛》的节令还要早一些,便只好将此诗编于秦州诗之最末、《发秦州》诗之前了。其实杜诗注家在这里明显过于拘泥了,《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中的景物既可以说是深秋,也可以说是初冬,只从景物所表现的时令来看,实在与其他纪行诗难以区分先后。而当代学者李济阻等人在指出旧注的失误之后,又提出此诗应移到杜甫由同谷入蜀纪行诗中的新说。学界对这种说法目前尚少有讨论者,笔者以为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从纪行诗的角度看,杜甫由秦州至同谷作纪行诗有十二首,由同谷至成都纪行诗亦为十二首。若非巧合的话,这两组诗应是诗人有计划的创作,当不可增添移易。在宋本《杜工部集》中,于《发秦州》题下原注曰:“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县纪行十二首。”《发同谷县》题下原注曰:“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陇右赴剑南纪行。”这些题注若真是所谓“公自注”的话,似乎也可佐证我们上面的猜测。而《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却并不属于两组纪行诗中,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李济阻、严耕望等先生将此诗随意移动到第二组纪行诗之中,就打乱了两组纪行诗在数量上的整齐性。若再考虑到此诗应不晚于《发同谷县》,如此一来,此诗便只能作于寓居同谷这短短的二十多天之内了。曹鹏雁先生早就提出杜甫由栗亭赴两当县的可能性。⑪刘雁翔先生也已经指出,杜甫过访吴郁宅,只能在寓居同谷、栗亭时。⑫曹、刘两位先生之论,可谓先得我心。
第二,李济阻等人提出的杜甫从同谷入蜀途中前往两当县的说法,从距离来看虽然确实较近,然而杜甫此行入蜀,“首路栗亭西”之后,便须折而向南,此时距两当县虽比在同谷时近些,但若真的趁此时机去两当的话需要折而向西北,与目的地正好反向而行。杜甫这次由同谷出发,“辛苦赴蜀门”,有行李家小的拖累,有衣食寒窘的促迫,故出发后在途中专程折返前去两当,这在情理上是不易说通的,所以李济阻先生这种推测尚需斟酌。
第三,从时间来看,杜甫《发同谷县》题下原注曰:“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陇右赴成都纪行。”十二月已属于季冬,这与《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诗中描绘的深秋初冬景象已难相符,故主张杜甫入蜀初期前往两当县的说法在时间上亦考虑不周,存在明显瑕疵。
总之,李济阻等人提出的新说尚存不少问题,难以自圆其说,恐非定论。不过李济阻先生已经对自己的说法进行过反思,其云:
我们在撰写《杜甫陇右诗注析》时也选择了自同谷入蜀绕道两当的说法,然而书出版后反复琢磨,觉得仍有两个疑团:第一,杜甫沿木皮岭至飞仙阁间蜀道赴成都,这条路上任何一点距吴郁故宅也在一百里以上,路途中绕那么大的弯子去访友,总是不大便当,况且诗人是举家前往呢,还是寄家小于客舍只身过访呢?第二,杜甫是十二月一日离开同谷南下的,但《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劈头就说:“寒城朝烟淡,山谷落叶赤。”尽管两当地气较同谷略暖,可是寒冬腊月也难见到“山谷落叶赤”景象。⑬
李先生敢于自我质疑、自我否定的精神令人钦佩,这也说明杜甫入蜀途中由合河口前往两当之说实难成立。此后梁晓明、曹鹏雁、刘雁翔、孟永林等先生陆续提出,杜甫曾有栗亭之游,栗亭属于徽县,距两当县不远,则《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应作于栗亭之游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杜甫前往栗亭的时间,目前仍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是在杜甫寓居同谷期间,如嘉庆《徽县志》曰:“杜公祠,在县西三十里栗亭镇,唐杜甫居同谷,避暑栗亭元观峡。明御史潘公按部栗亭,梦甫,乃为建祠。”“杜甫钓台,元观峡内,唐乾元中,甫居同谷过夏,栗亭垂钓于此。”按,杜甫于乾元二年十月发秦州,至十二月一日离开同谷,故县志所谓杜甫曾去栗亭过夏避暑云云明显有误,不过其中称杜甫是寓居同谷期间前往栗亭之说则值得引起注意。另一种说法认为是杜甫由同谷入蜀时途经栗亭,如梁晓明《杜甫自秦州入蜀行踪补证》说:“杜甫乾元二年(759)十二月一日从同谷出发,东入栗亭并寄家眷于此地,然后单骑东去两当探访吴郁不遇返回后,即率全家开始了赴蜀之行。”⑭其依据当是杜甫的《木皮岭》:“首路栗亭西,尚想凤凰村。”按,以上这两种说法本来难以区分正误,不过杜甫除了在《发秦州》和《木皮岭》中提到栗亭外,还曾作《题栗亭》诗。咸通十四年(873)成州刺史赵鸿《栗亭》诗曰:“杜甫栗亭诗,诗人多在口。悠悠二甲子,题纪今何有?”注云:“赵鸿刻石同谷曰:工部《题栗亭十韵》不复见,盖鸿时已无公诗矣。”⑮如前所述,杜甫由秦州至同谷及由同谷至成都纪行诗均为十二首,数量非常整齐,故《题栗亭》明显不属于这两组纪行诗,则其只能和《万丈潭》等诗一样属于寓居同谷期间之作。同样地,《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亦应系杜甫由同谷去栗亭、两当县考察时所作,而非作于入蜀途中。如此来看,《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亦只能置于两组纪行诗之间,次于《发同谷县》之前为妥。
综合以上各方面情况,《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应作于杜甫寓居同谷期间。然而诗人在同谷的生活极为困顿,《同谷七歌》甚至给人以“惨绝人寰”之感,那么处于如此境况之中的杜甫是否还有可能前往两当县探访吴郁故宅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杜甫在此期间仍然曾去栗亭游览,栗亭距两当县较近,则杜甫顺路前往两当县的可能性极大。不过由于对杜甫困居同谷的印象过于深刻,所以才有学者反对《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作于此时,甚或有人提出此诗只是悬想怀人之作,因为诗人似乎毫无必要前往一座遥远的空宅,⑯殊不知这正是杜甫人格的伟大之处,孟永林先生说:“杜甫毅然的两当之行,其实是杜甫人生中非常人所能理解的一次抒情行为”,⑰此言得之。杜甫寓居同谷期间生活虽极为困顿,前往两当县吴郁故宅也并不顺路,需要经过长途跋涉,但他仍坚持去造访老朋友那座遥远的江上空宅,种种不同寻常的情况正好表明,诗人是多么重视此次两当之行,此举体现了杜甫对吴郁被贬事件的深深自责与愧悔,可见他在《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中“至死难塞责”“于公负明义”云云并不是什么客气话,而是发自心底的不安与愧疚。虽然吴郁被贬时他自身亦处于被肃宗冷落排斥的境遇之中,但杜甫却并不能因此原谅自己,所以在故友尚在贬所的情况下,他仍克服诸般困难和阻碍,不顾一切、步履踉跄地来到吴郁的江边空宅,细语倾诉衷肠,真诚道歉忏悔,从中体现出杜甫笃于情义的敦厚个性与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尚人格。这正是隐藏在《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创作时地问题背后的丰富隐情,值得后世读者仔细品味,故特为之钩沉发覆,希请方家批评指正。
注释:
①(宋)赵次公著,林继中辑校:《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修订本)己帙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9、1450页。
②(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八引,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69页。
③(清)黄生:《杜诗说》卷十一,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412页。
④⑦李济阻、王德全、刘秉臣:《杜甫陇右诗注析》,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页、第305页。
⑤(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69页。
⑥(清)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一之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3页。
⑧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38页。
⑨孙士信:《杜甫客秦州赴两当县考》,吕兴才主编:《杜甫与徽县》,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
○
1
0高天佑:《杜甫赴两当县路线杂考》,《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239页。
⑪曹鹏雁:《杜甫由同谷县栗亭赴两当县吴郁宅的可能性》,聂大受主编:《杜甫流寓陇右1250周年纪念专刊》,天水杜甫研究会2009年,第106-110页。
⑫刘雁翔:《杜甫陇上萍踪》,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26页。
⑬李济阻:《走出陇右及其他——杜甫陇右行踪通考系列论文之五》,天水师专中文系编:《杜甫陇右研究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⑭梁晓明:《杜甫自秦州入蜀行踪补证》,吕兴才主编:《杜甫与徽县》,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1页。
⑮(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页。
⑯李子伟:《杜甫客陇右赴两当县考辨》,聂大受主编:《诗圣与陇右:天水杜甫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页。
⑰薛世昌、孟永林:《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9页。
责任编辑 张芷萱
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杜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孙微,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5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