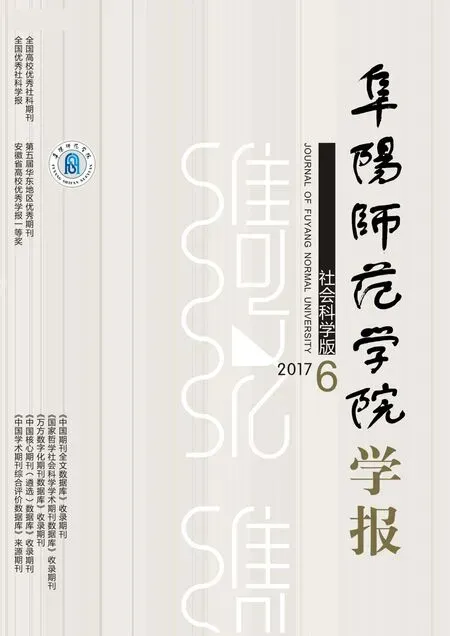等待“正名”的“西方之‘道’”——以美国为例
2017-04-15蔡觉敏
蔡觉敏
等待“正名”的“西方之‘道’”——以美国为例
蔡觉敏
(天津外国语大学 国际传媒学院,天津 300221)
上世纪以来,伴随着《道德经》译介的盛行,民间出现了大量与“道”相关的大众读物,其所倡扬的精神被称为the Tao of the West(西方之“道”)。对此,赞扬肯定者有之,猛烈抨击者更不乏其人,但正反双方都没有进行详尽描述和分析。从分析可发现,这种“道”肯定了传统道家智慧,与西方学界对中国道家的诠释相通;但是,它被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不是正宗的“taoism”,而只是“玩偶”,其“道”的内涵和存在的合理性也受到质疑。这一东方文化的西方传播现象,西方之“道”只收获了西方学界的单方面反应,可以说,这一文化现象亟待“道”的宗主国中国的哲学家为之“正名”。
道家;道教;西方之“道”
上世纪以来,“道”在西方由学者案头向大众蔓延,如刘笑敢先生所言,道家“花开他乡”,在美国尤盛,它“与六十年代的禅宗相类”[1],并形成了“西方之‘道’”(the Tao of the West)。 这种兴盛固然得到了一部分学者的欣赏,更多则是批评和责难,但正反双方均是略述其观点而不言其所以然。以此,笔者以其中影响最大、最能够体现西方之“道”的大众读物为对象文本,研究西方之“道”的内涵、流行原因及尴尬境遇,希望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并为之“正名”。
一、通俗读本中的西方之“道”:主张无为、体道、整体思维
笔者参考了销售排行榜,对畅销大众读物的高频词和读者反馈进行了量化分析(限于篇幅不列出),可知读者所欣赏者集中于“生活智慧”或“思维方式”方面;以此为切入点,结合文本具体内容可知,“智慧”的具体内涵往往是主张“无为/接受”的人生态度,而改变人生态度的关键即在于改变思维方式,从视自我和他者为二元对立转变为与对象形成“平衡”的“和谐整体”。
以这种智慧和思维方式指导生活,有人提出了“follow Tao(体道)”的生活模式。“Tao”几乎成了万灵药,被与不同职业不同行业结合起来,指导人们从追求物化自我和抽象义理转而为在现世生活中修道、体道、悟道并最终与道合一。另一方面,“follow Tao” 看似容易,但它是要改变以往追求物欲名声的人生模式,要有反叛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勇气,而这与美国文化中提倡的个性相吻合,这也促成了它的流行。有学者认为,《道德经》之所以流行,是因为:“那些疏离西方理性主义的人,在《道德经》中发现了对分析理性的否定与对直觉思维的肯定。另外一些人,在返回自然的名义下,从中找到了对社会传统和价值判断的否定。”[2]西方之“道”受到欢迎的原因,与此完全同理。
“follow Tao”的生活中,“道”完全是引导人积极地面对生活:“与等待别人给我们发号施令不同,‘道’要求我们为自己服务,顺从它的行为和沉思冥想……我们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从竞争走向合作,与最小的个体到最大的社会组织间都存在的自然规则一起律动。”[3]可见,这是一种仔细体察万事万物规律基础上的“无为”(不妄为)。这与比较哲学家安乐哲先生所言神似:“人类在求道之途中,拥有一种主动力量……我们的求道之途就包括通过把握这一发展过程中更多流动、不确定的机遇,而从生活经验获得有效的判断和调整。”[4]柯恩(Livia Kohn)的一书中,也多见以庄子精神释放人的生命力量。德国哲学家也认为:“对于今日之思想来说,道教是一副全然有效的令人净化的治疗药物……对于欧洲新思想来说,《老子》有着进行链接的某些可能性。”[5]
以此,西方之“道”是一种认识人生和处理事物的独特方式,帮助人们越过繁琐的西方逻辑分析和热衷对抗的二元论,从充满主观意志的“自我”中摆脱出来,在愉悦与自由中释放潜能。其对“道”的认识与哲学家们的严谨诠释不“约”却“同”,可见其并非想当然的呓语。但是,这种西方之“道”受到了许理和(Erik Zürcher)、卜松山(Karl-Heinz Pohl)、柯克兰(Russell Kirkland)等的尖锐抨击。
二、宗教学者眼中的西方之“道”:西方文化的“玩偶”和新“殖民主义”产物
自“道”走向民间,与它的迅猛发展相伴的,是不断出现的否定声音,笔者择其要者而言之。
许理和是著名的佛教学家,但他认为西方之“道”只是在扭曲和误读老子,对将道家与生活联系起来的大众行为,他评价说:“道家的‘整体论’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应该被经理和工业资本家所运用。虽然这看起来使我们发笑……从60年代末期‘东方神秘主义’浪潮涌起,出现了关于《老子》的‘通俗而不乏荒谬’的出版物。”[6]笔者认为,结合许理和自身对老子的认识可知,他对这一文化现象的否定与其强调老子修炼的一面相应。可佐证之一是,同是通俗读物,强调修炼的布洛菲尔德的《老子》就被肯定。
许理和对西方之“道”仅是点到而已,卜松山的态度更为鲜明,他在《时代精神的玩偶──对西方接受道家思想的评述》中说:“一如二十年代那样,‘道’又被当作拯救所谓物质泛滥而精神空虚的西方文明之灵丹妙药。这种庸俗化的道家学说成了‘新时代运动’的核心‘哲学’。”其倾向与许理和相近,但具体观点有所不同,例如他抨击卡普拉(Fritjof Capra)的,但肯定,认为“pooh”(即“朴”)具“无为”“自然”特点。这当与卜松山认为“老庄”特点是“朴”有关,他之否定西方之“道”是因为大众对“道”的理解不够严谨、过份随性:“道家开放性中蕴含的多功能性使其具有吸引力,但也往往使得道家成为时代精神的玩偶。”[7]
这种对“道”的“正宗”的强调,在柯克兰和康加迪(Louis Komjathy)那里表现得更为鲜明,两位学者基于其对中国道教的学术研究,构建了他们认为的“正宗道教”,以“正宗道教”为标准而强烈否定西方之“道”。康加迪提出:“无数人都在剽窃《道德经》,包括。新时代的话语共同体和长青哲学将它当成传统的普世智慧。”[8]在“Common Misconception Concerning Daoism”中提出大量畅销文本等都只是对道的误解。与之近似,柯克兰在“Teaching Daoism in 1990’s”中提出,大众将“道”包装成一个普遍的和没有“文化传统”的救世主义,抛弃了道教中应有的宗教维度,只不过是美国文化对中国“道”的殖民。但是,通过前文所述文本研究可知,这些读物中虽有可与西方文化类比之处,而其真具西方精神的词语和“个性/自我”相对数量并不多,且其中一部分“个性/自我”只是强调以美国注重自我个性的精神来坚持道家式自我。
许理和认为西方之“道”缺乏“修炼”,卜松山认为缺乏学术性,柯克兰康加迪则指责其不“正宗”。这几位著名学者或从宗教角度出发,或从科学性出发,强调“正宗”,但是,真有“正宗”吗?
三、孰为“正宗”:Religious Taoism(仪式道教)/哲学道教(Philosophical Taoism)
上述学者否定西方之“道”,因其没有修炼仪式等,不是“true Taoism”。但是,以“道”的宗主国中国的传统而言,修炼科仪是否“true Taoism”的必要条件?
在大部分西方宗教学者看来,“修炼”或“仪式”才是“正宗道教”的本质和判断标准,但“true Taoism”的争讼仍一直未停,因其本就包罗万象极其复杂。汉时道教即既有政治之道又有修炼之术;六朝刘勰《灭惑论》称:“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道安《二教论》也说:“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无为,二者神仙饵服,三者符箓禁厌。”不一而举,“道”本就有多重表现形式,“上标老子”和“老子无为”或是所谓文人之“道”都是“道”之一流,为无为、弃名利、同生死、轻去就等当然也是“道”。如果说,“道”文化是一条大河,西方之“道”即是与其中的这些思想即道家的影响有关,即令其与另一个部分即仪式的联系很少,我们也无法以此否定它与道文化整体的联系。
与对“道家”的否认相比,更为吊诡的是,道教学者一方面多指责近代以来太过重视“精英”的儒家,这种传统使得非精英的道教被“蒙蔽”,但他们自身又在无意识地维持精英传统——认为正统学术研究才能够担当起解释和传承“Taoism”的任务,大众化的西方之“道”则无甚价值甚至只有破坏作用。但在中国文化发展中,思想并非只能在精英层:“和依赖著述而传播的经典思想不同,这些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传播……通过各种最普遍的途径,比如观看娱乐性演出……大众阅读(如小说、选本、善书以及口头文学)等等。”[9]这种大众传播固然并不那么纯粹,但是并不会因其“杂交”而失去生命力,相反,有可能是得以更鲜活地表达与发展。柏夷先生(Stephen Bokenkamp)曾说,道教学界太执着于所谓的“纯粹”而对“杂交”抱以太多的偏见,笔者窃以为,宗教学家对大众化的西方之“道”的否认,也与此惯性有关。
再次,西方之“道”在现实生活中“热”,但在学界多遇“冷”。这种尴尬一方面与“道”(家)研究的西方处境有关,方破(Paul Fischer)认为,在宗教领域,宗教人类学者接受他们研究对象的偏见,因而丧失了“旁观”者的立场,大部分宗教系关注作为宗教的道教;同时,“哲学道家没有人发言……大部分哲学系不会顾及非西方的哲学”[10]。研究道家的西方学者本就有限,且其重点多在玄远的义理而不在于西方之“道”这一世俗现象,对比之下,道教学者从宗教角度对西方之“道”的苛责显得分外高亢。遗憾的是,在这些“他者”纷纷苛责西方之道时,在道家宗主国中国,西方之“道”也没能得到足够的关注和回应,更遑论支持,也无人站在“道”的角度来鉴定和判断其是非对错(如果它真能被判定的话),以至于如克拉克(Clarke)和Siegler E 所言,对西方之“道”的判断缺少“真正的发言人”,最终也就是Solala Towler所说,不知道“谁代表道家发言”。
以此,“道”的痴迷者如美国著名作家厄秀娜等的诉求不能被忽视,学界“不要仅仅因为研究者假定它缺乏真实性就对它作出判断或对现代的宗教现象视而不见。比较恰当的做法应当是,鉴别它对历史资源的阐释,将它置于相关的背景下对它进行评估”[11]。尴尬的西方之“道”,固然需要西方的发声,但是,它是“玩偶”,还是发展中的“新变”,这亟待“道”的宗主国中国的道家学者作为“真正的发言人”和“代表”为之“正名”。
[1]Louis Komjathy 康加迪(2009),“misconceptions concerning Daoism”, [Online] Available:http: //media.bloomsbury.com/rep/files/9781441168733_commonmis-conceptions_dao isttradition.pdf(03/17/2014)
[2]Livia Kohn Michael Lafargue. Lao-tzu and the Tao-te-ching /[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2.
[3]Dreher D E. The Tao of Inner Peace[J]. Tao of Personal Leadership, 2000,4
[4]安乐哲 郝大维. 道不远人:比较哲学视域中的《老子》[M].何金俐,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68.
[5]汉斯·格奥尔格·默勒.《老子》和道教思想对德国新哲学的启迪[J].张思齐,译.中国道教, 2008(3):19-23.
[6]许理和, 张海燕. 东西方的老子观[J]. 国外社会科学, 1993(9):34-38.
[7]卜松山, 赵妙根. 时代精神的玩偶──对西方接受道家思想的评述[J]. 哲学研究, 1998(7):36-46.
[8]Komjathy L. Tracing the Contours of Daoism in North America[J]. Nova Religio, 2004, 8(2):5-27.
[9]葛兆光. 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14-15.
[10]Fischer P. The Creation of Daoism[J]. Journal of Daoist Studies,2015:8.
[11]何乐罕.道教环保主义在西方:厄秀娜对道教的接受与传播[M]//刘笑敢.道教与生态.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325.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7.06.06
B712
A
1004-4310(2017)06-0028-03
2017-10-12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当代美国道教学研究”(16YJA730001)。
蔡觉敏(1975- ),女,湖南岳阳人,博士,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汉学、宗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