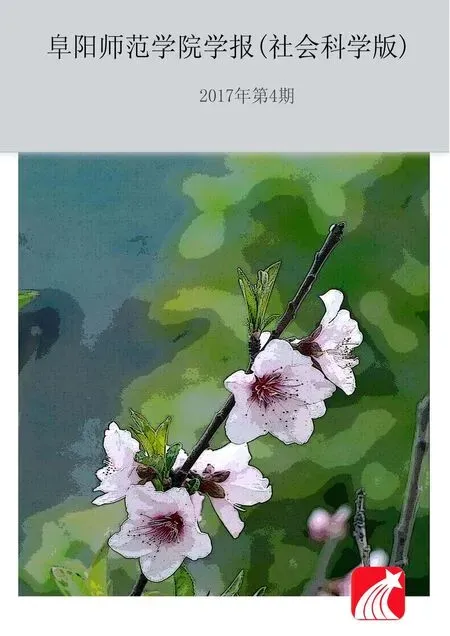晚唐张乔诗歌的语言艺术与美学风格
2017-04-15任冬青
任冬青
晚唐张乔诗歌的语言艺术与美学风格
任冬青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张乔是晚唐池州诗人,《全唐诗》存其诗两卷共171首。他的语言艺术与美学风格相互生发,多变的语言艺术生成四种美学风格。清雅明净的语汇追求和“以文为诗”的语言技巧构建出清雅明净的美学风格;对先贤诗歌“夺胎换骨”式的借鉴与“曲笔传情”的典故运用,形成婉曲流逸的美学风格;瘦寒孤冷的意象选择与冷色调的色彩描写,烘托出瘦寒孤冷的美学风格;张乔边塞题材的诗歌创作,营造了悲怆奇崛的美学风格。
张乔;晚唐诗;语言艺术;美学风格
张乔,字伯迁,安徽池州人,“九华四俊”“咸通十哲”之一,《全唐诗》存其诗两卷共171首,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参加京兆府解试,凭《月中桂诗》名动京城。乔诗虽产在晚唐,却有清新骚雅之音,偶有振聋发聩之句,他的语言艺术与美学风格,代表了继贾岛之后,大批苦寒诗人呕心沥血的创作过程与实际成果。张乔诗歌的美学风格总体上呈现以下四种范式:即清雅明净之美、婉曲流逸之美、瘦寒孤冷之美和悲怆奇崛之美。
一、清雅明净之美
张乔是晚唐一介苦寒书生,有着传统文人先验而自觉的审美追求,即对“诗骚传统”的传承与发扬,尽管每逢乱世,诗人们总有些低迷之音,但是诗骚传统从未断裂。这种传统表现在诗歌上,则是一种清雅明净的美学风格。张乔诗歌清雅明净的美学风格由以下两种因素构建而成。
第一,张乔追求清雅明净的语汇。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评其诗:“诗句清雅,敻无与伦。”[1]元辛文房《唐才子云》评其诗:“诗句清雅,迥少其伦。”[2]着重点都在“清雅”二字,试看《曲江春》:
寻春与送春,多绕曲江滨。一片凫鹥水,千秋辇毂尘。
岸凉随众木,波影逐游人。自是游人老,年年管吹新。
首颔二联的“曲江滨”“凫鹥水”“辇毂尘”和颈尾二联的“随众木”“逐游人”“游人老”“管吹新”都能成一幅独立的画面,这就使平淡无奇的画风生出清雅明净之美。在春日曲江,这个充斥着寻春与送春的时空里,人们哀而不伤,清雅明净的风景与无可奈何的惆怅夹杂丛生,“游人”的重复使用增强了诗歌回旋跌宕的抒情效果。王镇远评张乔“为诗勤苦,能于炼饰中见清新浅切之致”[3],如《隐岩陪郑少师夜坐》有“砚磨清涧石,厨爨白云樵”之句,磨砚、厨爨本是日常行为,但张乔借来“清涧”“白云”语汇,造语雅致。张乔诗中,风、花、雪、月、云、石、竹、松、钟等雅致语汇频频出现。仅云意象就有65次,月55次,风40次,花23次,雪18次。典例如下:
竹风山上路,沙月水中洲。(《岳阳即事》)
武林春草齐,花影隔澄溪。(《寻桃源》)
白雪无人唱,沧洲尽日闲。(《郢州即事》)
断虹全岭雨,斜月半溪烟。(《思宜春寄友人》)
第二,张乔“以文为诗”的语言技巧构建出清雅明净的美学风格,即将散文化的笔法引入诗歌,使得诗歌在意脉上自然衔接、明白如话,避免了芜杂的叙述,具体到字词上,则是动词和连词的巧妙映衬。
动词类如下:
调角断清秋,征人倚戍楼。(《书边事》)
穷荒回日月,积水载寰区。(《送棋待诏朴球归新罗》)
车舆穿谷口,市井响云间。(《北山书事》)
连词类如下:
带雪复衔春,横天占半秦。(《终南山》)
落花兼柳絮,无处不纷纷。(《送友人往宜春》)
辛勤同失意,迢递独还家。(《送友人归江南》)
张乔用动词或连词将相邻的名词串联,避免了意象之间的割裂与断层。他的擅场之作《试月中桂》有“根非生下土,叶不坠秋风”之句,格调甚高,胜在“生”与“坠”两动词。同年应试的顾封人也有《月中桂树》一首,曰“皎皎舒华色,亭亭丽碧空”。《唐诗观澜集》对比两者,认为“(张乔)超心炼冶,笔有化工,顾封人作,徒色相耳。冲口而出,不知乃百炼而得,元气淋漓,此岂寻常蹊径?”[4]追求“色相”的顾诗与追求“清雅”的张诗相较,输在气韵。清人谭宗《近体秋阳》还将张乔与许浑作对比:“乔诗高清,突绽漂忽而来,迥出尘外,读之令人风生习习。许浑以才情赡迈,雄视晚朝,每拈一题如泉涌云蒸,视张郎辈,几区区不屑,而不知一种不受烟火之气,飘萧遥越,虽百浑身要不能一得矣。”[5]2766张乔身上的这种“不受烟火之气”,正是其诗歌清雅明净的美学风格的内在源流。
张乔还与致力于恢复风雅的同乡杜荀鹤相友善。张乔在黄巢之乱后隐居九华,于僖宗中和二年(882年)路过扬州,偶遇正要远行入幕府的杜荀鹤。杜荀鹤作《维扬逢诗友张乔》为纪念,其中一句“雅篇三百首,留作后来师”,惹来颇多争议。王运熙说:“雅篇三百首,留作后来师。”乃是杜荀鹤自称[6]。陈贻焮则认为:“雅篇指高雅的诗篇。此指张乔之诗。”[7]汤华泉《张乔考论》也赞同陈的观点[8]71。包括陈友冰《安徽文学史》均认为是杜荀鹤颂扬张乔的句子[9]。笔者从后者观点。张乔在《送许棠及第归宣州》中坦言自己欣赏的创作态度是“雅调一生吟”,“吟”是文人君子之风,是诗人抒情言志的手段,张乔诗中出现“吟”字33次,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也说:“张乔,咸通骑驴之客,吟价颇高。”[10]张乔每每吟诵的都是清雅明净之句,采取“以文为诗”的诗法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幅清雅明净的画面。
二、婉曲流逸之美
钱志熙《唐诗近体源流》称乔诗风格为“清峭隐秀”[11]126。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载:“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12]“隐秀”概念一出,后世诗人们力求在有限言语中尽力涵括无穷的意蕴,成为中国古典美学孜孜以求的目标。张乔诗歌的第二种美学风格是婉曲流逸,这与张乔学习前人写作经验有关,即“夺胎换骨”法,也是张乔诗歌“曲笔传情”的外化特征。
第一,张乔擅长扬弃前人经验和教训,采取“夺胎换骨”法。他在炼字上常常不经意地化用前人成句和意境,善于脱胎,变化无迹。张乔追慕盛唐之风,学习并借鉴李白、杜甫、王维等人的诗歌经验。试看以下三例:
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远适无前期。(杜甫《晓发公安》)
舟楫故人少,江湖明月多。(张乔《送陆处士》)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王维《终南山》)
树黏青霭合,崖夹白云浓。(张乔《华山》)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渡荆门送别》)
水近沧浪急,山随绿野低。(张乔《浮汴东归》)
单从诗歌标题看,张乔诗歌主题与前人相似,就诗歌内部措辞与间架结构而言,张乔的模拟痕迹也较明显。然而张乔又与李白、杜甫、王维不同,张乔没有他们的笔力和才思,更达不到盛唐诗歌的阔达境界。因此,张乔常常以景作结,将人生的未解难题放置到广大的自然中,不再讨论生老病死、爱恨别离之苦。这种“夺胎换骨”的诗法,一方面成就了张乔诗歌,一方面也使得他浸濡先贤之风,在科举场屡试屡败后,依旧保持温柔敦厚的品性。
第二,张乔诗歌擅长“曲笔传情”,这种“曲笔传情”在显层次上表现为“借典传情”,在隐层次上则表现为“曲笔而讽”。例如他说“相如曾醉地,莫滞少年游”(《送蜀客》),“几时献了相如赋,更向嵩山采茯苓”(《赠友人》),这就是“借典传情”,张乔曲折地吐露了求仕之心,甚至设想了成功后的急流勇退。再如《自诮》“只应抱璞非良玉,岂得年年不至公”,借卞和献玉的典故,抒发内心的遗憾。“抱璞”典出《韩非子·和氏》《新序》等书,比喻坚持美德,也有怀才不遇之意。《贵池唐人集》在此诗下注有:“不怨人而自怨,厚之至也。”[13]“曲笔而讽”是“曲笔传情”的更高境界,《台城》最能说明:
宫殿余基长草花,景阳宫树噪村鸦。
云屯雉堞依然在,空绕渔樵四五家。
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十七“建康府”下“历代宫苑殿阁制度”条载:“台城一曰苑城,即古建康宫城也,本为吴后苑城,晋成帝成和五年作新宫于此,其城唐末尚存。”[14]台城本是三国吴的后苑城,东晋成帝在此新修了建康宫,历经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一直是宫殿和台省处所,兼具政治中心和游乐宴饮的功能。张乔看到鸦巢几经风雨摧残,乌鸦们却照样争先恐后地喧噪,如云聚集的城墙空绕渔樵人家,更加凸显了台城的荒凉凄冷。公元589年,隋兵攻入建康,陈后主与张丽华在井内躲避,后被活捉,押往洛阳,客死他乡。刘永济评此诗:“此兴亡之感也。语指南朝,意实在唐代。”[15]张乔已经洞察到了大唐大厦的颓倾之势,他在诗歌中委婉表达,收敛了锋芒,形成婉曲流逸的美学风格。
三、瘦寒孤冷之美
计有功《唐诗纪事》评晚唐诗:“唐诗自咸通而下,不足观矣。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气丧而语偷,声繁而调急,甚者忿目褊吻。大抵王化习俗,上下俱丧,而心声随之,不独士子之罪也,其来有源矣。”[16]清翁方纲《石洲诗话》云:“咸通十哲,概乏风骨。”[17]无论是“亡国之音”,还是“概乏风骨”,均是针对晚唐诗中的客观存在的低迷现象,诗人的群体缄默,使得张乔倾向于选择瘦寒孤冷的意象,以及冷色调的色彩艺术描写,这两点共同成全了张乔诗歌瘦寒孤冷的美学风格。
第一,瘦寒孤冷的意象选择。张乔诗中,“瘦”出现2次,分别是“马登青壁瘦,人宿翠微闲”(《送许棠下第游蜀》)和“瘦根盘地远,香吹入云清”(《和薛监察题兴善寺古松》)。“寒”出现20次,“孤”15次(“独”20次),“冷”2次(“凉”11次)。吴经熊(John C.H.Wu)《唐诗四季》()用四季来概括唐诗演进的历程,在《冬之心理分析》中,作者列举张乔《山中冬夜》的“长吟语力微”[18],借此阐述唐朝末代之音的微弱。试看全诗:
寒叶风摇尽,空林鸟宿稀。涧冰妨鹿饮,山僧阻雪归。
夜坐尘心定,长吟语力微。人间去多事,何处梦柴扉。
寒叶、空林、涧冰;鸟、鹿、雪,这些瘦寒孤冷的意象连缀在一起,传达出诗人寂寞的意绪。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三 “寒苦”条下亦举例此诗。[19]宋高似孙《砚笺》评唐人诗:“白乐天诗,砚温磨冻墨。郑谷诗,寒砚旋生澌。喻坦之诗,砚和青霭冻。温庭筠诗,砚水池先冻。张乔诗,近腊砚生冰。”[20]其孤寒程度,可见一斑。再如张乔《听琴》:
清月转瑶轸,弄中湘水寒。能令坐来客,不语自相看。
静恐鬼神出,急疑风雨残。几时归岭峤,更过洞庭弹。
此诗写琴音的美妙多变,开篇以“清月”渲染环境,缓缓琴弦,声调清幽,“湘水”也笼罩着一丝寒意,继而琴声扣人心弦,主客不语,再写静急的变幻,如“鬼神出”,如“风雨残”,末联想象演奏者“归岭峤”“过洞庭”弹奏,别是一番佳境。明张大命《太古正音琴经》卷八评:“此类甚多,数语尤有致。”[21]张乔笔下还多次出现“松”意象,松树是长寿的象征,夏代和周代分别以松树和粟树代表社神。魏晋玄风大炽,名士清谈常以松品评人物,如山涛评稽康:“稽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22]“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有《赠从弟三道》,诗曰“岂不罹霜雪,松柏有本性”就是用松树来比喻君子的人格,勉励从弟在战乱频繁的艰难时也中坚守操。唐人已有意识地欣赏松柏的古老沧桑之美,对老松怪异之美的描写在中晚唐表现得尤为突出。张乔笔下的松,有时出现在参禅悟道的古寺里,有时候出现在送别友人的道路上,这些松树是古老的,是寒冷的,是枯瘦的,甚至是坚贞的。如“向水千松老,空山一磬秋”(《再题敬亭清越上人山房》),“地寒松影里,僧老磬声”(《题山僧院》),“静迟松桂老,坚任雪霜凋”(《兴善寺贝多树》)。这些松树是张乔寒微人生的一点温存念想,如“旧时僧侣无人在,惟有长松见少年”(《寄山僧》) ,“院凉松雨声,相对有山情”(《题诠律师院》)。
第二,冷色调的色彩艺术描写。张乔频繁夜宿于凄风苦雨的僧院,描摹古寺森森的生活景物,但他又不同于贾岛式的苦吟,他并不刻意搜罗生冷孤僻的词语,而是在诗歌中自然注入文化心理上的孤寒之感,实际上是整个晚唐时代的孤寒写照,张乔曾明确表达“山河几更变,幽咽到唐朝”(《青鸟泉》)的离乱之感。他将冷色调的色彩艺术描写发挥得最好的是《题贾岛吟诗台》:
吟魂不复游,台亦似荒丘。一径草中出,长江天外流。
暝烟寒鸟集,残月夜虫愁。愿得生禾黍,锄平恨即休。
贾岛的事迹被晚唐诗人加工演绎,他由一个生前落魄的苦命文人转化成为富有传奇色彩的才子形象。方岳《深雪偶谈》:张乔、张蠙、李频、刘得仁,凡晚唐诸子,皆于纸上北面,随其所得浅深,皆足以终其(指贾岛)身而名后世[23]。闻一多《唐诗杂论》提出“贾岛时代”[24],意指整个晚唐五代都在模仿和学习贾岛诗歌题。胡中行对晚唐诗和晚唐诗人有这样一个评论:“晚唐的绝大多数诗人是贾岛的启继者,其人数之众,作品之富,历时之久,蔚为大观,贾岛所开创的诗派在晚唐占着数量上而不是质量上的绝对优势。”[25]张乔也是其中一员,《题贾岛吟诗台》中,张乔称赞贾岛的诗名像江水一样流向远方。“暝烟寒鸟集,残月夜虫愁”两句,暝烟、寒鸟、残月、夜虫,构成了贾岛吟诗台的荒凉寂寥之景,同时也是对贾岛诗歌境界的比喻。张乔巧妙地冷色调的描写方式注入不平之气,“愿得生禾黍,锄平恨即休”,使得诗歌境界得以提升。汤华泉也认为“张乔不是贾岛所能范围的,似乎可读的作品要比贾岛多些”[8]74。
四、悲怆奇崛之美
张乔出生于江南的秀丽山水,奔波辗转于云诡波谲的京城长安,他屡试不得,于是来广漠荒凉的边塞,他一口气写下了十篇边塞诗:《宴边将》《河湟旧卒》《北山书事》《书边事》《再书边事》《赠边将》《塞上曲(塞下曲)》《送河西从事》和《游边感怀二首》。他有不凡的历史洞察力,张乔的边塞诗不再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也不再缱绻于儿女情长的闺怨,甚至激荡人心的边塞风光也不再震撼诗人的眼眸,他善于在平静的心态下,简笔勾勒晚唐西风残照的风景,于广漠无垠之间体悟生命的渺小和对戍边战士的同情,因此他的边塞诗呈现出显著的悲怆奇崛之美,这是张乔诗歌的第四种美学风格,也是张乔诗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使得他较之“咸通十哲”和“九华四俊”诸辈,略高一筹。
唐代边塞诗的主题发展,历经初盛唐的颂战、尚战,中唐的怨战、厌战,最后定格在了晚唐的休战、反战。晚唐边塞诗虽无前人边塞诗的雄心壮志,却是一次对传统边塞主题的反叛与逆袭,从而达到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在美学风格上呈现悲怆奇崛之美。例如“谁将倚天剑,削出倚天峰”(《华山》),其语之悲怆,其言之奇崛,震撼人心。赵荣蔚评张乔律诗:“多故国望乡之思,时有衰飒气,然绝少庸俗,亦无滑易之嫌,句意流利清畅处,则与韦庄相近。七律时有追慕大历处,亦有悲慨之音。”[26]“悲慨之音”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试看《书边事》:
调角断清秋,征人倚戍楼。春风对青冢,白日落梁州。
大汉无兵阻,穷边有客游。蕃情似此水,长愿向南流。
此诗意境开阔而深远,笔法流畅,一气呵成,抑扬顿挫,跌宕生姿。余成教《石园诗话》卷二说:“其五七律起句,俱多挺拔语。”[5]2766俞陛云在(诗境浅说》中说:“此诗高视阔步而出,一气直书,而仍顿挫,亦高格之一也。”[27]钱志熙称《书边事》“是晚唐诗人笔下难得的关怀时事之作”“极虚实相生之美”。[11]126《河湟旧卒》更是一首荡气回肠的七言绝句:
少年随将讨河湟,头白时清返故乡。
十万汉军零落尽,独吹边曲向残阳。
宋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五举例张乔《河湟旧卒》,评:“张乔多有好绝句……亦籍、牧之亚。”[28]清吴昌祺《删订唐诗解》云:“沙场之惨,隐然自见,最得绝句之妙。”[5]2767清沈涛《匏庐诗话》评:“张乔《宴边将》云云,《河湟旧卒》云云,试掩其名,读者鲜不以为右丞、龙标。然则初盛中晚之分,其亦可以已乎?”沈涛认为如果将张乔诗歌掩盖了名字,大约时人都会认为这是王维、王昌龄的作品。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选录此诗,评价“此诗与古诗《十五从军征》同旨,着重在久戍幸存”[29]。湟水源出青海,东流入甘肃与黄河汇合,湟水流域及与黄河合流的一带地方称“河湟”。杜牧和司空图等晚唐诗人都曾写过河湟诗。张乔笔下的“河湟旧卒”,就是当时久戍幸存的一个老兵。此诗叙事简淡,笔调并不突兀,却造成了语意上的悲怆奇崛。首句“少年随将讨河湟”,颇为豪气,次句说“头白时清返故乡”,略有庆幸,从“少年”到“头白”,多年殷切的盼望,俱成泡影,但他毕竟是生还了,更多的边兵则暴骨沙场。第三句 “十万汉军零落尽”从侧面落笔,反映了唐代人民为战争付出的惨重代价,幸存者陷入不幸之心境。第四句集中塑造了一位老兵的形象,“独吹边曲向残阳”,一个“独”字交代老人目前处境,暗示家园变故,垂老无家,流露出深沉的哀伤,“残阳”二字暗示日薄西山的大唐景象。龙榆生《中国韵文史》第十五章《晚唐诗》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晚唐人诗,惟工律绝二体;不流于靡弱,即多凄厉之音,亦时代为之也。”[30]
张乔诗歌中悲怆奇崛的语言大多集中在他的边塞诗中,偶尔有些奇崛之句散落在咏怀诗中。这种悲怆奇崛的特点,使得张乔避免走向晚唐诗人孱弱的心灵之境,为其诗歌增添了铿锵之声。
综上所述,张乔的语言艺术与美学风格互相生发,他的诗歌美学风格可以概括为四种:清雅明净,婉曲流逸,瘦寒孤冷和悲怆奇崛。对于张乔诗歌语言艺术和美学风格的深入剖析和解构,对晚唐诗歌的披沙拣金乃至中国古代诗歌的掇菁撷华,大有裨益。
[1]王定保.唐摭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14.
[2]唐才子校笺:第四册[M]. 傅璇琮,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302.
[3]王镇远.古诗海: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052.
[4]唐诗观澜集[M].李因培,选评,凌应曾,编注.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天津图书馆藏.
[5]陈伯海.唐诗汇评[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6]王运熙,杨明.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隋唐五代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670.
[7]增订注释全唐诗:第四册[M].陈贻焮,主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1218.
[8]汤华泉.张乔考论[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1985(1)71.
[9]唐先田,陈友冰.安徽文学史:先秦至北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151.
[10]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78.
[11]钱志熙.唐诗近体源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2]刘勰.文心雕龙[M].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451.
[13]贵池唐人集[M].刘世珩,辑校.郑玲,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3:289.
[14]王象之.舆地纪胜[M].北京:中华书局,1992:731.
[15]唐人绝句精华[M].刘永济,选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55.
[16]计有功.唐诗纪事校笺[M].王仲镛,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2235.
[17]翁方纲.石洲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7.
[18]吴经熊.唐诗四季[M].徐诚斌,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81.
[19]魏庆之.诗人玉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66.
[20]高似孙.砚笺二卷[M].台北:广文书局,1980年.
[21]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1093册[M]. 顾廷龙,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47.
[22]刘义庆.世说新语译注[M].张万起,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588.
[23]陈增杰.唐人律诗笺注集评[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1063.
[24]闻一多.唐诗杂论[M].傅璇琮,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6.
[25]胡中行.论贾岛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3):48.
[26]傅璇琮.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汉唐五代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468.
[27]俞陛云.诗镜浅说[M].北京:中华书局,2010:25.
[28]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3:445.
[29]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38.
[30]龙榆生.中国韵文史[M].钱鸿瑛,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7-48.
A Study on the Language Art and Aesthetic Style of Zhang Qiao’s Poetry in Late Tang Dynasty
REN Dong-q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gjing 210097, Jiangsu)
Zhang Qiao is a poet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He was from Chi Zhou, a city of Anhui Province. There are two series of his poetry, 171 poems included in. His language art and aesthetic style influence each other. The changeable language art produces four aesthetic styles. The pure and clear vocabulary and the language skills of “Taking Writings as Poem” build a clear aesthetic style; The implicit and flexible aesthetic style is formed by the use of predecessors' poems, such as the skill of “changing the bones and altering the fetus” and “using allusions to express feelings”; The lonely and cold image choice and cold color description foil the lonely and cold aesthetic style; Zhang Qiao’s frontier poems create a tragic and great aesthetic style.
Zhang Qiao; poetry in late Tang ; language art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7.04.13
I207.22
A
1004-4310(2017)04-0071-05
2017-05-05
任冬青(1990-),女,汉族,江苏扬州人,南京师范大学2016级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