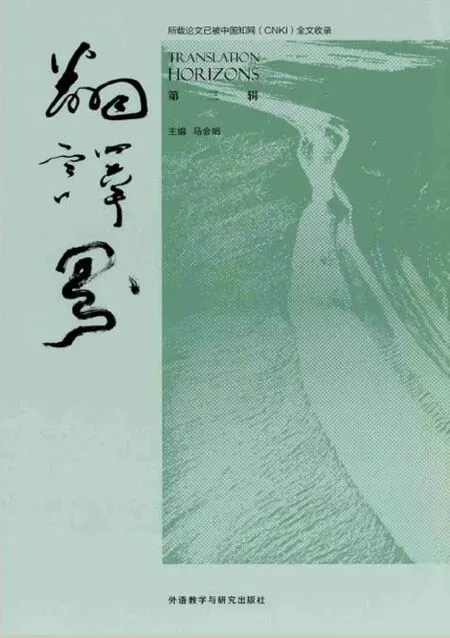离散诗学视角下的翻译与重构*
——以张枣对谢默斯·希尼诗歌的翻译为例
2017-04-15王岫庐
王岫庐
中山大学
离散诗学视角下的翻译与重构*
——以张枣对谢默斯·希尼诗歌的翻译为例
王岫庐
中山大学
离散诗学通过对诗歌语言、主题、意象等方面的探究,彰显离散诗歌写作中的矛盾性、流动性、多样性和异质性。在跨文化交流的翻译语境中,如何再现离散诗歌写作的特性以及原作衍生出的文化身份思索与文化认同建构成为翻译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以张枣对谢默斯·希尼诗歌的翻译为案例研究,从离散诗学的视角,解读谢默斯·希尼诗歌中的文化记忆和本土经验之间的错置和交集,通过对张枣译本的文本对比研究以及对译者文化身份的反思性分析,探究希尼诗歌离散意识在翻译中的再现和重构,并进一步揭示译者文化离散身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
离散;文化身份;翻译
1. 引言
“离散”(diaspora1)这一术语最初指的是犹太人被巴比伦人放逐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境况,后来用以泛指人们远离家园、漂流异地的状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民族国家概念的模糊,当代“离散”这一概念的含义不再局限于地理或民族疆界的跨越,而已经成为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意识范畴以及文化生产模式。许多学者(Hall, 1990; Gilroy, 1993)从杂合(hybridity),流动性(mobility)与语言混合(creolization)等不同角度对离散经验进行反思,使得这一概念成为了“20世纪末学术对话中最流行的术语之一”(Baumann,2000:313)。
翻译研究作为一门跨文化研究学科,对“离散”现象一直相当重视(Robinson,1997;孙艺风,2006;Leonard,2007)。目前翻译研究的离散命题主要从对离散文学的翻译、离散译者的研究以及翻译属性的反思这三方面开展(王晓莺,2011:12-16)。诗歌具有其他文学体裁无法企及的张力,离散诗人书写的诗歌“渗透着诗人们独特的体温与族裔情感”(蒲若茜、宋阳,2011:146)。离散诗学通过对诗歌语言、主题、意象等方面的探究,彰显离散诗歌写作中的矛盾性、流动性、多样性和异质性。本文利用离散诗学的视角,解读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诗歌中的文化记忆和本土经验之间的错置和交集,并进一步通过对张枣译本的分析以及对译者文化身份的思考,探究希尼诗歌离散意识在翻译中的再现和重构。
2. 谢默斯·希尼诗歌中的离散意识
2.1 希尼的文化身份
谢默斯·希尼(1939-2013)是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爱尔兰诗人。早在80年代中期,我国已经开始了对希尼的译介,许多著名的诗人和诗歌翻译家,如袁可嘉、王希苏、傅浩、黄灿然等人都曾翻译过希尼的诗作。1995年,希尼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国内各大外国文学期刊纷纷推出特辑,对希尼的代表诗作与文论进行系统介绍。90年代新诗写作的代表诗人孙文波(2000:12-14)认为,希尼冷静的诗歌写作姿态对中国90年代诗坛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文学史上,如何界定爱尔兰这一特定地区作家的身份,一直都是敏感话题。希尼本人曾在1983年以诗歌的形式发表了《一封公开信》(An Open Letter),对1982年出版的《企鹅当代英国诗集》(The Penguin Book of Contemporary British Poetry)将自己归为“英国诗人”表示反感,公开声明自己的爱尔兰身份。在这首诗中,希尼写道:
……请注意
我的护照是绿色的
我们从未举起酒杯
向女王致敬
(Heaney, 1983: 9;本文作者翻译)
虽然绿色护照不容置疑地证明了希尼的爱尔兰公民身份,但是公民身份和文化身份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
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然而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大多主张与爱尔兰合并,与亲英的基督教新教派之间常年纷争不断。希尼出生于北爱尔兰传统天主教家庭,他在政治上认为北爱尔兰属于爱尔兰,自己是爱尔兰人。但希尼就读的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地处北爱尔兰,提供的却是纯正的英式教育。可以说,希尼始终身处北爱尔兰乡土经验和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交界地带,他的文化身份也充满了复杂和矛盾,绝非护照颜色那么简单。
根据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对文化身份的理解,共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习俗对身份认同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文化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本质,也不是我们可以追溯的某一个特定的起源,而是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中建构起来的,既是一种“存在”(being),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生成”(becoming)(1990:223-226)。在《一封公开信》中,希尼明确宣布了自己的爱尔兰身份。多年之后,诗人在牛津大学的讲座中重提“绿色护照”的话题,强调自己并不是要抹杀英国和隶属英国的北爱尔兰之间的关系,而只是希望“在国界线范围内保持差异的存在”(1995:201)。显然,和《一封公开信》中斩钉截铁的政治式宣言相比,后者的态度要温和得多。对自己手中所持的“绿色护照”的不同解释,恰恰说明了希尼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追寻是一个充满着矛盾和变化的过程。
希尼并不讳言自己的身份在爱尔兰和英国文化之间的纠结。他曾将自己作品中的阴性因素归于爱尔兰的影响,而其中的男性张力则归于英国文学,并认为自己“象征性地置身于英国影响的痕迹和本土经历的诱惑之间,置身于‘庄园领地’和‘沼泽地’之间”(1980:34-35)。虽然在希尼的眼中,这样的“双重意识”(two-mindedness)无损于自己的爱尔兰身份(1995:202),然而面对激烈的英爱冲突和爱尔兰岛上南北分治的现实,希尼不可避免地承受了文化归属和身份错置的压力。在《曝光》(Exposure)一诗中,希尼曾将自己描述为“家园中的流浪者”(an inner émigré)。诗人在70年代曾迫于政治原因离开家乡,举家移居爱尔兰共和国,后于1981年至1997年在哈佛大学任教授,并于1988年至2006年任驻校诗人,1989年至1994年在牛津大学任教授。作为一个游走于不同文化之间的边缘人,希尼有着与离散族裔极其相似的心灵体验。这种内在的、心灵的流亡,让希尼的诗歌创作超越了单一文化视角,呈现出强烈的离散意识。
民族主义学者威廉·萨夫兰(William Safran)曾经指出,对故乡的记忆、想象和迷思是现代离散族裔的一个重要特征(1991:304)。这种“原乡之思”虽然饱含了个体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但并不意味着狭隘的民族/种族主义立场。希尼眼中的爱尔兰并不是本质化的单一传统,他的故乡北爱尔兰,更是由于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归属,充满了多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织和冲突。希尼则建议自己的同胞应该“用想象面对现实的压力,并在想象中重新进入整个爱尔兰王国”(1995:202)。希尼的诗歌在原乡迷思的基础上,通过不同的文学想象展现出一种广阔的书写世界,表达了诗人建构爱尔兰民族主体身份和文化认同的诉求。
2.2 希尼诗歌中的家园建构
对家园(homeland)的追寻是希尼诗歌的核心主题之一。希尼笔下的家园并不只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范畴,同时也意味着历史和心理的沉淀。正如诗人自己所言,只有把“地理国家”(the geographical country)和“心理国家”(the country of the mind)结合起来,才能够对家园做出最丰富的解释(Heaney, 1980: 132)。
从希尼作品中我们亦可看出诗人将爱尔兰本土体验和个人经历结合起来,重塑家园的努力。这些诗作不乏关于北爱尔兰地貌和乡土风俗的直接描述。例如《挖》一诗,咏诵了父亲挖土豆和祖父掘泥炭的情景;《冬青》一诗,回忆了孩子们圣诞节前采冬青的快乐;《山楂灯笼》一诗则以爱尔兰冬季成熟的红色山楂为灵感。希尼曾说过,“在爱尔兰,我们拥有一个稳定的因素——土地,以及一个无常的因素——人。我们必须通过这个稳定的因素来寻找身份的延续”(Heaney, 1980:149)。诗人立足土地,通过对爱尔兰地理环境以及与土地密切相连的民俗民风的再现,力图用本真和原初的眼光去呈现自己理想中的家园。除了强烈的乡土情怀,希尼还非常擅长向记忆深处挖掘题材,从个体经历和感受出发,在地理国家之外,通过回忆和想象重塑心理家园。
诗人张枣译了希尼的六首诗,其中,除了《山楂灯笼》取材于神话以外,其他都和希尼的个人经历紧密相关。《新婚日》通过对婚礼当天事件的回忆,展现了诗人复杂而矛盾的心理纠结;《挖》《铁道孩子》《冬青》取材于诗人对儿时生活的回忆;《来自写作的边境》源于诗人亲身经历的,发生在爱尔兰南北边境上的一次例行军事检查。在一次采访中,希尼承认自己的大多数诗歌都“基于回忆,多少带有自传色彩”,但他也指出回忆本身并不是自己写作的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回忆带来 “定型的冲动,产生激动并最终凝为整体”(Henri & Heaney, 1997)。这种对“定型”和“整体”的追求,源自诗人对自己身份危机的体认,以及内心对稳定家园的渴望。
希尼的诗歌在回忆个人生活经历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对自己当下的心灵家园的反思和想象。例如,在《挖》一诗中,诗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手中并没有继承父亲和祖父的铁锹,但是却可以用笔为武器,继续挖掘自己的身份。《铁道孩子》《冬青》将天真无邪的儿时经历和成年后的反思及选择巧妙糅合起来,从语言的角度探索“词语”与“世界”的多重可能性。《来自写作的边境》则更明显,标题本身便已经暗示了边境跨越这一行为在地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意义。在这首诗中,希尼将边境关卡和想象中的思维审查并置,表达了用文字重塑现实和自由的希望。
有评论家将希尼看作是“一位家园诗人(the poet of the patria),恋家的飞鸟,故土的挖掘机,希望寻找失落的忠诚”(Kearney, 1988: 101)。虽然张枣的翻译只是希尼作品中很小的一部分,这六首诗作已经可以让我们从不同角度对希尼诗歌所构建的家园有所体会。希尼将自己的文化之根深扎于爱尔兰的土地,而诗人的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使他拥有更广阔和多元的视角。希尼诗歌中的家园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是回忆的,也是想象的;是现实的,也是语言的。这个家园不但饱含了诗人的乡土之情、童年回忆、个人经历,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现实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想象和愿景。
3.翻译、身份和家园重构
3.1 张枣的文化身份与诗学追求
张枣翻译的六首希尼诗作收录于1998年出版的张枣个人作品集《春秋来信》。就其流传范围和影响程度而言,这几首译诗并无过人之处。但是就译诗的用词和句式特点而言,张枣的翻译则体现出相当与众不同的个性。作为一个旅居德国,而又一直坚持以母语写作的诗人,张枣特殊的文化身份和诗学主张在其翻译作品中的体现,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张枣出生于湖南长沙,于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完成本科学业,后考入四川外语学院(今四川外国语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专业的硕士。1986年以后,张枣前往德国,历时十年获特里尔大学文哲博士,后任教于图宾根大学。这样的教育背景和常年旅居海外的经历在中国第三代诗人中并不多见。德国汉学家顾彬在张枣诗集《春秋来信》译后记中,将张枣看作是“中文里唯一一位多语种的名诗人”,认为他不但能够熟练使用多种语言,而且擅长在与外来文化和语种的相遇中,重新发现并塑造自己的“诗歌构图的形式和结构”(顾彬,1999:42)。
张枣和希尼一样具备多重的文化背景,然而不同文化场域对这两位诗人造成的心灵冲击却迥然不同。张枣曾回忆自己刚出国时,虽然能够“非常敏感地感觉到地域的差别”,然而“以外语命名的另一个世界和事物对我来说并不可怕”(2012:210)。在西方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甚至“越来越觉得东西方区别不会太大”(2012:229)。对张枣而言,多重文化背景并没有带来个人身份的危机。毕竟,中西文化的差异与英爱之间的历史纠葛及政治冲突不能相提并论。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张枣一直是一位坚定而严肃的汉语写作者。虽然他精通多种外语,也长期旅居国外,却一直对自己的母语保持着近乎宗教式的皈依感。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表述,就是“母语是我们的血液,我们宁肯死去也不肯换血”(2012:53)。
对于自己在国外漂泊的生活状态,张枣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判断。他当初决定出国读书,背后有一个“秘密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广纳各种语言的长处,探索语言的边界,“发明一种自己的汉语”,建立起“一个新的汉语帝国”(2012:209)。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张枣没有继续学习英语,而选择去德国学习另一种语言,寻找另一种陌生化的诗意。诗人的好友宋琳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从张枣“只身远赴异地”的决定中,看到了一种超越国家概念的、以“中西双修,古今融通”为己任的诗歌和艺术追求。
换言之,张枣在海外离散的生活经历可以被看作是诗人的一次自我放逐。实际上,“离散”在这里不但反映了诗人置身海外的现实,更重要的是指向了语言层面的流亡。北岛曾经将这种状态在诗中自省为“词的流亡”。对张枣而言,他出国读书的经历不啻为一次“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而其中最大的危险便来自失语的威胁。根据张枣自己的回忆,刚到德国的时候,他有整整三个月讲不出话,连日记和信都写不出来(张枣:2006)。在《跟茨维塔耶娃的对话》中,张枣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母语之舟撇弃在汪洋的边界,
登岸,我徒步在我之外……
张枣这里描述的不单是茨维塔耶娃在法国的流亡,也表达了自己漂泊异乡的身份失落。在远离母语的环境中,张枣切身体会到了言说之难与存在之难。如果说“原乡之思”是现代离散族裔的重要特征,张枣在离散海外的过程中也深刻体验了文化乡愁。
无家可归的人,总是在回家:
不多不少,正好应合了万古愁。
但是,张枣心目中的家园和希尼的“地理国家”和“心理国家”不一样。张枣并没有从具体的祖国、故土,或是个人记忆中寻找家园,而是坚信“母语之舟”能够载着自己实现还乡的梦想。张枣的德国朋友、汉学家苏桑娜·葛塞博士曾敏锐地看出,母语是张枣“随身带着的家园”,他为自己“用词语修建房屋”(2012:258)。在异乡的流亡中,张枣虽然也曾感到孤独、恐惧,甚至绝望,但他始终坚守着汉语诗歌的精神性。这种坚守使得张枣的身上没有出现希尼所经历的那种在地与原乡之间的身份撕扯,也将“孤悬海外”的张枣能够始终与留守国内的诗人“紧密地搂抱在一起”(张枣,2012:59),共同承担起中国诗人这一称号。
3.2 张枣译诗:寻找母语之舟
张枣不是一个高产诗人,诗歌翻译数目也不多。《春秋来信》中收录的译诗都没有标明翻译完成的时间,但是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张枣除了在1985年翻译了荣格的文章《论诗人》一文之外,在1986年出国以前并没有做过太多翻译的工作。《春秋来信》出版于1998年,当时张枣大部分时间还在国外。另外,张枣好友的回忆也多少印证了张枣在德国期间对诗歌翻译颇有心得2。综合各方资料,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其《春秋来信》收录的译作,包括张枣所翻译的希尼诗作六首,有很大可能是张枣在德国完成的。
实际上,这里诗人到底置身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在语言中自我流放的张枣而言,翻译的意义不只是语言的转换,更重要的是为诗人提供了一种用母语言说的可能,一种对梦想中汉语诗歌帝国的构建。这一以母语为家园的诗学主张,在张枣的翻译观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曾比较过两种不同的诗歌翻译方法,认为“粗糙的直接的翻译可能更会导致语言与诗歌上的革命,而精微性的翻译最终是满足了翻译家自身的创作欲”,而自己的诗歌翻译就是为了“将诗歌独到的语言优美地传递给读者”(2012:236)。
张枣对于“粗糙的直接的”和“精微性的”这两种翻译方法的区分,难免让我们联想到翻译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文”与“质”、“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的论争。然而,张枣的出发点和翻译研究中对于原作/译作之间的二元关系的各种讨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作为诗人的张枣,他提出的这两种翻译方法都是基于译作、译入语这一单方面的考虑。如果说,吉迪恩·图里提出了以目的语为导向的(target-oriented)描述翻译学研究范式,张枣在这里提出的则是以目的语为导向的诗人译诗的方法。张枣所说的“粗糙的直接的”翻译就是对原文进行逐字逐句的、直译式的处理,而这样做往往会为目的语带来陌生化、异质性的表达方式,因此在诗人眼中是有价值的:“会导致语言与诗歌上的革命”。“精微性的”翻译则是针对“粗糙”一词提出的。陌生化、异质性的表达、语言和诗歌的革命固然重要,然而对张枣而言“翻译家自身的创作欲”也同等重要。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的译诗绝不是简单直接地展示差异,而应当是优雅地跨越差异,实现语言的诗意在翻译中的复制和重塑。
从张枣翻译的希尼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枣作为一个诗人秉持一种对诗意的追求,力图以“精微的”方式翻译并创作,从而丰富母语、重新发现乃至发明母语的努力。这一点在张枣译诗用词的层面上尤为明显,他尝试用古老的汉语去表达现代的诗意。我们可以略举数例对此加以说明:
(1) Under my window aclean raspingsound
在我的窗下,一阵酸心刺骨的声音
(2) and everything is pure interrogation
until a ri fl e motions and you move
with guardedunconcernedacceleration—
而一切不过是纯粹的盘问
直到一杆长枪移开,你才
启动,小心而无动于无衷地加速
(3) But sometimes when your breathplumesin the frost
it takes the roaming shape of Diogenes (Heaney, 1987: 7)
可有时当你的呼吸在霜中载蠕载袅
便幻化出了那漫游的戴欧几尼斯的体态(张枣,1998:163)
张枣曾说过,“古典汉语的古意性是有待发明的”(2012:216),而这三处翻译似乎为这句话添上了生动的注解。例(1)中希尼用clean和rasping这两个词语来形容铁锹挖到石头发出的响亮而刺耳的声音。张枣用了自创的“酸心刺骨”一词来翻译,而这个词在他1984年的代表作《何人斯》一诗中出现过。对 “锥心刺骨”一个字的改动,让这个成语在表示疼痛的感觉以外,更具备了酸楚的含义。例(2)中张枣用“无动于无衷”来翻译原文中的unconcerned一词,通过对成语“无动于衷”的改写,不但形成拖沓的节奏,从而体现出加速的缓慢,而且用“无衷”来衬托下文即将出现的空虚和无奈。例(3)中原文 plume这个动词描写的是冬天口中呼出的热气遇冷凝成白雾,在空中升腾的情景。张枣用了一个相当奇特的词“载蠕载袅”来翻译3,将“蠕”所表示的动作之慢、“袅”描绘的体态轻盈,以及四字短语的典雅文气巧妙融合在一起。这个翻译一方面可以被看作是实现了对原文的最大忠实,因为英文中的plume一词做名词的时候,不但可以用来指鸟类的羽毛,也可以指蠕虫身体上的羽状毛;另一方面却又因为借用诗经体“载……载……”而使得译文充满中国式的诗情画意。无可否认,张枣的用词奇巧而缜密,诗人创造性地吸纳了母语的营养,却同时又保持着与母语的疏离,并发现了未知的汉语性。
在整个诗篇的层面上,张枣并没有努力对希尼的原诗中的场景进行还原。例如希尼《挖》一诗文风通俗甚至略带俚语色彩,相当贴近爱尔兰的农村生活。张枣的译诗却在许多地方体现出他一贯儒雅唯美的特质,例如“我们采摘/并喜欢它们清凉坚实的手感”,“马铃薯样品冰凉的气味,被拍打得/吱咯直响的泥煤,刀锋急促的飞舞”。相比之下,袁可嘉的译文“我们捡在手中,/爱它们又凉又硬的味儿”以及“白薯地的冷气,潮湿泥炭地的/咯吱声、咕咕声,铁铲切进活薯根的短促声响”,在文风上和希尼的原作更加接近。
在另外的几处地方,张枣的译文和原文描绘的意象也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偏差。例如在《山楂灯笼》一诗中,张枣将crab翻译成了“酸苹果”
(4) The wintry haw is burning out of season, /crabof the thorn, a small light for small people,
冬天的山楂正燃烧着退出季节。/荆棘丛中的酸苹果,小人物的小小灯盏
这里原诗中山楂是红色的意象,与“燃烧”和“灯盏”相呼应。“crab”是一种颜色艳红的野生小苹果,在这里将其译为“酸苹果”,似乎突出的是果实的味道,而颜色方面却容易让人有绿色的联想。如果译为“海棠果”,在色彩上与原作整体的红色调似乎会协调。再如《铁道孩子》一诗有这样的句子:
(5) We thought words travelled the wires / In the shiny pouches of raindrops
我们以为词儿旅行在/这些闪光的雨滴的口袋里
Each one seeded full with the light
Of the sky, the gleam of the lines, and ourselves
So in fi nitesimally scaled
每滴雨都布满了天光的/种子,线条的徽光,然而我们/缩成无穷小的规格
希尼的原诗中,孩子们幼稚地以为铁道边上的电报线就是直接传递消息的通道。但是在张枣的译文中,传递消息的通道由“电线”(wires)直接变成了“雨滴的口袋”。而这里的误读,在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接下来对于雨滴中影像的误解。在原诗中,孩子们凑近雨滴,看到了天空,电线,和他们自己。也正是因为看到自己在雨滴中的影像,孩子们觉得自己变小了。张枣的译文却将孩子们独立出来,直接声称“我们缩成无穷小的规格”,难免使这一变化显得突兀而奇怪。
上面几个例子也许还有可能是张枣在翻译中试图进行诗意的再创造,下面这个例子则应该毫无争议是张枣对原作的误译了:
(6) When I went to the gents / There was a skewered heart / And a legend of love.
我曾来到绅士们之间/那儿有叉烧肉/和爱情的谣传。
在《新婚日》的结尾,希尼回忆自己在婚礼结束前,去厕所看见穿着爱心之箭的涂鸦。希尼试图通过将厕所与婚礼并置,将自己的爱情从仪式的虚无缥缈带出来,最终在俗世的场景得到沉淀。张枣的译文将gents理解为“绅士”而非“厕所”,将skewered heart理解为“叉烧肉”而非“爱心涂鸦”,是对原诗中的关键意象的重大误读。
张枣曾表示自己“非常不愿翻译”,因为“在翻译中容易产生改动别人作品的欲望”,同时“自己听到的那个声音没有完成”(2012:218)。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在翻译中觉得受到原作束缚,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这是在所难免的。从上文张枣对希尼诗歌翻译的分析中,我们明显感受到译者发出自己声音的渴望。正如苏桑娜·葛塞所言,翻译是张枣在异乡的身份认知。对海外漂泊的张枣而言,翻译首先是一种特殊的母语使用方式,他希望能够通过翻译,乘坐母语之舟返回家园。在翻译家自身的创作欲高于忠实再现原诗愿望的情形下,诗人采用了“精微的”方式去翻译,在每一个重要的语词上细致琢磨,每一个词都成为一页小舟,是诗人追寻、靠近、回到、发现母语的机会。张枣翻译中奇巧而缜密的用词、儒雅而精致的文风与他自己的诗歌创作特色如出一辙。但是必须指出,这样的翻译观和诗学观,也造成了张枣翻译中对原诗总体文风的忽略,以及某些特定意象大而化之的理解。希尼和张枣不同的离散经历,带来不同的家园之思以及相应的诗学追求。希尼的家园是乡土的、童年的、个人经历的,但是张枣的家园更指向语言本身,因此他的翻译出现的特点是词汇层面的精雕细琢,但在更大的意象、主题、场景的层面上却往往并不和原文一致。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张枣的译诗也带领我们回到了家园,但是这家园并非希尼笔下虚实交织的爱尔兰王国,而是张枣心中古老而又开放的汉语帝国。
4.结语
张枣和希尼一样,生活在不同文化的交错空间里。虽然两人的文化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出离散性的特点,但他们的诗学立场和现实关注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希尼希望通过诗歌,融合自己的乡土回忆和现实思考,实现自己的爱尔兰民族主体身份建构的诉求。而张枣则更多的是希望在语言本体的向度上,用诗歌对母语进行探索和再发明。从离散诗学的角度对诗人和译者的文化身份进行探究和解读,有助于我们理解希尼诗歌中的家园意识,同时也让我们能够对张枣译诗的策略和侧重点做出更加公正而全面的评价。
张枣曾表示,自己相信“诗歌命定是不可译的”,所以他“会刻意挽留其中的某些部分”(2012:218)。和一般的诗歌翻译者不同,张枣试图挽留的并不是原诗中的某些特定意象或事件,而是一种可以启发自己探索并发明母语的诗意。张枣试图通过翻译、通过与外语的勾连,在现代汉语中寻找,追溯,并恢复古代汉语的那种甜润流转的诗意。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张枣译诗与希尼原作中构建的家园不尽相同,但我们不应该纯粹从对“原文是否忠实”这个角度来进行评价。我们更应当看到的,是张枣作为一个诗人的努力,他以一贯坚守汉语性写作的立场进行翻译,将诗歌独到的语言优美地传递给读者,重构了原作的诗意,也挽留了自己对汉语诗歌帝国的原乡想象。
注释
1. Diaspora 一词在中文中有不同的翻译,从族裔散居、移民社群到流亡、离散以至飞散与流散等(参见颜敏,2007:69-72)。本文所采用的“离散诗学”这一术语,主要是参考了饶芃子和蒲若茜在《从“本土”到“离散”:近三十年华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评述》一文中对离散文学、离散诗学、离散批评理论的论述,以及目前翻译研究中对diaspora一词的通常译法。
2. 欧阳江河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张枣在荷尔德林故居前现场翻译《面包和美酒》;树才也曾经和张枣探讨过法国诗人勒内·夏尔的翻译。
3. “载蠕载袅”最初是钱钟书在《围城》 中杜撰出来的一个词,用典雅的古体表述来描写腊肉中钻出来的一只蛆虫,通过语言和意义的反差实现了幽默的效果。张枣是否借用了钱钟书的表达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显然,张枣所使用的 “载蠕载袅”在这首诗歌的语境中,表达出了非同寻常的诗意。
Baumann, M. (2000). Diaspora: Genealogies of Semantics and Transcultural Comparison. Numen, (47), 313-337.
Gilroy, P. (1993).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London: Verso.
Hall, S.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pp.222-37).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Heaney, S. (1983). An Open Letter. Derry: Field Day Theatre Company.
Heaney, S. (1980). Preoccupation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Heaney, S. (1995). The Redress of Poetr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Henri, C. & Heaney, S. (1997). The Art of Poetry LXXV. Paris Review.
Kearney, R. (1988). Transitions: Narratives in Modern Irish Culture. Dublin:Wolfhound Press.
Leonard, K. (2007). Transnationalism, Diaspora, Translation: Comparing Punjabis and Hyderabadis Abroad. Sikh Formations, 3(1), 51-66.
Robinson, D. (1997). 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Manchester: St. Jerome.
Safran, W. (1991).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Diaspora, 1(1), 304-305.
顾彬.(1999). 综合的心智——张枣诗集《春秋来信》译后记.作家,(9).
蒲若茜、宋阳.(2011).跨文化的语言嬉戏与离散身份书写. 学术研究,(9)146-151.
苏桑娜·葛塞. 芮虎译. (2012). 风的玫瑰——致张枣. 张枣随笔选(109-11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孙文波. (2000). 我理解的90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 王家新,孙文波.中国诗歌90年代备忘录.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孙艺风.(2006).离散译者的文化使命. 中国翻译,(1):3-10.
王晓莺.(2011).当代翻译研究中的“离散”内涵与命题.上海翻译,(1),12-16.
颜敏.(2007).“离散”的意义:“流散”——兼论我国内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独特理论话语.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69-72.
张枣.(1998).春秋来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张枣.(2006). 80年代是理想覆盖一切理想主义.新京报,(4).
张枣.(2012).张枣随笔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吴文安)
* 本论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及涵化研究”(16wkpy25)及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五四时期西诗汉译流派之诗学批评研究”(15YJA752105)的阶段性成果。
王岫庐,博士,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翻译、比较文化、中国当代文学外译。
作者电子邮箱:wangxlu6@sys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