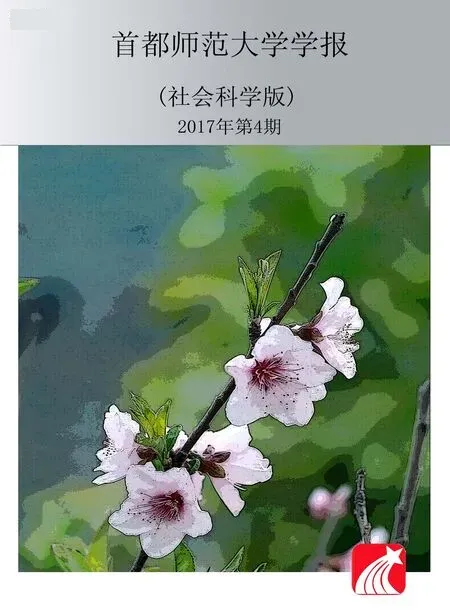从合作到冲突:李士珍与戴笠关系的演变
2017-04-14詹林
詹 林
李士珍一般被认为是国民政府警界的代表人物,故而现有的研究多限于考察其警政经历与警政思想。①仅有几篇论文研究李士珍警政经历与思想:龚维秀、郝骥:《李士珍警察教育思想探析》,《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87-92页;孙静、刘嘉:《李士珍警察教育思想述评》,《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60-62页;柳卫民:《李士珍警察教育思想述论》,《中国电力教育》,2010年第10期,第6-8页;孟奎、周宁:《李士珍和抗战后期的五年建警计划》,《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第77-81页。而关于戴笠的研究,因其身份的显著,对其特务政治的研究较为充分与深入。②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和传记有:江绍贞:《戴笠与军统》,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刘会军:《蒋介石与戴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美]魏斐德著,梁禾译:《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朱小平:《从军统到保密局(1925 至1949年国民党特工轶事)》,北京:西苑出版社,2014年版;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7年版;王蒲臣:《一代奇人戴笠将军》,台北:东大图书,2003年版;申元:《关于戴笠生平的辫正》,《浙江学刊》,1988年第1期,第116-123页;伯亮:《戴笠直接控制的西安“查干班”》,《民国春秋》,1999年第1期,第56-58页;陈学峰:《“天字号特务”戴笠》,1999年第4期,第51-53页;林凡:《戴笠与蒋介石的恩怨亲疏》,《湖北档案》,2011年第3期,第43-44页。实际上,以戴笠为首的特务政治与警政关系密切,以李士珍为代表的警察又与情治系统关系复杂。略有几篇史述性的文章谈到戴笠与李士珍围绕警权展开的争斗,但史料真实性不够,所以结论带有一定的推测性。①参见赵映林:《李士珍与戴笠之死》,《文史春秋》,2008年第10期,第16-19页;赵映林:《戴笠与李士珍争“官”》,《文史博览》,2009年第3期,第57-59页;王鹰:《两败的民国警政双雄》,《法人》,2015年第8期,第94页。本文将根据零散的档案、日记、报刊等史料,分析国民政府时期两人在特务渗透警察中的合作与冲突,以期厘清两人关系的演变,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当时警察与特务的复杂关系。
一、渗透警界的通力合作
1932年初,李士珍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任参谋本部二厅上校情报参谋,并以黄埔二期毕业生代表身份,成为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而黄埔五期的戴笠,资历虽略逊李士珍,但此时已担任参谋本部办公厅主任。②张毓中:《沧海拾笔——追忆侍从蒋介石的特勤生涯》,台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5页。戴笠长期听命于蒋介石,并参与复兴社开创工作,是该社核心组织力行社常务委员,被蒋介石破格提名主持特务处。由于“屡建功勋”,戴笠在军事情报界的地位和蒋介石给予的信任度明显高于李士珍。在复兴社开办的“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戴笠以“事务”名义主持班务。李士珍任该班训育主任兼任队长,与郑介民等协助戴笠工作。其后,在戴笠发起裁团改警、“全国警界捐机祝寿”、成立中国警察学会等向警界渗透的活动中,李士珍均与其配合默契。基于良好的合作基础,复兴社和戴笠推李士珍主持警察教育,积极支持他谋划创设中央警官学校。为统一全国警界思想,戴笠提出创办中国警察学会,李士珍以弘扬研究警察学术理论积极附和。
根据日本特别高等警察理论,李士珍提出建立“政治警察”,戴笠也表示赞赏。李士珍所提的政治警察,侧重于在警察机关内部设立应对政治活动、社会舆论的专门警察,作为社会管控的手段之一。戴笠提倡的政治警察,内容上有所不同。戴笠希望建立的政治警察,实际上是以防止间谍敌特的警察特务化,试图以警察机关掩护秘密特工,最大限度地发挥情治一体的作用。为此,戴笠命人捉刀编著《政治侦探》宣传自己的观点,并作为培训特工的教材。两者虽有所分歧,但也注意互相弥补。
两人也共同参加复兴社组织的多项活动。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张学良、杨虎城联手发起的兵变中被扣。15日,复兴社胡宗南、黄杰、宣铁吾、康泽等领衔发表通电,“以促张学良悬崖勒马,将领袖护送南来,并即日释兵,自缚待罪国门。若仍甘冒不韪,肆行叛乱、警当擐甲执戈、团结待命、用张挞伐、而振纪纲”。③《文电》,《申报》1936年12月15日(第4版)。李士珍与戴笠等在通电上签字,表示同仇敌忾。同月20、26日,在戴笠、李士珍串联组织下,王固磐、蔡劲军、酆裕坤、陈希曾、赵龙文、蔡孟坚等16名重要警察机关负责人签署《警界领袖联名通电》,提出:“我全国警界袍泽、久承领袖熏陶、同深义愤、惟责在安内、恨未能执戈前驱、亲扑此獠,自当谨遵中央决策、努力绥靖后方、务期谣诼潜消、人心静谧、抒政府后顾之忧、褫奸赃万恶之魄。”④《警界领袖联名通电》,《申报》1936年12月26日(第4版)。
为赶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对沿海各省县长、县公安局长、教育局长、中小学校长等进行抗日动员和战时轮训。1937年6月,国民政府开办庐山暑期训练团。受复兴社指派,李士珍到庐山兼任训练教官,为训练团警政组学员讲述战时警政和改革警政等课程,并将讲稿整理编印成《警察行政地位及其重要性》一书。⑤李士珍:《警察行政地位及其重要性》,中央警官学校,1937年版。在戴笠推荐下,该书成为此后一段时间内全国警政的指导意见。⑥徐源堂整理:《李士珍先生年谱》,未刊,未编页码。
二、对中央警官学校控制权的争夺
1936年,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与浙江警官学校合并成立中央警官学校,李士珍被任命为教育长。《中央警官学校组织规程》中,明确规定学校日常事务由教育长全权负责。但浙江省警官学校早已沦为特工培训基地,它的并入造成中央警官学校必须继续培训特工。部分教职员及学员,因为是特务处成员,也须听命戴笠指挥。不仅如此,戴笠还提出成立校务委员会,欲以集体负责制形式监管中央警官学校,并得到蒋介石批准。
1936年9月3日,蒋介石致电内政部:“中央警官学校应设校务委员会,承校长之命,负责设计指导监督之责。简派戴笠、王固磐、酆裕坤、赵龙文、李士珍为校务委员,以戴笠为主任委员,即日起成立校务委员会。”①《内政公报》,1936年第9卷第9期;中央警官学校校史编辑委员会:《中央警官学校校史》,中央警官学校,1973年版,第109页。蒋介石要照顾警界各方利益,五名校务委员均明确为简任官。前四人均为特务处要员,且皆浙江省警官学校人马。但从构成来看,又显得较为平衡。李士珍与赵龙文是合并的两校代表;戴笠是复兴社负责渗透警界与推动成立中央警官学校的幕后指挥者;王固磐为全国最重要警察机关的负责人;酆裕坤是全国最高警察机关的代表。所幸的是,五人中除李士珍为中央警校正式职员外,其余均为兼职。看上去李士珍势单力薄,但实际在校掌控实际权力。为保证校务委员会合法运转,蒋介石还批准修正《中央警官学校组织规程》,规定校务委员会职责为“承校长之命,负设计、指导、监督校务之责”;教育长“承校长之命,处理校务并执行校务委员会决议事项”,形成李士珍受制于校务委员会的局面。有前军统成员认为:“蒋介石圈点李士珍任教育长,使强烈竞争此职位的戴笠极不甘心,为争夺全国警察教育训练大权,成立校务委员会钳制李士珍。”②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文史集粹》(第2辑)政治军事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20-646页。此话不尽准确。其时,戴笠担负抗战及剿共的情报工作重任,志不在于争夺警察教育训练权。而是要求学校听其指挥,作为攫取全国警察机关的基地,从而实现其“领导全国警察,实行以警治国”的长远目标。③钟敏等:《蒋介石警察秘档》,北京: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任职后,戴笠安插大量亲信进入学校,使得原浙江警官学校和特务处成员占据学校主要职位,如郑锡麟为事务处长,马耐园为训育主任,王泰兴为毕业生调查室主任,杨俊奇为大队长,谷风远为大队副,张永竹、潘其武、梁翰芬、阮笃成、谈枬荪等为教官。④《内政公报》,1936年第9卷第9、10期。除抓人事安排、在师生中发展特工外,戴笠还直接按照自己意图插手教务。特别是在淞沪抗战爆发后,戴笠向蒋介石提出要利用中央警官学校教学资源培养“政治、军事、情报、警察四者兼长的政治警察干部,以适应抗战时期治安之需要”。在未与李士珍沟通的情况下,他以中央警官学校名义开设自任班主任的特种警察训练班,先后在湖南临澧、黔阳两地招生。1938年6月23日,内政部“派戴笠兼任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主任”。⑤《内政部“渝警字第00630号”训令》,《内政公报》,1938年第11卷第4-6期。这意味特务处利用中央警官学校特训班培训特工的合法化。戴笠的这种分割警权的做法,让李士珍深为忌惮。
两人矛盾还延伸至“政治警察”之争上。戴笠提出在警察机关设置“政治警察”的观点,李士珍曾表示支持,甚至还撰写文章对政治警察进行学术论证。在两人矛盾加深后,这却成为相互攻击的焦点。戴笠、酆裕坤等提出“吾国社会情形复杂,必须造就优良之高等警察,方可应付”,要求中央警官学校“政治警察之教育,特别注重,务求适合现代环境需要”。⑥《中国国民党历届历次中全会重要决议案汇编(二)》,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1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9年版,第349-401页。主张将政治警察等特工课程列入中央警官学校编配的学科教学中,在各科员生中普及特工理论及培训特工技能。李士珍表示反对,并组织人员在中央警官学校刊物上撰文予以驳斥。这些文章从警察教育的法理出发,批评“将政治警察教育与正规警察教育混为一谈”,主张“统一事权为现代国家行政之最高准则”,“裁并骈枝机关,凡与警察性质相似之机构,应一律予以裁并;划出非警察之业务。恢复警察真面目,以光明正大之态度,律己爱人之德性,使人民认识新警察完全爱民卫民”。⑦李士珍:《我国警政问题之检讨与改进》,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训练班,1943年版,第6页。
戴笠后将李士珍派人所写的文章收集起来送呈蒋介石。“李士珍这位黄埔同学不顾大体,诋毁校长耳目,不免有同室操戈之嫌,令人胆寒。”蒋介石让人传话李士珍,不得再在刊物上撰文批政治警察教育,两人矛盾愈演愈烈。
三、戴笠的攻击与李士珍的防御
由于与戴笠矛盾不断加剧,李士珍试图以中央警官学校为基地进行抗争,这是企图独控警界的戴笠所不能容忍的。在1937年至1939年里,李士珍连续四次遭遇暗算。
(一)第一次暗算
这次暗算发生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同年9月3日,奉内政部和军委会“迁往长沙训练”的命令,中央警官学校师生家属正在南京下关码头准备登船,蒋介石突然下令暂停搬迁。同月19日,蒋介石召见李士珍,要派其赴淞沪前线:“南市防务甚为重要,汝去沪上,负责督率上海警察,必须死守。现南市驻兵一旅,可与联络。”①台湾国史馆馆藏:李士珍:《参战前后日记》,1938年版,第3页,案卷号不详。此时,戴笠正在上海指挥特务处、上海市警察局警察总队、上海市保安总团、沪宁铁路警察协助国军抗战。②良雄:《戴笠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派李士珍前往受戴笠控制的上海市警察局,“负责督率上海警察”,其中似有蹊跷。李士珍婉转提出:“惟上海环境复杂,警察素质未尽纯粹,现正战时,又无训练机会,欲使个个警察均能与倭寇作战,似觉鲜有把握。”③台湾国史馆馆藏:李士珍:《参战前后日记》,1938年版,第6页,案卷号不详。李士珍暗指上海警察局上下均为特务处控制,且戴笠和军统要员蔡劲军坐镇指挥,派其去沪督率,很有困难。但蒋介石仍决定派李士珍前往。9月23日,李士珍抵沪,在“出示蒋介石手谕,告之来意”后,遭受到蔡劲军的冷遇。“似有所误会,色不愉,经余再三解释,谓此来系与渠共支危局,生死以之,他何所期,伊始释焉”。④台湾国史馆馆藏:李士珍:《参战前后日记》,1938年版,第8页,案卷号不详。李士珍赴沪实是戴笠的如意算盘,目的在于将李士珍调出中央警官学校。在上海视察一周后,为避开戴笠陷阱,李士珍再次以“上海环境复杂,且值战时,倘非熟手,必多遗误,恳赐鉴察”的理由,请求不再赴沪。蒋介石有所不快,令李士珍“再赴沪参赞一切”。⑤台湾国史馆馆藏:李士珍:《参战前后日记》,1938年版,第15页,案卷号不详。似有使李士珍与上海共存亡之意。九年后,李士珍在《警校十一年来之回忆暨今后努力之目标》文中就回忆道:“去上海视察了一周后回到南京见校长,告知没有到上海以前,觉得没有把握,看了以后,更没有把握,因为上海警察人员分子复杂,指挥有相当的困难。蔡同学在上海作局长已有两三年的历史,两三年的经验,他在那里比我好。”⑥李士珍:《警校十一年来之回忆暨今后努力之目标》,《中央警官学校季刊》,1947年第1卷秋季号,第11-18页。10月4日,李士珍以“奉内政部蒋部长之命令代表来沪犒劳”参赞警察名义到沪。⑦台湾国史馆馆藏:李士珍:《参战前后日记》,1938年版,第25页,案卷号不详。这是蒋介石惩罚性地派李士珍赴沪的体面理由,实际仍是“参赞”蔡劲军防守南市。此次在沪李士珍试图缓解矛盾、减轻压力。他两度与“戴笠兄”会晤,还“同往某银行,登一十六层之高楼上观察敌情”,“用小电影机照拍数尺电影,以资纪念”。⑧台湾国史馆馆藏:李士珍:《参战前后日记》,1938年版,第16页,案卷号不详。表面看很融洽,实际两人关系并未缓和。
李士珍在沪时的心情颇为忐忑,他在给内政部次长陶履谦的信中表明了其时的心迹:“职在此间,对于协助警局筹划江防工事,整饬纪律,并代表内政部犒劳沪警等任务,均告一段落,原无续留上海之必要,惟捐躯之志已决,见危授命,义无反顾”。⑨台湾国史馆馆藏:李士珍:《参战前后日记》,1938年版,第44页,案卷号不详。同时,他还给中央警官学校发电以示诀别:“珍虽赤手空拳,决以个人血肉,与倭寇一拼,以争我中华民族之人格,请密报部长,并转知靖、化、庆诸兄,但勿使家人知晓为盼。”⑩台湾国史馆馆藏:李士珍:《参战前后日记》,1938年版,第50页,案卷号不详。这种心迹表明了李士珍在遭受戴笠打击和蒋介石误会双重痛苦下的呐喊和抗争。“沪市7 千警察健儿均将以热血头颅,向倭寇争取代价,自顾貌兹微躬,安忍独全”,“于是权衡轻重,实行昨夜预定主张,自动再回上海,与袍泽共赴大难”,李士珍送走随员,独自一人留在上海,并电告蒋介石“即晚仍返沪,继续协助准备参战”。⑪台湾国史馆馆藏:李士珍:《参战前后日记》,1938年版,第51页,案卷号不详。在此之前是受命在沪,此后则为负气行事。好在李士珍很快恢复了理性,及时收住了缰绳,未使事态进一步恶化。11月12日,“上海既失,留此亦无意义,乃决定取杭甬、京杭两国道回京”。戴笠、蔡劲军也撤离,“已无协助之必要,决即日返京请罪”。①台湾国史馆馆藏:李士珍:《参战前后日记》,1938年版,第56页,案卷号不详。蒋介石未追究李士珍的负气之举,仍准其回校。李士珍回南京之日,内政部再次下令,指定中央警官学校迁校到重庆。令李士珍感动的是,代理校务的戴颂仪、刘诚之、马耐园在南京连日遭遇空袭、各机关院校相继撤走、交通工具奇缺的险情下,带领中央警官学校师生家属,坚持等待其一同撤退。②六十年来的中国警察编辑委员会:《六十年来的中国警察》,中央警官学校,1971年版,第584页。这无疑使李士珍增添了坚持留在中央警官学校的信心与决心。
(二)第二次暗算
在沪安全脱身1个月后,李士珍再遇暗算。1937年11月26日,中央警官学校师生家属乘火车经陇海线转去汉口,在郑州接到蒋介石“本校迁移地点,尚有变更”的电令。李士珍回忆:“接到军事委员会两个电报。一是要吾赶快回南京,一是要把中央警官学校改迁宝鸡或汉中。经长途电话请示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说明中央警校仪器与部分东西已交船运往重庆,如无必须改迁宝鸡或汉中,希望仍迁重庆;同时请转呈校长蒋中正,是否必须要李士珍回南京。旋接到电话,谓有人建议迁宝鸡或汉中比较适中,如仪器已运往重庆,可仍迁重庆;至于要回南京,是因南京警察厅长有病,要吾继任,守卫南京,不过已决定另外派人,可不必再往南京。”③李士珍:《警校十一年来之回忆暨今后努力之目标》,《中央警官学校季刊》,1947年第1卷秋季号,第11-18页。《李士珍先生年谱》也说:“先生于郑州车次,曾接军事委员会电话,奉派为首都警察厅长,以交通不便未果。”④徐源堂整理:《李士珍先生年谱》,未刊,未编页码。中央警官学校记载称调李士珍回南京的原因是:“首都警察厅长王固磐有病且年纪偏大,不适合参加即将展开的南京保卫战,需要挑选年富力强者接任首都警察厅长,建议李士珍回京接任首都警察厅长。”由此来看,此次摆布李士珍的是对任免首都警察厅长有话语权者。从当时情况分析,只有戴笠才具有这样的能力,其目的与前次一样,既要其离开中央警官学校,又要将其作为“替身”置于险地。已在千里之外的李士珍以“交通不便”再次推辞。随后,首都卫戍司令唐生智保荐的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代理首都警察厅长,最终与南京城共存亡。⑤中央警官学校校史编辑委员会:《中央警官学校校史》,中央警官学校,1973年版,第543页。
(三)第三次暗算
1938年2月,中央警官学校刚撤至重庆南岸弹子石。蒋介石电令李士珍飞汉口。李士珍抵后,何应钦告其有人向蒋介石建议,汉口危急,要其作汉口市警察局长。后经何应钦对蒋介石说明教育的重要性,才未成行。⑥李士珍:《警校十一年来之回忆暨今后努力之目标》,《中央警官学校季刊》,1947年第1卷秋季号,第11-18页。此事外界并不知晓,校内仅知李士珍,“二月七日,奉命飞汉听训,并主持五期招生事宜”。⑦中央警官学校校史编辑委员会:《中央警官学校校史》,中央警官学校,1973年版,第544页。何应钦的这次“义举“是李士珍后来构建与军方高层良好关系的重要起因。
一连三次的调动,均应为对任免重要警察机关负责人有建议权、又能随时晋见蒋介石的戴笠所为。次年,又有了第四次。不过,这次不是调动李士珍个人,而是欲将中央警官学校与陆军大学对调,将其赶出重庆,迁至贵州。此举的目的在于将李士珍与蒋介石隔离,再图倒李。后因何应钦、陈诚等军方人物的再次干涉而未能成功。
四、两人处境的逆转
(一)李士珍地位的抬升
在戴笠的穷追猛打下,李士珍不顾抗命风险坚守中央警官学校。学校迁渝后,李士珍小心谨慎,不断反省,他认为只有紧跟蒋介石才能摆脱困境,随即采取了一连串迎合蒋介石的举措。1938年12月19日,为表达对国民党的忠诚,李士珍策划中央警官学校全体毕业生集体加入国民党。⑧中央警官学校校史编辑委员会:《中央警官学校校史》,中央警官学校,1973年版,第158页。并组织人员研究蒋介石警政思想,试图从中找到改革警政的思路以贴近领袖。根据蒋介石警政思想,李士珍随后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警政的方案,并受到蒋介石的好评。由此,在军方高层何应钦、陈诚等人支持下,李士珍的政治地位不断抬升。
1945年5月,李士珍被蒋介石圈定参加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政治地位首次高于戴笠、酆裕坤,成为警界政治地位最高之人。1946年2月16日,李士珍以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参加留京中委第三次谈话会,与中常委张道藩、马超俊等连续研究关于革新党务政治问题。①《文电》,《申报》1946年2月16日(第1版)。同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召开,李士珍以浙江省宁海县国大代表身份出席会议。②《文电》,《申报》1946年11月15日(第2版)。在国大代表草拟审查会上,李士珍力争警察在宪法中的独特地位,提倡警察体制在宪法上的独立完整,呼吁由国民党中央制定警察制度,交各省县依照施行,该提案获表决通过。在随后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第108条第17 项中明确规定:“警察制度由中央立法并执行之,或交由省县执行之。”③中央警官学校校史编辑委员会:《中央警官学校校史》,中央警官学校,1973年版,第224、556页。由于李士珍的活跃表现,会上李士珍还被选为宪草整理委会委员。1947年,蒋介石宣布自10月1日起,“不再兼各军事学校校长职务,并由各该校教育长继任为校长”,“即令士珍升任校长,但凡一切重大措施仍报请蒋公核示办理”。④《李士珍赠中央警官学校校史馆题词》,《中国民国时期事事与警政奠基历史人物李士珍先生照片资料档》,李士珍外孙女李莹莹2016年赠。1948年3月29日至4月19日,李士珍参加行宪第一届国民大会,4月5日与于右任、谷正纲、胡适、张群等85人当选为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积极与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等参会24名警界代表活动,⑤《李士珍参加行宪第一届国民大会》,《中国民国时期事事与警政奠基历史人物李士珍先生照片资料档》,李士珍外孙女李莹莹2016年赠。支持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⑥徐源堂整理:《李士珍先生年谱》,未刊,未编页码。
(二)戴笠逐渐失宠
1942年后,由于与孔祥熙、宋美龄交恶,戴笠常遭蒋介石斥责,心中不时郁郁不乐,处事风格也有所转变,“爱惜羽毛,缓和外面之阻力,逐渐在政治上求发展,不可拘于特务工作之一隅”。⑦公安部档案馆编:《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此后,戴笠对李士珍的打压逐渐放松。特别是1943年4月三青团改组,“雨农、介民、唐纵均没有选出”。表面上的原因是“书记长张治中不愿使青年团特务化”,⑧公安部档案馆编:《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页。实则戴笠权力太大,得罪多方。何应钦、陈诚等军方高层,对特务机关的行事作风与其掌有别动军等武装力量深为顾忌,在蒋介石面前时常抨击戴笠。1945年,在美、英等国压力下,国民政府逐步加快民主化进程,提出废除军、警、宪、特四位一体的恐怖统治。自此,戴笠逐渐失宠。
结语
表面上看,李士珍只是国民政府时期最高警察学校的领导者,至多掌握着全国警察的教育权。但李士珍的个人能力与政治履历使其成为国家元首蒋介石身边的重要政治人物,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李士珍能够直接干预并作用于全国警政建设。他与戴笠的关系并不仅仅反映着两个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也体现了国民政府时期警察与特务两大系统之间的复杂纠葛,而警、特关系的走向对国民政府的政局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李士珍与戴笠两人的警、特观与实际争执决定了两人最终的分野,也影响了两个人物的最终命运。由于抗战期间特务机构做大对蒋介石的统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威胁,以及战后各界一致要求取消特务机构的强烈呼声,戴笠逐渐失宠并远离政治中心,并在谋求新出路的征途中命丧黄泉。李士珍由于反对战后军统被裁撤人员并入警察的方案,而丢掉谋求已久的警察总署署长之位,被迫退囿于中央警官学校之内。⑨公安部档案馆编:《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页。1949年1月,身心疲惫的李士珍在蒋介石下野后辞去中央警官学校校长。倦鸟归林之后,李士珍赴台湾研究《周易》。在《周易分类研究》一书中,他提出:“《周易》刚柔动静之道,主中庸,重协调、而其要旨,存诚而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得道多助。事必有成。”⑩李士珍:《周易分类研究》,台湾书店,1981年版,第115页。此感悟同其与戴笠及特务之间的历史关系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