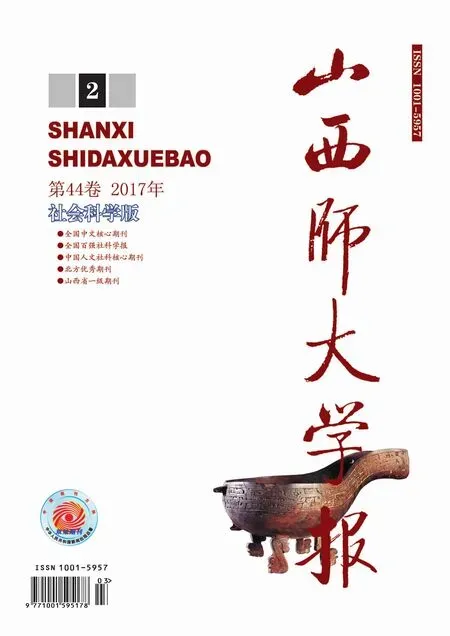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
----现代希腊国家中的马其顿人
2017-04-14王小平窦红梅
王小平,窦红梅
(山西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认同(identity)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其最初的研究主体主要指向微观层面的个人,关注个体对自我现状、现实情境、社会期待等各层面的感知,追求自我的统一性和连续性。随着对认同研究的不断深入,对认同主体的研究也上升到群体层面,涉及到家庭、社区乃至民族和国家。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社会心理学派系统地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该理论奠基人泰弗尔认为社会认同“来源于个人对自己作为某一(或某些)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的认识,以及附加于这种成员身份的价值和情感方面的意义”[1]。随着社会认同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以此理论为依据,从宏观的民族角度出发,有关民族认同的研究也得到发展。根据社会认同理论,民族认同来源于个体对自己作为民族群体成员身份的认识,更多强调的是民族成员共有的价值观和个体对民族的归属感。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在研究民族主义时,把民族认同界定为“由民族共同体成员们对构成诸民族独特遗产的象征、价值、神话、记忆和传统等模式的持续复制和重新阐释,以及带有这些传统和文化因素的该共同体诸个体成员的可变的个人身份辨识”[2]20。简单而言,就是个体承认自己是某民族的一员以及对该民族文化上的认可和情感上的归属。
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其文化对周边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希腊民族主义者看来,亚历山大大帝及古马其顿人都成长于希腊文化,都是希腊人,并不存在马其顿民族。故现代希腊自独立以来,为实现民族认同的统一,希腊政府就努力致力于重塑希腊民族,通过国家政策和政府权力的介入来构造现代希腊的民族历史神话,强调古代希腊和现代希腊在种族和文化上的连续性。在此过程中,希腊北部爱琴马其顿的马其顿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团体,其权利和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同化和压制,因此,关于这一群体的民族认同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代希腊民族认同的建构
希腊经独立战争实现民族独立后,就积极构建自己国家的民族认同,即努力构造古代希腊和现代希腊之间的历史连续性,将现代希腊人视为古代希腊人的后裔。在其国家建设过程中,通过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和学校教育的开展,构造出了一套关于现代希腊民族的历史神话,认为现代希腊民族是自古希腊以来,经拜占庭帝国后而形成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单一民族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对“使命”的信仰,希腊人相信:作为伟大文明的继承者,只是在曾经的蛮族统治下受到奴役而有所贬损,希腊人注定要在净化自己后,在整个东方播撒文明。[3]249而连接古希腊和现代希腊的希腊民族重塑过程,实则是希腊民族认同的建构与表达过程,是一个把同一身份从古老认同转变为新的认同的历史性尝试,是一个构建过去和现代之间历史桥梁的过程。
现代希腊民族认同的建构是在其独立以后才兴起的,它的连续性却已经受到了质疑。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希腊认同代表了真正的古代,但是这种代表源自欧洲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西方古典文明‘根源’的复兴,而在古典文明中,希腊发挥着核心的作用,是哲学、科学、自由和民主的源泉,这些反过来成为现代欧洲新出现的意识潮流的标志。”[4]而且,在不同社会政治背景下,民族认同所关注的侧重点并不相同。例如,与现代希腊民族主义者的主张相反,在古希腊时期没有所谓的身份认同,那时政治身份认同关注的是个人所属的城邦,唯一的明显区别是城邦和个人。因此,对古希腊的民族认同是现代以来欧洲历史发展的产物。结构主义学派和一些历史学家们也指出,发生在罗马扩张、拜占庭帝国建立和奥斯曼帝国出现之后的不明确的身份认同模式的转变都发生在全球压力下。
随着基督教国家东罗马帝国的建立,“希腊人”指的是外邦人、非基督徒,而“罗马人”指所有地中海的基督徒——“罗米人”(Romoioi)就是用来区分这些人群的。这与种族认同并不矛盾,因为希腊人并不是一个种族。在罗马帝国时期,希腊人作为类别仍然存在,但类指的是在基督教秩序外围的异教徒。由于对“希腊人”的定义不明确,因此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一个种族划分标准还不是特别清楚。而后出现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划分类似于种族的差异化,帝国制定了自身的宗教结构,基督教已经扩散到了所有的希腊人都是罗米人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那时东西部正统教会出现了矛盾,东正教代表“真正的”基督教,而西部代表着异教徒,曾经的神学分歧到现在转变为了一种种族差异。在某种意义上,在奥斯曼帝国系统中,宗教对立的民族化是希腊认同的基础。事实上,希腊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把自己归入东正教徒的政治宗教范畴。
此外,希腊民族认同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伴随着反对“罗米人”的宗教身份而出现的。随着希腊地区逐渐融入欧洲经济,它也很快被纳入为新兴的欧洲认同的一部分。在欧洲经济、科学和民主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构建希腊民族历史神话的声音也被提出,这种对希腊认同的重新建构,相对于东方专制文化而言,是可以为西方国家利益服务的。从这种角度看,现代希腊民族认同也是一种西方帝国主义的建构,而且对新兴的欧洲认同也至关重要。因此,新的希腊民族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欧洲民族主义。
希腊民族主义者积极维护古希腊和民族认同之间的链条,在此情境下,他们声称历史作为一个不变的事实可以被建构和重新呈现。他们从精神、政治等不同的层面来解释其意识形态的民族认同,这些都离不开渴望恢复与古希腊联系的这一希腊民族认同建构的背景。因此,现代希腊民族认同建构的中心是从过去到现在的过渡,如果没有这个过渡,希腊民族认同的建构就不能实现其功能。
总之,从希腊民族认同建构过程的演变中我们可以得出:首先,这种演变不能理解为仅是希腊本土范围的演变,它是全球化过程中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次,关于希腊人的重新定位以及与古希腊之间的历史连续性的构造,是一种现代欧洲民族主义的体现。最后,希腊民族认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全球紧密联系的社会政治关系中以各种形式变化形成的,这样的民族认同是在发展中不断被建构的,同时也受到全球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
二、现代希腊国家中马其顿人的身份
18世纪中期以前,在巴尔干半岛,宗教被认为是区分民族认同的决定因素,并根据人们的宗教信仰来划分他们的认同。所有奥斯曼帝国内的东正教徒,不论其文化背景,都是罗米人。单词“罗米人”含有一种政治宗教关系含义,一般而言,罗米人中拥有希腊文化背景的人们构成了更高的社会阶层。自17世纪以来,希腊语就成为巴尔干半岛中东部地区最主要的商业文化用语,因此,罗米人中讲希腊语的人们相比于其他东正教徒来说在希腊文化中更占优势地位。然而,主要的巴尔干国家的建立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在巴尔干半岛发展起来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人们的自我认同和对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等词的赋义也发生了改变。随着新的具有民族意义的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等概念的出现,民族主义者把现存的社会文化视角纳入到民族主义视角中。那些曾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受希腊文化影响或希望得到希腊文化熏陶的人们更愿意称自己为希腊人,而不再是罗米人。同样的,位于较低社会阶层上的人们趋向于称自己为保加利亚人。国家宣传在马其顿人面前设置了一个艰难的选择:他们不得不选择一个国家认同,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同时称自己归属于两个国家。
当然,我们不能拿社会文化特征和社会结构来解释民族认同或偏向于某一个民族,因为其他各种各样的因素也会影响民族认同的选择。民族认同的决定因素取决于拥有决定权的人们的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和对各因素优先顺序的考虑,可能是种族优先、家庭优先或个人优先。这种多因素决定的民族认同使得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在马其顿人中普遍存在“民族认同的流动”现象。由于马其顿人的民族认同具有流动性,因此总会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发生:例如同一家庭的成员属于不同的民族,如父亲是真正的希腊人,却也会抚养具有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认同的孩子。很多时候,教区、村庄的马其顿人中持希腊认同的人会转变为保加利亚督主教的支持者,反之亦然。令人惊讶的是有时他们还会再次转为他们原先的民族认同。总之,民族认同的流动在马其顿人中是一种常态,而非个例。
虽然民族认同是个人的政治决定,但并不意味着马其顿人可以自由选择民族认同。作为家庭成员的马其顿人不能只顾自己的真实感受去选择一种民族认同,因为在那种“生活已失去它的价值和意义”的大环境下,他们为生存选择一个民族认同意味着至少有一个政治组织可以去保护其家人免遭其他民族的迫害。
同时,希腊马其顿人的民族认同也具有一种模糊性。在现代希腊国家建设的同化过程中,他们大多都讲希腊语,使用希腊文字,和希腊人的文化大致相同,但希腊的单一民族政策则把他们排除在希腊认同的大门之外,不承认希腊有马其顿民族的存在。因此马其顿人在认同过程中存在着纠结和冲突。希腊马其顿人的少数民族地位在大的希腊民族认同中遭到了身份的丧失,认同出现混乱。小认同在大认同下受到打击和压制,马其顿人的身份出现尴尬。
三、希腊政府对马其顿人的同化和压制
巴尔干战争(1912—1913年)标志着土耳其帝国的覆灭,从而导致马其顿从土耳其帝国中分裂为塞尔维亚(瓦尔达尔马其顿)、保加利亚(皮林马其顿)和希腊(爱琴马其顿)。[5]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重新划分了马其顿的领土,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三个国家分别开始了一个对马其顿人的强制性同化过程,这三个国家进行强制同化时所采取的方法差不多相同,不过相对而言,希腊政府在主导国家建设进程中对马其顿人的同化最为成功。强制性的希腊语言教育、掠夺、杀戮、大批的逃离、生理和心理恐吓等形象地形容了爱琴马其顿在接下来的几十年的特征。今天,我们用新术语“种族清洗”来形容一个种族团体对其他占有土地的种族成员实施控制的系统性消灭。然而,这个术语是新的,与其相类似的其他实质性内容在二十世纪初的马其顿就早已存在,换句话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各国不仅想同化马其顿人,而且想破坏深深植根于马其顿人民的有关文化、语言、宗教等民族文化遗产。
马其顿人口版图在1919年希腊和保加利亚签署条约相互交换人口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导致大约六万的马其顿人不得不离开希腊而移居保加利亚。不久,同样的情形于1923年间又发生在希腊和土耳其之间,1923年希腊和土耳其签订的以宗教而非族群为名义的人口交换条约,主要是以土耳其的东正教徒与希腊的穆斯林人口的交换,而这种名义上的宗教人口交换致使大概四万马其顿人被迫离开了希腊。这种人口的转移对希腊马其顿人来说是灾难性的,在巴尔干战争之前他们在希腊北部整个区域内人口还是处于优势地位的,此时他们则变成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因此,在国家建设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进程中,希腊政府在统治爱琴马其顿之初采用的是不公正的政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马其顿人不是被同化就是被压制。在这期间,希腊承认了马其顿人的少数民族地位,并称之为说斯拉夫语的希腊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其希腊化,让爱琴马其顿人通过抹去从马其顿那里继承的文化,使他们融入到希腊文化中。在1926年所有城镇和村庄的马其顿名字被改为希腊名字,在1927年所有教堂的斯拉夫语印刷品全部被销毁,马其顿语也被严格限制使用。希腊政府这种狭隘的政策在梅塔克萨斯君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专政时期达到了顶峰,甚至个人私下里使用马其顿语也是禁止的。而马其顿人对这种政策的反抗导致了更严苛的政治对待,许多反抗者被定罪,流放到荒凉的希腊孤岛。1936年希腊政府还通过法令强制马其顿人改用希腊名字。
南斯拉夫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对爱琴马其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二战结束后,爱琴马其顿为了抵御法西斯的占领,形成了斯拉夫民族解放阵线,成为希腊共产党的一支力量。在1946—1949的希腊内战时期,大多数的马其顿人加入了民主主义共产党的阵营。希腊共产党为了吸引马其顿人为他们而战,保证了马其顿人的少数民族地位并承诺在希腊共产党统治下爱琴马其顿有很大的自治权。然而在1949年内战结束,希腊民主主义共产党失败,君主派获胜。希腊君主主义派的胜利意味着马其顿人的少数民族地位在希腊不会继续被承认。
内战结束后不久,希腊政府试图同化那些战后仍留在希腊的马其顿人。20世纪50年代,政府在马其顿民族的聚居地——弗洛里纳地区开设了许多幼儿园,用希腊语而非马其顿语来教化当地孩子们。1959年,希腊政府在狭隘地对待马其顿民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迫使马其顿人公开表示在公共集会中不再使用马其顿语。在希腊的军事专制独裁时期,(1967—1974)马其顿人居住的边界地区被视为限制区域,人们进出该地区的活动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更有甚者,1969年的一项法案规定希腊居民可以占有逃离的马其顿人留下来的财产,爱琴马其顿人民在接下来的几年一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迫。所有这些事实显示,现代希腊政府对马其顿人一直以来都实施的是狭隘的民族政策,对他们的同化和压制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因为马其顿人在希腊得不到官方承认,他们的各项基本人权也都受到限制,这种情况迫使许多马其顿人移民到别的国家。
总之,希腊政府并不承认希腊马其顿人作为少数民族的存在。希腊官方对它本国所有的少数民族的态度可以简单地总结为一句话:在希腊只有一个少数民族可以得到国际的认可,那便是少数宗教派——色雷斯的穆斯林。从希腊官方的态度我们能够看出马其顿人在希腊的位置——对希腊政府而言,他们是不存在的。希腊虽承认在爱琴马其顿有不同的人们存在,但视之为“讲斯拉夫语的希腊人”。因此,希腊马其顿人连自由表达自己民族认同的权利也被剥夺了。马其顿人针对希腊在国家建设中的残忍政策也曾团结起来发起数次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现今在希腊仍有数个马其顿人的组织在为得到希腊官方承认、维护其民族权益和保留和传承其民族文化而奋斗。这些组织从未提出如自治或脱离等敏感的话题,然而希腊政府不仅没有同意这些运动组织的请求,反而还对他们的活动进行残酷地镇压。
四、结语
毫无疑问的是,希腊政府对爱琴马其顿少数民族的压制剥夺了其基本的民族权利,并在此基础上损害了他们的其他权利,如建立文化组织机构的权利、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权利等。希腊政府除了承认希腊人以外不承认其他少数民族的存在,不仅不允许马其顿少数民族的发展,还坚持对他们的同化,只要有人挑战希腊民族认同的神话,狭隘的民族政策便会针对、迫害他们。这对于被誉为“民主的诞生地”的希腊而言无疑是一场悲剧。
现代希腊民族认同的构建和希腊官方爱琴马其顿地区马其顿少数民族的态度可以为其他现代民族国家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通过教育体系、大众传媒、公共权力干预等手段自上而下构建的民族认同,可以使人们共同享有具有同质性的民族文化,增强民族群体内的情感归属和群体整合,进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但对除本国主体民族外的其他少数民族的排斥和敌视,甚至通过公权力的强力介入对实现对少数民族的同化和压制,进而达到消除民族文化的异质性的目的,这些做法不仅会严重损害少数民族人们的基本权利和利益诉求,也与我们倡导的坚持文化多样性的理念背道而驰。
[1] Tajfel H.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London: Academic Press,1978.
[2]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 (希)约翰·科里奥普罗斯,萨诺斯·场在戏剧结构中的美学价值维莱米斯.希腊的现代进程[M].郭云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 J Friedm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4.
[5] 郝承敦.从巴尔干联邦计划看苏南在冷战时期的战略分歧[J].聊城大学学报,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