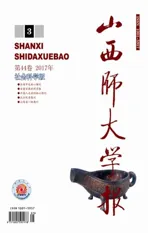明清时期北京通州晋翼会馆研究
----以明清时期的翼城商人和山西布商为重点
2017-04-14孟伟,杨波
孟 伟,杨 波
(北京晋商博物馆,北京 100025)
明清时期,通州是京师东面的门户,距京师60里许,在还没有火车的时代,从北京城到通州大约需要多半天的行程。由于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作为运河码头的通州的历史地位从元代开始,一直到晚清,备受关注。在现在通州区的博物馆内,有一块制作考究的展板,醒目的标题为“通州商业会馆分布示意图”。这一分布图以通州城区地图为底图,给出的是明清时期在通州设立商业会馆的情况,具体位置标注详明,该图与李金龙、孙兴亚等编《北京会馆资料集成》一书中所录入的图示一模一样[1]1441,本文并不希望就通州商人会馆展开全方位的论述,仅仅围绕其中的“晋翼会馆”予以考释,并且给出“历史细节”,还原“历史真实”,重点回答为什么通州会出现“晋翼会馆”?“晋翼会馆”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事实和轨迹?
一、晋翼会馆考证
(一)通州的商人会馆概况
就明清时期通州的会馆而言,目前可考如下:江苏漕运会馆(江苏漕运总局)、江苏漕运会馆(江苏漕运分局)、江西漕运会馆(万寿宫、许真君庙)、浙江漕运会馆(浙江漕运总局)、浙江漕运会馆(浙江漕运分局)、江西会馆(万寿宫)、浙江乡祠(真武庙)、山左会馆(三义庙)、晋翼会馆(翼城会馆)、山西布行会馆(布行公所)、山西染行会馆(染行公所)、张家湾山西会馆、马驹桥山西会馆[1]。
将通州会馆的特点稍加概括,不难发现:第一,通州辖区内目前可考的明清时期的会馆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具有国家地方政治特征的“漕运会馆”,另一类则是“纯粹民间的会馆”,两者本质大相径庭。国家政治与民间经济的有机结合,才是通州的历史文化真实。第二,明清时期的布匹、皮张和茶叶的贸易都离不开通州,通州在晚明前清时期维护民族关系方面的功能作用和经济效应无比巨大,没有哪一座城市能与之相提并论。第三,不能简单地将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作为“地域性商帮”,而忽视了山西商人在通州地区的文化影响和作用。第四,除了大运河的国家转输功能之外,京津唐地区的村庄、集镇市场的发展,另有其发展轨迹。大运河的国家政治功能,不是决定相应地区的“商贸格局”和“民间经济模式”的绝对因素。明清时期的国家漕运,绝对不是通州地区的全部。
事实上,通州的几个山西商人会馆本身各有其特定的历史和各有特色的商业史背景,诸如,张家湾山西会馆是以山西茶商为主的“恰克图茶叶转输码头”,马驹桥山西会馆则与城镇集市密切关联。而位于通州教子胡同的“晋翼会馆”则是山西翼城县商人的“专门化会馆”——一个深处太行山腹地的小县份,竟然具有晚明前清时期山西布商垄断北方布业的特征。对于“晋翼会馆”的特殊性,有必要进一步具体考察,而通过该会馆的碑刻可以揭开背后的秘密和历史真实。
(二)晋翼会馆现存碑刻情况
虽然通州晋翼会馆早在文革时期已被拆除,但幸运的是该会馆的部分碑刻因为镶嵌在通州区工商业联合会的后院墙壁中而得以保存至今。通州晋翼会馆碑刻共有四通,大体情况如下:
1.创建晋翼会馆碑序5输财姓氏,大清乾隆四年岁次己未蒲月谷旦立
2.重建晋翼会馆碑序,龙飞大清道光十七年岁次丁酉六月吉日立
3.新建布行公所碑记,大清道光十七年六月吉日合行同立
4.三圣会(通州)碑记,大清咸丰元年岁次辛亥如月谷旦立
现就北京通州晋翼会馆碑刻中的相关历史记载,稍加说明和延伸:
其一,通州晋翼会馆是由山西平阳府(现临汾市)翼城县商人兴建,酝酿发端于康熙后期,历雍正年间,最终于乾隆四年建成,道光、咸丰有所修葺、增扩,晚清、民国期间情况不详(缺碑记),解放后废,前后存续300多年。具体位置为原通州县城教子胡同七、八号。目前基本建筑全无,仅存碑刻四通。
其二,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不同情况,有过不同的称谓,分别为:晋翼会馆、三圣宫、布行公所、染坊公所。大略如下:通州晋翼会馆于乾隆四年“终观其成”。最初是翼城商人在通州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设“火德真君、关圣大帝、增福财神神位”,因此也称之为“三圣宫”。迨至道光年间,彻底大修,与此同时“又于会馆东偏余地亩一块,建为布行议事之所。凡议行规则,则不渎神厅,而祀事孔肃矣”。实际上,该“布行公所”是独立的,开有专门的“门楹”,属于较为纯粹的“专门化的行业性公所”。这里需要稍加指出,一些研究近代史的学者,缺乏更多的实地考察,也不曾真正了解晋商历史,仅仅凭借民国前后的情况就断然说:“会馆”和“公所”是两个时代不同的产物,“公所是西方社会的舶来品”,等等,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关于明清时期的“会馆”和“公所”的学术讨论,目前有较为普遍的偏差,抑或是缺乏实地的田野调查,抑或是“不熟悉山西商人的历史”。事实上,在京师的山西商人会馆中,衍生出“行业公所”的情况非常普遍,诸如平遥会馆与颜料公所、临襄会馆与油行公所、太原会馆与煤炭公所等,都在清代前期就是“会馆与公所”并行的情况。。在翼城商人看来,会馆与公所是一回事。纵然有所区别,仅仅在“公所”更侧重“行业议事”,会馆则强调“籍贯归属和神灵祭祀”。
稍后的“晋翼会馆”和“布行公所”,从外面看是两个独立的院子,但内部是连通的。咸丰、光绪之后,两者分开,各有门牌,门牌号码分别被标为通州教子胡同七号和八号,而依然共祀“关圣帝君”。整合起来的时候,一度也被当地人和后人称为“布行公所”,遂留下了“布行公所”的记载。
咸丰年之后,伴随着天津开埠和崛起,大运河的淤塞,南布难以北运。中国江南的布匹愈来愈被西方进口布所代替。翼城布业出现了阶段性的、地域性的萧条——在通州的布商开始减少。但是产地在冀东、行销西部地区的山西布商依然活跃。因此处于水陆码头的通州印染和颜料行业却得到发展,化学的进口颜料受到欢迎。所以,当时董理晋翼会馆的商号多为经营印染业的,往来其间的也多为从事印染和颜料业的山西商人。晚清前后,通州的人口不断增多,地方性商业长足发展,特别是“地域化的行业管理”兴起,翼城布商逐渐消失,“三圣宫”的祭祀活动也愈来愈少。
到了民国期间,晋翼会馆终于被称为“染坊公所”——以染冀东地区棉布为主。这一公所与翼城商人渐行渐远。解放后,公私合营的改造运动使得红火了近300多年的晋翼会馆失去了更多的历史氛围和韵味。与晋商在全国各地的会馆一样,晋翼会馆与翼城商人没有了直接关系,纳入了当地政府的管理体制之下。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原有建筑很早被废,更由于以通州为支点的传统山西布商的消失,以及通州区的城市化进程飞速,人口流动加快等原因,关于通州晋翼会馆的“历史细节”也随之成为“尘埃”,真正知晓这一历史真实的人也愈来愈少。
其三,虽然我们对明清时期中国戏曲史较为陌生,但是有义务也有必要为戏曲史学界提供资料和提出问题:在乾隆早期的通州晋翼会馆中,明确建有戏台,那么,当时的会馆唱不唱戏?唱什么剧种的戏?更为重要的是,什么人唱戏?什么人听戏?什么时候唱戏?为什么要唱戏?一系列的问题,直到现在我们并不清楚。这可以肯定涉及到戏曲发展史的重大问题,因为运河沿线乾隆年间至少有三十座(处、所)的山西会馆(包括山陕会馆)中都有戏台。这涉及商人与戏曲的关系问题,进一步说,山西商人与梆子戏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发展轨迹呢?
其四,需要强调的还有,晋翼会馆中,关帝为主神,陪祀则为“四大王”和“财神”:财神很普遍,而“四大王”则是指“运河神”——保护商旅安全渡河之神。这一情况也反映在另外的一条商路上,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独立庙宇——“四大王庙”和“陪祀神”,这条商路便是:淮安—周口—博爱—高平(阳城)—沁水—翼城、曲沃、襄汾—平阳府。恰好正是明代、前清时期泽潞、平阳商人南下江南的必由之路。
二、以通州晋翼会馆为线索的考察
众所周知,明清以来的山西商人行商天下500年。但是目前学术界并不完全清楚,山西商人之所以能够辉煌的背后,隐藏着更为重要的特色化经营模式和运营机制——山西商人“行商天下”的同时“会馆兴建在大江南北”——以会馆作为群体运营的工具,既开拓市场,还保障权益;既祭祀敬神,还联络乡谊。事实上,现在可考的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会馆(包括山陕会馆)数量,至少有1000余座(处、所)*明清时期山西会馆的数量,目前并不是十分清楚,十多年来笔者潜心考察,逐步发现,截止2015年夏天,已经落实1000余座(处所)。,遍布全国的大江南北。仅仅在京师便有129座(处、所)*关于山西商人在京师的会馆,必须注意:第一,山西的会馆99%属于山西商人会馆,占京师商人会馆总数的90%以上,与其它行省在京师的会馆大相径庭,不能简单地按照“京师的科举和士人会馆”来对待;第二,就会馆所建位置来看,山西商人的会馆在京师包括两大方面,109座在京师内城,20余座在京师郊区乡镇及其商路上。将以上两个方面与全国各地的会馆稍加比较,就会发现山西会馆在京师的特殊性。,甚至一个州县的商人也会在京师兴建多座(处、所)会馆。所谓的“通州晋翼会馆”,其实就是:山西平阳府翼城县的商人在通州兴建的会馆,因此而命名为“晋翼”。
以上认识充其量还停留在表面,依然回答不了为什么翼城商人会在通州兴建会馆?除了通州,翼城商人还在哪里兴建了会馆?他们建会馆的目的何在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以通州的晋翼会馆为线索展开相关的追寻,不失为一种“追根溯源的方法论”。
(一)晋翼会馆的主人:翼城商人
可以充分肯定,出现在通州的晋翼会馆的主人,就是当时的平阳府翼城县的商人。他们酝酿在通州兴建会馆是在清代康熙后期,直到乾隆四年“总观其成”,值得追寻的是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通州?从何时就出现在了通州呢?为什么要兴建会馆呢?
首先,山西翼城商人是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一支劲旅,其源头可上溯到明初——朱元璋逐蒙元北遁之时,为了强化军事、巩固成果,采用了一种特别的政策,习惯上称之为“开中制”——国家征召商人,将“九边”将士所需军粮、布匹、马草转输到指定仓库,然后,国家颁发给“盐引”,到盐区支取食盐,再行销引岸。如此一来,商人可一举两得,国家也可收一石三鸟之效,既解决军需,又行销食盐,还为商人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遇。总之,“开中制”带有国家政治扶持商业的特点。
翼城商人便是伴随着明代“开中制”的起落,而将自己的专业化经营逐渐地落实在了布匹之上,形成了明清时期独具特色的经营传统。到晚明时期,初步彰显出了“南布北运”的垄断特征。
现在的地方文化学者更看重翼城布商崛起的另外一个原因,他们主张:晚明前清时期的翼城布商的成功和辉煌,与当时的万历皇帝的母亲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慈圣皇后是翼城人,而其父则显贵一时,曾经负责为明军织造布匹,自然地成为翼城商人投靠巴结的对象,对翼城布商走红京师起了决定作用”[2]107。很显然,这纯属附会之传说,不足为凭。
其次,需要强调的是,有明一代的200多年里,一直到满清入关后的前150年(乾隆朝后期以前),翼城人所贩运的布匹,基本以“松江布”为主,也即采购地在江苏的松江府(今上海市松江区),行销地则在京师,或者九边宣大,或者张家口。而贩运棉布的线路,主要在京杭大运河上。理所当然,翼城商人难以绕开京师的门户、京杭运河的北码头通州。因此才会有一个县的商人在通州兴建专业化的布匹转输会馆。
如此情形,就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而言并不奇怪,然而就通州而言,则不能不是奇怪的问题:中国的州府、县份成千上万,何以仅仅出现唯一的一个县域商人会馆。翼城县的商人建会馆于通州,在中国的商业史上,言之为绝无仅有,堪称奇迹,也丝毫不为过。
第三,明中叶开始,一直到晚明前清时期的文人留下的笔记中,大量记述着时人对山西商人的评价。然而,稍许注意,其区域则集中在“平阳和泽潞”地区,与后来勃兴的汾州、太原府商人基本不相干。而所谓的平阳、泽潞也不是全部:平阳、襄汾(太平、襄陵)、曲沃(包括现今的侯马)、翼城、新绛(从该县过黄河与三原、泾县商人合称“山陕商人”);长治、潞城、高平、阳城、泽州。这一区域在地理的纬度上基本相同,他们出山西的商路主要在太行山东南方向。而翼城则处于以上州县的中间。这些州县商人的辉煌阶段,以晚明前清为最;换一句话说,中国明清时期的商业革命就是由以上地区的商人所掀起——山西商人“合伙制”的滥觞之源头。因此不可能不带有宋元以来“村庄自治”的传统遗风。这一点与稍后时期的晋中祁太平商人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必须引起足够的学术注意。
最后,通州晋翼会馆属于较为完全的翼城商人会馆,带有晚明前清时期平阳泽潞商人的痕迹。这在大清乾隆四年岁次己未的《创建晋翼会馆碑序5输财姓氏》碑记上表现出明显的“家族式合伙制”,尚属于不纯粹的“合伙制”,或者称之为“早期山西商人的合伙制”也是恰当的。
比如:
郭靖斋偕子铨施银六十两
刘玉值偕经、刘玉枢偕纶、李泰西偕缟,各施银一两三钱
樊秉诚偕文学施银一两一钱
安康偕宪中、宪文施银八两八钱
史含章、史含奎偕宗愈、宗迁施银三两五钱
常兆祥偕天奇、薛慥偕犹龙各施银二两
吕乾偕景镛施银一两四钱
张国纪偕凤翔、宋永申偕大观、大道、程义、王瑗各施银一两
王瑶、常鸿达、常鸿祉偕述孔、王景铎、张寿铜、焦清涟、张嘉斋各施银一两
薛绍瑄偕瀚,吕良佐偕次伊各施银八钱
……
这种“父偕子”的捐输和布施,通常出现在村庄庙宇的碑记中。而相比之下的汾州府、太原府商人的合伙制中,通常已经没有了“父子同在一个字号”的情形,甚至成为汾州、太原府商人的“民间习惯性”原则,诸如“坚决不准舅爷、少爷、姑爷在字号中从业”等号规和章程。
事实上,最近几年出现的山西商人的民间性文献资料,愈来愈清楚地表明:就明清以来山西商人合伙制的机制之先进性和纯粹性而言,平阳、泽潞地区的合同和章程,的的确确与汾州、太原府地区的商人有所不同,汾州、晋中商人的合同、章程等经营机制更加完备。
强调这一点,一方面是为了更加科学地理解翼城商人出现在通州,并修建专门化的会馆的时代与背景;另一方面,有助于理解翼城商人以及山西布商的兴衰和嬗递:商业活动起源较早的平阳、泽潞商人何以会被后来的汾州府、太原府商人所超越,这才是最为本质的方面。
(二)苏州—通州—前门外:三座“晋翼会馆”
如果一个深处山西内陆地区的小县份的商人在京师的通州码头兴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会馆,尚不足为奇的话,那么,更令人惊诧的是:翼城商人前后还在天下四聚中的两地亦兴建了会馆,一个在苏州,一个在京师的前门外。甚至,在京师并不仅仅是一个会馆,竟然区分为东晋翼会馆、西晋翼会馆以及翼城会馆。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会馆的兴建时间最迟在乾隆前期。透过这些会馆,不难理解和想象,晚明前清时期的翼城商人至少以贩运棉布而独领风骚。
1.苏州的翼城会馆。在苏州,翼城商人建有一座“翼城会馆”,始建何时,没有创始碑刻留存,但是清顾棣《桐桥倚棹录5卷六》记载:“翼城会馆,在小武当山西,翼城县商人建,有关帝殿,俗呼‘老山西会馆’。”[6]324由此可以初步断定,该会馆最迟也建在乾隆早期之前。因为苏州的“新山西会馆”——现在尚存的“全晋会馆”建于乾隆三十年,而翼城会馆既然称作“老山西会馆”,一定早于全晋会馆。也就是说,最早在苏州兴建会馆的山西商人是翼城商人,那么他们在此从事什么行当呢?毋庸置疑,他们从松江购买布匹,并且在苏州整染,而后沿运河北上,行销北方。
兴建于苏州的“翼城会馆”与建在通州的“晋翼会馆”,遥相呼应,所有的差别也不过是地理上处于“京杭大运河”的两头。抑或苏州的翼城会馆更多是为“购买”服务——从松江地区购买“松江布”;而通州的晋翼会馆则更侧重“转输”而已——大量地供应京畿地区,以及北边地区的布匹使用。
尽管属地在京师和苏州,但其功能和属性应当是标准的“水陆码头”之地的“商人会馆”,全部活动都是商人的、民间的,几乎与国家政治毫无关涉。
2.前门外的晋翼会馆。与苏州、通州的晋翼会馆相比较,在前门外鲜鱼口的晋翼会馆则要幸运得多,直到现在还保留着以往的主体建筑,位置在小蒋家胡同。因为该建筑的存在,以及这一条街上几乎清一色的翼城布商字号,因此,习惯上还称之为“布商街”。
前门外的的晋翼会馆创修于雍正十一年,完成于雍正十三年,其主体布局与苏州、通州的晋翼会馆具有相似的情形,关帝为主祀,另有四大王、财神做陪祀,现有碑刻三通留存。
不言而喻,前门外的晋翼会馆更多是服务于翼城商人在“京师布商,铺面和柜台销售”的会馆。
将苏州、通州、前门外的三处晋翼会馆稍作比较,更为重要的是将这三处会馆整合在一起,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不难发现:其在明清中国的地域性、行业性的商人历史上,乃至中国的商业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最为典型的以会馆为点,三点一线的采购、转运、加工、柜台销售一条龙、独立垄断式商业模式。
(三)恰克图的早期贸易:南京布
以通州、苏州和前门外的三座晋翼会馆为中心,进一步延伸,另外一个关乎中国经济史的大问题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从康熙年间的《尼布楚条约》签订所开启的满清与俄罗斯的商贸活动,一直持续到嘉道年间的,长达一百多年的恰克图贸易,中国出口的商品是以“南京布”为主的。那么史书中大量记载的所谓的“南京布”,到底是怎样被运出国境,又由哪些商人转输出去,采用怎样的转输方式远销草原和俄罗斯的呢?截止目前,没有一本论著交待清楚。俄国人的史籍中没有记载,中国人的资料中也没有相关的记述。然而依据海关报告等给出的进出口数字却格外清晰和分明,如此情况,委实是学术史上特别怪异的情形。究其原因,根本在学术传统——商人不入志。
最近几年,伴随着国家文化产业的政策推动,民间文献“井喷式”爆发,一系列的民间文献出现,诸如商人字号和商人家族的账册、书信、合同、清单等,给我们提供了相关的线索。其中,就有部分翼城布商和相应时期其他地区从事布匹生意的资料。一个具体的轮廓开始能够被勾勒出来:山西商人按照籍贯的行业分工之外,尚有空间地理的相互协作。
翼城商人专门从江苏松江购买布匹、沿运河转输至通州和京师;而汾州府的商人则从翼城商人手中接过相应的布匹,运抵张家口和归化,继而再行销草原,运抵恰克图与俄罗斯以物换物,换回毛皮。两个地域的商人群体,前后衔接、合力完成了“南布北销”,乃至远输俄罗斯的贸易活动。
平阳府的翼城商人秉承的是“开中制”以来的传统,汾州府商人则更多地享有“宣大议和”和“内务府皇商”的恩典、特权——以部照、部票的方式,在草原从事商贸活动。两大商贸群体,则以“京师—通州—张家口”为相互连接点,有机衔接,分享布匹贸易的利润。
以上初步显现的商业轨迹和模式,有如下线索和关联可寻:
第一,道光以前的俄罗斯海关资料证明,进入俄罗斯的“南京布”,每年有几百万两的价值与相应的皮毛易换,是既定的事实;乾隆年间库伦大臣所报告的恰克图货单中,各种“布匹”的的确确是大宗。
第二,截止目前,我们尚没有康乾时期任何汾州府商人到松江购布,以及平阳府商人在草原和恰克图的任何线索、相关资料。与此相反,平阳商人在运河沿线营建会馆;汾州府商人在草原和恰克图则格外分明和清晰,甚至在草原和恰克图的商人部照清册、名册中,95%是汾州府商人。
第三,目前有几十份康熙、乾隆年间的布商清册出现,充分表明了南来布匹在京师和张家口囤积、一次性批发的情形——账册中有“西铺存货38000两,九扣”的记载。
第四,运河北码头的通州有两个山西会馆,一个是翼城商人兴建的晋翼会馆,在通州城教子胡同南口;一个是汾州府商人为主体的“山西会馆”,在通州南十里许的张家湾。两个会馆兴建的时间几乎相同,在乾隆三十七年重修山西会馆碑记中,已经出现几十家“布商字号”,这两个会馆中的“山西布商”,他们在通州形成“对接”。将这两个会馆的“布商”予以“统一”,则一个南来,一个北去。各自的经营特征一目了然。
(四)山西布商的兴替:中国棉布的生产重心及其移动
显然,凭借晋翼会馆的兴衰未必能看到中国棉布业的兴替,而中国棉布业也不会完全由流通领域所决定。有关中国棉布业生产重心的移动,前贤学者们有过潜心的考察。但是总结前贤学者的学术成就,一个突出的问题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很好解决,那就是:庞大的棉布数字,无论是棉布本身的匹,还是与之对等的价格“白银两”,都缺乏与之相对应的行销区域和转输它们的商人(棉布字号)之间的关联性,抑或语焉不详。
也即,我们清楚地知道从元代开始,一直到清代乾隆后期的松江是整个中国的棉布生产基地,也较为清楚随后的湖北、河南、河北一线的棉布业兴起,乃至榷关和常关统计的棉布流通量,但是,截止目前并没有人清楚这些棉布的终极消费市场的“梯度分派”情况——沿北上运河码头逐渐扩散,一直到通州和京师,更没有人知道诸如翼城商人能够活跃在棉布贩运业三百多年的历史真实。
结合三座专门化运营棉布的晋翼会馆,从专门化、专业化经营棉布流通的翼城商人的兴衰,窥视棉布业的生产中心及其移动,则毫无疑问是一个有效的视角。
伴随着民间性文献的大量出现,我们可以将山西布商划分为四个明显的阶段,分别对应四个不同的时代和棉布生产重心,以及其主要行销区域和商人群体的兴替。
第一阶段,以明初“开中制”为依托的翼城商人,对应着江苏松江布的生产。在苏州整染,沿运河北上,梯度分派,供应黄河以北的北方地区、九边军需,乃至与汾州府商人配合,供给满清前期的草原和恰克图,等等,主要经营模式是“贩运批发”,运河沿线兴建的码头会馆和布商专门会馆是突出的表现。与此同时,当时所谓的“山陕商人”中,也有一批专门经营布业的商人,从河南过紫荆关入陕西,进入甘肃兰州地区,其中不乏翼城布商。以会馆为依托也是他们习惯的“运营模式”和“通常做法”。
第二阶段,大体从嘉道年间开始,另一批从事棉布业行销棉布的商人开始兴起,那就是山西晋中祁太平地区的商人,他们购买布匹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湖北、河南地区,以汉口为中心,水陆兼运,大有替代翼城商人之势,基本占据西北地区、草原和东北等地,而此时的恰克图棉布则近似消失。与此同时,与之相伴随的是晋中商人中的颜料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而票号则成为这一时期布商的资金供给后盾。
第三阶段,大体在嘉道时期,鲁西北、冀东南地区的棉布业兴起,与之对应的新一轮布商则开始转向忻州地区,他们凭借地理优势,一方面转输山西,一方面转输东、西两口(张家口和归化),供给草原以及走西口人们的生活需求。与此同时,平定、盂县地区的印染行当则对应地占据以上棉布生产地区,成为棉布生产的一个环节。
第四阶段,伴随着恰克图贸易的变迁——大量的俄罗斯工业棉布进入草原和西部地区,特别是天津开埠之后西方工业纺织品的泛滥,洋布开始占据华北市场,中国传统的棉布业以及与之对应的布匹商人明显地衰退,而新型的洋行代理行销模式成为主流。
以上情况及其发展轨迹大体上与翼城商人专门化会馆的兴衰相对应,也与山西布商的兴衰相对应,当然还有与之关联的颜料、印染、运输等行业的变化。虽然不是全部,但基本上是一个主流情形。至少,通州晋翼会馆就出现过“翼城棉布商人—布行公所—染行公所”的历时性转型。
三、结语
对以上论述稍加归纳总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如果单纯、孤立地看待大运河的北码头——通州所出现的会馆,就其中的“晋翼会馆”而言,难免会不甚了了。然而,当宏观地、整体地将这一会馆纳入明清以来的中国布业史、山西商人兴衰史的范畴予以考察,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晋翼会馆出现在通州,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它与带有浓厚国家政治色彩的、所谓的“漕运会馆”并不属于一类,有着鲜明的特征和界限。晋翼会馆属于纯民间的、纯商人的“经营模式”中的一种“工具”。
第二,将明清时期曾经引领时代、带有垄断经营特点的翼城商人——山西布商在不同地点所兴建的三座晋翼会馆予以整体考察之后,不难理解其商业垄断的形成背后,隐藏着以会馆为依托的、集购买、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一条龙运营模式。而商人会馆的“运营工具”属性得以彰显。回顾中国会馆的学术史,如此独特的商人会馆的本质属性,却被“祭乡神、联乡谊”等泛泛而谈的文化解析所笼罩。因此必须将商人会馆的本质属性予以深刻的再认识,将商人会馆研究,科学实证地回到经济史的领域中来。特别是明清的京师——明清会馆荟萃之地,一定要严谨地区分会馆的类型和属性,将纯粹的商人会馆与科举会馆、士人会馆严格地区分开来,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地再现京师的历史图画。通州的会馆情况也不例外,需要区分会馆的类型和属性。
第三,山西商人经销布业,抑或山西布商持续了明清整个历史阶段,但在山西内部的空间区域和商人群体的对应上,呈现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对应关系,与山西商人的整体发展相吻合,也与山西商人作为中国布匹的主要运销商人相吻合——由南向北,次第转移:平阳翼城布商—汾州府介休、汾阳布商—晋中祁太平布商—忻州布匹商人。
第四,面对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会馆,单纯静态的考察是难以看到历史图画的,必须改变学术方法论,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动态地整体考察。因为任何的山西商人群体都不会无缘无故地跑到异地异乡,建一个会馆去祭祀、去磕头。兴建会馆的目的,还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丝毫不能动摇的原则——商人会馆肯定是商人群体展开经济活动的“经营模式和经营工具”。
[1] 李金龙,孙兴亚.北京会馆资料集成(下)[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2] 山西政协,临汾市政协编.晋商史料全览5临汾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3] (日)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M].张正明,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4] (俄)阿5科尔萨克.俄中商贸关系史述[M].米镇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5]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6] (清)顾禄.桐桥倚棹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
[7] 范金民.清代江南棉布字号探析[J].历史研究,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