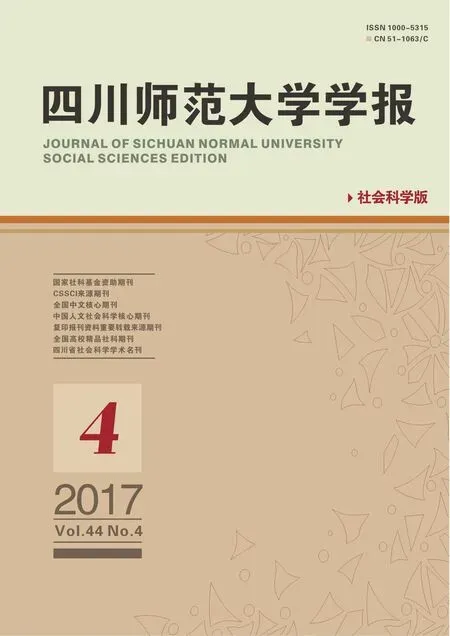清代四川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
2017-04-13林移刚
林 移 刚
(四川外国语大学 社会学系,重庆 400031)
清代四川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
林 移 刚
(四川外国语大学 社会学系,重庆 400031)
清代四川并不存在明显的祭祀圈和信仰圈。作为四川“地方性”文化的主导因子之一,民间信仰与综合文化的分区基本一致。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可分为川西平原民间信仰区、川东北民间信仰区及川南民间信仰区等三个大区。川西民间信仰区自然崇拜遗留较多,与农业相关的神灵崇拜及民间信仰较为兴盛,民间信仰的娱乐化特征非常明显;川东北民间信仰区自然崇拜等信仰遗存较多,质朴而有古韵,与农业相关的神灵崇祀虔诚而质朴,尚巫传统突出,鬼巫信仰兴盛,各亚区存在较大差异;川南民间信仰区古老信仰保留最多,最为古朴,特色民间信仰较多,受少数民族影响更为明显,民间信仰更加古朴和原始。清代四川民间信仰的地域差异是四川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差异的一种适应性结果。
民间信仰;清代;四川;区域差异
民间信仰的地域性与区域化是民间信仰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的相关研究倍受关注,民间信仰的分类研究与区域研究全面展开,并已有大量的成果问世,除江南地区的民间信仰研究成果以外,还有以妈祖崇拜为核心的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以及集中于碧霞元君、女娲、关公等神祇信仰的东北地区信仰研究成果问世。进入21世纪,随着地方性文化意识的增强以及城市化对民间信仰生存空间的挤压,区域性的民间信仰研究逐渐从东南地区扩散到全国各地,几乎每一个地区、民族甚至族群都拥有了自己的民间信仰志。作为中国民间信仰非常有特色的四川地区,学界对其区域民间信仰的考察还远远不够,不论是对四川民间信仰的描述性研究还是对四川民间信仰的区域化进程及现代转型研究都刚刚起步[1],四川民间信仰的个案如川主信仰、梓潼信仰、坛神信仰[2]、璧山神信仰、马头娘信仰等少有研究成果出现或研究不够深入,四川民间信仰的整体研究仍然缺乏、断代研究也非常薄弱,对四川民族地区的民间信仰的形成及变迁研究成果更少。清代作为四川民间信仰以及四川文化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偏偏又是四川民间信仰研究最薄弱、成果最少的朝代之一。鉴此,本文拟通过对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分析,试图对四川民间信仰进行初步的整体勾勒①。
一 清代四川文化综合分区与民间信仰的分区
在清代四川,明显的祭祀圈和信仰圈并不存在。原有土著社会和信仰形态的巨变以及移民“五方杂处”、“各祀其神”的现实,既打破了原有的土著社会所构建的信仰格局,又使得新社会中以所谓乡神崇拜为主要内容的信仰体系缺乏明确的地理边界,使大范围内某一神灵被广泛接受并排斥其他神灵而存在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虽然清初四川移民人数众多,自清代中期之后大多数地方移民人数已超过土著,但是移民社会中以会馆祀神为主体的信仰形态象征意义更明显。基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巨大差异,移民并不能将其原籍信仰形态移植于清代四川社会[3],经过精心选择的会馆神灵更多体现了移民融入当地的决心[4]。因此,清代四川民间信仰既没有因为移民的进入而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也没有因为移民的进入和在地化而形成新的祭祀圈和信仰圈。所以,不能以祭祀圈理论来分析清代四川民间信仰格局。
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四川的文化独立性较强,是中国复杂地方性知识体系中的重要区域。“夷汉杂居”的民族成份和“大移民”的背景,又使之具备了一种“杂糅”的独特信仰风俗。有清一代,四川区域文化经过不断的渗透与同化,在生理、心理、性格以及劳动方式、饮居习惯等方面都发生了适应新环境而相关整合的衍变,并磁化般地不断衍生出一些既不同于四川土著又异于移民原籍的新四川的“地方性”,这种文化深深地刻上了巴蜀地域固有山川地势、饮居条件等自然印记,表现出与四川传统生存主体一脉相承的群体性格特征和地方意识。因为移民来源与分布在四川各地区有明显的差异,加之地理环境与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差异的影响,清代四川文化区域性差异比较明显。蓝勇曾以政区、移民、方言、民俗、民风(个性特征)与文化区域的关系等为主导因子对古代四川进行文化区的划分,并将其划分为川西平原文化区、川东北文化区以及上下川南文化区,他“对四川三大民俗区的形成依据的主要历史文化积累主要是明清时期”[5]454-500;序言。民间信仰是四川“地方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导因子之一。笔者在对明清以来四川方志中祠庙部分进行排比统计和研究之后发现,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区域差异,并根据这些差异将其分为川西平原民间信仰区、川东北民间信仰区及川南民间信仰区,这与蓝勇提出的四川综合文化分区基本一致。
二 清代四川民间信仰三大区的差异
(一)川西民间信仰区
该区由成都府、龙安府、绵州直隶州、眉州直隶州、资州直隶州以及邛州的大邑、蒲江等地区组成。从文化分区来看,成都和邛州可以算一个亚区,眉州、资州、龙安府和绵州文化有更多相似之处。在信仰方面,这方面的区分不是特别明显。川西民间信仰区地处四川盆地以及盆地的低山地区,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相对较好,是传统天府之国的核心区域,其民间信仰具有非常典型的特征。
1.自然崇拜遗留较多
成都平原有着长期的经济文化繁荣,时至清代,在文化方面仍然有着丰厚的积淀,这在民间信仰方面有多方面的表现。在自然崇拜方面,各种天体、天象崇拜尚有遗留。在成都、丹棱、简阳、德阳等地区都有祭祀天神的“上九节”,但其主要活动都是以放灯为主的各种娱乐及商业交流。在金堂县、江油县和成都等地,农历十一月十九日有祭祀太阳的“太阳会”,“各刹诵佛念经,乡人亦于斯日虔礼而敬祀”[6]卷三《风俗》;成都的太阳会期“告白,大书特书太阳胜会,合资演戏”[7]234;华阳县还有清代重修的雷祖庙,用于“春秋致祭”[7]554。成都等地都有东岳庙,但东岳信仰已经更加世俗化,东岳神的神职更加泛化。该区内河流纵横,涪江、岷江、沱江、青衣江、大渡河等穿过境内,因此该区水神崇拜盛行。植物崇拜方面,德阳县还有古树崇拜的遗留,人们用该县东玉皇观前的古柏树,“下注艾以灸之,云能祛病,在目齐目,在心齐心”[8]卷十八《风俗》;成都、华阳、郫县、金堂县则有清明插柳戴柳辟邪的习俗[9]卷九《山货》。简阳县等地尚存石敢当信仰,“有不埋石者,必于门中直钉一虎头扁(匾),中书‘泰山石敢当’或立石刻此字,犹古意”[10]卷六《风俗》。成都府火神崇拜兴盛,灌县、汉州、华阳县地方志中都有五座以上火神庙,且大多为清代所建;这些地方都有火神会,时间从四月到十一月不等。温江的城隍信仰比较虔诚,体现出该地区老四川文化的特色。
2.与农业相关的神灵崇拜及民间信仰较为兴盛
成都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发展农业的重要基础,唐代成都就有“扬一益二”之称。区域内人们重视农业,社神、田祖及土地神等与农业相关的神灵崇拜都比较兴盛[11]。《崇宁州志》记载:“各乡村设立土地庙,岁逢六月初六或七月初七,乡人置办香烛、鸡、酒,诣庙祭赛,以祈秋稔。”[12]卷二《风俗》华阳县、温江县等都有祭祀社神的社日,温江县乡民还要“各备牲体献奠”[13]卷十四《风俗》。在“春夏栽秧毕”后的五月二十日“谷神生辰”这一天,灌县、成都县、温江县都要祭祀谷神,金堂县人还要“筹钱请梨园作剧,祈祷年丰以祀禾神”[14]卷二《风俗》,新繁县“谷王诞”、“谷王会”,“县之清流场于是日演剧赛神”[15]卷二《风俗》。
川西农业发达,牛王崇拜突出。金堂县民间过牛王节“自明时皆然”[10]卷六《风俗》,这是关于四川牛王会的最早记载。查阅清代以来的四川地方志,全省有牛王会的习俗共有53县,而在川西民间信仰区内的35个县、州中,方志中明确记载有牛王会的共21个[16]。牛王会也是人们对牛耕文化的一种体现,反映了人们对牛的敬重、保护之情。
川西蚕桑业发达,清代仍有大量蚕神崇拜的习俗和表现。四川以蚕丛为始祖和蚕神,双流县有蚕丛祠[17]。据记载,新繁县蚕市边的三皇殿内的神像,“即蚕丛氏也”[15]卷二《风俗》;大邑县、江油县、眉州等县都有在正月十五“祀先蚕”、“浴蚕种”的习俗[18]卷三《风俗》;彭山县“(九日)浴蚕种,十五日祭先蚕”[19]卷三《风俗》;清代成都县、华阳县还把对蚕的祭祀与蚕器的买卖活动结合起来。
农业社会对医药行业的依赖较大,在川西的多数州县,药王崇拜非常突出。成都、新都、金堂、郫县、双流、灌县、新津、德阳等地都有药王庙,基本上都奉祀孙思邈。金堂、新繁、新津等地在二、三月份还举办药王会,医家奉“孙思邈”为药王。《成都竹枝词》中有反映药王会的繁荣景象和药王崇拜的世俗化特征的竹枝词:
绿色二月好春光,席扎牌楼灯烛光。妇女丁男齐结束,药王庙里烧拜香。采亭罗鼓送南瓜,送到人家一片哗。吃罢酒筵才散去,明年果否有娇娃?[20]3199
3.民间信仰的娱乐化特征非常明显
川西平原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发达的经济状况使其自古以来就有繁荣的商业和“俗好娱乐”的传统,市侩气息非常浓厚,并因此养成了居民尚游乐、重饮食和休闲的传统。在民间信仰方面,该区域内的民间信仰都显得严肃不足、娱乐有余,祀神、娱神成份不多,娱人要素十足。一年之中,游百病、踏青、赶花会等与民间信仰相关的活动,都成为川西民众游乐的机会。而风行于川西平原各地的名目众多的迎神赛会,则是该地区游乐的最主要的体现和最重要的空间载体。无论是成都的药王会、花会,还是绵州、龙安府区的下元节赛会;无论是正月初九日的“上九会”,二月十六日的“玉皇会”,还是二月初三日的“璧山会”,五、六月之间的“青苗会”,十月的“牛王会”等等,在这些以祀神名义举行的赛会中,“每逢神会,必演戏庆祝,祈福还愿者皆携香楮、酒肴致敬尽礼焉”[21]卷十五《风俗》。
(二)川东北民间信仰区
川东北信仰区包括重庆府、夔州府、忠州直隶州、酉阳直隶州、石柱厅、顺庆府、绥定府、太平厅、潼川府以及保宁府。该信仰区幅员最为辽阔,东靠湖北,北接陕西,南临湖南、贵州等地。其中,保宁府和太平厅属川北区。明清以来,随着土著的消失和湖广移民的进入,川北地区的文化独立性慢慢消失,“今川东和川北地区更加自成一体,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风俗区”[5]473。石柱直隶厅和酉阳直隶州位于巫山、大娄山山区,区内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杂居,其民间信仰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但是因其地接湖北、重庆,又接受了中原王朝的统治和汉化,且清初接受移民众多,所以总体上尚属于川东民间信仰区。川东北区域内的民间信仰特征非常鲜明,各亚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1.自然崇拜等信仰遗存较多,质朴而有古韵
川东北地区地形复杂,人口众多,与成都平原相比,该地区较为封闭、落后,因此,自古以来就是民间信仰的兴盛之地。时至清代,各种民间信仰类型仍有大量保留,且多有古韵。在自然崇拜和自然神信仰方面,天体、天象崇拜皆有遗留。如秀山县有太阳庙,并有民众“祀日”的作法[22]卷二《地志》;云阳、万县、涪陵、大竹等地有供祀雷神的雷神庙、雷祖庙或雷祖殿,人们在此奉祀雷神,举办“雷醮”等活动,“祈佑民和岁稔”[23]卷十九《杂俗》;新宁、广安、三台等地在六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要举行“雷祖会”,祭祀雷神;綦江县在六月二十四日有祭祀风神的习俗;南川、云阳等地都有清代重修的地母殿[24]卷五十八《风俗记》。社神、土地神及田祖等农业神灵同样在川东北被广泛崇祀。川东北河流纵横,长江穿区而过,所以境内水神崇拜最为兴盛,无论是江渎神、龙王或龙神,还是杨泗、李冰、大禹,甚至包括肖公、晏公及天后等各路水神,在该区域内都有被大量崇祀。合江县的真武阁还将真武当水神崇祀,这在四川比较少见。在川东北地区,地形多以山地为主,境内山岳林立,故而山神崇拜直至清代仍见余绪,其中如巫山神女崇拜、中江石崇拜等直至今天仍有表现。在酉阳、石柱等民族地区,自然崇拜更为盛行和古老。如酉阳的蚩尤庙是煮盐行业的保护神,在彭水县,“夏月天旱,土人常祷雨于此”[25]卷四《艺文·祀鹁鸠井记》,蚩尤也充任了水神。酉阳的山神造型奇特,神通广大,有“退贼”、“疗疾”、“雨阳立应”等功力,人们对其极为虔诚,祭祀非常讲究[26]卷九《祠庙》。在川东北,火神崇拜同样盛行,域内火神庙的数量几可与水神庙相当,其方志中记载的火神庙就有60余座。动植物崇拜方面,川东北的牛王庙和马王庙数量众多,用桃木等植物辟邪的观念在潼川府、重庆府、夔州府各州县都比较常见[27]卷三。重庆府非常重视对花神的祭祀,是四川花朝节最集中的区域之一②。
2.与农业相关的神灵崇祀虔诚而质朴
作为四川地区重要的粮食产区,川东北地区农业神灵的祭祀盛行。春秋社祭在许多地方仍有余绪,禁忌颇多。如三台、蓬溪、云阳等地都会在二月二日“醮谢中霤,祀田祖以祈谷实”[28]卷四《风俗》。云阳、万县等地,在“社日”禁不动土,谓为“五戊大社”,民间无敢犯之者;闺房是日停针线,不作组钏,谓之“忌日”[29]卷二《风俗》。在大竹等地,三、四月间,要祭土谷神,并用傀儡演秧苗戏,但相对于成都平原的娱神性质的祭祀演出,川东北的各种演戏显得质朴而又富有野蛮性。大竹、荣县六月初六日祭祀神农“田祖”炎帝时,老百姓都要在神龙宫定期奉上丰盛的供品,“大乐数日乃止,各乡村亦于是日宰鸡鸭,以血涂钱纸,歃田亩”,与远古时期的“血祭”社神略有相似;同时还要祭祀雷神和火神[23]卷十九《杂俗》。作为农业保护神和家乡保护神的土地神,在川东北可谓“村巷处处奉之”[30]6-3-9700。在邻水县、云阳县等地,土地祠“上下街皆有之”,农家“或家自立祠,或坊村共之……坊市仅祀当坊土地,村庄兼祀青苗、蝗虫”[29]卷二《风俗》。潼川、顺庆等地,在清代形成了养蚕专区,“比户饲蚕”[31]187,成为长江上游产蚕基地之一,因此祀蚕神的活动同样较多。三台、盐亭、遂宁、射洪、苍溪等地都有拜“蚕夫姑母”的活动,三台县在二月朔日还有蚕姑会[28]卷四《风俗》。
3.尚巫传统突出,鬼巫信仰兴盛
川东北“居重山之间,壅蔽多热,又地气噫泄而常雨,土人多病,瘴疟头痛脾泄”[32]卷六《夔州药记》。又加之地邻荆楚,因此自古有尚巫的传统,至清代鬼巫信仰仍然分外盛行,在清明、中元、冬至三个节日都有祭鬼习俗。在清明时节,酉阳、巫山、万县等地都要扫墓、祭祖,州县官还得主持“祭无祀鬼神”。中元时节,巫山县“各庙作盂兰会,半月之间,金鼓嶢钯之声,刮耳不休。又于旷野放路烛,河干点放河灯……赈济孤魂野鬼”[33]卷十五《风俗》。酉阳于中元节前几天就要焚烧纸钱,“县官祭无祀鬼神”[26]卷十九《风俗》。万县除“中元祀祖”外,对新鬼要“剪纸为礼服,当亵服贮纸箱中焚之,谓之送寒衣”,还要“醵金作盂兰会”,以“赈济穷鬼”[34]卷十二《风俗》。而在巴县、温江、丹棱、彭山等地,“送寒衣”习俗主要是在冬至节。巴县、合川、万源等地都有用石敢当、吞口和将军箭镇厌不祥的信仰。《渠县志》记录有关吞口的材料,其作法颇显独特与古朴:
居室犯凶煞者,于门前立石高三四尺,圆瞪两目,张口露牙,大书“泰山石敢当”五字于胸前,或于门楣悬圆木若车轮,以五色绘太极图及八卦于其上,或贴“一善”二字与“山海镇”三字。凡以镇厌不祥也。[35]卷二《礼俗》
川东北地区迷信色彩较浓,禁忌较多。南川、巴县、合川、铜梁、江津、大足等地,在正月元旦,多有“禁扫地,倾水,忌兆财出”[36]215的习俗。武胜地区,正月、腊月多禁忌,“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谓为杨公忌日,诸事不宜,每晨忌说梦鬼猴蛇虎豹”[37]卷六《礼俗》。在川东北地区,“疾病虽用医药,而亦不废巫师”[31]145,治病、驱疫、祈子、卜物等都大量采用巫术,因为迷信使该地区巫覡地位较高,信巫、招巫风俗盛行。在南川、江津等地,“岁暮万物已息,百业当休,城郭烟户稠密,招巫赛神者,夜夜不绝”[38]卷六《风土》。在巴县、合川等地,还有抓开水、抓油锅等各种神判巫术,各种祈晴求雨、“平安清醮”等活动在生产过程中仍然常见[39]。
4.各亚区民间信仰存在较大差异
川东北地区东临湖北、湖南,南接贵州,北连陕西,处于秦、楚、蜀文化的交界带,幅员辽阔,虽然整个区域内民间信仰有共同的基本特征,但是各亚区内的民间信仰各具特色。大体来说,该区域民间信仰可以分为:保宁府亚区,夔州和忠州亚区,潼川府亚区,顺庆府、绥定府及太平厅亚区,重庆府亚区,石柱厅和酉阳州亚区。
夔州府、忠州亚区,位于川东之门户之地,地形以山地为主,比较封闭、落后,古老民间信仰保留较多,三国人物崇拜较为盛行。光绪《奉节县志》云:“初七为人日节,夔人重诸葛公。旧于是日结伴出游八阵图,谓之踏碛”;因地近湖北,自古巫风盛行,“妇女拾小石之可穿者系于钗头,以为一岁之端”[40]卷十七《风俗》。
石柱厅和酉阳州亚区位于巫山、大娄山山区,内部民族为汉族或者少数民族,汉夷杂居。秀山、黔江、酉阳等地“社公社母”、“山神”等原始信仰盛行。酉阳州二月“上丁,州县官齐宿,从事于圣庙。次日,祀山川社稷诸神”;人物崇拜方面,既崇祀三国人物张飞等,也在土主庙中崇祀“湖耳青草公”[26]卷十九《风俗》。该区虽为民族地区,移民带来的外来信仰也有所体现,区内移民会馆众多,祀神与其他地方无异。酉阳忠烈宫“祀唐雎阳殉难裨将南公齐”,其水神信仰中有来自于湖北的杨泗,也有来自于江西的萧公[26]卷九《祠庙》,五通、五显等外来信仰在酉阳、石柱等地也有一定影响与表现。
绥定府、顺庆府、太平厅亚区,东靠夔州府,西邻潼川府,南为重庆府,北邻保宁府,接陕西地界,这样的地理区位使该地区民间信仰独立性并不太强。临近夔州府的州县尚巫崇鬼,临近潼川府和川西平原的州县有文昌会、土地会、观音会、关帝会等祀神集会,临近保宁府的营山有瘟祖会、禾苗会等。元宵前五日,营山还有逐鬼风俗存在。渠县正月二十八日有土主会,崇祀渠县冯公。该亚区内以祀神名义举行的集会较多,有一定的娱乐色彩和商业性,除上文所述外,还有城隍会、盂兰盆会、川主会、中元会、鹊桥会、雷公会、药王会、龙会、禹王会、王爷会、许真君会、新宁镇江王爷会、报恩会、雷神会、渠县草王会、办社会等。川北保宁府的仪陇、阆中、苍溪等地五月十五日有瘟祖会,为诸会之最,“每日远近诸庙拜跪者,香烟如雾,彻夜不息”[41]卷二《风俗》,但此地将梓潼帝君作为瘟祖神崇祀,颇有区域特色。因地近川西平原,保宁府的信仰娱乐气息十分浓厚,在瘟祖会期间,有神像出游,演剧至数十日。另外,该地区祈子风俗较盛,求子方式多种多样,广元有请紫姑求子,“假神诞滨送子之戏”[42]卷七《风俗》;阆中“妇人之无子者,窃面盏以归,和油煎而食之,则生子。次年遇此会,出油数斤以答神贶”,“也有妇人往往登塔子山扫塔以求子者”[43]卷三《风俗》;巴州则有“打儿洞”③求子。
重庆府亚区,州县较多,地域广袤,商业繁荣,“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44]423,迷信色彩相对较浓,禁忌很多,民间信仰兼有楚、蜀特色。农业神灵崇祀盛行,牛王会在许多州县都有举行。花朝、上巳等传统节日和八月中秋偷瓜送子之信仰仍有保留。璧山神崇拜是该区较具特色的古老信仰,在璧山、江津、合川等县较为盛行,并影响川西德阳、川南夹江等州县。重庆府在清代是重要的移民汇集区,湖广移民众多,因此区内移民信仰遗留和影响较多。
潼川府亚区,地处四川盆地的低山丘陵地区,民间信仰与重庆更为相似,敬神祀鬼,也有牛王会、送寒衣、清明、中元及下元祭鬼等习俗,射洪、盐亭、三台、遂宁都有花朝祀花神的活动。但是,该区临近川西成都府,风俗亦与成都府相近,蓬溪、安岳等地文昌崇拜盛行,文昌会等迎神赛会的娱乐气息较川东其他地区更浓。
总之,该区域内信仰类型最复杂,相比成都平原,不管是农业神灵,还是自然崇拜,抑或巫术信仰,都显得较为质朴。虽然明清时代的移民改变了其信仰主体,带来了楚、秦信仰等新的信仰元素,但是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区民间信仰的内容和特色。
(三)川南民间信仰区
该信仰区由叙州府、叙永厅、嘉定府、泸州直隶州、宁远府以及雅州府东部的雅安、名山、芦山、荥经、清溪等县组成,这个区域大部分属于蓝勇先生所说老四川的版图,是四川文化和民俗区中的相对稳定区[5]482-484,其民间信仰表现出如下特征。
1.古老信仰保留最多,最为古朴
在自然崇拜方面,这一区域的古老信仰保留最多,山岳崇拜、水神崇拜、火神崇拜盛行。如《大宁县志》载:“初九日为上九会,祀神如元旦,邑人士肃衣冠,迓地方官师,设堂祀上帝祈谷,曰‘春祈会’。先期斋沐,禁止屠宰,极其诚敬。”[45]卷一《风俗》宁远府的会理州有风神庙,并保留着比较古朴的风神信仰。南溪县有东岳庙,以“神颇灵异”著称,“每年办会,乡人报祈演剧,甚为踊跃”;每年三月,乡人还要筹办东皇会,“架设棚楼出神演戏,全镇男女游观不绝”[46]卷三《风俗》。马边厅、冕宁县地方志中都记载有四川社会少有的西岳庙。区域内河流纵横,长江穿境而过,因此水神崇拜尤兴,且异常古朴。珙县尚存祀“珙水之神”的普惠侯祠,据称“祷雨则应”[47]卷三《坛庙》;合江的真武阁所祀真武也被人们奉为水神。泸州、嘉定府、叙州府等地区火神崇拜非常突出。合江县方志中记录有9座火神庙,且多为清代所建[48]卷十七《祠庙》;乐山县有泌水院,内供神农以镇厌火患,每年五月初一日,还要举行颇有特色的炎帝会;南溪县崇祀火神祝融最为隆重,祭品丰富,有“帛一、猪一、羊一、果品五盘、尊一爵”[46]卷三《风俗》。合江县等在二月十五花朝也要祀花神。宜宾县在清初还保留着将古树当作神灵的原始崇拜[49]41。
川南信仰区以稻作为主,对农神和谷神的供奉仪式更为古朴虔诚。合江县 “乡城居民,各择山谷清幽之地建立土坛,祀五谷之神”,名曰“天堂”,又名“清斋山”;在“每岁三、六、九月,用牲醴致祭,亦祈年之意也”[48]卷十八《风俗》。洪雅县在三月十五日要祀农神炎帝;乐山县、夹江县都在农历五月初一举行“炎帝会”崇祀农神。这与前面提及的川东地区大竹县六月初六祭祀农神“田祖”炎帝及雷神、火神的习俗略有不同。
2.特色民间信仰较多
作为文化区,川南区是土著文化保留最多的文化风俗区,在饮食、游艺、语言和节庆方面保留了许多古老文化,存在许多独特的民间信仰类型。在嘉定府,虽然也有李冰(父子)、大禹等水神,但是影响最大的是其区域性的水神——太守赵昱。该神被崇为川主,影响了周边地区,并成为四川普遍崇拜的水神之一。在洪雅县和彭山县,清代流行着三霄娘娘信仰,该神掌握着人间的生育和婴幼儿的祸福。洪雅县还将三宵神的祭祀和上巳节祀高禖相联系,并有庆贺“媒神圣母诞辰”的“三婆会”,“演剧庆祝,妇女求子者杂沓”[50]卷三《风俗》。该信仰区也是三大区域中川主信仰最集中的区域。据统计,清代有川主会的州县共有37个,而上下川南区便占14个,而且川主会比其他地方更原始、更隆重[5]473-474。
3.受少数民族影响更明显,民间信仰更古朴和原始
该区域内,历史时期的人口以少数民族为主。明清时代仍然“华与夷杂”,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风俗相互影响,互为交融。在民间信仰方面,汉族的信仰有少数民族的影子,少数民族信仰浸染汉族要素。各种原始信仰、自然信仰和人物崇拜都较为原始,各种信仰活动如汉源、荥经、雅安、天全等县的天公会、土地会以及名山、荥经等地的王爷会、城隍会等均较为古老而纯朴。宁远府的川主会往往与彝族的火把节混在一起;盐源县的“火把会”实则汉族川主会与彝族回星节的混淆。其他宗教性神会,如大烛会、九品烛、九皇会、盂兰盆会、蟠桃大会、观音会、大佛会,虽然宗教意味十足,但受汉族的影响,已被充分娱乐化和商业化。如名山、荥经等地举行城隍会时,迎玉烛的活动甚为热闹,已少有宗教意味[31]107。雅州府东部虽然少数民族众多,然而由于其毗邻汉族聚居地,且与汉族杂居,所以迷信色彩浓厚,巫术盛行,巫医活跃。如天全、雅安、荥经等地均有镜听、乞巧等问卜风俗;荥经县同样是“商俗尚鬼,经民甚焉。有疾病城市尚服药,乡民则延巫祈鬼,或迎村神于家以祷之,并卜吉凶”[51]卷二《舆地志·风俗》。
总之,川南民间信仰区是四川三大区内民间信仰内容最为古朴的一个地区,无论是保留至清代的各种自然崇拜、鬼巫信仰以及人物、人神崇拜,还是各种祀神的活动,无论是辖区内少数民族的信仰,还是汉族民间信仰,从信仰的形式到内容都体现了历史时期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这与蓝勇所说上下川南文化区作为“老四川”的区域文化特色相一致。
三 民间信仰区域性差异之导因
“一个区域文化特色的形成既取决于一定地理环境和在此基础上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也取决于受外来文化交流的影响。”[5]455由于四川三大民间信仰区地形、气候、地貌、植被、水文等自然环境因素差异较大,其产业方式、开发程度及经济发展水平也有明显差异,反映在民间信仰方面就表现为显著的区域差异。与此同时,明清是四川区域文化构建的重要时期和人文环境变动最大的时期,这种变动在民间信仰方面有多方面的折射。因此可以说,清代四川民间信仰的地域差异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差异的一种适应性结果。
(一)对自然环境的感知和调适的差异
地处长江上游地区的四川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四周多为海拔1000-3000米的山地和高原,西南分别是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北面是大巴山,东面是巫山,中部是平原,整个四川处于一个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地理单元内。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四川有着一个封闭的、稳定的文化结构”[52]605。在民间信仰方面,明清以前,四川受外界影响较小,民间信仰有典型的承袭性,但区域内各地区之间自然环境差异较大,区域文化和民间信仰同样有着明显差异。
川西民间信仰区的核心区域为成都平原区,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平原和河网稠密地区之一,地势平坦,海拔450-750米,地表相对高差都在20米以下,气候温暖湿润,地表松散,沉积物巨厚,为四川最肥沃的土壤区,加之交通便利,因此成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农业经济区,自古以来也是西南地区的繁华地带。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折射在民间信仰方面有三种表现:其一,平原地带地域和经济的开阔性,使得川西平原的民间信仰表现出相对于四川其他地区难得的开放性,川主信仰、梓潼信仰、马头娘信仰等都从蜀地辐射影响到周边省份,特别是梓潼信仰还得以沿长江流域传播,最终成为全国性的信仰;其二,川西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其民间信仰表现出明显的包容性,人们尚自然,自由率性,对周边省份和省内其他地方的民间信仰能够兼容并包;其三,川西平原繁荣的经济和富足的生活使得人们自古就有重娱乐的传统,其民间信仰的娱乐色彩普遍较强。
川东北民间信仰区东临湖北、湖南,北连陕西,南接贵州,西以龙泉山等与川西平原划界,幅员辽阔,地多险峻,以丘陵、山地为主,东有巫山,北有大巴山,南有大娄山,东南有武陵山,地形由南北向长江河谷倾斜。这种封闭式的地理环境孕育和保留了大量古老的民间信仰,同时使得巫术在川东北地区广为流传,经久不衰。域内峰峦叠翠,江河纵横,使得各种自然崇拜直至清代仍然非常盛行,特别是在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川南民间信仰区位于岷江中下游地区、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系中段,地貌类型为中山峡谷,全区面积94%为山地,海拔多在3000米左右。该区从区位来说,处于四川的西南腹地,远离发达的秦陇文化和荆楚文化,长期以来主要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因此,直至明清,川南地区一直只能算是川西平原文明的末端,其文化和风俗与滇东北更为相似,川西多游艺、享乐之风对其有一定影响。其地理的封闭性和地缘的特殊性,使得川南民间信仰区的信仰在四川最为古老和独立。该区降水较少,因此,水神庙数量最多,对水神的奉祀尤勤,迎城隍的活动最为虔诚。
自然环境对清代四川民间信仰的构建和区域性差异起着决定性作用。首先,地缘关系决定着移民的来源和分布。川东与荆楚的历史渊源和地缘优势,使得川东移民更多,其民间信仰也更为相似;川西与秦陇民间信仰渗透更多;川南与滇东北更为相似,川南地区古老的民风与信仰同样是吸引闽粤客家的重要因素。其次,移民进入四川后,只能在尊重自然环境、充分利用自然条件的基础上休养生息。因此,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民间信仰也同样是以一定的自然环境为依据。如水神信仰以及和农业相关的神灵信仰在清代四川各地都非常盛行;在瘟疫、蝗灾等频发的年代,瘟神信仰、刘猛将信仰风行于各地,在川北的仪陇、阆州、苍溪、营山等地瘟疫多发地带还有专门庆祝瘟神诞辰的“瘟祖会”。清代初年的战乱使得人口凋敝、草莽丛生,虎患四起,川西尤甚,虎崇拜因此盛行。
(二)地缘关系的差异
在区域文化交流较少的背景下,民间信仰往往都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即使是区域之间的传播,近地缘的民间信仰之间的传播更容易被接受。蜀文化处于秦巴文化、荆楚文化的交界带,明清时代又与滇东北文化、黔北文化多有交流,不同的区域受地缘文化的影响有一定差异,因此在民间信仰方面也就多有不同。
川西是典型的蜀文化的摇篮。明清以前,川西文化受秦陇文化的影响更明显,其民间信仰与陕西多有相似。如对孙思邈、诸葛亮的崇拜就是川陕民间信仰相互渗透的结果;关中民俗尚巫的传统也使道教俗神信仰在川西甚为兴盛;在明清时代移民运动及经济交流背景的影响下,陕西人大量进入川西,成都平原的人们更多继承了秦人商战的传统,原有质朴的民风在商业文化面前显得十分微弱,游艺、娱乐之风颇为盛行,其民间信仰同样体现出明显的娱人色彩,各种琳琅满目的迎神赛会,宗教意味不浓,商业、娱乐色彩较强。
川东是巴文化繁荣地,受荆湘文化影响更突出。荆楚同俗,自古如此。晋代有“其人半楚”之称;隋代荆州蛮“僻外山居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在“湖广填四川”中,川东是湖广移民的集结地,湖广移民占大半以上[5]58。这些因素使得现代川东北的许多民间信仰实际上主要源自荆楚文化,源自中古四川的民间信仰反而不多。如《城口厅志》记载:“朔望及四时佳节,祀神,喜放火炮,除夕尤甚。元宵城市张灯,以祈年榖,其风颇近荆楚。”[53]卷六《风俗》川东地区崇祀的水神多为杨泗、大禹,川东北地区普遍信仰源自楚地的坛神,楚人“尚武信巫”的文化传统对川东人影响明显,而在川黔交界处的南川、綦江等地与黔北民间信仰多有交叉,如贵州地方神灵黑煞神在綦江等地同样被奉为风神,而贵州等地也同样崇祀四川的本土信仰川主。
川南文化是四川文化中较为稳定,受荆楚文化及秦巴文化的影响都比较小,文化自成一体。但是,其民间信仰中还是有许多内容来自于周边省份。如屏山县六月六日要祭祀杨四将军和黑土神。黑土神本是贵州的区域神,屏山县人将黑神与水神杨泗同祀,让人颇为费解。盐源县等地民间信仰与滇东北地区相似处更多。据记载:“(二月)初二,城内及盐井‘文昌会’,谈演《大洞仙经》,盖越西有紫府飞霞,故俗尤恭敬,其声乐则沿滇俗焉”;盐源县的火把节来历也与云南有关,“云南鹤庆有妖物,居山洞中,出则风雹损禾,一道人令居民乘夜然火击鼓以助声威,遂除其患,今犹然火把以禳雹也”[54]384。
(三)明清以来土著损耗比例及移民构成的差异
移民的进入使得四川民间信仰主体发生了变化和重组。虽然四川民间信仰体系并没有因为移民的进入而完全解体和重构,但是,移民以会馆祀神为主的神灵信仰体系对四川原有民间信仰带来了巨大冲击,促使其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囿于一地走向全国。四川不同区域接受移民的籍贯有一定差异,这也导致了民间信仰的区域性差异。
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川北和川东所受战乱最为酷烈,土著损失最为严重,是移民进入最多的地区。川东民间信仰区的湖广移民占大半以上,广东和福建移民较少,贵州移民相对较多。这种格局使得川东民间信仰区的民间信仰荆楚因素更多,而天后信仰等在川东北民间信仰区少见。同时,受湖广移民影响,令川东和川北地区更加自成一体,成为一个独立的民间信仰区。川北地区虽然地近关中,但是大巴山的阻隔和湖广移民的影响,使其与川东地区的民间信仰更为相似。川西民间信仰区,特别是成都平原,原以陕西移民最多,后来发展为湖广移民最多,因此,明清以来湖广文化逐渐取代秦陇文化的地位,精明的湖广人使成都平原的商业气息更加突出,由此使得成都平原的享乐之风更盛,民间信仰中娱乐色彩更浓。川南信仰区的土著保留最多,在移民中闽粤、湖广和贵州移民较多,因此,天后信仰、黑神信仰在川南有一定传播。
(四)经济发展状况和区域开发格局的差异
历史时期四川各个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开发格局不是同步的,在不同时期各区的产业结构也不一致,折射在民间信仰上也就有一定的差异。川西平原自古以来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农业最为发达,人们有更多的闲暇用于娱乐和发展文化,商业最为繁荣。在传统商业文化的影响下,川西平原市侩气息最为浓厚,并因此形成了居民尚游乐、重饮食的传统。川西民间信仰区的民间信仰中,与农业相关的神灵和祀神活动备受重视,各种信仰活动更具商业意味和娱乐色彩。川东民间信仰区山高水险,古代森林茂密,先秦时以渔猎经济为主,在明清以前狩猎经济仍有一定地位,但农业文化的影响占有绝对地位,商业文化相对于成都平原就略显薄弱。川南民间信仰区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与川东民间信仰区基本相同,但是由于远离中原地区,开发相对较晚,明末清初以后受战乱影响较小而慢慢发展起来,因此保留了许多土著和少数民族的古老民间信仰。
经济发展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与差异在清代四川行业神信仰中表现得尤其突出。随着清初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四川经济在雍正、乾隆之后进入了繁荣时期,特别是在川西平原地区,商业重新繁荣起来,出现了“商贾辐辏,街道肩摩,百货骈集”[7]206的景象。地区之间的商业流通异常活跃,《成都竹枝词》描绘了川西经济中心——成都的商业枢纽地位:“郫县高烟郫筒酒,保宁酽醋保宁油,西来氆氇铁皮布,贩到成都善价求。”[55]87商业的繁荣建立在城乡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商业的飞速发展加剧了城乡手工业的竞争态势,从而又刺激了手工业新的发展甚至革命。清政府明确废除匠籍制度,使手工业者获得了身份自由。同时,清政府还缩小了官营手工业的经营范围和规模,部分取消了官方垄断,改变了官营手工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因此,四川在清代中期后进入了封建社会手工业最繁盛的时期。行业的发展需要正常的规范体系和市场秩序,还需要各种要素来整合行业的力量,形成良好的竞争态势和发展势头,清代四川行业神信仰正是迎合这种需要,在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行业繁荣的背景下兴盛起来。
在世俗的观念中,行业神或为祖师神,或为单纯的行业保护神,都能掌管行业,引领行业健康发展,并保障行业中个人和行会利益[56]24。区域经济体系的构成和产业结构方式的差异会在行业神信仰方面得到体现。在最紧迫、最受重视的行业或最繁荣、最有特色的行业中,其行业整合的需求更大,行业神信仰也就更兴盛。川北大绸扬名蜀中,丝织业的发展使得蚕神信仰盛极一时,驱蝗神刘猛将也深受敬仰。清代四川处于城市化进程中,县城和市镇的建设使木厂一片兴旺景象,“冬春,匠作背运庸力之人,不下数万”[9]卷十四,因此,鲁班成为传统手工业中最受崇祀的神灵。行业神崇拜和行业的垄断和竞争态势也有关系。当行业处于寡头垄断(比如完全的官方垄断)阶段时,行业神已成为垄断者的工具,神的地位和作用就将被弱化。清代四川井盐制造业和冶铁业都因为技术的改良等原因达到空前繁荣的状况,但是这些都是官府垄断的行业,因此行业神崇拜并不发达。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时代,商业人口所占城市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成为世俗社会普通大众的共同愿望,因此财神被许多行业作为行业神并虔诚奉祀。在旱涝多灾的清代四川,告别病恙、保持健康成为人们的共同追求,药王在得到医药行业奉祀的同时也获取了更广泛的信众群。
(五)居民个性特征和文化传统的差异
蓝勇从历史文献记载、地理环境的差别以及区域开发历史进程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发现,四川三大文化区对居民个性的影响呈现出三种类型,其中川西尚文、川南尚仁、川东北尚武[5]489-500。这种居民个性的差异在民间信仰中表现非常明显,同时也是四川民间信仰区域差异出现的重要原因。
川西尚文之风在居民民间信仰方面多有体现。川西民间信仰区文昌、魁星崇拜盛行,绵州、龙安府尤甚,各地崇祀魁星的各种建筑较多,且多为文人培修或官民共建。德阳县魁星阁,“原建在县城南学宫左,后改四面鼓楼上。乾隆中知县周际虞仍于旧地重建。道光二十八年士民培修”[8]卷十七《祠庙》。文昌宫在川西被封为“祖庙”,各县甚至乡镇都有文昌宫,灌县有文昌宫九座,梓潼县还被称为“文昌”故里。在崇尚娱乐的川西,“文昌会”显得比较严肃。如金堂县,“二月三日为文昌生日,士人多入庙行祀,相戒勿演戏,恐渎神也”[14]卷一《坛庙》;江油县“乡村有演戏者,城内各官致祭,绅士颁胙”[6]卷二《祀典》。在成都平原地区,这种尚文的特征表现得尤其突出。如成都县有供奉造字之神的苍圣祠;新都县有两座仓颉祠;华阳县有惜字宫,同样奉祀仓颉,而且两地分别将仓颉与文昌、大禹同祀;崇州街子古镇还有建于清代、表征人们珍惜文字和用以收集焚烧字纸的惜字塔[36]210。
如前所述,川东地区,居民个性特征中的强悍、尚武、爽直体现得十分明显,这种个性在民间信仰方面多有体现。川东北民间信仰区同样也有文昌和魁星崇祀,但形式和特色却差异颇大。川西民间信仰区文昌和魁星区分清晰,而在川东北民间信仰区,二者几乎不加区分,甚至与其他神灵混淆。《蜀典》关于“奎星”解释中,作者将文昌与魁星并提,认为文昌与“祀魁星其说亦近是”[57]卷七《方言》。而在太平县魁星楼,崇祀的竟然是刘猛将军。该区的文昌会也体现出更多的娱乐性和世俗化,文化意味较淡。南充县祀文昌时,“无不演戏迎神,以祈福庇”[58]卷一《风俗》。涪州,“二月三日,祀文昌,童稚放风筝为乐。里社建清蘸祈谷,大傩,平畴播谷”[59]卷二《舆地志·节序》。
川南民间信仰区作为四川中古文化保留最多和文化最稳定的区域,居民个性特征表现为质朴、尚仁、知礼,其民间信仰显得古朴原始。如江安、纳溪、合江等地都有魁星阁及塑像,与其他地方不同;川南地区的城隍庙和土地庙的数量在全川最多,城隍也是川南地区祈雨时依赖的主要神灵,而其他外来的神灵如杨泗、萧公、天后等相对崇祀较少。
四 余论
从共时性上将历史文献考证得到的历史事件放到具有特定地理背景区域,和特定历史时期的自然、社会、文化和经济政治条件相结合进行分析,探讨历史时期民间信仰的地域特征及地域差异,探讨自然环境、地方社会等因素在民间信仰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意义,从而揭示民间信仰在地域上的分布和在历时性上与地域社会中自然、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理清民间信仰的源流。
民间信仰是理解区域文化的重要角度,而从环境机理和人地互动角度探讨民间信仰的建构、变迁以及区域差异的肇因,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和传承区域民间信仰以及理解区域文化的建构与变迁。在文化建设备受重视的今天,清代四川作为一个特定的时空区域,其民间信仰的建构和变迁对于其他区域民间信仰和地方性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应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在研究区域方面,本文参照谭其骧先生的作法,将清代嘉庆二十五年的四川政区作为研究的基点。但是,因作者水平和文章篇幅所限,本文研究的空间范围主要侧重于清代四川汉族聚居的川东北、川西平原以及川南地区,对松潘厅、懋功厅、杂谷厅、茂州直隶州等川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民间信仰只是略有涉及。本文的研究时间为有清一代,即1644-1911。不过,信仰世界潜在的连续性使我们在分析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必须涉及清代前后的一些情形,而且许多四川史志编撰时间都在民国时期,虽然记录多为清代情形,但也已涉及民国。
②据地方志资料了解,花朝主要分布在大宁、忠州、巴县、遂宁、广元、新津、绵州、合江、叙州府、綦江、定远、灌县、新繁、江北厅、铜梁、合州、璧山、江津、三台、盐亭、长宁、南溪等地区,重庆府占据其中8个地区。
③道光《巴州志》卷一《地理志·风俗》记载:“诣南龛寺设大蘸会礼佛请福,山前圆洞二穴,妇人无子者以物掷之,视其中否以祈嗣,谓之‘打儿洞’。”
[1]贾雯鹤,欧佩芝.清代四川民间信仰研究综述[J].中国俗文化研究,2016,(8).
[2]林移刚.清代四川坛神信仰源流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3]林移刚.川主信仰与清代四川社会整合[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4]林移刚.民间信仰与清代四川移民社会整合[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5]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6]武丕文,欧培槐,等.江油县志[M].光绪二十九年(1903)刻本.
[7]傅崇矩.成都通览[M].成都:巴蜀书社,1987.
[8]何庆恩,刘宸枫,田正训.德阳县志[M].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9]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M].道光二年(1822)刻本.
[10]张澍.蜀典[M].道光十四年(1834)张氏安怀堂刻本.
[11]林移刚.清代四川土地崇拜和土地神信仰[J].农业考古,2014,(3).
[12]陈邦倬,易象乾,等.崇宁县志[M].民国十四年(1925)刻本.
[13]李绍祖,徐文贲,等.温江县志[M].嘉庆二十年(1815)刻本.
[14]谢惟杰,黄烈,等.金堂县志[M].嘉庆十六年(1811)刻本.
[15]顾德昌,张粹德,等.新繁县志[M].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
[16]林移刚.清代四川汉族地区耕牛崇拜研究[J].农业考古,2013,(4).
[17]熊德成.论古蜀农耕文化起源于双流[J].中华文化论坛,2009,(2).
[18]赵霦,等.大邑县志[M].光绪二年(1876)余上富增刻本.
[19]史钦义,等.彭山县志[M].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
[20]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G]//雷梦水,潘超,等.中华竹枝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
[21]陈霁学.新津县志[M].道光十九年(1839)刻本.
[22]王松寿,李稽勋,等.秀山县志[M].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
[23]蔡以修,刘汉昭,等.大竹县志[M].道光二年(1822)刻本.
[24]曹学佺.蜀中广记[M].两淮马裕家藏本.
[25]庄定域,支承祜,等.彭水县志[M].光绪元年(1875)刻本.
[26]王鳞飞,冯世瀛,冉崇文,等.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M].同治三年(1864)刻本.
[27]陈祥裔.蜀都碎事[M].两淮马裕家藏本.
[28]沈昭兴.三台县志[M].嘉庆二十年(1815)刻本.
[29]朱世镛,刘贞安,等.云阳县志[M].民国24年(1935)石印本.
[30]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档案馆.淸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G].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31]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
[32]李复.潏水集[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3]连山,李友梁,等.巫山县志[M].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
[34]王玉鲸,张琴,范泰衡,等.增修万县志[M].清同治五年(1866)刻本.
[35]何庆恩,贾振麟,等.渠县志[M].同治三年(1864)刻本.
[36]山川早水.巴蜀旧影[M].李密,李春德,李杰,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37]罗兴志,孙国藩,等.新修武胜县志[M].民国20年(1931)排印本.
[38]黄际飞,周厚光,等.南川县志[M].光绪二年(1876)刻本.
[3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巴县文史资料:第九辑[M].1993.
[40]曾秀翘,杨德坤,等.奉节县志[M].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
[41]曹绍樾,胡晋熙,等.仪陇县志[M].同治十年(1871)刻本.
[42]张庚谟.四川保宁府广元县志[M].乾隆二十二年(1757)刻本.
[43]徐继镛,李惺,等.阆中县志[M].咸丰元年(1851)刻本.
[44]段渝.四川通史:卷一先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45]高维岳,魏远猷,等.大宁县志[M].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
[46]胡之富,包字,等.南溪县志[M].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47]姚廷章.珙县志[M].同治八年(1869)刻本.
[48]秦湘,等.合江县志[M].同治十年(1871)刻本.
[49]戴维·克罗克特·格雷厄姆.四川的树神[J].江玉祥,译.文史杂志,1990,(2).
[50]王好音,张柱,等.洪雅县志[M].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51]贺泽,张赵才,等.荥经县志[M].民国四年(1915)刻本.
[52]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M].北京:中华书局,2001.
[53]刘绍文,洪锡畴.城口厅志[M].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
[54]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第4册[G].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55]杨燮,等.成都竹枝词[M].林孔翼,辑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56]李乔.中国行业神信仰[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
[57]张澍.蜀典[M].光绪成都尊经书院刻本.
[58]袁凤,孙修清,陈榕,等.南充县志[M].嘉庆十八年(1813)刻,咸丰七年(1857)洪璋增刻本.
[59]吕绍衣,王应元,等.重修涪州志[M].同治九年(1870)刻本.
[责任编辑:凌兴珍]
The Regional Discrepancies of Folk Beliefs of Sichuan in the Qing Dynasty
LIN Yi-g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In the Qing dynasty, no distinct sacrifice sphere or belief sphere exists. As a major component and one of dominant factor of “local” culture of Sichuan, the division of folk beliefs basically consists with that of comprehensive culture. This paper divides the folk beliefs of Sichuan in the Qing dynasty into three areas, namely, the area for folk beliefs of West Sichuan Plain, area for folk beliefs of Northeast Sichuan and that of the Southern Sichuan. In the area for folk beliefs of West Sichuan Plain, much worship of nature are remained, the worship and folk beliefs of deities and sprits relating to agriculture are popular and of strong recreational nature. While in the area for folk beliefs of Northeast Sichuan, lots of simple yet old remains of worship of nature are left, while the worship of and sacrifice for the deities and sprits relating to agriculture are pious yet simple. In this area, the tradition of valuing sorcery is outstanding, the belief of ghost and sorcery enjoys great popularity, and great discrepancies are existed among the subareas. In the area for folk beliefs of Southern Sichuan area, most old beliefs are remained, and there are lots of unique folk beliefs. Influenced by the majorities in a more serious fashion, the folk beliefs in this area are more simple and primitive.
folk belief; the Qing dynasty; Sichuan; regional discrepancies
2017-01-08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巴蜀移民社会研究”(13XZS031)、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及其现实价值研究”(2014BS061)、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大招标项目“基于统筹城乡改革视角的重庆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文化传承的实证研究”(sisuzd201204)的阶段性成果。
林移刚(1978—),男,湖南洞口人,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民俗学、社会史及农村社会学。
K203
A
1000-5315(2017)04-014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