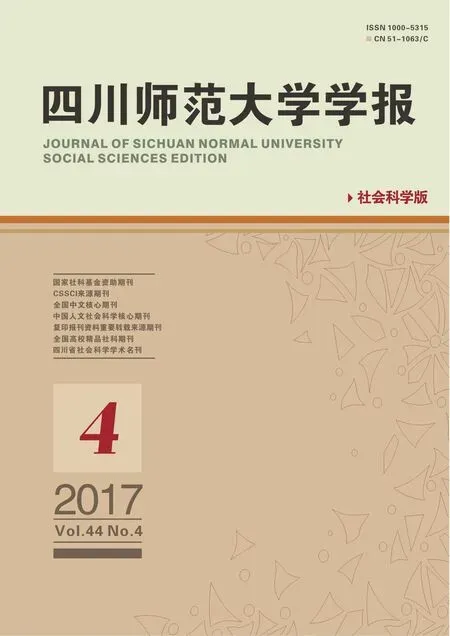“疯狂”与“黄金中道”:贺拉斯的伦理智慧
2017-04-13李永毅
李 永 毅
(重庆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1331)
“疯狂”与“黄金中道”:贺拉斯的伦理智慧
李 永 毅
(重庆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1331)
贺拉斯心目中的诗艺绝不仅指艺术技巧,而是指诗人的一切修养,其中伦理智慧尤为重要。他早期的《讽刺诗集》和晚期的《书信集》都是以伦理探讨为主的作品,即使以抒情为主的《颂诗集》也渗透了他的伦理思想。贺拉斯从“黄金中道”的观念出发,讽刺了人类在对待财富、权力、宗教等问题时的疯狂与愚蠢,这种伦理观念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伊壁鸠鲁哲学追求的“不动心”状态,在一个动荡无常的世界中实现心灵的独立与自由。
贺拉斯;贺拉斯诗学;黄金中道;伦理
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了极有见地的一个观点:“正确写作的发端和源泉在于智慧”[1]239。在他的语汇体系里,“智慧”(sapientia)几乎就等于哲学(philosophia),而“正确写作”无疑让人联想起“正确生活”——伦理哲学的目标。所以,贺拉斯所言的“诗艺”并不仅仅包括格律、辞藻和种种手法,在更高的层次上,它意味着对生活和世界的理解,伦理智慧在其中占据着尤其重要的位置。
他对荷马的评价也特别突出了道德教益:“光荣或可耻,有益或无益,克吕西波/和克兰托尔都没他表达得清晰、深刻”[1]175。克吕西波是斯多葛派的代表,克兰托尔是学园派的代表,贺拉斯认为荷马史诗的伦理价值超过了这些著名的哲学家。《伊利亚特》为读者提供了众多反面的教训:“因为内讧、阴谋、邪行、淫欲与愤怒,/伊利昂城墙内外,罪恶都罄竹难书”[1]175。与此相对,《奥德赛》的主人公却是“德性和智慧”的化身。
贺拉斯早年在雅典接受过系统的哲学教育,他对伊壁鸠鲁哲学特别认同,但也吸收了学园派、斯多葛派等其他派别的思想。他对哲学的兴趣在早期的两部《讽刺诗集》中有充分体现,里面的大部分作品在勾勒罗马社会众生相的同时,也在探讨古典哲学的一些基本命题。他晚期(公元前23年—前8年)的重心无疑是两部以伦理为主要内容的《书信集》。即使在创作生涯中期的三部《颂诗集》里,伦理思想也占了相当的分量。
从早期的《讽刺诗集》到晚期的《书信集》,贺拉斯的作品涉及了许多伦理哲学问题,但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黄金中道”(aurea mediocritas)的思想。这一说法出自《颂诗集》第2部第10首,贺拉斯在诗中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它的内涵:“若要明智地生活,就不应/偏执地追逐深海,当你怵然/躲避风暴时,也不应过分迫近/危险的岸。”[2]188这意味着,伦理智慧的关键是在两种相反的趋向中不偏执一端,因为一旦越过“中间值”和“确定的边界”,人的行为都将偏离正道[1]93,而偏离正道即是“疯狂”。
“疯狂”是贺拉斯伦理诗中频繁出现的一个概念。《讽刺诗集》第2部第3首更是他关于人类疯狂的长篇布道。据托伊菲尔统计,仅在这首诗里,表示“疯狂”的不同说法就有12种[3]170。世人判断疯狂的标准是,某人的行为是否和多数人一样。但多数人的行为是否就是符合理性的?在《讽刺诗集》第2部第3首中,贺拉斯借斯泰提纽之口,概括了人类的四种疯狂:贪婪、野心、放纵和迷信。这位斯多葛派信徒得意地宣称,除了哲学家,所有人都是疯子[1]149。然而,他在这首诗里最终也成了丑角,因为在贺拉斯看来,他和他所批判的人犯了同样的毛病——偏执,偏离了理性的中道。无论是讨论财富、权力还是宗教,贺拉斯都秉承了“黄金中道”的原则,批判了一切偏执的行为,主张理性与适中。
一 财富的考验
财富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基本问题,因为只要生存,便需要相应的物质资料。贺拉斯对财富问题最集中的论述见于《讽刺诗集》第1部第1首。从表面上看,作品中有两个彼此独立的主题,一是人们对自身现状的不满,二是对财富的贪婪。奈普指出,两个主题之间存在有机联系,构成了问题与答案的关系;人们普遍对自身现状不满,认为别人的处境比自己好,但又不愿真正与别人交换,其实他们羡慕的不是别人的整体状况,而是他们的财富[4]91-109。
面对财富问题,人们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贪婪,这是贺拉斯反复批判的“疯病”之一。贪婪的人欲望是永无止境的,贺拉斯有一句名言:“贪婪者永远贫乏。”[1]177水肿症是贺拉斯为贪婪症量身定做的意象,如同水肿病人越喝水越渴,贪婪之人财富愈多,欲望愈大,愈不满足,又需追逐更多的财富,使得自己成为自己最残酷的监工,人生成为漫长的苦役。贺拉斯指出,这样的追逐是违背天理的。人们常把勤劳的蚂蚁视为榜样,但在诗人看来,谨守自然之道的蚂蚁远比人类有智慧,它们虽然也提前囤积食物,但它们的囤积是有度的,并且知道何时放松下来享受,而人却沉溺于物质的积累中无法自拔[1]89。
人之所以互相攀比财富,是因为他们深信自己拥有财产的所有权。贺拉斯却釜底抽薪,证明这样的所有权其实是子虚乌有。卢克莱修曾在《物性论》中用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法律差异来讨论人的生命,说“生命无人有所有权,但所有人都有使用权”,在这个意义上,生命不能称为“属于我们的”[5]507。如果说卢克莱修否定了人对生命(自然也包括生命中的一切)的所有权,那么贺拉斯对使用权也表示怀疑。他笔下的某人认为,“从这里到那棵白杨树,一概/是他的”[1]219,贺拉斯却评论道:
确定的边界排除了邻居的争端,
仿佛真有什么属于他——然而,转瞬间,
捐赠、购买、没收、抢夺,还有死亡,
都可以让财产易主,被别人支配分享。
无人有永久的使用权,所以财产就这样
不断更换继承人,像后浪推动前浪。[1]219
即使在人有限的一生中,人也不能无间断地占有和享用自己的财产,无数偶然的、不可预见的因素都在不断改变着这些财产的使用权。既然我们并不真正拥有我们的财产,那么为积攒财富而积攒就没有意义,财富的目的是使用而非攀比。
贪婪者由于对财富的迷恋,往往把对财富的追求变成了人生的目的而非手段,所以贪婪者往往也趋于吝啬,拉丁语用同一个词avarus来形容这两种密切相关的特质。贺拉斯诗中对此种人有生动的描绘。《讽刺诗集》第1部第1首里的吝啬者拥有大量的金钱、粮食和美酒,却过着乞丐不如的生活,丝毫不敢动用自己的财富,“仿佛它们是不可碰的圣器”,并且“整日悬着心,半死不活”。钱本是用来满足生活基本需要的,此人却把它变成了焦虑恐惧的祸根,让人生变得索然无趣。不仅如此,吝啬者嗜钱如命,也丧失了正常的人类情感,难免众叛亲离[1]91。
有些人则相反,极度蔑视财富,这又包括两类人。一类是放纵挥霍的人。他们不仅耗尽了祖先的积累,还往往债台高筑,最终失去了按自己意愿安排生活的自由。《讽刺诗集》第2部第3首就刻画了这样一位败家子[1]159。另一类是故意选择赤贫生活的哲学家。针对历史上伊壁鸠鲁派先驱阿里斯提波和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的著名争论,贺拉斯明确表示支持前者。他极不认同第欧根尼故意用贫贱污秽的生活来标榜坚忍品质的做法,因为他相信,刻意选择赤贫仍然表明第欧根尼很在意财富,一旦生活的境遇逆转,他一定不能坚守最初的立场。与第欧根尼不同,阿里斯提波对富贵和贫困同样淡然,体现了“黄金中道”的可贵品质。贺拉斯称赞他:“能适应每种形式、地位/和境况,目标远大,却以眼下为依归”,“无论/穿什么衣服都会坦然穿过最拥挤的人群,/两种角色他都能和谐无间地扮演”[1]107-109。
对待财富的“黄金中道”就是像阿里斯提波那样,既不偏执地追逐财富,也不无条件地摒弃财富,既不让自己陷入赤贫,也拒绝奢侈,既不吝啬,也不挥霍,这样才能做一个“单纯快乐的人”[1]219。在贺拉斯看来,人享用了财富却否定财富是一种虚伪,但追求财富的底线是不能损及精神的独立:“我不会飨足了禽肉却赞叹穷人的安睡,/也不会用自由的闲暇去换阿拉伯的富贵”[1]181。
二 权势的诱惑
在古罗马的政治实践中,为了维持自己的影响力,追求和掌握权力的人需要付出巨额财富来迎合民众,争取他们的拥护,恺撒如此,屋大维如此,各级官员、议员都是如此。所以贺拉斯认为,野心家与吝啬鬼有相通之处:“把拥有的一切扔进/深渊和从不享用财产有什么分别?”[1]155正因为看到了这一层,《讽刺诗集》第2部第3首中的富翁奥皮丢在临终前严禁两个儿子从政,诘问他们:“难道你愿意向民众扔鹰嘴豆、扁豆、羽扇豆,/就为了受民众瞻仰,就为了变成青铜像,/失去田地,失去金钱,跟疯子一样?”[1]157贺拉斯在这里以幽默的口吻描绘罗马官员或候选人向民众免费发放食物的行为。奥皮丢认为,牺牲财产以换取民众的拥戴,得不偿失。
显赫的权势容易迷住人的眼睛,让人失去理智,以为一切尽在自己掌握,万事皆可达成。在贺拉斯看来,这是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以悲剧收场的关键原因。公元前30年9月,克里奥帕特拉和她的罗马盟友安东尼的死讯传到罗马,贺拉斯写了《颂诗集》第1部第37首来纪念。长期以来,这首诗都让评论者困惑。诗的前半段洋溢着不可遏制的狂喜和对克里奥帕特拉的辱骂,似乎和官方宣传口径完全一致[6]39,但在诗的最后三节,克里奥帕特拉的形象却明显转变,成了一位勇敢、冷静面对人生挫折的斯多葛式的英雄,贺拉斯的语气也几乎变成了颂歌。转变的谜底在于克里奥帕特拉恰恰因为失去权势而恢复了理智。
通过法律生涯或军事生涯积攒名声或资历,逐步进入政界,并力争成为执政官,这是许多罗马人(包括西塞罗在内)梦想并践行的人生道路。贺拉斯却认为,这种追求是不明智的,权势不值得尊崇,因为追逐权势的一个惨痛代价是失去人生的自由。贺拉斯写道:“贵族不也和平民一起被捆绑,/拖在荣光神的彩车后面?”[1]127“荣光”(Gloria)在古罗马常指位高权重或者武力征伐所带来的荣耀,这里被拟人化了。贺拉斯想象的场景是古罗马常见的凯旋仪式,被野心驱使的人就像荣光女神的俘虏,作为战利品绑在凯旋马车后面。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人要获得权力,必须要有自己的追随者,而这些追随者总是被利益和时势左右,并无坚定的立场。他将罗马选票的最大来源形容为“无常的庸众”[1]187。二是因为政坛变幻无常,将人生与权势绑定,便将在宦海浮沉中失去心性的自主权。贺拉斯写道:“神能选择/变换至低与至高,贬抑显赫之人,/显明幽暗之物;抢掠成性的时运/从这位头顶倏地叼走冠冕,/又飞向那位,欣然相赠。”[1]33
但这并不意味着贺拉斯自甘贫贱,也不意味着他认为人不应参与公共生活。为了避免堕入赤贫(那也意味着失去自由),贺拉斯认为,人应该追求适当的地位,所以他一直很感激父亲的远见。他父亲是一位获释奴隶和税吏,却执意让贺拉斯从小接受罗马最好的教育,以提升他的地位[1]129。但改变地位的目的不是获得权势,而是获得尊严,而尊严固然与地位相关,但更重要的决定因素则是人品。贺拉斯之所以称赞自己的恩主麦凯纳斯,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后者理解尊严的真正来源[1]125。在没有野心的前提下追求尊严,既可以避免赤贫造成的依附,也可以远离权势造成的束缚,保持身心的自由。同时,罗马公民也应履行自己的责任,如他所描绘的,“现在我变得活跃,热心公民的事务,/守卫真实的美德,做它严格的追随者”[3]18,不以野心为动机,这样的行为就是美德的体现。
三 宗教的分寸
贺拉斯虽然在诗中经常提及各种神祇的名字,但他和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不少知识分子一样,已经不再虔诚地相信罗马传统的多神教了。在他笔下,对神灵的迷信常被描绘为一种可笑的做法,甚至是一种疯病。
在《讽刺诗集》第1部第5首里,他嘲笑了那提亚人向异乡人兜售的神迹。当地人称,神庙门槛上的乳香没有火也会融化,并将它视为神的干预。贺拉斯却不相信,并说:“我知道众神过得平静惬意,/倘若自然制造了奇迹,一定不是/他们心绪不宁,从天界穹顶降下来的。”[1]123古代广泛流行的说法是:各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不同情绪的表现。贺拉斯此处却引用卢克莱修的《物性论》的说法[5]653,认为神不会操心世间的事,不会用“超自然的”法力改变自然,自然现象只能用自然原因来解释。
在《讽刺诗集》第2部第3首中,贺拉斯更明确地将宗教迷信形容为人的四大疯病之一,并举出了两个例子:一位年老的获释奴隶恐惧死亡,向神祷告,要求神单独为他改变自然规律,许他不死;一位迷信的母亲为了给儿子治病,非让他赤身站在河里向神致敬,反而断送了他的生命。贺拉斯在这首诗里把“对神的恐惧”称为“瘟疫”,显然背离了各民族的正统宗教立场[1]163。
然而,贺拉斯并未断然否定神的存在。他在《颂诗集》第1部第34首里宣称自己因为亲身见证了晴天霹雳的现象,断定自己以前对待神的懈怠态度是错的,应该更加虔敬才对。在古希腊罗马世界,雷霆是大神宙斯(朱庇特)的主要武器,也是神意和神威的主要体现形式;在古罗马,雷霆常被视为朱庇特降下的兆象,有警示和预言作用,而以理性的、自然的方式解释雷霆则成了哲学家的标记。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完全否定了晴天霹雳的可能性[5]800。西塞罗在《论占卜》[7]268-271称朱庇特不可能将自己的意志示人,并建议读者接受斯多葛派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卢克莱修、西塞罗和塞涅卡都曾试图对雷电做出科学解释。但对古代的一般人而言,雷霆是可畏的事,尤其是晴天霹雳这样的罕见现象,如果它让贺拉斯暂时对自己以前的宗教态度产生了怀疑,也并非不可想象。
关于这篇作品的宗教态度,学者争论不休。古罗马注者波皮里昂判断,贺拉斯在诗中表达了忏悔之情,否定了年轻时代追随的伊壁鸠鲁宗教观,相信神对世界无兴趣,也不干预世界。如果贺拉斯的哲学态度发生了转变,他转向了何方呢?坎贝尔等人认为,他转向了斯多葛主义[8]121-123。然而,斯多葛派也倾向于用自然的理由解释所谓超自然的现象。许多注者对贺拉斯的真诚表示怀疑,因为他在这首诗里似乎否定了他一贯的哲学态度。按照罗斯的概括,我们所知的贺拉斯是这样的:他的哲学是杂糅的,偏学园派;他的伦理学主要倾向伊壁鸠鲁派,有保留地赞赏斯多葛派;他通常不相信奇迹和超自然的现象,不相信灵魂不朽;他在形式上支持罗马的国家宗教,而对各种推崇魔法的异族宗教表示轻蔑[9]192。麦凯相信,这首诗不仅没有否定伊壁鸠鲁哲学,反而强烈地表达了作者继续信奉这一学派的决心[10]10。
第6段最后一句,句式不算复杂,但从个人的教学经验来看,学生理解句意也稍显吃力。在讲授的时候,先请学生反复朗读来体会句意,然后可以进行小组讨论,老师需要在适当时候对难点进行点拨,比如句式的对比sometimes,at others,动词offer sb sth的双宾语结构,请学生识别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decline the honor具体所指,词组be mortally offended的含义等等。
其实,从心理的角度来理解贺拉斯所表达的与“平素”不同的宗教立场,并非那么困难。即使在哲学上持理性立场的人在情感上也可能为神保留一个位置,从出生到死亡时时刻刻都不信神的人其实非常罕见,在特定时候出于心理需要暂时转向神并不奇怪,何况贺拉斯在许多问题上的态度原本就比较温和,不趋于极端。他虽然反对迷信,但也不过分强调理性,如果迷信是一种病症,滥用理性就是一种僭越。
在《颂诗集》第1部第3首的后半段,贺拉斯便谴责了普罗米修斯盗天火、代达罗斯为人制造翅膀和海格力斯侵入冥府的僭越行为。这段文字的主题是人类的僭越之罪,“桀骜”、“妄作”、“渎神”等词都展现了人类自恃拥有智力而无所忌惮的心理,“不可触碰”、“被禁止”、“不许人拥有”等说法则表明,这些行为是神所禁止的,至少越过了合理的边界(倘若读者不信神的话),所以结论就是人类“愚蠢”,人类犯了“罪”[1]10-12。特莱尔提醒我们,贺拉斯在表面的渎神主题下选取的普罗米修斯、代达罗斯和海格力斯三位人物都体现了勇敢的可贵品质,读者很容易钦佩而不是否定他们[11]132。埃尔德干脆提出,诗歌的主题就是赞美勇气,“哪怕勇气的结果是毁灭”[12]152。然而,“愚蠢”(stultitia)和“罪”(scelus)两个词无可辩驳的贬义似乎让上述观点难以立足。到了最后三行,时态从现在完成时(拉丁语中相当于过去时)切换到一般现在时,人称也从第三人称变成了“我们”,表明贺拉斯此时谈论的已经不再是神话中的过去,而是当代的现实了。在经历了多次大规模内战的公元前1世纪,贺拉斯对“僭越”的悲剧性后果应该深有体会。对神灵的迷信固然可能导致悲剧,但完全抛弃对神的信仰,欲望的无限膨胀就会让理性成为借口,同样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既摒弃迷信,又不臣服于理性,这就是贺拉斯的中道。在他的作品里,神依然存在,但他们并非膜拜的对象,也非诋毁的靶子,而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也是伦理的必要预设。既然贺拉斯认为公平和正义都发源于功利[1]107,而宗教的部分教义又可起到规范道德行为的作用,那么就不应弃绝神的概念。在沉痛反思罗马内战的过程中,贺拉斯反复使用的两个词就是“渎神”(nefas)和“不虔敬”(impius),例如《颂诗集》第1部第2首和35首、《长短句集》第7首和第16首,可见贺拉斯相信,敬神的心理与道德的自我约束之间有重要的关联,即使只将神视为一种比喻的说法,宗教也有存在的必要。所以,他如此告诫罗马人:“因为你在神面前保持谦卑,才统治/世界:一定记住,以此为万事的终始。/神遭到轻慢,降下这许多灾难,/给悲伤的意大利,西方之地。”[2]258
四 结语:中道与不动心
贺拉斯坚持“黄金中道”,一方面受了亚里士多德的启发,一方面也是以自然为师。他在诗中反复强调,自然不会永远保持一种状态。他曾以诗意的语言如此形容:
大雨不会永远从云端倾泻,浸灌
杂乱荒凉的原野,里海不会永远
被乍起乍落的风暴袭扰,朋友
瓦尔鸠,冰盖不会长年
封住亚美尼亚的土地,从不挪动
分毫,加尔加努山的橡树不会始终
被北风百般折磨,白蜡树凋落的
叶子,岂会永远失踪?[2]185
所以,偏执一端是违背天道的。但他倡导黄金中道更重要的原因无疑是伦理的,他所推崇的伊壁鸠鲁学派相信,不动心(ataraxia)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贺拉斯明确告诉朋友努米丘,不动心是“唯一带给你幸福并保持幸福的品质”[3]48。他相信,偏离“黄金中道”的两个极端本质上没有区别,都会让人的内心失去平衡:“害怕相反的东西和贪恋这些东西/其实无分别,两种人都被恐惧侵袭,/一旦他们被某种意外的景象吓瘫”[3]49。反过来,坚守黄金中道的人任何时候都知道“足够”,只有知道“足够”,才能无欲则刚,不受外物所累。无论拥有多大的财富、多高的地位,无论如何依靠神,如果没有这种内心的平和,都难以消除“心灵可怜的骚动”[2]208。相反,不贪恋外物的人却可以坦然对神宣告,“既然朱庇特予夺随心,/让他给生命,给财物,我来给宁静的灵魂。”在《颂诗集》第3部第3首开头,贺拉斯如此描绘一位不动心的人:
一位追求正义、目标坚定的人,
无论狂热支持恶行的同胞公民,
还是以愠怒眼神相威胁的暴君,
都不能撼动他的决心。
主宰动荡的亚得里亚海的喧嚣南风,
驱动闪电雷霆的朱庇特的巨手也不能:
即使世界破碎、崩塌,被废墟
击中的他也处变不惊。[2]235-236
这样的境界才是贺拉斯“黄金中道”思想的真正用意所在,也是他所有伦理诗梦想的目标。
[1]贺拉斯.贺拉斯诗选:拉中对照详注本[M].李永毅,译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2]MOORE C H.Horace:Odes,EpodesandCarmenSaeculare[M].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02.
[3]MORRIS E P.Horace:SatiresandEpistles[M].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09.
[4]KNAPP C. Horace, Sermones, I, I[J].TransactionsandProceedingsoftheAmericanPhilologicalAssociation, 1914,(45).
[5]LEONARD W E.DeRerumNatura:TheLatinTextofLucretius[M]. Madison: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2008.
[6]BOWRA C M.InspirationandPoet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55.
[7]CICERO M T.DeDivinatione:LibriⅡ[M]. Lipsiae: Crusium, 1793.
[8]CAMPBELL A Y.Horace,aNewInterpretation[M]. London: Methuen, 1924.
[9]ROSE H J. Horace,Od. I. xxxiv-xxxv[J].TheClassicalReview, 1916, 30(7) .
[10]MACKAY L A. Horace: Odes I. 34, 35[J].TheClassicalReview, 1929, 43(1).
[11]TRAILL D A. Horace C. 1. 3: A Political Ode?[J].TheClassicalJournal, 1983, 78 (2).
[12]ELDER J P. Horace, C. 1. 3 [J].TheAmericanJournalofPhilology, 1952, (73).
[责任编辑:唐 普]
2016-06-27
本文为2015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贺拉斯全集译注与研究”(106112015-CDJSK-04-JD-01)的阶段性成果。
李永毅(1975—),男,重庆开州人,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古罗马文学和西方文论。
I106.2
A
1000-5315(2017)04-01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