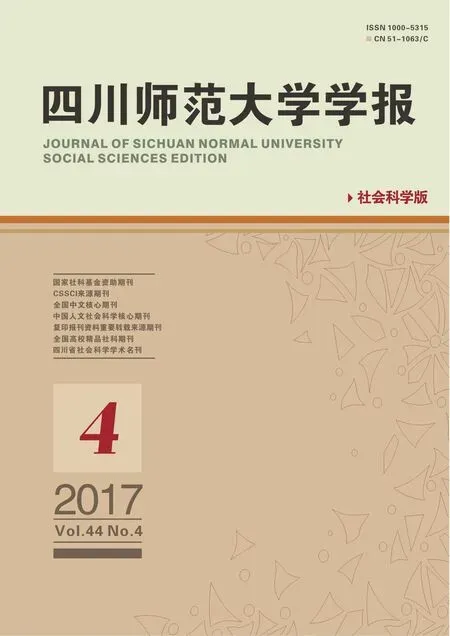论中国教育研究的实证转向
2017-04-13戚务念
戚 务 念
(1.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江西分中心,江西 上饶 334001;2.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南昌 330038)
论中国教育研究的实证转向
戚 务 念1,2
(1.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江西分中心,江西 上饶 334001;2.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南昌 330038)
中国教育研究正在发生实证转向,但也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如有人认为从“思辨”走向“实证”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会导致理论的退化。教育实证研究的兴起,是对中国当下规范研究、思辨性论述等主流研究路数的反动。在复杂的经验世界中,知识获取既需要理性证明,也需要经验检验。西方理论和概念的经验基础是西方本土的教育经验与事实,中国学者容易产生认知偏差和误用。规范研究表现出理念建构现实的特征,混淆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界限,也混淆了研究者的角色定位。学术调查与普通调查的区别,关键在于研究假设之有无。现代学术中知识的“系统”与“累积”背景下,问题意识是教育与社会科学的安身立命之所。实证研究的脉络中,对于研究结论(理论)与常识之间的关系有三种态度:“与常识决裂”、“道不远人”、“赋常识以理论”。常识与研究/研究结论的符应类型,可分为符合、不符合、部分符合部分不符合三种类型。实证研究有着严格的研究规程,其功用在于架起理论与经验之间的桥梁。
教育研究;实证研究;学术调查;问题意识;常识
一 中国的教育研究正处在实证转向之中
在中国大陆,种种迹象表明:实证研究之风正在吹洒着教育研究领域。近年来,一些杂志如《教育学术月刊》从2011年开始将“实证导向”作为办刊宗旨;从2015年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等单位每年联合举办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2017年开年之初,中国14所大学的教育科学学院院(部)长、32家教育研究杂志主编、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光明日报教育研究中心负责人齐聚华东师范大学发布“加强教育实证研究”的行动宣言。一些教育学者也开始了反思,有学者直陈:“从世界范围来看,像我们这样的学术研究已经不多见了,博士论文中完全可以没有数据,硕士论文中可以不用实地调研,一项又一项的研究成果可以表现为理论推导、思维演绎。”[1]更有一些学者尝试实证转向的动机是“如今不搞点数据,论文不好发了”,“现在的趋势是实证研究更好申报课题,更容易得到国家资助”。如此看来,在中国教育研究中的实证转向,在一定程度上不排除有一种对于现实压力的妥协成份,有着落伍于世界潮流的焦虑以及基于论文发表、基金申报等方面的功利性追求。也有些学者面对这种潮流“内心不服”。正所谓,面对这种现象,有人认为是“一股清风”吹进了沉寂已久的教育研究领域,也有人认为是“一个幽灵在游荡”。
近年来,关于教育实证(经验)研究的讨论文献不时见诸于报刊,其中不乏质疑、迷惑与误解之处。在现实中,“实证研究”的提法也确实令人思维混乱,如笔者经常碰到这样的提问:“实证研究是否先有个理论假设,然后到一线去收集资料以验证你的假设?”这种“田野打捞”心态在学术界也确实存在。也有人认为,教育“经验研究”就是满足于原始的经验材料的收集与分析,并不进行“文献”阅读与比较,所以教育研究从“思辨”走向“实证”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2];更有人明确表示“不欣赏教育领域的某些实证研究”,这是“用一种貌似科学的方法来证明一个常识性的问题”[3];也有人认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纠缠并不意味着教育学的进化,相反是教育理论的退化[4]。
从中英文互译来看,有人认为经验研究对应的英文是empirical research,实证研究对应的是positive research,二者是有差别的[5]。在中国的当下语境中,更多是将实证研究与经验研究等同使用,所对应的英语术语是比positive research更加变通、开放与包容的empirical research,本文即持此用法。广义上说,实证研究主张研究真实的世界(别于由语词构成的概念世界或由信条构成的理论世界),是指从经验资料中总结理论并用经验资料检验理论的过程。这里的经验材料可以是研究者亲自观察、问卷调查得来的一手资料,也可以是历史档案、他人收集的现成数据等等。为了澄清学术界对教育实证(经验)研究的一些误解,笔者认为,需要作一些更深入的学理性思考。如除了外在的功利性追求之外,中国教育研究实证转向的内在正当性是什么?实证研究到底是怎样一种研究?教育研究的实证转向如何对待理论与经验,真的是一种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还是旨在架起理论与经验之桥?等等。本篇文字尝试回应这些问题。
二 中国教育研究为什么需要实证转向
在教育领域兴起实证研究,是对于当下中国教育学研究中一些基本特征的反动,其对应的靶子是过去主流现在依然占主流的类似于规范研究、思辨性论述等研究路数。那么,这些流行已久的基于价值立场的规范研究和纯思辨性的逻辑推演又存在什么局限呢?
(一)对于思辨研究的反思
1.教育研究范式之中西分野
虽然16世纪即诞生了近代科学,但裴斯泰洛奇、福禄贝尔、黑格尔、赫尔巴特等的教育研究范式,遵循的依然是目的论范式——在道德哲学、价值哲学等指引下,讨论达成目的的内容、方法和手段,如围绕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方法等来展开论述。西方教育研究的实证转向也经历了较长时间。最主要的范式演进线索是:研究运动的萌芽可以说是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建立的第一个心理实验室时出现的。几乎同时,英国的高尔顿与皮尔逊开展统计方法的研究并被运用于教育研究。20世纪初,测量运动之父桑代克认为数量关系模型最重要,不能量化的关系都是不重要的,如研究刺激反应关系等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教育研究中广泛运用。不同于桑代克与课堂情境只有表面接触,斯金纳的研究等开始观察学与教的情境。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50年代系统展开的教学层面的定性研究,当然这种定性研究已经脱离了哲学框架。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宏观的教育政策研究,采用了系统的社会开放系统理论的研究方法。时至今日,更是倡导和推广严格方法特别是随机试验的实践项目,基于此研究结果指导教育政策与实践,如《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法案中关于支持那些“基于科学证据的研究”被提及百余次[6]。西方现代意义的教育科学研究,尽管受到诠释学、批判理论的批评,但并没有否定“科学—实证”取向的作用,而是一直把目光锁定在“科学—实证”的方向上[7],日益重视“事实材料”。在实证主流中转型不及的教育学院,如曾经雄杰一时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系甚至面临被裁撤境地[8]。新中国教育学科的创建主要借鉴苏俄传统,之后又经历一段较长时期的学术断层。改革开放之后引入多国教育理论时又过于关注理论而忽视了方法及其科学精神,加之中国治学中的尊崇学术权威、重思辨传统在教育学研究中得以代际传递,对名人名言旁征博引、基于概念定义的逻辑推理成为教育学研究经久不衰的套路。具体表现为以抽象的概念、命题为直接操作对象,以逻辑分析作为具体研究方法。
2.逻辑推演之概然性
诚然,当前中国这种主流的纯思辨性的逻辑推演也是一种求知的方式,只是这种求知路向更类似于逻辑和数学推理的演绎推理。逻辑学表明,并非所有的推理都是必然性的推理,科学推理“只具有概然性”[9]5。理智的作用对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观念之间的关系”,一类是“事实”[10]26。与此相对应,人类的推理和知识也分为两类:第一类关于理性的观念对象,可得必然的结论,只要观念本身不变,它们的关系就不变,包括直观、数学和逻辑演绎的知识;另一类则涉及理智的经验对象,以经验式推理为特征,包括关于实际的存在和性质方面的知识,是需要经验才能做出判断的知识,因而只是或然的推理。关于事实的知识则不具有前一种知识的近乎完美的品质,不能妄自断定它的确定性,而必须借助于外部对象的实际状态。在复杂的经验世界中,逻辑演绎的结论并非必然,也即结论只代表一种可能性,如果前提为真并且推理正确,那么结论仅仅可能为真,实际结果还会有别的可能性。不少师范生毕业从教后发现,教育学心理学课本上的知识与理论在实践操作中多有行不通之处。因此,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产生了一种互相瞧不起的风气:书斋学者认为“一线老师只靠经验办事,太不爱学习了”;一线教师认为“大学教授们的理论太高深了,与实践不搭调,根本没用”。这些事实表明,逻辑推理上正确的事情,在实践上可能行不通;教育一线的鲜活隐含着丰富的教育问题,而这背后又隐含着诸多等待生发的理论。
3.实证研究对于概然性知识的意义
思辨研究过分注重对事物内部统一性的探求,从而忽视对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或变动性的知识,容易出现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的倾向。再者,思辨研究的命题大多无从观测与证明,在当下的教育研究中,或落入宏大叙事的窠臼,或成为苍白的语言游戏[11]。在科学征途中,哲学思辨是一种过渡阶段的产物,哲学史上的哲学问题一次又一次地交给科学家去回答。哲学家赖欣巴哈即认为哲学问题必须由经验科学来回答,这样的答案更深刻、更可靠[12]234。实证研究则有利于探求一个理论的真伪以及成立和发生作用的条件。教育学也脱胎于哲学,教育学之父赫尔巴特在《普通教育学》中呼吁把教育学建立在心理学和实践哲学的基础上,预示着科学化是教育学独立的基本动机和目标。无论是采取哪种性质的研究,任何科学所要呈现的东西必定是“知识”。什么是“知识”?柏拉图《泰阿泰篇》的解释是:“附带逻各斯的真判断就是知识,在无逻各斯情况下,判断不属于知识(陈庆译)。”[13]也即,“知识=被证明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JTB))”。按此定义,“知识”之存在需要三个必要条件:第一,必定存在一个“判断”;第二,判断者“相信”所存在的“判断”是真的判断;第三,关于这种判断之“真”的“相信”是被证明的。这里的证明则兼容理性证明(先天的知识)和经验证明(后天的知识)。科学求知的路径不能只有逻辑推理这一条。胡适在1928年《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将科学方法的应用归结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4]。其实,假设和求证只是基本的规范性要求,假设可以从逻辑演绎中得来,也可以从现象归纳中提出,但都必须经过“求证”以证实或证伪。这就好比初中语文时学过“议论文”写作的三要素,论点、论证、论据缺一不可。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流行一种研究方式叫三角测量法,这一来源于天文学等领域的方法,其依据的原理大意是仅仅从一个点出发来观测只能知道某个点是否在这条视线上,而不知其具体位置,要确定空间中某个点的具体坐标,必须增加别的观测点。同样的道理,教育领域中研究问题的解答,仅仅从逻辑思辨出发是残缺的,要尽可能的求得真知也需要增加别的观测维度,用经验事实检验理论的真伪及其条件性,从多个角度(含不同的理论视角、不同的研究者)或立场收集并解释信息,或者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研究策略与方法。
4.西方教育理论的经验基础存在认知偏见
理论作为一种认识方法、框架或视野,对于认识教育经验的指导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当前中国教育学使用的理论和概念,绝大多数来自西方。作为来源于西方的理论,其经验基础自然是西方本土的教育经验与事实,从实践中直接提炼出来的理论尤其如此。所谓“数据本身也是心灵的产物”[15],处于某种社会文化圈中的理论生产者因对自身社会背景、出身背景,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认同缺乏反思,也容易产生认知偏见[16]42。只是这种抽象性理论背后的经验痕迹往往被隐藏、被消弭。而又由于其逻辑上的自恰性,其背后隐藏或隐含的经验基础或前提常常成为别国学者的盲点。当我们运用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问题时,由于对理论的经验前提和基础的无知、忽略、忽视,往往会误解、误用理论,可能发生“指称错位”问题。因此,中国教育研究对于实证取向的渴求,也是中国教育改革实践的丰富性、复杂性与西方理论的经验基础中可能存在的匹配偏差所决定的。中国有些教育现象、教育制度,如班主任制度等[17],与西方不同,亟需更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讨。西方文化与经验基础上产生的知识也有可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中国经验基础的审视有助于改善西方主导理论的普适性。实质性概念和理论的创新应该来源于扎实的经验研究而不是照搬西方理论[18]。
(二)对于规范研究的反思
1.当下的“问题—对策”范式
当下中国教育学研究还有一个基本特征,即规范研究占据主流。长期以来,教育研究论文写作套路是:设定的研究目的是要“发现”教育领域中的“不良现象”、“错误方向”、“弊病”或“存在问题”,然后广泛、全面地寻找这些现实问题的原因,接下来是要找出解决办法,例如建议有关当局设立相应的政策来引导等等,以便能将这些“走入歧途”的教育实践或发展“指引”到“正确”的方向上来。有些论文整篇的主旨就是这个,有些论文则是在行文中或多或少流露出这样的意识,有时政策建议还是论文的重心。这种现象如今虽有减弱,但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类论文标题常常是类似“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要着眼于价值重建”、“新农村建设的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必须由教育家来办大学”、“大力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等表述。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规范研究路数,笔者把这种研究下的写作风格称之为“问题—对策”范式。
与实证转向通过客观材料考察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不同,规范性研究就是从理论出发看待一个事物应该是怎么样的。规范研究表现出先验论特征,注重从逻辑性方面概括指明“应该怎样”、“应当怎样”或“应该怎样解决”。其主要特点是在进行分析以前,先确定相应的准则,然后再依据这些准则来分析判断研究对象目前所处的状态是否符合这些准则。如不符合,那么其偏离的程度如何,应该如何调整。我们不能否认,这类研究的优秀成果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教育研究界也确实需要有价值的政策研究。虽然这些规范研究中不少是基于扎实的数据材料来提出政策建议的,但一般不会因为这些研究使用了经验资料就把它作为实证研究,因为实证研究更关心“是什么”、“为什么”等问题而不是“应该怎么办”。
2.规范研究的角色定位之困
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上述“问题—对策”范式的写作路数,在某种程度混淆了研究人员的角色定位,也即学者“干了不该干的活”,把学者身份等同于“官员”、“国师”、一线工作者,或者把学术论文与政府调研报告等文体等同起来,从而混淆了服务面向[19]。也就是说,一个写手不是不能写这类文章,但是要明白自己的读者或服务对象是谁?如果是为学术交流、获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可而写作,此时的身份就是学者。如果是为政策咨询、教育实践工作而写作,则无可厚非。实际上,这种研究范式对于一些有志于研究工作的一线教育工作者也起到一些不好的导向,他们认为教育研究就是这种套路(找问题、分析原因、寻找对策),否则就不是教育研究。
在方法论上,这样一种范式下提出的各种方法或政策建议,只是一种猜想、假设或解决问题的可能路径,这些方案方法是否可行有效需要后续的检验(含证伪),然而这些后续工作却没有下文了,如果这些建议真正被采纳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后果。这种范式下提出来的对策与政策建议,也受到一线教育工作者、了解基层情况且具备一定决策权和执行权的教育行政官员的提防,“他们是知识分子是学者,他们写这些东西是为了职称为了课题。如果按照他们提出的这些政策方案去决策或执行,造成失误和损失,最后挨骂的是我们又不是他们”。这种用理念建构现实也许是受“理论指导实践”这一宣传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学者的“专制”,但这种做法也属于乌托邦革命。其实,经验科学只能帮助决策,而不是自身做出决策。因此,一些教育学者常常抱怨“政府不听我的”,官员又抱怨“学者写的东西没用”。也有的官员为此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学者为什么急于干后面的事,提一大堆政策建议,而不打个提前量,把事情和问题真相搞清楚,把逻辑理顺”。其实,作为有实证精神的社会科学家,往往有意识避免做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因为他们意识到两个问题,一是自己的研究也具有价值关联性,二是研究方法具有局限性,无法达到不容置疑的结论。相对于纯思辨讨论和规范性研究而言,实证研究更强调“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3.规范研究的价值中立之坎
关于研究中的价值中立问题,存在一定的争议,而且教育又是有价值倾向的实践活动。的确,就本体论而言,教育的定义要排除“恶的教育是教育”这一命题[20]。但我们要明确,“教育”与“教育科学研究”不是同一件事情,二者遵循不同的逻辑和伦理。价值中立,强调的是科学家对待科学的态度而不是对待社会的态度。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对象更为复杂,而且研究者也置身于切实的文化与社会之中,这很容易诱使人们将价值与利益的关系置于事实本身的考虑之上。在主流研究还处于哲学的思辨与道德说教的教育学研究背景中,重提价值中立问题是有必要的。一门学科要走向成熟,就不能将信仰和理想、个人好恶、流行的价值观念做为科学立论的根据,因为这是缺乏科学解释力的。价值中立原则强调科学探究自身的逻辑,不能从事实判断中逻辑地导出一定的价值判断,也即“是”与“应该”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不能简单地从“是”与“不是”中推论出“应该”与“不应该”[21]509-510。韦伯整合了实证主义与新康德主义,区分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相关性和价值中立性,认为作为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可以估量行为的可能后果,但不能做出“价值判断”(即“应该做什么”),这是一个科学研究者和政治家或者普通公民的区别[22]52-53;但是,价值中立也并不必然地排斥一切规范性的研究和科学命题中的价值含义。为此,吉登斯提出,社会科学的核心任务旨在说明行为情境及其认知能力的局限性[23]465。如“吸烟有害健康”,这是一个具有价值判断色彩的陈述,但这一陈述的科学性依赖于经验证明(吸烟行为造成的病理事实),而不仅仅是主观好恶的表示。同理,社会科学中,我们需要思考规范研究的可能性及其界限,这几乎具有决定性意义。比如,规范研究中预设某种价值或理想状态时,其关键在于能否把规范性命题还原为实证性命题,即经验地描述出这些价值所依托的事实和事实关系。
三 教育实证研究之是与非
笔者亦任一家学术刊物的副主编,一些作者得知拙刊倡导实证研究且认为短小精干的论文可遇而不可求,便说“我写了一篇实证研究的论文,花了很长时间,有两万字”。我收到邮件后打开一看,发现这其实只是一个调查报告而已。调查报告,如果不具备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无助于认识事物的特性和发展规律,一般来说是很难发表在追求学术品味的刊物上的。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社会调查(教育调查)与实证的社会科学研究有无区别?类似的问题还有十多年前中国教育学界广泛争论的“质性研究还是新闻采访”[24],而早在上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学界也产生了“社会学调查与社会调查”之争。不少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都从技术层面来论证自身合法性,如社会学家专注于问卷设计的技巧和调查操作的质量,而教育学者如陈向明、阎光才、张雯闻等也从如何获得真实有效的资料与研究结论来论证新闻调查不属于质性研究[25-27]。据笔者所知,客观真实同样是新闻的生命线,新闻采访中也提倡借鉴社会科学方法[28],不少记者和媒体也在进行深度调查[29]。但是,同样有人类学家提请学界反思,人类学怎样才能比一个深谙访谈的调査型记者做得更出色[30]?那么,我们不妨反思这样一个问题:一份调查是否由社会科学家去操作就变成“学术”的了,如果一个记者甚至普通大众也像社会(教育)科学家那样使用精深的方法和程序获得同样质量的资料、信息,他是否就是在从事科学研究?为此,我们有必要思考学术调研与普通调查的区别何在?社会(教育)科学研究的安身立命之所是什么?如何看待科学研究的结论与大众常识的关系?
(一)学术调查与普通调查的区分:研究假设之有无
在社会学产生之前以及社会学产生之后,普通的社会调查一直存在着。20世纪初,中国一些教会学校的外籍教授为指导学生实习,从事一些小规模的调查研究。如1918-1919年间,美籍教士甘博(S.D.Gamble)与燕京大学教授步济时(J.S.Burgess)等曾仿照美国春田社会调查的成例,调查北京社会状况,内容包括历史、地理、政府、人口、卫生、经济、娱乐、娼妓、贫穷、救济、教育等。此后,中国学者李景汉出版《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是早期社会调查研究的代表作。然而,这些社会调查被认为没有方法论的指导,调查与研究割裂。因此,吴文藻引进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研究法和以英国马林诺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观点,在中国提出并践行“社会学调查”[31]365。此所谓社会学调查,即社区研究,就是应用社会学的一般理论,深入一个有限制的地域社会内,进行对整个社会的性质和问题的分析研究。比之于过去的社会调查,社会学调查强调专业学术活动的目的性,不同于社会调查着重实际社会问题的材料搜集以了解社会现状,社会学调查强调围绕研究问题深入社区搜集资料而不必面面俱到,着重通过调查研究考察社会变动,发现或发展人类共同生活的原理。
再以社会科学研究者和普通工作者都常用的定量的问卷调查为例。不少人认为,使用了问卷调查,得到了确切的数字、百分比,就得到了科学的研究结果,就算是科学研究了。的确,社会科学的问卷调查与普通的问卷调查,在形式、内容、操作技术上都极难有明确的界线,或者说,二者在这些维度上只是处于连续光谱的不同位置而已。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普通的问卷调查,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绝对数调查。简单地说,就是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多少人做过某种事,或者某种社会现象涉及多少人。如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902万人,这就是2016年由民政部牵头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的调查结果。二是百分比调查。仅仅得到各种现象的百分比就足矣。如全国留守儿童中隔代监护的占90%。这类调查的提问可能有很多,但是所问的现象都是相互独立、没有关联的。调查者也并不期望从中发现别的什么,或者有心无力。三是分布调查。比前两者稍有深入,除了数字和百分比外,更想知道它的各种分布状况。比如90%的隔代监护留守儿童主要分布在什么年龄段,男童多还是女童多,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儿童多还差的儿童多,学业成绩好的儿童多还是学业成绩不良的居多,离城区远的学生多还是近的多?如果要了解这些分布状况,就要在问卷设计时把时空、分层、范围等纳入。
这种“分布调查”,其实就是从普通问卷调查向社会科学问卷调查的过渡形态。因为它已经有了最基本的相关假设。社会学界的问卷设计有“五朵金花”(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的说法,因为,如果不询问这“五朵金花”,研究者就无法判别被访者的社会阶层归属,更无法知道某种现象在不同社会阶层中有无差异及其差异程度。这样,这个调查就下降为数字调查、百分比调查了,属于普通的问卷调查,仅仅调查一个现象的各种情况,属于“单纯的描述”,而不是在研究一个问题。社会科学的问卷调查与普通的问卷调查之间的分野,在此就可以分辨出来了[32]9-33。社会(教育)科学,之所以冠以科学之名,在于对自然科学之模仿,定量研究尤其如此。科学的灵魂就是首先提出相关假设,并对其检验,从中获得新认识。经典的社会科学研究最基本的预设就是社会运行存在着某些规律,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找出这样的规律并且加以解释。因此,社会科学的问卷调查不得不运用“相关假设-检验式”设计,以达到研究目标。在分布调查中,只要设置了一个指标,它背后就一定有一个相关假设。把“五朵金花”中的任何一个指标设置到问卷里,都意味着考察的社会现象与设置的这个指标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当然,调查的统计结果,可能表明双方确实是相关的,也可能表明相关假设是错误的。当然,在问卷调查实践中,有些只是简单地把“五朵金花”纳入问卷,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相关假设,如几乎每一份分布调查都问及被访者的性别,但并没有对这种现象进行性别视角的分析,也没有进行这种现象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假设。
(二)问题意识:学术研究的本质特征
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这看似不言而喻,但却常常被忽视或漠视。其实,这关乎学术研究的一个本质特征问题:问题意识[33]。同时,问题意识也是学术研究的安身立命之基。如果缺乏问题意识,没有问题的引导,哪怕是一名学者,写出来的文字也未必就是学术论文,可能只能成为新闻报道、政策分析、情况描述等等。我们也不否认学者、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的意义。然而,现实中,我们(研究人员)讲故事可能不如新闻记者、民间故事人、小说家等生动有趣,做政策分析不如政府官员等实践工作者那么有针对性和实效性。那么,作为研究者或学者的职业/专业的正当性何在?笔者认为,大致地可以从服务对象的视角来考察,记者、故事人等的受众是社会大众、实践业者,他们的作品更倾向于得到普通大众的认可,而学者的受众是学术界,其学术成果需要在参与理论对话中取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当然也不排除“雅俗共赏”的学术成果。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学者的研究工作需要回答学术共同体中的问题,参与学术共同体对话。
就教育与社会现实而言,学者与一般人对日常生活的思考,其本质不同在于,学者提出的理论通常是根基于过往学者所提出的理论之上,即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具有“系统”与“累积”的知识成为现代学术的特色。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已仔细研讨过前人的著作,他们知道前人是谁,他们的肩膀在哪里,他们的思考是需要进入学术或理论脉络的,有一批可供理论上或对话上的他者。在这里,相对于自说自话任意空谈,“问题意识”与“理论意识”密切关联,学者通常在一定的理论概念下思考和分析教育与社会现象。
诚然,实证研究者的研究资料来源于经验事实,但要求超越自身直接经验,如社会学的想象力要求“局部环境中的个人困扰”与“社会结构中的公众问题”勾联起来[34]33,摆脱个人观点的束缚以探索社会各种复杂关系。比如一位学者,作为一位父母,可能也困扰于自己过于关注自身学术成长而忽视了自己小孩的身心发展,但当他作为学者时,思考的是如“社会阶级、社会资本与文化再生产之间的关系”[35]等更通则性的问题。笔者自己的兄弟姐妹家里也有不少留守儿童,笔者与他们常常困扰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学习成绩等,但笔者作为学者时思考的问题则是“分隔多地的家庭成员如何维系家庭这种亲密共同体生活以弥补或促进儿童的成长”[36]。相对于普通人更倾向于思考狭隘的甚至是个人的议题,“科学知识的目的在于去掉一切个人的因素,说出人类集体智慧的发现”[9]10。一般而言,学者则针对广泛的教育与社会议题做总括性思考,其借用或提炼出的理论模型(案例研究中发现的因果机制)能够在脱离于具体现象的层面上明晰地表述出来,对类似问题具有一般层面的解释能力。当关注普遍性问题成为一种习惯时,或说习惯于从普遍层面解释命题时,注定是痛苦的。因为,首先,你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普遍框架;其次,那怕已经提出一种框架,但不知道它能否顶住后续出现的现象的考验。当然,专业和非专业的思考方式并没有确定的鸿沟。如社会学家瑞泽尔提到,“如果你读过这本书(一本普及性的理论读物,笔者注)后,也去研读过去的理论,然后以更系统化、更一贯性的方法去研究一般的社会议题,你也可以成为社会学者”[37]3。
问题意识既然是学术研究的本质特征,那么,提问则成为理论创新之源。何为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才是好问题,我们要如何提问?在科学研究中,所谓“问题”就是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的问题。也就是说,“问题”是相对于现有的“知识库存”而言的,是现有的“知识库存”不能解决或解答的问题。曹锦清从预期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出发,将问题分为三类:理论与现实的差异、政策与实践的差异、同类事物比较的差异[38]。仇立平将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或“真问题”主要梳理有以下四类:第一种是现有“知识库存”中还无法找到的,堪称填补空白的开创性问题;第二种“问题”是采用不同理论对一个旧的问题给予新的诠释,或者采用新的方法进行再研究;第三种“问题”表现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已有研究发生了新变化,或者原来的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变化了(着)的社会(教育)问题与现象;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问题本身也是一个问题,因其背后隐藏着理论或者方法论的选择,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39]。其中,第一个问题关于是否“填补空白”,学界有两种争论,一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一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不过,不管居于何种立场,都是将问题与知识库存进行对比(将今天的太阳与历史上的太阳进行比较)之后才能得出结论。一般认为,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填补空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当然不排除特例),需要反思自己对前人成果的掌握程度。
(三)教育实证研究的结论与常识之间的关系:证明还是符应
教育界存在这样一个社会现象,即社会上每一分子都可以对教育说上几句,学生家长、其他行业人士、政府官员都能对教育(教师)指手划脚,因为他们起码有过或多或少的受教育经验并有其自身的认识;而家长(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一职业更是无需持证上岗,只要结婚生子就自然当上了家长,凭借经验(包括他人经验、从父辈处习得的常识)和感觉教育子女;教育学者也常常感叹教育研究的门槛很低,谁都可以进行“教育研究”,困惑于教育学没有自身的理论与方法。这些现象,可以转化成一个教育(社会)科学的基础性理论问题:研究结论(理论)与常识之间的关系。从实证研究的脉络考察,可以将学者们对常识的态度划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态度,“与常识决裂”。这种态度主要表现在经典社会科学家那里,目的是说服学界和大众将社会学当作一门科学来接受。孔德号称实证哲学之父,把人类理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实证阶段)。虽未言明,但在孔德的科学分类里,没有任何属于常识的藏身之地。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涂尔干则更直接了当地指出:“凡是科学,其目的都在于发现,而凡是发现,都要或多或少地动摇既有的观念。因此,除非使常识具有它在其他科学里早已不复享有的权威——但不知从何处获得这种权威——,否则,在社会学中,学者就得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并对自己的研究结果坚决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态度。”[40]1作者接着指出:“我们还太习惯于按照常识的指引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所以很难将常识与社会学的讨论彻底分开。甚至当我们自以为摆脱了它的影响时,它也会趁我们没有防备而把它的决定强加于我们。只有长期不懈的专门实践,才能使我们避免这样的失误。因此,我请读者也不要忽视这一点。希望读者永远铭记,最常用的思维方式可能最有碍于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所以大家应当警戒第一印象的影响。”[40]1-2。他更是尝试通过对自杀率的研究,否定了常识(包括当时的心理学界)关于自杀的很多观点[41]7-24。处于反思立场的布迪厄在使用理论概念时,也务必是要与常识决裂的,不仅与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决裂,而且要与学界的套话决裂。其实,当前那种认为“研究结论只是一种常识,没有理论价值”的观点,其理论前设即包含认为科学研究必须优于常识,否则便失去了科学研究的正当性。实际上,即使涂尔干本人,并未成功地切开科学与常识之间的纠缠,常识并未被他抛开或者推翻,甚至成为其结论的基础。在他的自杀研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自杀者本人的“意图”(intention)的缺席,也许因为那是属于常识的范畴。不过,他所使用的自杀统计数字,则是由常识汇集而来的官方数据,其中包含的自杀案例全是常识所定义。另外,他所界定的“社会事实”,是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的。无疑,常识也应是一种社会事实,比如社会中的道德常识。因此,有学者认为,“反对常识,不过是他建立社会学科学地位的一种修辞罢了”[42]。
实证研究的第二种态度可称之为“道不远人”,认为教育与社会科学的规律来自于日常的、现实的社会生活,自然不会与常识太过疏远[43]12。加芬克尔甚至提出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一个根本的观点就是人人皆是社会学家,即常人与专业社会学家之间并无根本区别。吉登斯也没有一概否定常识,甚至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之一,就是确证妇孺皆知的常识观点事实上是有效的[44]5。吉登斯提出“双重解释学”,认为社会科学的逻辑包含着两套意义框架:其一是由普通行动者构成的充满意义的社会世界;其二是由社会科学家创造出来的元语言[45]。他把常识定义为行动者关于社会生活的陈述性信念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社会科学的确会批判常人行动者关于社会世界的虚假信念,但与自然科学比,这些批判的概念和理论得以构成的背景、实践意涵大为不同。社会科学的概念是被制造来分析社会世界的,又反过来被纳入这个世界,不可避免地为常人行动者的理论和实践所熟悉,不局限为一种专业话语[46]。在社会—人文环境中,即使是只具常识的“外行”,他们均时时处处参与着社会的建构过程,也是具有掌握知识和技能的行动主体,既在行动,也在阐释。反过来说,倘依常人(或外行)看来,用某种学术语言讲述的社会—人文专业知识也可能是常识[47]8。这种“双向阐释学”构成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基本品质。教育与社会科学的问题大多数是许多人感知的社会行为,我们不必看到研究结果同社会经验(常识)一样就大惊小怪。相反,如果大多数研究结论都与社会经验、大众常识不一样甚至相违背,也不正常。其实,我们应该这样思考:是因为公众的一般看法建立在长时间的敏锐观察基础上,从而让这个(种)常识经受住了科学的检验。也即,是常识与科学论证的结果相符合,而不是论证的结果是一个常识性的结论。
无论其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多么精深、分析技术多么复杂,根本上说与人们的具体生活经验密不可分[48]。那么,社会科学研究究竟在什么层面上增进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第三种态度,可称为“赋常识以理论”(make sense of common sense),科学对常识的证实和证伪都是有理论意义的,更惶论异于常识的新发现。生活经验中的“常识”和“感觉”,总是基于特定的人生经历和信息来源,不同的社会人群(如男性与女性、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生活体验往往大不相同,他们各自认为“显而易见”的结论也往往相互抵牾,基于大规模系统抽样的长期追踪调查则能更加全面、无偏见地解答这一问题。社会科学中没有任何结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常识更是如此。科学有助于明确常识的适用范围。常识生产过程中的背景知识和思维方式,大都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化”的结果,这种“理所当然”往往具有欺骗性。系统严谨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克服这些内在偏见,将“想当然”置于批判的放大镜之下。譬如,“父母离异会给青少年子女成长带来不利影响”堪称常识。但有研究表明,父母离异的青少年成长状况虽然不及父母婚姻幸福的子女,但明显好于那些在父母不幸婚姻中生活的子女。这里的常识就存在逻辑链条的断裂:子女的身心健康问题是由离异这一事件本身导致的,还是由离异前就已不幸的父母婚姻导致的?如此,父母婚姻不幸才是子女成长不利的元凶,及时了断不幸的婚姻反而有益。退一步,即使结论与常识无异,但逻辑推导的过程中常有新的发现。因为,日常生活中的思维往往模糊且跳跃,会模糊地意识到“A导致了B”,却很少考虑A是怎么导致B的,学术研究可以帮助了解导致某一常识成立的具体机制。
小结而言,常识与研究/研究结论的符应类型,可分为符合、不符合、部分符合部分不符合三种类型。常识看似正确的缘故是,任何一件事的不同观点,都有相应的常识谚语所对应,如“近朱者赤”与“出淤泥而不染”。常识也有被淘汰的过程,对于常识的证实或证伪有利于将相关观点正式纳入学术论的脉络,研究结论可以是进一步明确、验证或修改、修正或者引领常识,其意义在于考察常识在教育与社会生活中的应用范围、作用以及具体机制等等[49]。并不是说所有以验证常识为目的的学术研究都是有价值的,比如用学术行话、貌似科学的数字、公式和图表去重叙常识。学术研究要有所为,在于必须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或不是什么,并在回答问题中推进或构建理论[50]。能否“赋常识以理论”,关键是看这项研究对于智识有无带来任何长进。从认识论上讲,理性认识都是基于感性认识之上的,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认识从感性阶段向理性阶段的飞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环节),一是材料搜集中的经验(包括实验)事实是否完备、全面,二是对经验材料进行科学的逻辑加工、理论概括。科学之为科学,最核心的部分是一种对经验材料自组织的过程和理论自我改进的机制[51]。社会科学与常识并非简单对立,社会科学研究者也生活在日常世界中,研究主题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不得不注意拉开研究成果与常识之间的距离,保持一种“陌生人”角色和警醒意识。
四 教育研究的实证转向如何对待理论与经验
在一些社会科学的重建之初,一些实证研究工作,缺乏理论前提,或对隐含的理论假设未作明确和充分的讨论。还有一部分人,将实证研究标签为实证主义,而在中国语境下凡是主义就有极端之嫌,因此不符合“辩证法”,是“不正确”的。不可否认,他们一定程度上秉承了实证社会科学的经验性特点,但忽略了理论前提的需求[52]。从对实证(经验)研究的广泛定义来看,其理论旨趣是不言而喻的。与实证主义学派常常贬低理论研究和理论指导不同,应用经验(实证)研究方法并不等于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指导。在教育与社会科学中采用实证转向,并不是要偏废理论,反而是为了加强经验与理论的沟联,加强对理论的检验,以较准确的研究来指导实际工作[53]14。关于实证研究的规程,已经有不少优秀的教科书和论文出版,本文对此不赘述,只作原理性阐述。实证研究一般分为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两种,本文也依此分别叙述。
(一)量化研究:假设作为理论与经验的桥梁
从国际一流社会科学杂志的范文看,实证研究一般包括八个组成部分:问题、理论(文献)、假设、数据、测量、方法、发现和结论,称为“洋八股”结构。简言之,这种结构就是,一项研究要从问题出发,然后综述相关文献和理论、讨论各种不同观点和可能的答案,进而从中抽出假设命题;之后测量概念,收集数据,设计分析方案;最后分析数据以检验假设,并做出总结[54]。很明显,这是量化研究的套路。从方法论角度来看,问题、理论(文献)、假设可以称为“前操作化阶段”,而数据、测量、方法和结果可以称为“操作化阶段”。这种研究的核心是理论、假设和数据。其中,假设乃连接理论与经验之桥梁,假设便是论文的核心观点,需要论证才能转化为知识。这里的论证便包括理论论证和经验论证。以肖日葵的《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研究为例:
教育获得的影响因素中,家庭背景被学术界愈加看重。随着研究的深入,家庭背景操作化指标逐步精细与扩大,文化维度日益受到重视。基于现有问卷设计与模型建构的不足,作者梳理了文化资本的概念演变,将文化资本界定为高雅文化资本和文化资源,预设家庭背景通过文化资本进而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据此提出了家庭背景作用假设、文化资本作用假设、文化资本调节作用假设、文化资本作用机制差异假设、教育再生产差异假设等若干研究假设。基于上海市2008的调查数据,在变量操作化的基础上应用多元线性回归(OLS)模型检验所提出的假设,以分析家庭背景、文化资本对教育获得影响,揭示家庭背景影响教育获得的文化资本机制。[55]
好的经验问题背后,都有一个理论问题,实证研究的“问题提出”部分,特别强调理论缘由(theoretical rationale)。研究者的个人动机、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不能算理论缘由。理论缘由的获得必须进入学术脉络,可以是对著名理论的追捧,也可以是批判。当然,对理论缘由的追逐也可能将研究引向歧途。如一些西方理论可能根本不适用中国研究,生搬硬套就会衍生出不恰当的问题。一般而言,理论缘由在文献综述中寻找。这里的文献,主要指核心文献。作为一种书面论证,文献综述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前人研究中建立逻辑论证,寻找到可信的证据,回答研究问题,从而将一个论题推向前进[56]3。因此,文献综述功用有三:除了提出理论缘由之外,包括澄清贡献和提供理论框架。寻找理论视角是文献综述最重要的功用。即使研究者面对的是从未观察过或者西方理论从未考察过的新现象,比如中国的班主任制度[57],依然需要理论提供观察视角。与著名理论(学说)“攀亲戚”很重要,与他们“划清界线”更重要。通过澄清与现有理论的渊源和区别,研究者才能说明自己的创新之处。即使研究者创造自己的理论框架,仍然应认真对现有理论进行批判性回顾。
吴重涵发现,在中国的教育实证研究现状中,较好的文献综述分为相对独立的“问题综述”和“方法论综述”,前者旨在找到研究问题在问题链背景中的定位,后者旨在寻找与研究问题有本质理论联系的概念体系,形成新的视角,并以此建立关键词和研究变量,以更广阔地寻找文献[58]。在实证转向中,经验资料常常不能够直接检验理论,所以需要从理论中演绎出可验证的假设,特别是较具普遍性的理论,需要一些“中介”命题(假设)才能与资料发生关系。至于数据获得、概念的测量与操作化等研究设计,有较多的教材论及。最后的结论部分,一般有概括经验发现(对假设的检验结果)、探讨对假设的证实或证伪的理论含义、进一步的理论推论(新假设)等三个任务,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个任务,即回到文献或理论综述来阐明本研究的经验发现的含义。
(二)质化研究:从故事到理论
质性研究引入中国的教育研究已逾20年,然而,质性研究依然常常被误解。如认为质性研究就是讲故事,是对程式化数据分析技术的简单套用,对原始数据的简单呈现。因此,质性研究成为了方法论缺失、不进行文献综述、不参与学术共同体对话的借口。质性研究似乎意味着“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我们也不时会看到一些文章,故事有趣、文笔老到、方法可靠,但研究结果平淡无奇。其实,质性研究并没有那么简单,几乎任何一个学者都将“从原始资料中形成结论和理论”作为质性研究的特征。也就是说,质性研究者在研究之前可能并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也没有相对的基本假设/判断,但经历一定的田野工作之后,经验材料要进入相应的学术脉络,与学术共同体产生理论对话,否则可能成为没有问题意识的非学术文本,混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讲故事。
以王黎芳的一项研究为例:
县中现象在高中教育领域司空见惯。通过跟踪性个案调查发现,华北某一贫困县城的重点高中学校的日常运行管理中表现出如下特征:以升学率高的高中学校为模板进行资源重组,以高考为中心进行师资培训,依据考试成绩进行师生激励,以考试高分为目标的班级竞争,封闭式的时间管理等。在对经验资料的整理分析后,作者回到布迪厄的惯习理论中,认为县中现象的实践逻辑就是高考惯习塑造机制的生产和再生产,其根源在于学校场域中不同主体在高考惯习的型塑上寻找到了利益结合点,从而通过规范与利益的统一、规范与认知的契合为高考惯习的塑造奠定了坚固基础,最终实现了宏观社会事实与微观社会行动的联结。[59]
其实,质性研究者也强调理论框架和理论视角对分析经验资料的重要性[60]1-21,下述环节都是必需的: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从中找出自己的视角,构造分析框架,提出主要观点,然后讨论资料收集方法,分析经验数据。以扎根理论为例。扎根理论虽然名之为“理论”,其实为质化分析里的一种作法取向,属于方法。针对的背景是,当时美国社会学界流行两种趋势:缺乏充足经验数据的巨型理论和只有变量分析的经验性研究。这种两极化趋势加剧了理论与资料间的裂隙,无法产生足以解释变化着的、复杂的现代社会的理论[61]259-261。陈向明介绍过扎根理论的基本思路。(1)从资料中产生理论,通过对资料的深入分析,才能逐步形成理论框架。(2)保持理论敏感,这是扎根理论优秀与否的分水岭。不论在研究设计阶段,还是资料收集和分析阶段,都要对前人理论以及资料中呈现的理论保持敏感,注意捕捉新的建构理论的线索。(3)往复比较,数据收集和分析同时进行,在资料和资料之间、理论和理论之间不断对比,并根据资料与理论之间的关系提炼出有关的概念类属(category)及其属性。(4)理论抽样,资料中初步生成的理论作为下一步资料抽样的标准,数据收集由建构中的理论决定。(5)结合原始资料和自己个人的判断,灵活运用文献,将原始资料、研究者的前理解以及前人研究之间看作三角互动关系。(6)理论性评价。[62]其核心分析原理有理论敏感性、理论抽样、往复比较等。可见,扎根理论虽然认为在研究之前不必有理论假设,但其主要目的却是“填平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尴尬的鸿沟”,为定性研究的理论建构提供发展的空间。
一般而言,“洋八股”以演绎逻辑为主,归纳逻辑为辅,更适合于定量研究,尤其适合于规范化的学术训练,但对于高手则可以灵活变通,作为形式规范,可以纳入实质性的概念和理论。质性研究则更倾向于归纳逻辑,其结构大致为:提出问题、收集资料、分析资料、用理论解释经验发现、概括新理论。但在定量研究者看来,这种归纳过程只反映假设产生过程而不是假设检验过程。但也有质性研究者认为,质性研究更需要理论功底,也更能发展新的理论。中国的教育研究的实证转向正在开启,然而,任何转向所提供的探索空间都必将触及界限,亟须学人更多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探索和研究实际操作中摸索与体察。
[1]吕洪波,郑金洲.教育实证研究离我们还有多远?[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1):5-9.
[2]程建坤.反思教育研究的实证情怀——兼与D.C.菲利普斯对话[J].教育学报,2016,(3):11-18.
[3]王竹立.我为什么不太欣赏教育领域的某些实证研究?[EB/OL].(2012-09-12)[2017-01-01].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4df0fc0102dyy1.html.
[4]龙宝新.论教育理论的退化与应对[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2):1-9.
[5]阎光才.关于教育中的实证与经验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6,(1):74-76.
[6]SLAVIN R E. What works?Issues in synthesizing educational program evaluations[J].EducationalResearcher,2008,(1):5-14.
[7]范国睿,杜明峰,曹珺玮,等.研究引领变革:美国教育研究新趋向——基于美国教育学者公共影响力排名的研究领域与领军人物分析[J].教育研究,2016,(1):126-142.
[8]周勇.芝加哥大学教育系的悲剧命运[J].读书,2010,(3):80-89.
[9]罗素.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M].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0]休谟.人类理解研究[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1]彭荣础.思辨研究方法:历史、困境与前景[J].大学教育科学,2011,(5):86-88.
[12]H.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M].伯尼,译.第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3]陈庆.论“知识”的定义(上):作为知识定义标准的柏拉图式知识定义[EB/OL].(2017-01-13)[2017-02-08].http://mp.weixin.qq.com/s/x9KnFWlTLZZ9AomGRW81GQ.
[14]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J].新月,1928,(9):1-14.
[15]BARBER B R. Science, silence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me reflections on social scientific inquiry[J].ComparativeEducationReview,1972,(3):424-436.
[16]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7]李家成.论中国“班主任制”的意蕴[J].教育学术月刊,2016,(11):11-19.
[18]黄宗智.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J].开放时代,2007,(4):5-25.
[19]戚务念.陌生化的教育学[J].教育学术月刊,2010,(9):15-19.
[20]陈庆.从柏拉图“美诺之问”看教育哲学与教育学的基本问题——反思中国教育学研究之正途[J].教育学术月刊,2017,(1):3-15.
[21]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2]马克斯·韦伯.伦理之业——马克斯·韦伯的两篇哲学演讲[M].王容芬,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3]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M].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4]侯龙龙.质的研究还是新闻采访——同陈向明博士等商榷[J].社会学研究,2001,(1):110-117.
[25]陈向明.文化主位的限度与研究结果的“真实”[J].社会学研究,2001,(2):1-11.
[26]阎光才.也谈社会科学研究结果的“真实”[J].社会学研究,2002,(3):118-124.
[27]张雯闻,贾娜尔.为什么质性研究不是新闻采访——兼论教育与社会科学的方法学基础[J].教育学术月刊,2015,(8):26-32.
[28]黄淑敏.新闻报道在借鉴社会科学方法中应把握的原则[J].新闻爱好者,2015,(4):82-85.
[29]叶艳芳.民族志方法对深度报道的示范意义——以1998-2010年《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为例[J].新闻世界,2010,(10):31-33.
[30]阎云翔.小地方与大议题:用民族志方法探索世界社会[J].世界民族,2014,(1):54-58.
[31]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名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32]潘绥铭,黄盈盈,王东.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3]郭于华.问题引导下的田野调查与研究[J].民间文化论坛,2007,(1):28-29.
[34]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陈强,张永强,译.第2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35]姜添辉,周倩.社会阶级与文化再生产——不同社会阶级家长的社会资本对文化再生产之结构化影响及其因应之道[J].教育学术月刊,2017,(1):16-24.
[36]王晖,戚务念.父母教育期望与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成就——基于同祖两孙之家的案例比较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14,(12):66-71.
[37]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8]曹锦清.问题意识与调查研究[J].社会学评论,2014,(5):3-9.
[39]仇立平.社会研究和问题意识[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1):70-75.
[40]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1]迪尔凯姆.自杀论:社会学研究[M].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2]成伯清.社会学的修辞[J].社会学研究,2002,(5):46-61.
[43]张德胜.社会原理[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6.
[44]GIDDENS A.Socialtheoryandmodernsociolog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7.
[45]金小红.吉登斯的“双重解释学”与社会学理论批判[J].国外社会科学,2004,(2):16-20.
[46]吉登斯.何为社会科学[J].社会,2001,(11):12-17.
[47]黄平.未完成的叙说[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48]张跃然.学术研究的意义:为什么仅仅依赖常识是不够的[EB/OL].(2014-05-21)[2017-01-01].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caa10b0101ihff.html.
[49]罗国芬,于林英,田克家.社会学与常识:一个基本理论问题的三种透视[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6-9.
[50]邓猛,朱志勇.从话题到问题:教育研究方法刍议[J].教育学术月刊,2013,(3):25-29.
[51]金观涛,刘青峰.探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的方法[J].哲学研究,1985,(2):16-24.
[52]刘少杰.中国社会调查的理论前提[J].社会学研究,2000,(2):4-8.
[53]郭志刚.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4]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J].社会学研究,2010,(2):180-210.
[55]肖日葵.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J].教育学术月刊,2016,(2):12-20.
[56]马奇,麦克伊沃.怎样做文献综述:六步走向成功[M].陈静,肖思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57]杜时忠.“班主任制”走向何方?[J].教育学术月刊,2016,(11):3-10.
[58]吴重涵.教育实证研究中综述什么:研究方法论的视角[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7,(1):21-25.
[59]王黎芳.高考惯习的塑造与重塑:对县中现象的社会学解读——兼论对素质教育改革的启示[J].教育学术月刊,2013,(8):14-20.
[60]DENZIN N K, LINCLON Y S.Thelandscapeofqualitativeresearch:theoriesandissues[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8.
[61]GLASER B G, STRAUSS A L.Thediscoveryofgroundedtheory:strategiesforqualitativeresearch[M]. Chicago: Aldine, 1967.
[62]陈向明.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9,(4):58-63.
[责任编辑:罗银科]
On Empirical Turn of China’s Education Study
QI Wu-nian1,2
(1.Jiangxi Branch of Center for History of Republic of China, Nanjing University, Shangrao, Jiangxi 334001, China; 2.Jiang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chang, Jiangxi 330038, China)
China’s education study is now at empirical turn. There are some misunderstandings such as taking the change from illustration to empirical study as a binary opposition which would lead to the degeneration of theory. Empirical research is the revolution of main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normative research and critical illustration. Knowledge acquisition needs both rational proof and empirical test. The experiential basis of Western theory and concept is in western local educational experience and facts, which Chinese scholars tends to ignore. The character idea-constructed reality of normative research confuses facts with values, and blurs the role of researchers. Research hypothesis distinguishes academic research from common research so that question consciousness is the basis of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 Empirical research has three attitudes towards theory and common sense, i.e., the violation of common sense,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common sense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y to common sense. There are thre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mmon sense and research result, namely, consistent, partially consistent and inconsistent. Empirical research has its strict research procedure with its function as a bridge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ence.
educational research; empirical research; academic investigation; question consciousness; common sense
2017-02-08
戚务念(1976—),男,江西赣州人,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江西分中心客座教授,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组织与制度、教育分层与青少年社会化、教育研究方法论。
G526.4
A
1000-5315(2017)04-0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