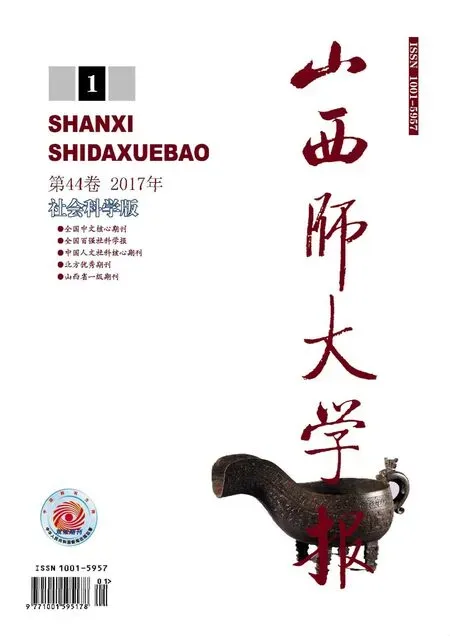论贝恩戏剧《伪装的风尘女》中的性别冲突与妥协
2017-04-13郑伟
郑 伟
(凯里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凯里 556000)
在英国封建社会趋于崩塌,资产阶级伦理尚未建立的历史夹缝中,复辟时期的英国女性表达出了比18世纪甚至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更加强烈和激进的性别意识。作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业女性作家的阿芙拉·贝恩就生活在这一女性意识贲张的特殊时代。她的剧作大多数围绕两性之间的对抗展开,《伪装的风尘女》(1677年,以下简称《风尘女》)亦是如此。贝恩将此剧呈献给内尔·格温①,并在献辞中称其在女性中不仅容貌举世无双,而且谈吐不俗,充满睿智:“您金口一开,那些崇拜者全都侧耳倾听,有如聆听神谕或者先知的预言。他们无不为你话语中的智慧倾倒,并将你雅致的谈话在上流家庭中广为传颂。”[1]92她不仅赞扬女性的智慧,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站在女性角度对英国社会的质问,显示出作家已经自觉地意识到女性群体的“他者”地位。她说:“身处这样一个不允许女性拥有才智的邪恶社会,我们女性因为展现了自我意识,就要受到世人激烈的非议。这些不顾事实做出错误判断的人不过是一群可耻的鼓噪者。”[1]92贝恩夫人在这段话中使用“我们女性”这一短语表明她已经意识到女性在自然属性上与男性对立的关系。内战与复辟带来的社会混乱、封建意识形态崩塌以及激进清教思想的控制力减弱等因素,客观上促使女性呈现自我,重塑理想性别、爱情、婚姻伦理成为现实。《风尘女》生动地写出了复辟时期女性的命运。作品通过女性的眼光反映出男女主人公围绕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权展开的性别之战。本文将从戏剧舞台性道德的变迁、戏剧语言的狂欢化以及性别伦理的妥协三方面考察以《风尘女》为代表的复辟时期戏剧背后隐藏的社会历史变迁及思想更替模式,并以此探寻从人文主义到近代早期这一历史转型期的英国民众在性别伦理认知模式上的突变。
一、 戏剧舞台性道德的变迁:从文艺复兴到王政复辟
《风尘女》以三位来自意大利贵族家庭的少女玛赛拉、柯妮莉娅以及卢克莉西亚为摆脱包办婚姻不得已假扮妓女为中心情节。玛赛拉在维泰博已经爱上了菲尔默,因此她极不愿意嫁给身患残疾的富翁奥克塔威。柯妮莉亚则急于摆脱被家人送到修道院幽禁的命运。后来,玛赛拉与柯妮莉娅姐妹俩遂伪装成妓女逃避到罗马,分别化名为尤菲米娅和希尔维安娜。菲尔默的内心陷入了矛盾,他一方面深爱着玛赛拉,另一方面又无法克制尤菲米亚的吸引。卢克莉西亚了解到加利亚德喜欢一个叫希尔维安娜的名妓,她也伪装成妓女以期引起情人的注意。奥克塔威得知玛赛拉爱上了菲尔默,不禁怒火中烧,决定加害他。为了拯救菲尔默,玛赛拉毅然化装为仆人阻止菲尔默去赴约。假扮成希尔维安娜的卢克莉西亚在黑暗中以为得到了加利亚德的结婚誓言,但事后得知该男子却是朱利奥。白天来临,众人的身份真相大白。奥克塔威放弃了与玛赛拉的婚约,菲尔默与玛赛拉喜结连理,加利亚德与柯妮利亚也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朱利奥亦与未婚妻卢克莉西亚完成了婚姻的约定。《风尘女》喜剧氛围浓厚,带有轻佻欢快的情调。女性活动的空间大为扩展,并且最终把握了自己的命运。
戏剧一开场向观众展现的就是男性像追逐猎物一样追逐女性的场景。朱利奥在大街上偶遇卢克莉西亚。于是他和仆人一路尾随,企图勾引她。《风尘女》中几位品行不端的男性对于女性的追逐可谓明目张胆。他们不仅掌握着性权利上的主动权,并且极少受到道德习惯的约束。道德对于像提克泰克斯特这样虚伪的清教徒的限制同样是有限的,他们只要表现得更加伪善一些就不会受到社会的谴责。此人非常好色,想去妓院寻欢作乐,被侄子撞破以后,只好遮遮掩掩地说自己是来劝导妓女迷途知返的。布封则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富家公子,碍于家庭牧师提克泰克斯特的看管,也不能自由自在地到风月场鬼混。他举止愚蠢,屡遭算计,是一个类似福斯塔夫的喜剧人物。总之,除了菲尔默这样一位爱情哲学家以外,上流社会男性无不以追求女性作为展现男性气质的象征。社会学家斯坦伯格认为:“男性把女性当成了物,比他自身不太真实的东西,一种具有性别的东西。他把这个东西看作他的性猎物、性目标、性异己。”[2]48加利亚德、朱利奥,清教徒叔侄追求异性尽是为了满足男人的欲望,而不是以婚姻为目的。加利亚德流露出要在罗马寻欢作乐的想法时,菲尔默劝诫他说:“对男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对爱情忠诚更快乐的事情了。”加利亚德马上反唇相讥:“忠诚?你难道要我像那些傻瓜恋人一样相信从一而终,白头偕老么?我才不怕背上那个可诅咒的放荡的恶名。我是伟大的爱情胜利者,最痛恨的就是长相厮守,就让内心的激情鼓动我不停地征服女人吧。”[1]96加利亚德在剧中还算不上是不可救药的男性中心主义者,但他这一番赤裸裸的充满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宣言,足以让人们了解复辟时期的英国男性在性权利上的绝对霸权。
从历史上看,虽然从莎士比亚去世到查理二世登基还不到五十年,但英国的戏剧舞台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伦敦繁荣一时的十几家剧场到了查理二世时期只剩下了国王剧院和公爵剧院。文艺复兴时期的清教意识形态非常强大,例如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就不时表现出清教主义的严格禁欲观。陈雷认为:“莎剧《哈姆莱特》中的王子表现出一种对肉欲近乎偏执的痛恨。当哈姆莱特有机会在疯傻的伪装下无所顾忌地抨击世事时,人的性欲便自然成为他火力的焦点。事实上,他此时所攻击的已不只是无度的性欲,就连作为人类社会存续基础的婚姻和生育,也因为与性欲相关而遭到他的诅咒。”[3]哈姆莱特之所以极端反对人类性欲或许因为他身负杀父之仇导致精神异常,但伊丽莎白时代清教徒敌视一切娱乐活动的历史却是真实存在的。伦敦的舞台演出因此中断了十八年之久,圣诞节一度被禁止,乡村的五朔节花柱亦被拆毁。复辟时期的戏剧在性道德方面与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有着天壤之别。《风尘女》中的玛赛拉不再满足被男性塑造的理想身份,她恣意表达的自由思想完全颠覆了男权话语系统。总而言之,处于王朝更替、政体转换、宗教混杂的迅疾情势变化下的英国社会,在性道德领域经历的从斯多葛主义到伊壁鸠鲁主义的转变,在《风尘女》中得以全面的呈现,这种剧烈的变化,伴随着女性反抗的历史暗流与社会巨变相互呼应,却意外地推动了英国在性别建构上逐渐走向现代。
二、王纲解纽:秩序崩坏下的性/性别话语狂欢
《风尘女》中伪装成妓女的少女们借助身份的转换酣畅淋漓地表达了推翻父权社会的声音。柯妮莉亚与玛赛拉姐妹俩不希望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在一个女性没有职业和公共空间的社会,妓女身份反而讽刺性地变成了女性拥有情感自由和在公共场所活动空间的保障,以上现象的产生都与复辟时期的宫廷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查理二世时代的宫廷弥漫着淫荡的氛围,国王本人风流成性,且拥有众多情人。他手下的廷臣如罗彻斯特伯爵等贵族追逐异性的行为也介于强奸与诱奸之间。梁实秋认为:“国王尽管荒唐,却颇受大众的爱戴,主要的缘故是此前清教徒主政的时期,对人民生活方式控制太严,宗教的气氛太浓,因此查理所带来的轻佻的作风形成一种反动,正适合一般人的要求。”[4]306查理二世显然不是一位可堪大任的君主,复辟时期的英国亦是一个王纲解纽、法理制度和人伦关系完全混乱不成体统的特殊国家。因此,宫廷的放荡也影响了英国的世俗文化,在社会上造成轻浮的氛围。《风尘女》虽然以意大利为背景,但反映的却是英国的现实。加利亚德始终为自己放荡不羁的行为辩护。他的伊壁鸠鲁主义式话语随处可见。当菲尔默劝说他“为满足情欲追逐女性是危险愚蠢的行为”,他反而振振有词地说:“我还太年轻,搞不懂你说的那些大道理。等到有一天你从翩翩少年变成老朽,对着妻子衰老的容颜再忏悔也不迟,那个时候你就明白了什么是花开堪折直须折。”[1]96加利亚德与菲尔默是一对性别伦理观完全相反的人物:菲尔默赞成的是合法婚姻内的愉悦,而加利亚德则大肆鼓吹开放的两性行为。
戏剧作为文学类型的典型特征在于其表演性和现场性,加利亚德之所以能够毫无忌惮地在舞台上宣示男性在欲望上的放纵与彼时放荡的社会风气密不可分。复辟时期伦敦剧场内的观众与戏剧黄金时代的观众构成有着巨大差别。何其莘认为:“在复辟时期观众的眼里,剧场并非艺术的殿堂,只不过是他(她)们聚会的一个场所,舞台上的演出也只不过是一种满足感官需求的消遣。剧作家经常抱怨观众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表演和台词上面。纳撒尼尔·李在为他的悲剧《索福尼斯巴》收场白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剧场中观众的表现,‘前半场他们在喧嚷吵闹中度过,后半场他们睡醒后把全剧骂得一无是处’。”[5]232试想一下,当剧场里的观众不是在睡觉,就是在忙着吊膀子调情,如此趣味低下的观众怎么可能对严肃庄重的戏剧感兴趣呢?如果说加利亚德是性享乐主义者的代表,那么清教徒提克泰克斯特、布封则是带着面具追逐女性的伪君子。特别是牧师提克泰克斯特,此人虽然是布封的精神导师,但却好色成性。他垂涎于希尔维安娜的美色,还要装作正人君子,不愿自己所谓的名声冒任何风险,绝类莫里哀笔下的达尔杜弗。理发师佩德罗给他拉皮条,他一方面心猿意马,另一方面又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竟然恬不知耻地说:“既然这些妓女拥有从业证书,那么通奸就是合法的,合法的就是无罪的。”[1]100后来提克泰克斯特在黑暗中与同样好色的加利亚德亲吻拥抱,因此受到了观众的嘲笑。
《风尘女》中尤其能体现复辟戏剧性别话语狂欢特征的是女性独立反叛思想的表达。狂欢化是巴赫金文艺美学的核心概念,最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中被提出。巴赫金认为:“在狂欢节广场上形成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有的特殊类型的交往。在此形成了广场语言和广场姿态的特殊形式,一种坦率和自由,不承认交往者之间的任何距离。”[6]12《风尘女》中的女性藉由身份的伪装,只有隐姓埋名采取“狂欢化”的形式,才能更加自由地表达对父权社会的反抗。玛赛拉与柯妮莉亚是反叛男权世界的先锋。一开始玛赛拉表现得较为懦弱,她劝柯妮莉亚考虑一下整个世界都会把她们当作敌人的后果。柯妮莉亚则痛斥这是一个该死的邪恶社会,她出主意说只有伪装成妓女才能自由恋爱。为了爱情,她们必须带上妓女的面具。因为在这个荒谬的时代,妓女拥有比宗教更多的信徒。玛赛拉和柯妮莉亚姐妹对父权社会的反抗犹如一部女性的“成长史”,当两人漫步在罗马的街道上,面对着花园、喷泉和一丝不挂的雕塑商量获得爱情的对策时,此时一方面玛赛拉要勇敢主动地向菲尔默表达爱情,另一方面她又害怕这种大胆的举动为保守专制的社会所不容。柯妮莉亚比玛赛拉更具反抗意识,她说:“三从四德是多么巧妙的陷阱。我遵守誓言,为了家族的名誉唯命是从。他们要我嫁给一个残疾人,一个坏心眼的家伙,不然就是大逆不道。凭什么我就不能自己选择一个风流倜傥的如意郎君?”[1]110假扮为妓女的柯妮莉亚希望自由恋爱,在爱情战场上本来是猎手的男性在她面前反而变成了猎物。男女两性作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地位也因此实现了逆转。卢克莉西亚的反叛更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她要在和朱利奥的包办婚姻举行之前完成一次自由的恋爱之旅,即追求英俊的加利亚德。卢克莉西亚是一位爱情中心主义者。她本能地对无爱婚姻充满厌恶,于是以婚前出轨的极端方式反叛哥哥奥克塔威。为了与花花公子加利亚德偷情,她一面假扮成风度翩翩的伯爵,一面伪装成妓女,并且乐此不疲。卢克莉西亚主动勾引加利亚德的理由更接近男性追逐女性的行为动机。她在和仆人西尔维奥的谈话中直截了当地承认:“现在我已经和加利亚德是朋友了,但朋友和男欢女爱相差太大了,而今只有假扮妓女才能进一步享受恋情。当我的心上人拉着我的胳膊,将我紧紧拥抱,靠近他坚实的胸膛,亲吻我的脸颊,将我称作他的小美人,那时他一定会惊奇这样一位美艳少女怎么会和男人一样勇敢,而且又如此年轻。”[1]116可见,此时的卢克莉西亚已经沉浸在和加利亚德的偷情想象中,在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之后,她赶紧打住。卢克莉西亚充满性话语的独白是剧中女性话语狂欢化宣泄的高潮。巴赫金认为:“狂欢的堕落并不等同于绝对的破坏,而是进入再创造的低级阶段,为新生孕育力量。”[6]45贝恩在《风尘女》中表现的狂欢化精神也体现了女性对传统性别和阶级统治的反叛。
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标志着英国封建制度的崩坏。克伦威尔依靠强权建立了共和国体制,在欧洲大陆使英国获得了尊严,被封为护国公。但是共和政体对于保守的英国人民来说是一件新鲜事物,国家的基础完全建立在领袖的个人威望之上。王政复辟后的查理二世依靠怀柔政策和投靠法皇维持着表面上的君主统治。复辟时期的英国在政治上、宗教上已经失去了中心,但是这样一个秩序崩坏、王纲解纽的乱世,恰好为英国女性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表达女性思想的舞台。《风尘女》中的女性之所以能够挣脱父权话语的锁链,在舞台上宣扬女性的主张,与众声喧哗的复辟时期文化语境密不可分。
三、走向折衷:性别伦理妥协下的风俗喜剧
复辟时期的思想家霍布斯认为:“人类各行其是的作法既意味着自由,同时也意味着不自由。自由的一面体现在个人可以采取必要手段追求幸福;不自由的方面则体现在人们在追求自由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他人的自由。内战带来的混乱和失序导致手足相残,结果破坏了群体的幸福生活。道德律令固然存在,但当人们面临生命威胁之时很容易被合情合理地突破,所以人的自然状态无非是一系列无休止的争斗。”[7]59男女之间以性为战场的斗争也是如此。父权制社会因为男性权利占绝对优势实现了以男权为中心的稳定社会结构。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面对性话题不仅藏着掖着,而且以不近女色作为高尚品德的象征。到了封建意识形态受到怀疑的复辟时期,男女之间的对抗无论在婚姻还是在爱情方面,都需要依靠性别伦理的折衷主义来解决。
为了调和性别冲突,贝恩夫人特意在《风尘女》中塑造了一位理想化的男性菲尔默。菲尔默自始至终忠于玛赛拉的爱情,与剧中其他放荡的贵族男子形成了鲜明对比。他遇到伪装成妓女的玛赛拉,不仅极力压制自己的情欲,更要求其他男性也要遵守严格的贞洁观。菲尔默追求的是和宗教伦理一致的纯洁爱情,不像加利亚德这一类登徒子那样只是在女性身上猎取皮肉之乐。面对玛赛拉的爱情,菲尔默表现出如女子一样的无力感。他无法控制局势的发展,也拿不定主意。在加利亚德的怂恿下,他接受了尤菲米亚的约会,结果险些失去了玛赛拉的爱情。菲尔默承认男人的天性在情欲面前如此脆弱,导致他变成了俗世中的男人。[1]127换句话说,菲尔默认为自己从前过于纯洁的生活方式是“非男性”的。菲尔默的女性气质还体现在他心思细密、多愁善感的性格上。他称玛赛拉是“亮闪闪的可爱造物”,结果让加利亚德直呼:“娘里娘气的真让人受不了。”[1]127最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菲尔默与尤菲米亚的约会中,当尤菲米亚穿着暴露地出现在情人面前时,菲尔默向她表白自己只能在梦中思念玛赛拉。尤菲米亚因此讥笑菲尔默:“真实亦不过是幻梦。爱情的羽翼鼓动起来的一丝微风也足以使之毁灭。无论激情似火还是爱意缠绵,醒来都是一场空。俗话说,女追男,隔层纱,稍有姿色的女人就足以把在热恋中昏睡的男人摇醒。”[1]142玛赛拉伤心的是像菲尔默一样忠贞的男人最终也抵制不住诱惑而背叛爱情。当菲尔默教训尤菲米亚:“你年纪轻轻不该堕入风尘。难道你一直都如此淫邪?尽管你已犯罪,但天堂的大门依然朝你打开,因为你是如此美丽。”[1]142此时的菲尔默尚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玛赛拉,他自以为站在道德的一面,而做妓女的尤菲米亚是“反道德”的。玛赛拉站在自己的角度自然认为菲尔默赴妓女的约会更加违反道德。戏剧矛盾因此产生,只有舞台下的观众处于全知视角,了解双方冲突的缘由。假扮成妓女的玛赛拉迁怒于菲尔默的不忠,故意说了许多偏激的话刺激对方。菲尔默与玛赛拉的话语对抗充满混杂性。男性与女性的价值伦理在戏剧舞台上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而这种价值观的反转,无疑是对处于正面冲突中的性别话语进行调适进而寻找新的两性和谐的一种方式。菲尔默与加利亚德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爱情婚姻观,一种是世俗淫荡的,另外一种则充满宗教的崇高,而大多数男性都在两个极端之间徘徊不定。
男主人公加利亚德是一个说话粗俗的花花公子,在他眼中女人只是被征服的对象而已,他整天想着如何利用金钱和更多的女人上床。菲尔默对爱情的专一态度以及对婚姻的神圣看法反而不时受到他的嘲笑。在厌婚主义者加利亚德看来,婚姻简直就是自由生活的坟墓。女扮男装的卢克莉西亚声称要睡遍罗马城的女人,结果大获加利亚德的赞扬。当柯妮莉亚公布自己的身份不是妓女而是一位出身高贵的淑女并愿意嫁给他时,加利亚德几近疯狂,质问她为何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波伏娃认为:“婚姻对双方都既是一种负担又是一种利益。但是在男女两性的处境中并不存在对称性。对女孩子,婚姻是结合于社会的唯一手段,如果没有人想娶她们,她们简直就成了废品。”[8]489加利亚德惧怕婚姻乃是因为基督教规定不得随意离婚,而且必须实行一夫一妻制。柯妮莉亚在与加利亚德结婚之前对婚姻的看法异常清醒:“我明白让您这样一位公子哥儿收心是多么困难,那我只能尽量做一个像情人一样的妻子。大伙儿都明白,女人在婚姻市场上并没有多少退路。结婚也可能付出昂贵的代价,结果一个有了外遇,另一个在幽会偷情。这样的婚还结什么呢?”[1]180即使是拥有智慧和理性的柯妮莉亚也要在婚姻中回归社会,特别是对加利亚德这样一个浪荡子进行改造,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任务。两人之间的对抗贯穿剧情始终。柯妮莉亚反对加利亚德的对白堪称一席女性主义宣言:“你以为我是傻瓜吗?你觉得我是水性杨花的女人,然后去找一个自作精明的情人?有些男人嘴巴上彬彬有礼,结果在外面惹是生非添的乱子比一百个傻瓜还要多。男人可以肆无忌惮地追逐女性,得之则吹嘘,弃之如敝屣。世人还要责备女人没有智慧留住男人,实际上是因为她不够愚蠢才被情人抛弃,所以女人要想和你们这些坏透的聪明男人结合,先得主动放弃自由和思考的权利。谁更有智慧不也是成者王、败者寇的事情么?”[1]152柯妮莉亚的一番论述让加利亚德大为佩服,赞扬她深得马基雅维利主义之精髓。
朱利奥的放荡行为与加利亚德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卢克莉西亚与朱利奥算是一对同床异梦的夫妻,他们的偷情行动却讽刺性地实现了性别上的平等,同时也表明妓女和妻子其实在某些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朱利奥叔侄与奥克塔威是父权社会的坚定捍卫者。在得知姐妹俩离家出走以后,叔叔称侄女是“女人中的害虫”,哥哥称妹妹是“该诅咒的女人”,在他们眼中畸形残疾的奥克塔威反而成了绅士般的贵族。朱利奥称自己的妹妹是家族的财富也表明他在内心深处认同妹妹是“物”,而非“人”。女人的行为只要稍微偏离男权体系,就被视作大逆不道,有辱门庭,而男性则可以寻花问柳,朝三暮四,最后还要说是女性脆弱的天性导致男人的堕落。
贝恩为了呈现出英国在性别建构与规训上日趋折衷的趋势,塑造了多位具有男性气质的女性形象。卢克莉西亚在戏中就是一位颇具“男子气概”的典型女性。她也因此遭遇了双重身份矛盾。卢克莉西亚在伪装成伯爵时将自己的“男性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她要仆人西尔维奥忘记其女性阴柔的一面,并且骄傲地向对方炫耀自己的英姿:“看我体型矫健、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这气质,这排场,难道不是男人中的男人?我变成了王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1]112卢克莉西亚的性别转换证明了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并不是那么大,只需要把装束变换一下,她同样可以打败男人,赢得女性的芳心。但是性别发生反转带给她的变化只是暂时打破了性别界限,她始终无法找到内心自我,最后只好委身于朱利奥,依赖回归传统婚姻重返社会。
四、结语
德雷克·休斯认为:“《风尘女》表明贝恩夫人已经注意到了天主教谋杀案之后伦敦戏剧舞台的变化,在经历了上一个年度惨淡的戏剧市场后,她是在此期间唯一有喜剧上演的剧作家,这更加奠定了其在复辟时期戏剧中的重要地位。《风尘女》一剧格调轻快,但在主题上却反映了作者在性别层面更加深刻的思考。剧本尽管揭示了妓女与妻子在受压制地位上的一致性,但反映的问题也只是女性可见的表面。”[9]114—115《风尘女》是一部典型的“风俗喜剧”,紧张的性别冲突一直延续到最后一幕,但最终以男性的妥协获得了圆满的结局。奥克塔威立下誓言再也不会相信朝三暮四的女性,并放弃与玛赛拉的婚约,从此云游四方,远离红尘。于是玛赛拉得以合法地成为菲尔默的妻子。浪荡子加利亚德则坦言自己憧憬的生活场景是“晚上与情妇欢度良宵,早晨醒来却发现是憨妻在侧”。[1]179他终于在菲尔默的鼓励下同意与柯妮莉亚结婚,同时柯妮莉亚也做出了让步,两人在相互妥协的条件下走进婚姻殿堂。花花公子朱利奥与卢克莉西亚经历了种种误会,两人尽管在婚前都有越轨之念,但终究未铸成大错而染上道德污点。
《风尘女》中的戏剧矛盾中心尽管是包办婚姻和父权制度下男性对女性的身体控制,但贯穿重要人物始终的冲突根源来自于性别差异。剧中的女性人物屡次使用“我们女性”“你们男性”指称性别群体,表明人物因为性别不同已经自觉地将对方划分为“他者”。女性一旦僭越了性别伦理,《风尘女》中的男性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顾亲情关系对女性进行规训与惩罚。弗里德曼认为:“性别不同于主体性的其他构成成分,它致力于考察性别的语言过程和效果,凸显身体和欲望在塑造语言和被语言塑造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二元对立,这些问题在那些无视性别因素的诗学中便经常被忽视。”[10]41复辟时期戏剧表现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英国大众在理性与情感、权威与反叛、社会与个人冲突中的焦虑与对抗。贝恩戏剧中的女性反叛在封建秩序崩坏的历史机遇下发出了超越时代的声音,其思想之激进、行动之开放、语言之犀利让维多利亚时代保守的女性叹为观止。尽管《风尘女》中女性争取自由的方式都异常苦涩地要从假扮妓女或者男人开始。玛赛拉被动地接受扮演妓女,柯妮莉亚要在保持身体贞洁的条件下才能在婚姻市场上赢得主动,即便是泼辣的卢克莉西亚见到心上人脱口而出的仍然是“我的征服者”,这足以从侧面反映出女性认同男女之间主奴关系的影响之深。近代早期的英国女性要想有所作为,首先要突破男权社会对女性的限制。《风尘女》中的女性已经意识到争取女权首先要从掌控自己的婚姻开始。她们在性别对抗中有勇有谋,甚至拔剑与男性决斗,捍卫自己的权利,最终迫使男人妥协。三位女主人公以假扮妓女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的行动充满了荒诞,但毕竟走出了实现女性独立的第一步,亦体现了阿芙拉·贝恩思想的进步性,这或许正是阿芙拉·贝恩的戏剧尘封百年后,经过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推介重新获得西方学界热烈关注的原因。
[1] Aphra Behn. Oxford World's Classics, Jane Spencer,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2] John Stoltenberg. Refusing to Be a Man: Essays on Sex and Justice. London: UCL Press, 1989.
[3] 陈雷.文森修公爵的为政之道:《一报还一报》中的道德哲学[J].外国文学评论,2010,(4).
[4] 梁实秋.英国文学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5] 何其莘.英国戏剧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9.
[6] 巴赫金全集[M].钱中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7] David Scott Kastan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 V.3.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9.
[8]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4.
[9] Derek Hughes.The Theatre of Aphra Behn. New York: Palgrave. 2001.
[10] (美)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图绘:女性主义与文化交往地理学[M].陈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