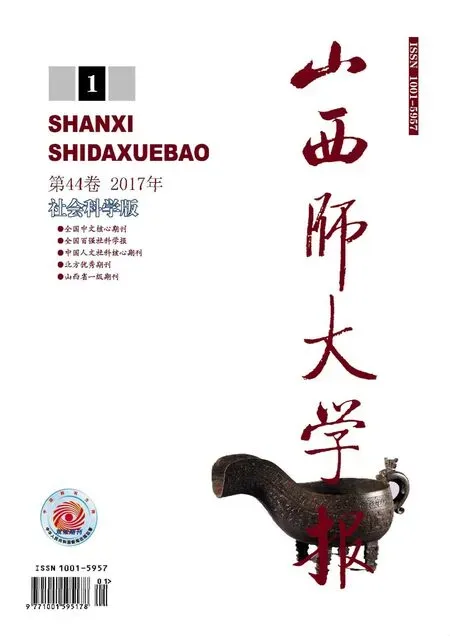图文关系的审美互动形态分析
——以古今《红楼梦》图文本为例
2017-04-13高雁,卢兴
高 雁,卢 兴
(1.辽宁大学 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0004;2.沈阳体育学院 体育人文学院,沈阳 110102)
国内现有的图文关系研究多是从符号性质出发对图文二者进行比较,也有不少对图文各自功能地位所做的文化阐释,然而这些角度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地说明图文关系,或者说只是图文外部关系的研究。而且很多研究将静态图文关系(即静止的图像和文字语言的关系)与动态图文关系(动态影像与文字语言的关系)混为一谈,两个根本不同的研究内容未作区分,这很难深入到问题的本质。本文的研究是对静态图文关系的研究,从二者内部入手,以《红楼梦》为例,把图像和文学文本之间形象意识之间的互动当作研究对象,把图像艺术观念的变化和图像的接受创作都纳入到图文关系问题考虑的范围内,力求深入到图文肌理的关系研究。选取《红楼梦》图文本为例来说明图文关系审美形态的变化,是因为依据《红楼梦》小说内容所绘图像数量众多,而且人物形象和绘制方法各时期差异巨大,能够很好地说明关系变化这一问题。
根据《红楼梦》小说绘制的图像有如下几种形式:其一,文中图,又可分文前图和章前图,如程甲本配24幅图,翰苑楼本64幅人物图,这是文前图。万有文库本《增评补图石头记》241幅则是章回图。其二,单独图册,如改琦《红楼梦图咏》50幅,每幅配一到三首诗咏不等,王墀《增刻红楼梦图咏》120幅人物像,一画一诗等。其三,小说外的图像衍生品,如月份牌、烟标、火花等。不同的图像形式和图像距离文字的位置会造成阅读的迟缓与绵延,而艺术家对前文本的理解程度的差异、对图文功能理解的差异、对内容拣选并赋形表现能力的差异,都会使图文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通过对众多《红楼梦》图文本的梳理和比较,《红楼梦》的图文关系审美表现形态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展示维度的图文关系——这是一种趋向零度、带有复述性质的关系;第二种是阐释维度的图文关系——这是一种解释或翻译的关系;第三种是隐喻维度的图文关系——这呈现的是一种对话关系。
一、展示维度的图文关系
展示是事物的陈列和视觉在平面上不歇息的运动,热奈特称展示是“最大的信息量和最少信息提供者的介入”[1]111,这种特征与展示维度图文关系的描述非常近似。展示维度的图文关系表现为图像对文字内容中场景的复现,这里的场景不仅指一个场面、物体的摹画,还包括物品间的排列结构,也包括某一场景中的人物形象和人物顺序,这种复现是趋向零度的。所谓趋向零度是说图像向着文字靠近,用绘画还原文字,用一种符号去模仿另一种符号传递意义,而不随意对图像要素做主观拼合缝补,只是将抽象的符号意义形象化。从一般意义上说,趋向零度的再现是很难实现的,像摄影艺术也并非是完全对现实的照抄照搬,因为摄影艺术有其独特的观察视角和选择态度,使得这门艺术看似再现却总是有别于现实。甚至在今天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模仿也带有了创造的味道和性质,因为中间隔着一个模仿者,这就使模仿结果总会打上模仿者的烙印,不会是模仿对象本身。如果涉及到两种表达方式的模仿,则二者间就不仅是横亘着模仿者,还横亘着表现方式和表现符号自身的性质和特点。但是相较其他图文关系,展示维度的图像和小说确实有着最为近似的表现。
以《红楼梦》图像为例,展示维度的图文关系,大多反映在《红楼梦》插图上。因为图像和文字的距离近,总是免不了会被用“似与不似”的标准和文字中的内容进行一番比较。特别是场景和场景之中器物、人物形象,最易被展示型的图像把握(因为对图像而言连续的动作和内心感受是比较难以描绘的,不适于表现的则会被舍弃)。如上世纪30年代万有文库本《增评补图石头记》的大观园一图就体现了图像对小说文字的展示。小说第十七回写道:“只见正门五间,上面筒瓦泥鳅脊,那门栏窗槅,皆是细雕新鲜花样,并无朱粉涂饰,一色水磨群墙,下面白石台矶,凿成西番草花样。左右一望,皆雪白粉墙,下面虎皮石,随势砌去,果然不落富丽俗套。……开门进去。之间一带翠嶂挡在面前。”[2]188图像上,无论是“正门五间”,还是一进门看到的翠嶂,甚至院落亭台、山石楼阁的经营位置也是一如文字描述,线条细密、绚丽、丰腴,精雕细镂,很好地诠释了小说所说的“富丽不落俗套”。况且这种把小说中线性文字描绘的场景一一直接进行视觉展开,又体现了皇家贵族的威仪和恢宏震撼的气势。此外,人们按文于图中寻找各处又颇得一种乐趣。试想图像如果不是对小说做了精到展示,而是按照一般山水园林的意境味道进行描绘,虽可得曲径通幽之美,却又取消了“展示”所带来了平铺的气势与趣味。像民国时期的石印《全图增评金玉缘》在内容上的减省, “正门五间”变成了“三间”,“一带翠嶂”也被切成了几个假山石,将大观园一进门所展示出的恢宏之感削弱了许多。看过小说都知道,大观园的占地面积一定不小,《增》的大观园全图确实画出了这种味道,而《全》的只能是依靠读者自己想象。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从程甲本开始的那种对木刻版画精细展示的追求到了民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审美疲劳,也说明民国时期图像质量的下降。
虽然展示型的图文关系具有优势,但其缺点也十分明显,它一方面会束缚人们对于文字内容的想象,固化人们对于形象的感知觉与想象能力;另一方面图像对文字的描绘展示越详尽精到越会如阿兰5罗布-格里耶认为的那样:“形式和体积上的精确、细巧和细节越是积累,物体就越是丢失它的深度。”[3]149过度重视细节与场景的摹画会让观看替代文字阅读带来的回响,使观者体验陷落在细节的探寻之中,从而消解了作为读者一维该有的主体性,沦为观赏活动中被动的客体。每次读到《红楼梦》的文字内容,绘画中的形象就会浮现于脑海,文学中那种“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林黛玉”的形象特殊性也就消失了。同时,精到展示也导致图像绘画本体性的失落,只是沦为文学的点缀和装饰。再有,因为形象的易于理解,使得视觉不受阻滞、一目了然,不再使读者获得视觉惊奇,也减少了艺术创造带来的丰富的审美体验。
二、阐释维度的图文关系
阐释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姚斯在《文学与阐释学》中说:“理解意味着把某些东西当做一种答案来理解。”[4]411姚斯把理解看做阐释的第一层级,并以此来说明理解或者阐释本身类似对对象做出的回答,包含了特殊性,包含了阐释者对阐释对象特定的观点意图和倾向,不同的阐释者对问题应有不同看法。胡经之先生在说明阐释内涵的时候也说:“按照本文的意向性,像它所期待着兑现自己的要求那样,把自己的生活积累灌注到本文的基本构架中,从而使解释变成再认识,再创造。”[5]38这里的“自己”也是强调了阐释的特殊性,阐释是属于个体的活动,而且这种活动是创作性的,不该重复。
阐释维度的图文关系也具有阐释的内涵特性,且比文学作品的阐释更加复杂一些。根据艾伯拉姆斯的观点,文学活动由四个要素或环节构成: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其中作品反映了作者对世界的理解,读者则对作者和世界进行理解,不同的作者和读者对世界的理解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就阐释维度的图文而言,文学活动的四要素还应加上图像环节。图像是对文学作品的再阐释,又与文学作品共同被读者接受。而且图文关系中,作者和读者的内涵也该是双重的,作者既指向文学作者,也指向图像的创作者,特别是后者,不同的图像创作者所理解的世界是不同的,其所创造的作品所构成的世界也是不同的,其所隐含在作品中的唤起读者感受的要素应该也不相同。读者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既是文学阅读者也是图像观赏者。在观看中,文学形象、叙事内容和图像形象、形式相互交汇碰撞,彼此影响。
阐释维度的《红楼梦》图文关系中,图像把《红楼梦》小说文本当作了一个问题,它不想复述它,而是试图以自身的观点和视角去回答、去解释。接受者透过自己之前的审美累积完型了答案,并使用自己的言语表述逻辑和叙述视角将之明确表达出来。比起展示维度图文关系中图像的亦步亦趋反映小说,这里可以看到明显的“人为加工”痕迹,无论是图像的创作者,还是图像的接受者,都不再是失于主观意图的跟从,不再任由图像或小说意义的引领与摆布,而是随自我的目光游览。图像也有意在画面布局上打破前文本的内容和顺序,使原来的图像不必调整步调适应文字,而是适当调动文字配合图像表现本身,使之更适于图像符号本性,符合一般的理解。例如《红楼梦》中对于第三回中“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一节的描述,文本内容为:“黛玉听了,方洒泪拜别,随了奶娘及荣府几个老妇人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只船,带两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2]26文中记载黛玉随行仅几人而已,但清代孙温的绘全本《红楼梦》中,画面里随行的人数量近三十,显示出图像和小说的差异,体现了图像作者的观点。在作者生活的时代——清代中期,等级制度严格,像林如海这样的官员和荣国府那样的地位,小姐林黛玉出行仅几人随从是很寒酸的。尽管画面无法容纳更多的人物,我们也能从图像本身看出排场和气度,蓬船比较豪华,随行人员年龄身份不同,显然各有职责。这些显然是图像绘制者的理解。另一种能体现图文阐释关系的例子是在人物顺序的安排以及图像内容的选取上。如张惠的《程甲本版画构图、寓意与其他〈红楼梦〉版画之比较》中指出:程甲本的图像在内容的选择上反映了贾府的现实状况,也体现了一种道德教化观点。如不同于传统审美的钗、黛、湘三幅,没有选择从传统的审美着眼点表现“宝钗扑蝶”“黛玉葬花”和“湘云醉卧”,而是“宝钗绣鸳鸯”“黛玉调鹦鹉”和“湘、翠论阴阳”。作者认为这更靠近古代封建社会对妇女“德容言功”的要求。而且在人物图像的顺序安排上也显示了这一观点,作者认为《十二钗》图谱的人物座次排名上就体现了“名分”观点以合于“礼”的看法。[6]
上述例子意在说明阐释维度图文关系中图像对小说的加工理解,它们自发还原与补足小说的内容。这与展示维度图像近乎失去自我,亦步亦趋地靠拢小说的那种图文关系相比,阐释维度的图文关系则显示了更多的“改编”观念,图像并不臣服文字,而是有特殊的理解和处理方式。
阐释型图文关系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从姚斯把阐释界定为“一种具体化了的对一个问题的答案”[4]411已经表明阐释的具体化和唯一性,也就是说当一种阐释出现,它必须是明确提出的,而且很有可能被固定下来,成为其他阐释的限制,从而减少阐释对象自身存在的那种被无尽阐释的可能性和魅力。特别是一种图像阐释影响力十分巨大时,它越详尽、越高级,也就越会成为范式受到推崇。如清代改琦的《红楼梦图咏》作为对小说阐释的图像,影响非常大。“这套《红楼梦》插图,成为清代最富于文人气息的版本,得到当时士人的欢迎,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并对后来的《红楼梦》绘画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7]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后世《红楼梦》图像创作,从服饰、形象和审美气韵都对改琦的图像有所借鉴。如服装上,改琦没有沿用一般的清代服饰,而是使人物着明清戏服改良的服饰,简洁又大气;男子形象没有清代男子标志性的长发辫,而是明代男性形象,尤其在今天的影视作品中我们还能看到改琦的这种影响。
虽然比起展示维度的图文关系,阐释维度的图像显示出了更大的对前文本——小说理解的自由,但是图像总是预留一些与文字前文本的一致的信息使图像的解读与阐释紧密缠绕,图像作为绘画艺术的特殊性还是受困于插图这一身份。在这一点上,隐喻维度的图文关系所提供的可以诱发想象张力的意象在自由度上则又上了一个台阶。此类图文关系中文字对图像的限定越来越松懈,图像提供的形象和要素直接使接受者跌入理解的浩海中,意义漂浮于图像之上任由接受者肆意拨动。
三、隐喻维度的图文关系
通过众多《红楼梦》图文本的比较可以发现,图文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发展过程:图像试图挣脱语言,想获得更多言说的可能;但又不断靠近语言以获得深度。同时图像作为绘画,其自身的艺术性也经历了从隐到显,从被动到自觉的过程。图文关系中绘画本体性的展露与西方现代美术不断彰显自身的本体语言——形式,强调形式本身的审美价值和意味是分不开的。它使图文二者由不平等的主从关系转向图文的平等对话,图像也由文学的阐释者逐渐转变为一个开放体,让观者走进来,被它吸引,它不提供意义,类似英伽登的“图式观相层”*英伽登在其《文学艺术作品》中提出,文学分为四个层次:语音层、意义层、再现层和图式观相层。他认为纯粹的文学作品只是一个构架,是在各方面都是图式化的构架。它包含有空白、未确定的和图式化方面。这里的构架指的就是观相,是作品的呈现方式,不同读者的观相现实是不同的,所以文学作品呈现出一种敞开的状态,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解读。,只是骨架、框架、一种图式,其中充满了许多“未定点”需要观者去补充。“就好像提纲挈领的简笔画,刺激并规范着读者的想象。”[8]图像从意义的切实附着体变成了“观象层”,对读者而言是充满了未定点的图式结构,读者已经不能顺着图像提供的能指链条走回到原来的文学文本那里,也无法像阐释维度图文关系下的图像那般提供具体、明晰的阐释。但这种未定仍然是有条件的,漂浮着的所指仍然受到前文本的拨动和规范,不会造成理解的太大偏误。
这种图文关系可称之为隐喻关系。修辞学当中,隐喻是一种暗喻,本体和喻词都不出现,以部分指代整体,喻体本体明显是不对称的,这使得喻体必须包含许多未定点,与图式观象层的未定点都具有不确定性。当代虹鸣的《红楼梦》图像作品很好地体现了隐喻型图文关系。从种类来说,虹鸣所绘图像不是插图,而是专门的绘画,它摆脱了插图之于小说的从属地位,遵从作为独立艺术门类的发展规律及其表现的特殊性。其次,它们与小说的关系不符合传统对图文关系的看法,这种图文关系是隐性的,属于小说文本缺席的图像,作者只保留了前文本中关于人物的特征符号,如《黛玉》一幅采用的是立体主义方式,对人物的处理是印象式和碎片化的,视觉因素在空间和时间上形成一种重叠。它颠覆了传统的《红楼梦》人物像。从清代开始,那种瘦弱、幽怨的女子形象在这里完全找不到踪迹,甚至人物连基本的轮廓也没有,剩下的只有人物形象的特征符号规定着内容。“眼泪”“竹子”“珠帘”是唯一对绘画进行意义阅读与内容判断的线索,它们连缀成为判断人物的关键词。因为分解和碎片的隐喻使《红楼梦》图像不是向着小说文本还原,而是独立地将审美经验传递出来,使绘画看起来逐渐向思、向语言靠拢。“破碎的外观,凌乱的色彩,零散的构图,消解了形与破碎的形象。对分解的一贯强调不同寻常的牢固。艺术家之所以要打碎他的材料,其目的在于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关联来重构。”[9]218这种碎片的拼合重构使文本和绘画之间留出了大量的空白,像一个没有边界也没有中心的场域,让观看画面的读者调动大量的业已形成的认知和经验去补足,让已知经验和暗示碎片交汇融合产出新的内容。这种重构给予了观者更大的自由,也使图像的观看成为一个历时的过程。
因观者的不同,对未定点的补充也有巨大差异。根据戴维森的隐喻理论可知,隐喻并不是二维的关系,而是一种三角关系,即涉及说者、听者与世界,在隐喻维度的图文关系中,观者作为图文之外的存在,与图文对话,也是图像、观者(世界)的对话,隐喻的主体就是图像和观者的对话。图像带着前文本出场,观者带着世界出场,世界包含观者的小说阅读体验,也包含前人理解模式的出场。这场对话在图文构织的空间中展开,喻体向本体运动又超越本体,意义也在竞争和辩证中凸显。
在众多图文关系中,隐喻维度的图文关系并不是很多,以《红楼梦》为例,在其成书之后所形成的图像集群构成一个强大的世界,这个世界俨然已经不是一个任凭自己对小说文本的理解就可以随意运用形象符号组织的图像世界,它必须符合多数人对《红楼梦》表现形态的认可以及接受规律,过度逾越了《红楼梦》图像传统表现形态的都可能会被认为是创作失败,得到差评。这种失败不仅是形式上的失败,还是理解上的失败。因此隐喻维度上《红楼梦》的图文关系相比其他两种图文关系数量较少,即使如此,它又确实与前两种图文关系不同,显示出一种变化,说明了图文关系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
综上,对图文关系的分析是比较复杂的,可以有多种划分依据和分类方法,如果只归结在二者的“疏离”或“互仿”关系中是不能把现代图文关系互动变化阐述清楚的,本文借助文学阐释和隐喻观点希望会给图文互动关系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此外,这种专注静态图文关系的研究也有效地避免了动态图文关系研究对图文本质问题的遮蔽,使图文关系研究回到图文本身。
[1]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法)阿兰·罗布-格里耶.为了一种新小说[M].余中先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1.
[4] (德)姚斯.文学与阐释学[A],周宪编译,激进的美学锋芒[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 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 张惠.程甲本版画构图、寓意与其他《红楼梦》版画之比较[J].红楼梦学刊,2009,(3).
[7] 静轩.改琦:来自《红楼梦》时代的图像[J].红楼梦学刊,2006,(6).
[8] 吴子林.英伽登的文学作品结构理论新解[J].文艺理论,2012,(1).
[9] (美)凯瑟琳·库赫.分解:现代艺术的核心[A],周宪编译, 激进的美学锋芒[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