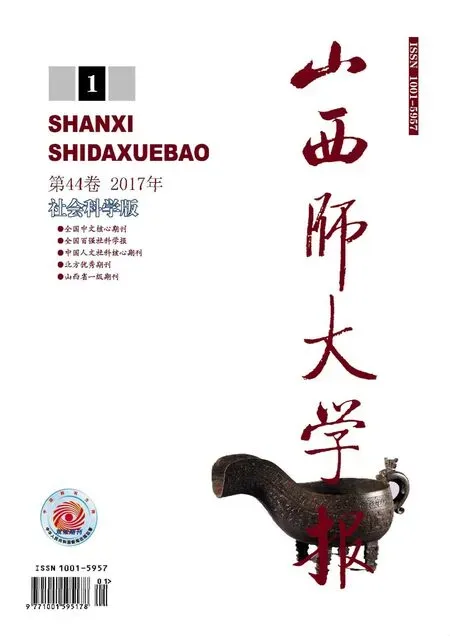传统社会中的村落神庙联盟与村际关系
2017-04-13姚春敏
姚春敏,刘 佳
(1.山西师范大学 戏曲文物研究所,山西 临汾 041004;2.山西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系,山西 晋城 048026)
传统社会中,除了行政统治中心四堵墙围绕的所谓省府、州县、城市外,大量存在的村落是其最重要的基层单位。因为远离政治统治中心,它们具有相对独立的组织结构,这些组织除了处理村落内部矛盾外,还可以与外界政权、利益集团或组织进行抗拒和协调,并因此逐渐形成村落与村落之间的关系网。当下学界以传统村落为中心的研究中,过多倚重对村落内部民俗和宗族发展的分析解释,这种孤立地观察乡村的模式,很难获得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完整理解。传统意义上的村落,无论坐落空间多么偏僻,村落集体性仪式呈现出怎样的精神自足特征,也必定会以周边村落为参照,其仪式细节的设计或调整也会经常与邻村的当下活动形成互动的态势。[1]因此,村落与村落之间的关系即村际关系亦成为了解传统乡村社会必不可少的窗口。关于村落之间的关系,目前学界有从信仰、婚姻、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进行解读。鉴于乡村社会的复杂多样,地域变化种类繁杂,加之传统社会中区域交往相对比较闭塞,故无论哪种单一的理论都难以成为解释村际关系的唯一模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家族、信仰还是经济、政治,传统村落都不可能仅依靠其中一种关系而稳定和巩固下来。依据数年的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本文试图从传统社会中村落之间神庙的联盟来管窥村际关系的发展及历史衍变。不妥之处,望同仁指正。
一、具有血缘关系的村落神庙联盟
具有血缘关系的神庙联盟指的是在传统乡村社会中,由不同村落之间的神庙主神具有父母与子女以及姐妹兄弟等血缘关系而结成的一种联盟。两村及两村以上村落的神庙以此关系结亲,以维持固定的巡境及走亲等仪式,甚至在灾害发生时开展联合祈雨等出行活动。此类血缘关系按照亲疏远近又可以分为父母与子女关系、姐妹关系以及甥舅关系等。
把主神排列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村落神庙联盟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结合形式。如,陕西蒲城县尧山圣母仪式圈里有十一村社轮流主持仪式的习俗。除尧山上所建灵应夫人祠外,以尧山为中心,周围十一村社还分布有各社的尧山庙, 碑文中一般称之为圣母行宫,或曰“行殿”“行祠”。上述尧山圣母庙会的十一村社神庙,根据民间传说原是圣母的十一个儿子,每个儿子轮值一年将圣母接回家中供养,这里的十一个儿子之间是兄弟关系,而与尧山圣母则为母子关系。再如,山西省太谷县东怀远村和徐沟县西怀远村,历来隔畔种地,和睦相处。传说有一年农历七月初一日,两村人共引河水浇地,捞出顺水漂来的木块,用之雕成女像一尊,名曰“圣母娘娘”,并各建圣母庙。从此两村结为秦晋之好,东怀远为圣母娘娘的娘家,西怀远为婆家,每年七月初一日,两村举行盛大的迎送圣母娘娘活动,第一年西怀远到东怀远迎亲,次年东怀远再从西怀远迎回,如此周而复始,虔诚信奉的人们向其求子祈福还愿降香。直至1936年香火仍很旺盛。[2]141—142
有些村落神庙结盟关系较为复杂,除了父母子女关系外,还夹杂着姑表亲戚关系,但核心仍是父母子女直系血亲关系。如山西垣曲岱嵋圣母,当地民众认为南北白鹅村为圣母的娘家,无恨村为圣母的舅舅家。双方的“神亲”关系在垣曲县南、北白鹅村、无恨村以及相邻的河南省渑池县西山底村、东关村之间形成。具体表现为河南渑池县西山底村每年农历三月十五会将岱嵋圣母像送回作为舅舅家的无恨村并于四月十五接回;南、北白鹅村会在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去渑池县东关村接岱嵋圣母,而七月十五东关村会去南、北白鹅村接回圣母。[3]2此类结盟在乡村社会中亦不在少数,外围关系网以血亲为主依次形成,对直系血亲联盟形成拱卫趋势。
另外,在民间村落中,姐妹关系也是村落主神联盟非常重要的形式。如山西省洪洞县的“接姑姑迎娘娘”活动,如今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的姑姑和娘娘即舜帝的两个妻子娥皇、女英姐妹。洪洞县的羊獬和历山就分别成为两位女神的娘家和婆家,羊獬人称呼她们为 “姑姑”,历山人称她们为 “娘娘”,两地结成联姻。每到农历三月初三这一天,洪洞县羊獬村民都会接“姑姑”回乡省亲,到了四月廿八尧王生日当天,历山人民又前来给尧王拜寿,将两位“娘娘”迎回去,于是渐渐形成了“三月三接姑姑送娘娘”的习俗。[4]126两姐妹结盟最为常见,但是也有三个甚至更多的姐妹神庙。如山西榆社的三姐妹神庙联盟,榆社的崇纂、榆社城、云簇等三地的奶奶庙,其庙会的时间分别是农历四月十四日、四月十八日、四月二十一日。传说这三个“奶奶”,原是三姐妹,因搭救百姓被妖魔害死。三姐妹死后多日,虽正值盛夏,面容姣好如初,即被百姓奉为神灵,并分别立庙祭祀。
村落神庙结盟中,除了亲近的父母子女及姐妹关系外,甥舅关系必不可少。如,青海省贵德县六月会是由两神相会仪式衍生出来的,在两神相会仪式当中,来自周屯的二郎神是来自刘屯文昌神的舅舅,所以,两神相会仪式又称为甥舅相会仪式。具体举办者为周屯、刘屯两村,神祇主角为周屯二郎庙的二郎神和刘屯文昌庙的文昌爷。[5]38山西省太谷县南郊与榆次市的德音相隔数十里,本来没有什么世俗交往,但相传南郊村的龙王爷原为德音村人,名叫焦疙瘩,其南郊村的外甥天旱之时给舅舅家洇西瓜地,在地里滚了滚干地就湿了; 另外,他还给周围村庄降下雨来。因此,他死后成了南郊村的龙王爷,称为焦爷爷,其灵验远近闻名,这一传说使德音与焦爷爷攀上了亲,该村遂与南郊结为以焦爷爷为共同敬奉对象的神亲。[6]
除了以上这些血缘关系外,在传统民间社会中,还存在着更为错综复杂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神庙联盟关系。比如,河北省安国县杨翟村、南章令村、北章令村、西章令村、子娄村、淤村,它们均是以金龙四大王为主神的村落,金龙四大王庙是村落宗教生活的核心。当地村民认为,杨翟村的金龙大王是杨翟本村人,姓翟。南章令村是金龙大王的姥姥家,而淤村是金龙大王的爷爷家,至于子娄村则为其姨家,北章令村和西章令村分别为金龙四大王的大哥、二哥。[7]这样,围绕着金龙四大王,出现了他姥姥、爷爷、姨姨以及兄弟等复杂关系。再如,山西省长治市长治县的唐王岭“十转赛”,即围绕着二仙奶奶的姥姥、娘家以及小姨、舅舅家等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构成了九个村落之间神庙的联姻,以此为由头,每年二仙奶妈定期要在不同的村落之间巡游。
二、非血缘关系的神庙联盟
非血缘关系的神庙联盟指通过婚姻、结拜、收养等方式组成亲属关系的村落神庙结盟。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主神之间的婚姻关系。婚姻关系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也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是传统社会中形成各种人际关系的重要载体,因此村落神庙之间也会因婚姻关系组成联盟。在这种以婚姻关系为纽带的神庙联盟中,以姑娘嫁龙王居多。如山西省榆次县后沟村的龙王之妻是龙田村的一位于姓女子,相传一次后沟龙王被请到龙田祈雨,该女子站在楼上观看,说要嫁给龙王,说罢坠楼而亡。村民都说“这是龙王爷娶上走了”,龙田村为她塑像,就是龙王娘娘,也供入后沟村的龙王殿内,从此两村结为神亲。[8]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清代山西泽州(今晋城市)普遍流传着一种“丑姑娘嫁龙王”的传说。如,民国十七年(1918年)辛壁村龙王殿碑刻《龙王殿金妆神像油画全殿碑》曾载,辛壁村冯姓丑姑娘嫁给二十里外的黑龙王并多次回乡行雨。*见民国十七年(1928年)《龙王殿金桩神像油画全殿碑》,现存于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大东沟镇辛壁村。同处泽州的沁水县交口村光绪九年(1883年)的《娘娘神语传来碑记》也载:本村张姓女子浣纱时突然失踪,后显灵托梦给外甥言自己已经嫁给了外村的黑龙王,自称黑龙娘娘。*见光绪九年(1883年)《娘娘神语传来碑记》,现存于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土沃乡交口村。此类本村丑姑娘嫁给他村龙王的村落神庙联盟在当地不胜枚举。丑姑姑嫁给龙王后,两村神庙正式联盟,定期举行互访。丑姑娘嫁龙王母题类同于远古时期河伯娶亲的牺牲祈雨,也契合了当地浇旱魃龙母、虐待丑妇的传统,也许是这两类传说的结合变异。
除了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外,主神之间结拜形成模拟血亲也是联盟的一种方式。如,山西省长治北石槽村庙宇正殿内供奉两座三嵕神像,一座端坐正中,摆在台子上,另一座在神像正前方,端坐在椅子上,前方的神像是可以抬起来的。距此村大约三里地的五马村内有一座关公庙,两村人认为关公与三嵕神为兄弟。每年六月初六北石槽村祭祀集会时五马村会将关公神像抬至庙中,七月初五五马村祭祀关公时北石槽村会将三嵕神像抬到五马村关帝庙中,酬神谢戏的时间有多长,神像就停留多久,双方在抬神像时对方村落都会派人迎接,以确保神像安全抵达。[9]山西省太谷县的郭堡、佛峪、王公为太谷三个相邻的山区村落,每村各有一个龙王爷,这三个龙王爷不愿孤独,结拜了兄弟。太谷的白脸龙王是老大,佛峪的黄脸龙王是老二,王公的红脸龙王是老三。三个村庙结为神亲,老大的诞辰是四月初一,届时郭堡村人把他连同老二、老三一起抬回本村过生日,并住三个多月到老二的诞辰七月二十一日,佛峪村人来郭堡把这三兄弟抬到佛峪庆贺小住到十月初一老三诞辰,王公村人来佛峪抬三个龙王回到王公庙。如此循环,年年相同。[6]
兄弟姐妹之间的结拜可以随着村落的增加而无限增长。比如,台湾彰化南瑶宫妈祖会,分成十个大妈会,即老大妈会、新大妈会、 老二妈会、兴二妈会、圣三妈会、新三妈会、老四妈会、圣四妈会、老五妈会和老六妈会。这里十个妈祖名称上的排行,明显是模拟姐妹关系的村落神庙联盟。
三、神庙联盟的交往仪式及历史衍变
传统村落神庙联盟中最常见的交往通常被叫做巡境、绕境或游神。山西所属的华北地区,类似的活动比比皆是。在某些特殊的日子,一般固定为神灵的生日或者是出嫁的时间,将一个或一组神灵(尤其是女神) 从神庙里抬出来,放在神轿中到很多村子里去游行,接受一个仪式圈内信众的参拜和施舍,并举行可观的娱乐活动,然后再择日送回神庙。这样的仪式活动,在汉族地区十分常见。[10]
“巡境”带有联村仪式的特征,是具有神庙联盟关系的村落形成仪式共同体的具体表现。参与此种联村仪式的各村在举办庙会时,会照会其他村落的组织前来商议。下帖子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如甲村欲赴乙村, 甲村就用红纸誊写一份文书送到乙村村社,告知何时何村欲赴。此外,甲村也会主动邀请乙村。甲村下帖子后,乙村视对方所尽礼数和本村的接待能力,商议之后再给予回复。如同意即由乙村择定吉日并书面告知甲村。这样帖子会以公开发布的形式张贴在村落大庙墙壁上。例如,笔者调查中发现的一副道光年间山西泽州从中村到云首的祈雨邀请帖:
敬启
晋属中村社友诸君等知悉:敝村等恃昔社交,同气相求,敢烦贵社枉驾沁境,祈祷雨泽,以全民生日。今天久不雨,二麦未熟,大秋禾至今未种,西成何望?即二三急于种植者,亦无萌蘖之生焉。听农民之嗷嗷,瞻山川之涤涤,诚无草不死,无木不萎也。向有同事之情,必有同心之举。敝社等诚忧心殷殷,无处可诉。想贵社昔年祈祷雨泽,无不朝祈而夕降者。因不揣鄙陋,境治隔异,敬祈贵社光临以慰民望,如或甘霖普降,不惟余等神圣之有灵应,亦贵社之厚贶也。惜社交同事之情,敢祈贵社枉驾光临是幸。
固县村转南河底、转小南山、转管头村、转贾寨村、转车山村、转寺头村、转中村、固县村。南河底社 仝 谨具*《泽州中村去云首祈雨记》原文写于当地的毛边纸上,存于山西泽州中村段永贤家中,此文为笔者整理。
很快得到的回复是:
启覆
沁属固县南河底社友诸君等,知悉:所来之信吾等接之,村众商酌,急速挪神擎驾往神潭祈祷,求神普降甘霖。惟幸候转单到时定期,余不多覆。(回信照来信覆转)
中村民众社首仝 具*《泽州中村去云首祈雨记》原文写于当地的毛边纸上,存于山西泽州中村段永贤家中,此文为笔者整理。
由上可见,村落联盟之间通讯方式在识字率极低的传统社会中显得极为正式,成熟的交流模式表明两村之间的联盟存在时日很久。同一份文本中也详细记录了在行进中所经神庙的各项繁琐见面仪式:
(中村)至上村二里,两起驾。到河落驾没香桌,摆(到)子孙圪瘩落驾,用柿圪连米汤,用毕起驾。铳四声,落驾一声,起驾一声,庙起驾一声,大庙(子孙圪瘩村社庙)前一声。由官坪院撤至(盘龙)寨跟(前),有香桌在场落驾,没香桌不落驾。由工上至主师阁,摆至大庙(盘龙寨社庙)谒庙落驾。铳五声,寨跟落驾一声,起驾一声,主师阁一声,十字街一声,大庙前一声。*《泽州中村去云首祈雨记》原文写于当地的毛边纸上,存于山西泽州中村段永贤家中,此文为笔者整理。
此类见面仪式被规定为缺一不可,文书中随处可见因没有严格遵循这种巡境仪式而导致神灵责难等。神灵巡境代表着村落和村落联盟对地域的支配权,一般情况下,参与此类仪式性活动的人群和村的范围,特别是游神经过村子的路线图有严格规定,社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有例不减,无例不添”,即有份参加游神的村落是基本固定的,不能随便增减。有例证表明这种神庙联盟也不总是风和日丽,有时候也会出现雨雪冰霜,因赛社仪式上的争强或者因为村落内部联姻的裂变都会导致村落神庙联盟的崩盘。
从空间区域看,村庙联盟往往并不在相邻的两个村落中发生。上文的清代泽州凤台县辛壁村从凤台县跨越到了阳城县与章训村龙王庙联盟,而在相隔辛壁村五里的徐沟村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白龙王庙,舍近求远是村落神庙联盟的主要特点。相邻村落之间呈现疏离状态,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现象一方面是村民对其村落自足状态的想象与追求,另一方面也是村民对村际间关系的一种处理方式,是乡民对于建立某种明确、澄澈的村际关系的设计,同样体现出对于乡土片区稳定状态的珍视。[11]但笔者猜测更多的可能是对资源的激烈争夺而导致的相邻村落互不结盟。
传统村落的神庙联盟方式虽然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是透过以上的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以及婚姻和结拜组成的模拟血缘神庙联盟方式,我们可知血缘和姻缘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此二者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构成社会关系的基础,最初的聚落也是这样形成的。单一聚落又通过这种方式不断进行扩张,形成村际关系网。实际调查中也确实发现有些村落之间存在着实际的联姻关系。如山西太谷县的西贾村和石堡寨,一个在县北,一个在县东南,中间隔山相望,相隔七八十里,其交往最早是因石堡寨位处山区,草木茂盛,吸引西贾人到此放羊,而擅长放羊的石堡寨人遂揽下西贾的羊,后来有的就落户到西贾,听说石堡寨龙王灵验,一遇天旱西贾人就在这些迁居人的指引下到石堡寨抬龙王。开始时是偷着抬,后来两村便结成神亲。西贾到石堡寨抬龙王成为习惯,两村的交往也逐渐增多。民国年间,石堡寨有三十来户人家,其中就有十来个姑娘嫁到西贾,还有十家搬到西贾落户。[12]29笔者也发现,即使没有村落神庙联盟,村落之间的戏班子也往往在有实际婚姻关系的村落之间频繁流动,甚至在赛社活动中,本村的出嫁姑娘会以隆重的仪式邀请远在数里之外的娘家姑嫂前来观赏。
促成神庙联盟的主要因素并不仅仅是信仰,某种程度而言,信仰只是其外在表现形式。除地域、婚姻、血缘外,甚至市场资源也是村落神庙结盟的主导因素之一。关于此论,杜赞奇在文化网络理论中有详细解释,他把乡村民间信仰分为村中资源组织、超村界的资源组织,以及以村为单位的非资源组织和超村界的资源组织。[13]
以上村落神庙联盟除了血缘关系和模拟血缘关系的划分外,还存着一种以“分香”为基础的村落神庙联盟。如山西泽州的府城玉皇庙,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由远在陵川下壁村玉皇庙分香建立*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玉皇庙碑文》,现存山西省晋城市府城玉皇庙内。,泽州高平县大量存在的汤帝庙也由明显的分香层级关系形成。嘉道年间,广西省山内小江水、三合水和花雷水三江流域分别形成了以庙宇为中心的村落联盟,马河甘王庙、大坪刘大姑庙和蒙冲三圣宫正是三大水系的村落联盟的中心。马河甘王庙建于乾隆年间,据称是有香炉自象州飞降其地而立庙,即被视为象州甘王祖庙之分香。[14]就华北而言,“分香”建立的村落神庙联盟要远远早于以血缘关系和模拟血缘关系建立的村落神庙。分香神庙联盟到了明清日渐衰败,不但巡境仪式无法保障,甚至子庙的势力日益强盛超过了母庙,进而摆脱了与母庙之间的层级联系。明清以降,尤其是清代乾隆朝之后,这种以分香来确定村落神庙层级的现象渐渐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以血缘和模拟血缘为基础的平级联盟关系。此一发展过程和华北村落的形成过程轨迹基本一致。黄忠怀曾将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的村落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永乐到乾隆时期“村落数量不断增加”,但大多数村落的规模仍然较小,所以仍以散村占据主导地位。二是乾隆以后“村落数量的增长明显放慢”,村落发展主要表现为规模的扩大“逐步形成以集村为主的乡村聚落格局”。[15]这一发现在田野调查中也被印证。[16]故此,笔者并不同意笼统地把这些村落神庙联盟归为信仰圈和单一神亲链中去解释,某种程度而言,分香神庙联盟和信仰联系紧密,而血缘和模拟血缘神庙联盟基本只是以信仰为旗号,实质内容无论狂欢精神也好,还是市场和资源联系也罢,都离信仰渐行渐远了。
村落联盟一旦形成,一方面借用官方认可成为乡村的正统组织,另一方面通过固定的仪式性活动强化内部凝聚力,它强调明确边界和人员组成,客观上也起到了抵制外来流寇、乞丐团伙和盗贼的作用。如道光年间浙江省金田地区以新墟三界庙为中心的村落联盟在与官方组织合流,实施对盗、匪等异类的排斥方面表现得特别典型。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大量的村落联盟禁碑,也是此证。
现代社会中,村落神庙联盟的发展似乎并未停止前进的脚步。在山西省万荣县的上朝村,此村神庙为姑母神庙,是一位典型的当地神灵。但,距此不远的万荣后土庙便是声势显赫的全国文保单位,上朝村并不属于后土庙的“十村六社”范围,可确实在其集市圈范围内。因后土神庙在现代的名声远播,上朝村民认为自己村的姑母曾经和后土娘娘结拜为干姊妹,并且煞有其事地在本村神庙中添加了后土神像。这样的现代传说使得上朝得以在后土祭祀中分得一杯羹,因此,一个地方性神庙从属村落从此便有了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属村落平等的地位,故而也加强了相邻村落的交往和合作,促进了区域社会的和谐。
[1] 赵丙祥.多村落的民俗学调查[J].民间文化论坛,2007,(1).
[2] 吴长根.太谷民间故事集成[M].太谷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1990.
[3] 关强.山西垣曲岱嵋圣母信仰调查[D].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15.
[4] 石耀辉.根祖文化新探[M].临汾市尧文化研究会编,内部发行.
[5] 韩洁.村落关系的历史性与现代性研究——以贵德两神相会仪式为例[D].西宁:青海民族大学,2015.
[6] 王守恩.山西乡村社会的村际神亲与交往[J].世界宗教研究,2012,(3).
[7] 徐天基.村落间的仪式互助——以安国县庙会间的“讲礼”系统为例[J].宗教人类学,2013年第4辑.
[8] 侯娟.明清以来的民间信仰与乡村基层组织——以山西榆次八社十三村为例[D].太原:山西大学,2008.
[9] 杜妮.明清时期三嵕信仰下的神亲关系[J].黑龙江史志,2015,(7).
[10] 陈泳超.接姑姑迎娘娘走亲习俗解读[J].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3).
[11] 张士闪.村庙:村落叙事凝结与村际关系建构——冀南广宗县白刘庄、夏家庄考察[J].思想战线,2013,(3).
[12] 李文慧.民间信仰与村落关系[D].太原:山西大学,2006.
[13]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J].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14] 唐晓涛.神明的正统性与社、庙组织的地域性——拜上帝会毁庙事件的社会史学考察[J].近代史研究,2011,(3).
[15] 黄忠怀.整合与分化:明永乐以后河北平原的村落形态及其演变[D].上海:复旦大学,2003.
[16] 姚春敏.明清以降山西村落与庙宇[J].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