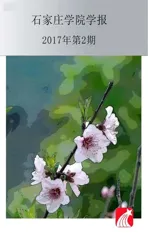“政治抒情诗”的考辨及其域外资源问题
2017-04-13张立群郑志杰
张立群,李 阳,郑志杰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政治抒情诗”的考辨及其域外资源问题
张立群,李 阳,郑志杰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政治抒情诗”是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概念之一,它在特定的时代出场,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并得益于域外资源的借鉴。结合“政治抒情诗”的概念解读和历史考察,分析其域外资源与本土融合、多重演绎及复杂性、自我演变等方面的问题,可以深入认识政治抒情诗的发生与发展。从特定历史语境来看,“政治抒情诗”在汲取域外资源时还有不同表现形态的诗歌写作作为“参照”,它可以深化人们对于“政治抒情诗”的历史认知。
“政治抒情诗”;域外资源;当代诗歌史
如果只是从命名的角度审视,那么,“政治抒情诗”的概念自然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被提出的,但作为一种文体实践特别是后来的历史评价,“政治抒情诗”出现的时间却“变得”更为早些①比如,在张德厚、张福贵、章亚昕的《中国现代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122页中,关于蒋光慈的诗歌,就被直接说成是“具有革命政治抒情诗的鲜明特色”以及“在新诗史上,蒋光慈对政治抒情诗的开拓,在现实主义精神中融入理想主义色彩,无疑都是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后来革命诗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龙泉明的《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196页中,著者将2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革命诗歌”及“普罗诗派”的作品作为政治抒情诗予以论述。而在洪子诚、孟繁华主编的《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中,“政治抒情诗”的写作者荣光启就曾有“‘政治抒情诗’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在50年代后期,但其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形态的诗歌形式,它的出现要早得多”的说法。。仅从艺术源流的角度上考虑,就有研究者在结合历史之后指出:“从艺术渊源上说,政治抒情诗写作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新诗中有着浪漫派风格的诗风……当然,更直接的承继是30年代的‘左联’诗歌,和艾青(如《向太阳》)、田间(如《战斗者》)和抗战期间大量出现的鼓动性作品。另一是从西方19世纪浪漫派诗人,尤其是苏联的革命诗人的诗歌遗产……苏联革命诗人,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从处理现实政治,到艺术表现,都给当代政治抒情诗提供可直接仿效的基本方法。”[1]74-75“政治抒情诗”既有特定的主题和艺术,又有多样的文化资源,并在特定时期成为一个文学史概念,表明其只有进行历史的考察才能明确具体的内涵,而在此过程中,我们所能涉及的问题还有许多。
一、“政治抒情诗”释义
“政治抒情诗”作为一个偏正短语,顾名思义,其“政治”和“抒情”的修饰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要在表达现实政治的同时兼具浪漫的气质。而事实上,“政治抒情诗”无论就其名称出现的年代,还是其写作上的精神价值取向,都预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时代已经来临。自1955年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和1956年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十年颂歌》等作品出现之后,“政治抒情诗”便作为一种“崭新的形式”为诗坛所认可,并逐渐出现了理论上的阐述,如徐迟在1959年一本歌颂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编选的诗集序言中就曾指出——
热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诗,可以说是我们的诗歌中一个崭新的形式。政治抒情诗,最鲜明、最充分地抒发了人民之情。虽然它还是个人抒情,可是在政治抒情诗中,诗人是一个公民,他和共和国的精神,全民的精神是一致的。热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诗是广阔的,是祖国河山的回声,是世界的回声,是亿万人民合唱的交响乐。热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诗是时代的先进的声音,时代先进的感情和思想。它是鼓舞人心的诗篇。它以雄壮的响亮的歌声,召唤人们前进,来为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热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诗是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喉舌,热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诗是最有力量的政治鼓动诗。[2]237-238
“政治抒情诗”的时代性、进步性、人民性以及热情澎湃,使其成为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诗歌表现形式。时代需要“政治抒情诗”,并使之成为这个时代诗歌创作的主潮,而其自身也理所应当地获得命名的权利。
特定年代的出场不仅决定了“政治抒情诗”的命名,还决定了其艺术特征。正如后来一些研究者概括的那样——
首先是思想内容上强烈的政治性,以及对诗的政治功能的强调。它要求诗人服膺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巨大的政治热情,关注和表现国内外正在进行着的政治斗争,反映社会的重大矛盾。题材的这种社会性和政治性的特点,使诗歌的主题通常是一个普遍性的政治主题,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常常不是富有独特个性的诗歌自己,而往往是一个作为阶级代言人的抽象的“大我”。政治抒情诗的这个最本质的特征,把它从一般的抒情诗中区分开来。这是五十年代以来强调把文艺(诗是其先驱)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这一观念的实践的产物。
其次,政治抒情诗的艺术结构,往往表现为观念演绎的形态……
第三,情感效应,是政治抒情诗所十分重视的。这是强调它在社会生活中、在群众中的战斗性和鼓动宣传作用的结果。这一诗体十分重视思想观念的激情负载,重视诉之读者耳朵和心灵的,能直接产生情感效应的节奏与音韵。而它所表现的情感,又偏于对激越、豪壮的追求。[3]185-187
“政治抒情诗”的“质”与“形”特别是其笼统的命名,虽可以使其和此前新诗史上出现的许多诗歌创作联系起来,并同样适用于某些创作,但在本质上,它却具有时代、历史、政治文化意义的规定性。“政治抒情诗”不仅要有鲜明的阶级立场,“以不同的方式反映阶级斗争”,还要“表现出无产阶级的胸襟和思想境界”;不仅要抒情,“要求热烈的、燃烧的情感”,还要密切联系时代,表现时代政治主题,“及时地配合政治运动、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4]。“政治抒情诗”在凸显自身意义和价值的过程中,同样凸显了自身所处的时代语境和写作者及诗歌抒情主人公的政治文化立场、身份和自我认同。像历史上所有可被称之为“政治诗”的创作一样,“政治抒情诗”高度语境化。它首先是时代与诗歌、诗歌与现实互动的结果,而后才是一个资源、方法以及命名的问题,而对此,我们所要呈现的内容还有很多。
二、域外资源与本土融合
在“政治抒情诗”的发展过程中,域外资源即外来文化的影响在本土产生的效果同样值得关注,而这一点,也正是“政治抒情诗”在以往研究中常常被简单化处理甚至忽视的地方。如果仅仅从“楼梯式”的形式看待问题的话,那么,前苏联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自然可以被看作一种直接的源头。早在20年代中期,蒋光慈就曾在介绍“十月革命和俄罗斯文学”的文章中,以“伟大的天才的诗人”来介绍这位“革命的诗人”①蒋光慈的《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原文曾连续刊载于1926年4月16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2期、1926年5月《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6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均署名“蒋光赤”,但不完整。本文依据《蒋光慈文集》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134页。文中马雅可夫斯基被译为“马牙可夫斯基”。;30年代马雅可夫斯基的“政治诗”,无论是观念,还是具体的写作实践,都曾对我国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马雅可夫斯基更是由于其先驱身份而被置于崇高、伟大的地位。1953年6月为纪念马雅可夫斯基诞辰60周年而召开的座谈会,1957年至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五卷本的《马雅可夫斯基选集》,并且不断在重要的诗歌刊物介绍其生平、事迹②单以《诗刊》为例,1957年6月号在翻译马雅可夫斯基《穿裤子的云(第二章)》的基础上,又开辟大篇幅介绍了他的《“最后一次的演说”(速记)》;1958年1月号以“诗集评介”的方式刊载了《祝贺“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一卷出版》;1963年7月号刊载了臧克家长篇论文《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战斗的伟大歌手——纪念马雅可夫斯基诞生七十周年》以及徐迟撰写的《三八线上的马雅可夫斯基纪念会》,等等。,本土创作如《致青年公民》《放声歌唱》《东风万里》等不断呈现出其诗歌的“艺术投影”,这都说明了这位诗人以及这种诗歌形式在当时产生的重要影响。
然而,在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不断通过译介的方式引入并对中国新诗特别是对五六十年代诗坛产生重要影响的背后究竟隐含着怎样的内容呢?这一点,或许并不能仅仅从“政治”和“抒情”的字面上得到解释。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普罗诗歌”,显然可以作为那一时期的“政治抒情诗”。但正如前文所言,“普罗诗歌”以及所谓的“革命的浪漫蒂克”,由于其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以及无法绕开的真实性,在30年代的左联时期便遭到了历史的“清算”。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理论不断发展,特别是在进入当代语境之后已经日趋成熟的前提下,诗歌写作似乎也同样期待一种进步。然而,在“政治抒情诗”逐渐兴起、风靡一时的过程中,人们不难看到,这是更为革命、浪漫的诗潮。它因寄托着集体的想象而实现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真实,它虽同样“公式化”“概念化”,却能和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不能不说其本身需要的是“讲述话语的年代”。
对于“政治抒情诗”的内容及其艺术表现,以往的文学史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共识性”的论述,但就在这常常易于为人忽视的外部显现的背后,却隐含着诗歌与时代话语权力之间的复杂内容。首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国家的社会性质、时代氛围等因素都决定了外来文化的引进方向和内容,所以,苏联文艺观念就在总体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内文艺理论建设上的薄弱以及以往的历史成因,也造成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在“二元对立”逻辑上一度唯苏联文艺马首是瞻。这样,在具有“历史基础”和视野相对单一的前提下,选择其代表诗人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诗坛的榜样,就在政治身份认同的前提下变得顺理成章起来。其次,由于建国之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被进一步强化,对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逐渐让位于政治宣传并进而产生了诗歌表面化、单一化的倾向,是以,在极易造成诗歌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之余,寻找一种可以进行“过分依赖和颂扬”的依凭,就在符合外部政治标准和内部政治文化心理的需求下,成为一种写作上的逻辑。况且,以马雅可夫斯基和伊萨科夫斯基为代表的“政治诗”和“抒情诗”创作,已经在翻译和宣传的过程中,预设了一种文化心理,而这,对于“中国五六十年代诗歌创作的两种基本模式的形成”,自然是“起了重要作用”①详见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版,第12页。其中两种基本模式即为“政治抒情诗”和“生活抒情诗”。。最后,从诗艺流变的角度上讲,曾经在延安时期出现的诗歌采风以及即将到来的“新民歌运动”,都在一种近乎不约而同的现实指向下,涉及到新诗自身的形式问题以及接受过程中的朗诵与诵读的问题。以贺敬之为例,因熟识民歌体的创作,使其易于在这种“规范形式”下的写作中进行更为自由的、现实的表现与抒情。不仅如此,“政治抒情诗”的广阔性还在于它的形式感、韵律感可以与诗体建设的问题进行一种历史的“遇合”。
三、多重演绎及其复杂性
正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言,“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5]523。当代“政治抒情诗”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流行开来并产生重要影响,当然不是因为它已弥合了以往创作的弱点,而应是其观念与形式“并重”之后,符合并顺应了这一时期的共同“政治标准”之下的资源借鉴、本土融合以及最终的内容表现。
“政治抒情诗”社会性、政治性的特点以及反映普遍意义上的时代主题,不但使其和一般抒情诗容易区分开来,而且,其强烈的“政论性”色彩和说教性倾向也要求它在注重情感、气势和音韵朗诵的过程中呈现其宣传鼓动的作用。对比历史上同样可以称之为“政治抒情诗”的创作,如蒋光慈、殷夫的作品,虽然后者也在文本上出现了词语反复、音节短促、情感激昂等特点②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殷夫的组诗《血字》中的《意识的旋律》以及《May Day的柏林》等作品,参见《殷夫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但当代“政治抒情诗”却明显在激情宣泄的同时注意了形式上的自我规范。因而,所谓“楼梯式”并不仅仅是注重了诗的音乐性和形式感,其深层内涵在于“拆行分句”后带来情感抒发上的起伏和节奏的铿锵以及可以容纳更多的内容篇幅。
“政治抒情诗”作为“颂歌”创作高度发展的阶段,不但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和人们情绪高度政治化的结果,而且,其抒情主人公常常被提升为时代“大我”的形象,甚至是其象征性意象,如“天安门”“井冈山”“红日”“红旗”“青松”等所特有的抽象抒情功能,充分说明了当时社会“集体式”的政治心理以及对于诗歌写作艺术所能抵达的认知水平。但即便如此,对于采取“楼梯式”创作的政治抒情诗仍需指出的是,它内部的差异性不但反映了外来形式本土化过程中的“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性也较为深刻地反映出同一社会政治模式下不同个体之间的政治意识。
以常常被视为“政治抒情诗”代表诗人的郭小川和贺敬之为例,虽然两者均借鉴了“楼梯式”并风靡一时,但就诗体的角度而言,郭小川的“楼梯式”,如《向困难进军》等,却往往在激情之余缺少对汉语语音特点的关注,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丢弃了马雅可夫斯基“楼梯式”的精髓——“许多人摹仿马雅可夫斯基写散文化的诗,但马雅可夫斯基本人的诗却是有韵的。”[6]610于是,在郭小川早期的“政治抒情诗”中,“思想(其中也有一些闪光的成份)常常呈现裸露的状态,形象往往是一种比喻,零散地缀在思想的枝条上”[7]201。相比较而言,贺敬之的“楼梯式”,却很少那种直接堆砌政治术语和呼喊口号的现象,在《放声歌唱》等作品中,贺敬之总是以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提升诗歌的听觉效果和视觉效果,从而以极大的限度发掘诗歌的审美潜力。不但如此,贺敬之还常常在“楼梯式”使用的过程中融入“民族化”的意识,加上对中国古典诗词中一些技法,如排比、对偶等手段的借鉴,成为其写作模式更易为读者接受的重要原因。自然,“这种形式上把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的外壳赋予以讲究对称美的传统格调、而且适于朗诵的形式,内容上以配合形势重现重大的政治事件的诗,由于一批诗人的全力实践而得到广泛的流行”[8]149。
而从个体与社会,同时也是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角度上说,郭小川总是以一个“自觉的诗人”身份,希望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展现个体与社会的融合,这样的出发点往往造成了个体生命在具体感知过程中“不和谐”因素的出现。因而,在《向困难进军》等受到评论界和读者一致赞赏的时候,诗人本人更多保持了一种清醒的态度①参见郭小川《〈月下集〉权当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本文依据的是《郭小川全集》第5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3-394页。。上述过程既是郭小川不断进行艺术探索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其《望星空》《一个和八个》等遭受批判和诗人“检讨”②关于“检讨”,具体可参见郭晓惠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中的相关内容,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的重要原因。与之相比,同样在处理这种关系的时候,贺敬之则“从不(或极少)表现其间的裂痕、冲突”,“在他的诗中,‘抒情主体’已是充分‘本质化’了的,有限生命的个体由于融入了整体,由于对‘历史本质’的把握,而转化为有着充分自信的无限存在”,因而,“在他的诗中,难以发现不协调的因素,和情绪、心理上的困惑、痛苦”[1]76,而在不同时期不断删改自己的创作恰恰可以克服创作上的尴尬。
四、自我的汰变与沉潜
以“楼梯式”为代表形式的“政治抒情诗”在其盛行的时代,无疑在宣传鼓动方面起到重大的历史作用——“《向困难进军》曾不止一次在成千人参加的朗诵大会上朗诵过,许许多多青年人从中得到鼓舞力量。这是政治性很强的诗!它确实起了诗的武器作用。”[9]但当政治抒情诗成为一种模式流行之后,对它的竞相模仿便逐渐发展为普泛意义上的抒情,与实际社会现实相脱离。这种倾向不但为其当事人所察觉,同样也为其他一些人士所察觉,然而,这种“察觉”并没有阻止“政治抒情诗”在一定时期内的继续泛化。
针对“政治抒情诗”成为潮流并日趋空泛的现象,王亚平在1960年1月号《星星诗刊》发表的《那不是诗歌创作的坚实道路》一文提醒道:“写政治抒情诗,要富有热情,却又不单靠热情,还得有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又有通过具体事物对政策的深刻感受,抒发出来的诗情,才是真实的动人心弦的。没有这些,就是虚伪的感情,不真实的诗!同时,我觉得一个初学写诗的同志,政治思想修养差,历史知识不够,不应该抢着写毫无把握的政治抒情诗”,“题材不熟悉,就没有思想基础,只好求之于贫乏的语言。这一切正是严重第违反了创作规律(任何作者都应该写他熟悉的题材)……这就接触到一个创作上的重要问题。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诗人,当然要写有积极政治意义的主题,要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有国际意义的主题。但一个没有生活基础,没有思想准备,对所写的没有深刻的感受,又没有语言的深厚修养,只抱住这个庄严的主题就挥笔成诗,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机和思想支配他写作哩?”[10]王亚平的提醒无疑是客观而中肯的。因为这种提醒不但切中了当时流行的政治抒情诗在实质上“政治”与“抒情”已然脱离的事实,而且也深刻说明了任何脱离现实生活的写作,即使表现了时代的主题,也必然要陷入到空洞无物的状态中去的事实。然而,这种提醒在“观念已然大于写作”的时代无疑是不合时宜的。果然,在随即发表的《王亚平反对的是什么?》一文中,王亚平的提醒遭到了严重批判:“文学艺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目前诗歌创作中出现大量的政治抒情诗(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各项政治运动的伟大胜利),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诗歌创作的特点,是党的文艺政策的胜利。……王亚平同志用这种理由来告诫青年作者不要写‘政治抒情诗’,我认为是不恰当而且有害的。它会给正在发展中的群众创作运动泼冷水,它会打击青年作者在诗歌创作中的政治热情,从而引导他们脱离政治。”[11]
既然反对的声音已经遭到批评,那么,“政治抒情诗”势必还要继续在一定的范围内书写下去并扩大自己的范围。1962年底,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全国的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当代诗歌也迅速作出反应,一改20世纪60年代初期略显平静、写实的诗风,浪漫的激情再次被点燃。“从1963到1965年这三年间,诗歌创作出现了如下现象”——
第一,政治抒情诗成为占据诗坛主导地位的潮流。具有“写实”倾向的作品大量减少。理性成为诗歌构思的轴心。以政治激情来宣释当时流行的某些政治信念,成为诗歌创作一时的风尚。许多诗人的创作风格,急遽地发生突变:从纤细轻柔的田园牧歌,变为粗犷豪壮的时代“战歌”。
第二,与50年代相比,诗的主题从对劳动、建设的美的歌颂,转向对“继续革命”的感情和行动的宣扬。在思想的表达上,只有把每一样实际工作都视作“斗争”,而且必须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才能取得淋漓尽致的宣传效果。诗的表现无论在题材内容、形式结构或形象体系上,都走向空疏博大。
第三,诗的想象方式和象征体系也发生了变化。比兴象征,托物言志的方法大量运用。红日、红旗、青松、风暴、井冈山、天安门……等等,再也不是它们本身,而是赋予了政治含义的一组使用频率极高的通用的象征符号。适应舞台表演式的朗诵的需要,赋体广泛流行,押韵和大量排比句,成为这一时期诗体的主要特征。[3]33-34
“政治抒情诗”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不再经过任何挑战和反思就进入了“文革”。然而,作为一种极为独特的政治性诗体,“政治抒情诗”毕竟只是从属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诗歌概念,它是通过外来文化资源与本土诗歌创作融合并最终呈现出观念大于实践的一种写作。而其之所以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复杂而特殊的概念,除了源自“政治”本身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发生变化,还反映了在政治与诗歌势力强弱对比的过程中,包括诗人创作心理在内遭遇政治制约以及自省后对诗歌艺术的自觉意识与要求。
五、余论:另一种潮流的资源与书写
在前文谈及前苏联诗歌资源对当代中国诗歌的影响,进而对“中国五六十年代诗歌创作的两种基本模式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对这一时期若干重要诗人的‘风格’的形成,也有直接影响”[3]12时,我们已触及到“政治抒情诗”之外的另一种诗歌主潮,此即为“生活抒情诗”。以当时闻捷、李季的诗歌创作为代表的“生活抒情诗”是“政治抒情诗”的重要参照与补充,它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当代诗歌的创作,而且还能深化人们对于“政治抒情诗”的认识。
首先,就写作本身而言,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
生活抒情诗与政治抒情诗的重要区别在于:其一,生活抒情诗不是关注重大事件,而是关注具体的生活事件,它所表现的是相对较少的题材;其二,生活抒情诗在篇幅上一般较为短小;其三,由于篇幅短小,生活抒情诗在诗体上就较为注重对诗的文体规范的尊重。二者的共同性在于,由于产生于同一种政治氛围之下,生活抒情诗所谓的“生活”实际上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所以,生活抒情诗同样无法摆脱政治观念的约束,只是不那么直接而是间接地阐发政治观念而已。诗歌观念与思想流向上的同一性同样构成了生活抒情诗在一定程度上的单调化与表面化。[12]372-373
显然,作为同一语境下的另一种诗歌范式,“生活抒情诗”在与“政治抒情诗”有所区别的同时,同样也有“共同的部分”。像“政治抒情诗”一样,“生活抒情诗”的出现自然无法离开时代、社会公共阅读标准的检验。以闻捷的《天山牧歌》为例,诗人以明朗、轻快、乐观、积极的抒情笔调,书写了西北边地少数民族的地域风情、精神生活,直接表现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这些题材新颖、主题鲜明、音节响亮的抒情诗篇,给人以清新明丽的感觉。这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中第一部反映边疆民族新生活的诗集,立即赢得了人们的注目和喜爱。”[13]2当然,若就诗人具体展现这些场景的情况来看,“把爱情作为政治的附属物,给它加上社会性的装饰,以爱情来证实某种政治性原则”[3]98的看法,也符合从创作主体到接受主体的实际心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生活抒情诗所谓的‘生活’实际上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结论并不过分。
其次,就域外资源与本土转化的角度来看,“生活抒情诗”与“政治抒情诗”也有相似之处。正如许多著述已经指出的,苏联诗人伊萨科夫斯基的创作对当代中国的“生活抒情诗”产生了重要影响①具体可列举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版;吕进的《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朱栋霖主编的《中外文学比较史1949-2000》上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伊萨科夫斯基是苏联著名诗人,他的诗深受苏俄民间诗歌传统的影响,有一种田园牧歌的调子。他的诗不仅开创了反映苏维埃农村生活和农民内心世界之抒情诗的新阶段,而且还适于配乐演唱。《喀秋莎》配乐演唱之后,在苏联卫国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堪比重要的武器;它和另外一首配乐演唱之后的名曲《红梅花儿开》一样,深受中国观众和读者的喜爱。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文坛曾大量介绍伊萨科夫斯基的作品,《人民文学》等刊物还多次刊发其谈论诗歌创作的理论文章,他的专著《论诗的“秘密”》也被翻译出版。伊萨科夫斯基的诗之所以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曾被归纳为:“一是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影响,在50年代,中国诗界的目光主要投注在苏俄诗人的作品上;二是他的诗具有田园味,民歌味,语言清新,节奏明快,以乐观为基调,正适合50、60年代中国人在颂歌时代所形成的那种顺应时势的文化心态;三是接近具体的生活现实,有一定实感,容易为普通大众所接受。”[12]373通过上述归纳,我们不难看出:“生活抒情诗”与“政治抒情诗”之间的共通之处,除了域外文化资源相同之外,顺应时代的某些需要也是两者成为五六十年代诗歌两种基本范式的重要前提。“政治抒情诗”关注重大问题,图解时代政治观念,强调宣传鼓动作用;“生活抒情诗”立足于真实的生活,多以积极向上、乐观抒情的曲调为现实生活谱写光明的赞歌,两者就思维方式而言,都不约而同地体现了时代对于诗歌的内在规定性。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政治抒情诗”和“生活抒情诗”作为五六十年代两种主要诗歌范式,一直具有共同的本质。“政治抒情诗”在表现社会、时代主题时展现出来的内容和情感上的真实性,源于诗人真实的内心和集体的想象;“政治抒情诗”交流视域过于狭窄、指向过于集中,造成其创作在大面积铺开后的模式化、概念化。盛行于同一时期的“生活抒情诗”由于生活本身和艺术经验的多元化,往往可以更为广阔地表现生活并对前者形成适度的补充,但同样在创作上存在相同的不足,而这些只能使其在面向历史的过程中成为特定的概念和诗歌潮流。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徐迟.徐迟文集:第五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3]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4]谢冕.阶级斗争的冲锋号——略谈政治抒情诗创作 [J].诗刊,1964,(10).
[5]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6]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10卷[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7]洪子诚.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谢冕.浪漫星云——中国当代诗歌札记[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9]臧克家.在1956年诗歌战线上——序1956年“诗选”[J].诗刊,1957,(2).
[10]王亚平.那不是诗歌创作的坚实道路[J].星星诗刊,1960,(1).
[11]尹一之.王亚平反对的是什么?——关于诗歌创作的道路问题的商榷[J].诗刊,1960,(2):85-89.
[12]吕进.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13]闻捷全集:第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周亚红)
On Textual Research and Foreign Resources of Political Lyric Poetry
ZHANG Li-qun,LI Yang,ZHENG Zhi-jie
(School of Arts,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Liaoning 110136,China)
The political lyric poetr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s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It emerged in a given age,and it has a profou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benefits from overseas resources as well.An analysis of the fusion of the foreign resources and local resources,the deduction and the complexity can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lyric poetry. From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there are different forms of political lyric poetry in absorbing foreign resources,thereby deepe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political lyric poetry.
political lyric poetry;foreign resources;history of contemporary poetry
I207.25
A
1673-1972(2017)02-0119-06
2016-01-12
张立群(1973-),男,辽宁沈阳人,教授,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