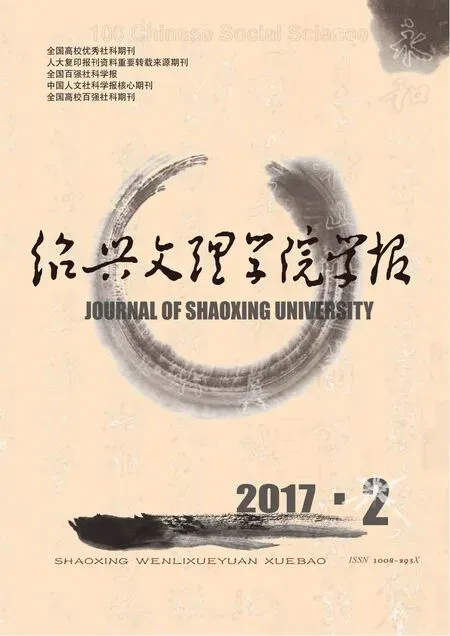藏书世家山阴祁氏家风及其地域传承
2017-04-13许经纬
许经纬
(绍兴文理学院 图书馆,浙江 绍兴312000)
藏书世家山阴祁氏家风及其地域传承
许经纬
(绍兴文理学院 图书馆,浙江 绍兴312000)
藏书世家山阴祁氏不仅因三代藏书而闻名遐迩,而且,其家风传承也独具魅力:藏书传家是祁氏家风传承的基本范式,忠敏齐家是祁氏家风的价值取向,艺文怡家是祁氏家风传承的主要方式和状态。祁氏家风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兼含“时代性”和“区域性”特质,具有越文化基因,于今仍可资借鉴。
藏书世家;三祁;家风特色;越文化
中华书局在《祁彪佳集》前言中曾指出:“祁氏的澹生堂藏书,在明代的浙江,是和会稽钮氏的世学楼,宁波范氏的天一阁齐名的。”[1]1祁氏藏书家世发轫于七世祁清,于九世祁承、十世祁彪佳、十一世祁理孙形成了藏书文化抛物线之高峰。“三祁藏书”被图书馆学界认为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
所谓“三代而下,教详于家”,祁承、祁彪佳、祁理孙藏书家学三代因袭,其良好家风又通过家规、家训、言传身教,世代传承,堪为典范。
山阴祁氏家族处于明清社会剧变之际,作为藏书世家,祁氏家族家风传承的基本范式、价值取向和传承方式有其独特秉性。
一、藏书传家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杜春生编纂《祁忠惠公遗集》时根据祁氏家谱编成山阴梅墅祁氏世系。祁氏一脉自明初定居山阴梅墅,始祖祁茂兴至十一世祁理孙为止的谱牒应为可靠。后绍兴文史工作者编写《祁承家世》,世系续至二十一世孝字辈,弥补了祁氏家谱“文革”时被毁的缺憾。笔者外子老家梅墅,排辈分应为祁氏二十三世孙。这门望族在梅墅曾经是一个巨大的存在。这里不仅有被称为“察院第”的台门、“旷园”的假山等地表遗址,更有大量文化遗存。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长期以来形成的能够影响家庭成员精神、品德及行为的一种传统风尚和德行传承。”[2]76有论者认为,儒家伦理“是传统家风的价值取向,‘耕读传家’是传统家风的基本范式,家学传承、家规、家训、家庭教育等是传统家风传承的主要方式”[3]145。我国传统文化历来推崇“耕读传家”“书香传家”,祁氏家族当无例外。只是这种家风传承的基本范式,于祁氏家族则主要通过藏书家学得以凸显。
一个家族的振兴,内因多在于良好家风的作用;而良好家风的形成和绵延,则离不开家族中成功者的引领。祁氏家族自四世祁仁入仕为官起,书香传家开始蔚然成风。祁家为教育子孙计,遂大量聚书,藏书,至七世祁清、八世祁汝森,已有遗书五、七架传于九世祁承。
祁承非常认同司马光的聚书爱书以及训子的“贾竖藏货贝,儒家唯此耳”的话,藏书的目的性更为明确,自觉性更强。他认为,自己既然是一个儒家信徒,就应该积极地聚书;同时为了儿辈的发展,更应该勉励他们继承家风,有所发扬,决不能让读书种子断绝。
“藏书传家”实为“读书传家”。祁家是“读书之藏书家”,而非“藏书之藏书家”,如祁承所言“世有勤于聚而俭于读者,即所聚穷天下书犹亡聚也”[4]103。只是他家儿孙所读的书已经过了成功者的筛选。有了私家藏书,读书会更方便,针对性可更强,视野也会更开阔。祁承充分认识读书的意义和作用,提倡有选择地收藏,有选择地阅读,他对于择书、藏书、读书、用书的要求可见诸其《藏书约》之中。
祁承对儿辈提出以能读为继承藏书家传的先决条件。对于图书,不仅能聚能藏,而且能读能用。他提出收藏图书的标准是:“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和“别品类”。简言之,其藏书要藏好书,藏有用的书,不仅可供儿孙博览,还在于经世致用,有利于儿孙成才。
《祁承示彪佳扎原迹》有云:“父母生子,恨不得一日见他成立。汝体父母之心,只是一刻不闲过,用心读书,便是好儿子。”[5]1祁彪佳从小就寝馈在家藏的书卷中间,加上父亲的精心教育,十七岁便中了举人,二十一岁成了进士。由于家庭环境熏陶,彪佳对于图书方面的各种活动,也早已司空见惯。鉴于《澹生堂藏书约》有非常严格的限制,不能满足要求,祁彪佳便像他父亲那样“穷收博采”,而且继往开来,建起了自己的“八求楼”。彪佳《八求楼》一文亦道出了他藏书之目的:“丁颉有曰‘吾聚书多矣,必有好学者为子孙’。以先子一生孜孜矻矻,青缃世继,予不敢为他日可勉也,庶以望之后人云耳。”[5]40彪佳并留下遗嘱云:“书可共守,要看者可分取”。
祁彪佳长子理孙也算得上善于继承家风遗志的肖子。他卖田聚书,建立了“奕庆藏书楼”,并历经十年之久,把先人遗书和自己增益的部分汇编成《奕庆藏书楼书目》。祁理孙对于丛书立部这一创制,为藏书家学的弘扬做出了新的贡献。
祁氏祖孙三代藏书,对于图书的聚、藏、读、用一系列工作,绝非以前绝大部分藏书家所能企及。此一家学,一脉相承,然又各有特创。祁承在图书分类和编目方面堪为先驱。祁彪佳注意广为收集戏曲等艺文类作品,建起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特色馆藏,同时他又是一位戏曲和散文学家,中华书局在《祁彪佳集》前言中说:“他所作的《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是我国古典曲、剧中的最重要的文献,足以和吕天成的《曲品》、高奕的《新传奇品》后先媲美。”[1]1祁理孙则在编目方面匠心独具,至今被图书馆学界誉为“我国优秀的目录学家”。被称为“浙东三祁”的藏书家学、藏书文化成了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以后,因国祸家祸,祁家藏书多有流失,但祁家子孙们仍牢记先祖手书的《藏书铭》中留下的“子孙益之守弗失”的遗言,最终,保留了万卷藏书。1954年,祁氏二十一世孙祁起孝向国家捐献了“澹生堂”遗书,至此,祁氏藏书家世已基本结束。然而,爱藏书、爱读书的家风仍然绵延未绝。
二、忠敏齐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士大夫们尊崇的信条。祁氏一脉读书为仕,注重修身养性,自不待言。当时,梅墅故宅挂满名人匾额楹联,其中有朱熹撰写的“存忠孝心,行仁义事”,曾国藩书写的“传家惟孝友,报国有文章”的对联,祁家台门充满书香传家的浓浓气氛。从家风传承的角度考察,儒家伦理是祁氏家风的价值取向,而忠敏齐家,即以忠诚奋勉之精神治家,是祁氏家风的基调,也是特点。
祁氏家族自四世祁清始,相继走上“读书做官”的道路,因一门连出七进士,被公认为山阴望族。这一家族发扬越中“自我实现”的精神,形成了勤奋读书、勤勉为官、忠诚义烈、爱国爱家的风尚。称为“浙东三祁”的祁承、祁彪佳、祁理孙三代,把此一家风渲染得更为浓烈,展现了鲜明的价值取向,树起了祁氏家风之标杆。
祁承勤学苦读,坚持不懈,直到四十三岁才中进士。其为学为官,淡泊明志,忧国忧民,耿耿于怀。他的《闻警》一诗,写于明败于后金之际,“既知残奕推劫胜,坐视危樯欲覆舟”,对当权派“食肉者鄙,未能远谋”之形状表示了深深的忧思和愤懑。祁承那些与做官经历相关的著作《澹生堂杂著》、《澹生堂全集》等后被清廷列为全毁之书,足可反证他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十分强烈。祁承十分重视对后代的“忠敏”教育,他还把祁彪佳从小带在身边言传身教。他亲自选定子孙读书的书目,“他认为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读书,要能把忠信孝友四个字贯彻到日常生活和言行中去,能经世致用,以有利于国计民生。”[5]5
祁彪佳自幼奉夷度公(承)持身修心之学,在博览澹生堂藏书中,他特别爱看史书,逐步养成了喜爱忠贞之士,痛恨奸恶之徒的感情,立下了忠贞为国的志向。
诚如范文澜先生所言,“忠实于儒家学说的儒者,常为人民发出诉疾苦、申冤抑的言论,也常为人民作出去祸害、救灾难的事迹,甚至不惜破家杀身对君主犯颜直谏,要求改善政治。”[6]116祁彪佳就是这样的大儒。处于明季王朝没落之际,社会求治之心愈显迫切。祁彪佳在朝为官时,革耗清弊,刚正不阿,曲体下情,直言谏陈;任职地方时又颇多善政:治海寇,禁恶讼,平强籴,救灾荒,仰慕先贤,甄录人才,上表名硕,风励来兹……如会稽名士吴杰所言,后之学者“读其制义而挹其经腴”,“读其奏议而想其忠謇”。
明朝亡国后,祁彪佳拒绝清廷招抚,留下“含笑入九泉,浩气留天地”之绝笔沉湖殉节。南明唐王谥之为“忠敏”。
忠敏齐家,于此熠熠生辉,更为后人坚守。祁氏家族良好家风的形成,还得益于女眷。彪佳夫人商景兰缅怀先人,作《悼亡》诗云:“公身成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折槛生前事,遗碑世后名。存亡虽异路,贞白本相成。”商景兰敬仰丈夫气节,忠敏齐家,使族人后辈,涵润其中,皆知书明理。
彪佳殉节以后,祁理孙、祁班孙及族中兄弟,广结抗清复国之士,并毁家纾难,以图复明。后因事败受到牵连,兄弟俩在受审时又争先承担,表现了舍生取义的高贵品德。理孙秉承先人遗志,弘扬忠敏家风,及至临终遗嘱,还对夫人张德惠明示:“子孙生计,不必予为筹划,至于忠孝,是我家故物,应勉励儿辈毋坠家声。”[5]71自理孙辈起,祁氏一族坚持不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也没人做过清朝品官,他们都一直保持着祖宗的民族气节。
祁氏家族忠敏义烈相传,英杰辈出。此一家风,遗绪尚存,祁家后裔不乏抵抗外侮的志士和献身人民解放事业的功臣,族中更有科教兴国、实业富乡之人范。
三、艺文怡家
论者普遍认为,家教、家学是传统家风传承的主要方式。笔者对祁氏一脉藏书家学和以儒家伦理治家之家教主轴已作概论。然而,家教、家学之内化过程,更多体现在润物细无声的文化熏陶之中。祁氏家族注重培养和提高世族子女的文学素养和艺术才能,其优美之门风,凝成了特色鲜明的家族文化。艺文怡家也是祁氏家风的状态和家风传承方式的特色之一。
所谓艺文怡家,乃指祁家用特色的文艺才能、文化修养涵养性情、抒发情感,形成了和谐环境、睦谊家风。在祁氏大家庭中,充满着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最具影响力的是他们在文学、戏曲和园林艺术方面的造诣和成就。
诗词几乎成了“三祁”及其家庭的共同爱好及擅长。祁承的《澹生堂诗文抄》稿本、祁彪佳的《远山堂诗集》、祁理孙的《寓山诗稿》和《藏书楼诗稿》、祁班孙的《紫芝轩逸稿》等诗集,大多渗透着他们寄情山水、寄托思念、坚持民族气节的高雅格调。值得一提的是,以祁彪佳夫人商景兰为领袖,祁家还有一批诗坛才媛。她们的诗歌造诣被认为超过了她们的男人们。商景兰有《锦囊集》、其女德渊有《静好集》、德琼有《未焚集》存世,《吴越诗选》之“名媛诗”也收有理孙夫人张德惠、班孙夫人朱德蓉的诗作。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会稽吴杰在为《祁忠惠公遗集》作序时,有赞云:“读诗、词、尺、牍而知公(祁彪佳)之逸致,读锦囊集而知公倡随之雅,读紫芝轩逸稿及未焚集而知公家学之富、遗泽之长。”[1]1
祁家亦爱好戏曲。以祁彪佳为代表,从其父辈到族中兄弟姐妹及儿孙辈,组成了一个戏曲家群体。收藏剧本,整理曲目,品剧演戏,是祁氏家族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祁承的“澹生堂藏书楼”就收藏了大批戏曲作品,祁彪佳收藏的曲品、剧品合计有708种。祁彪佳不仅大量收藏戏曲作品,而且还亲自创作、改编了一批戏曲,可以说,他的文学成就和贡献首先在戏曲上。其论著《远山堂曲品》和《远山堂剧品》最受今人推崇。
祁家又素有园林之好。祁承在梅墅建有密园和旷园,祁彪佳营造了寓园,从兄祁豸佳筑有柯园。承号夷度,又称旷翁,密园老人,这与他喜爱园林艺术是分不开的。祁彪佳后来耿于碑石,经营寓山,完全受承的影响。祁彪佳家居时乐此不疲地建园,并多方求取题咏,并编撰《寓山志》和《越中亭园记》,读之可知其适意于林泉,那一亭一阁、一草一木、一丘一壑中无不寄托着作者某种忧愤之思和人生感慨。
综上,祁氏家风传承的主要方式,内化过程,可归纳为言传身教、环境熏陶,他们赋诗抒怀,建园作记,作曲品剧,展现了祁氏家族的文化成就和独特的文化个性,可谓家风之“殊相”。
四、越文化基因
我们考察山阴祁氏家风,不仅因为其家学传承,家庭文化氛围及家庭生活方式使然,其家风传承的独特内涵,还包括了祁家秉承了越文化的优秀传统,烙有地域文化的深深印记。
“藏书传家”不仅是祁氏家风传承的基本范式,更是越文化之传统。绍兴名人辈出的两条基本途径是:外推式的强烈的树人意识和内在式的强烈的成才意识。这种意识及至宋明之际几乎成了越中的心理倾向,汇成了“自我实现”的人心主流。在成才入仕的心理动力驱使下,致使士大夫家族更喜聚书,藏书,读书。有鉴于此,宋元明清时,越中涌现了很多藏书家。据《嘉泰会稽志》所记,南宋时,“越藏书有三家,曰左丞陆氏,尚书石氏,进士诸葛氏”。他们都是三世或二世藏书,尤以陆游家族的藏书最有影响。在元代,又有杨维桢的铁崖岭藏书,及至明代除祁氏祖孙三代藏书外,与之齐名的还有钮石溪的世学楼藏书,另有山阴徐渭、新昌胡桢、上虞韩广业等多家。除私家藏书以外,还有官府藏书、书院藏书、佛寺藏书等等,至清代,越中藏书事业更为繁荣。藏书成为越中风尚,遂有越中“耕读传家”传统之说,盖与越中“自我实现”的人文精神相关。
祁氏“忠敏齐家”有其独特内涵,其价值取向亦根植于越文化之土壤。明清之际,越中理学一新,王守仁倡导阳明心学,一改程朱理学之传统教义,提出了“致良知”说,后刘宗周又提倡“自我诚意”,将“慎独”之功,置于“修身”、“治家”之首位,建立了“慎独”为宗旨的儒学思想体系。祁彪佳称贽刘宗周门下,不时与之探讨生死义利问题。后祁彪佳、刘宗周在三天内先后沉湖、绝食而死。诚如学者赵素文所言,“这绝不会如前人解说的仅为国殉节那样单纯,而是一种很具有时代特征的行为。”[7]5刘宗周、祁彪佳同以自身的人格特质,实现了心灵境界的升华,树起了人格典范。祁氏家风修身标诚意,师友重气节,因此祁彪佳对“忠敏”内涵的诠释,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这正体现了越中人物精神的传承。
祁氏“艺文怡家”的文化个性,亦与社会文化背景相关。明清以来,随着经济发展,越地深藏于民间的文化因子被激活,民间文艺勃兴,最能体现越文化精粹和区域文化特色的要算地方戏曲和文学创作。祁氏家族不仅形成了浓郁的崇尚戏曲和诗文创作的氛围,而且,他们走向社会,与戏曲家文学家们广泛交流,同时也为地方文化的兴起推波助澜,做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山阴祁氏因“书香传家”而造就了藏书世家及其特色家学;他们秉承儒家的价值取向,从而,在明清之际的特定社会环境中树起了忠敏义烈的标杆;他们崇尚文学艺术,在诗意地栖居,祁氏大家庭文以化人,以高雅情操和审美观念,营造了优美的门风。此一家风传承样本,于今可资借鉴。
[1]祁彪佳.祁彪佳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郝亚飞,李紫烨.中国古代家风建设及其当代启示[J].河北大学学报,2015(1).
[3]周春辉.论家风的文化传承与历史嬗变[J].中州学刊,2014(8).
[4]杨绍溥.明季江阴祁氏家族述略[J].求是学刊,1993(6).
[5]钱亚新.浙江三祁藏书和学术研究[M].南京:江苏省图书馆学会,1981.
[6]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赵素文.祁彪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林东明)
The Family Tradition and Its Regional Inheritance of the Distinguished Book-Collecting Clan Qi in Shanyin
Xu Jingwei
(Library,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The book-collecting family, Shanyin Clan Qi, has been famous for their collection of books for three generations and has showed the attractive features of the family traits heritage as well. Namely, Clan Qi’s basic style of family traits heritage is to collect books and hand them dow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Clan Qi’s value orientation is to hold family together with loyalty; Clan Qi’s main state of family traits heritage is to make family happy with arts and literature. With Yue culture genes, Clan Qi’s tradition has its own unique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cluding the times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still worth learning today.
book-collecting clan; three Qi’s; family characteristic; Yue culture
10.16169/j.issn.1008-293x.s.2017.02.006
G253:B823.1
A
1008-293X(2017)02-0045-05
2017-01-11.
许经纬(1977- ),女,浙江绍兴人,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地方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