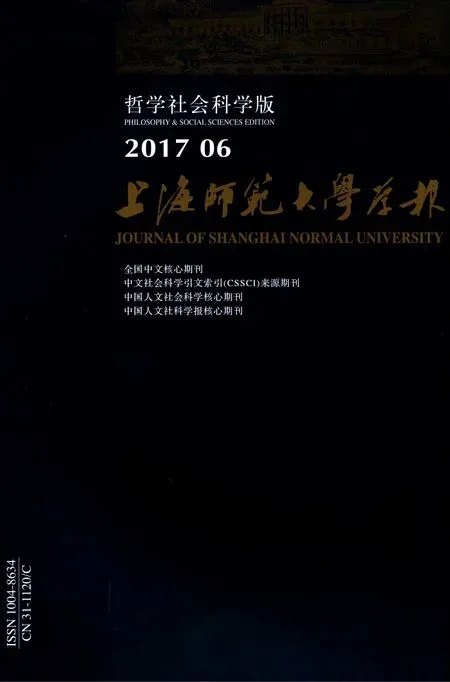国学在21世纪的弘扬和发展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考量
2017-04-12崔宜明
崔宜明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国学在21世纪的弘扬和发展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考量
崔宜明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所谓国学,应该从学术研究的主观精神去理解,应该定义为特定的“意向结构”或者学术宗旨。中国人的意向结构是生成式的,“世界”的结构是“一本”的,这是一幅包容和成长的世界图景。西方人的意向结构是聚焦式的,“世界”的结构是“两分”的,这是一幅分裂和对抗的世界图景。着眼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根本的事情是在理论上揭明两种世界图景的不同,并且整合进法治、民主和自由等个人主义的观念来说明“世界”的结构是“一本”的,“大家”可以互相包容、共同成长。这是“国学”的历史使命,它包含守护和弥纶两方面的工作,而首先需要一场中华文明“人文”和“民本”的启蒙运动。
西学;国学;意向结构;世界图景;霸权主义;天下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学热”已经很有些年头了,但是何谓国学,则至今未明,需要深入讨论。所谓国学,当然不是指专为中国人所有、外国人几乎无法染指的学问,否则国学是中医中药、音韵目录等学科的相加之和了。其次,国学不是指专门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因为这门学问在西方叫作“汉学”。再次,国学也不是指以中国传统典籍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因为这门学问应该叫作“文献学”或者“古典学”。那么,什么是国学?笔者认为,所谓国学,不应该从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去理解,应该从学术研究的主观精神去理解;不应该定义为特定的知识门类或者学科形态,而应该定义为特定的“意向结构”和学术宗旨。也就是说,区分开国学和西学的是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心灵结构,这种心灵结构在时间上和逻辑上都在“哲学”之前,并且范导和决定了不同的世界观,然后才有了不同的知识形态和知识门类划分。
一
讲国学,必然是相对于西学讲的。所以,讲中国人的“意向结构”和学术宗旨,就只能在与西方人的“意向结构”和学术宗旨的对照中来讲。
所谓意向结构,指人在意识到世界之先、并且决定了人所意识到的世界是怎样结构的先验意向。也就是说,第一,人有意识,是因为已经存在着意向结构,人才能把世界作为自己的对象在意识中建构起来;第二,意向结构是先验的,从而决定了所意识到的世界的结构范式,使人对世界的经验得以可能,所以,意向结构不能被人的经验证实或者证伪;第三,意向结构的先验性来自于不同民族历史生活的特殊性,是“文化”的固有本质,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生活决定了不同的意向结构,由此,不同民族所意识到的世界就是不同的,首先是世界的结构范式是不同的。
自先秦以来,中国人的意向结构是生成式的,即从意向出发,把所经验到的外部现象都理解为“自我”;于是,“世界”的结构是“一本”的:敬天保民、存心养性事天、天人合一,等等。这是一幅包容和成长的心灵图景。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人的意向结构是聚焦式的,即以意向为中心,把所经验到的外部现象理解为“对象”。于是,世界的结构是两分的: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等等。这是一幅分裂和对抗的心灵图景。[1]
不同的意向结构决定了所意识到的世界是不同的,也决定了价值观念的不同和思想理论学术宗旨的不同。
源于“一本”的世界,宗旨是:安身立命、家国情怀和天下大同。源于“两分”的世界,宗旨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霸权主义。
生成式的意向结构决定了中国人把经验到的外部现象都理解为“自己”,那么,“自己”永远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随着所经验到的外部现象不断拓展和深化,“自己”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之中。这就产生了一个无可逃避的根本问题:何以安身立命?
聚焦式的意向结构决定了西方人把经验到的外部现象都理解为“对象”,那么,“自己”也通过“对象”被定义了。这也产生了一个无可逃避的根本问题:怎样才能通过对“对象”的攫取来充实和发展自己?
对中国人来说,找到安身立命的基点就能够去充实、发展和实现“自己”,而最切己的途径就是“家”。“家”的存在不仅是“自己”的血缘所来之根和血脉延续之本,也是“自己”的当下生活,离开了“家”,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虽然“国”的存在要疏远些,但是生成式的意向结构决定了中国人只能是按照“家”的方式来理解“国”,所以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P16)更何况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数次与异民族的生死较量让中国人痛切地感受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3](P2939)“国”破“家”何存?总之,“国”无非就是“大家”,每一个中国人组成的“大家”。
对西方人来说,虽然“家”的存在也是血缘所来之根和血脉延续之本,但是这些不过是属于“对象”世界的事情。对于古希腊时代的雅典人来说,“家”是卑微不足道的“私域”,作为“公域”的城邦才是自己的生活舞台;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4](P7)进而,聚焦式的意向结构决定了西方人理解到的“国”只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国”不过是利己主义者结合起来共同攫取利益的绞肉机。当然,也正是通过“国”,利己主义者成长为个人主义者,他宣称:个人是至高无上的,是这个宇宙的终极存在!也就是说,所谓个人主义,不是通过单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通过单个人和“国”的关系被理解到和被定义的。
对中国人来说,在家国情怀之后,接下来是追求天下大同。当然,这只能是理想,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所希冀的最高理想。家国之事已然让人焦头烂额,以至于中国人从来没有讲清楚天下大同是怎么一幅景象,又怎样才能实现天下大同。今天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礼记·礼运》中的那段文字,不过是秦汉之际二、三流儒生的作品,无论是理论思维的水平还是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离孔子、孟子和荀子的距离不可以道里计;思想史的实际是:孔子、孟子和荀子这三位先秦儒家宗师偏偏没有一个字谈及天下大同。但是,只要中国人的日子好过一点,总会情不自禁地向往天下大同。
对西方人来说,天下大同是不可理解的。秉承着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我”与在“我”之外的“世界”处在永恒对立之中:第一,“我”的利益和其他人的利益总是不同的,所以,“我”与这个“国”中所有他人在“国”之中相对立;第二,唯有在“我”的“国”与其他“国”相对立的条件下,“我”才能与这个“国”中所有他人的利益相一致。所以,在国家关系中只有一个目标:称霸。
为了称霸,就必须要有敌人。如果没有外部敌人,“高尚”的个人主义就会蜕化为“恶俗”的利己主义,就会在“国”的内部出现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国”就会分崩离析。所以,即使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来。
有一件被西方人当作宝贵历史财富和伟大精神遗产的事情值得中国人牢牢记住。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地中海世界两强并立:罗马和迦太基。老加图——此人被古罗马人当作人格的典范——在公元前175年目睹了迦太基的繁荣富强以后,他“所有在元老院的演说,不论讲的什么题目,皆以一句严厉的信念作结:‘还有,我想,迦太基必须歼灭!’”[5](P146)而迦太基也终于在公元前146年灭亡于罗马人手中。
二
当然,上述中西思想理论学术宗旨的种种不同是就其“主流”而言的,中西文明都是伟大的,其思想学术传统非常丰富而复杂,以至于可以说:凡是“主流”的主张,必定有“反主流”的主张与之对立,相辅相成,砥砺前行。就像共产主义学说诞生于西方的霸权主义传统中一样,中国人以“何以安身立命”为人生的根本问题,却并不能消解“何以养家糊口”这个人生切要问题。“利己”同样是基本的生活态度,“利己主义”同样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如杨朱和韩非的学说。
要认真地讨论问题,就只能着眼于“主流”而暂时悬搁起“复杂性”,虽然人类的相通性正体现在这些“复杂性”中。但是如果说不清中西文明的差异性,人类的相通性就更说不清楚了。
源于聚焦式的意向结构,存在着的“世界”已经是“两分”的了: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等等。那么,为了通过对“对象”的攫取来充实和发展自己,认识对象世界就是第一要务。进而,因为存在着的“世界”是“两分”的,所以,对对象世界的认识是如何可能的?存在于对象世界之外并且与对象世界相对立的人,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就成为认识对象世界首先要搞清楚的事情。于是,认识论问题成为贯穿于西方哲学史中的一个基本主题。
古希腊人提出了理性精神,认为依靠纯粹的理性就能够“客观”地认识对象世界;而所谓纯粹,就是尽可能地排除人的感情、情绪和习惯观念等的干扰,尤其是不能有丝毫的功利考量。由此,认识对象世界以自身为唯一目的的观念被确立,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为科学而科学。这里确实有非常了不起的东西。因为对于西方人来说,那个无可逃避的根本问题是:怎样才能通过对“对象”的攫取来充实和发展自己?可是,古希腊人却做到了:为了更好地攫取“对象”来充实和发展自己,就必须在认识对象世界的整个过程中彻底排除掉功利的考量。
这一意义上的理性精神是西方文明的终极力量。
利己主义的宗旨决定了对对象世界的认识要服务于攫取“对象”来充实和发展自己,于是,与古希腊人不同,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近代西方人把科学转化为技术,科学与技术彼此携手促进发展,西方文明由此变成了强力的文明,没有任何文明在力量上能够与之抗衡。
利己主义的宗旨不仅决定了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也决定了经济体制的变化,这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在近代西方的出现、确立和发展。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都是靠砍砍杀杀来牟利的,中世纪的贵族骑士们更是把砍砍杀杀上升为一种特权和荣耀。但是,客观的、冷静的和理性的利益计算表明,做生意能够带来更大的尤其是更加稳定的利益。于是,古老的、零星的市场交易发展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与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创造了匪夷所思的生产力,创造了匪夷所思的物质财富。
当然,不能把这一切算到“恶俗”的利己主义头上,这应该是“高尚”的个人主义的功劳。
严格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一道在西方近代历史中诞生。相应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冷静的利益计算表明,尽可能地遵守契约符合每个人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于是,契约精神诞生了,并且被理解为是一个人是否具有人格尊严的标识。进而,契约精神也是一个国家的国格尊严的标识,这就是所谓法治国家的要求:既然任何人都以自身利益为最高原则,都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人生信条,而不惜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必须用法律来限制统治者利用公权力来谋取私利,尤其是防止他们串通一气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于是有了依法治国的核心理念,有了任期制、分权制和代议制等制度建构。也就是说,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同样是契约精神的产物,它与市场经济制度相呼应,既限制、也满足了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些东西既包含着冷静的利益计算,也具有精明的妥协意愿;既可以说它们“恶俗”到除了个人利益之外世界就是一片虚无,也可以说它们“高尚”到高扬起人的“自由”的旗帜。
个人主义的核心理念是:自由。正如100多年前严复说的“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6](P23)那样,近代西方社会是以市场经济制度为其经济基础,以民主法治为其上层建筑,而人的自由则借康德的话来说是整个大厦的“拱顶石”。[7](P2)
“高尚”的个人主义来自和服务于“恶俗”的利己主义,既是对利己主义的约束,也是对利己主义的升华;既肯定和满足了人的物质欲望冲动,又鼓励和提高着人的精神境界追求。这是西方文明对人类文明做出的独特的伟大贡献。但问题在于,还有一个蛮横的霸权主义。
人类近代历史的基本情况是:每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都作为一个“自己”与外部世界相对立,都必须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攫取来充实和发展自己,都必须与整个外部世界为敌。当然,在还没有强大到与整个外部世界单打独斗之前,结盟就是必然的选择。结盟就是组成一个虚拟的“自己”,共同去攫取外部世界;可惜的是,这个“自己”是虚拟的,在现代民族国家之间根本不存在基本的、稳定的共同利益。所以,在近代以来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永远在上演着重新排列组合的结盟游戏。还是近代以来最老的“玩家”英国人说的最坦率:没有永恒的敌人和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不过,就算是英国人也没有说过霸权主义的游戏是怎么玩的,也许这属于祖传秘方,不可示人。但实际上并没什么特别的奥秘,说穿了不过如此。
例如,如果我具有强大的经济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最有利于我的就是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市场,也就是经济全球化。我置身于全球经济产业链的高端以获得超额利润,这是霸权的最高境界。
但是没有任何霸权是一劳永逸的,即便是霸权的最高境界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总有人借势经济全球化而发展他的经济生产力和科技实力,以至于也慢慢置身于全球产业链的高端——这意味着我的霸权即将丧失。但是,我在经济上能够做的十分有限,除了在细节上尽可能地给那个人增加麻烦和困难以外,我不能放弃经济全球化的努力,否则也是一个输家。
好在我还有“高尚”的个人主义,有民主、法治、人权和自由这些观念的武器。我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来妖魔化那个人,只有在那个人被我成功地妖魔化以后,我手中号称打遍全球无敌手的军队才能派上用场。
总之,经济生产力、科技实力和军队实力是我的硬实力,民主、法治、人权和自由等观念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是我的软实力。
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一方面玩好排列组合的结盟游戏,一方面玩好把制造出来的敌人妖魔化的游戏,叫作巧实力。如果说西方世界两千多年玩的就是霸权游戏,那么,巧实力是当代霸权主义者的新玩法。
可是,中国人不玩霸权游戏。如果中国人玩霸权游戏,那输定了。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人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暂时都不如别人的,更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玩过这个游戏,不会玩。那么,中国人究竟擅长什么?又怎么应对躲不掉的霸权游戏?这就要回到“国学”这一主题上来了。
三
经过了汉唐盛世,自宋至明清,中华民族的运势走的是一条下坡路,其典型表现之一是有清一代的士大夫们致力于训诂考据之学。虽然他们从事的是“守护”中华文明的事业,但事实毕竟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萎缩进了故纸堆。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入侵,没有人知道接下来的事情会怎么样,历史无法假设。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成为西方人的“对象”,不堪一击而一败涂地。可是,100多年过去了,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成为让霸权主义者感到芒刺在背的“那个人”了。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变化的合理解释是什么?
这是一个够将来的学者们研究几千年的题目。但是,有一点是今天就可以明确的:中华文明的优越性是根本原因。
从历史过程说,亡国灭种的危险激活了中华文明。首先是士大夫们(后来逐渐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从故纸堆中回到了现实生活,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社会总动员开始了,从“万马齐喑究可哀”到“每一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这里发生的事情是:从西方接受来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描绘出一幅天下大同的美好图景,饱受屈辱和无尽苦难的生存境遇激发出家国情怀的生死斗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被建立为安身立命的终极指向。于是,梁启超看到了“少年中国”,郭沫若看到了“凤凰涅槃”。
从心灵结构说,中国人的突出优势在于无与伦比的学习能力。中国人的意向结构是生成式的,那些异域的东西,世界上其他的民族文明形态,对于中国人来说,都不是“对象”,不是“他者”,而是“自己”。中国人乐于、也善于学习其他民族文明中的好东西,鲁迅称之为“拿来主义”。历史上最著名的案例是中国人从当时的“西方”印度“拿来”了佛教,并且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
近代以来100多年,中国人一方面和西方文明的侵略与欺凌做着殊死的斗争,一方面贪婪地向西方文明学习。时至今日,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有数不清的向西方学来的东西已经被中国人当作属于“自己”了。
中国人学来了科学技术,学来了市场经济制度,学来了依法治国的理念和制度建构方法,学来了民主政治的理念,并且探索着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建构途径,等等。通过学习,中国人的“世界”越来越大、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美好;通过学习,中国人“自己”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踏实、越来越大度。这一切都只能从中国人的心灵结构和原初的意向结构中得到说明。
但是,相应于历史上的佛教中国化,西方文明的中国化还远远没有完成,而这正是“国学”的使命:本于安身立命、家国情怀和天下大同,汲取西方个人主义的精华,限制利己主义和消解霸权主义。
在当今世界,思想领域的主要矛盾之一是中国人的天下大同宗旨与西方人的霸权主义宗旨的冲突。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甚至吊诡的矛盾冲突,远比你想要霸权、我也想要霸权意义上的矛盾冲突复杂而难解。
在中国人看来,自己根本不想称霸世界,中国人追求的是人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天下大同,西方人为什么要把中国人当作敌人呢?可是,要让西方人懂中国人的意思是不可能的。就像不可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不可能让具有聚焦式意向结构的西方人“听懂”天下大同——其心灵结构是:处在必然对立关系中的我和对象世界。
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已经习惯了一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中国,已经把自己的霸权当作是天经地义了。对于发展起来的中国很不适应,对于中国人恢复自己本来权利的主张和行动很不适应,他们认为是与他们争夺霸权。
这里的事情有些复杂,值得多说几句。西方人在自己国家内部搞民主、法治和自由是认真的,这些东西不仅是他们的立国之本,也给他们带来了国力的强盛;但是,他们在外部世界推行这些东西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些东西不过是、也只能是维护霸权的工具。事实上,他们既可以与世袭君主制国家结盟,并且尽心尽力地帮助维护其君主专制制度;也可以为了推行所谓“民主制”,用各种手段,直至用武力去颠覆一些国家的政权;这都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为了自己的霸权。西方人在某些时候会遵从和维护国际法的规则,这是因为遵从规则能够带来利益,而维护规则就是维护霸权;他们也在某些时候玩弄和颠覆国际法的规则,这是因为遵从规则有损利益,那么,为了维护霸权就必须玩弄和颠覆规则。
心地善良的人会指责西方人搞双重标准,这种指责的时间已经够久且数量已经够多了,但是,这丝毫不妨碍西方人我行我素。其原因就是这种指责在西方人看来非常可笑,他们心里在说:民主、法治和自由等东西都是我们的利益工具,我们的立场是始终一贯且逻辑自洽的,何来双重标准?
着眼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对于中国人来说,根本的事情是在理论上揭明两种世界图景的不同,并且整合进法治、民主和自由等个人主义的观念,从而来说明“世界”的结构是“一本”的,“大家”可以互相包容、共同成长。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法治、民主和自由等个人主义观念已经是“自己”的了,但还需要把它们落实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以至于用法治、民主和自由等个人主义观念来向西方人解说天下大同。这是唯一可以让他们听懂的语言。
这件事情是“国学”的历史使命,具体地说,这一使命包含两方面的工作:守护和弥纶。
第一,守护。前文说到,有清一代的士大夫们致力于训诂考据之学就是在“守护”中华文明。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守护的事业变得复杂、纠结而胶着。既有王国维、陈寅恪那样“保守”的守护;也有胡适那样在主张“全盘西化”的同时,醉心于新考据学的“激进”的守护;还有鲁迅这样既有“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8](P12)的痛彻,也有十年与碑帖为伍的沉静,在“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期待中成就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一生守护。所谓国学,就在与西学的碰撞、交流和融汇中被意识到,虽然它究竟是什么,至今还是不清楚。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儒家有个沉甸甸的词——“天命”,指在历史过程中的中华文明传统和国运的兴衰。所谓国学既然在中华文明危亡之际被意识到,在求生存、求发展的风云际会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在成为让霸权主义者感到芒刺在背的“那个人”的今天,就必须承担起重塑人类文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这就是天命!
国学是中华文明的永远的守护者,当然,怎么守护则随着国运的兴衰变化而不同。尽管中医中药、音韵目录、碑帖金石、简帛文献等研究是基础性的守护,但是在今天,更加重要而迫切的守护是在与西方文明的对比中揭明中华文明独特的心灵结构和世界图景,以及通过对五千年历史经验的总结,尤其是通过对100多年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揭明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独特优势和发展趋势。
这一意义上的守护要求有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对国人进行中华文明的启蒙。1919年的“五四”开启了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启蒙运动,但是还远没有完成;如果说“五四”运动是西方文明的“科学”和“民主”的启蒙,那么,在百年后的今天,要完成的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和“民本”的启蒙。当然,新的启蒙是上一次启蒙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否定和对抗。
第二,弥纶。《易大传·系辞上》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9](P511,P513)弥者,遍也;纶者,络也;《周易》之道,天地之道也,无所不至而无所不赅,故能包容一切。汲取西方文明之精华,把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发展到新的高度(如当年佛教之东来),是国学的根本任务和目标。
当然,这件事情意味着描绘出新的世界图景,意味着生成式意向结构和聚焦式意向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整合,意味着形成了以包容和成长为人类生活最高准则的人类共识,所以是极其困难的。但这就是国学的历史使命,虽然没有人能保证一定会成功,但是只要我们做到了守护而不抱残守缺,弥纶而不凌空蹈虚,就大有希望。
[1] 崔宜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质[J] .船山学刊,2017,(5).
[2] 杨伯峻.孟子译注·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 司马迁.史记·第九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5]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上[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6] 王栻.严复集·第一册 [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8] 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济南:齐鲁书社,1979.
OnthePromotionandDevelopmentofGuoxuein21stCentury——BasedonCommunityofCommonDestinyforMankind
CUI Yimi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Law and Politic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The so-called Guoxue (studies of Chinese arcient civilization) should be understood from the subjective spirit of academic research, which also should be defined as a specific “intention structure” or academic purpose. The Chinese intention structure is generative, and the structure of “world” is “one”. This is a world view of inclusion and growth. The Western intention structure is focused,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ld” is split into two. This is a world view of division and confrontation. Focused on the general trend of huma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fundamental thing is to revea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world views in theory, and integrate into individualistic concepts such as rule of law, democracy and freedom to show that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ld is “one”, and make people understand that we can tolerate each other and grow together. This i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Guoxue, and it contains two aspects: guarding and promoting. Above all, an enlighten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bout “humanities” and “people-oriented” is required.
B2
A
1004-8634(2017)06-0012-(06)
10.13852/J.CNKI.JSHNU.2017.06.002
2017-07-01
崔宜明,安徽桐城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和伦理学研究。
Western learning, studies of Chinese arcient civilization, intentional structure, world view, hegemonism, great harmony,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mankind
(责任编辑:何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