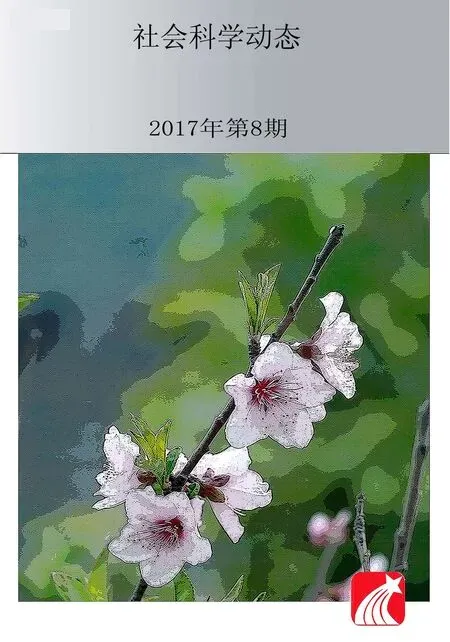2016年澳大利亚及欧华文学研究概况
2017-04-12欧阳光明
欧阳光明
2016年澳大利亚及欧华文学研究概况
欧阳光明
澳大利亚与欧华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区域的华文创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2016年的澳大利亚与欧华文学研究依然在稳步推进,从理论探索到作家作品研究、从文学现象的阐释到文学会议的召开,都有新的收获。理论视野在探索与论争中不断扩大;对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研究在2016年的澳大利亚及欧华文学研究中占有较大比重。没有微观方面的作家、作品分析,就不可能对某一区域、某一文学的存在形态进行理论上的归纳与建构;华文文学会议的召开,对于华文文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也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澳大利亚及欧华文学研究;理论视野;文学现象;文学会议
澳大利亚与欧华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区域的华文创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2016年的澳大利亚与欧华文学研究,依然在稳步推进,从理论探索到作家作品研究、从文学现象的阐释到文学会议的召开,都有新的收获。
一、理论视野在探索与论争中不断扩大
对于一个学科来说,理论视野的开拓,直接关系到该学科的发展走向,它不但显示了该学科研究的意义和发展空间,而且对该领域的研究起到了规范和指导作用。正是因为这样,在澳大利亚与欧华文学的研究过程中,理论探索一直是学者们重要关注的对象。当然,研究者们对于理论视野的拓展、研究范式的探索,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一区域性文学,而是在更宏大的层面上,使理论思考带有更普遍的意义。因此,澳大利亚与欧华文学的理论探索,很大程度上也是放在华文文学这个层面上展开的。
“海外华文文学”的属性与归属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从众多的论述当中,大致可归纳出以下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倾向于将它视为独立的文学存在形态,或者视为所在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它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延伸,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持这两种不同意见的学者,似乎都能找到充足的理由,并进行严密的逻辑论证。但是,海外华文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特征,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因此,这种属性之争,一直延续了下来。
2016年, 《中国比较文学》第3期,刊发了陈思和的 《旅外华语文学之我见——兼答徐学清的商榷》和徐学清的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的杂糅——与陈思和商榷》两篇商榷性文章,再次将这个 “熟悉”的问题展现在人们眼前。事情的缘起,是陈思和在加拿大 《世界日报》的文艺副刊 《华章》 (2014年12月26日) “名家谈——华人文学之我见”专栏所写的短文 《旅外华语文学之我见》中所发表的对 “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的见解,认为 “中国大陆或者台港地区的第一代海外移民作家”的创作,本质上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在 《旅外华语文学之我见——兼答徐学清的商榷》这篇文章中,陈思和继续坚持这一观点。文章中陈思和指出, “‘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相当混乱。在我看来,它至少包含了两类互不相干,甚至自相矛盾的文学:一类是从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去外国 (主要是北美、欧洲)发展的作家的华语创作;另一类是东南亚国家华侨作家在自己国家里的华语写作”。在陈思和看来,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形态,第一类,也即 “中国大陆或者台港地区的第一代海外移民作家”,无论是语言(中文)、审美情感 (民族性)、所表述的内涵,都与母国文化构成了直接的继承关系,因此, “从本质上说,旅居作家构成的华语文学只是在世界交流频繁过程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一脉支流,它是当代文学的有机构成”。在面对徐学清的 “商榷”和“质疑”时,陈思和也给予了明确的答复, “文学的本质是由语言构成的美学文本,其实与作家的国籍有何干系?……与其无法落实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还不如淡化国籍而强化语言,形成一个丰富而多元的 ‘中国当代文学’”①。
对于陈思和的这种观点,徐学清显然有不同的意见,她认为, “海外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在世界性的文化地理位置上,各自呈现文化原乡/异乡的杂糅,由丰富的第三元组成万物众生象”。 “华文文学鲜明的在地性和强烈的时间性决定了它的不可取代的个性,使它成为中国文学的大叙事之外的华语文学。”②这里,徐学清强调的是 “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性,而不是对母国文化的传承性。因此,文章得出 “它成为中国文学的大叙事之外的华语文学”这一结论,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从某种程度上看,陈思和与徐学清的分野,可视为中国本土学者与海外学者研究立场与视野的区别。中国本土学者对各种不同的海外华文文学存在形态,有着清楚的认知,对其复杂的审美内涵,也有着明确的把握。因此,在分析具体的文学形态时,他们并非进行笼统地概括,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外,尽管各地区的汉语文学形态具有不同的文化诉求与审美内涵,但是,也同样具有精神上的联系,因此,中国本土学者也在寻找整合性研究的基础。这在黄万华、刘俊、朱寿桐、洪治纲等学者的研究中都有显著的表现。朱寿桐近些年来提出的 “汉语新文学”,也是这种整合性研究的重要成果。
朱寿桐和陈瑞琳在2016年发表的 《汉语新文学的传统及其世界意义》一文中就曾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走出国门进行文学创作,如果一味机械地运用地区、国家的方式来界定这一复杂的文学现象,将难以把握其内在本质。所以必须寻找一种新的研究视界,既能超越特定的国家、政治的限制,又能揭示出文学的内在本质,而 “汉语新文学”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汉语新文学最能够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避免在国家、政治归属的意义上去界定现在越来越多的海外写作者。这些人实际上不一定就是 ‘海外’写作者,只不过他的文学活动空间是在海外罢了。现在我们非常开放了,作家文学活动空间所呈现的归属地很难用一个地区、国家来框定,所以在这方面,从语言的角度使用汉语文学或汉语新文学这样一种概括方式,可以不至于有歧义。” “汉语新文学的文化价值功能就是走 ‘统一起来’的道路:无论是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澳洲等,只要用汉语写作,只要在汉语文化圈实现交流的职能,就属于这样一种文学样态。这样一种样态现在没有办法用 ‘中国文学’来概括,那么就只能用汉语语言文学来概括。”③以语言为基础来整合世界各地区出现的汉语文学形态,确实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可以最大程度地排除由命名带来的混乱,进而把握其内在本质,最终有利于推进汉语整体文学的建构。
而海外学者则在各种 “后”学思想、特别是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下,极力推崇 “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立性。为此,他们提出了较具理论创见也带有明显缺陷的 “华语语系文学”这一概念,集中表达他们的理论诉求。自从史书美提出 “华语语系” (Sinophone)这一概念,用于研究 “发生在中国大陆之外的以华人和华语为主体的文艺实践,包括电影、美术、文学等等”之后④,迅速得到了海外学者的认同与推广。王德威曾连续发表了 《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象与越界建构》、 《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 《中文写作的越界与回归——谈华语语系文学》等文章,大力实践这种理论范式。虽然王德威在使用“华语语系文学”这一概念的时候,对史书美的一些论述进行了重新解释,但这种理论视野所运用的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研究方式,鲜明的 “去中心”、 “反本质”主义的学术理路并没有改变。随后,国内一些学者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梳理与辨析。如李凤亮、胡平的 《“华语语系文学”与 “世界华文文学”:一个待解的问题》、刘俊的 《“华语语系文学”的生成、发展与批判——以史书美、王德威为中心》、朱崇科的 《华语语系的话语建构及其问题》等,这些文章一方面分析了 “华语语系文学”这一概念的理论创见,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其存在的学术缺陷与偏见。
2016年,王德威发表了 《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继续他的理论实践。国内学者也对此进行了跟踪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李相银、陈树萍的 《国际视野与本土能力——“世界华文文学”、 “华语语系文学”与 “本土批评”》、刘俊的 《“世界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视野下的 “新华文学”——以 〈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为中心》、刘大先的 《“华语语系文学”的虚拟建构》,以及李杨的 《“华语语系”与 “想象的共同体”:解构视域中的 “中国”认同》等。这些文章一方面继续对 “华语语系文学”这一概念的理论局限保持警惕,一方面又展现出包容与理解的态度。正如李杨所说的那样: “我们无法为其贴上一个 ‘去中国化’的标签就将其扔进 ‘历史的垃圾桶’了事。事实上, ‘华语语系’的价值取向并非如同我们所批评的那么简单。”⑤
庄伟杰在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现状、相关问题与拓展境域之思》一文中,也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属性进行了论述,认为 “作为一个边缘化文化谱系,它虽然不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却是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一种世界性延伸或拓殖”。并且通过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现状的考察,认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真正自觉时代刚刚到来”,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如 “学术批评的总体价值评判缺乏统一的标准或尺度”、 “研究错位”等问题,因此, “要寻求新的创作与阐释空间,一方面要着力拓展一片宽广的学术境域,另一方面要建立一种多元的、立体的、开放的、互动的华文文学研究的诗学对话”。还要超越种种既定的论述框架,先在观念的束缚, “自觉地从华文文学的内在逻辑发展中寻求建立华文文学史的叙述脉络”⑥。肖淳端的 《英国华人文学:学理命名与指涉内涵》,根据英国华人文学所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对 “英国华人文学”这一命名进行学理性考辨,并界定了其内涵,同时指出“‘英国华人文学’这一指称既客观反映目前英国华人文学的发展现实,又高度体现英国华人群体的认同意识,也彰显了其与华裔美国文学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主题特征上的鲜明差异”⑦。这为人们加深对“英国华人文学”的认识与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论视野的探索与拓展,将一些曾经模糊的、歧义纷繁的、甚至被遮蔽的问题展现在研究者面前,并在论争与辨析中不断廓清迷雾,突显出内在的肌理与脉络,建立新的研究范式。这对推进澳大利亚与欧华文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二、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研究
对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研究,在2016年的澳大利亚及欧华文学研究中占有较大比重。事实上,文学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很大程度上是在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深化的结果,没有微观方面的作家、作品分析,没有对文学现象的宏观把握与阐释,是不可能对某一区域、某一文学的存在形态进行理论上的归纳与建构的。
从文学现象研究方面来看,有刘红林的 《从移民角度看中国丝路文化在澳洲的传播与发展》、黄晓敏的 《从华人法语女作家的创作看跨界文学》、戴瑶琴的 《论海外 “70后”华人作家的文学想象》、荒林与陈瑞琳的 《全球视野下的汉语女性文学》、施文英的 《欧洲华文文学的困境与发展》,以及万灿红的 《德国华裔移民文学简介》等文章。
刘红林的 《从移民角度看中国丝路文化在澳洲的传播与发展》,以移居澳大利亚的新疆人群体为考察对象,通过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展现了这一族群丰富多彩的族群文化,并对他们作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为中国丝路文化在澳洲的传播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黄晓敏的 《从华人法语女作家的创作看跨界文学》一文,从性别的角度,阐述了华人女作家跨界文学创作的现状。第一部分梳理了华人法语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 “女作家的贡献及写作特征”,重点分析了山飒、应晨、魏薇、杨丹、黄晓敏、金丝燕等女性作家的作品,把这个独特的写作空间及其特征呈现了出来。
戴瑶琴的 《论海外 “70后”华人作家的文学想象》一文,虽然不是专论澳大利亚与欧洲 “70后”华人作家的创作,但从文章理论的角度来看,显然是将其包括在内的。文章在比较研究中,认为海外“70后”华人作家倾向于向 “传统和民间寻根”,以“平民为关怀对象”, “作品中流转着自由的观念和节制的感伤”,并且 “缺乏驾驭宏大叙事的文学力道”。这样的概括虽有些片面,但也提供了一种阐释的视野。荒林与陈瑞琳的 《全球视野下的汉语女性文学》,从 “当代女性创作何以在海外华文文坛占突出地位?” “国内与海外的女性文学生态是否有很大不同?” “今天的全球汉语女性文学呈现出怎样的版图?” “面对网络时代,女性文学将如何迎接挑战?”等四个方面,对全球化时代下的汉语女性文学的存在现状、创作优势、创作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宏观上的把握,视野开阔,论述简洁。这为建立全球汉语女性文学的整体研究,提供了一种阐释的方式。
施文英的 《欧洲华文文学的困境与发展》一文对欧洲华文文学存在的困境进行了一番梳理,认为“欧洲华文文学发展迟缓”的原因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生存压力限制创作”、 “读者成为少数民族”、 “媒体助力日益薄弱”、 “华文写作题材狭隘”、 “作品自我确认模糊”。总结了原因之后,作者对欧洲华文文学的发展提出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对策: “善用欧洲文化特色”、 “在社会变化发展中继往开来”、 “运用双语写作”、 “设立华文或双语学校”、 “抱持全球观”。文章的视野较为宏大,但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却显得力有未逮,甚至出现了自我矛盾的现象。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欧洲华文文学面临的困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向。万灿红的 《德国华裔移民文学简介》,则对德国的华裔移民文学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介绍了周仲铮、周春、关愚谦、海珮春、王小慧、罗令源等人的创作。但文章仅仅满足于简单介绍,因而既无法展现德国华裔移民文学的整体面貌,也无法深入揭示华裔移民文学的独特审美特性和文化诉求。
从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来看,黄万华的 《大隐隐于西:从程抱一创作看中华文化和欧华文学》,通过全面考察程抱一的创作与精神追求,展示了程抱一致力于沟通中西文化的努力和抱负。文章认为,程抱一在生命感受的基础上,超越了二元对立的观念,并提出了 “三元思想”,这是道家和儒家共同之道,又与西方艺术思想有精神上的暗合相通,最终将 “三元论”提升为人类的宇宙观,从而既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获得了新的生长点,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精神资源,同时,也丰富了世界文化。
江少川的 《地球村视域下现代人精神世界的探寻——评林湄的长篇小说 〈天外〉》、戴冠青、叶婉婷的 《在欲望中挣扎的追求者——论 〈天外〉中的郝忻形象》、燕世超的 《论林湄小说 〈天望〉的复调叙事》、谢楚婧的 《繁华世景,奈何人性——论林湄长篇小说 〈天外〉的现实意义》这四篇文章,对荷兰籍华人作家林湄2014年出版的新作 《天外》,从内容到形式、从精神追求到现实意义、从人物形象到文化冲突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释。刘莉的 《在原乡和异乡中游走——虹影小说的跨国界书写及其意义》与杨杰蛟的 《个体叙事与自我认同——虹影与杜拉斯小说主题的文化解读》这两篇文章,则集中对虹影的小说进行了分析。刘莉的文章着重分析了虹影小说 “原乡和异乡的不同叙事,并揭示其作品的世界性意义”。而杨杰蛟的文章,则在比较研究中,从情爱、家园、历史三个方面,分析了虹影与杜拉斯之间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 “除了东西文化之间的差别之外,还与两人的主体精神建构和写作环境上的区别有直接的联系”⑧。
陈立峰的 《新移民文学的创伤记忆及其文化表征——以比利时华文作家章平的中篇小说 〈狗肉的道歉〉为例》,集中分析了欧洲华人移民在文化冲突的环境中所遭受到的创伤性记忆,也指出了西方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的偏见与歧视。王孟图的 《叙述者的魔术——高行健长篇小说的叙述人称之魅》,在分析高行健高超的叙事技巧的基础上,对高行健的 “叙事理念”、 “叙述主体 ‘否定之否定’的存在状态”、 “‘没有主义’式的深度哲学思考”等方面进行了深度阐释。陈秀端的 《兼传统与现代——赵淑侠小说的叙事结构》,也集中论述了赵淑侠小说 “缜密而浑圆”的叙事艺术,并指出她的小说结构,既有对传统叙事艺术的继承,也有对现代叙事艺术的开拓,从而展现出丰厚的艺术魅力与审美空间。
欧阳昱的 《把你写进诗:漫谈诗歌的全球写作》是一篇很有意味的文章,作者将在全球游走过程中的所见所闻,熟悉的陌生的,美好的丑陋的都写进诗中。跟着他的诗歌,我们的目光也铺张到了诗人曾经触碰过的地方。于是,东方的、西方的、南方的、北方的,各式风景,各式人群,都一一呈现出来。 “要 ‘把你写进诗’,也就是把人写进诗,包括素不相识的路人,即凡是能让我产生诗意的人,尤其是平头老百姓。诗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诗就是一个既要让诗人活、让大人物活,也要让从不见经传的人见经传,通过我诗而活下来。”⑨这里,诗人不但给我们分享了他的创作历程,他的诗意,他的视野与思想,也展示了他对诗歌的理解,对诗性的独特领悟。
阎纯德的 《法兰西天空下的文学中华——巴黎华裔女作家素描之一》,正如文章题目所显示的一样,是对法国华裔女作家的 “单色绘画”,或者说印象式的描摹与介绍,却缺乏学理性的研究,对她们文学的创作特征与审美特色,也缺少学理性的思辨。冯新平的 《个人生活和精神的困境——论薛忆沩长篇小说 〈遗弃〉》,从内容到形式,较为详细地阐释了薛忆沩的这部代表性作品。段榕的 《〈京华烟云〉:风雅的趣味,无法承载现实》,文章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解构了林语堂追求的 “风雅”趣味的价值,认为 “风雅”趣味只不过是在男性的 “超意识形态”的眼光下,对女性生命的想象性言说,因而无法反映真实的社会和人生,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对 “东方主义”的迎合。林楠的 《跨文化书写的可喜实践——解析德国华裔作家刘瑛的小说创作》,对刘瑛的创作进行了印象式点评,虽没有太多学理上的辨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刘瑛小说创作的魅力。
倪立秋2016年在 《文学教育》上发表了一组文章,从第1—12期,每期介绍一个海外华人移民作家。在这些华人移民作家中,来自欧洲与澳洲的有虹影、北岛、章平、欧阳昱等四位,即 《虹影:写实,是因为不满足于虚构》、 《北岛:摇诗橹漂泊异域,荡文舟回归故土》、 《章平:不愿苟且,努力追寻诗和远方》、 《欧阳昱:在中英双语之间自如游走》。文章夹叙夹议,既有作家主体情感的加入,也有理性的分析,将这些作家的人生经历、创作历程、作品特色进行了一番讲述和点评。这组文章或许不能称为严格的学术论文,但却在轻轻点染之下,展现了这些华人移民作家的丰富人生与创作魅力。
而秦贤次的 《民国时期文人出国回国日期考》这一组文章,共计5篇,分别发表于2016年的《新文学史料》第1、2、3、4期,最后一篇 “尾声与花絮”,则发表在 《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1期上。这是一组非常有意思的文章,作者在细致的史料挖掘与辨析的过程中,将民国时期多达70余位文人出国与回国的日期进行了考证,包括陈寅恪、林语堂、宗白华、冯友兰、陈西滢、章伯钧等。这些文人,可以说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一些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著作或者教程当中,也将其中一些文人的海外创作视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前奏。因此,对这些文人出国回国日期的考证,为今天研究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心路、所遭遇到的文化冲突,依然具有借鉴作用。
除了这些研究文章之外,还有一些作家访谈。如易晓明与奥地利华裔女作家方丽娜的访谈,以《在蔚蓝的天空下回望故土的百灵鸟——奥地利华裔女作家方丽娜访谈》为名发表于 《名作欣赏》2016年10期。他们围绕文学创作理念、移民经验、中西文化观念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这对于理解海外华文作家的精神文化诉求、审美观念等具有重要作用,也为解读他们的文学作品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
这些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研究,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澳大利亚及欧华文学的存在现状,也对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阐释,这为推进该区域华文文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三、华文文学会议
华文文学会议的召开,对于华文文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为此,饶芃子先生曾满怀深情地说道: “每次会议,都有新的论题提出,每次会议之后,都有新的成果问世,不断地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空间。从研讨的内容看,经历了海外华文文学的 ‘命名’,对海外华文文学 ‘空间’的界定、海外华文文学历史状况和区域性特色的探索、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关系探源、如何撰写海外华文文学史等重要问题,进而转入到世界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和世界华文文学史的编撰,以及从文化上,美学上各种理论问题的思考、追问。”⑩
2016年5月8日至15日, “欧华文学会首届国际高端论坛”在布拉格理查大学举办,来自世界各国的40余位华文文学作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除了中国大陆的华文文学研究专家之外,参加会议的欧洲华文作家有林湄、黄晓敏、施文英、余泽民、海云、李永华 (老木)、谢凌洁、林鸣岗、黄育顺等人。大会由欧洲华文文学学会会长、著名华文作家林湄主持。本次大会讨论的主题包括:“大时代中的 ‘欧华文学’”、 “‘欧华文学’的现状与发展”、 “个体命运与地球村里的机遇和思考”、“经典文本的经验构成”。2016年7月24日,在泰国曼谷帝日酒店举行的 “‘一带一路’与泰国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有来自德国的华文作家与学者与会,如沈奇、熊辉、叶霈琪等。
2016年11月7日, “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主办,暨南大学、广东中山市委宣传部协办。大会以 “华文寻根、文学铸魂”为宗旨,以 “中华情、民族梦”为主题,邀请海外、港澳台及大陆地区从事华文文学创作、传播、研究的文学界人士、影视剧编剧、网络创作人员等300余人与会。其中来自欧洲与澳洲的华文作家与学者50余位,包括澳洲的张奥列、胡仄佳、王世彦等11位,新西兰的范士林、林宝玉、郑月贞等11位,英国的虹影,法国的黄冠杰、梁源法、刘秉文、刘志侠、卢岚、施文英、杨咏桔等7位,德国的刘瑛、黄凤祝、宋新郁等11位;捷克的老木、李迅;匈牙利的李震、翟新治、张执任;俄罗斯的白嗣宏、左贞观,以及土耳其、比利时、瑞士的一些华文作家。
会议的召开,为世界各国的华文工作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一个相互学习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开辟了新的研究空间和课题,这对推动华文文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曾经,一些研究者在分析欧华文学面临的问题与困境时,总是为他们分散的存在、孤军奋战的状态而感慨不已,如施文英在 《欧洲华文文学的困境与发展》一文中,就曾认为 “华文作家人数稀少分散,大多是单打独斗,孤军奋战”,成为制约欧华文学发展的重要障碍。公仲在研究中也曾指出:“华侨华人在欧洲的地理分布,可说是 ‘小集中,大分散’。大分散是说百万人分散在全欧近30个国家之中。小集中即华人大多数人口集中在西欧英、法、荷、德等几个国家及东欧新移民较集中的国家之中。”这样的生存环境,使得欧洲的华文作家和研究者相互交流的机会比较少,从而限制了他们创作眼界的开拓和技巧的完善。另外, “欧华文学依托着浸润了数千年的中华文化的精神传统,又得天独厚地汲取了西方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的欧罗巴文化的营养,东方的 ‘儒、释、道’理念与西方的‘阿波罗精神’、基督教文明以及 ‘浮士德精神’,这在欧华文学中得到了一定的融合和体现,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世界文坛上的风景线。然而,又由于两种都具有千年历史的强大文化传统的保守性和排他性,致使欧华文学总是在 ‘万里长城’与 ‘马其诺防线’双重壁垒之间来来往往,艰难突围,这又是一种难得的世界文化新景观。”⑪这样的观点,也得到了吴奕锜、陈涵平等研究者的呼应。
钱超英也曾对澳洲华文文学研究滞后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该地区在历史上与中国近现代发展历程的相对疏远,和它在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直接关系中曾经无足轻重的性质;第二是由这种疏远和不重要而导致的对其文化面貌的资料收集不足,连带对其华人文化和文学过往和新近的发展也未予注意;第三是作为该地区主要部分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华人华文的文化表达直到九十年代以前都没有形成值得注意的规模;最后,第四,海外华人和华文文学研究的有效拓展,需要一种对全球文化转型的清晰认知和总体把握。”⑫这虽然是钱超英在世纪之交所提出的观点,到今天,十多年过去了,一些问题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观,甚至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但是,因为 “疏远”与交流不畅而导致的 “对其文化面貌的资料收集不足”的问题,或许依然是困扰澳洲与欧华文学研究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华文文学会议的召开,虽然不能彻底改变欧洲华文作家 “小集中,大分散”的生存状态,在一定的时期内, “孤军奋战”的局面还将持续下去,但是,至少能在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时间为这些华文工作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为他们获取信息与资料创造有利条件。
结语,或一种期待
相对于北美华文文学研究的盛况,2016年中国大陆学界对澳大利亚与欧华文学的研究显然沉寂不少,也缺乏一些影响力广泛的学术论文与学术著作,这与澳大利亚及欧华文学的创作实绩显然是不匹配的,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遗憾。
澳大利亚与欧华文学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看,并不逊色于北美华文文学。除了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外,其他的作家,也屡屡斩获一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学奖项。如1999年,程抱一发表的长篇小说 《天一言》,就获当年法国极有影响的费米娜文学奖;2001年,程抱一又荣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大奖和法国总统颁发的荣誉骑士勋章;2002年,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2005年, 《万有之东》列入法国著名的伽里玛出版社 《诗》丛书出版的诗辑,在法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戴思杰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小说 《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发行量超过了100万,英文平装本持续10周登上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畅销榜。第二部小说 《狄的情结》,获得法国文坛 “费米娜奖”,同时还提名法国 “龚古尔文学奖”和 “美第奇文学奖”两个文学奖。毛翔青曾三度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并先后获得了杰弗里·费伯纪念奖、霍桑登奖、福斯特奖、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张戎1992年获NCR图书奖,1993年获英国年度图书奖。虹影曾获 《英国独立报》2002年十大好书奖、 “英国华人诗歌一等奖”和意大利罗马文学奖等,其小说也被译成16种文字在欧美、以色列、日本等国出版。欧大旭的 《和谐绸庄》曾获得2005年惠特布莱德最佳小说新人奖,英国卫报最佳图书奖及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并入围当年布克文学奖。欧阳昱的诗歌创作也在国际上取得了重大影响力。等等。
文学奖项的获得,或许并不是文学价值的终极评判标准,但至少,获奖意味着这些作品得到了主流文学界的认可,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一文学领域创作的最高水平。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获奖作品,大部分都是用所在国语言创作的,这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内学界及时的跟踪阐释。但是,这些作家的创作,是澳大利亚与欧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得到学界的重视。澳大利亚和欧华文学研究的滞后原因众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技术上的问题会一一解决,剩下的,就是研究者利用各种条件,密切关注该地区的华文创作,书写出一批与该区域华文创作相匹配的研究论文与著作,从而全面开掘出这一文学形态的价值和意义。
注释:
① 陈思和: 《旅外华语文学之我见——兼答徐学清的商榷》, 《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3期。
② 徐学清的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的杂糅——与陈思和商榷》, 《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3期。
③ [澳门]朱寿桐、 [美国]陈瑞琳: 《汉语新文学的传统及其世界意义》, 《华文文学》2016年第1期。
④⑤ 李杨: 《“华语语系”与 “想象的共同体”:解构视域中的 “中国”认同》, 《华文文学》2016年第5期。
⑥ 庄伟杰: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现状、相关问题与拓展境域之思》,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⑦ 肖淳端: 《英国华人文学:学理命名与指涉内涵》,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1期。
⑧ 杨杰蛟: 《个体叙事与自我认同——虹影与杜拉斯小说主题的文化解读》,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⑨ 欧阳昱: 《把你写进诗:漫谈诗歌的全球写作》,《华文文学》2016年第1期。
⑩ 饶芃子: 《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概况》,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年第1期。
⑪ 公仲: 《“万里长城”与 “马其诺防线”之间的突围——欧洲华文文学新态势》, 《华文文学》2003年第6期。
⑫ 钱超英: 《“诗人”之 “死”:一个时代的隐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责任编辑 胡 静)
I206.7
A
(2017)08-0069-07
欧阳光明,华侨大学文学院,福建泉州,36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