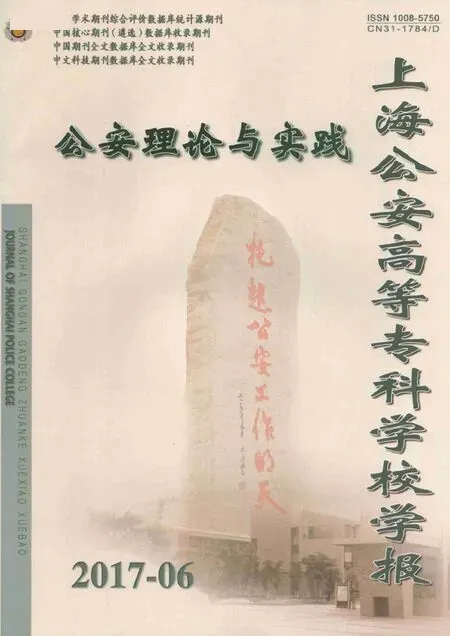新型支付方式下偷换二维码取财的定性分析
2017-04-11周淑芳
周淑芳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由于电子金融业务的流行和普及,以二维码支付、手机钱包等形式为特征的新型支付方式也开始成为人们日益青睐的面对面交易结款方式。相较于传统现金结算,这种新型支付方式更具有便利性、安全性。然而,在这一背景下也不可避免地共生出许多以此为载体的“新型”财产犯罪。其中,用于收款付款的“二维码”,以及移动通讯上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成为“新型”财产犯罪中的“重点关注对象”。不法分子通过偷换商家二维码、转移他人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等行为获取非法利益。然而,由于该类财产犯罪不同于传统犯罪,对犯罪行为的性质认定上具有不确定性,司法实践做法不一。如何对该类“新型”财产犯罪进行准确定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问题缘起
前段时间微信上广泛流传的偷换二维码案在刑法学界引起了不小的热议,学者们对此聚讼不已。大致案情如下:行为人甲趁店主乙不备,将店内用于收款的支付宝二维码偷换为自己的二维码,至月底结账时被店主乙发现,经侦查表明,甲通过这种方式共从几家店里获取了70万元。对于该案的定性,主要有盗窃罪和诈骗罪两种观点。在对该类犯罪进行定性时,学者更多的将关注重点放在谁是受害人的问题上,然而笔者认为,要认定行为人偷换二维码构成何种犯罪,理清谁是财物占有人以及是否具有处分财物的行为才是关键。
二、盗窃罪之否定
(一)财物占有人的确定
就偷换二维码行为如何定性,虽说主要是盗窃罪与诈骗罪两种观点,但在每种观点内部又存在着诸多分歧。主张盗窃罪的学者之中,有“普通盗窃说”与“盗窃罪的间接正犯说”之分,而主张诈骗罪的学者之中,有“普通诈骗说”、“双重诈骗说”与“三角诈骗说”等之分。主张盗窃罪的学者及部分主张诈骗罪的学者均认为,商家是财物的占有人。
占有既是法律上的十分重要的概念,但同时也是法律理论中争议颇大的问题,不仅在民法领域,在刑法领域更亦如此。刑法上的占有虽然不同于民法上的占有,但对刑法中财产犯的占有的认定离不开民法上对占有的界定。民法上的占有分为事实占有和观念占有。事实占有,是指行为人对财物所具有的物理上的、事实上的支配与控制。这种占有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仅从客观事实即可进行判断;观念占有,是指行为人并没有对物具有物理上的支配与控制,但根据社会生活的一般观念和习惯,能够推知财物由行为人支配与控制时,也可以认定行为人对该财物的占有。早期学者认为刑法中的占有仅限于现实占有,不包括观念占有。但现如今我国刑法学者均认同刑法上的占有不限于现实占有,又不完全等同于民法上的观念占有。与民法上的占有观念相比,刑法上的财产犯中的占有在对物具有更加现实的控制、支配的一点上具有特色。即民法上的占有可以是规范上、观念上的占有,而刑法上的占有必须是事实上的占有。这种占有并不是一般性的人和物之间的接触,而要达到实际控制、支配的程度。
本案中,商家并未占有顾客应当支付的资金。在顾客支付商品的款项之前,如果还没有完成扫码支付,那么钱款就一直在顾客的账户中,商家对顾客待支付的钱款就没有控制和支配。动产的转移占有以交付为标准,对于顾客即将支付还未支付的钱款,由于尚未交付这一事实,仍处于顾客的实际管理控制状态之下。有学者认为,偷换二维码的行为与在商家的钱柜里挖个洞没有本质区别,既然后者能够认定钱款已经由商家占有,前者也能作相同认定。然而,笔者认为,这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在商家钱柜里挖洞时钱已经由顾客转移到商家占有,即使商家的占有时间很短,只不过在放入钱柜的那一刻转移到了行为人手中。钱款在顾客支付之前处于顾客的支配状态之下,扫码支付之后由行为人占有,钱款从未进入过商家账号内,故商家无论是事实上还是观念上均未取得对钱款的占有。
另有一种主张构成盗窃罪的观点认为,在顾客扫码支付之前商品仍处于商家的占有之下,行为人秘密窃取与付款金额相当的商品。然而,客观上行为人并没有非法占有商品的行为,主观上也没有盗窃商品的故意,顾客错误支付的行为与行为人盗窃商品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并不存在盗窃商品的行为。
(二)是否存在处分行为
盗窃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从而骗取财产,造成他人损失,数额较大的行为。虽然盗窃罪与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财产权利的侵犯,但是二者在行为方式上并不相同:盗窃罪是行为人以秘密窃取的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诈骗罪是行为人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诈骗罪的基本结构是:欺骗行为→错误认识→处分财物→受有损失。诈骗罪是基于他人有瑕疵的意思表示取得财物 ,而盗窃罪是完全违背被害人意思取得财物的行为。在本案中,顾客扫码支付的行为是否能认定为财产处分行为也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关键。
处分行为是诈骗罪中的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指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使受骗人陷入错误认识从而“自愿”的处分财物的行为。有学者认为,行为人虽使顾客和商家陷入认识错误,顾客也处分了自己对支付平台的债权,但顾客的处分行为并非是因为陷入错误认识,而是基于买卖合同。也有学者认为,无论是扫码支付的顾客,还是指示顾客扫码支付的商家,都没有涉及将钱款处分给行为人的意识和行为。然而,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对处分行为的误解。这里的“处分财产的行为”的理解,不应当局限地理解为是否要处分财产,处分财产应当包括但不限于“是否处分、向谁处分、处分多少”内容。顾客扫码支付的行为与行为人非法占有财物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顾客之所以会“自愿”将支付平台里的钱款转移至行为人的账户之下,系因为行为人实施了偷换二维码的行为使得顾客陷入了错误认识,误以为其扫描的二维码是商家的二维码,从而作出了错误的财产处分行为。
在确定了扫码支付行为属于处分行为之后,则可以认定顾客自愿扫码支付的行为并不同于盗窃罪中违背他人意志转移占有的行为,故本案并不成立盗窃罪。
三、诈骗罪内部争议之评析
(一)三角诈骗说之理由及反驳
通常的诈骗案件中,被骗人与被害人属于同一个人,而在某些案件中,被骗人与被害人并不是同一个人,从而认定为三角诈骗。 “三角诈骗说”认为,本案中,受骗人是顾客,而被害人是商家,行为人实施了偷换二维码的诈骗行为,使得顾客陷入错误认识,误以为其扫描的二维码是商家的二维码,并且基于该错误认识处分了本属于商家的财物,行为人取得了财物,商家遭受了损失。依据三角诈骗的说法,客观上顾客处分了属于商家的财物的行为,主观上顾客因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了财物。
三角诈骗成立的前提,要求被骗人处分的是被害人的财产而不是自己的财产。然而,在本案中,如前所述,顾客支付平台上的钱款在扫码支付之前以及支付之后,商家均未取得对钱款的占有。在顾客扫码支付之前,依据生活常识来看,商家主观上也不会认为自己对该笔钱款已经具有了支配和控制的能力,否则顾客在即将付款但未付款时则无权反悔将商品放回原位,这样于情于理均无法说通。不能将即将归属于商家所有的财物直接认定为商家所有的财物,故三角诈骗的成立前提并不存在,不具有成立之可能。
针对此类特殊案件,张明楷教授提出,三角诈骗并不局限于受骗人处分被害人财产的这一种情形,还包括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受骗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自己的财产,行为人或者第三人取得财产,使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的情形。然而,笔者认为,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某一个疑难案件的定性问题就提出一种新型的概念或者扩大原有概念的范围并不妥当。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犯罪人的犯罪手段也层出不穷。网络金融时代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犯罪人带来了“商机”。我们不应在碰到新类型案件时即寻找新的理论概念或者寻求修改法律,而应该在现有立法以及现有理论的框架下穷尽一切可能性将其解释得合乎规定。在穷尽一切可能性之后仍无法对某类行为进行定性时才应考虑修改法律或者创设新的理论概念。而偷换二维码案,完全可以运用普通诈骗的理论进行诠释,无需创设一种新类型的三角诈骗。
(二)双向诈骗说之理由及反驳
“双向诈骗说”则认为,被骗人是商家和顾客,被害人是商家,诈骗客观方面可概括为:行为人实施了偷换二维码的诈骗行为,同时使商家和顾客陷入对“店内二维码是商家的二维码”的错误认识,商家基于错误认识指导同样基于错误认识的顾客通过扫码二维码处分了本属于商家的财物,基于错误认识的商家又向顾客交付了商品,行为人取得了财物,商家遭受了财产损失,且商家受损的是交付给顾客的商品。
双向诈骗中将行为人取得的财物认定为顾客支付的钱款,而商家损失的却是商品,这并不合理。在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中,要求他人遭受的损失正是行为人取得的财物,即被骗人自愿处分的财物与行为人所获取的财物具有同一性。在本案中,行为人不仅没有占有商品的非法目的,而且商家损失了商品并不是行为人偷换二维码所导致的结果,而是履行合同义务的表现,并因其交付行为使得买卖合同履行完毕,这并不能认定为商家处分财产的行为。
(三)普通诈骗说之提倡
在普通诈骗说内部,可以进一步细分为“顾客被骗说”和“商家被骗说”。“商家被骗说”认为,被骗人和财产受损人均是商家,行为人采取偷换二维码的方式,使商家误认为该二维码是自己的二维码,并基于该错误认识指示顾客扫描该二维码付款,处分了本属于自己的财物,行为人取得财物,商家遭受了损失。“顾客被骗说”认为,本案中的被骗人和被害人均是顾客,行为人采用偷换二维码的方式使顾客陷入错误认识,处分了自己的财物,行为人取得财物,顾客遭受了损失。针对顾客扫码支付的行为属于诈骗罪的处分行为,前文已经详细论述。此处应当考虑的是商家指示顾客扫码付款的行为是否应当认定为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从本案案情来看,客观上是顾客而不是商家向行为人交付了钱款,商家提供收款二维码的行为与商家遭受财产损失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认定为商家被骗则意味着该诈骗行为发生在行为人与商家之间,那么顾客的扫码支付行为则并不在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之内,可是如果没有顾客的扫码支付行为就不会有行为人取得财物的结果。主观上商家也不具有交付钱款的意思,而只具有收款的意思,并不符合诈骗罪中“自愿性”要求。笔者赞同“顾客被骗说”,本案中的被骗人与被害人均是顾客。
应当明确的是,刑法上的受害人与民法上的权利人并不相同。以现实中谁承担损失后果反推刑法中的被害人、被骗人有时是错误的。从财产保护角度出发,虽然民法和刑法都注重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但着重点并不相同。当财产遭受侵害时,民法更加强调财产权之恢复或者赔偿以达填补损失之目的,使得财产恢复到未被侵害的状态,所以,民法更关注最终的侵害状态。然而,刑法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如果财产权利遭受侵害,则权利恢复的可能性小,刑法更加强调盯紧侵犯财产权的每一个过程,以求以刑罚手段实现对财产权的保护。因此,刑法更关注直接的侵害对象。
本案中,作为被害人的顾客自愿通过支付平台支付钱款,行为人通过偷换二维码的行为隐瞒了事实真相从而改变了交易的路径,导致被害人作出了错误的财产处分行为。顾客原本是财物的占有人,但行为人使顾客丧失了对财物的占有,因此遭受损失的是顾客而不是商家。有学者认为,本案中商家实际上才是最终的财物损失者,当商家发现二维码被换之后,由于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并不能要求顾客再次支付钱款,只能向行为人追偿。而顾客既获取了商品,又支付了钱款,并无义务再行支付相同的钱款,并不存在财产损失,不是被害人。然而,笔者认为,之所以惩罚行为人不是因为其对某个具体的被害人造成了财产损失,而是其犯罪行为侵犯了被害人对其财物的占有状态。本案中,钱款由顾客占有,行为人却侵犯了顾客的占有,顾客为被害人。除此之外,从立法目的来讲,规定诈骗罪不仅由于其侵犯了被害人的占有,还在于对被害人自由处分财产意志的“误导”。刑法规制的是行为人的诈骗行为,从而达到预防之目的,而由该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则属于民法强调的范畴。因此,行为人的行为不仅侵犯了顾客对其财产的占有,还侵犯了顾客对于交易状况的知晓,将被骗人和被害人认定为顾客更能全面评价行为人的犯罪行为。
有学者认为,将本案的被害人认定为顾客是否会导致商家的损失在刑事审判中难以救济。笔者认为,刑法上的被害人既不同于民法上的权利人,也不同于刑事诉讼法上的被害人。因行为人的犯罪行为造成民事上的侵权的人均有权在刑事审判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只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减少审判的重复性,在刑事案件中对民事损害一并进行审理。本案中的商家可以作为刑事诉讼法上的被害人在刑事审判中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行为人赔偿损失。
综上所述,因该钱款处于顾客的占有之下,且顾客扫码支付的行为属于处分行为,故不构成盗窃罪。行为人实施了偷换二维码的行为,使得顾客以为该二维码是商家的二维码,陷入了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自愿处分支付平台上的钱款,行为人非法占有该钱款,顾客遭受损失,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四、结语
新型支付方式的日益常态化,致使越来越多的不同于传统财产犯罪的“新型”财产犯罪发生。以偷换商家收款二维码的方式取得钱款的行为仅仅是“新型”财产犯罪中的典型表现。此外还包括非法获取他人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获取他人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的银行卡资金等行为。网络金融时代是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时代,随着发展的日新月异,日后的交易方式不会仅限于第三方支付平台, 面对时代发展提出的挑战,不管犯罪手段如何变化,我们始终应该做到跳出传统思维的禁锢,抽茧剥丝,理清问题之所在,从而对新型犯罪行为准确定性。
[1]王宏宇.论财产犯罪中的观念占有[J].法学研究,2015,(12):107.
[2]黎宏.论财产犯中的占有[J].中国法学,2009,(1):112.
[3]马克昌.百罪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771.
[4]苗欣.偷换支付“二维码”侵财行为的定罪[N].江苏法制报,2016-11-30.
[5]周铭川.偷换商家支付二维码获取财物的定性分析[J].东方法学,2017,(2):113.
[6]武尚昶.偷换二维码,坐收顾客支付款的行为该如何定罪[EB/OL].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NTUyMDA0Mg==&mid=2651937545&idx=2&sn=3c8331fa54fd580265392330c9afca66&mpshare=1&scene=1&srcid=0629 CeM2UrIWUwqWCCADGJ1J&pass_ticket=Pe95 MCrkXl3YSqGIEd4FwamK4Cnc4aO7ZgKdu1W dpwBYmwbPk9zNl8JN0V8gqSoe#rd .
[7]张明楷.三角诈骗的类型[J].法学评论,2017,(1):20.
[8]张庆立.偷换二维码取财的行为宜认定为诈骗罪[J].东方法学,2017,(2):124.
[9]李勇.“调包二维码案”别争了,定诈骗![EB/OL].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NTUyMDA0Mg==&mid=2651937545&i dx=1&sn=0cecd52a631784923435d66230cd5c85&mpshare=1&scene=1&srcid=0629HKEmIVKfpgE V29UXhF7F&pass_ticket=Pe95MCrkXl3YSqGIE d4FwamK4Cnc4aO7ZgKdu1WdpwBYmwbPk9z Nl8JN0V8gqSoe#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