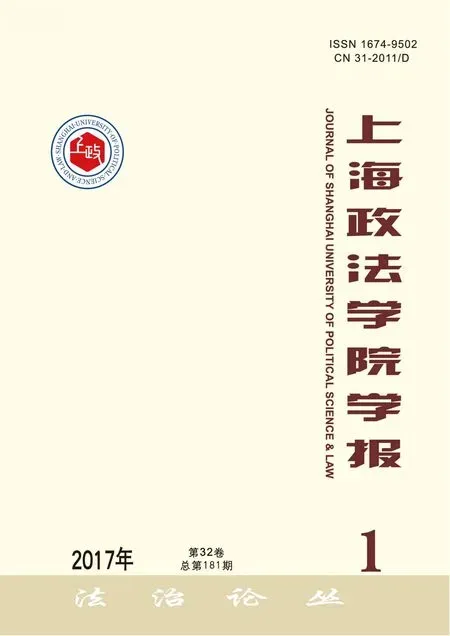论非法言词证据的界定
2017-04-11郭旭
郭 旭
论非法言词证据的界定
郭 旭
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确立了以“痛苦规则”为基
非法;言词证据;痛苦规则;自白任意规则
作者:郭旭,法学博士,南京政治学院讲师。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于2012年正式写入我国《刑事诉讼法》,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司法解释对该规则进行了细化。目前,界定非法言词证据的落脚点集中在侦查人员是否采用了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产生剧烈痛苦的方法以取得口供,“痛苦规则”成为判断非法言词证据的标准。①关于痛苦规则及其对口供判断的规则,详见龙宗智:《我国非法口供排除的“痛苦规则”及相关问题》,《政法论坛》2013年第4期。通过刑讯逼供手段获取的供述需要排除不存在争议,但对于威胁、引诱和欺骗的方法是否或者应否被纳入排除的范围,理论界和实务界却存在不同的见解。②杨宇冠:《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问题研究》,《法学杂志》2014年第8期。在“痛苦规则”作为判断取证非法的前提下,恐怕引诱、欺骗方式难以被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调整范围,因为此两种方法与刑讯逼供等暴力手段相比较,还是显得“温柔”多了,至少在犯罪嫌疑人供述作出之时并没有让其感受到肉体上或者精神上的剧烈痛苦。
立法者在界定非法言词证据时,一方面认识到了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给被追诉人人身权利造成重大损害,由此取得之供述可信性低,另一方面却又采取了“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并没有探究为什么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获取的供述不应当具有可采性。实际上,“痛苦”本身并不是排除供述的判断标准,基于痛苦而使得被追诉人“非自愿”地作出有罪供述,这才是得以排除的根本原因。自愿性应当是判断庭前供述是否合法的首要标准。
一、自白任意规则探析
口供的自愿性,在证据法意义上称之为自白任意规则或非任意自白排除规则,即自白只有在任意的情况下作出才具有可采性,自白任意性应当是可采性的必要条件。①张建伟:《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法律价值》,《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如相关言词证据的取得系违背了供述人的自由意志,那么该言词证据就不得用作不利于追诉其有罪的证据。
(一)自白任意规则在英美法系的发展
根据早先的英国普通法传统,但凡犯罪嫌疑人做出的供述,即便由刑讯逼供所致,也具有可采性。这种规则直到17世纪末期才得以改变。②Laurence A. Benner, Requiem for Miranda: The Rehnquist Court's Voluntariness Doctrin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67 Wash. U. L.Q. 59, 94 (1988)英国于1726年确立了非任意性自白由于其不可靠而不具可采性的原则。自白任意规则在The King v. Warickshall 案中予以明确,③The King v. Warickshall, 168 Eng. Rep. 234 (K.B. 1783)法庭认为“出于希望的谄媚或者对刑讯的恐惧所作出的供述,并不值得相信”。该原则在刑事诉讼案件中得到了严格的适用。英国普通法中排除非任意自白的理由在于,如果警察取证行为可能会导致虚假供述并使得无罪之人被错误定罪,那么该自白就应当被排除。因此,英国法庭在对案件进行判决时,自白的自愿性就成为了考虑的主要因素,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供述不是自愿作出本身就构成了排除的事由,而供述真假性则在所不问。④Welsh S. White,What is an Involuntary Confession Now 50 Rutgers L. Rev. 2001 (1998)
美国联邦法院、州法院乃至最高法院,沿袭了英国普通法传统。在Hopt v. Utah案中,⑤110 U.S. 574 (1884).联邦最高法院阐述了联邦层面的自白任意规则,并指出:“自白如果是在自愿的情况下作出,则是令人满意的最佳证据;但如果是基于威胁或者许诺,使得被告人产生某种恐惧或者希望,使得其失去了自由的意愿或者自控能力,此种自白就不具有可采性了”。自白任意规则于1897年Bram v. United States案件中实现了与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结合,⑥168 U.S. 532 (1897).自此以后任意自白规则就作为联邦宪法的应有之义,在联邦法院中不得将非任意性自白作为证据使用。在各州刑事程序当中并没有如此强制性的规定,法院可以依据本州之法律自由评价违反自愿性而作出的供述。这种情况直到1936年联邦最高法院在Brown v. Mississippi案的判决中,⑦297 U.S. 278 (1936).通过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原则”(due process clause)而将自白任意规则平等适用到州法院层面才得以改变。⑧关于美国宪法及正当程序原则,详见杨炳超:《论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原则——兼论我国对该原则的借鉴》,《法学论坛》2004年第3期。
根据正当程序条款,非自愿性供述不具可采性。判断自愿性时需要综合考虑所有因素,“自愿”与“非自愿”之间并没有明显界限。美国主要通过判例的方式逐渐发展了一整套的自白任意规则体系。正当程序当中的自白任意性体现了多重价值:第一,非自愿供述的真实性及可靠程度过低,如果可以在法庭上用作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则会容易使得无辜之人被定罪量刑;第二,即便在有其他证据对此份口供的真实性予以佐证、造成冤案可能性降低的情形下,该份供述也不可采,“任意自白规则并不仅是为了排除潜在的虚假证据,也是基于证据使用的公正性”,①Lisenba v. California, 314 U.S.219, 236 (1941).即警察在执行法律时也必须遵守法律;第三,采用刑讯或者其他骇人听闻方式取得供述,与文明社会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相冲突;②Mill v. Fenton, 474 U.S. 104, 109 (1985).第四,自白任意规则还与不同的诉讼模式有关,特别是在对抗制诉讼模式下,控辩双方在诉讼过程中应当视为平等的主体,“被告人的自由意志不应当受到政府的压迫,甚至成为对付自己的工具”,③H. Richard Uviller, Evidence from the Mind of the Criminal Suspect: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Current Rules of Access and Restraint, 87 Colum. L. Rev. 1137, 1146 (1987).通过强迫的方式取得供述,这对参讼双方而言无疑是极大的不平等;第五,人的尊严、个人自治以及自由意志,使得公民不能成为公权力滥用获取自愿供述的对象;最后,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上进行分析,该原则还能够对警察的非法行为形成威慑作用,降低将来类似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在众多案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Miranda v. Arizona案,④384 U.S. 436 (1966)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该案创立了米兰达规则,作为犯罪嫌疑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这一宪法性权利的保障,也成为了判断供述是否自愿的重要标准。在该案中,法庭指出:“被监禁之人在受到讯问前,必须被清楚地告知其有权保持沉默,所做供述的一切将会用作在法庭上指控他的证据;他必须被清楚地告知有权聘请律师,并在讯问时由该名律师在场;如果他经济困难,那么将会为其免费提供代理律师”。如果控方将被告人庭前供述作为证据使用,必须证明该被告人在“自愿”、“明知”且“明智”的情况下放弃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二)从身体强制到心理强制
随着刑事司法对程序正义以及人权保障要求的日益高涨,侦查人员获取被告人口供的方式也逐渐从刑讯逼供等身体强制方式转变至采用许诺、引诱等方法的心理强制。心理强制措施能否被视为违反了自白任意规则而将有罪供述予以排除,在理论在也有争论,从美国法院的判例情况上来看,法官们也在没有设定明确的界限。
早在1960年Blackburn v. Alabama案中,⑤361 U.S. 199 (1960).法院就指出:“被告人鲜血淋漓、皮开肉绽并不是鉴别非法讯问的唯一途径,强迫供述不仅可以作用于身体,还能够作用于精神”。通常用来判断心理强制是否存在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监禁的长短;讯问的长短以及发生时间;讯问过程是否与外界隔绝,以及被告人的个体因素(比如年龄,智力,受教育程度以及心理状况等等)。如果有其他心理强制因素的加入,比如不给水喝、不给东西吃,那么无疑会增加供述非自愿的可能。对于许诺(promise of leniency),美国联邦法院的判例则呈现了一种从严格到宽松的趋势。Bram v. United States案判决认为,①168 U.S. 532 (1897).供述的作出如果是出于直接或间接的许诺,不管多么微小,都应该被认为是强迫。在Lynunmn v. Illinois案中,②372 U.S. 528, 534 (1963).警察告知犯罪嫌疑人如果不交代罪行将会失去社会福利金,失去孩子的监护权,并会判处十年的监禁;如果她肯与警察合作,那么警方将会申请减轻量刑并帮助她照顾孩子。联邦最高法院一致排除了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在当时的解读是,警察的许诺行为导致了供述的非自愿性。但在1987年,最高法院在Colorado v. Spring的见解是,③479 U.S. 564 (1987)警察夸大了不供述所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才是判断供述非自愿性的最主要原因。根据Wayne Lafave教授的调研,“地方法院通常认为,通过下列许诺而获取的供述不具有自愿性:不起诉,撤销若干指控,药物治疗或者减少量刑。尽管如此,现在法院已经倾向于减少基于许诺而排除有罪供述的情况,还需要结合案件的其他情况进行分析”。④Wayne LaFave & Jerold H. Israel, Criminal Procedure, at 1449 ( West P. 2009)
许诺只是警察讯问进行心理强制的方法之一,随着美国联邦法院和司法部对采用暴力和刑讯行为的严格禁止,警察讯问方式就变得越来越“狡猾”,欺骗也是最常用的“技巧”。尽管在Miranda v. Arizona案件中,⑤384 U.S. 436 (1966)联邦最高法院严厉地批评了警察在讯问中的欺骗行为,但是越来越多的案例显示,法院对欺骗似乎也采用了一种容忍的态度:仅是向犯罪嫌疑人撒谎并不足以导致供述被排除。如果警察只是欺骗犯罪嫌疑人,告知他的同案犯已经全部交代罪行并已经有足够证据证明其罪名成立,尽管此行为是判断供述自愿性的重要因素,但不足以促使法院作出排除供述的裁决。⑥Frazier v. Cupp, 394 U.S. 731, 739 (1969)不仅如此,法院还通过判例确认了警察化妆成为犯罪嫌疑人的同监室友进而获取该人的有罪陈述的方式取得证据的合法性,⑦Illinois v. Perkins, 496 U.S. 292 (1990)而地方法院则许可了许多中形式的警察欺骗行为,最常见的是允许在讯问时谎称已经掌握了并不存在的被告人有罪证据。⑧State v. Patton, 826 A.2d 783, 793 (N.J. Super. A.D. 2003)
二、非法供述的判断标准:从“痛苦规则”向“自白任意规则”
根据目前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我国非法言词证据采用的 “痛苦规则”为基础的认定模式限制了非法言词证据的范围。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在随后制定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扩大了非法供述的范围,并似乎摈弃了“痛苦规则”作为判断言词证据合法性的唯一根据。该《意见》第8条指出:“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以外,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应当排除。”
《意见》在原先非法供述排除范围基础上进行了如下重要修改,增加了3类情形,此3类情形已经并不完全能够以“痛苦规则”为基础的非法方法进行界定:
第一类,采用冻、饿、晒、烤、疲劳讯问等方式获取的供述。此类模式实乃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扩充,随着现代刑事司法越来越注重在诉讼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保障,传统鲜血淋漓、皮开肉绽的刑讯方法已经被社会舆论所唾弃,但是“深层次”的刑讯行为已经通过另外的不留痕迹的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展现,冻、饿、晒、烤、疲已经被201 2年《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的“肉刑或者变相肉刑,给人的肉体或者精神造成剧烈痛苦”所含摄;
第二类未在法定场合进行讯问,所得之供述需要排除。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地点根据此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可以分为两种,尚未被羁押的,可以通知到其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他的住处以及侦查机关接受讯问,如果已经被羁押,则只能在看守所进行。在司法实践当中,讯问逼供多发生于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涉嫌严重犯罪的情况下。基于此种理由排除有罪供述,与“痛苦规则”的要旨关系已经不大,当然,可能有论者会认为,之所以在《意见》当中做出此种规定,就是为了针对在不法律规定以外的场合进行讯问所潜在的刑讯逼供的可能,但是,在笔者看来,这种解释远不如任意自白原则恰当。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进行讯问,已经给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压力,如果不在法律规定的场合,这种心理强制无疑会更加剧烈,有罪供述就难以确保其自愿性,虚假供述的概率就更高了。无论是从人权保障还是真实发现的角度,均不产生任何收益,反倒增加了成本;
第三类是应当录音录像而没有录音录像所取得的供述,应当排除,这已经超出了“痛苦规则”的要求。录音录像制度产生的目的在于规范讯问行为,不仅能够全程记录整个过程,还能够在证据合法性产生争议时作为证据使用。但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施行,在司法实践当中录音录像制度也出现了异化,并不全程进行(仅成为固定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载体),或者对于应当录音录像的案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提交相应的录音录像,使得控辩双发在法庭之中对取证合法性问题各执一词。《意见》将此种情形明确予以规定,要求排除有罪供述,其合理性也可以通过自白任意规则进行解释。法律明确规定的应当录音录像的案件通常都为重大复杂案件或者检察院自侦案件,这些案件要么因为社会影响重大侦查人员“背负”较大的思想压力,要么是比较私密的对合犯罪,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能够对查明案件事实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定罪量刑的关键因素。侦查讯问场合又不对外界开放,在相对隔绝的场合当中侦查人员更“容易”迫使或者诱使犯罪嫌疑人作出供述,录音录像的全程性能够为事后审查有罪供述的自愿性提供真实、全面、客观的判断依据。
非法言词证据的标准实现从“痛苦规则”向“自白任意规则”的转变并非不可能,在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文本当中,虽然主要均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作为排除供述的先决条件,但在表述当中仍旧出现了“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逼取供述”等词汇,即便采用了以“痛苦规则”为基础的非法方法,但这种非法方法却是以“逼供”为目的。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痛苦规则”带来的弊端至少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痛苦规则回避了一些并未带来痛苦但是也可以达到如同刑讯逼供般更加隐蔽的、对犯罪嫌疑造成心理强制的方法,比如理论上争议最大的引诱和欺骗,引诱和欺骗在获取口供时并不会对被讯问人造成所谓的剧烈痛苦,但不分程度的一律认可引诱、欺骗获得的供述,也不为当代刑事诉讼司法理念所接受;第二,痛苦规则在界定上存在不明确的地方,这点立法者也已经有所了解,并不断地对什么是“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进行扩大,将冻、饿、晒、烤、疲等方式纳入其中。立法应当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频繁修法或者以有权机关意见或者解释的形式对法条进行扩张解释,并不利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施行。这其中还涉及到新旧规定的衔接问题、法官责任问题,等等。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是扩大了非法证据的适用范围,实际上对于理解和适用该规则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随着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深入和人权保障理念的提高,非法言词证据的界定必然会从“痛苦规则”走向“自白任意规则”。《刑事诉讼法》第5 0条已经确立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自白任意的萌芽。论及此,有读者可能会指出,我国法律中还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该义务的存在就注定目前自白任意规则无法真正实现。①有论者认为“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实质上已经体现或者贯彻了无罪推定原则,而“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规定有违无罪推定原则,应予取消。顾永忠:《〈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无罪推定原则的名实辨析》,《法学》2011年第12期。笔者认为,如实供述的落脚点在“如实”二字,即对于侦查人员的讯问,犯罪嫌疑人享有“不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但如果他是在自愿的情况下做出供述,那么供述必须是真实的。
在司法实践当中,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均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多次讯问,以固定口供,形成数次供述之间的相互印证,以提高证明力。如果最开始的供述系非自愿情况下作出,那么后续自白的效果即重复自白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使用问题,也需要予以高度关注。②关于重复自白以及受到强迫取证行为直接影响的派生证据的排除问题,参见陈瑞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以非自愿供述为范例的分析》,《当代法学》2015年第1期。
三、确保自白任意性的配套制度
自白任意规则的实现,就我国目前刑事司法状况而言,还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其中就包括沉默权、讯问时律师在场、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等等。缺乏这些必要的配套制度而探讨自白任意规则如何在排除非法言词证据中发挥作用,是不切实际的。
(一)沉默权
沉默权被认为是自白任意规则的子权利。学界对沉默权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普遍认为应当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③何家弘:《中国式沉默权制度之我见——以“美国式”为参照》,《政法论坛》2013年第1期;刘根菊:《沉默权与严禁刑讯逼供》,《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冀祥德:《沉默权与辩诉交易在中国法中的兼容》,《法学》2007年第8期。实务界特别是侦查机关对此持相反观点,认为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刑事侦查活动将受到极大阻碍,不利于惩罚犯罪目标的实现。①笔者在湖南省某市与当地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调研时发现,部分公安干警认为犯罪嫌疑人就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否则就是认罪态度不好,阻碍案件的侦破工作。目前我国侦查活动还是以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为中心的,口供中心主义的侦查模式直接导致侦查人员更倾向于从犯罪嫌疑人口中获取证据,而不擅长从搜集其他言词证据或者实物证据来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②樊崇义:《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新发展》,《法学》2011年第7期。为了取得口供,侦查人员当然会采用各种途径,为刑讯逼供提供了心理动机。实际上,立法者也早已了解到口供中心主义的弊端,法条当中也已明确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于刑罚”。沉默权制度的建立,一方面为实现侦查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契机,促使侦查人员积极获取与犯罪事实相关的实物证据和其他言词证据,实现侦查技术和设备的更新换代,另一方面,也能够为犯罪嫌疑人在审前阶段的人身权利提供必要的保障,在行使沉默权的情况下,不会出现刑讯逼供、疲劳讯问等极端情况,因为除非犯罪嫌疑人愿意做出供述,否则他就有权保持沉默,任何明示或者默示的侵犯沉默权的行为将会视为对自白任意规则的违反,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排除犯罪嫌疑人的相关供述,理由在于“任何人不能基于他的违法行为而获利”。
(二)讯问时律师在场
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是确保口供自愿性的另一重要内容,早在十几年前,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就对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开展了试点项目。③樊崇义、顾永忠:《侦查讯问改革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实践证明,讯问时律师在场能够有效地规范讯问活动,并对侵犯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和人身权利的行为及时提出异议。遗憾的是,我国目前法律当中尚未规定此种制度,尽管2 0 1 2年《刑事诉讼法》已经进一步扩大了辩护的范围和程度,但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作为辩护人的权利仅能在“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方可行使。从法条的表述来看,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讯问的过程中是不可能有律师作为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的,即便在之后的讯问过程中,律师也没有在场的权利。实务部门对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心存顾虑,但笔者认为,在沉默权得以确立的基础上,担心律师在场而无法得到口供的顾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毕竟在此前提下,口供并非是破案所必须,有其他证据并形成证据链条且可相互印证的,仍旧可以将犯罪嫌疑人移送审查起诉。在犯罪嫌疑人同意回答的前提下,律师在场可以对该人的自愿性作见证,而且“被告人自愿作出的对己不利的证言,是最好的证据”。④顾永忠:《刑事辩护的现代法治涵义解读——兼谈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当然,考虑到目前我国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率普遍偏低,在没有其还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将是证明口供自愿性的最佳材料。
(三)同步录音录像
我国已经确立了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但从现有规定上分析,该制度仍有值得进一步完善之处。首先是应当录音录像案件的范围,《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仅强制要求对于可能判处无期、死刑以及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类案件进行讯问录音录像,其他的案件究竟是否录音录像则交给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自身条件进行自由裁量。⑤杨宇冠、郭旭:《录音录像制度与非法证据排除研究》,《人民检察》2012年第19期。在可录可不录的情况下,侦查人员通常都会选择后者。即便是法律中明文规定的“可能判处无期、死刑”的案件,公安司法人员也可以讯问时并不认为该案会判处无期或者死刑为由而不进行录音录像。该理由很难得到有效驳斥。侦查活动本身就是一个由表及里、逐渐深入的过程,侦查初期发现的相关证据可能并不足以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判处无期、死刑,但随着侦查的深入,更多的犯罪行为或者更加严重的危害结果被证实,继而导致法定刑或者宣告刑的提升,这种情况也是客观存在的。既然如此,司法实践中也就出现了一种规避法律的现象,对于明明可能被判处无期、死刑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并不进行录音录像,而是通过多次“教育”讯问口供稳定后,再对讯问进行录音录像,使得录音录像成为了固定证据的载体,丧失了本来应当发挥的效果。针对此种情况,立法应当扩大录音录像案件范围至所有刑事案件,以录音录像为原则,不录音录像为例外,对于没有录音录像的,应当作出合理解释或者补正,否则相关的供述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在目前的科技条件和经费水平下是现实可行的。其次是录音录像的全程性问题。我国法律规定的是“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对讯问前和讯问后的情况并没有作出规定,而根据笔者调研,真正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在一些地方目前侦查活动当中都没有能够完全实现,“打时不录,打完再录”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要充分发挥录音录像制度的作用,必须实现对录音录像的全程适用,这种全程不仅仅是覆盖侦查讯问活动,还应当包括从“进”到“出”的全过程。
(四)对逮捕的司法控制
逮捕受到严格司法控制,审前羁押不应当成为一种常态。我国目前审查批准逮捕活动主要采取检察机关审判模式,并辅之以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①杨宇冠、郭旭:《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刍议》,《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这种审批活动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三方诉讼构造,在形式上仍旧具有行政权行使的色彩。在司法实践当中,侦查机关和检察院通常采用的是“够罪即捕”的方式,一方面使得我国审前羁押率很高,另一方面这种羁押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犯罪嫌疑人违背自己意愿作出所谓的有罪供述形成了心理强制,同时也为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证言提供了“便利”。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于2014年12月16日制定并发布了第35号一般性意见,专门就人身自由和安全问题、特别是对自由的限制、剥夺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界定。该意见强调,尽管人身自由权不是绝对的,出于维护法治的目的可以对被追诉人的人身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或者剥夺,但是各国应当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不受到任意侵犯,包括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逮捕或拘留,未经授权延长其他形式的拘留,等等。即便根据法律进行的逮捕,也需要考虑使其包括不适当、不正当、缺乏可预见性和适当法律程序而导致的违法行为,以及羁押时间的合理性、必要性和程度等要素。如果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受到了不合理的限制或者剥夺,在此种情况下做出的有罪供述可以被认为是缺乏自愿性的,宜被纳入非法证据的范围。
(责任编辑:丁亚秋)
DF713
:A
:1674-9502(2017)01-127-08
础的非法言词证据界定方式。“痛苦规则”在实施过程中引发众多争议,并不利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以供述的非自愿性作为判断标准。实现从“痛苦规则”向“自白任意规则”的转变,能够更加发挥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的功能。同时,为了保障该规则的贯彻落实,还必须建立和完善沉默权制度、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律师讯问在场制度以及对逮捕程序的司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