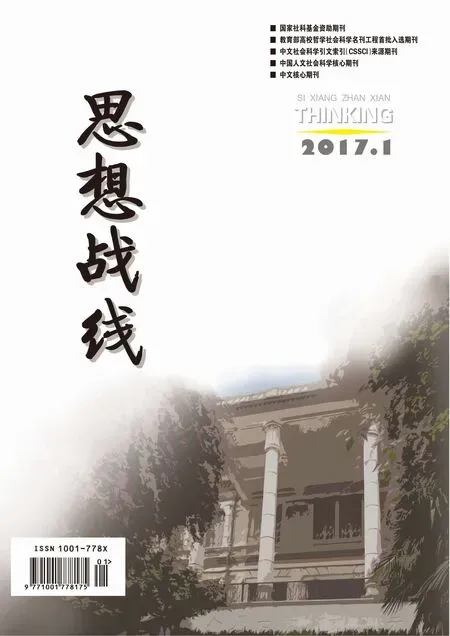商业信息传播与唐宋商品经济的发展
2017-04-11唐国锋
唐国锋
商业信息传播与唐宋商品经济的发展
唐国锋①
唐宋时期,商业信息传播得到迅速发展。较之前代,除了普通商人、作为中介商的牙人之外,政府和普通民众也纷纷主动利用商业信息传播为其商业活动服务。商业信息传播呈现出商业信息总量增大、信息传播方式增多、传播媒介更为丰富、信息传播速度大幅提升等异于前代的特点。这一时期,商业信息传播为唐宋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市场环境,加快了商品供需满足速度,成为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强大助力。
唐宋;商业信息传播;商品经济;交易成本
马克思说过:“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67页。然而,商品如何才能得以流通呢?在商品流通之前是否存在着商业信息的传播过程?答案不言而喻。在商品流通前如果没有商业信息传播,那么商品就不知流向何方。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商品价格、供求状况等商业信息被商人、消费者及时搜集并随时传播。甚至在商品流通结束后,商业信息仍有可能在不同的商业活动参与者和组织中继续进行传播。我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经历了数千年的积累与发展,呈现出三次较为明显的高峰。其中唐宋的商品经济上承秦汉,下启明清,成为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一时期商业信息传播的快速发展无疑助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一、唐宋商业信息传播的表现
唐宋时期,商业信息传播较之前代更加广泛地存在于商业活动中,普通商人、牙人、政府和消费者纷纷成为商业信息的传播者。
其一,普通商人亲自深入市场,如同刘禹锡《贾客词》所言:“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他们游走在各级市场,通过耳闻目睹的方式接触或者传播各种商业信息,然后根据市场供求做出买卖的决策,正所谓“乘时知重轻,心计析秋毫”。*刘禹锡:《贾客词》,载谭国清主编《传世文选·乐府诗集三》,北京:西苑出版社,2009年,第15页。另外,《夷坚志》中记载了一家富商,“事紫姑神甚灵,每告以先事之利,或云下江茶贵可贩,或云某处乏米可载以往,必如其言获厚利”。*洪 迈:《夷坚志·夷坚甲志》卷16《碧澜堂》,清十万卷楼丛书本。透过材料发现这些商人正是因为准确地掌握了各个市场的物价、商品供求信息,所以才能够获得巨额利润。
其二,除了直接深入市场获取商业信息外,资财雄厚的大商人更多情况下通过雇佣人力,分赴各级市场,搜集和传播商品物价高低、供求状况信息,如茶叶“大商刺知精好之处,日夜走僮使赍券诣官,故先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闰六月己卯”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37页。另外,温州永嘉商人何子平“尽知四方物色良窳多寡与其价之上下”,*周行己:《周行己集》,周梦嶷笺校,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48页。商人何子平是怎样了解到四方物价情况的呢?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下,要做到及时详细了解各地商品物资供求状况及物价涨落情况,除了雇佣他人迅速收集、传播商业信息外,大概难有其他途径。
其三,还有部分资财雄厚的大商人通过与权贵交往及时获取商业信息。唐高宗时的邹凤炽,玄宗时的王元宝,昭宗时的王酒胡,他们分别是唐代前中后期的巨富代表,同时也是皇室的座上宾。史书记载:“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全等,国中巨豪也。各以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朝之名僚,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为豪友。”*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豪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页。而众多大商人来到长安销售奢侈品,往往也是“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陈 均:《宋九朝编年备要》卷第26,宋绍定刻本。这样一方面可以掌握这一阶层的消费意愿、消费需求,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借此探知朝廷的政治、经济政策变化。这一现象在宋代仍然比较常见,如林摅任开封府尹时,有“大驵负贾钱久不偿,一日,尽辇当十钱来,贾疑不纳,驵讼之。摅驰诣蔡京,问曰:‘钱法变乎?’京色动曰:‘方议之,未决也。’摅曰:‘令未布而贾人先知,必有与为表里者。’退鞫之,得省吏主名,阗于法”。*《宋史》卷351,“林摅传”,北京:中华书局,第11111页。国家钱法尚在决策之中,大商人因为与制定钱法的官员勾结,提前获得钱法变更的信息,因此拒绝使用旧钱。
其四,以撮合交易为主要职责的中介商——牙人,直接从事商业信息传播工作。唐宋时期,在乡村市场中,“老翁主贸易,俯仰众所尊”。*释道潜:《参寥子集》,“参寥子诗集卷1”,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主持交易的老人因为熟悉市场行情,并且较为公平地为买卖双方提供商业信息,因此成为交易的关键人物。在城市市场中,“(建康城)数十万家之生齿,常寄命于泛泛之舟楫,而米价低昂之权,又倒持于牙侩之手”。*周应合:《南京稀见文献丛刊·景定建康志》,南京:南京出版社,第568页。正是这些牙人掌握着外来米谷的货源信息、消费市场的批零兼营发卖信息,故而能够操纵拥有数十万人的建康城的米价。甚至一些妇女也投身牙人行业,她们“插花作牙侩,城市称雄霸。梳头半列肆,笑语皆机诈。新奇弄新妆,会合持物价”。*陈普:《石堂先生文集》卷16,“古田女并序”,明万历三年薛孔洵刻本。在榷场和市舶司中,牙人也成为商业信息的重要传播者。如元丰年间,“缘边州军主管刺事人,乞选募,人给钱三千,……其雄霸州,安肃广信军四榷场牙人,于北客处钩致边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元丰二年七月甲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267页。在边贸和对外贸易中,缺乏牙人的语言翻译和信息传播,就会出现“波斯捧出海南香,白眼昆仑与论量。贾客不谙弹舌语,只看两个鼻头长”*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1649,释端裕,“偈二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461页。的尴尬局面。反之,凭借大量牙人语言的沟通,实现商业信息在买卖双方之间的传播,从而有效地促成交易,正如诗文曰:“珠商贝客市门听,牙侩闲边自品评。”*曾丰:《缘督集》卷13,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其五,唐宋政府顺应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潮流,不断调整国家商业政策,积极利用商业信息传播尽量降低交易费用。政府在制定商业政策时,经常邀请商人参与讨论,陈述利弊。如太宗至道年间,三司使陈恕在出台新的茶法前召来数十名茶商共同商议,听取意见:
陈晋公为三司使,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唯中等之说,公私皆济,吾裁损之可以经久。”于是为三说法,行之数年,货财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实。*江少虞:《新雕皇朝类苑》卷22,日本元和七年活字印本。
景祐三年(1036年)政府改革茶法时,同样召集了一批茶叶商人前来商议:
三年正月九日,命知枢密院事李谘、参知政事蔡齐、三司使程琳、御史中丞杜衍、知制诰丁度同议茶法,仍许召商人至三司,以访利害。*《宋会要辑稿》食货30之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657页。
通过上述史料可见,宋政府在制定商业政策时积极吸收商人的意见,其实是在小范围内提前传播该商业信息,从而获知广大商人的反应并进而调整完善该政策。吸收了商人们的意见后形成的商业政策变得更加切合实际,同时这些商业信息经过商人之口又将快速地传播开去。
另外,唐宋时期的官员也越来越多地利用商业信息传播为其管理工作服务。唐代宗时,刘晏“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旧唐书》卷123,“刘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15页。刘晏招募一批善于疾走的人建立了一个商业信息收集、分析、反应的信息传播机构,通过这一机构反馈的信息及时调整国家的商业政策,从而保障了粮食、食盐等大宗商品的正常流通,为唐王朝政权稳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唐代卢坦走马上任宣歙观察使之际,“值旱饥,谷价日增,或请抑其价。坦曰:‘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辐凑,民赖以生”。*《资治通鉴》卷237,“唐纪五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653页。卢坦认识到了谷价上涨的信息必然为粮商随时掌握,因而他拒绝了一些官员降低谷价的请求,反而允许谷价适当上涨,最后米谷源源不断地从外地运到宣歙地区,老百姓因此得以生存下来。
宋代官员“范文正治杭州,二浙阻饥,谷价方踊,斗钱百二十,公遂增至斗百八十,众不知所为,公仍命多出牓,沿江具述杭饥及米价所增之数,于是商贾闻之,晨夜争进唯恐后,且虞后者继来,米既辐凑,遂减价,还至百二十”。*吴 曾:《能改斋漫录》,王仁湘注释,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第22页。灾荒来临,范仲淹不但不抑制谷价上涨,反而将谷价“增至斗百八十”,同时还让人印出榜文,沿江到处传播杭州的灾情和米价上涨的信息,最后大量商人“晨夜争进”,争先恐后地调集粮食运往杭州,谷价因为粮食供应充足自然又降到灾荒刚开始的价格。而南宋治荒名臣董煟更是提出政府要充分利用“价格”商业信息传播的作用,他指出:
比年为政者不明立法之意,谓民间无钱,须当藉定其价,不知官抑其价则客米不来,若他处腾涌而此间之价独低,则谁肯兴贩?兴贩不至则境内乏食,上户之民有蓄积者愈不敢出矣。*董 煟:《救荒活民书》卷2,“不抑价”,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董煟认为,政府只有采取不抑制粮价的措施并传播不抑价的商业信息,才能吸引商人运来粮食,一旦外来商人开始调运粮食,本地大家富室因担心粮价下跌就会主动开仓卖粮,这样粮价就自然下降。
其六,唐宋时期,普通民众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商业信息传播的参与者。这一时期,商业广告的多样化发展助推商业信息传播走近民众,使得人人都成为商业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无论是招牌、幌子、欢门、彩楼、灯笼等有形广告,还是通过器物敲打、口腔吹奏、吟唱出来的无形广告等,两者分别是通过视觉和听觉直接作用于市场中的买卖者,甚至是那些不准备买卖商品的过往者,从而完成了市场内商业信息的传播与反馈过程。另外,正是这些成千上万的普通消费者,他们把商品购买、消费过程中获得的商业信息以及消费感受传播给其他人,在这种商业信息的反复传播过程中,人们逐渐确立了诸多的优质产品,各地的品牌商品由此诞生。唐天宝元年,大臣韦坚为取悦玄宗收集了各地品牌商品进行集中展示:
若广陵郡船,即于栿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旧唐书》卷105,“韦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22~3223页。
北宋初年的陶榖在《清异录》中记载了当时天下的“九福”:“京城钱福、眼福、病福、屏帏福,吴越口福,洛阳花福,蜀川药福,秦陇鞍马福,燕赵衣裳福。”*陶 谷:《清异录》卷1,民国影明宝颜堂秘籍本。“九福”实际就是各地的名牌产品。无独有偶,太平老人《袖中锦》更加详细地指明了全国各地的品牌商品:“监书、内酒、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定瓷、浙漆、昊纸、晋铜、西马、东绢……,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太平老人:《袖中锦》,学海类编本。这些品牌商品一方面因为其本身质量好,深受消费者喜欢,另一方面,这些具有良好口碑的商品信息被商人或其消费者以各种方式四处传播,因此闻名遐迩。
二、唐宋商业信息传播的特点
(一)商业信息传播的信息量增大
在唐宋以前,商业信息的传播主体主要限于职业商人、作为中介商的牙人等商业活动的参与者。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腐蚀力”越来越强,更多阶层的人群参与商品交易之中,大量的官员、士大夫、农民、僧道人士、军人等积极参与商业活动中来。宋太宗时的范晞“尝为兴元少尹,居京兆,殖货巨万”,*《宋史》卷249,“范质传附范晞”,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798页。仁宗时的孙沔以资政殿学士知杭州,“尝从萧山民郑昊市纱”,在并州又“私役使吏卒,往来青州、麟州市卖纱、绢、绵、纸、药物”。*《宋史》卷288,“孙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689~9690页。梅尧臣笔下读书人则背着笥箱从事贩卖茶叶的活动,“浮浪书生亦贪利,史笥经箱为盗囊”。*梅尧臣:《宛陵集》卷第34,“闻进士贩茶”,四部丛刊影明万历梅氏祠堂本。另据《东京梦华录》记载,“遇补年,天下待补进士都到京赴试,各乡奇巧土物都担戴来京都货卖,买物回程,都城万物皆可为信”。*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遇补年”,永乐大典本。而晚唐时的姚合在诗中写到:“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姚 合:《庄居野行》,见《全唐诗》卷498,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661页。宋代,亦农亦商的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太平(半)在外”。*《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073页。甚至连效力于国家的军人也纷纷加入了商业活动之中,北宋成都府“押纲使臣并随船人兵多冒带物货、私盐及影庇贩鬻,所过不输税算”。*《宋会要辑稿》食货42之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937页。南宋以来,殿司诸统领将官公开“差兵营运,浸坏军政”。*《宋史》卷194,“兵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847页。这些商业活动的参与者历史地承担起了商业信息传播的重任,极大地丰富了商业信息传播的主体。
唐宋时期,在商业活动主体增多的同时,商品市场不断扩大。在城市,出现了坊市不分的现象,在农村出现了各类型的草市、墟市、集市,正所谓“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刘 宰:《漫塘文集》卷23,民国嘉业堂从书本。同时,唐宋时期还出现了多种经济作物以及相应的手工业生产区。这些地区大多以较为单一的产业为主,其他诸如粮食、茶、盐等生活资料则依靠商人的运输。如苏州洞庭山的桔园户和种桑户“糊口之物,尽仰商贩”,*庄 绰:《鸡肋编》卷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湖中安吉人,……唯藉蚕办生事”。*陈 敷:《农书》卷下,清知不足斋丛书本。商品经济的浪潮席卷了城市和乡村的众多角落,从事商业活动的主体增多,商业活动的频繁,商品市场的扩大,这些因素客观上导致商业信息量较之前代必然倍增。与此同时,面对商业信息倍增的状态,各交易主体对于商品信息、商业交易对象、市场供求状况、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动乃至农业气候变化都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搜集、整理、分析,同时将这些信息又传播给他人,传播到他地,这样商业信息即实现了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同地、异地之间的交叉传播,从而使得信息的总量在传播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呈几何数倍增。
(二)商业信息传播方式增多
在保持传统人际传播方式的基础上,唐宋时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组织传播。行的产生和兴盛成为组织传播的有力通道。唐朝东西两市各有二百二十行,据西湖老人《西湖繁盛录》的记载:“京都有四百四十行”,*西湖老人:《西湖繁胜录》,永乐大典本。南宋临安城内,“市肆谓之行者……,如酒行、食饭行是也”。*佚 名:《都城纪胜·诸行》,清武林掌故丛编本。各行头、行老熟悉行内商品物价、供求状况,一方面直接为居民提供人力资源信息,“凡雇请人力及干当人,如解库掌事、贴窗铺席、主管酒肆食店博士……俱各有行老引领”。*吴自牧:《梦梁录》卷19,“雇觅人力”,清学津讨原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另一方面,行老还承担着为政府旬估定价提供商业信息的职能。天禧二年(1018年)十二月诏云:“自今令诸行铺人户依先降条约,于旬假日齐集,定夺次旬诸般物色见卖价,状赴府司,候入旬一日牒送杂买务,仍别写一本,具言诸行户某年月日分时估,已于某年月日赴杂买务通下。取本务官吏于状前批凿收领月日。”*《宋会要辑稿》食货55之1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260页。能参加政府召集的会议者显然是某一行的行头,并且较为熟悉本行各种商业信息的传播。由官府召集“行户立价,定时旬价直,令在任官下行买物”。*《宋会要辑稿》职官27之2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723页。根据元代人所作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记载:“司县到任,体察奸细、盗贼、阴私、谋害不明公事,密问三姑六婆,茶坊、酒肆、妓馆、食店、柜坊、马牙、解库、银铺、旅店,各立行老,察知物色名目,多必得情,密切告报,无不知也。”*佚 名:《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辛集,明刻本。行会成为同类商品的集中销售地,同时也成为商业信息的汇聚传播之地。行老、行头利用行会的组织优势,熟练地进行商业信息的组织传播。
(三)商业信息传播的媒介更加丰富
传播媒介是信息传播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信息传播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传播媒介的发展变化一方面推动了信息传播的发展,另一方面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讯息”,*[加拿大]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8页。一种新媒介的产生和兴起,都是信息传播速度提升和传播范围扩大的反映。唐宋时期,伴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雕版印刷的广告、榜文、邸报等应运而生并且开始承载越来越多的商业信息,成为商业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我国现存最早的广告镂版是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南宋刘家针铺铜印版。铜版上面刻有“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客转为贩,别有加饶,请记白”的文字广告。*卢嘉锡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图录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75页。这则广告是我国传统社会商业印刷广告的代表,它把山东济南刘家针铺的商业形象非常成功地展现出来了。唐宋社会的买扑信息和其他一些商业信息也多通过榜文发布,“于要闹处出牓,限两个月召人承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7,“熙宁三年十一月甲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275页。而邸报直接传播楮券的价格涨落情况:“楮券到今已是筑底,别无良策,朝廷且欲一时扛得价起,不得已行此策。昨日见邸报,闽浙四郡守皆以价高迁秩。”*袁 甫:《蒙斋集》卷7,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以上材料反映了商业信息传播由传统以声音为媒介、以口耳相传为主的传播方式,向以文字为媒介,以广告、榜文、邸报为主的传播方式转变。
(四)商业信息传播速度加快
基于商业信息传播主体的增多,传播渠道的丰富,传播媒介的增多,商业信息传播的速度得以提升,商业信息朝发夕至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如前所述,刘晏主持唐朝财政时,对于全国最远地方的物价不过四五日就可以完全掌握。南宋中期,知汉阳军黄榦说:“湖北糯米与饭米同价。去年粜两贯一石,今春粜两贯二百文一石。已而大旱,遂增三百,又增二百,遂增至三贯一石。客旅以一贯四百文搬贩糯米,经涉二三百里,而获倍称之息。”*黄 榦:《勉斋集》卷30,“申转运司为客船匿税及米价不同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商人及时地掌握了周围市场的商业信息,搬运糯米二三百里,就可以获取二至三倍的利润。唐宋时期,“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祖训被打破,一方面是因为交通工具的改进,交通费用成本的降低,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商业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商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知准确的商业信息,从而为贱买贵卖提供决策依据,从而更好地做到乘时逐利。唐宋时期出现各种“神行”信使便是人们对传播速度加快的描述,而《水浒传》里“日行八百里”的神行太保戴宗等,即是这一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加快的典型代表。
三、商业信息传播对唐宋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商业信息传播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市场环境
商品经济的核心是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商业信息的有效传播为商品生产和交换提供可靠的市场环境。如马克思所说:
产品交换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公社互相接触的地方产生的,因为在文化的初期,以独立资格接触的不是个人,而是家庭、氏族等等。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0页。
在这段话中,马克思在阐述产品交换向商品交换转变的过程时,说到家庭、氏族、公社在相互接触的地方,在相互接触的过程中“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三次用到“接触”,第一个“接触”是指地域空间上的接触,后面两个“接触”指的是作为信息传播主体的人或者组织的参与过程。在原始社会,通讯技术落后、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在邻近的地方,直接面对面进行交换,在产品交换的同时还伴随着大量商业信息的传播与扩散。
随着生产的发展,商业信息传播的拓展,人们在同一交换地点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获得自己想要交换的物品。同时还能把自己想要而市场暂时不能满足的需求信息传播给其他人,这样就吸引了其他能满足这一需要的人来到这个市场进行交换。“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郑 玄:《周易郑注》,“系辞下第八”,清湖海楼丛书本。固定的市场由此诞生。唐宋社会兴起了一大批市镇,如龙登高研究表明:“最高中心地(指州府或非州府城市)之下是县镇,它们是沟通城乡市场联系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农产品与手工业品由此集中向上进入高层城市,供农户和县镇居民消费的物品则由此向各村落、集市、墟市扩散。”*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6页。除了商品的流通外,市镇还是城乡商业信息传播的中转站,来自最高中心地州府城市和初级市场各村落草市、墟市的商业信息在此汇聚和交换,从而为“农产品的求心运动”和“手工业产品的辐射运动”*漆 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下),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1123页。提供了可靠的市场环境。
另外,唐宋时期茶肆和邸店的兴起又开辟了新的商业信息传播场所。茶肆、邸店一方面作为休闲和住宿、仓储的场所,另外一方面又作为商业信息的汇聚之所。众多的豪商大贾、贩夫走卒能够在这些地方获得商业信息,传播商业信息,有的甚至直接在这些场所进行商业交易。*唐国锋:《从<夷坚志>看宋代商业信息的传播途径》,《柳州师专学报》2004年第3期。这就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讯服务,从而加快了商业活动的频率。
(二)商业信息传播加快了商品供需满足速度
商业信息传播的发展,商业活动的频率加快,推动了商品生产的速度加快,商品种类不断增多。但是,衡量商品经济发达与否的标志不仅仅是商品的生产速度和数量的多寡,而且还表现在商品供需满足速度的快慢。欧阳修在《初食车螯》一诗写道:
累累盘中蛤,来自海之涯。坐客初未识,食之先叹嗟。……自从圣人(宋太祖)出,天下为一家。南产错交广,西珍富邛巴。水载每连舳,陆输动盈车。鸡潜细毛发,海怪雄须牙。岂惟贵公侯,闾巷饱鱼虾。*欧阳修:《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8页。
对于这种情况,宋人石介也曾作过记载:
夫朝持货而出者,曰金珍,曰珠玉,曰犀象,曰其绮縠,曰丝枲,曰布币、犀象、马牛、羊豕、犬雉、鱼鳖之属,虾蟹之细,米盐之品,葅醢之多,东暨日际,西极月竁,南极丹崖,北极朔陲,相会而凑于五都之市,朝而聚,夕而虚,大小无不用也,巨细无不取也,贵贱无不纳也,短长无不收也。*石 介:《徂徕文集》卷上,“代张顾推官上铨主书”,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材料中虽有文学的夸大其词,但也可以窥见一斑,盛产于东南沿海的海产品原来仅仅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现在因为商业信息传播的畅通,商品的流通加快,普通百姓也能经常吃到车螯等海产品。甚至是全国各地的货物也因为商业信息传播的加快从而实现了“朝而聚,夕而虚”的盛况,商品的供需满足程度得以加速。
在商业信息传播加快的基础上,全国各个地区的商品供需满足速度都纷纷加快,在东南市场,因为农业、手工业发达,商业信息传播加快,苏州商业繁盛,据《吴郡志》记载:“水浮陆转,无所不致。故其民不耕耘而富足,中家壮子无不贾贩以游者。有事商贾以吴为都会,五方毕至。”*范成大:《吴郡志》卷7,择是居丛书影宋刻本。而“吴侬之野”的佃户也频繁地卷入了商品交换:
予见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粜钱,复买物货,归售水乡佃户如此。*魏了翁:《古今考》卷18,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可见,普通佃户利用余粮在肆中交换得到日常生活用品,而商人则将收集到的米运至杭州、南浔、姑苏等大城市出卖,再买回大批日常生活物资销售给普通百姓,从而加快了商品的供需满足速度。
在宋代,甚至连较为闭塞的四川地区,也因为商业信息传播的畅通,而较大程度地突破了此前的封闭状态,商品流通进一步加快:
蜀于五代为僭国,以险为虞,以富自足,舟车之迹不通乎中国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后蜀之丝枲织文之富,衣被于天下,而贡输商旅之往来者,陆辇秦、凤,水道岷江,不绝于万里之外。*欧阳修:《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64页。
因为太祖平蜀,结束了四川市场与外界市场的隔离状态,实现了商业信息传播的畅通。四川市场不仅为西北市场提供大量的物资供应,同时四川市场的丝织品也行销全国。毋庸置疑,四川市场在产品外销的同时,也必然大量地购入其他市场的各类商品。
(三)商业信息传播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
费尔南·布罗代尔说过:“消息奇货可居,价值何止千金。”*[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44页。商业信息的有效传播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固然离不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商品经济作为一种以交换获取利润为目的的经济,应该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为目标,否则商品就难以大量地、迅速地销售出去。而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首先就得了解消费者的需求,要了解人们的需求,即要重视商业信息的搜集。因此商业信息传播之于商人、政府和其他商业活动的参与主体尤为重要。
商业信息传播同样成为唐宋商品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唐宋时期,“政府已经放弃了对商品运输、销售环节的控制,还位于商品流通的主体——商人”。*林文勋:《唐宋社会变革论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39页。政府通过发布入中的商业信息,从而吸引无数的商人不舍昼夜地将各种边关所需物资和金银输送到指定地点,接着持引到相应地方购买茶、盐、香料等等,然后再将这些大宗商品销售到全国各地,从而实现了茶、盐等大宗商品的运输与销售。也正是由于商人们熙熙攘攘的商业活动将各种商业信息传播到全国各地,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消费,扩大了消费需求,进而推动这些商品的生产。同样,在各级市场中,正是因为各行牙人为买卖双方提供了交易信息,从而使得交易双方都尽可能获得消费者剩余,加速交易完成。另外,广大消费者及时获取商业信息,在商品买卖过程中能够顺利购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进而将这种消费感受传播给其他人,在这种长期的信息传播中,催生了一大批品牌商品。另外,各级市场之间的商业信息传播也使得各地商品产销对路,购销对路,进而实现各个经济区的更好分工与协作。
四、结 语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商业信息成为商业活动的行动指南,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谁更快、更全面地掌握商业信息,谁就最有可能成为商业活动的赢家。唐宋时期,商业信息传播的发展使得整个商品经济活动参与主体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唐宋政府让渡出大宗商品的运输、销售权,利用商业信息传播吸引商人参与国家层面的商业活动中来,较高效率地调动物资、稳定市场、增加财政收入等;普通商人和中介牙人通过商业信息的传播及时掌握市场供求状况、物价涨落,及时准确地买进卖出,撮合交易,减少了交易成本,更大程度获取商业利润;众多商品生产者通过掌握商业信息传播,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不断满足市场需要;广大消费者利用商业信息传播则较为容易地获取价廉物美的商品信息,减少了消费障碍,刺激了消费欲望。
经过对唐宋时期商业信息传播的探究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商业信息传播广泛存在于商业活动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商业信息传播呈现了一系列异与前代的特点:商业信息总量相应增加,商业信息传播方式增多,商业信息传播媒介更加丰富,商业信息传播速度得以进一步加快。商业信息传播为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提高了商品供需的满足速度,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当然,这一时期的商业信息传播仍然没有单独成为一种行业,它如影随形地依附于商品经济而存在,依附于其他产业、其他职业、其他组织的发展而发展,因而它所发挥的作用还难以达到今天信息社会中商业信息传播的作用。与此同时,唐宋时期各阶层人们对于商业信息传播的重视、利用也还处于“实用主义”阶段,尽管这一时期也曾出现了诸如刘晏专门设立递铺探知各地物价的官员,但不得不承认,他对商业信息传播的利用主要还是着眼于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而像卢坦、范仲淹、董煟等人利用商业信息传播多属灾荒之时的应急之举。对于这些举措在没有灾荒的年份在多大程度上被同样运用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还值得深入探讨。而广大商人对于商业信息传播的利用则多是依靠父子相传、口耳相传。正因为如此,对于唐宋时期商业信息传播对商品经济的影响难以做出较为精确的分析。这些问题关乎唐宋商业信息传播的深度与广度,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 廖国强)
Dissemination of Commercial In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ANG Guofeng
Commercial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saw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During this period, government organs and common consumers, along with ordinary merchants and various agents, all took advantage of commercial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o promote their business. Commercial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during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ompared with that in earlier times, showed markedl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creased amount of information, multiplied forms of transmission, enriched media and quickened speed. During this period, dissemination of commercial information helped foster a sound market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and accelerated supply of goods, becoming a great boost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two dynasties.
Tang & Song Dynasties, commercial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ommodity economy, transaction cost
唐国锋,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 昆明, 650091)。
A
1001-778X(2017)01-016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