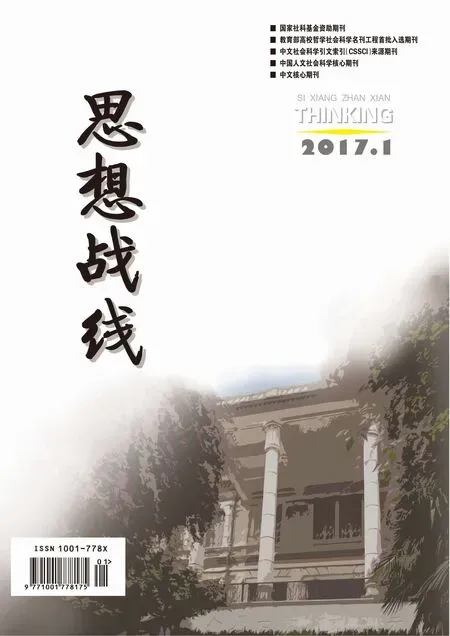重新发现的“原始艺术”
2017-04-11彭兆荣
彭兆荣
重新发现的“原始艺术”
彭兆荣①
“原始”已是一个不易言说的概念,“原始艺术”则更加难以周延圆满地辨析。人类学这一门学科恰巧与之结伴而行,并成为对待这一问题的行家里手。艺术遗产的研究显然无法与之撇开干系。从人类学的角度来透视艺术遗产,不仅可以建立更具学理性的认知逻辑,同时,可以借鉴相关的知识传统,借助民族志的方法,在新的语境中去重新发现“原始艺术”的魅力。
“原始”;“原始主义”;人类学;艺术遗产
小 引
美国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弗朗兹·博厄斯曾对北美西北海岸(Northwest Coast)部落的各种艺术风格、工具、装饰等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他不仅研究当地原住民的“原始艺术”(Primitive Art),*See Boas, F.,Primitive Ar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7.留下了大量艺术遗产方面的著述,还监督美国自然史(Natural History)*Natural History亦翻作博物学,而博物学与人类学具有学科上的“亲属关系”——笔者。博物馆对大量相关原始艺术作品的遴选、收集和收藏工作。*Jonaitis, A.,Art of the Northwest Coast,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6,xiv.他无疑是20世纪最重要的、最具影响力的美国人类学家。通过像博厄斯这样的人类学家们对“原始艺术”的观察、分析和判断,以及对“原始性”——原始社会、原始的思维、原始生活的原始表述,使不同的“原始艺术”成为了人类学家认知社会的重要依据,即通过观察特定的艺术风格去了解和判断对象的性质。比如,在印第安人的艺术表现上,“羽饰”是一件常有的事情,除了头饰外,更是图腾的象征、亲族的标志、思维的表达、美饰的方式。其叙事可以是:“我在故我思”。
我们无妨这么说,博厄斯所开创的美国“历史学派”的一个重要路径从这里拓展:“原始”成为不断被发现、被发明的“传统”。
人类学与艺术发生学
人类学与“原始艺术”的缘分从学科诞生就开始了。“现代艺术的发展和‘原始’形象之间的密切联系清楚地揭示了艺术与人类学的这种关系。”*[美]乔治·E.马尔库斯,弗雷德·R.迈尔斯:《文化交流:重塑艺术和人类学》,阿嘎佐诗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页。人类学在研究上有一个与其他学科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原始主义”。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质,即人类学是建立在“进化”的理念之上;即便在今天,人们对这一理念仍有不少的质疑,但在做实际判断的时候,通常依然遵循这一理念。因为进化涉及“时间”关系的价值观;比如说“进步—落后”“文明—野蛮”“高文化—低文化”,甚至当世人们所说的“发展”等。然而,对艺术的审美和判断却无法照搬“进化”的模式,甚至不能套用其相关的意义。“评论家会质疑公元前2世纪生活在西欧的凯尔特艺术家在描绘动物方面比公元前2万年的马格德林文化的艺术家们更为出色。在审美观点看我们会说没有进步。”*[英]戈登·柴尔德:《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方 辉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125页。具体而言,人们可以相信有许多东西是在进化、在进步,比如有些物种,技术、手段、工具等,都在进化和“进步”,却不能说,现在(现代)的艺术比“原始艺术”“更进步”。这一特质对艺术人类学来说尤其重要;这也是本文的基调。“原始艺术”足以在时间维度中让人们感受“永恒”和“不朽”。在这个意义上,“原始”背叛了时间的物理性。
在人类学家眼里,对于那些史前形态和无文字族群而言,“原始艺术”是人类学家藉以了解对象社会最重要的存在。人类学家在面对每一个具体的作品时,需要处理一个特别的纠结和纠缠,——哲学家擅长“普世价值”和艺术家创造每一个具体的“艺术品”却都是“典型”,——人类学家却要兼顾二者。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写过一些论著,讨论美洲印第安人的艺术,其中包括加拿大的钦西安人(the Tsimshian)的艺术,并专门论述了“双重化现象”,即画像的一边画上一种动物,另一边画上另一种动物,互为镜相。*[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 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6页。一边抽象、一边具像,一边普世、一边个案,人类学发现了人类认知上“悖论不悖”的情状。“原始艺术”竟有如此特质。他在《面具之道》的开章为人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
这里就是美国自然史博物馆,每天从早上10点到下午5点,人们络绎不绝前来参观。宽敞的一楼展厅是专门为阿拉斯加到英属哥伦比亚的太平洋北部海岸的印第安部落而设立的。
也许用不了多久,来自这些地区的展品就会从种族志博物馆迁入美术馆,同古埃及或古波斯的艺术品和中世纪欧洲的藏品一样占据一席之地。因为,即使跟最伟大的艺术相比,这种艺术也毫不逊色,而且在我们对它有所了解的一个半世纪中,它呈现出的多样性比前者更丰富,表现出一种不断更新的天赋。*[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面具之道》,张建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其实,“原始艺术”作品被放到博物馆里,原本是一种对现代艺术的反叛。很久以来,人们都将那些艺术制作与创作者一起置于“野蛮”的范畴;“野蛮”的面目通常都是凶猛的,因为它们或是代表着神圣的庄严,或是代表着自然的禁忌,或是代表着邪恶的力量,或是代表人类的卑微。“差不多所有的面具都是一些真率而生猛的机制。”“这些同样伟大、同样真实的传统技艺,召集只能在市场上的店铺和教堂里见到一些残留物,它们在这里却保留了全部原始的完整性。这种恣意抒发的融汇综合的天赋,这种把别人以为相异之物视为相同的绝妙的资质,无疑显示着英属哥伦比亚一区的艺术的独步天下的特点。”*[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面具之道》,张建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7页。换言之,“野蛮”的东西竟然与“高雅”的艺术同畴并置,对“西方中心”的历史无疑是一个“黑色幽默”。
我们接下来的讨论从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在西方历史上,“原始文化”是“原始主义”(primitivism)的具体。时间上,它针对“现代主义”;从关系上看,它是一个“对话性分类”(a dialogical category)。*Myers,F.,“primitivism”,Anthropology,and the Category of “Primitive Art”,in Tilley, C., Keane, S., Rowlands, M., and Spyer,P.(eds.),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London: SAGE Publications,2006,p.268.但这种分类在福柯的“话语理论”,即“权力—知识—交流”的框架里,浸透了“权力”性质。具体而言,相对“原始”,时间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实指那些“未发展的”“部落的”“史前的”“非西方的”“小规模的”“无文字的”“静止的”“落后的”“异民族的”“野蛮的”的社会形态。“‘原始’这个词通常指那些相对简单、欠发达的人和事,而这些特点是基于比较而言的。”*Rhodes,C.,Primitivism and Modern Art,New York: Thames & Hudson,1995,p.13.在人类学批评家眼里,“‘原始’是‘他性’(otherness)的标志,文化批评的对象也正是从中得来。‘原始’曾经位于人类学身份认同和学术地位的中心领域,它也成了现代艺术实践的中心内容”。*[美]乔治·E.马尔库斯,弗雷德·R.迈尔斯:《文化交流:重塑艺术和人类学》,阿嘎佐诗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页。
其次,鉴于人类学学科性质,决定了“原始文化”成为“民族志的”(ethnographic)一种商标性表述范式。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人类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和表述方式”这样的问题;毕竟人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原始文化”的许多特点、品质,正是人类不断求索的“自然”“和谐”的形态和状态。“未来的过去性”——即历史越往未来趋动,人类越是发现“美好”原来在过去。比如与自然、生态、环境、物种的和谐关系,在“图腾制社会”已然非常理想。在许多方面,“原始的野蛮人”正在教育、教导和教训着那些自诩的“现代的文明人”。这大概是人类在不断的追求中所始料未及。人类湮灭了这种形态、中断了这种情态、破坏了这种状态,却又在致力寻求它,以期找到回归的途径。这种悖论越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随着对“原始”的不停地发现,越加显现出来。
当“原始”成为历史的一种标签、族群的一种标识的时候,它事实上已非完全的客观性,而是在某种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被制造出来的社会价值。它的对立面是“现代”。西方的“现代”代表“文明”,以外的其他便属于“原始”和“野蛮”。毫不讳言,人类学这一学科也“参与”了那一个特定时代的价值制造工作。然而,困难的是,当我们使用“原始”这一概念时,却在现代社会和文化看到其身影,特别在艺术形态和形式中。*Layton, R.,The Anthropology of Ar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p.1.我们相信,所有的文化都是以人为主体的认知性产物;文化所以不同,在于思维和表述的差异:共性是思维性认知;差异是多样性表述。缘此,人类学家常常使用诸如“野性的思维”“原始思维”“神话思维”“前逻辑思维”“原逻辑思维”等术语;其中必包含二者之要。博厄斯在《原始艺术》中开章明义:
我们以两条原则为依据——笔者认为研究原始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该以这两条原则为指导:一条是在所有民族中以及现代一切文化形式中,人们的思维过程是基本相同的;一条是一切文化现象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美]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金 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前言”,第1页。
然而,思维的同质性是有限度和限制的,特别是在跨越时间链条的“断裂”时,需要特别谨慎。这一点在西方学者那里常显悖论而无法突围,根本原因在于死抱着“欧洲中心”不放,将自己置于“现代”(包含着“文明”“进步”等语义),而将非西方的“他者”——按照萨义德的“他者说”,东方他者是被欧洲人凭空制造出来的,东方他者原是一种思维方式,*[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2页。一并置于“原始”(包含“野蛮”“落后”等语义)范畴,并配合以“社会进化论”要旨。这样的设限在凸显权力的同时,又将自己推到了矛盾深渊,不能自拔:西方不仅成为历史的“弑父者”,也是自我遗续的“否定者”。
正因为这种无法克服的矛盾,不仅致使在判断上的失误,甚至在这一概念的使用上都显得越来越气急。比如,人类学家在很长的时期内也一直认为印第安人的文化不具有内在协调性,因为它们“太原始”了。这一悖论和矛盾事实上早就引起人类学家们的注意和警惕,他们意识到,“原始社会”有许多地方,特别是所谓的“艺术形态”并不逊于现代社会。因此,选择使用“原始”很可能是一种不幸的事情,只是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技术性术语(technical tern)被广为接受,以至于难以避免。*Evans-Pritchard, E.E.,Social Anthropolog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2,p.7.有的学者鉴于“原始”这一概念中羼入了许多模糊不清的语义和意义,尤其是在艺术之阈更是如此,因此建议废止使用这一概念。
导致这种混乱有两个重要原因:(1)将所谓的“原始文化”与“野蛮文化”同眸,这种政治话语的“固执”,成为难以逾越的樊篱。症结在于,对于西方而言,只有保持政治上的固执,才能保持“话语”的制定权,也才能够保持“中心/边缘”“文明/野蛮”的基本规范。(2)将“原始艺术”置于凝固的状态。其实,任何社会都有过“原始阶段”,也会留下各种“原始艺术”;当然,它们也都在变化,特别的艺术的转型。比如北美西北海岸的原住民艺术,到了19世纪末,已经发生了转型,这不仅包括外来移民的进入,出现了大量非原住艺术,即使是原住民艺术也因此产生变化。*Jonaitis, A.,Art of the Northwest Coast,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6,xvii.
高贵的野蛮人
“原始艺术”作为“原始主义”这一历史悖论的具体,集中体现在所谓“高贵的野蛮人”(英语:Noble savage,法语:Bon sauvage)的表述上,—— 一个西方制造的历史神话。这一神话的发明者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尽管已经去世两个多世纪,但他那种对当世社会和价值观的叛逆,某种程度上成为时代变革前夜的“预言家”。在他的散文中,“高贵的野蛮人”这一神话的拟人化表述,以及对“野蛮生活”浪漫的歌颂,藉于表达对自然的纯美的描述和向往。*Rousseau, Jean-Jacques,A Discourse upon the Origin and Foundation of the Inequality among Mankind,By John James [i.e., "Jack;] Rousseau, Citizen of GenevaLondon: R.and J.Dodsley.1761,[1755].此后,对“高贵的野蛮人”神话的赞颂和批评,也成为西方学界特别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持续性传统,因为人类学原本研究对象就是“高贵的野蛮人”。不少人类学家都参与了从不同角度的阐释和批评。马文·哈里斯说:
虽然在人类学家对诸如原始形态中的特性和特点的表述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对象从霍布斯的“war of all against all”*“war of all against all”出自西方近代哲学家霍布斯的名著《利维坦》,表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对此的翻译和解释多种多样——笔者。到对卢梭的“Noble savage”——找到人们如何已经从结束了自然状态,到达了他们现在的身着制服的完美时尚的解释。*Harrison,M.,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New York:1968,pp.38~39.
无论西方的学术界对这一表述的理解、阐释存在着多大的差异,其中有一个共识:即“高贵的野蛮人”是18世纪法国哲学家卢梭的一种理想,用以表示“自然纯洁的状态”——高贵、智慧,——以作为与现代文明腐蚀和堕落形成对比。*Ellingson, T.,The Myth of the Noble Sav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1,pp.1~2.“高贵的野蛮人”与他的“返回自然”的主张一脉相承。无论“高贵的野蛮人”如何带有想象性,无论卢梭本人是如何美化原始状态,在两百多年的演化中,这一概念不断地被“过度阐释”,其语义也随之扩大。重要的是,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有新的“发明”和“发现”。
就西方制造这一概念的历史语境而言,“高贵的野蛮人”是一个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的描述。在欧洲人的观念中,最初的“野蛮”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对外国人的“观察”而做的带有旅行民族志式的描述,也是早期人类学研究中常用的一个术语。那个时代正是殖民主义向世界扩张的时期。*Ellingson,T.,The Myth of the Noble Sav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1,p.11.因此,“野蛮人”作为“他者”是一个具有政治旨意,同时也是充满歧义的概念。“文化史学家开始对‘他者’这个概念发生兴趣,只是较近的事情。‘他者’(Other)首写字母为‘O’,或者是‘A’,因为法国理论家在‘他者’(l’Autre)的讨论中领先一步。用多元方式思考与自己不同的人,而不要把他们当做无差别的‘他者’来对待。”*[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 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9页。西方人对原始主义的制造一直存在着矛盾情结,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和变迁,其语义也随之产生一些变化。一方面,“高贵的野蛮人”这一句式本身就是矛盾的,“野蛮人”作为他者,本身就是西方“文明人”我者的反面、对立面。在艺术处理的方式上,把诸如印第安人与古代的蛮族人等同起来,并将“他者”形象视为“怪物族类”来对待和描述。*[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 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0~189页。另一方面,野蛮人作为历史演化的一种“自我的过去”的强烈反省——“我者”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具有某些前文明时态的淳朴、善良和自然之子的特点,这其实包含着卢梭在制造这一概念时所包含的意思,只是越到后来,距离本义越来越远。
在一些文学艺术作品中,“高贵的野蛮人”常常作为“伪善的文明人”的反面、对立面。在英语世界里面,“高贵的野蛮人”作为关键词,出现在约翰·德莱顿的英雄诗剧(Heroic drama)《征服格拉纳达》(The Conquest of Granada,1672年)中,剧中,一名伪装为西班牙穆斯林的基督教亲王,自称为“高贵野蛮人”。1851年后,这个词成为了修辞手法中的矛盾语。在文学的表现中,“高贵的野蛮人”也常常表现为“感伤主义”的怀旧情调,这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对旧时代的一种反映;此基调又与卢梭等“返回自然”——将物质贫乏但仍保持淳朴的生活方式和自然状态的主张相契合。这样的社会价值的运行轨迹也很自然地会反映到艺术家的观念导向,并以艺术的方式加以呈现,出现了大量以这一主题的艺术表现。比如高更的《塔希提岛》就是一个例子,那里到处是自然情调,那里没有工业革命带给人民的精神压力,那里没有为了物欲所进行的生死搏斗,有的只是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相协和相融。
这一旋律在19世纪弥漫在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中,有着集体性的反映。此时的“原始主义”一方面与进化论的理论,以及由此所带动的社会进化论的思潮相联系,人类学在这一时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这一时期的人类学视域中的“野蛮人”并不具有“高贵”的品性,以配合殖民主义的推进。反而在文学艺术领域中,还仍然保持着延续18世纪的主题。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曾经写过一篇以“高贵野蛮人”为题的杂文。到了20世纪,“高贵的野蛮人”越来越多地成为西方人对西方文明进行反思和反省的典型语句。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作家J·D·塞林格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自1951年问世以来,深受读者和评论界的追捧。这是一部以“原始主义”为语调的小说,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崇尚原始文化,渴望返回童年和自然,他厌恶现代生活、成人世界和文明教化,他有着浓厚的原始主义思想,是当代的“高贵的野蛮人”。
人类学在20世纪中叶以后,出现了对传统“他者”的全新视角,从学科角度进行了反思,不少人类学家从历史主义的角度,重新发现了原始社会中那些以往不为人知的特点和优势。比如,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在其1972年出版的《石器时代经济学》第一章“原初丰裕社会”中,即揭示了人们对原始社会“野蛮人”的误会和误解,以及人们对他们生活状态和环境的无知。这些所谓的“野蛮人”不仅生活在快乐中,而且“他们生活在物质丰富之中。”*[美]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2页。比如非洲丛林的布须曼昆人(Kung)即为代表。同时,在一些电影、电视和绘画等艺术中,大量出现的这样反思性的主题。电影《上帝也疯狂》便是代表。*《上帝也疯狂》(The Gods Must Be Crazy)由加美·尤伊斯编剧并执导。1980年(第一部)由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出品、上映。电影讲述了现代文明与原始社会的激烈冲突,对现代文明和所谓“文明人”进行了鞭笞,相反,赞颂了“基”这一原始人代表所表现出的高贵品质。
在人类学的历史中,“原始”是“进化”的产物。“高贵的野蛮人”不啻为社会进化论的一个“缩影”。众所周知,人类学这一学科的产生正是以进化论为学理依据。比如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中,一开始就确立了这样的基调:
如果我们沿着射几种进步的路径上溯到人类的原始时代,又如果我们一方面将各种发明和发现,另一方面将各种制度、按照其出现的顺序上逆推,我们就会看出:发明和发现总是一个累进发展的过程,而各种制度则是不断扩展的过程。*[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新译本)上册,杨东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3~4页。
摩尔根的进化理论不仅具有线路发展的图式,更有具体的发明和发现的客观指标。比如在“野蛮社会”阶段,人类经历过“低级阶段”(标志为制陶术的发明),“中级阶段”(标志:东、西半球出现的作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驯化,冶铁术的发明)和“高级阶段”(标志:标音字母的出现和使用文字的开始)。*[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新译本)上册,杨东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0~11页。这些历史上的发明和发现,以及材料的搜集在摩尔根那里所试图“证明”人类社会的“线性”进化阶段,后来受到学术界的强烈质疑。
今天,人们误以为后殖民主义的“东方主义”学说是当代社会精英反思和反叛的杰出成就,殊不知,在社会进化论那里,“文明/野蛮”早有型塑。这一历史事实性的“我者/他者”的建构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形成的价值观;于是才有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东方主义”。“被制造的价值”不仅只是历史上的殖民政治伎俩,同时也在制造艺术品。极具悖论性的争论是:艺术作品却作为“他者”被高调地请进了博物馆、艺术展览馆;那些“东方国家”的古代艺术品在法律上不受限制地进入到西方国家和收藏者的密室里。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的艺术品进口的国家,在这方面,美国的法律秉持对文化财产和艺术品以不干涉财产拥有者对私人财产进行处置的原则。因此,美国可能也是世界上唯一对艺术品出口不加限制的国家。总体上说,美国的法律除对那些在政治上受限制和危险的物种、物品外,几乎没有任何法律限制艺术品和文化财产的进口。与此同时,美国的法律也绝对不会同情那些外国政府宣称其归还被盗古董的权益。*Barnara T.Hoffman,“International Art Transactions and the Resolution of Art and Cultural Property Dispites: A United States Perspective”,in Art and Cultural Heritage: Law, Policy and Practice.(ed.by Barnara T.Hoff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59.这大抵是“高贵的野蛮人”和“野蛮的高贵人”的最大悖论:即当那些所谓的“高贵”的西方人,在制造东方主义的“野蛮人”的时候,无意中也“制造”出那些东方艺术品和文化遗产的“高贵价值”;而自己却充当了真正意义上的“野蛮人”的角色。
“原始形态”的再发明
法国画家让·雷诺阿在记述他的父亲的时候曾经有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将原始的、原著的、民间的艺术称为“皇上的艺术”:
描写雷诺阿在意大利旅行的著作已经出版的就有不少,其中有些著作史料丰富。我从和我的父亲的交谈中得到如下的印象:他最初出发去意大利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艺术的热情逐渐冷却了下来。然而随着他对意大利人民的加深了解,他对他们更加崇敬了。他说:“意大利人在贫穷中显得高贵,他们善于用皇上般的动作耕田!”通过“皇上”,他深入地、完整地了解了表现“皇上”的艺术——原始艺术,如乡村教堂里一幅来自无名氏的壁画——契马布埃或乔托的先驱,12世纪的柱廊,圣弗朗索瓦某个弟子住过的简陋的修道院。*[法]让·雷诺:《父亲雷诺阿》,载贾晓伟《美术二十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157页。
在这里,“原始艺术”指的是民间智慧以及表现形式,包括这些民间艺术的肥沃土壤,也是艺术家成长的地方和创作伟大作品灵感的源泉。
艺术遗产的一个本质特性,即艺术本身是一个具有时空关系的连续性过程,虽然每一个艺术家在特定的时代、时段所呈现出的艺术创作具有鲜明的个性,却同时构成了特定群体认同和时代的继续与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始的(具有时间特征)、地缘的(具有空间特征)和族群性(具有认同特征)的艺术品和艺术创作,都具有遗产的性质。这样,以往的原始土著“野蛮人”等带有“污名化”的指称,也就有了重新定义和反省的可能。在这样的反思原则之下,“原始艺术”中的“美”也就有了新的解释:“美感是大多数人天生就具有的,和我们的智识高低无关。这点我们可以从原始人的艺术创作中清楚地看到。”“最近这些年,有许多和这个主题相关的研究正在进行。我们现在也已经对人类学家所知最原始的人类(西元前3万到1万年前)的一些艺术创作,具有相当明确的知识。在旧石器时代的史前艺术中,现存的一些例子,可以被划为三个地理区域(法国的坎塔布里恩区,Franco-Cantabrian)西班牙东部和北非,其中位于西班牙阿尔塔米拉的岩洞动物素描最为著名(Altamira)。”*Herbert Read:《艺术的意义:美学思考的关键问题》,梁锦鋆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104页。从艺术遗产的角度看,且莫说当代世界的艺术创作中出现的“原始艺术”的“采借”甚至“盗用”之风,即便是完全看到不到受“原始艺术”影响痕迹的创作,也都不可能是传统的“断裂性”产物。因为,人类的认知、知识和表述是连续性的。就此,“皇上的艺术”也因此有了新的品质:艺术遗产之“原始性”(原初性)的发生学原理。
无论是“高贵的野蛮人”还是“皇上的艺术”,都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具体地说,是一种时代的“制造”。“原始主义”的制造与欧洲殖民主义发展几乎是并行的。因此,这种被制造的价值本身就存在着悖论,特别是当它附会到具体的事务上时更是纰漏迭出。比如,在艺术领域对“原始主义”的主导和主张就是这样:一方面,现代艺术需要“原始艺术”来帮衬、装点,以体现“古”;如果这只是一个时间的线性关系,那就简单得多;就像我们的今天也将成为未来人们的“过去”一样,“原始”只是指某种事情的“原来开始”。可是,“我者”制造的“他者”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建立历史时间表中的序列关系,而是要制造一种高低、贵贱等级,特别是在权力表述上,具有政治意义的“排斥关系”。另一方面,现代艺术中大量借用“原始主义”的东西——价值、理念、风格、符号、元素、手段、技法等等。所以,“原始主义以原始为先决条件。深入艺术的原始主义,我们就可以发现艺术‘原始的’作品的核心。在我们划分的浪漫的、情感的和理性的或形式的几种情况下,都有艺术作品被现代艺术家认为是原始的,并因此被欣赏,产生影响”。*[美]罗伯特·戈德沃特:《现代艺术的原始主义》,殷 泓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223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始艺术”具有超越时间、地域、风格等的特性和特点,而成为一种具有表述上的“范式”价值。
有意思的是,当世的人们有鉴于全球化的社会现实所带动的潮流,这股潮流又极大地损害了仍处于相对封闭的地区的族群文化时,就像那些生物物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其生活境遇遭到了灭顶之灾,生存难以为继时,保护生物多样性,进而保护文化多样性于是也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轰轰声响中发出嘤嘤细语;于是,“原始”又在不同程度上转换面目,改装上台,诸如“原生态”等表述再次“悖论性”地登上语义场。*参见彭兆荣《原生态的原始形貌》,《读书》2010年第2期。这种“静静的革命”,在原本已在反思、甚至批判的“原始”意义上注入了新的意义。更有甚者,西方学术界试图在超现实主义的主张中,重新释用“原始”,将“原始主义”作为“现代主义”批判的工具。*参见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1页。那些原属于“原始文化”范畴的用语、法术、魔幻等重新被派上用场,充斥在电影、美术、绘画、美学、技艺等诸领域,比如电影《哈里·波特》中所使用的巫术和法术。
“原始艺术”的各种表述的意义和意思虽充斥着矛盾,人们却表现出使用它的特殊偏爱。作为艺术遗产的一种历史特殊和特别的形态,以下几个层面需加以分析:(1)“我者的过去”就是“他者的现在”,二者形成历史遗产关系。(2)原始的土著艺术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并不是作为“艺术多样性”出现和存在的,而是作为西方现代艺术的对立,是作为西方“我者”的陪衬而出现的。(3)原始的土著艺术的独立性却并不因为“他者”身份而丧失自我的艺术价值。土著艺术具有自我的价值逻辑;宛若特殊的植物在特殊的环境和土壤中自我生长,绽放奇异的花朵。本土文化成为土著文化生产的一种传统方式。(4)西方的政治话语在当代的反思和反省中,出现了明显的对“我者”的批判意识,从而将土著的“野蛮文化”抬高到“高贵”甚至“皇上”的地位。如此的“转变”在政治上无疑是虚伪的,但在艺术范畴,正面和积极的因素显然更多,至少“原始艺术”被置于更为公平和公正的地位。(5)西方的艺术传统在多元化的发展变化中,也会被原住艺术的鲜明特色所吸引,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借、采纳原住艺术的形式、符号和元素,充实了现代艺术。“现代主义艺术的叙事不必暗示土著绘画只是西方绘画的等价物。批判的话语,不管是不是现代主义的,都不会这么头脑简单的。”*[美]乔治·E.马尔库斯,弗雷德·R.迈尔斯:《文化交流:重塑艺术和人类学》,阿嘎佐诗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8页。但原始的土著艺术深刻地影响现代艺术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6)影响从来都是双方的。原始、原住性的艺术在这样的互动中,自我传统也存在被撕裂的危险。“皇上的艺术”作为一个比喻,——如果排除雷诺阿个人的见解或理由,它是一个具有“双刃剑”的功效。“原始(原住)艺术”的“被打杀”和“被棒杀”,危险系数一样大。
“原始”的表述、意义、价值、行为、符号已然成为、作为一种新的、待“发明”和“发现”的历史库存,它存放着大量的存货,有形的、无形的,我的、他的,过去的、现在的,都无法抛弃,要可以被拿出来用,因此,不断的重新发现“原始”已然成为一种常态。
(责任编辑 甘霆浩)
Rediscovery of “Original Art”
PENG Zhaoyong
“Original”has become a concept that is hard to define. And it is even more difficult to discriminate“original art”satisfactorily. Anthropology happens to have such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original art that it has become a most useful tool for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It is apparent that the study of artistic heritag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anthropology.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analyze original 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more rational cognitive logic and rediscover, with the help of the methodology of ethnography, the charm of “original art” in a new context.
“original”,“primitivism”,anthropology,artistic heritage
彭兆荣,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厦门大学教授(一级岗)、博士、博士生导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11ZD123)首席专家(重庆,401331)。
G112
A
1001-778X(2017)01-013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