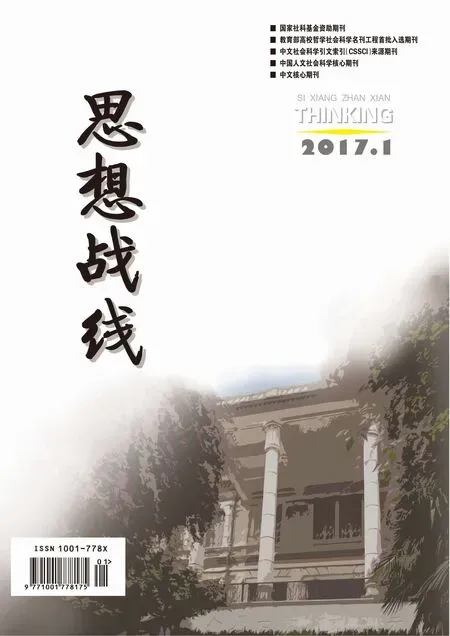20世纪早期费孝通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学术取向
2017-04-11段塔丽
段塔丽
20世纪早期费孝通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学术取向
段塔丽①
20世纪早期,费孝通以“认识并改造社会”、关注民生问题、“从实求知”以及坚守功能主义分析范式为其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学术取向。这一学术取向源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经济的衰败、乡土中国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社会调查之风在中国的广泛兴起。费孝通早期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学术取向及其实践,不仅为早期社会学的“本土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当代中国社会调查研究走向本土性、乡土性、系统性和整体性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示。
费孝通;社会调查研究;学术取向;社会学“本土化”
一、费孝通与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的调查之风
现代社会调查,兴起于西方。“作为研究社会的一种实践方法与技术手段,社会调查是社会科学界使用最多的研究方式之一,也是人们认识社会现象、探索社会问题的有力工具。”*黄盈盈,潘绥铭:《中国社会调查中的研究伦理:方法论层次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社会调查方法传入中国后,被当时知识界所接受和广泛运用,据有关学者的考证,社会调查大致于鸦片战争前后从西方传入我国,清末新政时期开始在我国兴起,民国以后得到进一步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进入了勃兴阶段。*赵金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农村社会调查勃兴的原因探析》,《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20世纪30年代初,当费孝通还是燕京大学社会学专业的一名大学生的时候,就对社会调查“情有独钟”。究其原因,这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广泛兴起的社会调查之风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一方面,“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衰败、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和各种新文化启蒙思潮兴起的刺激下,中国社会各界掀起了一股关注农村、调查农村和变革农村的浪潮”。*李金铮:《定县调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里程碑》,《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另一方面,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思想文化界变得非常活跃,社会改造的呼声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在西方兴起不久的实地社会调查理论和方法传入了中国,关心国家命运的有识之士、社会学者、归国留学生开始利用这种方法和理论指导实地社会调查研究工作。*赵金朋:《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学生时代的费孝通亲眼目睹和感受到了当时国内普遍兴起的社会调查运动的影响力。据他本人回忆,1933年初夏,费孝通曾应邀赴山东邹平实验区参加梁漱溟先生主持的乡村建设运动。*根据李培林等人的观点,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与当时的社会调查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两者都意味着“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略有不同的是,前者代表着知识分子“认识社会、改造社会路径的变化”;后者反映了知识分子“认识社会、经世治学方法的转变”。参见李培林,渠敬东等《社会学经典导读》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页。尽管费孝通事后对这场乡村建设运动中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做法感到不满,*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48页。但就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而言,他们不畏艰苦、身体力行地深入农村,教育和启发农民的思想觉悟,培养农民的团体合作精神的做法,对包括费孝通在内的青年知识分子走出书斋、了解社会,探索民族复兴之路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诚如李培林等所总结的,20世纪早期的社会调查运动,从其内涵和价值取向来看,它实际上体现的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信仰,一种人生道路和一种救国方法”*李培林,渠敬东等:《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6页。。它对青年时期费孝通社会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二、费孝通早期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学术取向
费孝通早期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学术取向,源于他在学生时代所接受的一套系统的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知识,以及日后长期从事的社区实地调查研究工作经验的积累。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认识并改造社会”作为调查研究工作的宗旨和目标
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学界,社会学在教学与研究上存在着两种偏好:*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8页;费孝通:《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收入《费孝通文集》第1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32页。其一是运用欧美国家的社会调查方法描述中国社会;其二是热衷于用中国的材料套用西方学者的理论。而对于年轻学子的费孝通而言,认识并改造中国社会,是费孝通早年从事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的一个出发点。早在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就将“认识中国社会”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和动力。费孝通常说:“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要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云南三村·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页。进而才谈得上改造中国社会。而要认识中国社会,就必须学会从实地调查入手。“以实地研究明了中国社会”,*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48页。进而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这正如当时在国内从事平民教育运动的晏阳初先生所说的:“调查的目的,既是为了了解事实,但事实的了解不是工作的终了,而是工作的开始。所以调查工作不是为调查而调查,必须要着眼于社会的实际的改造。”*晏阳初:《〈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序》,载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年,第2页。至于为什么要选择实地调查,费孝通曾在《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的编后记中这样写道:
现在中国念社会学的学生免不了有一种苦闷。这种苦闷有两个方面:一是苦于在书本上,在课堂里,得不到认识中国社会的机会;一是关于现在一般论中国社会的人缺乏正确观念,不去认识,……我们应当走到实地里去,希望能为一般受着同样苦闷的人找一条出路。*费孝通:《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载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怎样做社会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7页。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35年,费孝通在结束了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之后,毅然携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进行实地调查。他们希望自己的举动,能够“为研究社会的人提供一个观点,为要认识中国社会的人贡献一点材料”*费孝通:《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载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怎样做社会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7页。。尽管在大瑶山调查过程中发生了不幸,使他丧失了志同道合的妻子,自己也受伤严重,但困难和阻力都无法改变他开展社会调查,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决心和初衷。1938年,费孝通从伦敦留学回国,他没有留在大城市过舒适安逸的生活,却义无反顾地进入到条件艰苦的云南内地农村去做调查。究其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等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云南三村·序》,载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页。
(二)坚持“实事求是”“从实求知”的科学研究态度
如果说“认识并改造社会”是费孝通早期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指归和远大抱负的话,那么,“从实求知”与“实事求是”,则是他从事社会调查工作中所持的基本态度和一贯主张。在费孝通看来,坚持实地调查,是认识中国农村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正如费孝通自己所说的:“我学术活动的起点是实地调查,……实地调查是我学术研究的基石。”*费孝通:《〈中国乡村考察报告〉总序》,《社会》2005年第1期。尽管当时社会学界中的学院派对于实地调查研究并不看好,然而,费孝通却以“追求知识的劲”,一往无前地去探索。他曾说:“要解决具体问题必须从认清具体事实出发。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应是解决怎样建设中国这个问题的必要前提。科学的知识来自实际的观察和系统的分析。”*费孝通:《云南三村·序》,载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页。正是从这点出发,他坚持从实地观察方法开展社会问题的研究。并坚信:“只有实事求是得来的知识,才能成为促进人们生活的知识。”*费孝通:《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1996年,第198页。
纵观费孝通早期所从事的一系列社会调查,可以说都是在始终如一地奉行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去总结经验,也即“从实求知”的科学态度,并将其贯穿于他所从事的各类社会调查研究工作之中。
(三)关注民生、并以解决农民生计问题为己任
利用信息技术能够为幼儿提供正确的示范,形成正确的引导 幼儿教学是视觉的、听觉的、口语的活动,甚至是触觉的活动[2]。通过多种材料的对比,能够选择性地为幼儿呈现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的阅读材料和适当的教学媒体,给幼儿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仍是一个乡土气息十分浓厚的国家,然而,在外来资本主义和中国本土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下,中国传统农村经济遭遇空前的危机与困局。当时农村问题被视为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核心,许多关心国家命运、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到挽救农村危机的运动中。费孝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他的农村问题调查的。费孝通根据自己在江南水乡的江村和大西南的云南禄村所做的实地调查,感受到当地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农民苦于找不到生活出路的悲惨情状。在他看来,要解决农村问题,必须首先认识和了解农村。“农村调查是达到我们认识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基本的手段和途径。”*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怎样做社会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对此,他特意将自己社会调查研究的中心放在农村社区。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我是从农村调查人手的,并一直以认识中国农村社会为社区研究的主体。”*费孝通:《〈中国乡村考察报告〉总序》,《社会》2005年第1期。1935年,他携新婚妻子王同惠到广西大瑶山的民族社区调查,受伤后回家乡太湖边上的弓弦村所做的调查,以及后来从英伦回国后进入云南内地开展的一系列社会调查,都是以农村调查为中心,从农民的利益出发,为农民摆脱贫困、解决生计问题作为自己的学术使命。对此,美国学者大卫·阿古什博士曾撰文称赞他,其所从事的农村调查,“他所观察和搜集的材料比我们迄今看到的有关中国农民的著作更准确,内容更丰富和有价值”。*[美]大卫·阿古什:《从禄村到魁阁》,载潘乃谷,王铭铭《重归 “魁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四)将“功能主义”分析范式贯穿于调查研究工作的始终
功能主义堪称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最为久远的理论流派之一。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它萌发于经典社会学家孔德、斯宾塞,后经人类学家布朗、马林诺夫斯基的努力得到进一步发展。费孝通的功能主义思想体系是他在英国留学期间,在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逐渐成熟的。同时他吸取了法国社会学大师涂尔干和英国结构功能学派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功能观点,使自己的功能理论和方法增添了新的内容,从而具有了“本土化”特色。*唐 成:《费孝通社会研究方法探析》,《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费孝通是怎样理解功能和功能主义的呢?据刘豪兴的研究,费孝通的功能主义思想包括三个方面:*刘豪兴:《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社会研究方法述评》,《社会》2004年第11期。首先,他从孔德社会学的整体观和系统论出发,认为社会和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这一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各项社会制度。因此,在研究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时,必须将它置于一个宏观的社会文化体系之中进行分析。其次,他将“功能”理解为一种处在同一系统的整体之间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第三,他提出社会整体不仅有层次之分,而且整体处在一个经常变化的系统中。
费孝通的功能主义思想体系是他早期从事社会调查研究的一根主线。他的《江村经济》一书,就是一个很好地运用功能主义分析农村社区社会结构的典范。该书调查研究的对象虽只是一个拥有2 000多人口的小型农村,但作者却从功能主义研究方法入手,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然后在解剖“麻雀”的过程中,看到当时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等问题,进而提出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侵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的见解。*费孝通:《云南三村·序》,载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页。这部书英文版出版后,曾得到有关学者的高度评价,认为它表达了“人类社会结构内部的系统性和它本身的完整性”,“为功能分析或是系统结构分析作出了一个标本”。*费孝通:《云南三村·序》,载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6页。其次,抗战时期,他在云南禄村调查当地农民的土地问题时,更是自觉地运用功能主义思想指导其实地调查研究。如他在分析当地农村的土地问题时,指出:“土地问题决不能视为一个独立的问题,一地方土地制度的形态其实是整个经济处境一方面的表现。”*费孝通:《禄村农田·导言》,载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9页。此外,抗战时期,他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附设的社会调查研究室(魁阁)工作期间,曾尝试着集合多方面的人才,在同一具体问题上,做有系统的研究,这也是运用功能主义指导其社区研究的一种尝试。*许化宁:《费孝通社区研究方法考析》,《学理论》2010年第2期。
三、费孝通早期社会调查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对社会学“本土化”的贡献
(一)创立了独树一帜的“费氏本土方法论”,推动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实践
20世纪30年代初,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社会学尚处于草创阶段,有关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不少还在沿袭西方的一套做法。费孝通在明白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并没有对了解及改造中国社会有过任何贡献之后,坚定了他从乡土中国的国情出发,有选择地吸取国外一些较为成熟的理论与方法,分析和比较每个具体社区社会现象的异同,*李友梅:《费孝通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5年,第1页。逐渐在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探索出一套独具特色的“费氏本土方法论”。*官欣荣:《从“云南三村”看费孝通社区研究与本土方法论的贡献》,《学术探索》1995年第1期。正如有学者所说的:“费孝通是上世纪30年代初以实地研究开拓中国学术发展新路向中的人们的杰出代表。”*丁元竹: 《费孝通的治学特色与学术风格》, 《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2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调查实践中,费孝通对中国农村、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民族地区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开辟了以实地调查为特色的社会研究方法,对推进社会学本土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中,应用类型比较方法进行社区研究,堪称费孝通对推进社会学“本土化”实践上在方法论上的一个创新。它对社会调查方法和社会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不仅开阔了社区研究的视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和了解。”*许化宁:《费孝通社区研究方法考析》,《学理论》2010年第2期。
(二)培育出了一支优秀的社会学专业研究团队,产出了一批享誉中外的“本土化”社会学成果
开展社区实地研究,推进社会学“本土化”,离不开社区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团队的组建。这一工作先由吴文藻先生开其先,后由费孝通先生将此“接力棒”传递下来。抗战时期,费孝通从英国留学归国,家乡的沦陷,使他被迫由越南转道战略大后方的云南昆明,并在此聚集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从事艰苦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在他的社会学研究室里,先后有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古苞、张宗颖、胡庆钧等多位青年学者参与,从而形成了一个社会学专业研究团队。在战时艰苦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中,费孝通坚持以“传、帮、带”的方式培养新人。一位当年在那里工作过的年轻学者描述了“魁阁”(即“社会学研究室”的代称)的工作氛围:“自由探讨的空气、尊重别人意见、公开辩论和友爱的精神。”*[美]大卫·阿古什:《从禄村到魁阁》,载潘乃谷,王铭铭《重归“魁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1页。费孝通让年轻学者研究他们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在训练中帮助他们、培养他们。从1940~1945年的几年间,费孝通和他的学术团队不畏艰难,坚持实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费孝通《禄村农田》、张之毅《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与商业》;史国禄《昆厂劳工》、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的研究》;蒋旨昂《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等等。这些成果作为中国早期人文区位学研究的典范,为早期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和社会学本土化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成就也因此受到当时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赞誉,*当时知名社会学家吴景超博士曾撰文对费孝通等学术团队在抗战期间取得的突出成绩给予高度评价:“在过去的十余年, 中国的社会学者的主要工作, 在于介绍西洋的理论。真能利用西洋的理论与方法, 到中国的社会里去做实地研究的, 可谓绝无仅有。现在费先生带领着一班青年的社会学者, 在云南切实地做了许多实地研究的工作, 而且已有好几种油印成书。我相信这种风气的提倡, 一定会替中国的社会学奠定稳固的基础, 盖起庄严的建筑。”《新经济》1946年第6卷第9期,第1194页。还有西方学者弗里德曼称赞费孝通所率领的这支学术团队所取得的成绩时也说:“可以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北美和西欧之外,中国是世界上社会学蓬勃发展的地方,至少从这类知识分子的水平方面看是如此。”Mautice Freedman,“Sociology in and of China”,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3,1962,p.113.转引自阎 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57页。被国际社会学界誉为“中国学派”。*李培林:《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2期。而费孝通则是这支学术团队中的领军人物。
(三)提出了“乡村工业化”的主张,为复兴中国乡村经济提供了模式选择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广泛分布于乡村中,与广大农民的生计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使得乡村工业成为广大农民生活的一项重要补充形式。但自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渐渗透,“机器取代了手工,工业由分散走向集中,工业逐渐脱离乡村而独立,而尚未脱离的在与机器大工业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因而都市工业的发达促成乡村工业的崩溃”。*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46页。费孝通在深刻分析了上述乡土社会农民生产与生活方式之后,又通过将战时大西南内地乡村工业发展的现状与战前江南地区都市工业作对比,提出了他颇具特色的“乡土工业”的发展思路:即通过“工业下乡”的方式,推动中国农村“乡土工业”的发展,这不仅可以实现农村中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而且可以实现农民收入增加的目的。有必要一提的是,此处费孝通所说的“乡村工业”,并非简单地恢复中国传统的乡村手工业,而是指发展现代农村工业。*郑杭生,李迎生: 《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2页。在他看来,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农村,发展“工农相辅”的“乡土工业”,“既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出路,同时也是解决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办法之一”。*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47页。
抗战时期费孝通通过在云南内地农村不同社区的研究经历,强调在农村发展“乡土工业”的同时,为防止农村生产资料——土地所有权的过分集中,主张现代农村工业的发展应以“合作”精神为根本原则,同时还必须注意引进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和方法。在费孝通看来,只有引进科学生产技术和组织以“合作”精神为原则的新工业,才可以达到复兴中国乡村经济的目的。*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48页。上述费孝通关于“乡村工业化”发展道路的主张,包含着费孝通对乡土社会内生机理的深刻认知和精妙分析。正像有学者所称道的:
在民国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脉络之中,费孝通是最有识见、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费孝通通过实地调查,以其宽阔视野,对中国农村经济做了贯通而深入的研究,发表了比其他学者更加全面和独到的见解,为当时乃至未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破解之道。*李金铮:《“研究清楚才动手”: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农村经济思想》,《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责任编辑 陈 斌)
On Fei Xiaotong’s Academic Orientation to Social Investigation & Research in Early 20th Century
DUAN Tali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Fei Xiaotong made it his academic orientation towards social investigation to “know and reform the society”, to be concerned about people’s livelihood, to “seek knowledge from facts” and to follow the functional analysis model. Such an academic orientation resulted from the reality of the age he was living in: declining rural economy, starving peasants and popularizing social investigation in China after the May 4th New Cultural Movement. Fei’s academic orientation and work not only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early Chinese sociology but provided an enlightening model for China’s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o move towards locality, rurality, systematization and integrity.
Fei Xiaotong,social investigation & research,academic orientation,localization of sociology
段塔丽,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 西安,710119)。
A
1001-778X(2017)01-0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