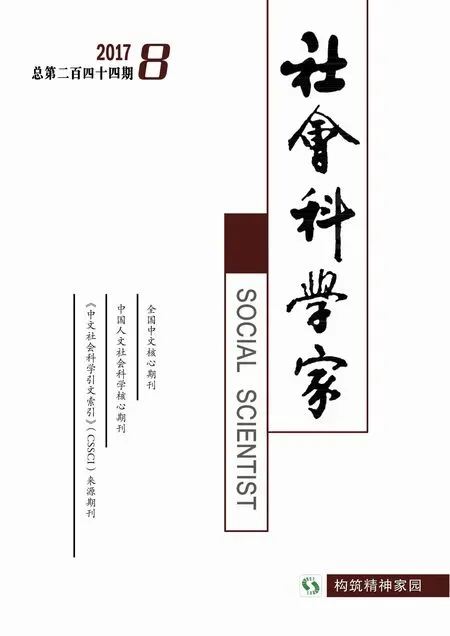孟子乐教思想新论
2017-04-11雷永强
雷永强
(河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洛阳 471023)
孟子乐教思想新论
雷永强
(河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洛阳 471023)
孟子以“承三圣”自我期许,自觉地接续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乐教传统,并发展之。他“攻乎异端”,孜孜于“辟杨墨”,力挽儒家乐教之道统而不坠。在新声勃兴、雅乐式微的时局下,孟子审时度势,以“仁政”理想的实现为终极指向,声言“今之乐犹古之乐”,以一种迂回的话语策略说服齐宣王“与民同乐”,表现出极高的权变智慧。这种权变,从容中道,在夹缝中为儒家乐教的复兴觅得一线生机。
孟子;乐教;道统;仁政;权变
孟子生于战国中期,当是时也,礼乐更加崩坏。清代硕儒顾炎武指认:“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1]顾氏所言甚确。在这种“邪说诬民,充塞仁义”的情势下,孟子自觉地担当起“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的文化使命。何谓“三圣”?孟子云:“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此乃一部自生民以来的华夏古史,经孟子删繁就简,仅剩下三座最具象征意义的文化丰碑矗立在那里:第一位圣人是“禹”,其最大贡献就是“抑洪水”,在人与自然的紧张与冲突中,人类最终战胜了自然,象征着人类已经摆脱他所源出的自然界的羁绊,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空间;第二位圣人是“周公”,其在华夏与夷狄的化变之间“兼夷狄”,象征着先进的华夏礼乐文明最终能够改变夷狄落后的生活局面,从而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第三位圣人是“孔子”,其功最著者在于“成《春秋》”。在仁人志士与乱臣贼子的博弈过程中,其弘扬了道义的力量而“乱臣贼子惧”,象征着正义是不可战胜的,并揭示了“仁”乃人之为人的内在本有规定与人之最本己的选择,为人类构建了一套赖以存身的价值准则,指示着人类挺起道德的脊梁,从而过上一种积极向上的道德生活。孟子“以承三圣”自许,其宗师孔子,高举儒学大旗,申言“乃所愿,则学孔子”。但是,“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为拨乱反正,孟子以捍卫与传承孔子所开创的儒学道统为己任,力“距杨墨”。学界向来将孟子之“距杨墨”目之为其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但仔细审查“杨墨”的文化立场,我们发现孟子之“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墨子“非乐”的回应,在维护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乐教传统方面居功至伟,成为战国时期儒家乐教思想传播中承上启下的代表性人物。现就孟子对儒家乐教的贡献略作申论,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距杨墨”——对墨子“非乐”的回应
孟子之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儒学式微,社会上诸说杂存、淆乱视听。孟子力主“距杨墨”,是站在道义的立场上为孔子进行辩护,以拨乱反正,使社会重新回归于“正道”。我们先来看杨子,史载“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虽然关于杨朱乐教方面的文字记录付之阙如,但由于其主张贵己、重生,故不大可能有太多的社会关怀,与儒家乐教成己、成物的教化旨趣不侔。孟子主张“仁政”,在乐教上倡导“与民同乐”,而这种政治关照是以“君权”的存在为前提的。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如果缺失了“君”这一环节,儒家所维护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伦常关系将瞬间崩塌,人类可能又倒退到史前无序的野蛮状态。可见,孟子这里的“君”应作广义解,代表着整个政治秩序的构建。同时,我们再来看墨子,他主张“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在实际行动中,“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可见,墨子以“利天下”为目的,主张“兼爱”、“非攻”,不是没有社会关怀,而是关怀的过了头,以至于“‘爱’的普遍性与由人的实存差异所生之‘爱’的等差性之间”[2]出现了紧张。同样是爱的施与,同样是社会关照,但在儒家看来,“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倡导“仁者爱人”,且认为“立爱自亲始”,事亲,事之本也。”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这里的“推恩”,即孔子的忠恕之道,或《大学》中的絜矩之道,而这推恩的前提就是亲亲之爱。正如《礼记·中庸》所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又:“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即君子之道,必由人的生命之最切近处发端,然后层层向外推扩。而其造端之始,必本于孝道亲亲,注重于家庭伦理。可见,儒家倡亲亲之爱,实有等差分别。
然而,孟子对墨家的批判,更多地指向于墨子“非乐”的文化主张。墨子批判儒家“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2]墨子于《非儒下》篇引晏子的话攻击儒者“好乐而淫人”,“孔丘成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营(惑)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愚)民。”墨子的话不可谓不尖刻。孔子对周公制礼作乐神往不已,称其“郁郁乎文哉”,并申言“吾其东周”的文化立场。现在,传统的礼乐文化在墨子的非乐声中,一股脑地都被否定了。这一点庄子看得十分明白,认为墨子“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这样,墨子之“毁古之礼乐”,对于“好古”的孔子之儒家来说,可谓是釜底抽薪。为了“闲先圣之道”,本不好辩的孟子不得不起而“距杨墨”,目的则在于“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
然而,墨家的理论体系不可谓不精致,否则,也不会出现“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局面。孟子有见于是,首先效孔子之“攻乎异端”而“距”之,指出了墨家在实质处“务外而不情”且与现实的脱离。紧接着,孟子指出墨家“非乐”似是而非的理论缺陷。《孟子·尽心下》载:“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其中,孟子“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正是对孔子“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的继承与发展。“紫”与“朱”颜色相近,但并非正色,若将其杂于“朱”色之中,往往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孔子“能近取譬”,就在于说明郑声的迷惑性。到战国时代,“乐以象德”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德音之谓乐”。但以郑声为代表的新乐,由于缺乏内在的“德”性根据,“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其虽非正乐,但往往会迷惑人的心智与正确判断力,像齐宣王就直言不讳地承认:“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面对郑声对雅乐的陵夷,孟子从形式到本质,对郑声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对墨家“非乐”做出有力的回应。因为儒家主张“与其奢也,宁俭。”并非如墨家所攻击的那样,“好乐而淫人”,“盛为声乐以淫遇(愚)民”。如果非要按图索骥,找一个合乎此类标准的对象,郑卫之音似乎更为符合,而不是儒家所提倡的正声雅乐。孟子通过这种辩说,实际上是在转移目标,将墨家所“非”的靶子转移至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新声俗乐了。
二、仁声与善教
孟子亦如孔子,十分重视人伦教化,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把人之“有教与无教”看作是人禽之辨,或人之为人的本有规定。“教”是人类智的提升手段,是通向“有道”的必经之路,也是“化”的终极指向,故古人多“教化”合称之。孟子继承了孔门儒家乐教的一贯传统,并在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儒家乐教与“仁”学结合为仁声之教,为传统“乐教”构建一仁学形上学的理论基址。
“仁”重视内在情感,孟子就从人类的审美趋同出发,逐步将个人对音乐的直观感受引向内在的道德认同。《孟子·告子上》云:“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此处,孟子将人耳之于声乐的审美趋同与人视、听、言、动的内在根据作比,并给予一种生活式、经验式的点化,使人类所“同然”并根植于“内心”的“理义”不再是外在的抽象,并以这种“同然”的“理义”作为“耳之于声”,即乐教的内在心理基础。虽然有学者认为“孟子虽谈礼乐,但多就辞受出处方面立论,抽象的理论并不多。”[3]但孟子以性善作为道德的根源,肯认了植基于“仁”、“义”所性的“仁声”的内在价值。
孟子认为“仁”、“义”出自于人之善性,是人性中本有的善的道德品质。所谓“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里,“仁义礼智”乃孟子“人性论”之“四端”。“端”者,根苗也。而这种根苗的成长,离不开人的精心培育与内心的护持,即教化的工夫。《孟子·告子上》云:“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苦彼濯濯也。”孟子以“牛山之木”比喻人之善良本心,其间虽有“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以及“萌蘖之生”,但在饱受斧斤之伐以后,且“牛羊又从而牧之”,无怪乎最终要落个“彼濯濯也”的下场。可见,坚持内心的守望与护持才能使其不失其美,须臾不离“求其放心”的涵养功夫。“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真可谓比喻贴切!乐教是先秦儒家所提倡的最为有效的一种教化方式,因为音乐“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故乐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入拨人之心”,敦厚“四端”,达到教化民心的目的;而“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一语,则表明“四端”为人先天固有之善端,与孔子“天生德于予”如出一辙,当其呈现于外时,则必有赖于“乐”以宣示之。孟子正是从内在的仁义善端出发来讨论“乐”的,其文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清代大儒王夫之释曰:“唯能以事亲、从兄为乐,而不复有苦难勉强之意,则心和而广、气和而顺,即未尝为乐,而可以为乐之道洋溢有余。乃以之为乐,则不知足蹈手舞之咸中于律者,斯以情益和乐,而歌咏俯仰,乃觉性情之充足,非徒侈志意以取悦于外物也。”[4]王氏对“乐之实,乐斯二者”的解释,深契于孟子“由仁义行”而为乐之旨趣。其中“则不知足蹈手舞之咸中于律者”云云,正与郭店简“其出于情也信”的外在呈现相合。这样,一入一出,乐教的功能得以全面的展现。可见,孟子所主张的人性修养充满着理性与感性相互交融的情感愉悦,随着修养之深化,甚至能够达到“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的审美境界。礼乐之实质,是内心调节与外在文饰的如如统一。质言之,孟子将道德人格的完善与精神情感的审美体验结合起来,寓教于乐,寓义理于愉悦的情感体验之中。如是,内在的道德心显发于外,转出为外在的感性表现,从而使“乐”不仅具有伦理学的指向,同时也深具美学的意蕴。
在孟子看来,人性之修养是身心合一,即现代人所云的知、情、意的和谐统一,它以内在的心性修养为根本,不仅充满审美的情感愉悦,而且诉诸外在的形体审美表现。孟子强调“仁声”对于人生命的感召力,并从人之仁心勃发、不由自己地生发、所产生的欣喜悦乐,以及手舞足蹈的表现来证说“乐之实”,从正面肯认了“乐”根植于仁心,是人之情性的“清和润泽”。孟子云“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何谓“仁声”?乃一种美、善合一的德音。何谓“美”、“善”?孟子云:“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为美”。在孟子看来,“善”与“信(真)”的统一及其完满实现(“充实”)方可谓之“美”。孟子之所以重视“乐”的道德教化功能,主要在于雅“乐”以情感人的美育作用。就个人而言,其能陶冶性情,铸就君子人格;对于国家、社会而言,以“仁义”为本的雅“乐”能发挥人伦教化之功,移风易俗,合同天下。首先,孟子发展了孔子“成于乐”的乐教思想,认为雅乐乃成德成性、境界提升的必由之路。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这里,孟子以“金声玉振”比之于孔子圣人境界的升进。先周雅乐,又称“金石之乐”,以钟、鼓、磬之类的打击乐器为主。其中,“金声”多指钟类乐器,“玉振”则为石磬类乐器,在审美上注重于音声的节奏感,强调于“条理”的有始有终。始条理为“智之事也”,象征着下学的工夫。终条理之为“圣之事也”,意味着德性人格的完成。这种圣德的完满实现乃循着孔子“下学而上达”的理路而贞定。因为“玉”乃天地精气的结晶,是石中之精华,所以古人多用之作为人神心灵沟通的中介物,王国维先生在《释礼》一文中认为甲骨文中的礼字:“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5]表明古代的玉具有不同寻常的宗教象征意义。“玉振”则意味着人神沟通,天人合一,在金石雅乐的陶冶下,上达天命而升进至圣域。同时,金始玉终,亦强调有始有终,“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孟子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主张尽心、知性而知天,在反身内求的基础上,层层上提,上接天道,以至于“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从而在道德人格上不断完善自我,并升进至圣人之境。
其次,在社会教化方面,孟子云:“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音乐乃人之真情实感的表达,作为“仁义”道德情感之表现的“仁声”当然具有巨大的社会感召力,“有诸内必形诸外”,其由内而外地通出,因而能感动人心,甚至“变国俗”,与孔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之教化旨趣相合。孟子认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赵歧注云:“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声,乐声雅颂也。仁言之政虽明,不如雅颂感人心之深也。”朱熹亦释曰:“谓仁闻,谓有仁之实而为众所称道者。尤见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之尤深也。”“仁声”本之“仁义”,是建立在“仁”德基础上的“乐”,其所以“入人深”,正因为它是“仁义”道德情感的真实外现。以“仁声”为教谓之“善教”,因为以道德理义为内容的“仁声”雅乐可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体验,唤起人的道德心,比单纯的语言说教更富于感染力,比“政教法度之言”也少一些紧张,故能使人互相亲睦,易为民众所认同和接受,从而善“民心”。孟子为了强调“仁声之入人深也”的教化功用,甚至把以“仁声”为教的“善教”视为其施行“仁政”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何为仁政?依照孟子的说法,就是“行不忍人之政”,其内在的心理根据是“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可见,孟子的仁政思想实际上是建立在其性善论的基础之上的。而儒家乐教就是强调通过雅乐来扩充人的先天善端。如果人们后天习染了不良因素而遮蔽了本心,致使本心放失,通过仁声之教可以使人复明本心。孟子认为,凡人皆有恻隐之心,不假外求,以这种与生俱来的人之善端来治国理政,是为仁政。他从社会政治的高度强调了“仁声”、“善教”对于“善政”的重要性,是孔子以降乐教思想的重大发展。
三、通权达变——对新乐态度的转变
为实现“仁政”理想,孟子发扬孔子经权思想,将儒家乐教合同天下的政治功能推向顶峰。孔子曾言:“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里,学、道、立、权代表着为学的四个境界,其中,能“权”最难做到,是一种“通权达变”的人生智慧。孔子又云:“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里,“义”是参照标准。义者,宜也,这种价值的抉择存在于主体性的权变智慧之中,表现为人伦日用中一贯的原则性与当下的灵活性的如如统一。我们从夫子“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的言语中,可以蠡测到其中两义相权取其重(大)的权变智慧。孔子教育弟子“毋固”,就是要求后学不要固执、拘泥于一端,当有变通之道。他主张“无可无不可”,展现出一种灵活权变的人生智慧。
对于一生“愿学于孔子”的孟子来说,当然深契于孔子的权变之道,其评价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圣之时者也”。这种“时”即是一种权宜,表现为因时(有道或无道)、因人(明君或昏君)、因事而制宜,从容中道。《孟子·告子上》云:“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这里,孟子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鱼”和“熊掌”二者之间的抉择。由于二者不可兼得,孟子最终的选择是“舍鱼而取熊掌”,反映了孟子的权变思想——两义相权取其重(大)。在孟子眼中,权变主要是指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中遇到行为准则发生冲突时于两难情境下所进行的一种变通行为。
考察了孟子的权变思想,我们再来看孟子是如何处理雅乐与新声的冲突的。战国中期,传统雅乐崩坏之后,继之而起的则是以郑声为代表的新乐。面对在上位者像齐宣王之流对新乐的痴迷,孟子并不是板起面孔来一番上纲上线的政治说教,或直接发表意见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而是先给齐宣王一通表扬,说“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一个“犹”字既调和了“今之乐”与“古之乐”的紧张关系,也避免了孟子与齐宣王之间在音乐审美上的正面冲突。
孟子明明知道新声似是而非,对雅乐危害极大,但却折中地用了一个“犹”字,体现了孟子极强的时局观。较之于孟子的仁政宏愿,雅乐的重要性要小得多,故两害相权取其轻,孟子也就不再说恶紫乱朱、恶郑乱雅了,一个“犹”字就在心理上拉近了与齐宣王的距离,后面通过“独乐乐”与“与众乐乐”的比较,很自然地过渡到其“与民同乐”的仁政理想。
孟子的“与民同乐”是一种音乐社会观,从群己关系以及个人的情感认同出发,指示出“仁声”乐教迈向“仁政”的通途。有鉴于桀纣之“侈乐”误国,孟子谏告在上位者:“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战国纷争,“得天下”就必须“得民心”,而要“得民心”不仅要“善政”,而且要“善教”,“与民同乐”。孟子云:“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本诸人心“所欲”、“所恶”之情感,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自古以来,圣王所贵,在于其能推己及人,有不忍人之心,并“举斯心加诸彼”,则“足以保四海”。这种“不忍人之政”即为“仁政”,其在和谐社会、行乐(yue)之乐(le)方面主要表现为以“仁声”“与民同乐”。齐宣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可爱而又率真,并不遮遮掩掩,只是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而“变乎色”。朱熹《集注》云:“变色者,惭其好之不正也。”因其所好的“世俗之乐”就是当时广为流行的俗乐、“新声”。孟子以“今之乐犹古之乐”为齐宣王找了一个台阶下,但就行乐中所得到的情感愉悦体验来讲,今人与古人无不同;若就“乐”之分享方式而言,却大不一样,其中有“独乐”、“与人乐”以及“与众乐”之分。然孟子这里在道德评价上并非对“今之乐”、“世俗之乐”与“古之乐”、“先王之乐”等量齐观,亦不从社会教化功能立论,其评判标准只是看能否“与民同乐”。在其眼中,只要“与民同乐”,就可以“得民心”。这与其主张以“仁声”、“善教”而“得民心”的立论角度是有所区别的。前者侧重于音乐审美的娱悦功能和这种娱悦的社会共享性,是借“与民同乐”而“得民心”;而后者则侧重于雅乐以情感人的道德教化功能,是通过使人“明人伦”、相亲睦的德教作用来“得民心”的。
孟子为了说服齐宣王,主张只要“与百姓同乐,则王矣!”甚至引晏子说服齐景公“作君臣相说之乐”的故事,要求齐宣王效仿景公而“与民同乐”,从侧面告诫齐宣王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广施仁政。虽有妥协、折中的一面,但谲谏效果十分明显。“乐”乃国家政治好坏的晴雨表,虽有权变之宜,但贵在“君子反经而已”。孟子坚持以礼正乐,以律正音,曰:“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赵岐注:“师旷,晋平公之乐太师也。其听至聪,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即使是善听音声,乐技极高的乐师师旷,若不用六律,也不能正五音。在乐教实践中,只有“复礼”,以礼为节度,由“恶郑声”而“反经”,即可归于常道,雅、颂之声方能复兴于世。
又《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贤者”,指有仁德,能以其“不忍人之心”实施“仁政”者。孟子又说“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亦天下,忧亦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始终坚持“与民同乐”、“与民偕乐”,所关照的对象未尝离开于“民”,是对“人”自身的关注与人性的高扬,反映了先秦的民本主义思潮。
然而,能否“与民同乐”也为墨家所关注。《墨子·非乐》篇就批判了王公大臣“不与民同乐”而独占性的音乐享受,并认为其“亏夺民衣食之财”,故“仁者弗为也”。然墨子矫枉过正,将一切人文化的精神价值,一并纳入了以“利”为标准的工具价值来取舍。以至于日后荀子作“乐论”而驳墨子之“非乐”,并在《非十二子》篇中斥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批评墨子不知乐教之文化内涵乃人之情性的本真表现,所以不能完全以现实功利的立场而加以否定。孟子之“与民同乐”说强调音乐欣赏的社会共享性,或许亦是由此而发。孟子认为君王应以爱民为出发点,“鼓乐”一事亦当以仁心为之,与民同乐。从音乐之审美效果上讲,行“乐”当寻求音乐审美中的情感交融与共鸣;反之,如果“鼓乐”只是在上位者的特权享受,自然会将“独乐”建立在人民的苦难之上。因此,孟子之仁政理想是使鼓乐成为君民同乐之事,在审美的“视域融合”中“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四、结语
孟子以“承三圣”自我期许,自觉地接过孔子之儒家乐教的接力棒,并发展之。这种发展主要见之于其有破有立的努力。孟子所“破”主要表现在他作雅郑之辨,“攻乎异端”,孜孜于“辟杨墨”,力挽儒家乐教之道统而不坠;其所“立”,主要表现在孟子发明仁学,第一次提出了仁政学说,并将儒家乐教视为仁政理想实现的必然路径和本有内容。在新声勃兴、雅乐式微的时局下,孟子审时度势,在批判新声俗乐“似是而非”本质缺陷的同时,以“仁政”理想为终极指向,说“今之乐犹古之乐”,以一种迂回的话语策略说服齐宣王“与民同乐”,表现出极高的权变智慧。这种权变,从容中道,在夹缝中为儒家乐教的复兴觅得一线生机,功莫大焉!但是,这种妥协,也是孟子所处的历史境遇使然,表现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艰难抉择。孟子虽表现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王道自负,但在其处处碰壁之后,不得不正面“不得其时”这一严峻事实。我们从孟子的天命观中可以窥得消息。孟子释“天”、“命”云:“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可见孟子的“天命”,乃行为主体无力左右的外部因素,人的主体性已杳无踪迹,表现出儒者无可奈何的历史境遇。
[1]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C].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
[2]李景林.孟子的“辟杨墨”与儒家仁爱观念的理论内涵[J].哲学研究,2009(2).
[3]杜国庠.略论礼乐起源及中国礼学的发展[A].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C].北京:三联书店1955.202.
[4]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下册)[M].中华书局 1975.616.
[5]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291.
B222.5
A
1002-3240(2017)08-0054-05
2017-03-2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秦儒家乐教文献的生成与思想演进”(编号:12CZX032)及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雷永强(1973-),哲学博士,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儒学。
[责任编校:赵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