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周公辅成王”与汉代政治
2017-04-11高二旺��
高二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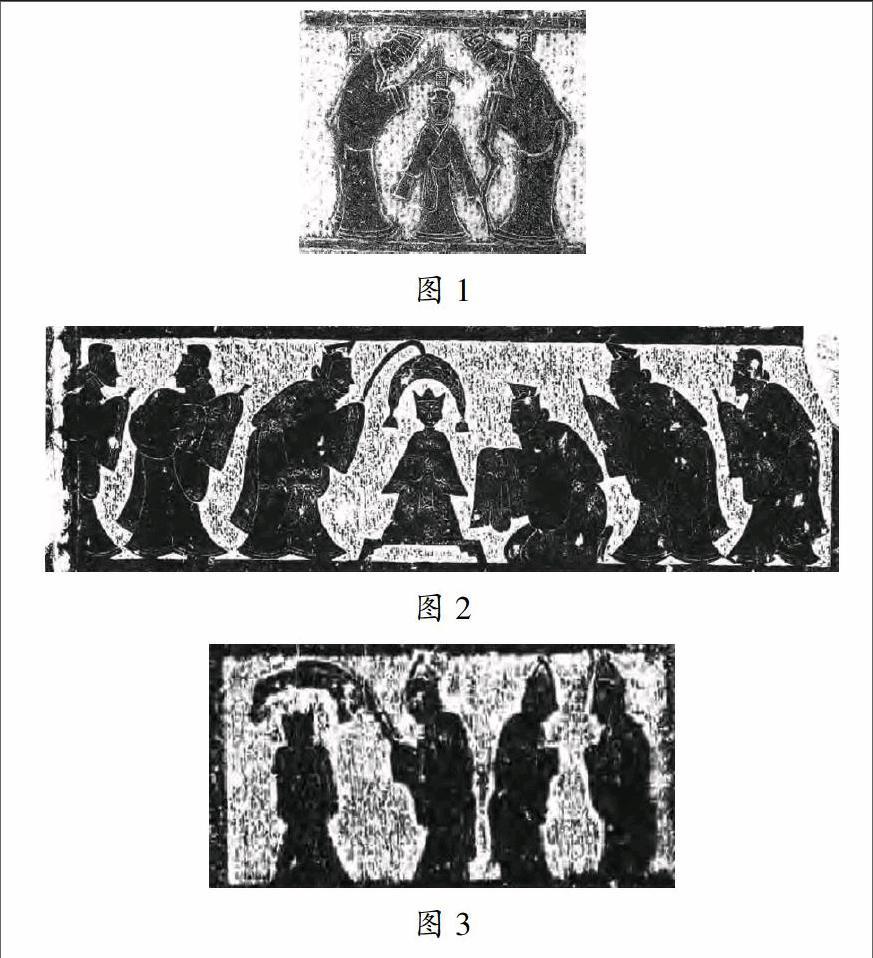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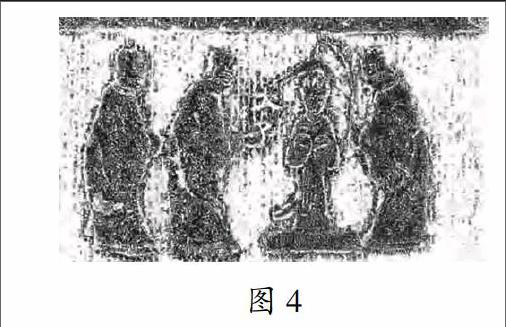
摘要:以“周公辅成王”为题材的汉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山东等地。周公辅成王的史实涉及幼主、权臣、宗室三个方面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周公就已被视为圣人。西汉时期,霍光和王莽都曾在政治上效法周公。霍光是比附周公的正面典型,而王莽则是假托周公的反面例子。到了东汉,官方更突出周公“圣师”的地位,并与兴学重教结合起来。“周公辅成王”汉画在东汉的出现与两汉的政治分不开,也同鲁地信仰周公的传统相关。
关键词:汉画;“周公辅成王”;汉代政治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3-0110-06
目前关于汉画的研究已经延伸到多个领域,但研究内容仍以汉代文化为主,借助汉画材料来研究汉代政治的成果尚不多见。“周公辅成王”汉画反映了汉代幼主当国,权臣专政等政治现象,值得深入探讨。
一、汉画与“周公辅成王”
1.“周公辅成王”汉画
在汉画像石中,有不少以周公辅成王为主题的刻画,目前发现的该题材汉画至少有十多幅,大多出现在山东,陕西也有少量出现。图中的布局有两种模式,一种情况是图中有三人,居中而立的成王头戴王冠,身形幼小。分立左右的是两位大臣,其中一位大臣躬身执伞盖罩在成王头顶,以显其尊贵和威严,另一位大臣躬身而立。两位大臣分别为周公和召公,如山东嘉祥县纸坊镇敬老院出土的画像石(局部),画面上明确标有“周公”“成王”“召公”字样,执伞者为周公,见图1①。
另一种情况是画面中有三人以上的多人,画面布局一般为成王居中,周公、召公及其他臣子分列左右。大臣们跪伏于地或俯身恭立,正在拜见成王,尽显恭敬谦卑之态。如宋山小石祠西壁画像周公辅成王图(局部),见图2②。
在多人画像中,一般是成王居中,但也有少量成王居边的情况。如武氏西阙子阙身南面画像(局部),见图3③。
收稿日期:2016-01-01
*基金项目:2014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汉画与汉代礼制研究”(2014BLS002)。
作者简介:高二旺,男,南阳师范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南阳473061)。
多人周公辅成王画像中有一幅画面中在成王旁题“太子”字样,见于山东嘉祥县纸坊镇敬老院出土的武士、吴王、周公辅成王画像(局部),见图4④。
图4
2.学界关于“周公辅成王”的争论
学术界关于周公辅成王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对周公的评价问题上,后人关于周公是否称王进行了争论,一称周公称王而且摄政,二称周公未称王只摄政,三称周公既未称王也未摄政。⑤顾颉刚《周公执政成王》认为周公摄政之说不过是后世儒者为美化周公编造的谎言,他是实实在在做了一任天子。常金仓先生则认为“无论是执政称王论者还是冢宰摄政论者都不否认周公在周初历史上的重要作用”⑥。从传世的各种文献来看,成王年幼时,周公的确摄行政事,虽未明言天子,但其专权的程度、奉行的礼仪都等同于周王:“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⑦阼阶是主人之阶,周公确实是以“假王”的身份摄政。后人关于周公是否称王的争论并没有多大的意义。问题的关键是,周公摄政之后能够主动返政成王,这是周公与一般的权臣不同之处。从汉画角度来研究周公辅成王的成果很少,赵晨认为,“周公辅成王”画像所要表现的其实不是故事,而是观念。“周公辅成王”是处在叙事性和象征性之间的一幅画,它所表现的既非成王,亦非周公,而是这一个场面所体现出的政治与人伦秩序。画面中每一个角色的动态、表情和道具包含了一个超越这一历史故事的政治、道德甚至是人生的理想——“君君臣臣”。⑧这种观点看似有道理,却忽视了历史背景问题,周公辅成王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观念,更是传递了关于汉代政治的一些信息。
王紫微等人认为,无论在文献记载中,还是在出土实物中,“周公辅成王”这一历史形象在两汉之际的变化都反映了王莽事件对东汉思想文化造成的影响。由于王莽当权时将周公的历史形象和王莽本人的政治形象几乎融为一体,为了恢复汉朝的正统地位、巩固君臣之间的尊卑伦理,东汉政权必须将周公形象与王莽形象分离开来,重新塑造世人对“周公辅成王”这一历史形象的认知。在东汉人眼里,周公完全成了一位本分忠臣的代表、温柔敦厚的化身。而这样一个全新的周公形象,也成为了东汉政教文化的历史缩影。⑨说《周公辅成王图》是受到王莽专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将其作为唯一原因显然不够。且周公居臣位在先秦的典籍中就已经有明确的记载,并非东汉才强调。欲对周公辅成王汉画进行解析,必须还原周公辅成王的历史事迹。
3.周公辅成王的史实及政治影响
周公辅成王是政治上忠诚的典型刻画,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他曾帮助武王灭纣,在武王死后,更是全力辅佐年幼的成王,维护了周朝的稳定,成王年长后,周公还政于成王,始终以臣子的身份恪尽职守。史载:“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⑩又载:“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B11
周公辅政,要面临幼主、宗室的质疑:“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B12周公一方面要教育成王,另一方面还要应对宗室的质疑乃至反对。对于宗室而言,他们对周公产生怀疑是难免的,“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B13。而其他一些表现激烈的宗室則选择武力反叛,“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B14。
无论怎样,后世对周公的评价都是正面的,早在先秦时期,孔子曾把周公看作是至圣之人,他曾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甚至连周公的缺点也能够容忍:“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B15秦国蔡泽也曾说:“夫商君、吴起、大夫种,其为人臣尽忠致功则可愿矣,闳夭事文王,周公辅成王也,岂不亦忠圣乎?”B16由此可见,在先秦时期,周公就已经以圣人的形象出现了。
二、周公辅成王汉画与西汉政治的关系
1.周公辅成王的政治隐喻
综合上述资料,周公辅成王画像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包括三个基本要素,一是皇帝年幼,二是辅政的大臣专权而且贤明,三是权臣对不听命的宗室可以“行管蔡之诛”,进行镇压。因此,周公辅成王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他涉及权臣、天子、宗室三层关系的处理。正是由于周公辅成王中包含着对宗室叛逆者的警告,故而昭帝初立,武帝长子刘旦自以长子当立,与齐王子刘泽等谋为叛逆时,昭帝遣宗正与太中大夫公户满意、御史出使燕地劝喻,公户满意对燕王说:“周公辅成王,诛其两弟,故治。武帝在时,尚能宽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于春秋,未临政,委任大臣。古者诛罚不阿亲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辅政,奉法直行,无敢所阿,恐不能宽王。”于是燕王刘旦“乃恐惧服罪,叩头谢过”。《索隐》认为武帝诛太子而立童孺,“亦由权臣辅政,贪立幼主之利,遂得钩弋子当阳”。B17
西汉末年,杜钦见王凤专政,告诫他说:“昔周公身有至圣之德,属有叔父之亲,而成王有独见之明,无信谗之听,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惧。”B18希望他像周公一样谦惧。
西汉时期突出周公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形象,其中蕴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希望权臣像周公一样辅佐幼主,维系帝统。二是权臣以周公自居,为自己的专权寻找历史依据。在汉代出现了两个明显以周公比照的人物,一个是霍光,一个是王莽。
2.武帝命画周公负成王图与霍光专政
征和二年(前91),武帝年老,准备立宠姬钩弋赵倢伃所生幼子为嗣,命大臣辅之。他感到群臣中只有霍光可以相托,“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并进一步指明:“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B19《史记·外戚世家》亦载:“上居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也。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而《史记·蒙恬列传》中记蒙恬之言云:“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褓,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孔子家语》也记载,孔子曾在明堂见到过周公辅成王的画面:“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图焉。”B20可见在西汉时期周公辅成王的标准画像是“周公负成王”。
武帝欲立少子,本身就是对嫡长子继承制的一种挑战,如此选择是出于多种原因。元狩元二年(前121),武帝立刘据为皇太子。征和二年秋,太子因巫蛊之事逃亡,八月自杀。钩弋夫人是武帝宠爱的夫人,立年幼的钩弋之子为太子是最理想的。武帝用画像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心迹,他知道废长立幼一定会遭到大臣和宗室的反对,所以一定要有一位强臣辅佐才行,且这位强臣又不能威胁到太子的皇位。霍光是最佳人选,而周公无疑是最好的榜样。武帝希望霍光如周公一样辅佐年幼的太子,待太子长大后再返政让权。后元元年(前88)二月,武帝立皇子刘弗陵为皇太子。不久,武帝崩。武帝在最后一刻立太子,一定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事实证明,霍光辅佐昭帝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班固评价:“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盍、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B21王吉对霍光也充满褒扬:“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亡以加也。”B22霍光也成为东汉辅佐幼主权臣的榜样,“周章身非负图之托,德乏万夫之望”B23。
霍光专权的程度应该不亚于周公,“(昭)帝年八岁,政事壹决于光”。然而,霍光与周公相比还是要差不少,先秦的周公与年幼的称王有着叔侄的亲属关系,而汉代的“周公”不过是老皇帝的崇信大臣。汉代对霍光专权也不乏批评的声音,时人认为霍光专政时间长,返政不及时:“光执朝政,犹周公之摄也。”“光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于周公,上既已冠而不归政,将为国害。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灾见。”B24既然武帝能够画《周公负成王图》表明心意,后人也有可能通过画像来重现霍光辅佐昭帝的历史,可以说,周公辅成王汉画某种程度上折射出霍光辅昭帝的历史真实。
3.王莽对周公辅成王故事的利用
王莽居摄专权,历史依据便是周公辅成王的故事。平帝驾崩后,他“择宗室幼稚者以为孺子,依托周公辅成王之义”B25,伺机取代汉室。王莽选择年仅两岁的刘婴继位,“风公卿奏请立婴为孺子,令宰衡安汉公莽践祚居摄,如周公傅成王故事”。太后并不同意,苦于力不能禁。其后,“莽遂以符命自立为真皇帝,先奉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惊”。B26王莽居摄也引起了一些大臣的不满,翟义对外甥陈丰说:“新都侯摄天子位,号令天下,故择宗室幼稚者以为孺子,依托周公辅成王之义,且以观望,必代汉家,其渐可见。”B27王莽专政不久,宗室安众侯刘崇及东郡太守翟义等举兵欲诛王莽。
王莽专权后,同样以周公“行管蔡之诛”的方式铲除异己。甄邯等白太后下诏曰:“夫唐尧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圣亡奈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辅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诛,不以亲亲害尊尊,朕甚嘉之。”此诏书的下达绝非太后本意,但王莽据此大肆打击西汉宗族大臣:“诛灭卫氏,穷治吕宽之狱,连引郡国豪桀素非议己者,内及敬武公主、梁王立、红阳侯立、平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杀。死者以百数,海内震焉。”B28
始建国元年(9)正月朔,王莽借符命称帝,他率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玺韨,上太皇太后,顺符命,去汉号焉”。王莽借周公之名专政,却未按周公那样返政,他自己也深知这一点。王莽策命孺子为定安公,读策毕,王莽亲执孺子手,流涕叹息道:“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中傅将孺子下殿,北面而称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动。”B29王莽把自己不返政的理由归为迫于天命,不愧为作秀的高手。王莽自比周公辅成王不过是欺世盗名,他没有周公之德,在专权上却处处效法周公。班固评价王莽“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丧我四海”,颜师古解释为“言其自号宰衡,而无周公、伊尹之忠也”。B30
综合西汉一朝的情况来看,在位的帝王希望幼主即位后,辅政的大臣能够像周公对待成王那样竭力辅佐。但遗憾的是,两汉的辅政大臣不是外戚就是宦官,周公辅成王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罢了。
三、东汉周公辅成王汉画出现的政治背景
1.汉代人对周公的崇拜和祭祀
周公辅成王汉画的流行,与汉人对周公的推崇有很大的关系。刻画周公辅成王汉画,正是表明了人们对周公的崇敬之情。在先秦时期,孔子等名人对周公仰慕有加。西汉早期,周公就已经被视为匡乱救危的政治家了,谁能被世人拿出来与周公相比则是对其很大的赞扬。司马迁评论周勃:“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B31司马迁对周公的仰慕之情也可以从不少地方看出,司马迁的父亲曾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在司马迁父子眼中,周公与孔子都是500年一遇的先贤圣人。他自己也提到,“依之违之,周公绥之。愤发文德,天下和之。辅翼成王,诸侯宗周”。B32公孙弘上疏请求效法周公之治推行教化,天子以册书答曰:“问:弘称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视孰与周公贤?”B33可以看出,西汉人们已经把周公看作圣人,在赞扬一些名臣时也往往将其比之于周公。
对于权臣,一些有识之士往往以周公之德进行告诫。如王凤专权,杜钦劝他效法“周公之谦惧”B34。王褒也提到:“昔周公躬吐捉之劳,故有圉空之隆。”B35对于王莽专权,一些大臣以及元皇后都持反对态度。如孙宝反对王莽专权时,他提到:“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B36
东汉时期,人们对周公仍充满敬意,一些辅佐幼主的权臣也以周公自居。和帝时,侍中窦宪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颇涉经学,上疏皇太后称:“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后,太公在左,召公在右。”B37请求桓郁、刘方侍讲和帝。在这里,窦宪显然以周公自居,认为自己应该对幼主的教育尽到责任。
可以说周代以降,历史上对周公的评价是一边倒的正面评价,对周公的祭祀也由来已久,最早是在鲁国,“周兴,以少昊之虚曲阜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以为周公主”。师古注曰:“主周公之祭祀。”B38《集解》引《公羊传》曰:“鲁祭周公,牲用白牡,鲁公用骍刚。”B39此后在鲁国朝京师的中转站许地也出现了祭祀周公的庙宇,据《史记·周本纪》索引注引《左传》云:“许是鲁朝京师之汤沐邑,有周公庙。”又引《括地志》云:“许田在许州许昌县南四十里,有鲁城,周公庙在城中。”B40
汉代帝王对周公的祭祀是从东汉开始的,永平二年(59)三月,明帝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大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B41。这是东汉大张旗鼓祭祀周公的开始。表明东汉时周公同孔子一样作为“圣师”被祭祀,是兴学重教的标志。因此,周公辅成王汉画的流行,与两汉时期人们对周公的崇敬有关,也与东汉政局以及对周公祭祀、对周公辅成王形象等各方面的认识有关。
2.东汉幼主当国及对幼主教育的重视
两汉有不少年幼皇帝,东汉尤多。如西汉的昭帝、平帝、孺子刘婴,东汉和帝、殇帝、顺帝、冲帝、质帝、灵帝、献帝都是在幼年继位,大者十来岁,小者一两岁。这种情况也是诱发外戚宦官专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刻画周公辅成王汉画,从权臣一方能够为自己专权的合理性寻求依据,从王室以及民间来说也是为了让权臣以周公为榜样,希望其自我约束。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抑或是出于对幼帝教育的目的,祭祀周公和图画周公图像便显得极为正常。
周公辅成王汉画中,画面一般有多人形象,这也与东汉人对周公辅成王的认识有关,除窦宪上书中提到成王被众人拥护的情况外,类似的描述随处可见,诸如:“昔成王之为孺子,出则周公、邵公、太史佚,入则大颠、闳夭、南宫括、散宜生,左右前后,礼无违者。”B42“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后,毕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挟而维之。目见正容,耳闻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旷然,言其法度素定也。”B43可见,多人画像“周公辅成王”画面中的人物除周公、召公之外,其他人物可能来自史佚、毕公、大颠、闳夭、南宫括、散宜生等人。而在《史记》《汉书》这类涉及西汉的史书中,并没有见到诸臣们前后左右夹辅成王的类似描述。受王莽专权的影响,东汉的权臣不敢轻易提摄政,而更加强调对幼主的教育。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东汉的周公画像有多人的缘故。由于画面难以显示前后方位,故汉画在处理人物时仅表现出左右的布局。
3.东汉的周公信仰与君臣礼教的成熟
日本学者佐原康夫认为祠堂的画像供祭祀先人之用,画像具有宗教的要素和教训的要素,画像中的圣人、烈女、孝子及刺客义士等画像都具有教育训诫后人的意义。B44周公辅成王汉画多出现在山东,也同东汉人的信仰有关,东汉人把周公作为圣人,在墓中或祠堂刻画这类图像,目的是希望自己的后代像成王一样受到贵人的辅佐和保佑,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子息繁衍,家业兴旺。在周公辅成王汉画的成王位置刻画“太子”字样,突出其太子身份。从这个角度来看,周公辅成王汉画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中间的成王象征家族的后代,生者希望死者的子孙能得到贵人的帮助和辅佐,光大家业。在嘉祥县(包括武氏祠在内)出现的周公辅成王汉画有10幅左右,占全国这类题材画像的大半,嘉祥位于山东西南,属于周公的封地——古鲁国的范围,从周公到孔子再到两汉硕儒,说明儒家思想在鲁地的深远影响。
汉画也是东汉推行以君臣伦理为中心的礼制教化的显现,当时已经有了系统的舆服礼制,并在《后汉书》中被记载下来,这是东汉礼教成熟的一个标志。东汉礼制更加强调崇君卑臣:“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B45王充甚至把君臣之分看作是不可更改的天命:“命有贵贱,才不能进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禀卑秩也。”B46君臣区分的强化在礼仪上得以体现:“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B47具体来说就是“天尊地卑,君庄臣恭”B48,周公辅成王汉画正是“君庄臣恭”的形象描绘。
周公辅成王汉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汉的政治实态。西汉帝王利用周公与成王的画像表达托孤的心愿,而权臣以周公自居,通过这样的画像为自己的专权与打击异己寻找合理性。另一方面,周公辅成王汉画也传达了东汉人的政治和教育观念,这种观念既包括儒家政治伦理层面的君君臣臣观念,也包括东汉人尊崇儒家教育,希冀子孙受到良好教育,弘大家业的愿望。此外,周公辅成王画像还反映了东汉幼主当国、君臣礼教强化、尊崇并祭祀周公等汉代政治的突出问题,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汉代儒学的兴盛,以及周公事迹在汉代的广泛流传。
注释
①④俞伟超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2·山东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07、106页。
②③俞伟超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1·山东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66、10页。
⑤杨朝明:《关于“周公辅成王”问题》,《文史知识》2006年第1期。
⑥常金仓:《从周公摄政的争论说到历史考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⑦B28班固:《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4080、4065页。
⑧赵晨:《汉画“周公辅成王”中的叙事与象征》,《美术观察》2010年第9期。
⑨王紫微,于志飞:《两汉“周公辅成王”历史形象的变迁》,《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⑩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132页。
B11B12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519—1520、1520页。
B13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549页。
B14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五《管蔡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565页。
B15杨柏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2年,第67、82页。
B16司马迁:《史记》七十九《范睢蔡泽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421页。
B17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王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2117—2119页。
B18B34班固:《汉书》卷六十《杜周传附缓弟钦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676、2676页。
B19班固:《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932页。
B20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上海书店,1987年,第72页。
B21班固:《汉书》卷七《昭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233页。
B22班固:《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061页。
B23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三《周章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158页。
B24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上《五行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1335页。
B25班固:《汉书》八十四《翟方进传附子义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426页。
B26班固:《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4031—4032页。
B27班固:《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传附子义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426页。
B29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中华书局,1962年,第4099—4100页。
B30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4240页。
B31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2080页。
B32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第3307页。
B33班固:《汉书》卷五十八《公孫弘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618页。
B35班固:《汉书》卷六十四下《王褒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823页。
B36班固:《汉书》卷七十七《孙宝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263页。
B37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传附子郁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255页。
B38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2页。
B39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王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2108页。
B40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150页。
B41范晔:《后汉书》卷九十四上《礼仪志上》“高禖”条,中华书局,1965年,第3108页。
B42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8页。
B43范晔:《后汉书》卷四十八《翟酺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604页。
B44佐原康夫:《汉代祠堂画像考》,《东方学报》1991年第63册。
B45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六《贾逵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237页。
B46黄晖撰,附刘盼遂集解:《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21—22页。
B47范晔:《后汉书》卷九十四《礼仪志上·序》,中华书局,1965年,第3101页。
B48范晔:《后汉书》九十六《礼仪志下》“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条,中华书局,1965年,第3153页。
责任编辑:王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