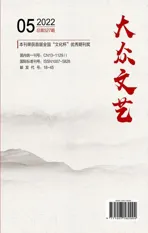朱景玄“格外逸品”在唐宋画论中的解析
2017-04-08黄梦洁福州画院350000
黄梦洁 (福州画院 350000)
朱景玄“格外逸品”在唐宋画论中的解析
黄梦洁 (福州画院 350000)
对朱景玄“格外逸品”的概述往往是将它作为“四品”评判标准之一进行比较分析,或者是探讨“逸品”概念的发展变化,“格外逸品”真正所含括的对艺术品的定位上,还是值得深入探讨。通过溯源,我们知道朱景玄所提到的“逸品”是在“格外”,意味着“逸品”是与“常法”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并且“不拘常法”,又说明两者在技法上面又有着明显的差别。苏轼提出的“墨戏说”是朱景玄“格外逸品”在唐宋画论中延伸的发展,既承袭了谢赫六法里的常法之外,又将这一理论进行完善和全面。
朱景玄;格外逸品;墨戏说
绘画中“逸品”之说,始见于唐代。中国传统书画批评的“品”论,最早运用于钟嵘的《诗品》,与古典文艺理论和美学结合起来,后来广泛转向以书画批评为主的理论现象。品评的主要特征是品第法。它涵盖的范围不仅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定位,还包括艺术家的价值取向及审美趣味,是一种整体性、直觉性、感悟式的批评思维。唐代的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序》中较早的指出“逸品”这一独特绘画风格的存在:“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优劣也。”朱景玄所提到的“逸品”是在“格外”,意味着“逸品”是与“常法”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并且“不拘常法”,又说明两者在技法上面又有着明显的差别。既然朱景玄所称的“逸品”是以“常法”作为对比的参照对象,那么我们首先要对他所称的“常法”作一番深入的了解,知“常”方能知“变”。
南朝梁谢赫提出的“六法”被唐人奉为正统,即朱景玄所称之“常法”,或“画之本法”,以此“画之本法”所作的绘画即是正统画或正规画。钱钟书先生曾在《管锥编》第四册中关于谢赫的《古画品》之“六法”部分重新标点:“六法者何?其一,气韵,生动是也;其二,骨法,用笔是也;其三,应物,象形是也;其四,随类,赋彩是也;其五,经营,位置是也;其六,传移,模写是也。 ”笔者认为这样的标注能直接说明“气韵”即生动,“骨法”即用笔,“应物”即象形等,均以浅近之词释义。“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就画论画,不根据艺术评论家的个人好恶,不参考画家身份官阶的地位高低,只是以画技与画迹对照六法,予以品第。谢式标榜以形写神、形骨相成、气韵至上视为作画的最高追求,在本质上是以绘画艺术自身的形式规定性来表达对象之形貌与神采(并能将画家的情趣寄托于绘画之中),藉由形貌描绘显现其神采又以神采表现来弥补形貌描绘的局限性,这是“六法”中最高要义,并且也得到后世画者的普遍信奉。
即便是在这种正统绘画之中,唐代依然有“士体”画与“宫体”画两种不同的区别,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始终在探讨的关于“文人画”与“院体画”之间的区别。我始终认为“文人画”和“院体画”只是中国绘画的两种表达方式,是基于不同的品味追求上显现出的审美特征,前者更注重一个人思想情趣的显露,后者想要精工细致地表达出事物的特性,这是取决于当下画家对艺术认知的目的不同,采用了不同的创作手段来展现风格,它们都是以物寄情,托画言志,并未脱离“六法”的讨论范围。唐代“士体”绘画虽然仍在“画之本法”的范围之内,但其“重神、重意、重情”,与朱景玄所提到的“格外逸品”绘画多有耦合之处,更接近于“文人画”的范畴。
我们且看在《唐朝名画录》中被朱景玄推为“逸品”三个代表性人物的描述:

逸品画家 为人 题材 作画方法与状态 艺术效果王墨(亦作王默、王洽,?-805)多游江湖间;疯癫怪异,野逸纵酒,不拘常礼,多有诡谲之举山水醺酣泼墨、脚蹙手抹、或挥或扫、甚至以头髻蘸墨作画,自然成象,随机造型应手随意,倏若造化,图出云霞,染成风雨,宛若神巧,俯视不见其墨污之迹,皆谓奇异也李灵省(生卒年未详,活动于元和年间,806-820)不拘礼节、恃才自矜、不尊权贵、率性而为山水、竹树凭借酒后灵感作画,一点一抹,便得其象,自由生发,一任自然,不拘于绘画品格,自得其趣物势皆出自然,得非常之体,符造化之功张志和(约730-810)虽为帝王赏识、名流交结,而性情高迈,退隐洞庭,不拘俗礼人物、舟船、鸟兽、烟波、风月其书法风格狂放,善作诗意画,随句赋象,皆依其文,甚有逸思曲尽其妙,为世之雅律,深得其志
(注明:图表来自于胡新群博士论文《唐宋绘画“逸品说”嬗变研究》 )
王墨、李灵省、张志和三人的绘画作品因现今已很难见到,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他人的一些文字描述来大致的了解三人作画的方法与作品的面貌。最能体现王墨、李灵省、张志和三人在绘画作品上与以往“画之本法”不同之处是上表中“作画方法与状态”一栏。从谢赫“六法”的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将属于“画之本法”的唐代画家薛稷、边鸾等人与属于“格外逸品”的王墨三人作一比较,就可以较为直观的发现两者的差异:
薛稷画鹤、边鸾画花,韩干画马、韩滉画牛,四人无不是遵循“六法”,从精心观察所描绘对象入手,提炼其形象的典型姿势与情态,追求形象生动、随类赋彩,并在细节表现上不遗余力,借写形“着力表现鹤之仙姿、牛之敦厚、马之神气”“花之生机”,进而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
“格外逸品”三人:其一,在用笔上,王墨、李灵省、张志和三人“脚蹙手抹、或挥或扫”、“一点一抹,便得其象”的简略用笔与薛稷、边鸾等颇为繁复、工致的用笔方法迥然有别。其二,在“随类赋彩”方面,王墨“醺醉泼墨”的用墨方法与“随类赋彩”的处理方式亦有着很大的不同。按王墨墨法师法项容,并又在项容的基础上有所变化。项容“以枯笔皴擦为主要造型手法,乃至作为轮廓结构线之骨法用笔融没于皴擦之中,似乎‘用笔全无其骨’”。王墨直接以泼墨造型,相对于项容,真正做到了全无骨法。王墨在以泼墨造型这一点上,确实已经突破了“随类赋彩”勾勒填色之法的束缚,从而与“画之本法”分离开来。其三,在“象形”方面,王墨“自然成象、随机造型”,李灵省“自由生发、一任自然,不拘于绘画品格”,张志和“善作诗意画,随句赋象”。三者皆与后世“写意画”之“境由意造,象由心生”已有些接近,而与“六法”中的“应物象形”有着较大的差别。“逸品”画风作画方法既然不同于常法,那么这种绘画作品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效果自然与用正统画法创作出来的作品的区别理当较为明显,以至于朱景玄认为“此三人非画之本法,故目之为‘逸品’,盖前古未之有也,故书之。”朱景玄采用“逸品”来为当时这种不合“画之本法 ”的作品风格定名,说明这种风格的出现在当时虽然是个体的,独特的,但已不是偶然现象,已经开始引起像朱景玄这样的绘画评论家的注意。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朱景玄所提到的王墨、李灵省、张志和三人皆是人格高逸、不拘俗礼、任性放诞之士,创作时完全按照自己喜好,具有艺术创造的主动性,能够“自得其趣”,具有娱情自乐的性质,与“画之本法”中“士体画”性质较为相近。前面我们说到,“士体重寄意”“士体绘画必以自由创造、自主选材、思路开阔、饱含诗情为其所长。”但它仍在“画之本法”的范围内寄意抒情,受到“六法”的规约。“格外逸品”则已跳出了“六法”的范围之外,比“士体画”在“写意”上更进了一步。相比于正统画,在朱景玄的眼中,“格外逸品”新奇、简约、自然,又与画家本身的超逸人格密不可分。正是画家人格之“逸”,导致画法之“逸”,从而出现了画风之“逸”,三者相互统一,融为一体,这也是朱景玄确立逸品的标准,三者缺一不可。人格与画品相统一,而不再简单的就画论画。诚如胡新群在其博士论文中所引钱穆先生所说:“谢赫论六法,有画品,无画家。主于形象,偏倾在外,遂使人仅重画中之神与物,而不重画者之人,最多亦是人以画重,重此画乃重此人……于是先贵有心中之天机,乃能有笔下之造化。必先有此画家,乃能有此画品。作画之能事,已先在于其人未画之前。然其所画之内容,则终是以在外者为主。 ”
朱景玄虽指出了“格外逸品”这种独特绘画风格的存在,但对“格外逸品”的含义并没有较为明确的解说。较早对这一绘画风格作具体阐释的当推北宋时期的黄休复。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对“逸神妙能四品”的概念均有明确的阐述,因本文需要,兹仅摘录“逸品”条目:“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黄休复解释较为具体:“拙规矩于方圆”即朱景玄的“不拘常法”“笔简”即“三五笔而成”,“形具”即“如从绳而正矣”,“得之自然”即“掇笔而描”。这就道出了“逸格”的要义,即“简率”。“简”为“简约”,“率”为“率真”,“简约”说明弃技得道,不恋于物,“率真”说明真我的存在。主要是在创作方面,往往能不拘一格,令人耳目一新;在造形上,能够以极简的笔画描绘出物象的轮廓;在技法上强调自然而然地表现出物象的神态。
黄休复的“逸格”虽与朱景玄之“格外逸品”有着一定的联系,但并未完全相同。黄休复对“逸格”风格方面的描述无疑是符合朱景玄“格外逸品”绘画风格的。其所推举的孙位在人格上与朱景玄推为“逸品”的王墨等三人也就相似,这是二者相似的地方。但朱景玄是将“逸品”置于“画之本法”以外,两者属于不同的体系,并不与“神妙能”三品以及“格外逸品”内部作高低的比较。而黄休复则不同,他将“逸格”置于“神妙能”三品之上,居最高地位,“画之本法”与“格外逸品”已经合二为一。而“逸格”之所以能够居于“神品”之上,一方面不仅强调技法上要达到很高的高度,即“笔简形具、得之自然”,又要“莫可楷模,出于意表”,同时画家人格亦须高逸,亦是三者相互统一。
被黄休复推为“逸品”的孙位其弟子孙知微亦能得其笔法,成都人蒲永升绘画亦能得二孙本意。对二人的人格及画风,从苏轼的《书蒲永升画后》一文来看,较为接近朱景玄所说的“格外逸品”。对于这一画风,苏轼不仅表示出了很高的赞赏,且从他本人的绘画作品来看,亦是十分接近这种画风的。苏轼赞文同画竹“斯人定何人,游戏得自在。诗鸣草圣余,兼入竹三昧。时时出木石,荒怪轶象外”,称黄庭坚书法“以平等观作软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将文同的画竹与黄庭坚的书法称之为“游戏”。黄庭坚则称“东坡墨戏,水活石润,与予草书三昧,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将苏轼的画和自己的草书视为“墨戏”;甚至撰《东坡居士墨戏赋》来赞扬苏轼的“墨戏”;至于米芾更有诗云:“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黄庭坚并称米芾“在扬州游戏翰墨”。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出生不同、秉性迥异:东坡本是豁达逸群的文豪,庭坚乃是端严耿直的学士,友仁当属特立独行的才子,他们的交谊情在师友,其艺术观念一脉相承,所谓“小大才则殊,气味固相似”,共同倡导“墨戏”,即是他们心中“士人画”的典型,其特征与朱景玄“格外逸品”相近,固北宋中后期“墨戏说”,亦可视为唐代以来绘画“逸品说”的新解。
显然,所谓“率性天工、自出新意,不求形似,合于自然”的艺术追求正是苏轼、黄庭坚、米芾心目中“士人画”的特质,也恰好符合朱景玄笔下王墨、李灵省、张志和的行为,所不同的是,苏轼赋予了这种画风以新的内涵——“墨戏”。苏轼提出“墨戏”的艺术观既符合道学大家、一代文宗的身份,极力倡导文人士大夫绘画中的“士性”,又能够在政治领域和艺术抱负上达到理想的追求。苏轼的艺术观为朱景玄提出的“格外逸品”即“逸品说”提供了深厚博大的理论补充,为其后文人“逸品”获得中国传统绘画之合法、至上地位的建构,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此即“大传统”之嬗变引起艺术观的转折。
朱景玄“格外逸品”新奇、简约、自然,又与画家本身的超逸人格密不可分。正是画家人格之“逸”,导致画法之“逸”,从而出现了画风之“逸”,三者相互统一,融为一体,这也是朱景玄确立逸品的标准,三者缺一不可。人格与画品相统一,而不再简单的就画论画。唐宋书画论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发展和补充前人提出的概念,通过解析“格外逸品”的具体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后来推崇的“文人画”有重要作用,也至此开始,艺术品评的标准不再单一对画面本身进行探讨,还需要参入画家人格等背后的故事。
[1]钱钟书著.《管锥编(第四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8).
[2]胡新群,黄惇著.博士论文《唐宋绘画“逸品说”嬗变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11.
[3]周积寅编著.《中国历代画论》.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
[4]王伯敏,任道斌主编.《画学集成》.河北美术出版社,2007.
[5]潘运告主编.《宋人画评》.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
黄梦洁,福州画院 国家三级美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