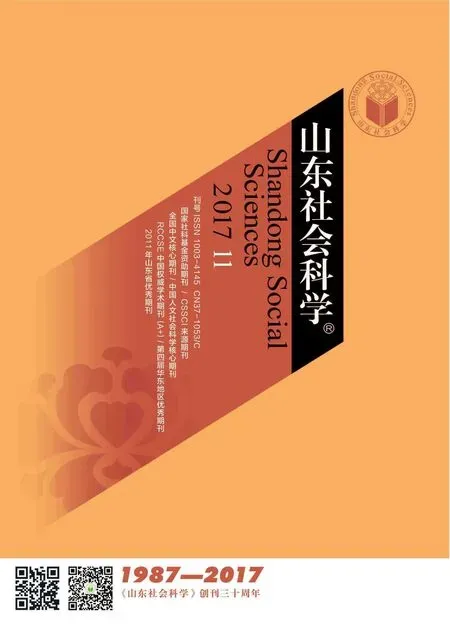绿色变革视角下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价值与局限
2017-04-02李彦文李慧明
李彦文 李慧明
(山东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002;济南大学 政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绿色变革视角下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价值与局限
李彦文 李慧明
(山东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002;济南大学 政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生态现代化”是一种解决环境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作为一种现实问题导向极强的生态政治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于促进当代经济社会的绿色变革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为当代社会绿色变革提供了一条经济技术路径,从现代化发展本身所具有的最核心要素之一——“经济技术”向度——为当代社会的绿色变革提供了较为现实的政策和手段选择。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不改变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其只能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生态改良思想,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当代社会的生态环境危机。
绿色变革;生态现代化理论;先驱国家;技术革新
一、引言
曾经有学者指出,当今时代人类面临许多重大挑战,但只有两个挑战真正可能毁灭人类:一是核大战,它可能在很短时间内使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从地球上灭绝;二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全球环境问题,它可能使地球生态系统逐渐失衡乃至崩溃,最后导致人类的毁灭。①张海滨:《环境与国际关系:全球环境问题的理性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面对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任何一种生态政治理论都试图寻找其根源,探究其表现,以期找到一条解决这种可能导致人类自身文明走向毁灭的重大灾难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西欧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即是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的一种理论解释和现实应对策略。②关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起源和发展可参见Arthur P.J. Mol and Martin Jänicke. The Origins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Theory. Arthur P.J. Mol, David A. Sonnenfeld and Gert Spaargaren. The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Reader: Environmental Refor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xon: Routledge, 2009.17-18; 李慧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内涵与核心观点》,《鄱阳湖学刊》2013年第2期。作为一种现实问题导向极强的生态政治理论,其最为鲜明的特点在于与现实社会的紧密结合,其最为核心的主张和观点是强调超越传统的那种末端治理方式,通过一种前瞻性和预防性环境政策的推动,促进技术革新,从源头上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为经济社会发展指出一条环境和经济双赢的道路和方向。③Arthur P.J. Mol, David A. Sonnenfeld and Gert Spaargaren. The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Reader: Environmental Reform in Theory and Practice[M]. Oxon: Routledge, 2009.但是,正如众多的批评者所指出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本质而言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的一种改良主义,这种改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促使当代经济社会(既包括资本主义的也包括社会主义的)走向一种可持续性,以及在一个日趋全球化的时代是否能够真正克服资本的逻辑、是否可以超越市场经济的缺陷,仍然充满诸多不确定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种相对保守的绿色变革理论,它的根本宗旨在于在不触动现存社会制度(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革新技术、增强公众的环境意识、改善国家的行政管治与市场经济手段等,以改良现代工业文明,尽可能减少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负效应。然而,在当代经济社会制度条件下,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态现代化可能是一种“最不坏”的选择,尽管这仍然是一种有局限(甚至缺陷)的社会变革理论,但比起其他激进社会变革理论或激进环境(生态)主义理论,这可能是一条能够得到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现实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促进当代经济社会的“绿化”无疑也具有重大的启示和价值,或者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不可持续性问题,可以首先经由生态现代化,“绿化”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为治本赢得时间和奠定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基于此,本文意在从绿色变革视角,对生态现代化理论进行全面系统的评析,探讨其对促进现代文明的价值及局限。本文所谓的绿色变革视角,实际上就是系统分析和探讨某一生态政治理论或环境实践运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真正促进当前经济社会的“绿化”,换句话说,就是该生态政治理论或环境实践运动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当前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促使我们的经济社会走向一种环境友好的状态,达到一种生态无害化的结果。
二、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绿色价值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经这样评价生态现代化理论:“毫无疑问,生态现代化将社会民主与生态方面的关注比过去所能设想到的还要更加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它拥有属于自己的现实成就:受到生态现代化很大影响的那些国家,在各个工业国家中还是最清洁和绿化程度最高的。”*[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渠敬东、黄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确实,正如当前德国、荷兰、丹麦以及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的环境治理现实效果所表明的,生态现代化在促进这些欧洲国家走向一条绿色发展道路方面的确功不可没。而当代中国正在实践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和实践。就促进当代经济社会走向绿色发展而言,生态现代化显然具有重大的意义。有学者已经指出:“从环境政治学的立场来看,生态现代化理论通过重新界定技术、市场、政府管治、国际竞争、可持续性等基础性要素的作用,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一种良性互动意义上的阐释。由此,它不仅在环境政治思维范式或‘意识形态’层面上为各种形式的环境改良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可以为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的成员国从而为国际社会提供环境政策创新与改革的政策指导。更为重要的是,它明确阐述了人类社会实现环境保护目标过程中工商企业界的积极性角色,从而论证了当代社会绿色变革进程中除社会动力、政治动力和文化动力之外的经济动力的重要性。”*郇庆治:《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绿色变革》,《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2期。也就是说,生态现代化为当代社会绿色变革提供了一条经济技术路径,从现代化发展本身所具有的最核心要素之一——“经济技术”向度,为当代社会的绿色变革提供了较为现实的政策和手段选择。事实上,本文认为,如果我们从一种更加广义层面上来看待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话,它不仅仅为当代社会的绿色变革提供了直接的“经济动力”,而且也为当代社会的绿色变革提供了清晰的发展方向、手段选择、政治保障与动力源泉。
1.生态现代化以技术革新为中介为当代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提供了一个现实可行的发展方向。技术和技术革新在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居于核心地位,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就指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第一位的推动作用。生态现代化强调,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促使经济社会走向“绿化”所能依凭的第一要素。传统意义上,科学技术往往被视为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个根源,所谓“科学技术失控说”就是认为各种技术如化学技术、核技术等在应用过程中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技术变迁是现代环境灾难的罪魁祸首。而生态现代化主张通过技术革新发展清洁技术,以技术去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把技术尤其是环境技术视为保护环境和改善环境的重要武器而不是“祸首”。如果我们把现代化定义为由机器或技术支撑的机械逐渐代替人力的过程,那么,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不可逆的进步过程,当代人们对机器的使用、对电力的使用,无疑极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环境。所以,技术革新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手段与方式,通过技术进步,把经济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降低,减少甚至消除经济社会活动的生态环境负面影响。因而,大力倡导技术革新,以技术改善当代经济活动的低效,提高物质资源的利用效率,打造一个更加清洁和经济的现代化社会,这无疑是一条现实可行的发展道路,也是能够得到社会大多数人认可和支持的一条发展道路。
2.生态现代化为超越当代环境治理中“末端治理”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被动应付方式提供了一条“从源头防治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道路和可供选择的政策手段。传统的环境治理方式主要是一种围堵和事后监管的方式,在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出现之后采取惩罚性措施,或者对既成事实进行修复和清洁化处理。这种方式成本高昂,效果不佳。而生态现代化一个核心主张就是“事前”预防和“过程”管理,防患于未然,在源头上采取净化措施或技术改造,尽量减少污染和其他环境负效应的发生。这种主张和理念在当前社会现实中不失为一种相对可行的环境保护方式。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德国著名学者耶内克教授在提出生态现代化理论时的主要考虑就是,比起“末端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改变,生态现代化是一条能为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可的环境保护方法。在现实意义上,这种方式方法对于促进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绿化”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它在源头上,从经济社会活动的开端和初始,就把生态环境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使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退化脱钩,甚至出现“正和”效应,这本身就是一种绿色发展道路。
3.生态现代化所要求的法治型保障政府的“政治现代化”为当代政府的身份定位和职能改革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启示,为当代社会的绿色变革提供了政治保障。生态现代化需要政治现代化为前提和基础,这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创立者耶内克反复强调的。因此,生态现代化本质而言是一个政治概念。生态环境保护无疑是当代各级政府所承担的最主要职责,但这种责任的履行手段和方式也需要革新,这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重要启示。现代化经济社会活动复杂多变,各种因素盘根错节,密切相连,政府保护环境的手段和方式必须要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生态现代化主张一种更加分散化的、灵活的、协商性的管治方式,为多层面的利益相关者提供参与决策的条件,依靠自愿行动约束企业的行为,通过公民社会的力量促进经济社会活动的“绿化”。公众参与和监督既是一种促进经济社会活动降低环境负效应的外在力量,同时也是促进社会行为、社会公众的环保理念、消费活动等方面更加“绿化”的一种内在力量。最终,在一个法治型政府的引导和带领下,各种社会力量将围绕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而走向一条绿色道路。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也将促进企业的技术革新活动和公民社会的监督行为,最终促使整个社会走向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4.生态现代化试图协调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各种力量,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契合点形成某种最为广泛的绿色变革政治力量联盟,为当代社会的绿色变革注入社会推动力量。生态现代化认为政府管治力量、工商企业以及社会消费者为核心的市场力量、社会公众参与政府环境决策以及监督企业的环保行为与政府的管治行为的社会力量之间,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可以达成某种契约,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社会力量,结成最为广泛的绿色变革“统一战线”,推动经济社会向着绿色方向前进。这种实践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社会的绿色变革解决了“依靠力量”问题,也就是激进生态主义者长期困惑的“代理人难题”*郇庆治:《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绿色变革》,《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2期。,这在当代社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当代社会尤其是政府在开展环境保护工作时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联盟战略,形成一种多中心协调合作的生态环境治理机制,*肖建华、赵运林、傅晓华:《走向多中心合作的生态环境治理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有效促进当代社会的绿色变革。
5.生态现代化强调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以培育和发展“领导型市场”为突破口,以“经济生态化”(ecologization of the economy)和“生态经济化”(economization of ecology)为当代社会的绿色变革提供了直接的动力源泉。领导型市场的培育与发展在生态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为生态理性日益彰显的当代社会提供了另外一条“理性选择”,就是一方面使经济活动更加符合生态原则,将生态原则整合进经济原则之中;另一方面也使生态原则产生经济效应,使生态化成为一种生产力,使生态产业成为当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价值。生态现代化认为,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不仅仅具有生态价值,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来看,其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化”既是生态现代化的手段,也是生态现代化的目的,从而实现经济与生态的相互协调。
三、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局限
吉登斯这样评价生态现代化理论,“生态现代化绕开了生态问题对社会民主思想所造成的一些主要挑战”,结果,这种理论“太完美了以致无法变为现实”。*A. Giddens. The third way.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57, 58.确实,生态现代化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调和”理论,它试图调和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它试图调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它试图调和资本逻辑与生态环境保护内在成本之间的冲突……但是,正如许多学者尤其是生态社会主义学者所强调的,“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就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和保证人类生存。”*[印]萨拉·萨卡、[德]布鲁诺·科恩:《生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堕落?——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陈慧、林震译,郇庆治:《当代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许多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内在的资本逻辑及其内在的逐利本性并不断增长的结构性动力,使其与生态环境保护所要求的经济社会变革变得不可调和。而生态现代化首先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它试图在不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社会制度的前提下,以技术革新、市场原则和政府的政治管治过程和手段的改变来协调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二者之间的内在矛盾性,为我们展示了一条乐观主义的经济技术改良路线,再加上外在要求的政治、文化(消费)方面的一些辅助手段。但是,正如当今世界依然在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危机所昭示的,尤其是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而国际社会依然深陷于每个国家的自身短期利益之间的博弈之中不能自拔,所有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悖论和人类智慧的缺失。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现代化只是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而做的一些手段性的改良,工具理性的色彩非常浓厚。它的乐观主义与经济技术手段事实上是在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辩护,是“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适应环境挑战并强化自身的一个战略”*Stephen Young. The Emergence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Integra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2000. 20.,在某种程度上它正在消解当代社会朝向更深层次绿色变革的社会动力,只能引起社会和环境的“浅绿”而表面性的变革。
1.生态现代化有意或无意回避了资本逻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内在结构性矛盾,试图以技术革新来协调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退化之间的深层次矛盾,有其内在的不确定性和经济技术发展的自我消解性。生态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技术决定论”,但在很程度上,它仍然把其社会绿色变革的动力、支点和手段选择都寄希望于技术革新,对技术进步和革新的估计过于乐观,似乎认为技术革新具有无限发展的潜在力量,认为“生态现代化(经济技术意义上的)的有限性是由技术的有限性所决定的。然而,这些有限性是动态的。它们能够通过科学研究(以及通过研究与发展政策)而加以延展”*[德]马丁·耶内克、克劳斯·雅各布:《全球视野下的环境管治:生态与政治现代化的新方法》,李慧明、李昕蕾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24页、25页。。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重大的生态环境难题,比如城市扩张、土壤侵蚀、生物多样性流失、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全球气候变化等,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依靠技术进步可以解决。正如耶内克本人也曾经强调指出的:“一般而言,当生态危机非常急切并需要紧急性防御措施的时候,‘生态现代化’方法往往是不可行的。”③[德]马丁·耶内克、克劳斯·雅各布:《全球视野下的环境管治:生态与政治现代化的新方法》,李慧明、李昕蕾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24页、25页。本质而言,生态现代化是一条渐进改良的社会变革之路,它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调节性和适应性,通过经济技术层面的某种改良与完善减少环境污染和环境退化,是一种治标之举。在某个阶段某些地方可能会取得良好效果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部“绿色”变革,但长远来看,或从全球范围来看,这种局部绿化很难具有可持续性,资源利用的全球性与环境污染的无国界性,最终可能会使这种局部绿化的效果被抵消或破坏。比如汽车的具体排放减少很容易就被随后日益增加的公路交通数量所抵消,这一问题就是耶内克所指出的“N型曲线困境”;再比如,1973年到1985年间,日本工业在能源及原材料的节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些成就都被这一时期高速的工业增长非常轻易地抵消掉了。④[德]马丁·耶内克、克劳斯·雅各布:《全球视野下的环境管治:生态与政治现代化的新方法》,李慧明、李昕蕾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24页、25页。所以,尽管生态现代化理论本身也强调需要超越技术革新的“生态结构性政策”,广义意义上的生态现代化也特别强调政府管治手段的变革、人们消费理念的变化以及工业的生态化重构,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生态环境危机的全球性蔓延。西方部分发达国家局部地区的“绿色”变革可能更多是生产的地区性转移和经济结构的地区性调整所致,而不是一种根本上的可持续的改观。比如污染工业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生产性工业企业在发达国家的退出,金融、信息和服务等相对清洁行业在发达国家的集聚,导致了今天西欧和北欧部分国家看来非常成功的生态现代化效果,而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性的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依然在恶化。而所有这些正是在当前市场经济逻辑在全球扩张的背景下发生的,经济全球化所激发的资本流动性的加快使资本的逐利行为更加强化而不是受到限制,原先曾经在一国或较小的地区范围内可以通过加强对生产过程的监管、引导绿色消费、强化企业的环保责任等方式实现对资本无限制逐利行为的制约,由于经济全球化而变得更加难以实现。
2.从全球经济的实践视角来看,生态现代化所强调的先驱国家与追随国家之间在环境技术和环境政策方面存在的“扩散—学习”机制往往被先驱国家和追随国家各自的经济利益动机所制约,追随国家不是主动学习先驱国家的环境政策而更多的是抵制这种政策的扩散。在经济全球化的实践过程中,先驱国家的革新性环境技术和政策往往会形成领导型市场,这种市场具有强烈的扩散动力,但这种动力主要是受经济利益驱动。在生态现代化的“扩散—学习”机制中事实上存在着三对密切相关的关系组合:“先驱国家”与“跟随国家”、“最好的实践与示范”与“学习与引进”、“领导型市场”与“外围市场”。基于这三组关系,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化的生态现代化结构,在生态现代化从一个国家或地区逐渐向外扩展的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先行者”与“跟进者”所组成的二元结构。在这种二元结构中,尽管处于其中的国家由于环境政策的调整或环境技术上的突破可能会改变在结构中的地位,结构的稳定会被不断打破,但总体而言,由于技术与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技术上的“先行者”以及率先把这种技术成功实现市场化的“领导型市场”将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其持续的优势地位,这种二元结构将有可能保持稳定。因此,这种扩散机制事实上存在一种使先驱国家保持其处于生产链高端地位固定化的趋势,而技术的扩散更多涉及知识产权或产品专利等国际规则,而使占据这些权利的国家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后发国家或追随国家基于其自身的经济利益考虑,也往往会抵制先驱国家的政策扩散,这方面表现最为典型的就是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发展中国家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于发达国家要求量化减排的政策扩散往往强烈抵制。对于仍然处于后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当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二者发生冲突与矛盾的时候,更多的情况下是把经济增长置于政策的优先地位。因此,从经济全球化的实践进程来看,经济利益与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往往主导了国家的环境政策或凌驾于全球性的环境保护之上,而使这种“扩散—学习”机制的环境效果被严重冲淡或扭曲,全球性的生态环境保护需求往往既被先驱国家的经济利益动机也被追随国家的经济竞争需求所取代。当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无论是环境技术还是环境政策的扩散也存在较为成功的实例,但总体而言,环境保护的驱动力量仍然没有超越全球性的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
3.从全球范围来看,生态现代化的乐观现实主义与全球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生态现代化实质上主要是以生态原则或者一种更符合生态化的方法给现代化框定一个方向和边界,生态现代化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改变技术进步的方向并把持续革新的强烈驱动力变成一种服务于环境的力量。但是,在现实世界,如何协调生态与现代化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普遍的难题。一般认为,假如我们承认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或增长的极限,但当代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都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标准和水平去发展的话,事实上已经超越了地球资源的承载能力,换句话说,迄今还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可能再也无法达到西方现代化的水平,但是,追求现代物质技术的进步,追求更宽敞的住所、更快捷的出行方式(汽车或速度日益提高的高速列车)和更便捷的通讯沟通方式,是当代人无法阻挡的渴望与梦想,也正是促进当代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力量,也就是说当人类的这种天性遭遇资源有限性的约束而无法实现的时候,也就陷入了一个普遍的两难,生态化与现代化就已经成为了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而难以解决。就拿当前人类遭遇的最最严峻挑战——全球气候变化难题——来说,温室气体的排放空间已经限定,或者说“碳空间”已经有限,那么,在当前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当化石燃料无论如何依然是支撑当代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根本和基石的时候,谁都想争得更大一点的“碳空间”而持续当前的经济增长,这就陷入了无法解决的两难境地,也许这正是当前面对温室气体持续增加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减排义务和责任分担问题陷入僵局,国际气候谈判举步不前的一个最深层次根源。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相对“浅绿”的生态政治理论,它对于当代社会的绿色变革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持“深绿”立场的激进生态主义还是持“红绿”立场的生态社会主义,对于当今社会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可能要比生态现代化理论更为深刻,但这些理论更多的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社会变革理论,其批判性十足但却建设性欠缺,正如摩尔和耶内克所指出的,“通过从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分析环保主义和环境危机的根源,戴维·佩珀(1984)没能针对这些根源提出一个可行的社会变革的计划。他以环境教育作为主要的战略而结束。”*Arthur P.J. Mol and Martin Jänicke. The Origins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Theory. Arthur P.J. Mol, David A. Sonnenfeld and Gert Spaargaren. The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Reader: Environmental Refor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xon: Routledge, 2009.25.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现代化理论针对现实社会的生态危机提供了许多可供选择和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尽管这些方案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再美好的理论和思想也必须经过实践变为现实。就此而言,在一个经济全球化时代,当结构性变革仍然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当生态理性仍然没有超越经济理性,当全球性生态环境保护的拐点似乎还比较遥远,当代社会的绿色变革不妨先从生态现代化方案开始,当然,我们需要牢记这绝不是最终的理想选择,我们仍然需要在绿色变革的实践中继续探索和寻找人类社会最终的可持续发展方案。
2017-07-10
李彦文,女,山东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生态现代化,生态马克思主义。
李慧明,男,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博士后,法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政治、全球气候治理与欧洲政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生态现代化与气候治理: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研究”(项目编号:14FGJ004)和山东省社科规划课题“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绿色中国梦:现实挑战与战略选择”(项目编号:13CZZJ08)的阶段性成果。
F205
A
1003-4145[2017]11-0188-05
(责任编辑:曹守新)